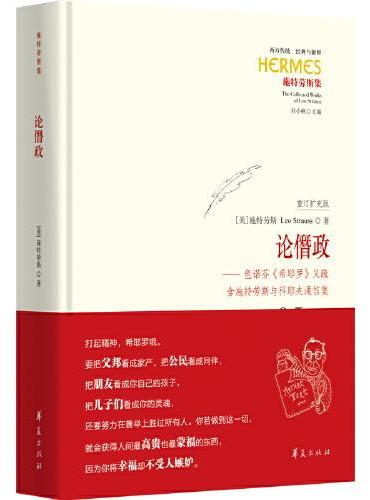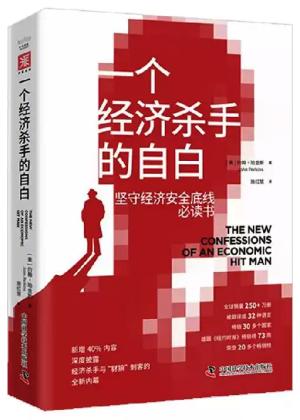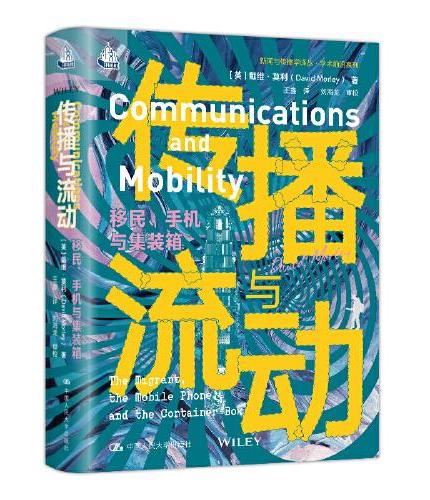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周秦之变的社会政治起源:从天子诸侯制国家到君主官僚制国家(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
》
售價:NT$
857.0

《
时刻人文·信用的承诺与风险:一个被遗忘的犹太金融传说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形成
》
售價:NT$
469.0

《
同与不同:50个中国孤独症孩子的故事
》
售價:NT$
301.0

《
开宝九年
》
售價:NT$
250.0

《
摄影构图法则:让画面从无序到有序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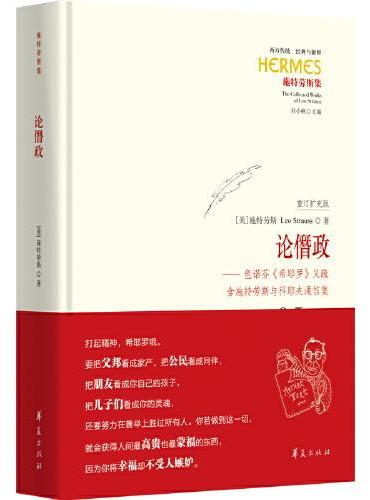
《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含施特劳斯与科耶夫通信集)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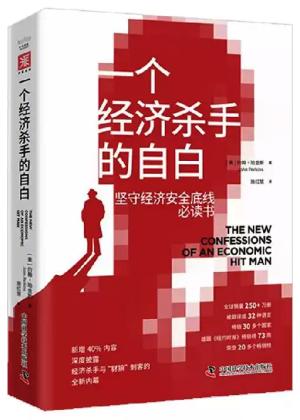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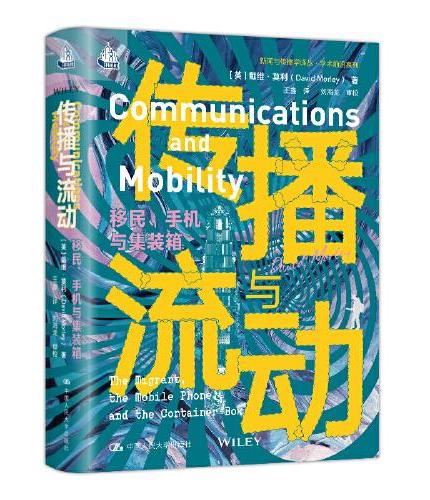
《
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用三根手指敲击的梦想,重残女孩的别样人生。
|
| 內容簡介: |
● 14岁时,她不幸患上一种被称作“不死的癌症”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被迫辍学,瘫痪在床。
● 18岁时,为了不连累家人,她选择割腕自杀,但死神没有收留她。
● 经历了死亡之后,面对年轻又黑暗的人生,她暗暗发誓要打破重重枷锁,要用自己残疾的身躯寻找一片自由的天空。
●他通过网络求职就业,自食其力,帮家里还债,供妹妹上学,筹集医疗费,还帮助病友,和他们亲如一家……她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
本书讲述了一个重残女孩自我救赎的心灵历程,她用十年的时间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了另一个高度。
|
| 關於作者: |
|
王晓晶,一个名字里有四个太阳的阳光女孩,在14岁时不幸患上一种被称作“不死的癌症”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被迫辍学,瘫痪在床。由于肌肉萎缩,她身体变形,只能靠三根手指打字。然而,她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用这仅存的力气,敲出了十几万字的书稿。并且,她通过网络求职就业,不仅自食其力,还帮家里还债,供妹妹上学,筹集医疗费……在命运面前,她没有妥协,而是通过奋斗赢得了新生,让曾经暗淡的生命如花一般绽放。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两个角落的相遇和靠近
在我难过的时候,听见一曲琴声
那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夏日午后,光线把我的房间分割得泾渭分明,窗外是明灿灿的亮到发白的阳光,照着寂静的院子和路上的行人,屋子里却幽暗又清凉,虽然有光线浅浅地飘洒着,但还是散不掉那种离世的气息。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准确地说是坐在房间里的床上,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架在床上,架在我僵硬的双臂之下。这便是我全部的生活,我已经活在这个房间里六年,六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扇小窗。前不久借钱买来了这台电脑,从此我的世界里才多了一个窗口。
我漫无目的地听歌看书,心中沮丧而失落。自从上网以来,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渺小与迷茫,许多事都与我以为的不一样,而自己也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强,两个月前我还梦想着通过电脑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出这个房间。而现在……看着自己的生活,我对自己更失望了!
我想整个下午都一个人待着,疲倦地无精打采地待着。
可忽然,有个消息在电脑的右下角闪了起来,那个熟悉的头像来自一个病友。在一个月的相处中,我们已经对彼此有了大概的了解。我知道他叫徐磊,二十二岁,东北吉林人,患的是全世界公认的无方可治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一种慢性且永久性发展的疾病,通俗地被称做“渐冻人”。
“一个人在家吗?”他问我。
“嗯,妈妈去上班了。”我简单地回复着,并不想多聊。
“下午打算怎么过呀?”他继续问。
“想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多闷啊,太封闭不好,你应该多出来透透气,多跟朋友们交流交流。”
看着屏幕上接连发过来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奇怪,甚至……特别能说。虽然心里也有一些感动,但还是提不起精神,摆脱不掉心中积蓄的挫败感。我只好漫不经心地回复着他,他说五句我回一句的。
也许,是他看出了我的低落,看出了我并不想说话,竟忽然说:“晶晶,我吹口琴给你听吧,怎么样?想听吗?”
“好啊,洗耳恭听!”他的提议一下子提起了我的兴致,开始有小小的兴奋在心中升起。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一个人为我演奏过,或是歌唱过,而现在竟有一个朋友要给我吹口琴了!而且,在这样的时刻里,我真的只想听一些音乐,安静柔和的音乐,他简直像能读心似的,一下击中了我心底的需要。
打开语音,他那边已经准备完毕,琴声随即流淌开来。
口琴的声音是静谧的,空灵而又质朴,就那么一丝一缕飘散在耳边,缱绻盘绕,整颗心都随之沉静下来。仿佛生命暂时停止了,可以停下来看看一路走来的时光,也可以抛却烦恼安享这一刻的悠扬。
我静静听着,把头靠在了床背上。我听出他吹的曲子是《送别》,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电脑的播放器里是陈绮贞版本的,现在第一次听到口琴版的,感觉非常不同,新鲜中依然吐露馨香。
而此时,窗外的阳光也不知不觉照了进来,穿透窗子斜斜地洒在了我的床前。屋子里一下子变得明亮极了,所有的物体都透出镜子一样的光芒。我的眼睛里开始有些反光,索性闭上眼睛,专注地听。
温暖,阳光照耀在脸庞是温暖的。
温暖,琴声流淌在耳边是温暖的。
温暖,在阳光下闭上的眼睛是温暖的,整个视线都是红色,暖融融清纯纯的红色,像四月的花海,像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吹起的微风。
这一刻的世界,简单极了,美好极了!之前所有笼罩在心中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都在丝丝缕缕的琴声中化为清风,化为明月,随着流淌的琴音飘到屋顶,飘到田野……
我不禁想,这么美好的声音是如何吹出来的呢?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只有几根手指可以动了,那又是如何拿得起口琴的呢?在这样巨大的病痛和死亡威胁中,为什么还可以如此安详如此温暖?
我太好奇这声音那端的情景了,我忍不住,想要走近他的生命,去一探究竟。
从耳朵到眼睛的距离
一个月后,我心中的疑问才终于被解开。
那天,我去向他请教学习口琴的方法,想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能不能吹,结果他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学,马上发来视频给我讲解。
视频里,他的脸上挂满了笑,略带腼腆,而又温文尔雅。他的脸色看起来苍白,像是很久都没有见过阳光了,而他温和平淡的眼神就像是夜晚的月光,淡泊地闪烁在苍白的脸庞上。整个人有种生活在夜晚的感觉,由内而外都呈现出宁静的气息。
“你能晒到太阳吗?”我问他。
“晒太阳啊,我都多少年没晒过太阳了,自从搬进楼房好像就没再晒过了。”他的语气里充满向往。
“那阳光好的时候不能到阳台上晒晒吗?”我觉得常年见不到阳光是很糟糕的事情。
“不能,我坐不住,再说我家阳台不是朝阳的。”他依旧缓缓地说。
“你那儿的天气是多云吧?”我看见他的脸总是一边明亮一边暗淡的,浅浅的光线飘忽不定,他的脸也跟着变幻莫测起来。
“是啊!”他爽朗地笑了,笑起来嘴巴大大的,眼睛弯弯的,很尽情。我不禁想,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笑的呀,要是每天都能生活在这样的情绪里,该有多么快乐!
这时,他妈妈把口琴拿了过来,那是一个绿色和银色相间的二十四孔口琴,随着口琴拿来的,还有一个金属的小支架。没等我问,他就给我介绍起来:“这是我爸给做的口琴架子,是我自己设计的,把口琴放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吹了。”
我观察着那个小支架,那是一个十来厘米高的非常简易的小工具,把支架放在他的面前,高度刚好处于他嘴部的位置,然后把口琴放在支架的托柄上,他就可以刚好碰到口琴的琴孔。原来他是这样吹奏的!我心中的疑惑在一点一点解开。
在给我讲了一些相关知识后,他选了一首曲子吹给我听,然后,一切就这么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他是一个真正的演奏者。
他在那一隅坐着,不,准确地说应该是趴着,整个上身前倾趴在床上的小桌子上,变形的脊柱导致他整个身体看起来歪歪扭扭,左肩膀矮矮地低下去,右肩膀尖尖地耸起来,整个身体都处于一种随时都要倾倒的姿势中。他就那样歪歪扭扭地“坐”着,坐在他的银色口琴面前。他让妈妈帮他把胳膊放在支架的底座上,压在那里来固定他的口琴。他的双手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显眼,演奏该是从来都离不开手的,然而他的手却以一种痛苦的姿势顶在桌子上,手指弯曲着,每一根都干瘦细长,没有健康的肉,只剩苍白的皮和骨。
我没有问他疼不疼,从他的脸上他的眼神里他的琴声里都只感受到安详。他是那么专注而投入,只靠着头部的左右移动,好听的曲子便随之流淌,这种移动是细微的,口琴的长度也只有不到二十厘米,这细微的移动,便是他仅剩的自由。
可当我看着他,看着他的身体全都不能动,看着他偶尔流露出的气息不够,我不觉得他是一个重病的人,一点儿也不觉得沉重!我会不自觉地嘴角挂着笑,欣赏眼前这美好的情景。
我第一次觉得,生命竟是如此高贵!不管处于怎样的废墟中,都不能阻挡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在这份热爱面前,病痛、死亡都显得弱小起来,在他无比安详的眼神中,他所承受的一切灾难都变成了淡化的背景,仿佛他就坐在一朵云彩上,安然地吹着一把口琴,天地风月,就此旖旎。
还有什么能禁锢一颗自由的心。
还有什么能夺走生命最朴素最纯真的高贵。
哪怕有一天,我们一无所有,连仅仅能动的一根手指也失去了,哪怕有一天,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再也触碰不到我们的所爱,也仍可倾其所有,换得满心温暖。
我想,从此以后,我都再也忘不掉今天看见的徐磊。
我想,从此以后,我都将倍加珍惜这个“月光”一样的——朋友。
左耳朵,右耳朵
阴天,却不下雨。
绵延的潮湿压迫我每一寸的身体,最怕这种天气,整个天阴沉地很低很低,整个空气都弥漫着潮潮的湿热,胸闷,发烧,身上痛。
躺在被子里,想昏昏沉沉睡上一会儿,好让睡眠来修复这一身的疲弱,可一旁的声音总是让我无法入睡。“你们小点声儿?我睡会儿?”“OK。”露儿和她的同学立马压低了声音,继续玩她们的电脑。
迷迷糊糊刚觉进入梦乡,一阵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笨重地把胳膊伸到被子外,拿起电话勉强递到耳朵边。
“喂?”
“是我,你在睡觉吗?我是不是吵醒你了?”电话那端传来徐磊熟悉的声音,听起来气息有些急促。
“没事儿,还没睡着呢,你怎么啦?”
“家里没人,都出去了,我一个多小时没翻身了……”
经过交谈,我了解到他的处境:平时他需要每隔一个小时就至少翻一次身,因为身体瘦得皮包骨头怎么睡都会压得疼,可今天家人有事出门,已经一个半小时没有人给他翻身了。一个半小时保持一个姿势,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甚至会带来危险。最令人着急的是,不知道他的家人多久会回来,他又完全不能和父母及其他人联系上,手机里没有通信录也没有相关通话记录,而他脑海里唯一记得的号码,就只有我的。这不奇怪,平日里跟他用电话联络的基本也只有我了。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能坚持多久?”
“麻木,酸,胀,感觉骨头压着骨头似的,就是不能动啊!”他的声音很虚弱,听得我眉头紧皱。我也经常会有类似的经验,冻得半死自己又一点招没有,坐在竹椅子上硌得骨头哇哇直疼还得继续等人回来,抱着电脑上网胳膊架在小桌子上一架就是好几个小时,身上许多关节都是疼的,但就是没办法,搬不动一个小小的桌子,够不着脚边的被子,撑不起椅子里的双腿。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有足够的能力把残疾人变成弱者。相比之下,我遇到的困难要比徐磊少多了,至少遇到这种情况,我还可以动动身体,改变一下压迫的部位,但他不能,他一点儿都动不了。
“你别急,阿姨平时出去不都是很快就回来的嘛,现在都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应该快回来了!”我只好先说些乐观的话,好让时间尽量多过去点儿。
“唉,你说我这脑子,怎么连一个电话号码也想不起来呢,这要是一直没人回来,我就撑不住了。我心脏不行,一难受就喘不过来气儿……”
想起他的身体状况,我就着急,他几乎三天两头需要用救心丸来维持生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有十来天身体舒服就是恩赐,不光是心脏不好、没有肌肉,而是整个身体的器官都不好,都在衰竭。
“这不还有我呢嘛,还好你这电话还能打出来,咱俩大活人还能没有办法呀!”嘴上这么说,我心里是真担心,现在知道他情况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又离他十万八千里,想了一圈也想不到跟他家人联系的方法,实在不行只能打110了。
“呵呵,给你打这个电话也费了半天劲儿呢,手机在枕头边,我够不着,是用头先慢慢一点一点够过来,再用嘴咬过来的。”他说这段话,语速很慢,说几个字就得停顿一下,气息之间明显透着辛苦和虚弱,还好,他还能笑,尽管笑得很轻,也让我安心不少。
我的脑海里已经清清楚楚浮现出电话那端的画面了,是怎样举步维艰地打来这个电话,是如何守着一个电话忍着难熬的分分秒秒……一时间,心生酸楚。
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对于他的体力和手机电量,这么耗下去都不是办法。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先挂掉电话,然后我每隔十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以确定他的状况。于是,开始了和时间的拉锯战。
“有人回来吗?”
“没有。”
“我给你出个谜语,你猜我是左手拿着电话还是右手拿着?”
“右手。”
“错,是左手。再猜我把电话放在左耳朵边还是右耳朵边?”
“左耳朵。”
“错,是右耳朵。”
……
十分钟后。
“还没回来吗?”
“没…有。”
“再坚持一会儿吧,下次打时还没人回来就打110吧?”
“那还不如直接打120呢!”
“对哦,那打110好还是120好呢?”
“算了吧,叫人来干吗呀?就为不能翻身啊!怎么说呀!”
“要是没办法就只能打啦,我们是真的需要帮助嘛!”
……
时间是不是停止了
如此打了五六次,还是没有人回来。时间已经慢吞吞地过去一个半小时,他也已经有三个小时没有翻身了,对他的身体这已经是个极限。
“你还好吗?”我心里火急火燎。
耳边传来“呼呼”的喘气声音,透过电话这声音显得特别大,不知道是被扩散了数倍还是他喘得真的如此厉害,反正听起来是糟透了!
“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他极其虚弱地说。
“不行,咱求助吧,我现在就打电话。”我是真急了,一刻也等不了了,眼睁睁在电话这头听着,听着他的疼痛,听着他的不支,听着他汗水直流的呼吸,我急,急得手足无措。
“不要,我还能坚持。”他虚弱而坚定地拒绝了我的提议。我理解他的不愿意,这是一种顽固的自尊,宁可自己再难受都不愿求助他人,尤其是诸如翻身、吃饭、上厕所这类事,就是再难再苦也都是自己的事,假手于人总是尴尬和抗拒的。此如我,这几年也都只让妈妈和妹妹照顾,没人在家的时候,就是自己再冷再饿再难受都不会求助亲戚。何况,是为了不能翻身而求助紧急部门呢。这确实有些尴尬,可我想不出别的办法,而又必须负责他的生命安全,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状况,并且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坚持再等一会儿,我只好同意,可电话那头不停传来喘气声和痛苦的呻吟声,这让我揪心不已,我慌张地想着,该怎么帮他呢?有什么办法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呢?
“我给你唱歌吧?”我说。
“好啊!我想听。”他的声音终于有了几分喜悦。
“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唱歌的,长这么大都没唱过,我这可是为你献出首唱啊,跑调了你不许笑。”
“好。”
我挣扎了几番,鼓足了勇气,憋住心里不停乱敲的小鼓,终于要开口了。可是,第一个字的声音就是出不来,不知道多少年没唱过歌了,平时妈妈老说我总是听歌为什么不能跟着唱唱?其实我有唱的,只在一个人的时候。现在火烧眉毛了,再不行也要唱,我狠了狠心,豁出去了!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这是我唯一歌词记得比较清楚的歌了,常常一个人在窗台下练习站立时就喜欢很文艺范儿地唱这首《爱的代价》。
电话那端竟异常安静,他没有笑,我就且当自己唱得还行,硬着头皮唱了一段,然后不出例外忘词了,眼珠一斜,把露儿她们勾过来,电话交到她们手上,示意她们继续。露儿的同学倒是活泼得很,从从容容唱了一首《擦肩而过》。两个姑娘唱得真诚,唱得温暖,她们知道电话那头是一个受困的急切的人,她们发自内心想用歌声来缓解对方一丝丝的痛苦。
我揪着的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稍稍缓解一些他的痛苦,至少这短暂的时间里,可以不光有痛苦,还有美好。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美好的力量是一定大于痛苦的,我能感受到此刻共通的感受和诉求,那是自眉眼流露,自心间传出,自声音播散,自宁静回应的一种本真的温暖。而这温暖,能让一个人在身体承受强烈痛苦的时候,保持内心不苦。
几分钟后,他家里终于有人回去,我挂掉电话,总算能把又酸又疼的胳膊放下来了。看看时间,从他打来电话整整过去两个半小时,他第一次长达四个小时没有翻身,我也第一次在如此焦急的状况下陪伴他人,好在,结果平安,一切无恙。
只是挂掉电话,才觉得肩膀和肘关节都疼得厉害,我怕发烧,只要体温稍稍升高身上就乱七八糟地疼,轻轻地,慢慢地把胳膊放进被子里,喜欢把手放在温暖的肚子上,安心依偎。
其实,我是很宠爱自己的。
离离楼上草
目光,转向窗外。
一束蓝色布质窗帘薄薄挂在窗边,黄昏的天色让其昏暗,看不清楚上面白色的花。只有一旁窄窄的玻璃窗子,泛着透亮透亮的光线,映衬着窗外灰白的天空。从床上望过去,天空还没有一块玻璃大,远远地模糊地挂着几层云彩。
我的目光最终落在天空下的那一角墙壁,青灰色的水泥墙,上面空无一物。可我久久地望着,勾勒着,试图还原出千里之外的另一个角落里,另一个人的视野。
那是几个月前,徐磊第一次跟我说起,那惊喜的语气像是发生了天大的好事!
“丫头,你知道我每天能看见什么吗?”
“天花板。”
“不,是小草!就长在对面,我每天躺在床上刚好能从窗户看见,真是太奇怪了,楼顶怎么会长出草呢?!我觉得可能是风把草籽刮过来的,然后就靠着水泥砖缝里的一点点土活下来的。”他略略停顿,仿佛若有所思,然后感慨一句,“太难得了!”
“那楼离你很远吧?你能看清吗?”
“相当清楚了,顶多二十米,现在还看不出是什么草呢,等再长大些就知道了。”他兴奋的语气就像是在等一个小宝贝长大,等长大了才能知道他她成为什么样的人。
此后的日子里,他便常常跟我说起这几棵小草。四月,他说小草长高了,在微风中绿油油地摆动着,看着都能闻到那青青的植物香。五月,他说小草好像结穗了,像麦子又像稻谷一样的穗子,可是,北方是没有稻谷的,麦穗也不会这样硕大。六月,他说昨夜下了好大的暴雨,连树枝都被狂风折断了,不知道那些小草能不能幸存。
季节就在他温柔的视线里变化流转着,窗外的小草生长着,他的心也跟着生长着。看着他深深的怜爱和凝望,我心怀感动却又不以为然。那不过是几棵平凡的植物,天地之间遍地都是,并无别致,更并无出众,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它们长在了他的窗外,长在了他唯一能看见的天空下。
这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悲悯呢?从窗里孤寂的一隅到窗外渺小的一角,从雨天里深切的担忧到微风里惬意的相伴,我想,他一定是把所有的寄托都倾注在了小草的身上。我从来没想过,这份寄托竟然会与自己有关,直到我点开他的博客,看他更新的日记:
“这几棵草,在我心里,绝不仅仅是草那么简单,因为这草出现得太及时了,在我失落彷徨的时候,它的出现,让我不再感到孤独,看着这棵草,看着它那随风飘摇的纤细身姿,不知不觉被它的那一份气质所感染。不由得产生一种悲伤,这种悲伤是种心疼,怜惜,我好想改变这棵草的生存环境,我想为它创造一片属于它的天空,我想让它快乐幸福,我想为它创造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我没能力做到,脑子里总是冒出来一些如果,如果我可以……”
看着长长的一篇文章,我的眼睛开始由平静变得深沉,而后温暖,湿热。
原来,在千里之外的视线里,竟然一直有自己的存在。
这一刻,我完全理解了他的“执著”,他的“多愁善感”,他随着小草的枯荣而悲喜的心绪。心中感动与勇气滋生开来,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要更加竭力生活,拥抱前方的所有艰辛与苦难。也许,只有穿越过无涯的苦难,我的生命才能最终挺立在阳光下,那时,所有爱我的人才会安心,才会欣慰。
这么想着,我静静关掉了网页,怀着无尽的勇气,把目光转向了窗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