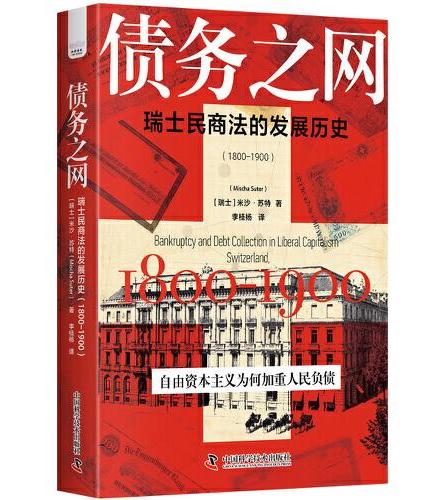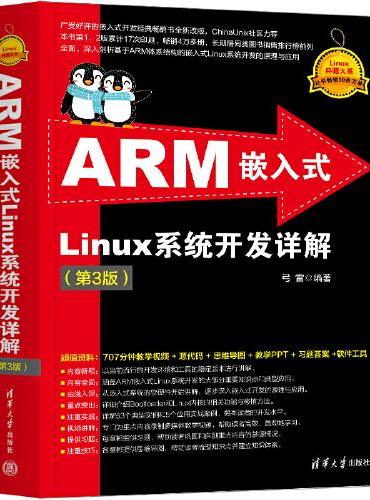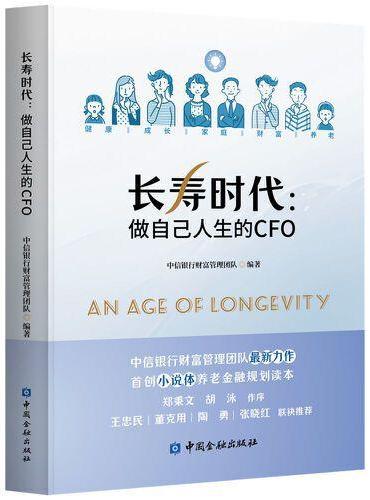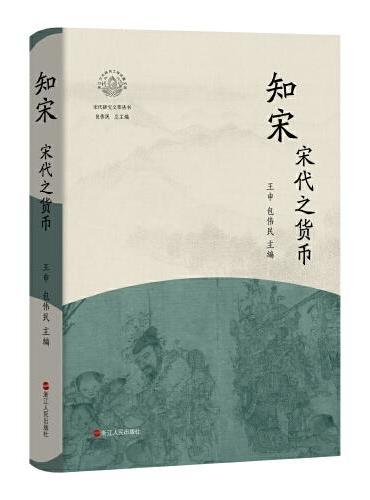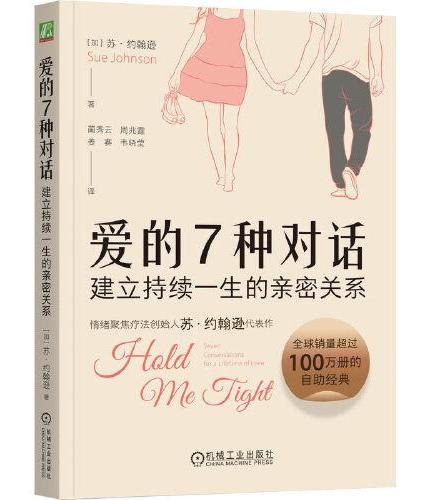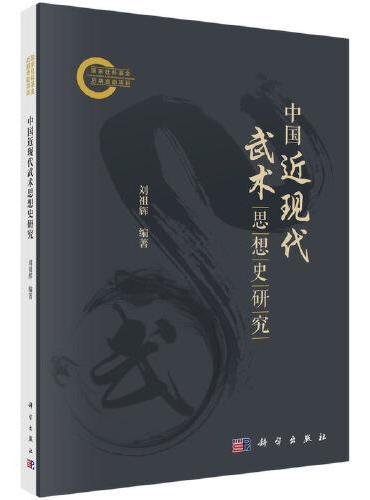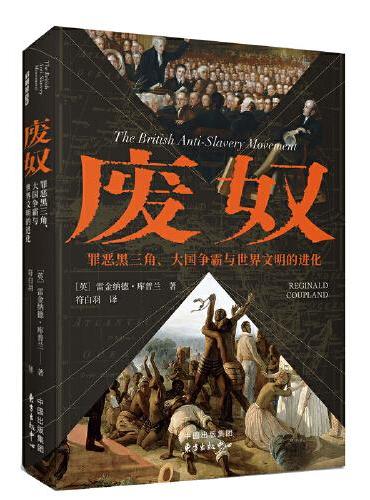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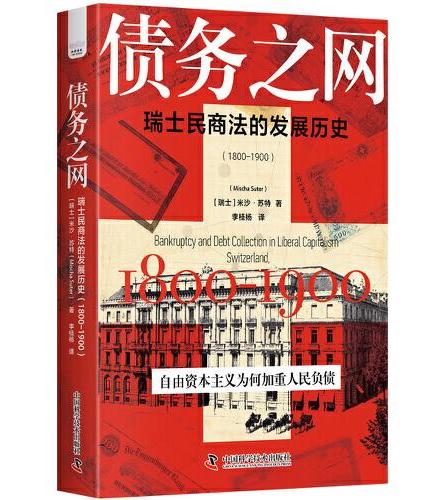
《
债务之网:瑞士民商法的发展历史(1800-1900)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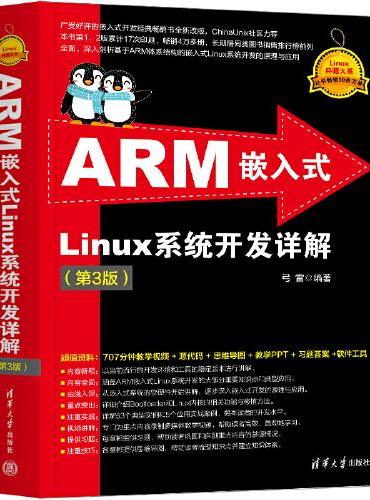
《
ARM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详解(第3版)
》
售價:NT$
5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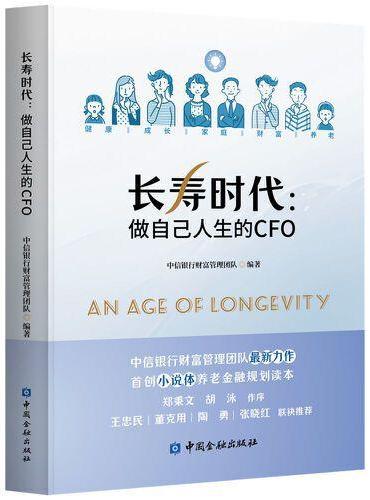
《
长寿时代:做自己人生的CFO
》
售價:NT$
310.0

《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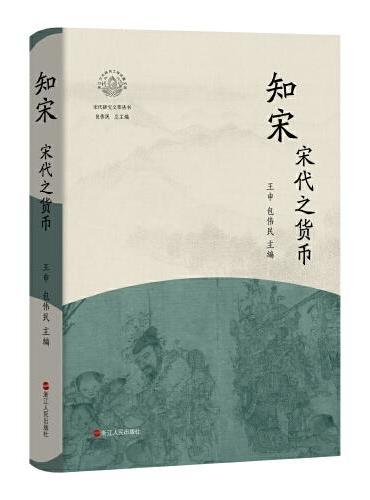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货币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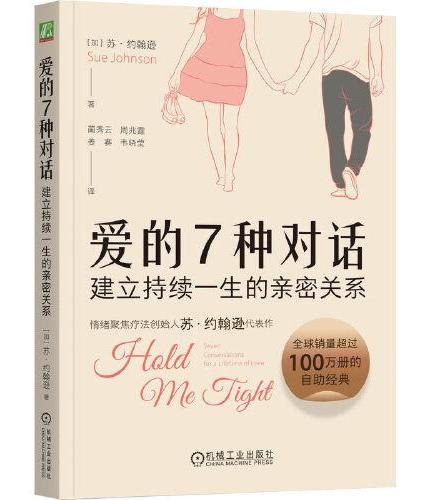
《
爱的7种对话:建立持续一生的亲密关系 (加)苏·约翰逊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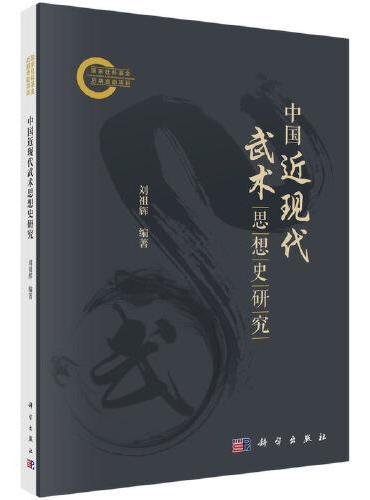
《
中国近现代武术思想史研究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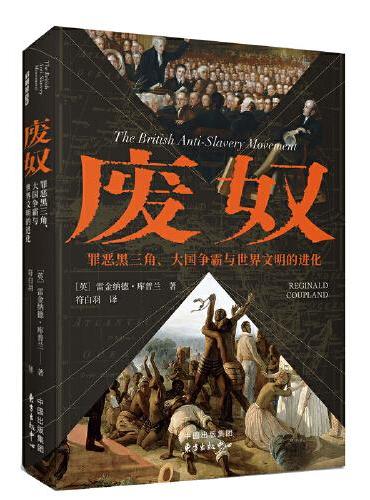
《
废奴
》
售價:NT$
350.0
|
| 編輯推薦: |
知名女性作家赵玫继《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之后力作典藏
一部现代爱情婚姻史。关及围城中人的背叛、对抗中的挣扎,她们或是妻子,或是情人,或是觊觎者,或兼而有之。谁,能躲过现代社会的婚姻危机暗潮?谁,敢说自己始终忠于相濡以沫的人?
当欲望吞噬了她们的灵魂……
有时候婚姻就如同疾病。一个从患病到死亡的可怕过程。有的如心脏骤停般当场毙命,但更多的却要经历难以承受却又无以避免的磨难。那绵延不绝丝丝缕缕却足以致命的伤痛。*终不得不终结于命数耗尽。总之,各种各样的终结。分手契约就等于是,病危或死亡通知书。
――赵玫
|
| 內容簡介: |
|
《六宫粉黛》是一个关于家庭和爱情的故事。仿佛不可能在恋情上,产生交集模糊地带的几位男女,分别意外地成为闺蜜或者熟人的爱情掠夺者。女诗人发现了丈夫的外遇,于是勾引别人的丈夫进行报复。女诗人的丈夫在大学任教,海归女博士激起了他争取世俗享受的斗志,并与其领导――海归女博士产生了激情和婚外情。女博士之母是杂志主编,与专栏作家激情燃烧,女编务――女主编的姐姐洞悉了这一切,并用小说反映了这一切,书畅销不衰,引发轩然大波和法律诉讼,女编务最终以跳楼维护了毕生追求的尊严。
|
| 關於作者: |
赵玫,满族,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职于天津市作家协会。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已出版《朗园》、《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八月末》、《林花谢了春红》、《铜雀春深》等长篇小说,《岁月如歌》、《我的灵魂不起舞》、《寻找伊索尔德》等中短篇小说集,《从这里到永恒》、《欲望旅程》、《左岸左岸》、《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博物馆书》等散文随笔集,《赵玫文集》、《赵玫作品集》、《阮玲玉》等电视剧本,计900余万字。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长篇小说《漫随流水》获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
|
| 內容試閱:
|
1
蓼蓝不确定。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老于世故。总之一种迷茫的感觉。湖光山色之间的那种,天高云淡。她走神了。
坐在那里,在觥筹交错中,却不知应该想到什么。
一次不能拒绝的聚会。不关乎友情。专栏作家儿子的婚礼。而她并不讨厌那个写作的男人。所以不得不来,还要不得不做出欢天喜地的样子。但总是被牵扯着,那不确定的,纯真。
婚礼仪式是《霓裳》杂志社一手操办的。被安排在郊外湖畔的草坡上。如镜的湖水,伴随着,青草的香。于是淡淡的典雅。
在大自然中构建如此婚姻的殿堂,大概也唯有《霓裳》愿意无偿地帮忙。鲜花布满目光所能及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可看到新人横着竖着的各种巨型照片。幽深处飘来悠远的《婚礼进行曲》。很好的乐曲,却仿佛很隔膜。完全从好莱坞电影中拷贝过来的婚礼程序。包括新娘新郎的服饰,交换戒指乃至当众接吻。只是缺少了神父或牧师。也没有关于婚姻的神圣承诺。更没有中式的掀开盖头后刹那间激动人心的场面。
或者因为,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成年处女了。
人们在约定的时刻翩然而至。沐浴着午后明媚的阳光。
人人都闻到了青草的清香。那也是婚礼策划者的创意。大概也只有婚礼的相关者才在意这浅薄而繁缛的程序。并没有人真的关心那对新人的婚礼是不是顺利。人们一走进花园就端起了高脚杯,在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中间往来穿梭。
《霓裳》的工作人员在女主编的带领下悉数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摄影师那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模特老婆。据说这女人曾一度罹患忧郁症,及至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模特出身的女人看上去依旧很美,那种矜持的高傲的冷的美。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她的两腮很宽,眼睛也离得很远,总之别一种滋味。她始终不笑,也很少讲话,之前从未来过编辑部,所以大家和她不熟悉。
此刻的蓼蓝形单影只。倘若她是独身女人,或者也不会觉得如此孤独。她邀请过自己的丈夫,那个落拓的男人,当然他才华横溢。生存的态度和一个人是否优秀毫无关系,至少蓼蓝是这样想的。或者他故意做出落拓的样子,为了让蓼蓝获得某种平衡?是的,他们终于共同地不思进取了,尽管他们还那么年轻。不是刻意而为,而是,一种几近于本能的选择。
不是谁在迁就谁,而是共同的愿望,就缔造了,他们都觉得很舒服并且本该如此的家庭生活。
是的,她邀请她丈夫了,或者说,专栏作家夫妇邀请她丈夫了。她丈夫也看到邀请函了。上边明明白白地写着“贤伉俪”这几个庸俗至极的字眼儿,怎么会出自那位锋芒毕露的作家之手?或者就因为这几个恶俗的文字,她丈夫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他当然看出了蓼蓝那些微的不快,但他说我们不是有约在先吗?我认识他们吗?你的那些同事?我了解他们吗?更不要说,他们是否了解我。不是早就约定过吗,我们只是,各自身后的影子。我们相爱,就足够了。我的同事或你的同事,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相干?
于是蓼蓝独自前往。和蓼蓝一样独自前往的还有那个女编务。不过,编务本人从来不喜欢编务的称呼,总是强调她是女主编的女秘书。其实这女人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却因为主编的执意挽留而一直留任。女编务独自前来是因为她一直独身。她从没有结过婚,不知道是不是就意味了从未有过性爱。这天她穿了一身粉红色的华丽套装,手臂上挽着一只时尚的香奈儿小包。一看便知是赝品,却表明了她对奢侈品向往的姿态。她用了很浓烈的香水,那种缺乏分寸感的喧宾夺主。不过蓼蓝站在她身边并不反感,因为她喜欢那种香水的味道。
穿梭往来的高脚杯不停地发出碰撞的声音。于是人们也开始醉眼迷离。蓼蓝对这冗长的难以承受的婚礼失去了耐性,这或许就是她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婚姻一个婚礼的原因,也是人生中最值得她骄傲的一次决定。
恍惚间她已经远离了婚礼现场。甚至连麦克风发出的声音都变得依稀。斜阳。是的,这湖畔,正在反射出黄昏的色泽。
那姗姗来迟的,却又不能不来的,那凄凄惶惶。为什么,老一辈简朴而实在的婚礼反而更令人神往?只要两套被褥搬到一起,两张板床拼在一处,便可儿孙满堂了。就像,她和她的丈夫。没有那些繁文缛节,亦没有所谓的仪式。仪式就那么重要就那么令人信服吗?她记得她和她丈夫一拿到结婚证就后悔了。一张纸,一张纸又能约束什么呢,他们何苦前来索取?
远远地,女主编和那个男人沿湖岸走来。在林间,影影绰绰地,是的,他们手牵着手。手牵着手就足矣了。毕竟,那边,人们似乎正在为新郎新娘的当众接吻而欢呼。如此性爱的举动,如果在那一刻,真的撩拨了他们的性欲?
在密林中,他们或许以为这里不会有人,至少,不会有编辑部的人。于是接吻,在他们之间,就不会像新郎新娘那般是做给公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两个身体的需要了。当然,在密林中,他们不知道有蓼蓝。而此刻蓼蓝所思所想的,也并不是他们的吻,而是,他们的方式。
他们手牵着手,在树影里,斜阳中,那般的美好。两个身影,或并排或重叠,影影绰绰的,就像是湖边的诗。蓼蓝可以迎上去,亦可以,择路而避,反正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至少在编辑部。他们并不特别掩饰彼此的关系。但蓼蓝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不管他们是否已经看到了她。
重新回到人群中,蓼蓝几乎谁都不认识。于是独自坐在餐桌前。没有圆桌,就像是没有大红的盖头。长长的餐桌是由无数方桌连接而成的。人们对坐,就像是意大利人的家庭聚会。
看得见仪式中飘来飘去的白色婚纱。亦能够远远瞟见那个粉红色身影。她觉得她是在不知深浅地搔首弄姿。
长桌前空空荡荡。人们正耽溺于相互的交往中。服务员不断摆上各种菜肴,那断然不会美味的食物。人们为什么迟迟不想入席,还有什么说不完的话?于是蓼蓝想到了诗歌,空谷幽兰,那是策兰写给巴赫曼的爱。
蓼蓝在心里默诵着,你这焚烧的风。寂静曾飞在我的前头;第二次实在的生命……
便立刻觉得不再无聊,因为她心中有了策兰,和他们的爱情。在漫长的生命中爱过一次又一次。曾经失落的,而失落也许就是拥有。但是她为什么不再写诗?蓼蓝问自己。而她的男人就是在诗中找到她的。又为什么,要在颓废中失落?床上流泻的那些激情,甚至,连痛苦都感受不到……
她觉出身边有人走过。那个摄影师迷人的妻子。她不声不响地坐在蓼蓝身边,又似乎并不想和她搭讪。于是她们就默默地坐着。那个仿佛不胜其苦的娇弱女人,不屑地说了一句“无聊”。然后她们相视一笑,紧接着又回到各自的沉默中。
终于等到人们坐回到餐桌前。唯独女编务意犹未尽,就仿佛那是她自己的婚礼。大家左顾右盼,相互寒暄。这一桌全是《霓裳》的人,就仿佛编辑部换了一个办公的场所。
2
她说她就站在监护室门外。等待着那个最后的时刻。她不知那时辰何时到来。她和他只隔着一层玻璃门。她这样说的时候满目苍凉,有一种难抑的亢奋和某种期待。
这一刻她就坐在主编办公桌的对面。她看到了窗外折射的浅灰色暗影。那是一扇很大的玻璃窗,稍稍走近便会有一种从身体深处油然而生的心惊肉跳。
女主编怀着同情地倾听。她本来是要她汇报下一期刊物的选题。女主编一丝不苟的发型,略施粉黛,她总是戴一串优雅的珍珠项链,以及,让人些微闻到的某种香氛。她信任眼前这个曾满怀激情的女编辑,尽管,她觉得她有时会表现出某种言过其实的夸张。
她说,她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死亡。而婚姻的崩溃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同人的死亡。她说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就等于是,婚姻即将死亡的通知书。大同小异的。没什么两样。婚姻就如同疾病。
然后,她缄默。
女主编想重谈关于杂志的话题。但弥漫于对方身心的绝望感却让她难以启齿。她不确定这个女人的抱怨来自于她的生活,还是她的想象?她一直觉得她就像一段段总是充满幽怨的诗行。是的,是的,下一期你打算……
要知道婚姻就像疾病,也有一个从患病到最终死亡的渐进过程。有的像风驰电掣般即刻毙命,“咯噔”一下子彻底结束;而有的则要经历诸多难以忍受又不得不忍受的,漫长磨难。
女主编慢慢听出了女编辑的思路,她觉得她也许并不是在抱怨自己的生活,而是在阐述她对于婚姻的思考。她于是立刻首肯了女编辑的想法,并顺着她的思路,或者,这一期我们就重点探讨生病的婚姻?
那绵延不绝的丝丝缕缕的却足以致命的,伤痛,就如同您窗外那片浅灰色的天空,最终会因生命耗尽……
女编辑的诉说突然被电话铃打断,她竟然蓦地抖动了一下,仿佛被惊吓,或者,她对她的话题太投入。
很自然地,主编可以随时打断下属。她拿起电话,向对面的女人摆了摆手,意思可能是不要讲话。哦,她的语气变得柔和,脸上甚至现出微笑。哦,我忘了,你要的那本英文书?就在我这儿。好的,一会儿让司机给你送过去。吃过早饭了吗?冰箱里有果汁……
然后她把目光移向女编辑,我女儿,你接着说。
最终因生命耗尽而不得不终止,总之,各种各样的死法,但大多要经历那深入骨髓的疼痛与折磨,于是死亡的时候已形容枯槁。
病人还是婚姻?
我是说,有病的婚姻。
可是,女主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你确实看到了什么,还是仅仅是感觉?
我不确定,正因为不确定才会备受折磨。
单单是感觉就能如此冲动?
电话铃再度响起。意味着,这里也许根本不是谈论生死的地方。
你到了?那上来吧。女主编无需任何歉疚地站起来。那是天经地义地,她是这里的主宰。于是,女编辑一如任人宰割的羔羊般也随之起身。她知道今天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女主编不再有听她诉说的兴致。
女编辑走出主编宽阔的房间。她披散的头发让她显得格外地苍白。她坐进办公大厅被切割的那个属于她自己的小格子里。抬头,就看到了对面女人投来的不怀好意的目光。是的,她不喜欢总是被她莫名其妙地凝视。她讨厌那个号称做了几十年编务的老女人。她知道这个女人不喜欢自己,而她也从未认真地对待过她。她觉得她就像一团无所不在的幽灵,又像是一个不肯退出舞台的老舞女。她每每看到她都会想到《蝴蝶梦》中的那个女管家。永远威严的目光,凛然的气势。她身上唯一令人认可的,就是她对主子的忠诚,这也和《蝴蝶梦》的女管家如出一辙。为此她不遗余力,舍生忘死,甚而烧了庄园,烧死了她自己。
紧接着,大厅的玻璃门被推开,那个不修边幅的男人走进来。俨然皇帝般地气宇轩昂,仿佛这地方是他的王国。他当然十分友好地和编辑部各色人等打着招呼,甚至不惜在一些小格前停下来,交谈几句。总之他一副名士风流的架势,在不耻下问中尽显尊者风范。是的,他当然就是尊者,杂志中所有那些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都出自他手,在某种意义上,他那些炮火硝烟的文章也扩大了杂志的销售。
他是女主编几年前在某小报上偶然发现的作者。他的名字所以只能出现在某小报上,是因为他的文字太具鲁迅遗风了。于是女主编“别有用心”地接纳了他,而那时《霓裳》正处在新一轮的瓶颈中。女主编知道她的杂志过于华丽了,甚至一种近乎奢靡的倾向,和普通读者越来越远。她知道要走出这种风格急需另一种声音,那种和大众更接近的,甚而敢于披露真相的声音。于是这位小报的专栏作家带来了这种声音,只是女主编将他的檄文打磨得更加圆润光滑罢了。他在女主编的打造下竟然迅速蹿红,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时尚
“潮人”,《霓裳》的销量也随之不断攀升。幸好这个骄傲的男人并没有居功自傲,无论人们怎样追捧,他都不曾终止过《霓裳》的专栏,也从不在稿酬问题上和编辑部计较。
从此杂志社和作家共同成长,而爱情也悄然降临到女主编和作家原本枯燥的生活上。他们童话一般的爱情就像细菌,慢慢侵蚀了杂志社的整个肌体。
于是每周送来稿件就成了作家的必修课,他自己也想每周都见到那位提携他的女恩人。他总是不敲门就推开女主编的门径直走进去。大凡作家驾到,女编务便会马仔一般地守候在办公室门外,须臾不离。这时候,她就会毫不通融地将所有企图觐见主编的人一律拒之门外,无论作家在主编的房间里耽搁多久。
很快,主编和作家的关系就成了杂志社公开的秘密,至少大家都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欣赏,志同道合。这无疑给了人们想入非非的空间,尤其当作家走进主编办公室的那一刻,人们便开始天马行空。尽管谁都不曾看到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到底做了些什么,但可以想象,那扇门的背后,或亲吻或拥抱,或干脆在主编中午休息的那张长沙发上的缱绻柔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