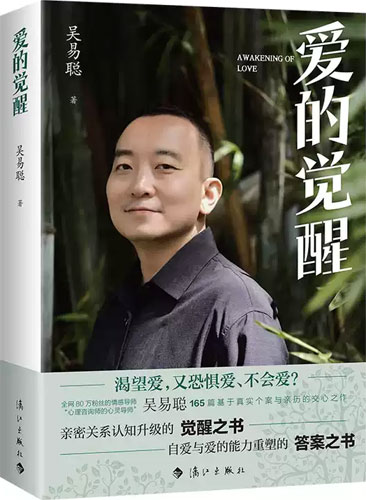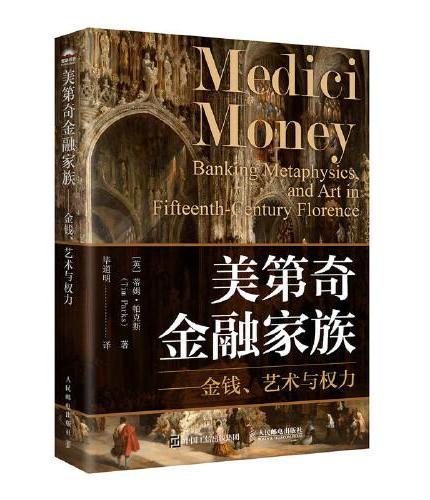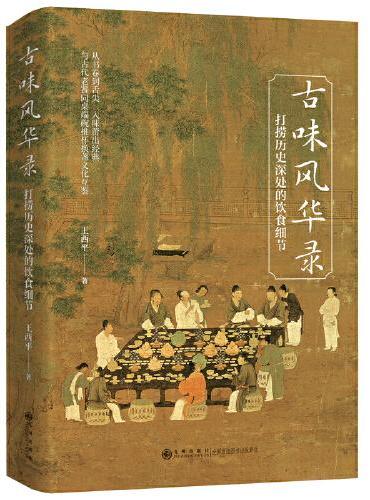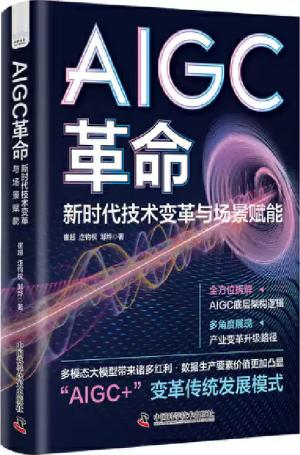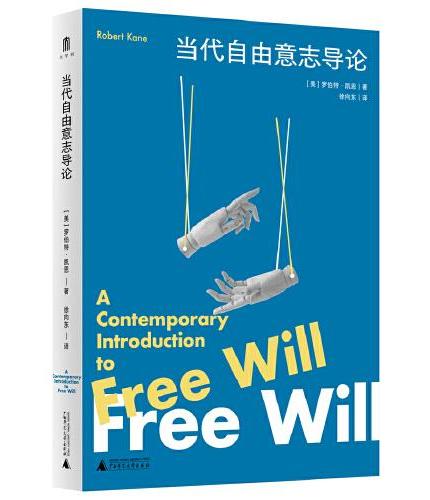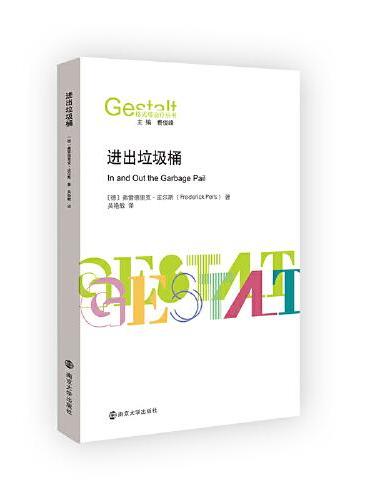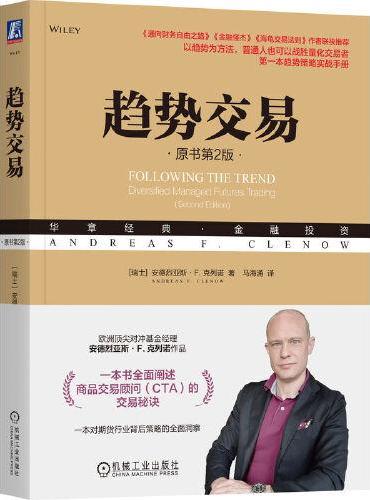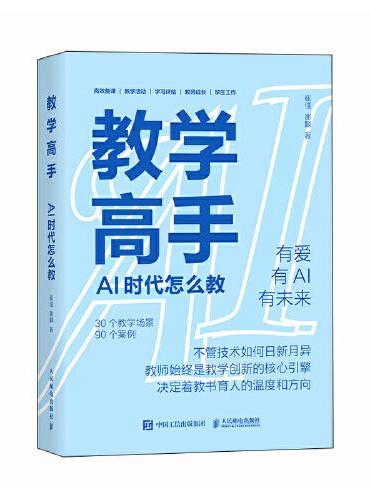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爱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NT$
305.0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NT$
347.0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NT$
352.0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NT$
347.0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NT$
449.0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NT$
454.0
《
教学高手:AI 时代怎么教
》 售價:NT$
305.0
編輯推薦:
1.权威学者,作全球视野下的历史新解,收获新知
內容簡介:
本书以几个富有特色的历史主题与文化意象作为线索,串联起世界多地在历史上开启互动的广泛历史。
關於作者:
杨斌,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博士,美国历史学会古登堡电子奖获得者,师从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帕特里克·曼宁。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国立新加坡大学以及澳门大学,对海洋史、全球史、科技医疗史以及艺术史颇有兴趣。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目錄
绪论 如是我闻:全球史的知与行
內容試閱
中国的命名:龙之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