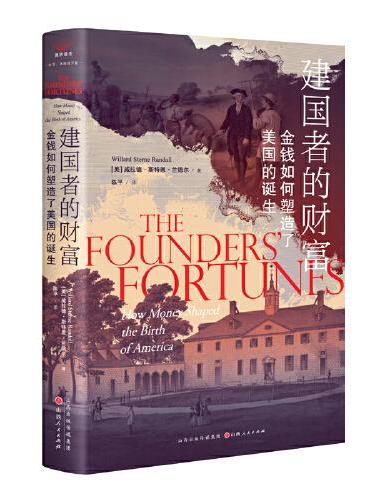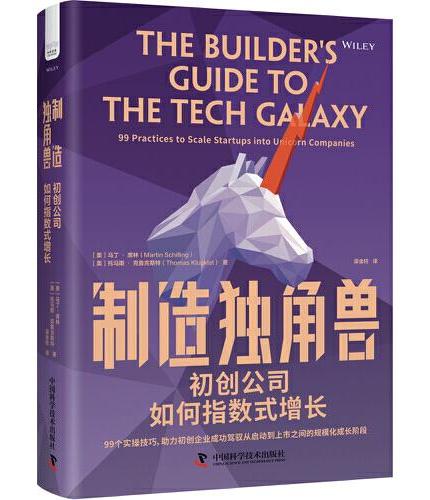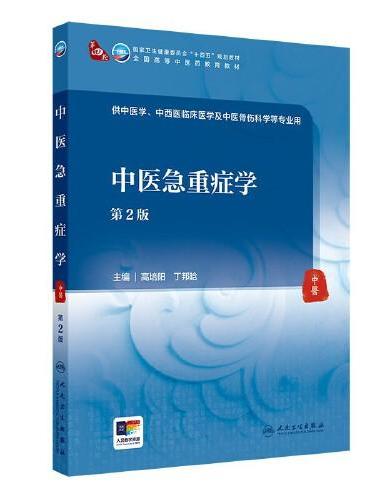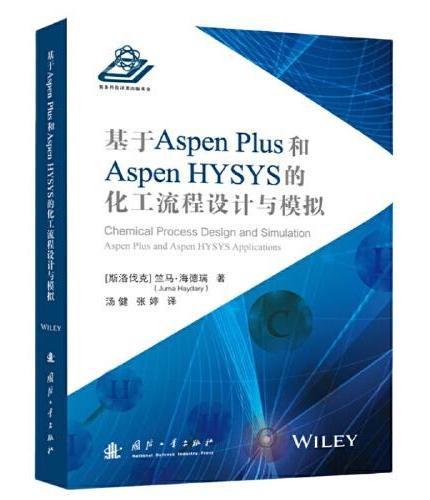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NT$
449.0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瑞士]安德烈亚斯· F.克列诺](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5/12/9787111768685.jpg)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瑞士]安德烈亚斯· F.克列诺
》
售價:NT$
454.0

《
中国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报告2025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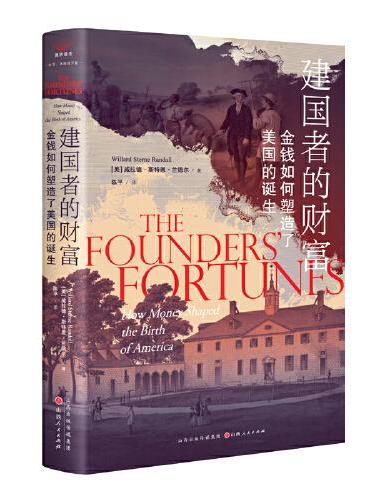
《
建国者的财富:金钱如何塑造了美国的诞生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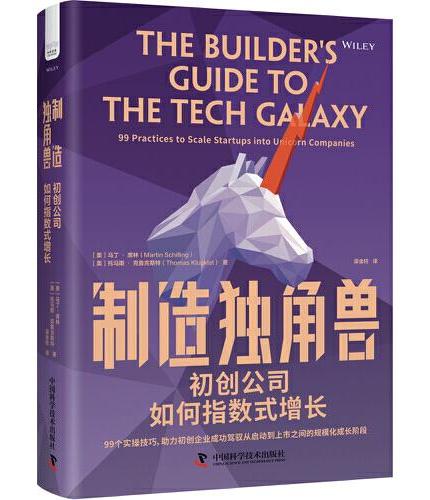
《
制造独角兽:初创公司如何指数式增长
》
售價:NT$
403.0

《
绿色黄金 : 茶叶、帝国与工业化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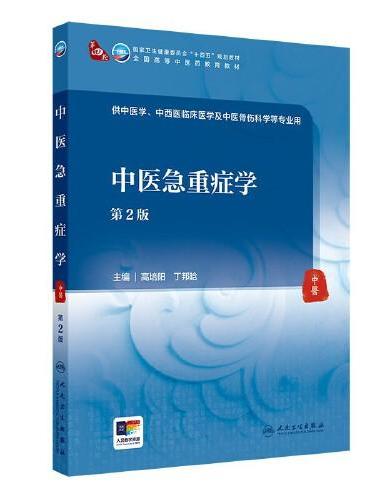
《
中医急重症学(第2版)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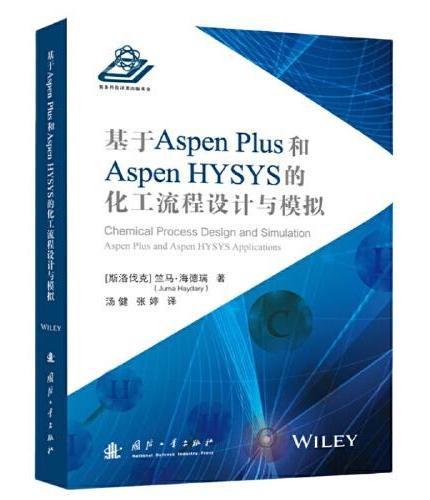
《
基于Aspen Plus 和 Aspen HYSYS的化工流程设计与模拟
》
售價:NT$
1010.0
|
| 編輯推薦: |
◆ 是被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出版商务周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重磅报道的「菜场女作家」
陈慧是浙江省宣传部浙版好书榜、《文学报》好书榜得主,也是个菜场小贩,她一边摆摊一边写出了3本书,登上过4次央视新闻,上过3次微博热搜,今日头条为她拍摄纪录片。她的从容自在、自由自洽,打动无数人。
◆ 从菜场到旷野,去3000多公里外追花养蜜蜂
当一个中年女性兼菜场小贩,突然决定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出走,来一场几千里的远行,会遭遇怎样的经历? 陈慧摆摊十几年,习惯了一单几块钱、几十块钱的小生意,往来都是熟面孔。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冲动到跟着养蜂人去3000多里外追花养蜜蜂。
◆ 亲历“追花夺蜜”的游牧生活,记录“养蜂人”的辛苦与甜蜜
从浙江一路北上,历时4个多月,跨越4省,辗转3000多公里。追赶着油菜花、洋槐花、荆条花……的花期,在一处处开满鲜花的旷野,陈慧遇见了狂风暴雨,也遇见了生命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
◆ 既是对重复人生的短暂出走,也是发人深省的自我探寻
4个月后,陈慧离开蜂场,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在外人看来,这次远行什么也没有改变。但至少,她不再是原来那个郁郁寡欢的自己。
|
| 內容簡介: |
《去有花的地方》是“菜场女作家”陈慧新作,记录了45岁的她决定走出菜场,跟着养蜂人到几千里外追花养蜂的经历——她生活在农村,28岁开始在小镇菜场摆摊谋生,半辈子围着家和孩子打转,自认不喜欢出门。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冲动到跟着养蜂人开始一场3000多公里的远行。
在江苏弶港,她遭遇十级狂风,先是闪电跃然而出,一道接着一道,风瞬间排山倒海地来了;在山东徂徕山,她最中意赶大集,小贩和顾客扎了堆,人多得像刚刨出来的新土豆,遍地都是;在辽宁瓦房店,玉米地与蜂场仅隔了一道窄窄的沟,她站在帐篷边,不时望见五彩斑斓的公野鸡在对面起起落落地撒欢;在辽宁常河营,特色是各式各样的虫子,一只牛虻从东南边的养殖场赶过来,狠狠咬了她一口,也许觉得南方人味道挺不错,隔天又来咬了第二次……
四个月后,她离开蜂场,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普通人的生活,还要继续苟且。但至少,她不再是原来那个郁郁寡欢的自己。
|
| 關於作者: |
陈慧
菜场小贩、作家
1978年生于江苏如皋,现定居浙江余姚
2006年开始在菜场摆摊卖杂货,并持续至今
2010年开始写作
已出版作品:
《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
《世间的小儿女》
《在菜场,在人间》
|
| 目錄:
|
开篇 去追花
一 夜奔东台
夜奔东台
取水记
夜晚的声音
刘大哥
风,风啊
送菜给我们的人去花舍
再见,八里
二 初到山东
化马湾的下马威
初到徂徕山
邻居们
王大爷
日常和赶集
老秋
第三站
司机和牙签
三 “蚂庙山”不是“蚂蚱山”
蚂庙山
在集上卖蜂蜜
散步
蜜蜂们
闲
老范
也苦,也美好
他乡的端午
四 与虫为伍
牛粪大礼包
等雨
唉!这些人啊
与虫为伍
蜂场来“客”
相亲
难采的蜜
热
爱笑的老朱
目送
新丽姐
五 回家
回家的路(一)
回家的路(二)
回家的路(三)
后记
人这一辈子,总要出走一次
|
| 內容試閱:
|
人这一辈子,总要出走一次
我打小很宅。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们不带我一起玩,我也无所谓,有一本厚实的书捧在手上,就能在屋前的水杉树下坐到天黑。自记事起到十三岁,我去得最远的地方是一百多里外的南通——三姨结婚,姨父家办酒席,派了辆面包车来接女方至亲。乘车途中,我数次晕车,把面包车吐得一塌糊涂,身体的不适加上驾驶员嫌恶的眼神,在年幼的我心中留下严重的阴影。此后,一提到出门,就联想到“遭罪”二字,下意识地排斥。
十四岁到二十六岁,我在如皋县城读书,职高毕业,开了间小小的裁缝铺子。一天到晚,像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把我妈用过的那台“飞人牌”旧缝纫机踩得咔嗒咔嗒响,很少会停下手中的活计,抬头望一望头顶的天空。最大的憧憬不过是日后找一个近处的丈夫,随时能回娘家,吃到妈妈亲手做的热腾腾的饭菜。
后来,我身染顽疾,不得不终止了裁缝生涯,被远嫁浙江的小姨接过去养病。二十七岁,我嫁到浙东小镇,正式落户。听起来,天地似乎变宽广了;实质上,固有的生活模式并未因地域的切换而有什么不同。二十九岁,我用一辆自制的手推车摆起了流动小摊,开启菜市场到家里两点一线的日子。每天不等天亮就起床,匆忙赶去喧闹的菜市场,忙碌一整个上午。下午半天,如果不必去市区进货,我就专心在家陪伴孩子。孩子进幼儿园后,我午睡醒来,闷在屋里看看书,写点不着边际的文字,直到去学校接孩子的闹钟响起,才踏步迈出房门。四十岁,我的婚姻解体。孩子渐渐长大,读寄宿学校。我一个人默默地进进出出,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他人眼中一个形单影只却又特别强大的人。
但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的强大不过是戏台上提着铜锤唬人的花脸。某个宁静的夜晚,我站在家门前,对着满天的星子,问自己:陈慧,你快乐吗?
答案是:不快乐,我很不快乐。
“出去转转”的念头就是在那一刻倏然而生的。并且,越来越迫切,迫切到如果不能如愿出行,简直坐立难安的地步。
跟随蜂农追花逐蜜的四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一段经历。忙碌的日常和艰苦的转场赐予了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在江苏东台弶港,十级狂风黑夜来袭,暴雨倾盆,我蜷缩在剧烈抖动的简易帐篷内面如死灰、瑟瑟发抖。在山东泰安化马湾,我的床头距离盘山国道不足三米,重型货车的喘息声彻夜不停,惊得我神经兮兮,夜夜难眠。在辽宁大连瓦房店,驻地对面横陈着一头将腐未腐的死猪,夜幕降临,嚣张庞大的苍蝇军团入侵帐篷,爬满了我目光所及的每一寸地方,似乎能随时随地将我吞噬。在辽西北票的常河营,不光有近在咫尺的重量级牛粪包,还有不用踮起脚尖就能一目了然的老坟堆。那是当地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都轻易不敢踏足的禁地,我们却要硬起头皮在那里安营扎寨。
幸运的是,几千公里的颠沛,每到一处落脚点,虽有大大小小的不如意,但也收获了众多美好的回忆。所有的感动和感激汇流成河,诞生了《去有花的地方》这本书。
二〇二三年八月中旬,从蜂场返回的我,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普通人的生活,还要继续苟且。但至少,我不再是原来那个郁郁寡欢的自己。
想起几年前春天的一个中午,我收了摊,走进梁冯桥的小吃店。在我吃馄饨的当儿,店里多出了一位讲普通话的中年男人,微胖,胡子拉碴,眼袋耷拉,满脸倦色。他点了份八块钱一碗的蛋炒饭,坐在我对面吃得斯斯文文。他的重型机车停在小吃店门口,两只鼓鼓囊囊的行李袋绑在车座上。我忍不住好奇,厚着脸皮与他搭讪。知道了他是福建人,在上海谋生多年。几乎每一年春季或秋季,他都要挤出时间,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离开家,没有目标地闲逛,逛完一圈再回去工作。我当时盯着他骑行服领口和袖口上泛滥的黑色污渍,看了又看,实在想不通这样的“千里走单骑”究竟有何意义。不安全,还辛苦,又孤单。老实蹲守家中,热饭热菜热水澡,难道不比风餐露宿的折腾更舒适吗?
事过境迁,我终于能理解那种独自“摩游”的心情了。人常常寄望远方,并非就向往别样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中偷得的有限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扑腾在庸常的柴米油盐里,而已。
二〇二四年四月
|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瑞士]安德烈亚斯· F.克列诺](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5/12/97871117686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