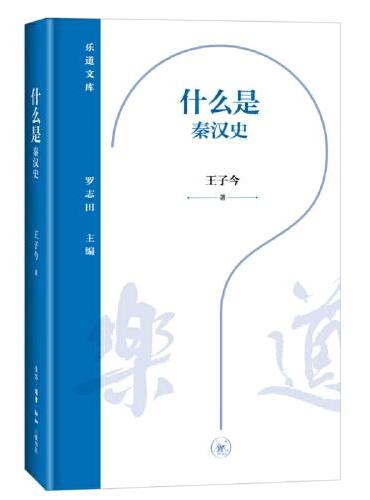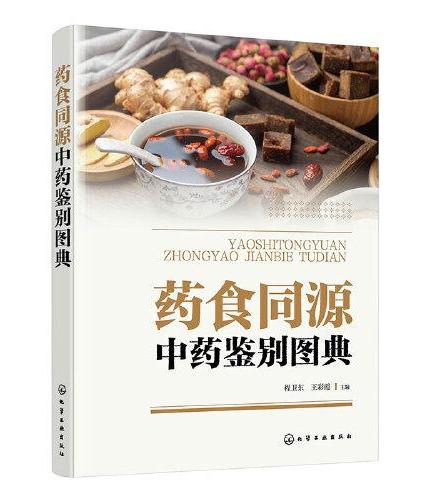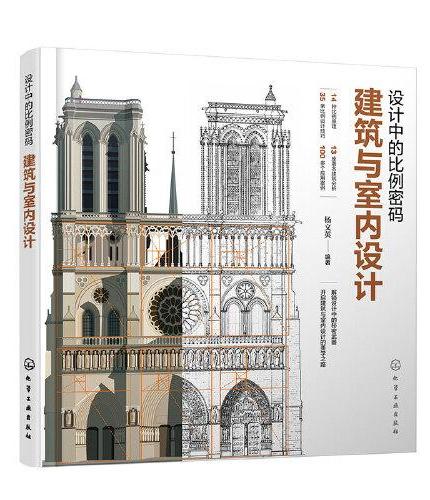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NT$
449.0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NT$
352.0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NT$
352.0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NT$
367.0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NT$
500.0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NT$
500.0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NT$
305.0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NT$
398.0
編輯推薦:
这是一本2021年上市的新书,它刚一出版,就在美国引起震动,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 首,2021美亚总榜年度TOP 100,goodreads万人评分4.5以上,小红书博主提前分享,微博大V半年书单介绍:这本书我给五颗星,我读得几度落泪。美亚读者评价说:这是今天的美国非常需要的书。
內容簡介:
痛苦不会凭空消失,时间也不会冲淡一 切
關於作者: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奥普拉脱口秀》的主持人和制片人。在她令人尊敬的职业生涯中,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二十五年来,她为观众带来了欢笑、启迪和鼓舞。
目錄
作者手记
內容試閱
第一章 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