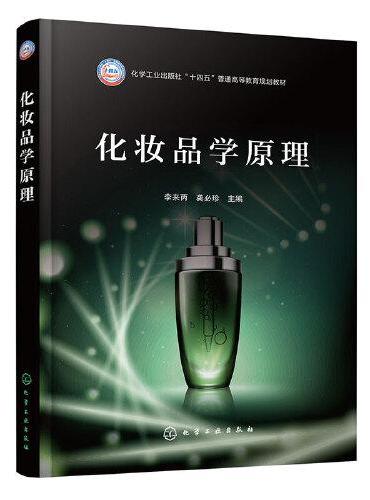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们身边的小鸟朋友:手绘观鸟笔记
》 售價:NT$
356.0
《
拯救免疫失衡
》 售價:NT$
254.0
《
收尸人
》 售價:NT$
332.0
《
大模型应用开发:RAG入门与实战
》 售價:NT$
407.0
《
不挨饿快速瘦的减脂餐
》 售價:NT$
305.0
《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守望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 售價:NT$
504.0
《
卫宫家今天的饭9 附画集特装版(含漫画1本+画集1本+卫宫士郎购物清单2张+特制相卡1张)
》 售價:NT$
602.0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NT$
254.0
編輯推薦:
国内屈指可数将自残单独列出进行研究的专著,专业且兼顾实用性。
內容簡介: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自残行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这些行为及与自己身体相关的精神病理学表现说明,青少年自残的根源在于家庭,而不是社会。这些青少年以前往往遭受过虐待,尤其是性虐待。因此,有必要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制定多渠道的完整治疗方案。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目錄
导言:身体的徽章
內容試閱
导言:身体的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