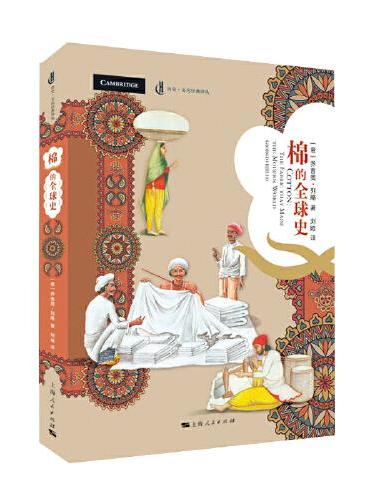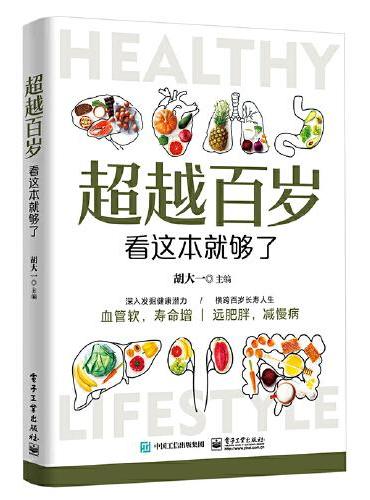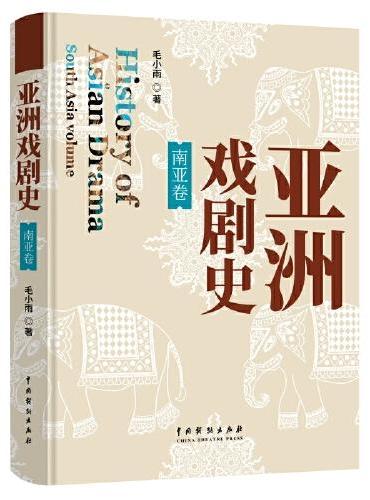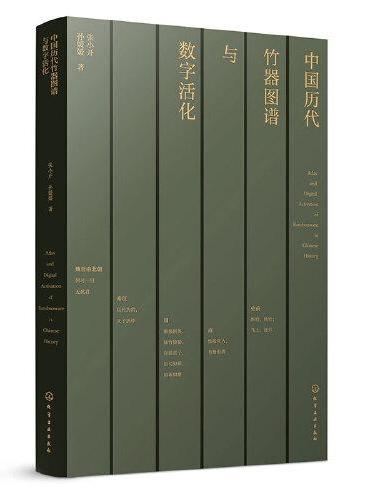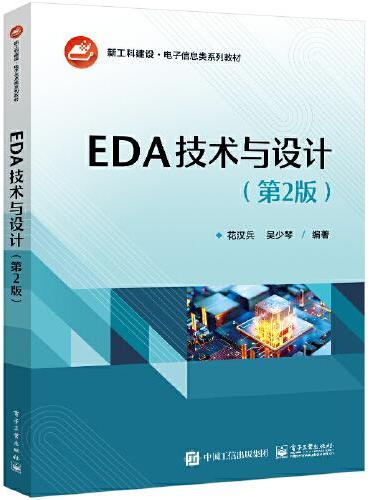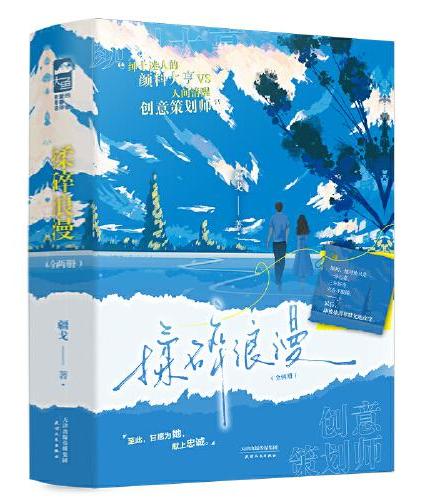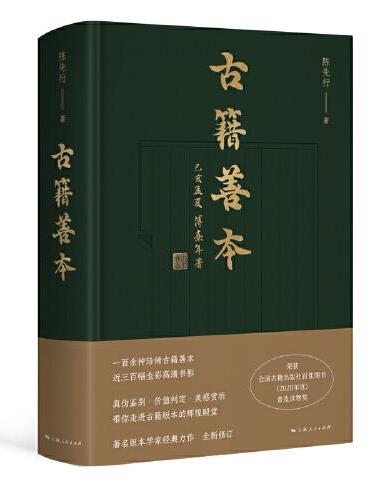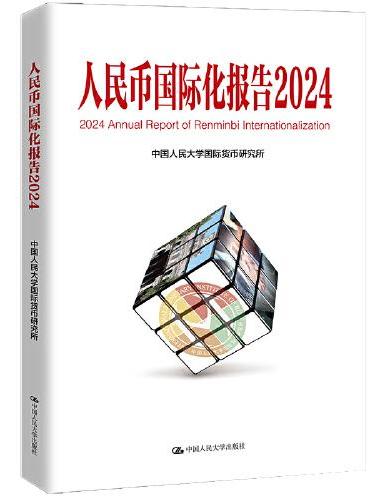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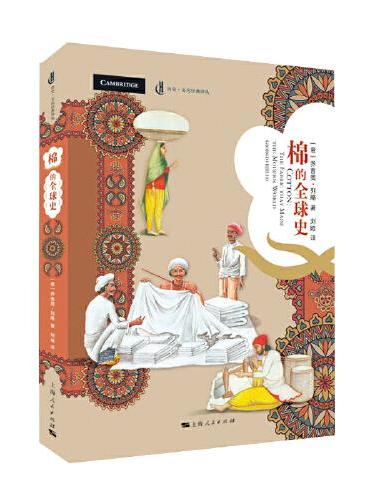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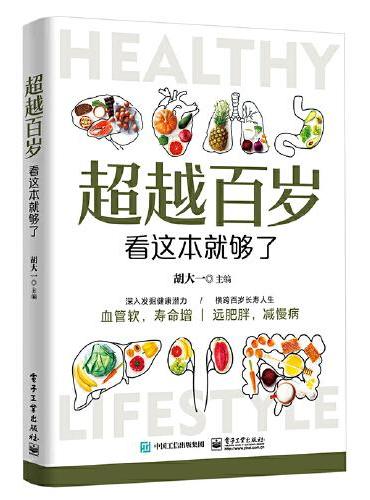
《
超越百岁看这本就够了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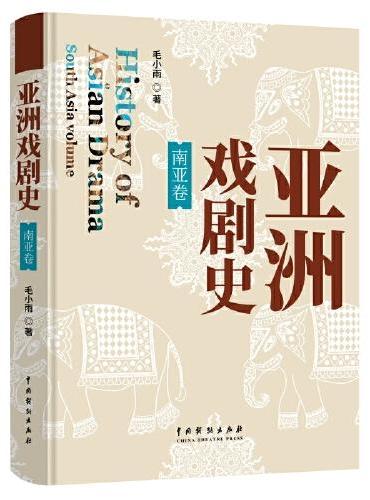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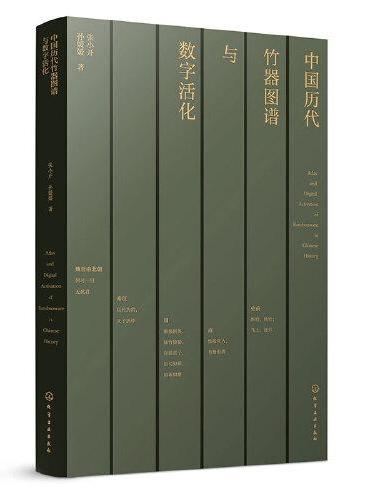
《
中国历代竹器图谱与数字活化
》
售價:NT$
2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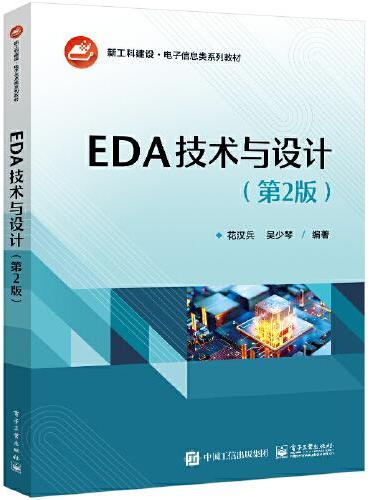
《
EDA技术与设计(第2版)
》
售價:NT$
3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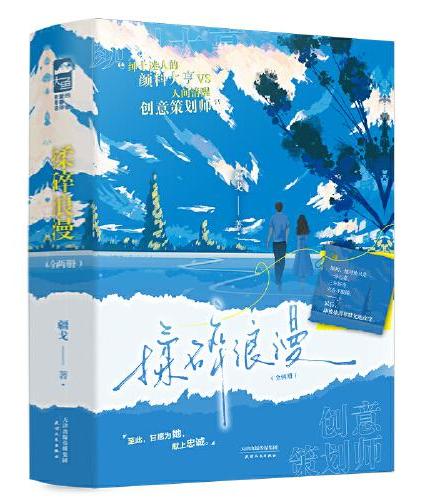
《
揉碎浪漫(全两册)
》
售價:NT$
3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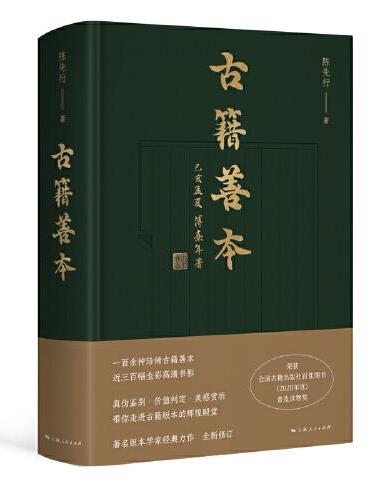
《
古籍善本
》
售價:NT$
24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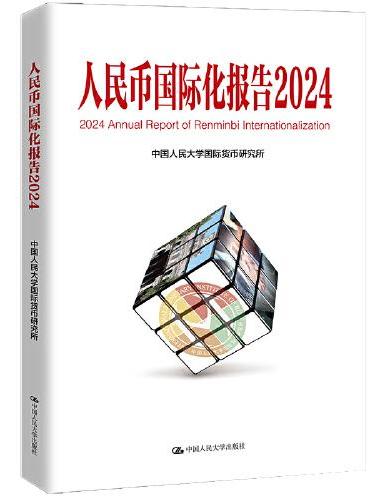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历经三十年,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有着良好学术风气。分布在海内外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固然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王守常先生语),然更重要的是,《导师文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汤一介先生语)。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严家炎先生关于现当代文学史上小说的专题论集,分别从总论、思潮、流派、作者、典型作品、专题等角度梳理了整个二十世纪小说的发展脉络,并回顾了一个世纪的小说史研究。作者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个人体会与学术信念融入史的叙述之中,每每采取历史主义态度评论作品;并认为对待文学作品,应首先着眼于艺术,其研究论文和随笔往往深藏着智慧。
|
| 關於作者: |
|
严家炎,1933年生,笔名稼兮、严謇。上海人。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肄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语言文学学科评议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丁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知春集》、《求实集》、《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世纪的足音》,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纲》,与唐弢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编辑《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四卷、《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17—1927》等十种。《求实集》获北京市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分获第一、二届优秀教材一等奖。
|
| 目錄:
|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代序)1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
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
——《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序
试说20世纪中国小说的总体特征
“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
“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
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
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
——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考察
须藤医生所写鲁迅病历为何与鲁迅日记及书信牴牾的再探讨
论彭家煌的小说
老舍短篇小说《微神》
论新感觉派小说
论社会剖析派小说
论京派小说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
——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
开拓者的艰难跋涉
——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
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艺术贡献
走出百慕大三角区
——谈20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
我看金庸小说
试说“中国的奥勃洛莫夫”
——从《王蒙自传》谈到倪吾诚形象的典型意义
论王蒙的寓言小说
从《檀香刑》看莫言小说的贡献
子规声声鸣,竟是泣血音
——评竹林小说《挚爱在人间》
鲁迅心目中文艺家和知识阶层的时代使命
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严家炎教授访谈录
总后记
|
| 內容試閱:
|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代序)
我从小喜欢文学。诗和小说都让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级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后,我奠立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从此,“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真成了我奉献的信条和毕生的体验。
上海于1949年5月下旬解放。那个暑假,我们吴淞中学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毕业,我为了圆文学之梦,竟违背家长要我进正规大学的愿望,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参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经历了农村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的较长时间工作锻炼,连续过了六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艰苦生活,积累了若干素材,写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笔记。
然而,1955年突发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风暴,使我极度震惊。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群向来被公认为进步的作家,其中还有不少党员作家——也包括我在华东革大时的教务处长、很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老师刘雪苇在内,何以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一些私人通信,又怎么会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我不禁感到事情的可怕,并陷入痛苦的沉思。于是,在一次政治学习会后的晚上,我撕毁了那几年写的一部分感情内容可能被指为“不健康”、“有问题”的草稿和笔记,第二天还向党组织交出了我收藏的胡风、路翎和雪苇的几本著作,如胡风的《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决心要变换自己的环境和道路。1956年,恰好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我便在这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一、从可疑之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
就在我研修了两年文艺理论专业课程,并逐渐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我再次转向。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我被半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准备寒假后为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二十多名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这不仅是岗位的变更,而且是专业方向的改动,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做起。我只能结合自己的备课,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办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这就是:抓住阅读中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紧追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入开掘,最终获得成果。我之所以在最初阶段采取这种方式,也许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关。
在两个月备课过程中,我首先读了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的“参考书”),不久又从旧书店里买到王瑶先生1953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因较多引用胡风的论述,在1955年胡风案件后当然失去了成为“参考书”的资格。其实这部书写作时间惊人地短促,内容却相当丰富充实,动用了作者长期关心新文学发展而形成的学术积累,虽然尚有若干疏简错失之处,但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首部奠基之作。上册,还翻阅了丁易等其他两三种相关的书。我发现50年代前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为了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断,往往在来不及阅读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就把1916年酝酿、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当做“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划入“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当时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于是连续二十多天到北大图书馆去查阅1915年到1920年间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我第一次去接触《新青年》。我阅读了这个刊物上所有署名陈独秀或以“记者”名义发表的文章,还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论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这番阅读带给我许多惊喜。我终于坚信:1918年以前,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还只是激进的民主派,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1916年,还曾经幻想中国应该走德国军国主义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胜利,芬兰、德国、奥地利革命发生,接着是欧战结束之后,李大钊、陈独秀才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而陈又比李晚了一年左右。我不仅弄清了两位重要人物思想转变的具体事实,还考察了1918年以后《新青年》文学活动的若干新因素、新变化:一是《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成员增多,陈独秀之外,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先后参加工作,“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见《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因而声威大振;二是涌现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月夜》《鸽子》《小河》等一批出色的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学开始在全国推开;三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的重视和研究已极一时之盛,诚如瞿秋白所言:俄国文学几乎“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出版。。我认为,这些正是文学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方向逐步转化的标志。我将这些想法连同稍后发现的若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材料,写成一篇题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的文章初稿,给学生讲述了我的意见。后来经过修改,曾作为“五四”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在会上发表,并刊载于上海《文艺论丛》第8辑。当时颇得会议主持人李慎之先生和一些与会学者的赞誉,认为材料充实,分析细密,相当有说服力,使课题研究深入了一步。
我研究“五四”文学的另外一些文章,也大多采取这种从疑点入手的方式。例如,陈独秀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真像有的学者所说,要“打倒”中国的“古典文学”么?那么《文学革命论》中为什么又对国风、楚辞、汉魏五言诗、唐代古文运动、元明戏曲、明清小说等给予高度评价,并对胡适所说“诗至唐而极盛”的提法也表示赞同?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我经过长期反复思考,又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外的大量文章尤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细读、研究和考辨,并联系陈独秀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的态度,终于得出结论:陈独秀所要“推倒”的“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实际上是指形式刻板、声律极严的骈文、律诗(尤其长律)以及桐城末流等一味“仿古”的文学形态,也就是他称作“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东西。于是,我写成《〈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辨》一文。这个答案至今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可。
又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提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而首开风气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林先生认为,正是由于“五四”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立场。”对于林教授这种观点,我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者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当然无法赞成。我觉得,林先生无论对“五四”或对“文化大革命”都了解得比较表面,因而撰写了《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一文,后来又补充、扩展为《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考辨》的论文。我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新青年》在帝制复辟声浪甚嚣尘上的年代,起来批判儒家的“三纲”,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以启蒙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有着巨大的功绩。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判断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致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说不通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做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内部,原本就有王充、李卓吾、黄宗羲、戴震等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五四”新文化就是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部这些“异端”成分的。我还论证了:“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运动。“五四”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愚昧迷信。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在上层是个人专制变本加厉,在下层是个人迷信极其盛行的产物;它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对“封资修”文化全面批判,实际上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回潮。“文化大革命”对于“五四”,是严重的反动和倒退;对于中华民族,更是一场少有的人为灾难。我所发表的这些看法,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赢得了不少赞同的声音。
总之,这种由发现疑点而起步的研究方式,似乎是一种舒卷两便、灵活可行的模式,它能适应多种不同的范围。大到一场文化运动的评价,小到半句文学口号的理解,都可采用这种方式应对。我的有关“五四”的多篇论文,便是这样产生的。
在这类研究过程中,最终决定着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时,主编唐弢先生一再强调:要“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还开列了几十种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名单。这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学者的成长确实极有好处。在两年多时间里,我先后阅读了近二十种文学和文化的期刊,留下了至今还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的笔记,弄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举例说,朱自清的《赠友》一诗,歌颂“手像火把”、“眼像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这对于说明作者的思想和交往应该说都很重要。但他所赠这位友人到底是谁?原诗发表于何处?都不清楚。我翻阅了20年代初期的一些期刊,发现此诗发表于1924年4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8期上。在此之前四个月,《中国青年》曾刊登过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其中引录了他自己所做的两首旧体诗,正是表达了“共产均贫富”的理想。那么朱自清赞颂的这位友人,也许就是邓中夏了。然而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尚不能确切地证实。及至进一步了解到朱、邓二人都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文科学生,虽然朱在哲学系,邓在国文系,却都是1920年毕业的,完全可能是熟识的友人;至此,这种可能性更有所增大,却还不能真正落实。我又从朱自清将此诗收入《踪迹》集时改题《赠A.S》方面查找线索,想弄清A.S是谁。经过苦苦寻找,总算从《红旗飘飘》上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说邓中夏1923年在上海大学工作时,曾改用“邓安石”的名字,正好符合A.S的英文拼音,这才算一切口径都对得上,终于获得定论。我之所以能从1963年8月起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发表《朱自清与邓中夏》等几篇文章,可以说正是大量阅读原始资料的结果。
二、着眼于艺术而又饱和着思想的小说评论
1958年4月,《文艺报》为了培养文学评论队伍,邀我当了业余的评论员。此后我经常接到一点编辑部交来的任务。虽然这近于“命题作文”,但我总是首先坚持从艺术角度对作品加以考量:看看它能否真称得上是语言的艺术,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在我看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赖于它是艺术。思想只能渗透于艺术之中,不能游离在艺术之外。脱离了艺术的思想,是干枯无生命的思想,根本打动不了人。真正的文学,总是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去吸引人和打动人。因此,我总是试着要将阅读作品第一遍的感想写成笔记。“我非常看重这读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认为它不仅是文学评论必需的素材,而且是正确地开展批评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常常说要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我认为这种结合的关键,首先在于从纯欣赏者的角度去读第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审美基础。”见拙作《回忆感想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一文,《文学评论家》1986年第6期曾予转载。收入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评论,就是在读者和作品之间搭起桥梁,真正让作品与读者做到“融通”和“不隔”。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需体察人情,体察生活,熟悉自己所要熟悉的那些生活内容,并有自身的真知灼见。正当多位评论家撰文赞许《创业史》塑造的新人形象梁生宝获得重大成就时,我也写了一组评论这部作品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1961年6月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中,我指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别人,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我通过对梁三老汉这位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老农层层深入的分析,细致地解剖了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两面性,以及由其贫苦地位和经历所决定的最终要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必然性。我认为:梁三老汉在第一部中是真正完成了的形象,“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富,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据《文学评论》编辑部张晓萃女士说,1961年秋天她到长安县柳青家中采访时,柳青对该文表示赞赏,认为它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意义阐发较深,甚至连作者某些很隐微的想法也都精细地触及到了。冯牧当年秋末在《文艺报》一次会后留下颜默(廖仲安)和我,说到作协领导同志(指荃麟)对评论梁三老汉形象的这篇文章给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写得有深度。唐弢先生则向吕启祥等几位当时的青年学者说:“好文章要写出气势,论梁三老汉形象这篇文章就确实有气势。”这里还有一则小故事:1961年9月,教育部人事司已与北京大学方面商定,派我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任教两年,接替即将回国的冯钟芸先生,并已为我预订了去欧洲的火车票。那时,唐弢先生刚被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他坚决反对将我放走,要求教育部给予支持。最后,教育部同意了唐的主张,我就回到了教材编写组。唐弢先生曾两次向我道歉,我则感谢他给了我很好的学习进修的机会。围绕《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1964年批判“中间人物论”的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都发生过许多可悲、可笑、可叹、可气、可歌、可泣的难以尽述的故事,而荃麟同志表现的那番独自承担厄运、决不诿过于年轻一代的傲然挺立的风骨,则令人永远钦敬。新时期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国新文艺大系》两套大型选集以及其他多种选集中,也都选入了这篇文章,可见它的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也是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很有兴趣,待第二卷出版立即投入较多时间进行研究的。我不仅反复钻研作品,阅览《明史》相关部分,还在一位明清史专家指导下,读了明末清初的《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传信录》《平寇志》《明季实录》《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等十几种野史,终于在1977年末、1978年初写成《李自成初探》这篇近四万字的论文。三十年后读来,某些文字虽不免带有特定的历史印记,但我相信,论文总体上仍保持着原有的厚重感和新鲜感。原因在于,论文一方面紧扣着小说《李自成》杰出的艺术创造深入展开评述,另一方面又力图将这些评述建筑在接近或符合历史实际的基础上。兵部尚书卢象升家里一个得心应手的贴身仆人李奇,竟然是东厂派来的特务,虽然他临离开卢府时保证绝不会说一句卢象升的坏话,事情本身却不能不让当事人惊出一身冷汗。一个很小的情节就把明朝的君臣关系和明朝政治的恐怖、黑暗,显示得清清楚楚,其作用不可谓不神奇。小说中连许多细节描写(如宫廷服饰、礼仪及北京城戒严由哪个衙门出布告)也讲求严格的历史真实性。可以不夸张地说,《李自成》真称得上是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迄今为止,《李自成》无疑是长篇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它所塑造的李自成、崇祯、刘宗敏、郝摇旗、李岩、红娘子、洪承畴等众多的成功形象,所营造的极复杂宏大,又严谨匀称、单元式组合的结构艺术,所呈现在许多画面和文字中的绚丽多彩而又浓淡有致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无不令人叹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小说定位为“一部反映明末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悲剧性史诗”,而不是有人误解的“李自成起义的颂歌”。他只是肯定李自成身上值得肯定的可贵素质,却也据实写出了足以导致李自成失败的严重局限。因此,我主张从明清之际的历史实际出发,探讨《李自成》中是否有某些现代化的问题;却不赞成由想当然而来的“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一类批评。试想,像高夫人这样一位在李自成去世后还主持大顺军长达十多年,坚持抗清,连南明大臣都要尊她为“皇太后”、向她跪拜的女性,可能是一个很简单、没有头脑、未经风雨的人物吗?我们总该顺着生活情理来想一想的吧。
三、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
1978年末开始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伟大运动。它既是一场思想运动,又是深刻的学风改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灾难是“左”倾思潮长期恶性发展的结果。因此,对它的清算,必须正本溯源,从根子上加以清理。
1979年起,我先后选择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界发生的三次思想批判,从原始材料入手,找出问题所在,写了《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等几篇论文,澄清数十年的沉冤。
1948年东北由《生活报》发动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是我要清理的首个目标。早在50年代前半期,我就读过《萧军思想的批判》一书,知道其中全为批判者的文章,附录所收则是被批判者的若干片言只语,对于了解事情真相并无帮助。因此,我决心寻找萧军主编的《文化报》来对照阅读。然而,走访了当时北京的三所图书馆,此报踪影全无。无奈,只得叨扰萧军,从他那里借阅。而当我原原本本地读完萧军的《新年献词》和八一五社评即《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全代大会”》一文。等文,委实大吃一惊:这些分明是一篇篇声讨蒋介石及其后台“美帝国主义”的檄文,哪里有批判者所指的“反动思想”的影子。例如,萧军从来没有说过“赤色帝国主义”这类字样。他只是从日本侵略者虽已被赶走,而另一副面目的美国却又进入中国这个事实,提醒人们注意帝国主义会变换不同装束、不同色调而已;批判者却从“各色”二字大做文章,恶意引申,硬说萧军的真意在于“反苏”。又如,《新年献词》本是萧军独创的由主人公“老秀才”以独白方式叙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小说体作品,尽管主人公原先对土改、对共产党有过错误看法,但后来受亲属中“革命者”的教育,终于改变想法,对党由佩服而衷心拥护,并向人民发出“支援前线”、“倒蒋驱美”、“拥护民主政府”、“开展新文化运动”等七点呼吁。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读者,都不会把作品中这个六十多岁的老秀才当做萧军本人,更不会把老秀才追忆自己旧思想时坦露出来的那些错误的话,当做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恶意”攻击。然而,当年批判萧军,恰恰出现了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局面,这确实说明批判者身上那些宗派主义和神经过敏、想入非非,已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顺便说明的是,直到1979年冬、1980年春出版的两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由于不重视原始材料,仍在沿袭旧说,大讲萧军思想如何反动以及东北如何开展批判。正因为这样,1980年夏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包头年会上就萧军问题发言时,才引起与会者的相当轰动,甚至郝铭鉴先生回到上海向出版社内的工作人员传达时还引起了热烈反响。
我选取的第二个目标是重新审视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所受的批判,因此写了论文《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我从分析《在医院中》的艺术内容入手,指出主人公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文化所要求的高度责任感与小生产者的愚昧、冷漠、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的尖锐对立,而不是批判者所说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与革命集体间的矛盾。从鲁迅小说开始的“五四”新文学对“国民性”的批评,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批判与改造。《在医院中》正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