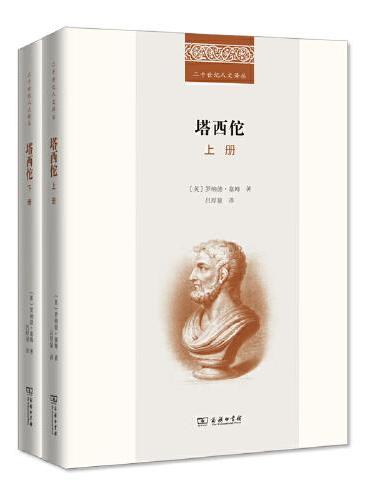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夺回大脑 如何靠自己走出强迫
》
售價:NT$
299.0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NT$
440.0

《
中文版SOLIDWORKS 2024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实战案例版)
》
售價:NT$
450.0

《
旷野人生: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
》
售價:NT$
345.0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NT$
845.0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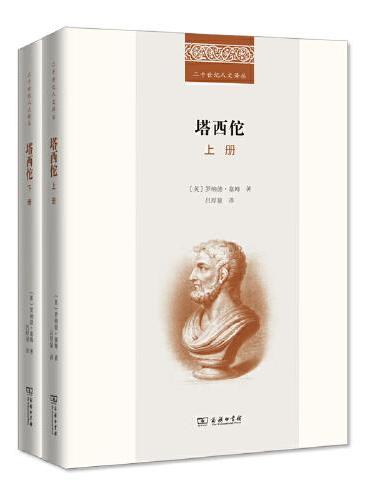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NT$
990.0
|
| 編輯推薦: |
|
贾平凹:在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总书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还问我最近有没有新作,我说刚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他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
|
| 內容簡介: |
|
“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收录作者1973年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其中分为短篇卷四卷,中篇卷六卷,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集,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作品集用“倒叙”的方式给读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
|
| 關於作者: |
|
贾平凹,1952年生,陕西省丹凤县人。陕西作协主席,中国书协会员,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使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奇才,别誉为“鬼才”。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最具叛逆性、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失策的为数不多的著名作家之一。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都有经典之作广为流传。其作品曾多次问鼎国内国际文学奖项,不仅在我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得到了不同民族文化北京的专家学者和读者的广泛认同。
|
| 內容試閱:
|
题?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的家事永远都在闪烁着斑斑驳驳的色彩;我怀念着那个孩提的年月,怀念着那个家庭,但我终是不明白,在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没有现在的思想呢?而那个可爱的家庭为什么竟没有继续了下来?!
上
一
按规律,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是大年初一。可是已经过了一个月,我还没有生下来。一家人便吓得战战兢兢的了。娘待在祠堂里,终日抱着个大肚子,没人处就哭,哭一气儿,就又咒我;婆和三个婶子就守在旁边,一步不离地说:
“没事的,没事的,瓜熟下蒂便会落的……”
娘说:
“要是个不熟的瓜呢?”
“咱就在这儿等它个一年半载,他敢不出来?拽也得拽出来!”
娘听了,又哭起来了:
“这冤家怕是要来收我的命儿的。让我回去吧,要死我死在家里。”
婆忌讳说这话了:
“不许胡说!傅先生的话还会有错儿?”
傅先生是南阳沟里一个阴阳师,娘刚怀上我的时候,他就来过家里看过风脉。在我上头,娘生过两个孩子,白白胖胖的小子,可都没留住,傅先生说是宅向不好,让娘搬住到祠堂里来生我。
婆又跪在堂前烧起香了,双手合在额前,一眼一眼看那香烟熏蒸起来,袅袅地抖,便对我父亲和大伯说:
“咱祖祖辈辈没做亏心事,咱会安宁的;为了保险点,你再去请傅先生一趟吧。”
父亲他们动身走了,天就下起雨来了。一时远山缥缈,近岭如墨,那祠堂门前偌大的荷塘里,风在不定方向地刮;雨脚匝匝,踢出一塘的水泡儿,冬日里的枯荷残叶,特意儿是留下听雨声的吧?娘歪在窗前,突然肚子就不自在起来,一扭一扭地疼……
雨下得更大了,河里开始涨水。眼见洪水扑过堤堰,漫了村前的河湾;半夜里,水就进了村。一村人都惊慌了,扶老携幼地往村里高处跑,祠堂门前一时就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哭喊声、叹息声、骂天声,使本来就不安宁的祠堂,空气越发烦躁了。婆把东西全拿了出来:油布、雨伞、被单、蓑衣……让人们顶在头上,但无论如何也不让外人走进祠堂一步,就拿一撮红线挂在门环上了。
娘肚子开始揪着疼,疼得打滚儿地叫,汗水湿了头发,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先是咬着被角呻吟,后来连呻吟声也没了,咬得满嘴淌血。守在一旁的大婶,心疼得直抹眼泪,婆把她支去烧水了:
“没出息!让老三来守。不疼能生下来吗?快了,快了!”
雨还在下着,屋檐吊线的;一声闷响,谁家的照壁泡坍了;打闪中,一头死猪从河上漂过来。人们叫了一声,就哗地闪开一条路来:大伯背着傅先生,父亲在一边撑着雨伞,气喘吁吁地赶来了。突然间,三婶就从里边着疯一样地冲出来,大喊大叫:
“生下来了!生下来了!是个小子啊!”
这时候,天已亮了,正是阴历二月初二。
二
二月二,龙抬头。家里人都说:这孩子是骑着龙头来的,要不就多孕了一个月?要不偏不倚生在这一天?要不无故二月里发了这么大的水?
夜里,雨便歇了,水也退了。村里人都搬回家去住,家家刮着院里的泥水,放一串鞭炮,就噼噼啪啪爆起炒豆儿吃。我和娘也搬回来了,我裹着红布,娘披着红头巾,像迎回来了菩萨。婆立即宣布:把她的糖罐抱到娘的炕上;家里的鸡儿下了蛋,别人便不准再吃一颗;叮咛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谁要委屈了娘,“我是不依的!”她说,“要不服的,你也去生个龙种来嘛!”
我父亲排行老四,娘是最小的一个儿媳。过门五年了,两个孩子都没留住,这在乡下,是件很丢人的事情。父亲又常在外教书,她便少不了被人白眼:哼,你能干了什么呢?连个娃娃都不会生!婆虽然疼她,但也常常对她说:
“你身子没有不舒服的吗?”
“……很好,娘。”
婆就皱皱眉说:
“你公公没福,打解放那一年下世了,咱逢上好世道了,日月盛起来……我老了,活什么呢?就活个孩子的,现在九个孙子了,再有一个就是整数了……”
娘就立即明白了,愧得脸色绯红。
婆说:
“你拾掇拾掇,过罢清明了,你到老四学校去吧。”
娘便去了。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这天日头很暖和,婆在院子里织布,娘帮她在捶布石上捶线,捶着捶着,娘心里就一阵恶心,说:
“娘,你陪我去一次卫生院吧?”
婆“啊”了一声,忙过来问:
“头疼?”
娘不言语,低了头。
“胃疼?”
娘摇摇头,耳根下冲起一点红。
婆突然叫道:
“莫是有喜了……啊,啥时感觉的?”
“前日。”
婆将娘一把搂了,夺了棒槌甩在门口,用指头点着娘的额颅骂道:
“死鬼!为什么不给我说?谁叫你擂棒槌,你是要把他擂下来吗?!”
娘开始什么也不做了,慢慢肚子凸起来,闲着没事,婆就领她去地里看看庄稼长势,到四邻人家逗逗趣儿;娘不去,婆说:
“羞什么?那脸才有盆子大哩!”
父亲请假回来,笑她是“骄傲的将军”。大婶和二婶很是不服了,曾讥笑着对父亲说:
“哼,我们生了三个四个的,也没这个福分!天下老,向着小。你媳妇怕是要生龙养凤了呀?!”
果然就生下个龙儿来了。
这天夜里,婆一定要二婶去炒三升豆儿,一家人都在中堂里坐了。除了娘和我外,四个儿子,三个媳妇,九个孙子,三个孙女,满当当地坐在婆的脚下,她让取了秤,将我称了,报说是八斤三两,就笑着说:
“好重,好重!方圆四湾十六村的,谁家生养这么重的?东村刘来顺家,说养了个四斤二两的,那真是个精光老鼠嘛!现在一家人都齐了,给咱孙子起个名吧。”
大家就起了好多,大伯说:排行第十,就叫个“十娃”。三伯二伯说:孙子辈里,都是太贵、太顺、太来、太民的,就叫个太水吧,活该今年发了这么场大水。婆却说不好,征求娘的意见,娘说:
“让他爸起吧,人家咬文嚼字的,查查字典上有什么好名儿?”
父亲便在灯下翻字典,但不是太文了,便是不顺口,婆就摇头。三婶就对婆说:
“这孩子是做婆的心蛋蛋肉,虽是做父母当伯婶的,也不一定起得好,还是老人家起一个吧。”
婆说:
“这老三家就会说话!我一个老婆子了,还能起个什么呢?”
便抓起一把炒豆儿投在嘴里,嘴里已经没了牙,嚅嚅了几下,就又囫囵吐出来,又投几颗在嘴里,说:
“这孩子排行是十,又是二月二生的,就叫十龙可好?”
大家便一哇声地叫绝。三婶说:
“妙!妙!又顺口,又有意思,活该是奔着老人家才来投胎的!明日嚷出去,村里往后生了孩子,怕都来找娘起名了!”
婆就乐得什么的,在院里烧纸敬了神,又放了一通鞭炮。
三
年景很好,发了一场水,反倒给麦田壅了一层肥泥。三月打了春,麦苗就起身了。去年村里转了高级社,当年落了好收成,家家有了二担压底粮,眼瞅着今年麦苗这般好,人心里都说不出的滋润。婆又是个极排场的人,旧社会儿女多,世道不好,一年到头在嘴上挖抓不过来,心盛也是无奈。现在,爷不在了,一家大小二十二口,她是主儿,总要在村里闯个名儿什么的,便思想为我办个热闹满月;主意拿定后,这天夜里,她把大伯和三婶叫到她的睡屋里,说:
“离了你爸,眼瞧着五年多了,家里没个外头人,咱娘儿们总使这个家没败下去,倒光景越来越走上坡路了!眼下家口这么重,我毕竟是妇道人家,手脚也一天不济一天的,全靠你两个帮我。我想给十龙过个满月,趁机会待一下亲戚朋友、街坊四邻,也不亏给你爸爸争个名儿,你们心下怎样?”
大伯是一个经世面的人,早年爷在世的时候,逃壮丁到铜川下过煤窑,后来就回来做生意,走过西安城,下过南阳川,在村里很有些头面。父亲一直在外教书,三伯又在乡政府当文书,二伯偏是个嘴头没话的下苦人,所以,家里一应外边事情,就全由大伯支应了。当下听了婆的话,便说:
“离了爸,村子里的人都说这家人是完了,咱反倒过得红火!老三、老四干公家事,都是人面前走动的人物,我是粗人,但在村里也不看谁眉高眼低的,一家大小出了门,谁个不英英武武的?十龙过满月,这么大个家,就得像个样儿,不敢叫外人耻笑了。至于待多少客,还要看家当而定,家里有多少粮食呢?”
三婶扳着指头,说:
“饭稻三担,酒稻五担,麦子大柜里还没动,瓮里的前一月后巷来借了二斗,总共算起来是四担,包谷六担,小米四斗,荞麦二斗,窖里存的五百斤洋芋一个没动,还有两坑红白萝卜,一棚白菜,蓖麻油一桶,棉籽油一桶,大宗的就这些了。”
大伯想了想说:
“不是多宽余的,这烟呀、酒的少不了几十块,柴也是个问题,还有油、盐、酱、醋的,一动弹花钱就像淌水似的……”
三婶就说:
“这好办。做几座豆腐,水菜就对付了,槽上两头猪,杀上一头,肉也有了,油也有了,烟酒花上五十元,二十斤粉条十五元,木耳黄花十元,小麻调料就算五元,再买两担引火柴四元,再计算上其他零花十元,一共是不到一百元。娘手里还有一百元,足足过一个好满月了……”
婆就叫道:
“让你管家,你倒这么清白!连我手里的钱一分一文都知道?!”
三婶撅了嘴说:
“我要是不清白,你倒骂我肉馕;如今我替你操心,倒叫你嚼起不是了!”
婆便笑起来了:
“哟,谁敢嚼你不是?这一大家人活该兴旺,就出了你这个管家子!”
三婶就说:
“瞧娘说的,要不是你给我撑腰,我能管得住谁呀?人多口杂的,你软了,他把你当软面儿捏,你硬了,就有人骂你是凶死鬼!”
这当儿,二婶给婆端了晚饭进来,听了不高兴,说:
“他三婶,孩子那日说了你一句,你别放在心上,家里你是握勺把的,谁敢不听你的?”
三婶便说:
“我哪一处不对,谁都可以说,反正好了大家好,败了大家穷,上有娘在,我只是替她少睡会儿觉罢了。”
婆问二婶:
“今黑什么饭?”
“糊汤煮洋芋。”
婆生气了:
“烧糊汤还煮什么洋芋?山吃海吃的,一顿吃了,下一顿把嘴吊起来呀?”
二婶不敢言语,放下碗,退出去走了。
大伯一直还在考虑着办满月的事,这时猛一拍手说:
“糟了,糟!”
婆问:
“什么糟了?”
大伯说:
“这硬柴火还没计算,集上买吧,一担二元,总得二十担哩!”
三婶说:
“这我也想了,坡根咱家那棵柿树,这几年不太结柿子,把那枝股砍了,一来让树聚些新枝,二来不就几千斤柴火了?”
婆便高兴了,筷子一敲碗沿说:
“这鬼管家的,倒比男人厉害,什么都想得周到!”
三婶就说:
“这是给咱十龙过满月哩,娘看他是银蛋蛋,做婶的就要看他是金蛋蛋哩!”
婆乐得呵呵地笑起来了,立即将一家人叫到一起,把过满月的事说了,又各人分了工:大伯去请亲戚朋友、街坊四邻,二伯砍伐柿树,大婶去做豆腐,二婶去淘萝卜、洗洋芋,爸爸去买烟打酒,置一揽子客货。分工末了,婆说:
“一应大大小小,他三婶经管,各人都往勤快些。这场喜事,只许办好,谁也不能给咱家丢人!”
四
三月初二,一起床,婆早早就到娘的房子来,用三尺红布将我裹了。吃罢早饭,客人就接二连三地来了,院子里毕毕剥剥不停地响着鞭炮。大伯是一直站在大门口的,进来一个,双手抱个拳,接了礼笼儿;中堂的柜盖上,就开始摆满了面鱼、面虎、挂面、灰面、红糖、项圈、三尺花布。来客们走进去,给婆道个万福,便抱着我看一番,说:
“哟,真胖!”
“一生下来就八斤三两哩!”婆说。
“真是龙种!头多大!”
“长得有些像他爸哩!”婆又说。
“他爸是教书的,将来怕要比他爸的本事更大哩!”
“真想不通,他倒投胎到我家来了。”婆再说。
“哈,都是你做老人积的德嘛!”
婆就乐得什么似的,等屋子里的客人挤得满满了,就把我抱在案桌上,在我面前摆了算盘、剪刀、镰刀、书本、笔,让我去抓。屋子里就静得没有了一丝儿声了,我眼光落到镰刀上,就“嘘儿”“嘘儿”地有人担心,婆的脸色都憋红了。但我没有摸那镰刀,目光又盯到书本前,手胡乱扬过去,婆就一把将我和书本抱起来,叫道:
“是个念书的,是个识字的!”
四周的人就一哇声地说:
“真是他爸的娃了!”
“早就知道他要抓书的!”
“瞧那模样,哪儿像是下苦的人呢?”
立即,我在无数只手上旋转着。三伯的小儿子太顺,我的第七个哥哥,挤了进来,硬要抱我,还把我脸贴在他脸上,说:
“我比他白,他是黑蛋!”
三婶一把就把他拉起来,在他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吃饭开始了。
我外婆家的都坐在我娘的房子里,三伯他们乡政府的客是高红漆桌子摆在中堂上的,院子里,就是一揽子众亲众邻了,一共坐了三十席。三婶在厨房指挥上菜端饭,大伯在外面敬烟敬酒,爸、二伯、几个大哥们穿梭往来地送上热饭煎菜,换下残汤剩水。那菜极多:红烧肉、白打肉、粉蒸肉、排骨肉、炒粉条、汤豆腐、黄豆芽、苜蓿汤、洋芋丝、萝卜片……一盘接着一盘,一碗紧着一碗。一时间,碰杯声、扒饭声、喝汤声、嚼菜声、打嗝儿声、喊声、笑声;人人嘴上闪光,头上冒汗,满院子已经热闹得不同一般了。
大伯是一直站在院中的,不停地喊:
“水酒甜饭,大家都往饱里吃哇!”
这时候,二婶在大门口和人争吵起来,接着就呼呼地关门。婆赶忙跑过来问,二婶说:
“有几个要饭的,给了一块儿馍,却还不走,说是要道喜,道什么喜?还不是为了吃饭!”
婆就骂道:
“你关了门挡喜呀?难得人来道喜,吃咱一碗甜饭,就把咱吃穷了?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坯子!”
二婶娘家在大深山里,最见不得人说她没见过世面,知道婆婆生了大气,不敢作声,当着众人面羞得脸红,将门打开了,便钻进厨房再不出来了。
眼看着客人们都吃得八九成了,三婶才走回房里,洗了脸,梳了头,走到娘的房里,一把抱了我,对我的外婆家客人打招呼:
“都要吃好!吃得越多了,我龙娃才越有福分!”
姨就端过一杯酒说:
“她三婶,亏你忙了一天,敬你一杯吧!”
三婶说:
“好,我就替我龙娃喝一杯!”
热酒下肚,脸便红起来,她越发来精神了,敬这个,让那个,惹得一房子的笑声。末了,走到院里,把大婶拉到一边,说:
“你坐在大门口去吧,过会儿散席,人多手杂的,注意村里哪个不争气的揣了什么走。”
五
过了满月,父亲就打整行李要返校了。在家一个多月里,他似乎是家里显得最清闲的人,一应粗细轻重之活,婆都不让他去做,专让他在娘的房里伺候什么的。但他对我很淡漠,对娘也没有多少话说。一坐下来,就抱着厚厚的书看,看完了,就在娘房子那头的木床上睡觉。这床是临时支的,他说他一个人睡惯了,和孩子睡在一块儿,他会失眠的。我生下头几天,娘让他去涮尿布,他不到村中那塘里去涮,总是盛在盆子里,跑上一里路到河边去。后来婆就不让他涮了,让太运、太顺或淑叶、淑枝姊妹去涮。他也便乐个自在,整天里在婆房子里坐坐了,就回到娘屋里看书。要不,就坐下来写信。他已经收到了三封信,发走了四封信,但还在写,娘就说:
“你给谁写信呀?有多少紧贴话儿说不完的?”
“给学校领导。”
娘不言语了。她虽然是农民,又不识字,但知道丈夫工作一定很好,要不,领导怎么不停地来信呢?
过满月这天里,客人们都走了,娘显得很高兴,在灯下逗着我玩,见爸又坐在那里看书了,就说:
“那书好看吗?”
“好看。”
“有咱十龙好看吗?”
“咳,该怎么对你说呢?”爸别转了身,“你们这些人,就知道你的孩子,孩子!”
娘便一把夺了他的书,把我塞在他的怀里说:
“是我的孩子?孩子不是你的?你生娃不管娃,你也该好好看看他嘛!”
爸只好把我抱起来,但像是抱着个冬瓜,不逗,也不亲;我在怀里哇哇地哭了。娘又抱起来,说:
“来,让娘抱,你爸那四个兜儿的,别给人家尿湿了!”
爸说:
“好了,天不早了,睡吧。”
就走到自己的床前,从枕头下取出信来,看了一遍,脱衣展被睡下了。
娘也上了炕,吹了灯,睡到半夜了,娘突然哽哽咽咽哭起来。爸说:
“你这是怎么啦,深更半夜的,叫别人听见了,还以为咱们吵了嘴了。”
娘说:
“让外人都听见就好了!”
爸不言语了,黑夜中点了烟在那里明灭着抽。
“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们娘俩儿。你常年在外,我在家里活受寡。我总想,这是我的错,我没本事,给你生不出个儿来,就天天盼儿。眼下盼来了,我总算对得起你了,你还是老样,不和我多说一句话,天一黑,你睡得呼呼噜噜……”
娘说着,就又哭了。
“你这女人……”爸便从那边走过来,睡在炕上。“我哪有什么话来对你说呢?睡吧,睡吧,睡在你跟前了,你就滋润,你真会折磨人,你这号女人……”
娘就止了哭声,问一声:
“你说,你爱我吗?”
“爱。”
爸说着,便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娘生气就把爸的那张木床拆了,在枕头底下看见了那一沓信,她不知道这信里有什么东西,丈夫总是睡前像温课一样地看。她掏出信,却发现里边夹一张照片:一个年纪很轻的女人,烫着发,穿着钉着大圆扣子的列宁服,侧着头,笑吟吟地坐在公园的石凳子上吧?娘看过一眼,心里就咚咚地跳,手脚也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末了“啊”的一声,就坐在那床上一动不动地了。足足呆了一个时辰,她就一捂脸走到三婶的房子,一头扑在三婶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了。
三婶正在那里抓了一大把黄豆,在炕上放着字儿计算过满月花了多少,又收了多少财礼。见娘这般模样,赶忙问怎么回事?娘哭着说了,三婶说:
“这他不敢,这他怎么敢?老四怎么是那种人?你敢情是看眼花了!”
娘就说:
“你没看他平日的脸色吗?原来他是有外欢了!他不念惜我了,也该想想孩子啊!这个不要脸的臭女人,天打雷击的……”
三婶也吃了一惊,但立即给娘擦了脸,说:
“真有这事,我来训他,你千万不要声张,免得传出去,引外人耻笑。你好生回去看十龙吧。我对付他,谁也从你手里夺不去他的!”
娘只好又回来,抱着我哭,中午饭也没吃,也不给我喂奶。三婶又来陪着叹气了一会儿,就把那些信和照片烧了。
中午,爸从公社邮局回来,手里拿着一封信,三婶就笑着说:
“老四,你床头那些破纸的,该没什么用处吧?刚才做饭,没啥引火的,我拿着烧了。”
爸就急出一头汗来,说:
“那是我的信呀!”
“什么金贵信?看你急得这个样儿?!”
“是学校领导写的。”
“哎呀!这可不得了!全怪我不认字呀,也不知道里边装了什么,一把抓来就点着烧了。”
爸不再说什么,就回到房里,骂娘不好生看管他的东西,娘趁机就又哭起来。爸说:他又收到信了,学校催他赶快回去。又把这话给婆也说了。
婆不明白他为啥走得这么急,就让三婶帮着打整行李。三婶便偷偷把照片之事说了,婆当下黑了脸:
“这几年,一家大大小小拨拉这个家,倒把他放松了!他敢这样,看我打断他的腿!我们家几辈可没出过这等人,不让他去教书了!”
三婶说:
“这事万万不可传出去,对家不好,对老四也不好。不如就让他走吧,暗暗敲敲他。”
婆说:
“他一走兔儿登天,把什么都会忘了,男人们啥都硬,就是招不住野婊子勾引的。”
三婶说:
“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不知行不行。老四常年在外,十龙妈不在身边,又挣那么多钱,一个人花不了,少不得会惹花拈草的。如今他大伯的太来和我们的太顺上完高小了,明年就要上中学,中学离咱村十五里,又不方便,干脆让老四把两个孩子带去经管上学。一来带了孩子,二来他身边又有了眼睛。往后让十龙娘多去几趟,他心会慢慢收回来的,娘,你说对吗?”
婆想了想,就笑了:
“我真是离不得你哟!赶明日我下世了,一定也勾了你陪我去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