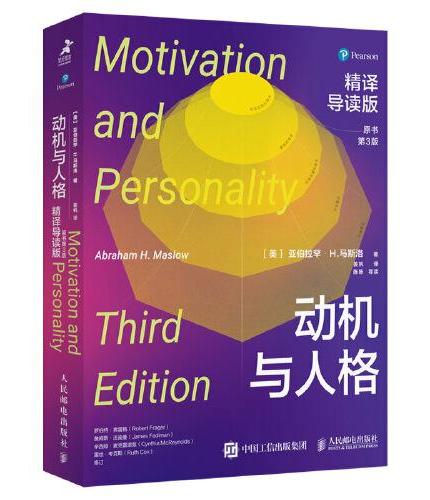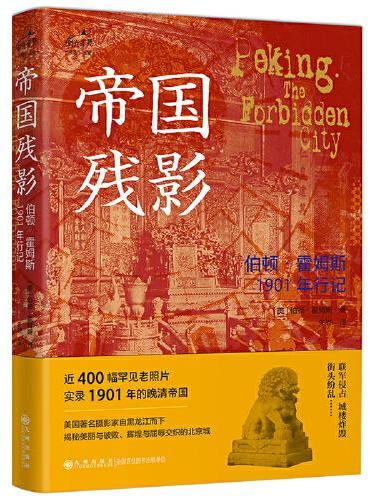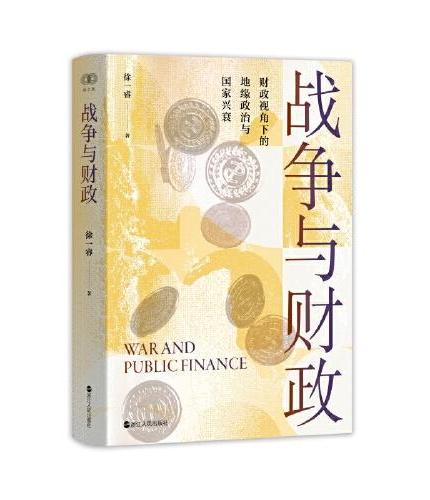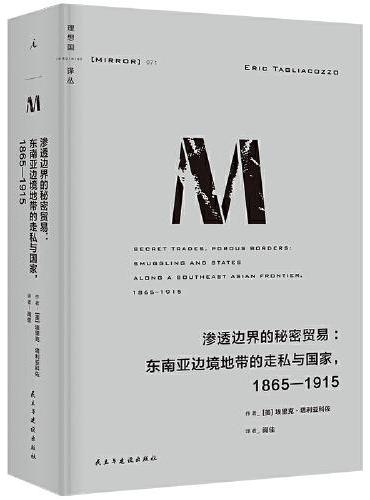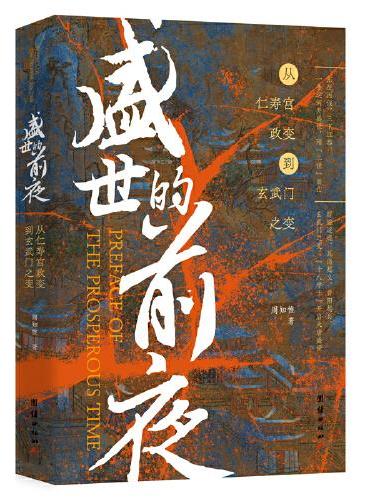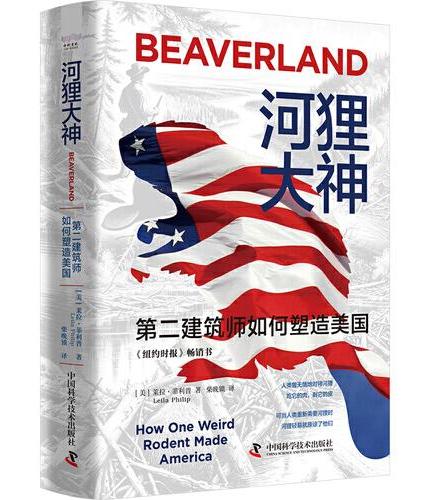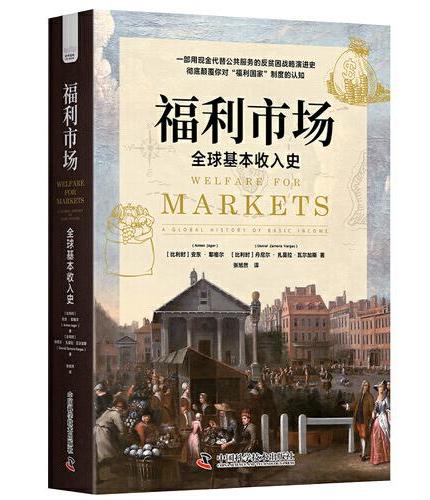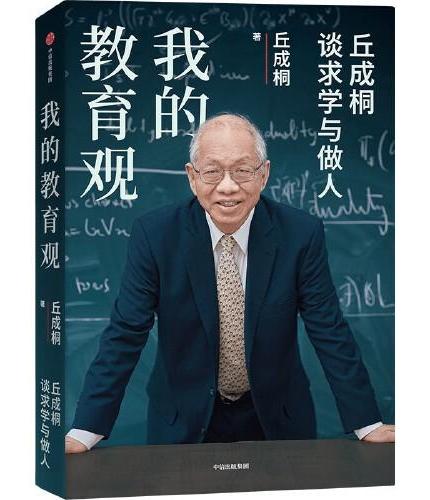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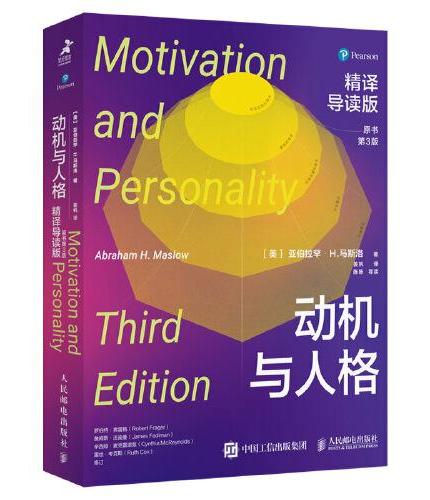
《
动机与人格:精译导读版(原书第3版)
》
售價:NT$
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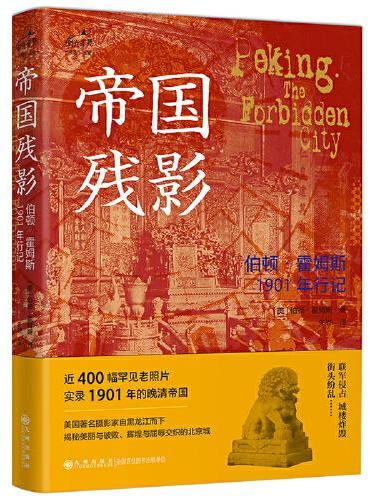
《
帝国残影:伯顿·霍姆斯1901年行记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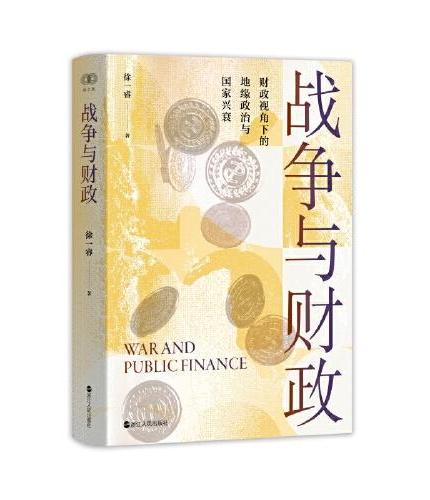
《
战争与财政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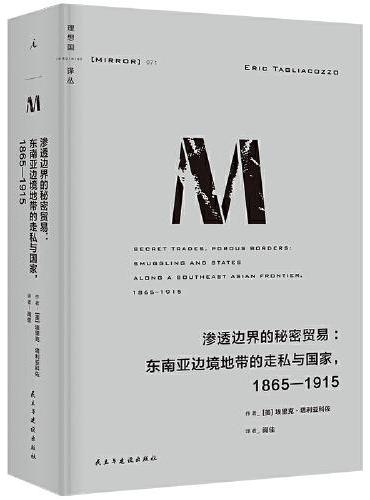
《
理想国译丛071: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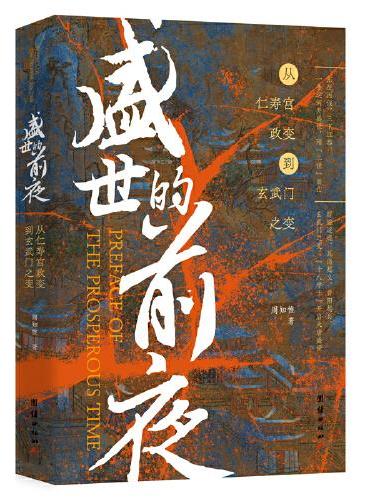
《
盛世的前夜:从仁寿宫政变到玄武门之变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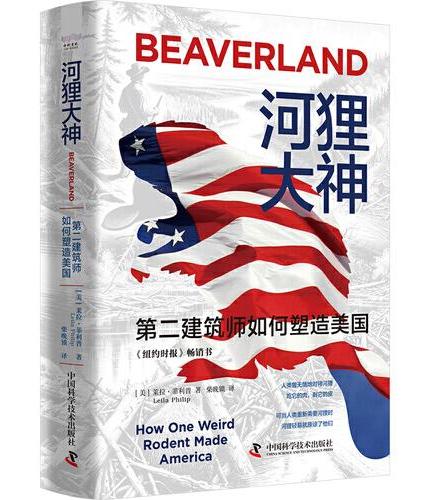
《
河狸大神:第二建筑师如何塑造美国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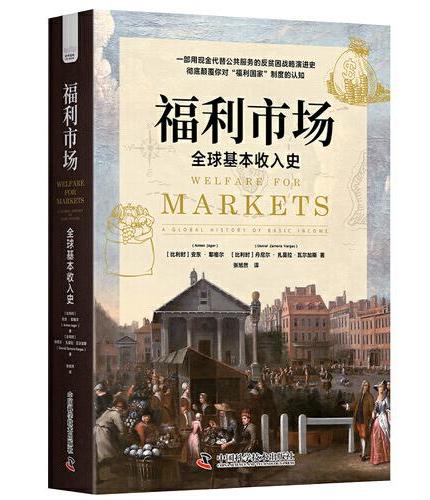
《
福利市场 : 全球基本收入史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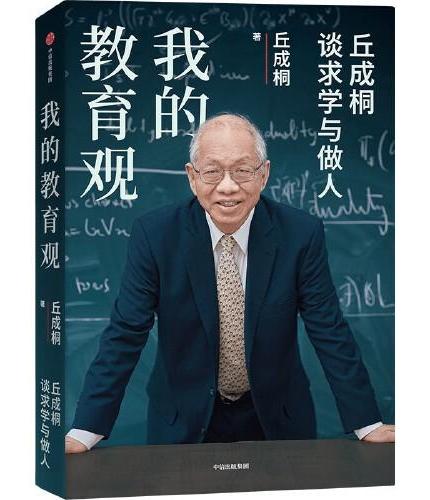
《
我的教育观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的代表作
加缪、萨特的精神导师,法国文坛无法越过的作家
选择“欲望”,还是忠于“道德”,仔细品读《窄门》,你便读懂了纪德的一生
随书附《田园交响曲》《浪子归来》、译者序言及纪德生平和创作年表
在我的理想和我的栖息地之间,隔着我整整一生。
卖点
1、加缪、萨特的精神导师,法国文坛无法越过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的代表作。选择“欲望”,还是忠于“道德”,仔细品读《窄门》,你便读懂了纪德的一生。
余华阅读《窄门》时盛赞:“毕生都想写出一部这样的书。”
2、拥抱一切能抓到的东西,强烈的欲望赋予我们支配一切的权力——这是人性使然,也是纪德在作品中努力想告知我们的事情。了解了追求快乐的痛苦历程,也就更容易理解纪德的这段话:“对人来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即便作品中描写的是痛苦,是矛盾,但纪德希望我们去追寻的,归根结底,还是快乐!
快乐、生活、幸福、爱……这些在纪德笔下全是同义词、主题词,构成纪德作品的鲜明的生命线。
3、语言简洁生动,剖析爱情及人生矛盾深刻而隽永——
#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因为宽门和宽路通向
|
| 內容簡介: |
究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爱情,即使毫无希望,也可以将它长久地保持在心中;
即使生活之心每天从它上面吹过,也始终无法把它吹灭?-----------------------------------------
在《窄门》中,纪德将爱情中的神秘主义体验推向极致,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纯洁炙热、却又含着无边孤寂和辛酸滋味的爱情故事:杰罗姆与表姐阿莉莎自小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也得到了周围人的支持,他们以全部的纯真与热情,一心只想为对方变成更好的人。但爱得愈深,愈不能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不完美,尤其是当阿莉莎目睹了母亲与他人私奔、妹妹过着平淡而又无爱情可言的婚姻生活后,愈发不能忍受任何阻碍通往完美爱德的崎岖,她甚至将自己的存在看作是杰罗姆穿越“窄门”的最大障碍。为了让爱人更加自由地到达彼岸、获得比爱情更好的东西,她选择了逃离,最终孤独死去。
|
| 關於作者: |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广泛关注宗教、爱情、家庭、政治等各类问题,热烈歌吟解放与自由,是现代西方文学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其著述颇多,作品兼容并蓄,风格迥异,包括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荒诞主义。主要作品有《窄门》《背德者》《人间食粮》《田园交响曲》等。
李玉民,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家。从事法国文学翻译二十余年,译著五十多种。主要译作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等;主编《纪德文集》(五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十卷)。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编选主译的《缪寒精选集》获2000年国家图书奖。
|
| 目錄:
|
译者序:自相矛盾的魅力 001
窄门 005
田园交响曲 135
浪子归来 189
纪德生平和创作年表 213
|
| 內容試閱:
|
窄门
“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第一章
我这里讲的一段经历,别人可能会写成一部书,而我倾尽全力去度过,耗掉了自己的特质,就只能极其简单地记下我的回忆。这些往事有时显得支离破碎,但我绝不想虚构点儿什么来补缀或通连——气力花在涂饰上,反而会妨害我讲述时所期望得到的最后的乐趣。
丧父那年我还不满十二岁,母亲觉得在父亲生前行医的勒阿弗尔已无牵挂,便决定带我住到巴黎,好让我以更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她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一小套房间,弗洛拉·阿什布通小姐也搬来同住。这位小姐没有家人了,她当初是我母亲的小学教师,后来陪伴我母亲,不久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两个女人中间,她们的神情都同样温柔而忧伤,在我的眼中只能穿着丧服。且说有一天,想来该是我父亲去世很久了,我看见母亲便帽上的饰带由黑色换成淡紫色,便惊讶地嚷了一句:
“噢!妈妈!你戴这颜色太难看了!”
第二天,她又换上了黑饰带。
我的体格单薄。母亲和阿什布通小姐百般呵护,生怕我累着,幸亏我确实喜欢学习,她们才没有把我培养成个小懒蛋。一到气候宜人的季节,她们便认为我脸色变得苍白,应当离开城市。因而一进入六月中旬,我们就动身,前往勒阿弗尔郊区的芬格斯玛尔田庄,舅父布科兰住在那里,每年夏天都接待我们。
布科兰家的花园不是很大,也不怎么美观,比起诺曼底其他花园,并没有什么特色。房子是白色三层小楼,类似十九世纪许多乡居农舍。小楼坐西朝东,对着花园,前后两面各开了二十来扇大窗户,两侧则是死墙。窗户镶着小方块玻璃,有些是新换的,显得特别明亮,而四周的旧玻璃却呈现黯淡的绿色,有些玻璃还有瑕疵,我们的长辈称之为“气泡”。隔着玻璃看,树木歪七扭八,邮递员经过时,身子会突然隆起个大包。
花园呈长方形,四周砌了围墙。房子前面,一片相当大的草坪由绿荫遮着,周围有一条砂石小路。这一侧的围墙矮下来,能望见围着花园的田庄大院,能望见大院的边界,按当地规矩的一条山毛榉林荫道。
小楼背向的西面,花园则更加宽展。靠南墙有一条花径,由墙下的葡萄牙月桂树和几棵大树的厚厚屏障遮护,受不着海风的侵袭。沿北墙也有一条花径,隐没在茂密的树丛里,我的表姐妹管它叫“黑色小道”,一到黄昏就不敢贸然走过去。顺着两条小径走下几个台阶,便到了花园的延续部分——菜园了。菜园边的那堵围墙上开了一个小暗门,墙外有一片矮树林,正是左右两边的山毛榉林荫路的交汇点。站在西面的台阶上,目光越过矮树林,能望见那片高地,欣赏高地上长的庄稼。目光再移向天边,能望见不远处村子里的教堂,在暮晚风清的时候,还能望见村子几户人家的炊烟。
在晴朗的夏日黄昏,我们吃过饭,便到“下花园”去,出了小暗门,走到能够俯瞰周围的一段高高的林荫路。到了那里,舅父、母亲和阿什布通小姐,便在废弃的泥炭岩矿场的草棚旁边坐下。在我们眼前,小山谷雾气弥漫,稍远的树林上空染成金黄色。继而,暮色渐浓,我们在花园里还流连忘返。舅母几乎从不和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每次回来,总能看见她待在客厅里……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晚上的活动就到此为止,不过,我们回到卧室还往往看书,过了一阵就听见大人们也上楼休息了。
一天的时光,除了去花园之外,我们就在学习室里度过。这间屋原是舅父的书房,就摆了几张课桌。我和表弟罗贝尔并排坐着学习,朱丽叶和阿莉莎坐在我们后面。阿莉莎比我大两岁,朱丽叶比我小一岁。我们四人当中,数罗贝尔年龄最小。
我打算在这里写的,并不是我最初的记忆,但是唯有这些记忆同这个故事相关联。可以说,这个故事确实是在父亲去世那年开始的。我天生敏感,再受到服丧的强烈刺激,或者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哀伤,至少是目睹母亲的哀伤所受的强烈刺激,也许就容易产生新的激情:我小小年纪就成熟了。那年我们又去芬格斯玛尔田庄时,我看朱丽叶和罗贝尔就觉得更小了,而又见到阿莉莎就猛然明白,我们二人不再是孩子了。
不错,正是父亲去世的那年,我们刚到田庄时,母亲同阿什布通小姐的一次谈话证实我没有记错。她正同女友在屋里说话,我不经意间闯了进去,听见她们在谈论我的舅母。母亲特别气愤,说舅母没有服丧或者已经脱下丧服。(老实说,布科兰舅母穿黑衣裙,同母亲穿浅色衣裙一样,我都觉得难以想象。)我还记得,我们到达的那天,吕茜尔·布科兰穿着一件薄纱衣裙。阿什布通小姐一贯是个和事婆,她极力劝解我母亲,还战战兢兢地表明:“不管怎么说,白色也是服丧嘛。”
“那她搭在肩上的红纱巾呢,您也称为‘丧服’吗?弗洛拉,您别气我啦!”母亲嚷道。
只有在放假那几个月,我才能见到舅母。无疑是夏天炎热的缘故,我见她总穿着开得很低的薄薄的衬衫。母亲看不惯她披着火红的纱巾,见她袒胸露臂尤为气愤。
吕茜尔·布科兰长得非常漂亮。从我保存的她的一小幅画像,能看出她当年的美貌:她显得特别年轻,简直就像身边两个女儿的姐姐。她按照习惯的姿势侧身坐着,左手托着微倾的头,纤指挨近唇边俏皮地弯曲着。一个粗眼发网,兜住半泻在后颈上的那头卷曲的浓发。衬衫大开领,露出一条宽松的黑丝绒带,吊着一个意大利镶嵌画饰物。黑丝绒腰带绾了一个飘动的大花结,一顶宽边软草帽由帽带挂在椅背上,这一切都给她平添了几分稚气。她的右手垂下,拿着一本合拢的书。
吕茜尔·布科兰是克里奥尔人,她没见过或者是很早就失去了父母。我母亲后来告诉我,沃蒂埃牧师夫妇当时还未生子女,便收养了这个弃女或孤儿。不久,他们举家离开马尔提尼岛,带着孩子迁到勒阿弗尔,和布科兰家同住在一个城市,两家人交往便密切起来。我舅父当时在国外一家银行当职员,三年后才回家,一见到小吕茜尔便爱上她,立刻求婚,惹得他父母和我母亲十分伤心。那年吕茜尔十六岁。沃蒂埃太太收养她之后,生了两个孩子,她发现养女的性情日益古怪,便开始担心会影响亲生的子女;再说家庭收入也微薄……这些全是母亲告诉我的,她是要让我明白,沃蒂埃他们为什么会欣然接受她兄弟的求婚。此外我推测,他们也开始为长成姑娘的吕茜尔操心了。我相当了解勒阿弗尔的社会风气,不难想象那里的人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个十分迷人的姑娘。后来,我认识了沃蒂埃牧师,觉得他为人和善,既勤谨又天真,对付阴谋诡计毫无办法,面对邪恶更是束手无策——这个大好人当时肯定陷入困境了。至于沃蒂埃太太,我就无从说起了。她生第四胎时因难产死了,而这个孩子与我年龄相仿,后来还成为我的好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