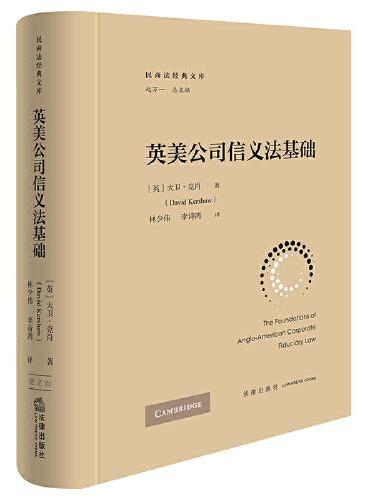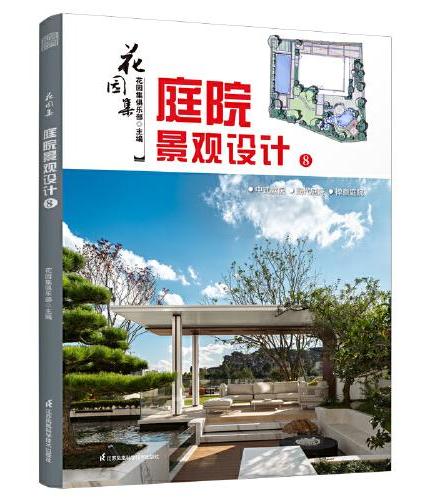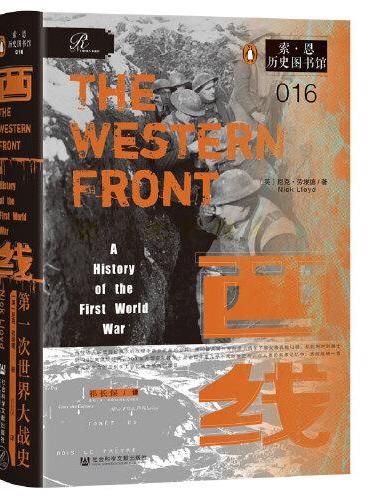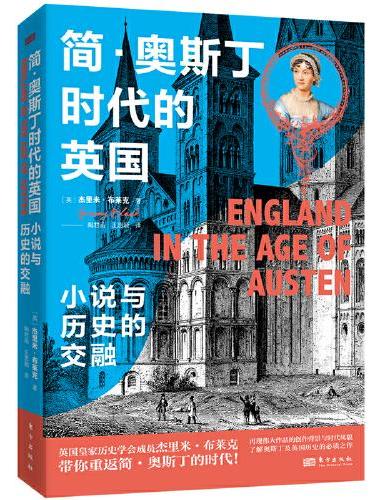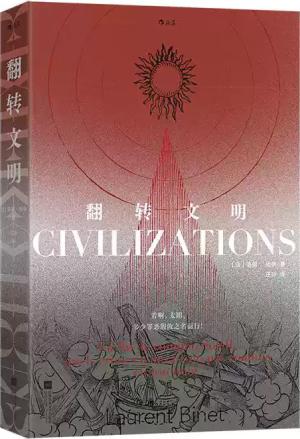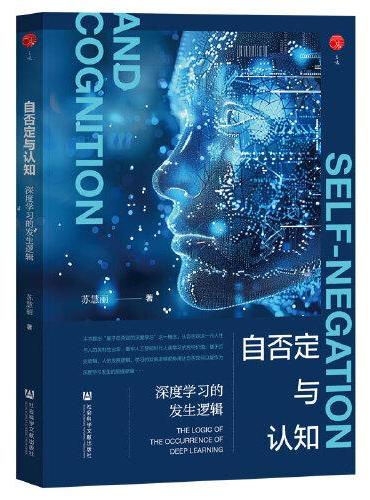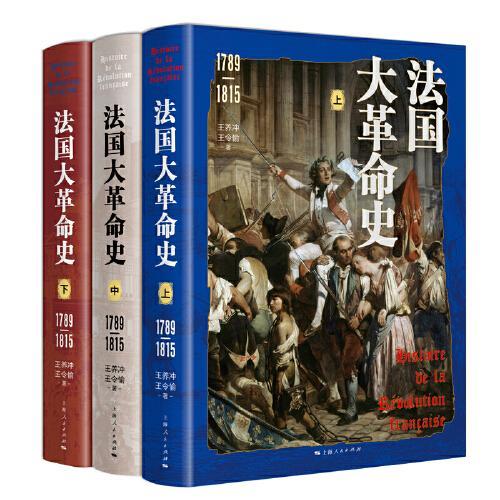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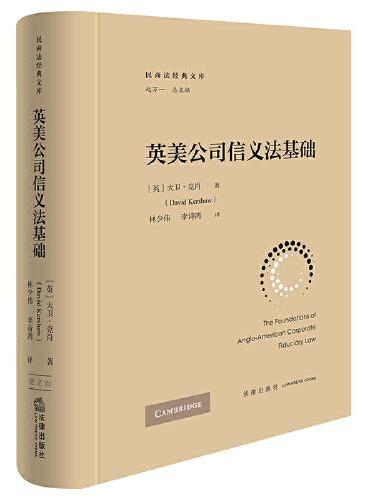
《
英美公司信义法基础
》
售價:NT$
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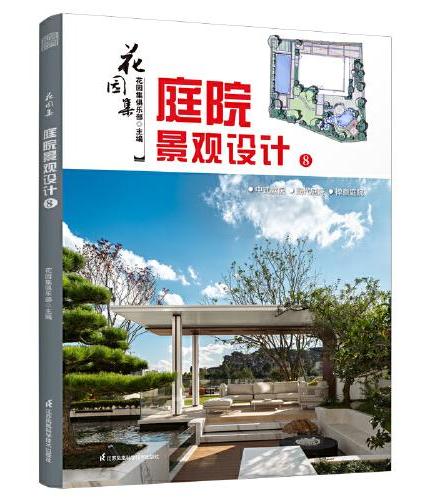
《
花园集 庭院景观设计8
》
售價:NT$
356.0

《
嫦娥四号科学研究创新成果
》
售價:NT$
45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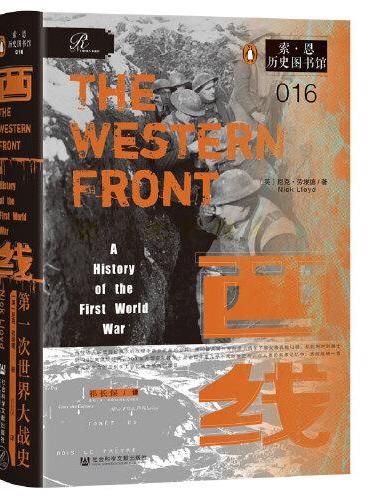
《
索恩丛书·西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
售價:NT$
7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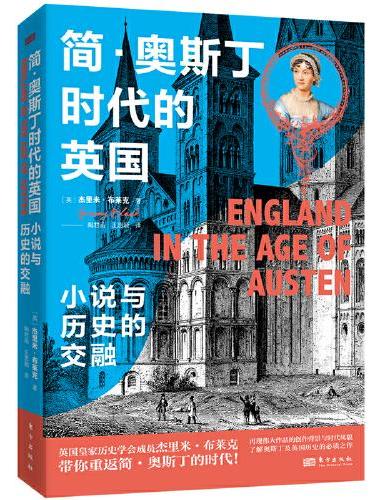
《
简·奥斯丁时代的英国:小说与历史的交融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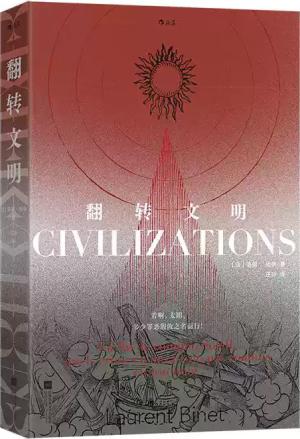
《
翻转文明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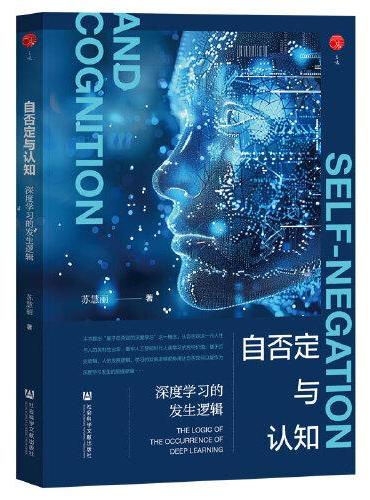
《
自否定与认知:深度学习的发生逻辑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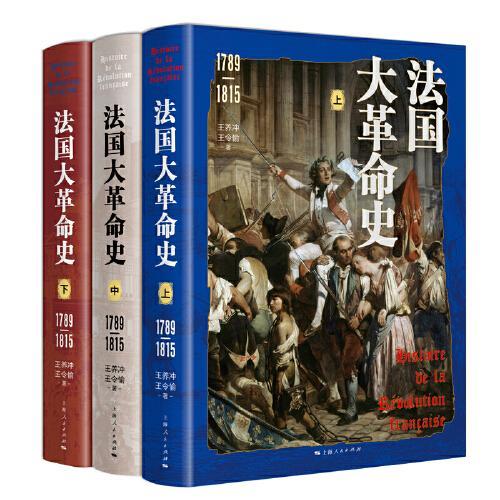
《
法国大革命史(1789-1815)(全三册)
》
售價:NT$
1520.0
|
| 編輯推薦: |
★ 雷蒙德·卡佛推崇的美国当代作家:“我很尊敬理查德·福特,甚至希望能成为他,因为他正是我所缺乏的一切。”
★第一位以同一部作品荣获“福克纳奖”&“普利策小说奖”两项文学大奖的作家
★《千百种罪》收录十个在微妙幽暗的灰色地带展开的故事,讲述生活中的失败者,那些“身处悬崖边缘,等待着纵身一跃”的人,探讨在婚姻与道德夹缝中的中产阶级男女的生活
★理查德·福特“迄今最令人坐立不安的短篇小说集”,揭示出男女亲密关系、爱情和婚姻失败背后,人生的种种荒诞、尴尬、痛苦和绝望。
|
| 內容簡介: |
“他们身处边缘,等待着纵身一跃。”
普利策小说奖、美国笔会/福克纳奖、马拉默德短篇小说奖得主
理查德·福特“迄今最令人坐立不安的短篇小说集”
本书是美国当代作家理查德·福特出版于二〇〇二年的短篇小说集,讲述了十个“令人坐立不安”的故事:一对从事法律工作的夫妻去缅因州度周末,试图找回他们早已在婚姻生活中消失的激情;一个春天的夜晚,妻子在开车赴宴途中,向丈夫坦白她与当晚宴会的男主人有染;两个分别已婚的男女房产经纪人,在行业会议中偶遇出轨,他们心血来潮一起去看附近的自然奇观大峡谷,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作者深刻、坦率地揭示出男女亲密关系、爱情和婚姻失败背后,人生的种种荒诞、尴尬、痛苦和绝望。
|
| 關於作者: |
理查德·福特
(1944— )
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自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初中教师,后在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读了一学期,即转学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攻读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师从著名作家奥克利·霍尔和E.L.多克托罗。
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一片心》。相继在大学任教、为体育杂志撰稿。一九八六年,出版长篇小说《体育记者》,第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石泉城》,这两部作品令其在美国文坛站稳了脚跟,和雷蒙德·卡佛、托拜厄斯·沃尔夫等人一起被称为“肮脏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一九九五出版《体育记者》的续作《独立日》,首次以同一部作品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福克纳奖两项文学大奖。目前已出版近十部中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并选编了多部美国短篇小说选,作品被翻译成近三十种文字。二〇一六年,获颁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二〇二三年,出版“弗兰克·巴斯科姆”系列小说最后一本《成为我的人》(Be Me)。
|
| 目錄:
|
隐私
好时光
呼唤
重逢
小狗
护雏
视线之外
支配
宽容
深渊
|
| 內容試閱:
|
视线之外
开车去尼克尔森家晚餐的路上——这是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第一次——玛乔丽·里夫斯告诉丈夫史蒂芬·里夫斯,一年前她和乔治·尼克尔森(他们要赴宴的主人)有过一段婚外情,但现一切都结束了,她希望他——史蒂芬——不要为这事太生气,能够照常生活。
说这事的时候,他们正沿着奎克大桥路行驶,离开了帕金斯大森林路,开始接近香尼普塞特水库,水库隐藏在暗影里,在晚春的暮光中静谧地映射出来。右边是茂密的小树,山毛榉和树叶青嫩的桤木树苗,地面潮湿松软。青蛙在有水的低地里叫唤着。他们离苹果园小道的那个转弯口还有一英里。
听到这个消息后,史蒂芬开始慢慢地、非常小心地驾驶他们的车——一辆有着黄色头灯的棕褐色奔驰休旅车——离开奎克大桥路,开上了杂草丛生的潮湿的路肩,这样他可以在继续前行之前妥善地消化这些信息。
他们非常年轻。史蒂芬·里夫斯二十八岁。玛乔丽·里夫斯小一岁。他们并不富有,但他们比较幸运。史蒂芬在帕克—威尔斯公司工作,那是家为汽车工业服务的小型预加工企业,他在其中一个大部门里的小部门当头,在那里任何对聚合流程的突然改动,甚至是可能要改动的传闻,都会颠覆整个重要的需求模式,从而影响许多重要客户职位的风险度和舒适度。他的工作就是关注各种深奥难懂的石化行业刊物,参加技术研讨会,飞到各地参加供应商大会,然后撰写详细的状况报告,以便他的上司们随时了解市场动态。他曾经获得贝兹学院的奖学金,主修化学,是缅因州佩马奎德市一个贫穷但正直的捕虾家庭的独生子,并且表现优异。他在帕克—威尔斯的老板们都喜欢他,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还看见了他们从未真正拥有的品质——金发瘦弱的毛头小子很容易在工作中受骗上当,但是他的谨慎、机敏和不折不扣的韧性支撑着他。他很机灵。这是他在这家公司工作的第七年——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和玛乔丽已经结婚两年,没有孩子。这辆车是两年前的圣诞奖金。
车缓缓停下后,史蒂芬让发动机空转着坐了一分钟,橙红色的仪表盘灯光照亮了他的脸。收音机一直在轻柔地播放——最后一条新闻,然后插进一段法国圆号。对任何信号都没有什么反应,他关掉了收音机,同时关掉了点火装置,只让车头灯照耀着空旷无人的乡间小路。车窗开着,让春天的新鲜空气进来,当发动机的声音停止时,夜晚的环境声在等待着。蛙声。几码外翅膀拍打灌木丛的声音。某样东西掉进水里的声音。小树苗丛后面就是西面,透过昏暗的树干看,那里的天空仍然因白日的光线泛着亮黄色,而奎克大桥路这边已经接近全黑了。
玛乔丽说刚才那番话时,一直目视前方,看着车头灯在黑暗中打出来的一条光的小路。也许她看了史蒂芬一眼,但话说完后,她就把双手放在腿上,继续看着前方。她是个漂亮的、没有坚定信念的金发姑娘,有着娇小端庄的五官——娇小的鼻子,娇小的耳朵,娇小的下巴,尽管笑起来时嘴唇会变得令人吃惊的丰润,她对所有人都这样笑。她喜欢在派对上喝得微醺,压低嗓音,坐在花纹图案的矮凳或者粗木桌面上,拿着一杯什么酒,露出过多的大腿或不恰当地展示她小小的胸部。她在印第安纳长大,在普渡大学学习艺术。史蒂芬是在纽约的一个派对上认识她的,当时她在一家专为某大型玩具制造商制作儿童广告的公司工作。他喜欢她的短发、柔弱娇小的五官、半透明的肌肤和轻微沙哑的嗓音,这嗓音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成熟,但也让她自以为真的很成熟。在他们位于哈特福德东部的社区,认识玛乔丽的女人都认为她是个荡妇,和可爱的史蒂芬·里夫斯的婚姻维持不了太久。他的第二任妻子才会真正适合他。玛乔丽只是开胃品。
然而,玛乔丽并不这么想自己,她只不过喜欢男人,和男人在一起让她感到快乐和自信,并认为史蒂芬会没有意见,从长远来看有一个漂亮热情、无人能轻易归类的妻子对他的事业会有帮助。为了让自己与众不同并对社区产生兴趣,她去哈特福德的一家儿童中心当义工,那里全是黑人。正是在哈特福德,她有机会遇见乔治·尼克尔森并在红屋顶旅馆跟他睡了,直到他们两个都厌倦为止。在她看来,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已经有一年没有发生了。
有两分钟,也可能是五分钟,他们在这凛冽的傍晚坐在奎克大桥路的路肩,任由春天的噪声从车窗里飘进又飘出,玛乔丽什么也没说,史蒂芬也什么都没说,尽管他意识到自己不说话是因为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意识到,失语意味着在听到刚才的事情后,脑海中似乎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说。他知道他是个新手——在某些方面还是个孩子——但是他不蠢。在贝兹学院,他上过苏多夫斯基博士讲解《尤利西斯》的课程,结束的时候对讽刺和幽默有了新的认识,相信真正的知识是一个精神历程,是一种追求,而不是储存干巴巴的事实——就像自由,你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充分体验到。他也打过冰球,知道知识和攻击性是一对微妙的、令人吃惊的、不寻常的组合。他在帕克—威尔斯公司实践着这两样。
但是在这阴冷沉重的半明半暗中,有那么短暂而恐惧的一瞬间,就在他开始体验到失语时,他进入或者至少是几乎陷入了一种虚弱的恍惚状态,他开始恐惧自己也许再也说不出话来;某件事(工作疲劳、震惊、玛乔丽的坦白带来的失望)在那一刻让他脱离现实、逃离当下,事实上他开始失去理智,变得疯狂,有可能会开始像黑猩猩一样胡言乱语,或者只是靠在带坐垫的门上慢慢倒向一边,很久很久——几个月——都不说话,然后只有借助药物才能说出一些密码般的简单语音,最终只能在达马里斯科塔母亲家的照顾下度过余生。一个可怕的念头。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和理智——他突然蹦出一个词,他能够在这辆散发着香气和微光的车里说出的任何一个词,他妻子显然在期待他对她不愉快的坦白有所表示。
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出来的这个词——确切地说是个短语——是“地面杂波”。他在他们穿着打扮准备出发时从电视天气预报里听到的一个说法。
“嗯?”玛乔丽说,“那是什么?”她把那张漂亮、娇小的脸转向他,她的珍珠耳环正好被某个未知的光源照亮。她穿着一件绿色的酒会小礼服、一双绿色的缎面鞋,露出她纤细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脚踝和苗条的棕色小腿。头上戴着两个绿色的小蝴蝶结。她闻上去甜甜的。“我知道这不是你想听到的,史蒂芬,”她说道,“但是我觉得应该在我们到达乔治家之前告诉你。我是说尼克尔森家。一切都结束了。绝不会再发生了。我向你保证。没人会提这件事。去年搬家的时候我昏了头。我很抱歉。”她把手指聚拢成塔尖形状,好像说这些话时她在非常用力地集中精神。但是现在她又平静地把手放到薄荷绿的大腿上。她特意为今晚去尼克尔森家赴宴买的裙子。她认为乔治会喜欢,史蒂芬也会喜欢。她转过头在车里发出一声轻轻的但仍可察觉的叹息。就在这时,车头灯自动熄灭了。
乔治·尼克尔森是一名律师,毕业于耶鲁大学,身材高大,胸肌发达,汗毛浓密,喜欢打壁球,曾驾驶自己的欣克利61型游艇驶出埃塞克斯,五十岁就从哈特福德收入丰厚的诉讼律师业务中退出,把更多时间投入壁球运动和高水平滑雪上。乔治是史蒂芬公司一个高级合伙人的大学室友,在里夫斯夫妇新婚搬到这个社区时,他“收养”了他们。他们在康涅狄格州的前六个月里,每个星期六玛乔丽都会和乔治的妻子帕西一起去圣公会旧货商店做义工。乔治·尼克尔森曾向史蒂芬回忆起一个难忘的、丰富多彩的夏天,他和几个健壮老水手在缅因州马提尼克斯一起捕捉龙虾。后来,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前臂上有一个褪色的文身,上面文着锚、球和锁链。但是后来,他睡了史蒂芬的老婆。
终于说了点什么,即使毫无意义,史蒂芬感到一丝阴郁、泄气的解脱,坐在这沉默的车里,坐在玛乔丽身旁,而后者仍然面朝前方。在他复苏的意识里,有两个想法开始打架。一个想法当然是由他对乔治·尼克尔森的印象所引起的。他认为乔治·尼克尔森是个混蛋,但也是个强悍的人物,扫除一切障碍得到了今天的一切。一想到乔治他总会想起马提尼克斯岛的故事,然后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自己的父亲和他一起在孟希根岛的某片海边拖拽捕虾网的场景。诱饵的臭味,晚春时节海浪的翻滚,迷雾中若隐若现的、树木成行的海岸那令人心安的单调。想到这一连串的景象总会让他隐约地钦佩乔治·尼克尔森,怪异的是,也让他认为自己现在还喜欢乔治,尽管发生了这一切。
与之打架的另一个想法是,玛乔丽性格中的一部分总让她坦白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但最终他相信都不是真的:在索格塔克做过一个夏天的站街妓女;读大学时跳过脱衣舞;尝试过海洛因;在她的家乡印第安纳的戈申市和高中男友一起参与过持枪抢劫。她在讲述这些不着边际的故事时会变得心不在焉,摇着头,就好像它们都是真的。而现在,虽然他并不特别认为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个变得真实了,但他的确意识到,他根本不了解他的妻子;事实上,了解另一个人的整个概念——信任、亲密、婚姻本身——虽然不完全是谎言,因为它曾经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即使只是作为一个想法(在他父母的人生中,即使只是勉强存在),也是完全过时的、不再起作用的,是另一个时代的特征,但不幸的是现在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认识一个女孩,坠入爱河,结婚,搬到康涅狄格州,买一栋该死的房子,和她一起开始生活,然后你就以为自己真的了解她——这最后一部分完全是虚构,让前面的一切都成了笑话。玛乔丽也许真的是个妓女,或者抢劫过便利店,对人开过枪,就他对她的了解而言。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对她说起这些想法,就像现在这样坐在他身旁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她要么一个字都听不懂,要么干脆简单地说:“好吧,没关系。”当人们谈论底线的时候,史蒂芬·里夫斯认为,他们不是在谈论钱,而是在谈论这意味着什么,这种致命的无知。钱——亏钱,挣钱,花钱,存钱——尽管是个好东西,但只是一个符号,象征着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
这时,有两道汽车大灯的光形成一道弧线投在他们坐着的旅行车的前方。灯光照亮了他们两人苍白的脸,他们注视着前方,一言不发。灯光还照亮了一只浣熊,它正从水库边穿过公路,向他们旁边的树林走去。汽车开的速度比看上去的要快。浣熊停下来看了看渐渐逼近的光束,然后继续走进安全的对面车道。但就在这时,它抬起头,注意到史蒂芬和玛乔丽的车停在路肩,在阴暗的夜色中沉默不语。正是这一瞥,它一定认为它原本待着的地方比它要去的地方更好,于是转身蹦跳着重新穿过奎克大桥路,跑向水库凉爽的水域,而这导致那辆车——实际上是一辆老旧的福特皮卡——轰隆隆地撞上它,把它甩飞,然后旋转着落在对面的路肩附近一动不动。“啊——呀——哟!”一个男人尖锐的声音从皮卡黑暗的驾驶室里传出来,后面跟着另一个男人的笑声。
接着一切又变得非常寂静。浣熊躺在距离里夫斯的车二十码的地上。它没有挣扎。它只是躺在那里。
“真恶心。”玛乔丽说道。
史蒂芬什么也没说,尽管他不像刚才那样失语。事实上,当他的眼睛盯着浣熊一动不动的尸体时,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们要做些什么吗?”玛乔丽说。她把身子向前探了几英寸,透过挡风玻璃研究浣熊的情况。在他们西面细长的山毛榉树后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不。”史蒂芬说。自从玛乔丽在他们赴宴途中说了那句重要的话后,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除了刚才那个毫无意义的词。
就在这时,他打了她。他打了她,在他意识到自己会打她之前,但是在他知道自己想要打她之后。他用张开的手背打她,甚至都没看她一眼,直接打在她的脸上,正中鼻子。而且打得很重。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个手势而不是击打,尽管他明白,这就是击打。他感觉到她柔软的鼻尖,然后是软骨抵到他手背上的硬骨头。他从没打过女人,甚至从没想过要打玛乔丽,每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这类悲剧时,他总以为自己不可能打她。他打过其他人,也被其他人打过,很多次——溜冰场上野蛮的缅因州男孩。但是,不打女孩。他父亲总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母亲也说过。
“哦,我的天啊。”玛乔丽被打后就说了这么一句。她立刻用手捂住鼻子,然后静静地坐在车里,两人都没有说话。他并没有心跳加快。手背有一点疼。这是完全陌生的体验。史蒂芬左侧鬓角下面有一块小小的玫瑰色胎记,形状有点像西弗吉尼亚州。他想他现在能感觉到这块胎记的存在。那里的皮肤在刺痛。
而事实是他甚至感到了更大的解脱,对玛乔丽完全没有歉意,后者呆坐在那里,用手捂住鼻子看着前方,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以为她肯定会哭。她是个爱哭的女子——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在他不小心说错话的时候,在月经快来的时候。哭是自然的。但很显然,对她来说,挨打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此它需要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不是新的,那就是通常为其他体验所保留的力量、韧劲和自我控制。
“我现在去不了尼克尔森家了。”玛乔丽几乎是耐心地说道。她拿开手,看着手心,就好像鼻子在手心里。果然,正如她想的那样,有血。他听见她用听起来像是堵住的鼻子吸气然后用嘴巴把气呼出来。她还没有哭。这一刻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打了她——那是不是只是他脑子里酝酿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没有付诸行动的手势。
但是,他现在想做的是直接跳到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陷在错误的、无关紧要的细节里。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乔治·尼克尔森,也不在乎他们在肮脏的小旅馆里做了什么。玛乔丽绝不会为了乔治·尼克尔森或者像乔治·尼克尔森这样的人而离开他,而乔治·尼克尔森或者像他这样的人——开欣克利游艇的有钱人——也不会为了像玛乔丽这样无足轻重的小女人而抛弃一切。他想到她的鼻子,又红又肿,黏稠的鲜血滴在她绿色的裙子上。他没想到鼻子会被打破。鼻子总能挺住。当然,车里有电话。他可以简单地给派对打个电话。他想象着尼克尔森家那栋大而不规则的白瓦房子在弯曲的车道尽头富丽堂皇地亮着灯,那些漂亮的榆树、脚灯,他们在里面打过球的昏暗的红土网球场,温水游泳池,草地暗处摆放着的随时可能将你绊倒的亨利·摩尔的雕塑。他想象着对某个人——不是乔治·尼克尔森——说玛乔丽病了,她在路边吐了。
但是,他要关注正确的细节。他要跟她搞清楚的是:你感到抱歉吗?(他忘了玛乔丽已经说过抱歉。)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细节。
出乎意料的是,那只被皮卡撞得一动不动躺在地上的浣熊,那个在黑暗中模糊的一团,又活了过来,现在正试图把自己废了的下半身拖离奎克大桥路,拖到草地的边缘,再进入水库边上的低矮树丛。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玛乔丽说道,又把手放在她受伤的鼻子上。她看见了浣熊的挣扎,把头扭向一边。
“你难道不感到抱歉吗?”史蒂芬说。
“是的。”玛乔丽说道。她仍然捂着鼻子,就好像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捂着鼻子这一事实。可能,他想,已经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糟糕。“我是说不。”她说。
他又想打她——这次是耳朵——但他没有。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打。没人知道。“好吧,那是什么意思?”他说,第一次感到盛怒。让他盛怒的——他这辈子最让他发狂的——是被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再也没有对的选择。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境地。“那是什么意思?”他愤怒地又说了一遍,“说真的。”他就应该带她去尼克尔森家,他想,让她鼻子肿着,嘴唇上流着血,鼻孔里塞着东西去面对他们。或者让她坐在车里直到晚餐结束,不然就自己走十一点六英里的路回家。也许乔治会出来用他的路虎载她回家。当然这些都只是想想。“那是什么意思?”他说了第三遍。他被堵在自己的话上,堵在这一点点可怜的好奇心上。
“我告诉你的时候感到很抱歉。”玛乔丽说道,非常镇定。她把手从鼻子上放下来,放到膝盖上。一个绿色蝴蝶结现在落在她裸露的肩上。“尽管不是非常抱歉,”她说,“我抱歉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件事。现在我告诉了你,你打了我的脸,可能还打断了我的鼻子,我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抱歉了——除了那件事。我很后悔嫁给了你,我会尽快修正这个错误。”她仍然没有哭。“所以现在,如果你还有一点善意的话,能不能下车去帮帮那可怜的动物,它被那群该死的乡下人用那辆该死的皮卡撞残了,然后还因为他们是狗屎一样的低等人类而嘲笑它吗?你能帮它一下吗,史蒂芬?这在你的容许范围之内吗?”她猛吸一下鼻子,然后发出一声短促而深沉的、带有挫败感的呻吟。由于鼻子堵塞,她的声音听起来鼻音更重,中西部腔甚至更明显了。
“我很后悔打了你。”史蒂芬·里夫斯说,然后打开车门,走到无声的公路上。
“我知道,”玛乔丽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情绪,“你会更后悔的。”
当他穿着棕色西装沿着空荡荡的碎石路走到刚才浣熊被撞后挣扎着拖到的公路边时,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小摊深色的血迹,他勉强能从坑坑洼洼的路面上看出来,那也可能是一摊油渍。没有浣熊。浣熊用它最后的野性、人类无法想象的意志力积聚起力量,把自己拖进了灌木丛里等死。史蒂芬向下凝望黑暗中那隔开水库的荆棘树丛。那里静止不动。他好像听见低矮的灌木丛中有窸窸窣窣的响声,那头动物可能在那里,它把自己安顿在柔软的青草和潮湿的泥土上,然后永久地睡去。湖边的某个地方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非常清晰的笑声。然后是远处一扇车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另一种门,一扇纱门,啪地被甩上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说:“哦,不,哦嚯嚯嚯,不。”在水库的另一端,在树林后面,亮起了一点白光,他没想到那里会有房子。他在想心中的怒火要过多久才能消退。他想了一会儿为什么玛乔丽要在此刻向他承认这件事。这好像很奇怪。
然后他听见自己的车发动的声音。奔驰车沉闷的金属柴油发动机的声音。车头灯灵巧地亮起,照在他身上。车里的音乐立刻响了起来。他转过身,正好看见玛乔丽漂亮的脸蛋被那橙色的仪表盘灯光照亮了,就像他刚才开车时那样。他看见她的指尖在方向盘上方,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在树林里,他注意到一道奇怪的光线穿过树木,一种黄色的东西,一种从潮湿的低地里冒出来的东西,一阵薄雾,一阵水汽,某种可能有魔力的东西。此刻空气闻起来有点甜。蛙声停止了。这事到此为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