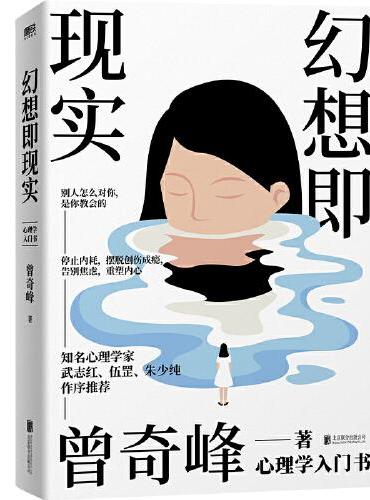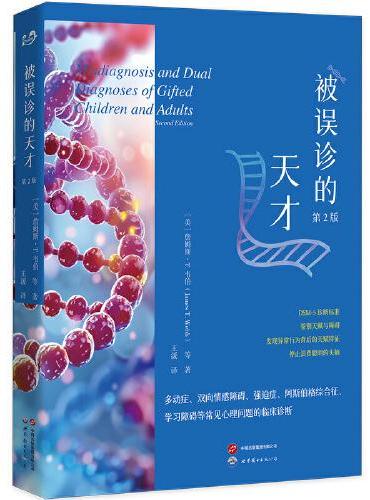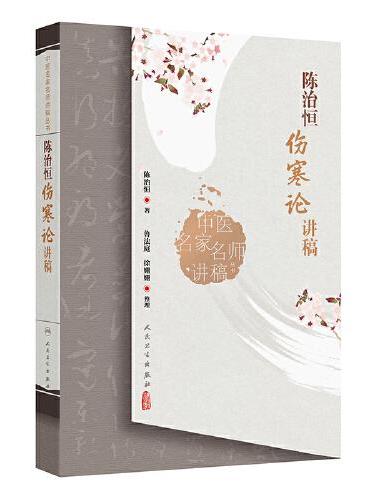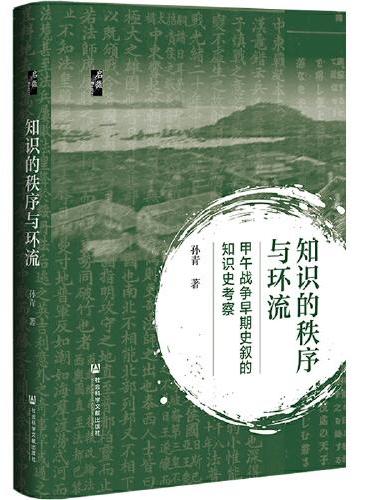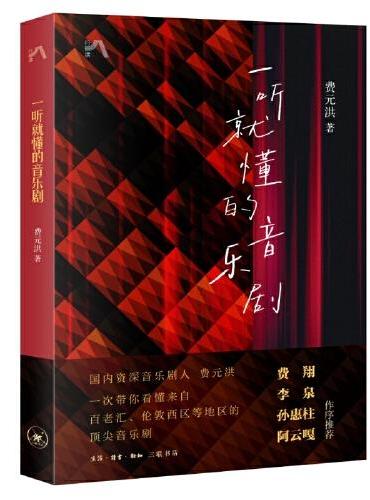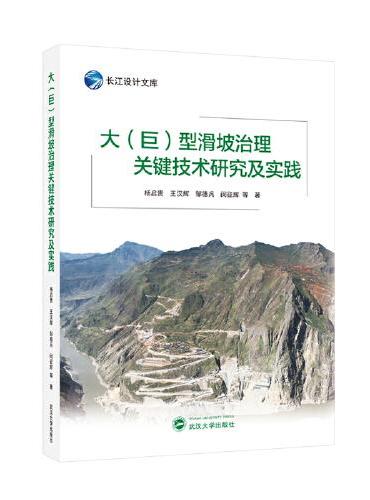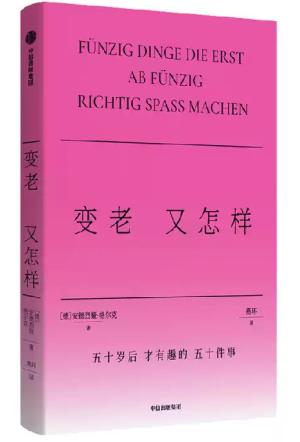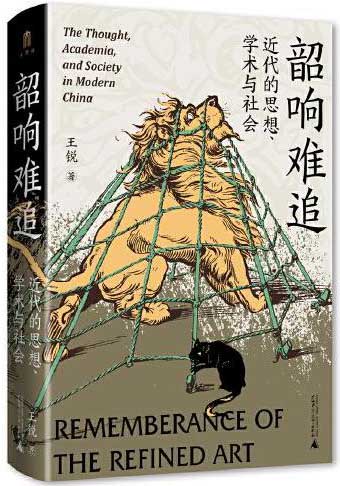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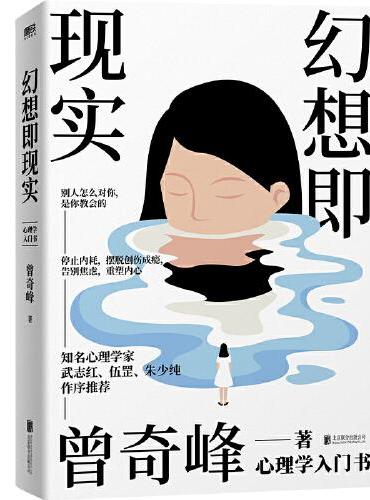
《
幻想即现实(再版)
》
售價:NT$
3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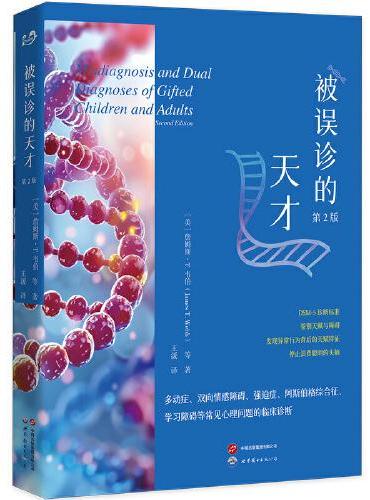
《
被误诊的天才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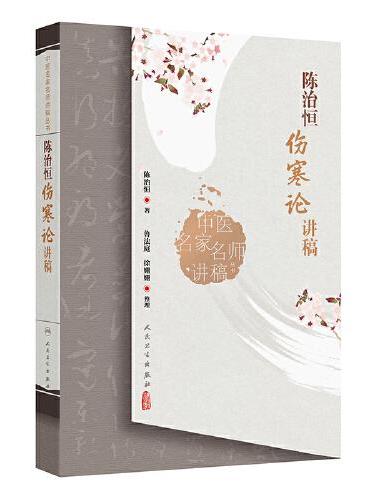
《
中医名家名师讲稿丛书——陈治恒伤寒论讲稿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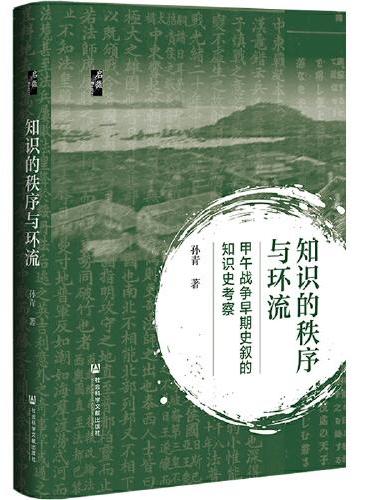
《
启微·知识的秩序与环流:甲午战争早期史叙的知识史考察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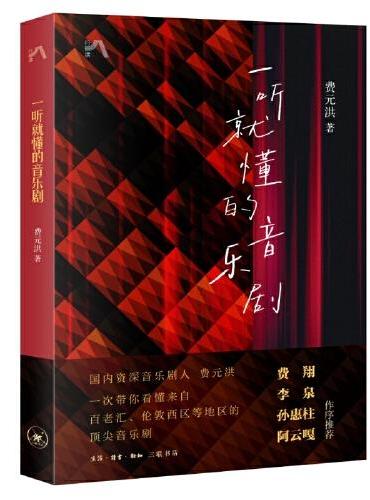
《
一听就懂的音乐剧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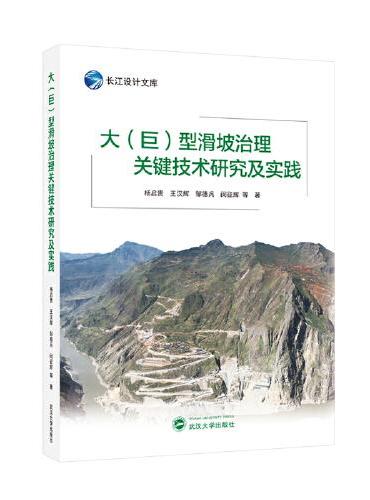
《
大(巨)型滑坡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实践
》
售價:NT$
6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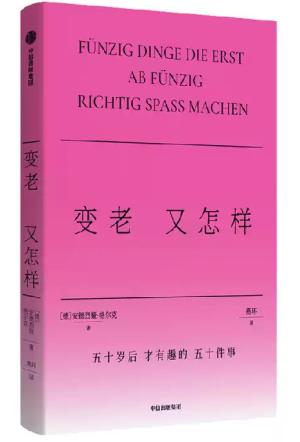
《
变老又怎样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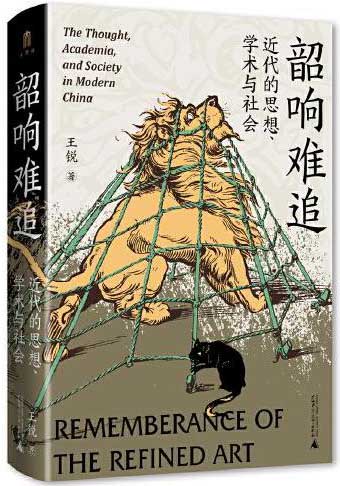
《
大学问·韶响难追:近代的思想、学术与社会
》
售價:NT$
398.0
|
| 內容簡介: |
|
收入《史学·史识·文化--刘桂生史学论文集》一书的文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作者刘桂生公开发表的文章。全书主要分为九个部分,主题分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华文化自信、中西文化交流互释、史家与史学理论、讲座与访谈、为师之道、清华园溯源、献辑佚和简历和年谱。其中“讲座与访谈”部分所收的主要是作者在清华大学等校给研究生讲课及接受采访时发表的谈话等。《史学·史识·文化--刘桂生史学论文集》一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
|
| 關於作者: |
|
刘桂生(1930.8-2024.6),云南昆明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等。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此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学术思想受陈寅恪、刘节、雷海宗、邵循正、丁则良以及孙毓棠、周一良诸教授之影响,承袭老清华“中西交汇、古今贯通”之学风,以“身、心、家、国、古今、中、外”八事相通为要领,以维护发展民族文化之自我更新为目的;强调为学须具“预流”思想和“一线”观念,重视多学科交叉和多种语言、多种档案在史学研究中之作用。
|
| 目錄:
|
“清华问道”丛书史学·史识·文化
——刘桂生史学论文集
刘桂生著版面字数:每页(33)行×每行(34)字×总页数(376)页=(422)千字图片1:1947年春,就读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一院高中部期间留影
图片2:1950年6月,岭南大学政治学会庆祝教师节暨欢送毕业同学摄影留念,前坐者为陈寅恪、唐筼夫妇,第二排中立者为刘桂生
图片3:1979年,在北京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东方语言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周策纵亲切交谈
图片4:1988年1月,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时留影
图片5:1980年代末,在清华大学家中接待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格鲁尚茨,左一、左三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柱洪、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主编张步洲
图片6:1997年10月,应邀赴美国科伦达参加美国“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年会,在会上作“论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曲解”主题发言
图片7:1998年6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期间,与曾赴中国访学的外国学生相聚,左一史奈德(Axel Schneider,曾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现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教务长),左二为林茹莲(Marilyn ALevine,曾任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副校长、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会长),右二为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曾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副校长,现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副校长)
图片8:1999年3月,在清华大学参加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发起的“五四运动研究历程回顾与检视座谈会”
图片9:2000年秋,在清华大学家中接待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墨子刻(Thomas AMetzger)
图片10:2002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时留影,中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家和教授
史学·史识·文化:刘桂生史学论文集>>><<<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论试析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研究他的思想发展道路,特别是他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对于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李大钊是从资产阶级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是一个成熟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各家所列举的论据不外他曾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进行过“揭露”和“批判”,写出了像《大哀篇》这样“申讨军阀专政的檄文”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M\\]//胡华主编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13。笔者认为,这种论断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问题出在用来支持这种论断的各种“论据”不是别的,而是一些对李大钊早期著作中的词语的误解,其中最主要的又是把他早期著作中不时出现的“暴民”“豪暴者”“骄横豪暴之流”等词误认为对袁世凯之流的批判性的称谓,因而便把载有这些词的文章误认为是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的批判文章,并据此作出判断,认为李大钊早期就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大钊只不过是一个满怀热忱的有志青年。他有着一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觉悟,一心一意希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以便“一力进于建设”。隐忧篇\\[M\\]//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我们只要把他这一时期所写的政论文章仔细阅读一篇,就不难看出,他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上的态度往往以进步党人以及同盟会温和派的意见为依归,而与同盟会激进派(以《民权报》为代表)言论明显地站在对立的位置上。那么,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言论和同盟会激进、温和二派以及进步党的言论分别进行对比。只要一比就能看出他的言论,究竟与哪一派相似,与哪一派不同。而且,通过这样的比较,就能把上面所说的那种误解,从根本上纠正过来。下面,我们就以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为背景,把这几个派别的言论和李大钊的言论,分别进行比较,以便读者从中探索究竟,引出结论。
一
民国成立后,在同盟会内部引起激进、温和两派公开论战的第一桩政治事件是张振武案。此文刊载于1913年4月1日所出版之《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这一案件引发出“弹劾”总统袁世凯的问题。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李大钊发表了《弹劾用语之解纷》一文。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早年入武昌两湖师范,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回湖北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担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袁世凯、黎元洪等人为了消灭湖北革命力量,合谋杀害领导这股力量的张振武。由袁出面,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议,电召张进京。张自湖北启程后,黎即密电袁要求将张处决。张于1912年8月2日抵京。袁假意殷勤招待,亲自设宴洗款,又令段祺瑞、冯国璋等轮流宴请。13日袁又得黎密电,再次要求将张处决。14日晚,袁设伏于张所居住之旅舍周围。张宴毕归来,即遭逮捕,送往军政执法处,即被杀害,时方15日之清晨。此事是民国史上屠杀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我们只要把这篇文章的论点,拿来和同盟会激进与温和两派的言论分别进行对比,就能看出李大钊这时赞成的究竟是哪一方的主张。
张振武案是民国成立后反动势力屠杀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主谋者是袁世凯和黎元洪。此案发生后,同盟会激进派义愤填膺,立即提出“武力解决”的主张。天仇(戴季陶)张振武案之善后策\\[N\\].民立报,1912-08-21接着天津《民意报》也于8月26日发表题为《讨袁黎两民贼》的社论,力主讨袁。而温和派却认为应当在法律范围内求得解决,他们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提出“武力解决”这种主张的人是“于国基未固之时,作动摇国本之论”,是“鲁莽灭裂”“意气用事”,欲“陷我国于不可挽救之境”。疾世再论鼓吹武力解决说者乱法误国\\[N\\].民立报,1912-08-26这时,激于义愤的湖北籍的议员在议会中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一项弹劾案。温和派对这件弹劾案亦持否决态度。这样,双方的争论,就从“武力解决”问题转入“弹劾”问题。反对弹劾的温和派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张振武案件的责任,不应由总统(袁世凯)来承担,而应该由陆军部长(段祺瑞)来承担。这是因为,中国采用的是责任内阁制,而“在责任内阁之国,总统当然不负责任”。况且,这次杀害张振武的命令,又是由段祺瑞附署。因此,他们认为,“张振武案之责任,当归之于陆军部长,而不当归于总统”。行严(章士钊)张方案之解决法\\[N\\].民立报,1912-08-20(天声人语)。(袁世凯杀害张振武时,亦将其部将湖北军政府将校团团长方维同时杀害,故此案亦称“张方案”。)
二、再就案件的性质说,此案只不过是陆军部长的“行政过失”。按照西方议会制度的原理,“弹劾”的适用范围,只及于政府的法律犯罪(如受贿、叛国等),而不及于政治问题。因此,此案不能用弹劾的办法来处理。议院如就这一事件而通过弹劾案,那就是议会“自紊其政制之理”。行严再论总统责任问题\\[N\\].民立报,1912-08-22
正当此时,梁启超派的《庸言》杂志编辑吴贯因在一篇介绍美国议会制度的文章中谈到他对“弹劾”适用范围问题的理解。他的意见与章士钊在《民立报》所发表的意见正好相反,即认为弹劾的适用范围既及法律,也及于政治。吴贯因共和国之行政权\\[J\\].庸言(创刊号):1-10这种言论等于从议会制度的理论原理的角度反驳章士钊的主张,实际上起着支持弹劾案的作用。于是,章士钊又写文章反驳,指责吴贯因把“弹劾”和“投不信任票”两件事混为一谈。他说,议会“课责”政府的方式,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投不信任票”,另一种是“弹劾”。前者专门针对政治问题,后者专门针对法律问题。两者性质不同,决不容混淆,混淆了就会引起政海“无谓之风潮”。行严弹劾发微\\[J\\].独立周报,1912,1(13):13-14
针对章、吴二人围绕“弹劾”适用范围问题的论战,李大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态度究竟怎样呢?
一、他明确支持章士钊的意见,文章这样说:“《独立周报》记者秋桐君秋桐,章士钊的号。,以‘弹劾’专属法律问题,于政治问题则行不信任投票,无‘弹劾’之发生。而《庸言报》记者吴贯因君,则并立法部对于行政之课责,无论关于政治或法律,概以‘弹劾’该之。……吾以为弹劾之语,兼用于政治、法律二方,究属不合,宜专用于法律问题,吾与秋桐君有同情焉。”原来,李大钊赞成章士钊的意见。
二、李大钊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他之所以支持章士钊的理由。他回叙欧洲议会制度的发展史,然后指出:在这种制度初创时期,“弹劾”本来包含着法律和政治两方面的含义。后来,由于政府由议会多数党组织这样一种做法渐渐成为惯例,此后议会和政府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便渐渐减少,此后弹劾在政治问题上的作用也便渐渐消失,只剩下了法律问题上的作用。这样,当1875年法国制定新宪法时,便正式作出规定,将二者明确加以区分;政府的法律犯罪,用“弹劾”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则用“投不信任票”的方法来解决。这样,流行于当前的“弹劾”只限用于法律问题的新观念便产生了。这无异说,吴贯因的意见从西方政治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也早已过时,而只有章士钊的意见才是正确的。
三、接着,李大钊又指出,由于(一)“弹劾”一词由日文译成中文时,未能分清上述两种不同含义;(二)南京临时政府在《临时约法》中使用“弹劾”这个概念时,又将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二者混为一谈,因此中国多数人迄今搞不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后果便是议会中屡次有弹劾案提出,使国家的政局变得很不稳定。“不独研斯学者,滋其惑误,而政局不时之动摇,……亦缘兹而起”。他郑重地表示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已于置辩者”,正是为着这一点。弹劾用语之解纷\\[M\\]//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12
根据以上所述,读者自能看出,李大钊在弹劾问题上的态度与章士钊基本上是一致的。站在相反方面的是激进派“武力解决”的主张和国会议员中对袁世凯政府的弹劾案。因此,假如我们把李大钊的政论说成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论,那么,与那些当时真正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论相差实在太远,历史研究也就很难有什么准则可言了。张振武案发生未满一月,章士钊就因态度调和深为同盟会员所不满而辞去《民立报》主编职务,可见他之以调和著称,确是事宜。
二
民国建立后另一个使同盟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是袁世凯所提出的“裁撤都督”问题。
袁世凯政府一成立就扬言都督应由它这个中央政府来任命。激进派从保护革命力量出发自然反对。事实很明显,如果让袁世凯来任命,那么,“将来各省都督皆为其爪牙”,“一旦袁世凯破坏共和,……则吾国民之死命,遂为其所制矣”。讨袁世凯:(一)\\[N\\].民权报,1912-04-26因此,他们提出都督应由各省议会选举的主张,与之对抗。
袁世凯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二计。1912年7月,他授意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关于袁世凯授意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主张一事,李宗一《袁世凯传》一书是这样记述的:“1912年6月中旬,袁世凯派袁乃宽到武汉,要求黎元洪发起实行“军民分治”。当时,黎在和同盟会的斗争中正迫切需要袁的支持,自然不敢违命,遂于7月1日通电各省,倡议实行“军民分治”,……黎还表示湖北愿意率先实行。”见李宗一袁世凯传\\[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200要求裁撤各省都督,改设督军,专管军事,而由中央另派民政长(后来改称为省长)来管理各省民政。对这种主张,革命党人同样懂得它的根本用意就是取消革命党人都督手中的权力(如广东胡汉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等)。因此,他们便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来与之对抗。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同盟会温和派的主张与激进派不相同。他们认为,只有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才是处理此事的最高准则。在这一条原则下,便是革命党人都督手中的权力,也应该交出去。他们完全赞成“军民分治”的主张,接着便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批判激进派的意见,认为:“吾人深观今日之大势,为拥障政权计,为恢复秩序计,为整理财政计,为消弭外侮计,……在法无各省设都督自管军事之理”。他们声称:在立宪之国,都督实为“无法保存之一物”,因此,“必须裁撤”。啸秋再论军民分治\\[N\\].民立报,1912-07-31
李大钊在裁督问题上的观点究竟怎样,与激进派一致,还是与温和派一致呢?在1913年6月发表的《裁都督横议》一文中,李大钊明确表示都督必须裁撤,并列举了五条理由:(一)解除军法,不可不裁都督;(二)拥护宪法,不可不裁都督;(三)巩固国权,不可不裁都督;(四)伸张民权,不可不裁都督;(五)整顿吏治,不可不裁都督。他认为,只有把都督裁了,才能“拔本塞源”地消除今日这种“割据之局”的“隐患”。这就是李大钊在裁撤都督问题上的基本态度。通过上述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这时的李大钊还不能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都督问题。他分不清哪些是作为革命民主派的代表而掌握的都督,哪些是真正的实行割据的军阀都督。因此,他才不加区分地一律反对。他完全从抽象的国家观念出发,把它们一律视为妨碍统一的“隐患”。唯其如此,他才对那些敢于“上抗”袁世凯“中央”命令的革命党人都督十分反感,在上引文章中指责他们说:“皖、赣、湘、粤,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三人都是同盟会员。湖南都督谭延闿虽不是同盟会员,但由于该会在该省的力量较大,因此在袁世凯之流的心目中,湖南也是一个“暴民专制”的省份。傲岸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在他看来,此时的中央并“非专制之局”,因而“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实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他甚至提出对那些敢于“抗不解兵”的都督,不仅“挞伐宜速”,而且还要“雷厉风行,不少宽假”。裁都督横议\\[M\\]//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39从这些言论看,他的态度是十分温和甚至是“拥袁”的,怎么能说他是个“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呢?
三
为着把这个问题彻底辨析清楚,还有一个多年来一直被人误解的问题,不得不在此说明,即李大钊早期政论中经常出现的“暴民”“豪暴者”“豪暴狡狯者”“骄横豪暴之流”这几个词,究竟指什么人?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一向认为指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其实,这几个词指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请看下面列举的理由:
在1913年4月所发表的《大哀篇》中,李大钊两次使用“暴民”“豪暴者”等几个词,一次说他们“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之下”,另一次则说他们“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注意,《裁都督横议》一文中指责胡汉民等四都督时同样使用“傲岸自雄”四字,恐非偶然。不可一世”。大哀篇\\[M\\]//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看出,这是指革命党人而言。试问,在民国初成立之时,在革命党人和军阀官僚这两种人之中,究竟谁更有条件去“论”革命之“功”,谁更有条件去从革命先烈身上窃取声誉以自饰,是前者?还是后者?当然只可能是前者,而不可能是后者,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这里,这几个词与军阀官僚是没有关系的,它们是从贬义上指责革命党人——尤其是那些掌握军权和政权的党人都督的讽刺性的称谓。
《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不劳尔辈先觉君子,拔剑击柱,为吾民争权于今日”。此文发表于1913年6月1日。引文见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这里说得很清楚,那些“拔剑击柱”的争权者不是别人,而是“奔走革命”的“先觉君子”,明白无误地指革命党人而言。
《一院制与二院制》一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一国之中,富者少而贫者多,愚者众而智者寡。若听其杂处于一院,则富者、智者将为多数贫者、愚者之豪暴所压倒,意思卒不得表现于国会”。此文发表于1913年9月1日。引文见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这里,作者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出,被他称为“豪暴”的那些人,正是“贫者”,而不是“富者”。如果认为这是指袁世凯之流而言,那么,难道李大钊竟无知到连此等人是“贫者”还是“富者”都分不清楚吗?可见,把这个词断定为军阀官僚的代称是与李大钊文章的本意完全不符的。
以上列举的是李大钊著作中使用这几个词的情况。
为了说得更充分一些,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社会舆论是怎样使用“暴民”这个词的。
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朱执信1914年6月在《民国杂志》第1年第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暴民政治者何》。文中谈到“暴民”这个词指什么人这一问题时,明确说:“暴民者,泛指非旧官僚党与之人人,而以革命党为其代表”。又说:“凡非旧官僚及其附和者,即悉入于暴民之列”。这里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暴民”正是以“革命党为其代表”。朱执信还指出,袁世凯之流攻击广东、湖南等省是“暴民专制”,其用意“不重专制,而是暴民”,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对革命党进行“征伐”。他接着说,只要“暴民”不变为“忠奴”,那么,袁世凯之流凭借武力,就不可能把他们“坑诛悉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文章中鼓励革命党人说;“暴民,勉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暴民政治者何\\[M\\]//朱执信集:上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25:173-176可见,朱执信不仅不回避,而且反借用“暴民”这个词来称呼革命党人。
革命民主主义者蔡元培于1912年7月27日在《民立报》发表《答客问》一文,其中非常坦率地说:“吾党虽不必无执拗粗暴之失德,而决无敷衍依阿之恶习”。这里,蔡元培虽把“粗暴”视为“失德”,但却不讳言它是革命党人们的一种习性。在他看来,这种习性比起立宪党人一贯依附权势“敷衍依阿”的“恶习”来,要高洁得多。
让我们再来看看章士钊、李剑农、梁启超等人的言论。
1914年5月,章士钊在《甲寅》月刊创刊号发表《政本》一文,其中说:“清鼎既移,党人骤起,……国人乃惶惶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可见,在章士钊心目中,“暴民”就是指革命党人。章士钊政本\\[J\\].甲寅,1914(创刊号):1-18
1917年6月,李剑农在《太平洋》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时局罪言》一文,其中回叙了民国元、二年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流斗争的过程。他说:“壬癸之交壬,即壬子,民国元年;癸,即癸丑,民国二年。,顽旧者据历史传来之势力与军队,以倾其所嫌恶之暴民。暴民据纸墨《约法》之势力与议会,以抗顽旧,……暴民倾而顽旧胜矣。及其既胜,顽旧之势力,一发而不留有余,……洪宪乃覆,……世所指为暴民者,亦于是而复其固有之位”。李剑农时局罪言\\[J\\].太平洋(上海),1917,1(4):1-12十分清楚,李剑农这里所说的“暴民”,同样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
还可看看梁启超的言论。1913年4月14日,他在北京万牲园举行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毫不隐讳地指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是“横行骄蹇之新贵族”,是专搞“暴民专制”的“暴乱派”。他对这种人表示深恶痛绝,宣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以上引文均见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67-668
最后再看袁世凯所说的“暴民”又是指什么人。他在1913年11月发表的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中宣称:“二次革命”是由“少数暴民”,“煽惑”而起,因此不能不对他们进行“讨伐”。可见,袁世凯口中的“暴民”同样是指国民党人。
不必再引。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在民国初年,在各派政治人物笔下,“暴民”这个词都是指革命党人。把这一点弄清,那么,对于李大钊笔下的“暴民”这个词究竟指什么人,就更容易判断了。只要把多年来存在于李大钊思想研究中的“暴民”一词的误解澄清,那么,建筑在这种误解之上的把李大钊这时的政论,断定为“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论的说法,想来是可以重新考虑的了。参见刘伟李大钊早期思想的阶级属性\\[J\\].社会科学辑刊,1985(4):11-17。作者认为,李大钊早期思想是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陈独秀思想之代表小资产阶级、胡适思想之代表资产阶级、形成三大典型。这种论断可真谓“奇”,然而却举不出任何文献根据,且理论上亦不能自圆其说,真所谓“一误再误”。又,同一时期——1913年4月,李大钊发表在《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上的《更名龟年小启》中,亦反映着同样的对形势的看法。现特将此文略加注释,附在本文后,以供参考。
四
综上所述可知:李大钊在民国元、二年间曾经把国家早日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政府身上。他对这个政府是支持和拥护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同盟会中温和派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与激进派坚决反袁的态度则是相反的。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他这时已是一个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
李大钊之所以“拥袁”,是出于切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的爱国热忱。这显然是建筑在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当稍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反动面目一旦暴露时,他立即由“拥袁”转变为“反袁”,投身到护国运动中去。这个从“拥”到“反”的转变过程,正好说明李大钊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始终如一的,正是这种思想推动着他随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前进。
反袁斗争胜利后,李大钊思想发生变化。在这之前,他希望通过统一和制宪,把政治生活引上民主主义的正轨。他心中有一个抽象的“调和立国”的政治信念。然而不久之后种种事实向他证明,这种美好愿望已被那种宪法之外的强大势力所粉碎。这种势力倒行逆施,使他痛心疾首,然而不知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种“法外势力”。这时,正是这时,云南起义的枪声响了。他没有想到,在这刀光火海的鏖战之中现出一线希望。原来,破坏宪法的“法外势力”,是可以用另一种“法外势力”来对付,这就是革命的法外势力。这样,他便在反袁斗争胜利后的第一个国庆纪念日,满怀信心,用酣畅淋漓的笔触写道:
“法外之势力而与宪法为敌,国民执宪法而无如之何,势亦以法外之势力制之。制造此种势力之代价,虽至流血断头而有所不辞也。法兰西帝政之旋起旋仆,卒绝其根株于共和宪政之下者,法兰西革命军之势力也。洪宪帝制之消灭于初萌者,西南护国军之势力也。法外之势力能摧残宪法,法外之势力即能保障宪法”。制定宪法之注意\\[M\\].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22
有了这样一种新认识,他便信心十足地宣称:
“异日苟有冒不韪,而违叛宪法者,吾民亦何敢避锋镝戈矛之惨,而各卫障宪法之血代价,以失先烈艰难缔造之勇哉!”制定宪法之注意\\[M\\].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22
一贯信奉“调和立国”,政治态度极为温和的李大钊开始注意到反抗流血了。这难道不是政治思想中发生的变化吗?
对于李大钊早期的思想,即其思想发展的起点,必须根据文献,实事求是地进行探讨。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无从研究他的思想发展道路,更不可能去探索他怎样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问题。本文写作的用意,就在于提出这个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附一:何兆武教授来信
刘桂生同志论李大钊政治思想一文,材料翔实、论证精确,对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以及广大读者中间人云亦云的一个问题,给出了断制性的答案;这个问题是:辛亥时期李大钊的思想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吗?从来在历史上,思想的发展当是可以而且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的,这里并没有一种唯一无二的绝对模式可循;它不像古典力学中的物体运动那样只能是遵循一条唯一的途径。假如社会的发展有其一定的阶段或形态的话,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思想的发展必然经历几个固定的、不可变易的阶段或形态,比如说;改良主义→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公式。本文功绩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理清历史学上一个具体疑难问题,即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性质,从而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和社会主义史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一是它通过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阐明了一个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来研究思想发展和变化的规律问题。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潮流是要求解放,但具体到每个个人,则其途径可以是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这一点可可以反映出历史发展面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读本文,深受启发,谨赘数语。
附二:《北京社联通讯》报道
此文发表后,《北京社联通讯》1986年第5期和北京《李大钊研究会通讯》1986年第1期,相继发表学术界座谈此文情况之消息,现将社联所发之消息,转录如后:
8月21日至23日,北京市李大钊研究会召开了学术座谈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李大钊生平史料汇编》第一卷提纲、交流近期李大钊研究工作的信息及成果。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刘桂生教授,就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李大钊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成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这一我国学术界几乎一致肯定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研究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分析比较同盟会进派与温和派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及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言论,不难看出,李大钊在民国元、二年间曾经把国家早日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政府身上。在这一点上,他与同盟会中温和派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与激进派坚决反袁的态度则是相反的。因此,不能说这时的李大钊已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只是一个满怀爱国热忱的有志青年。刘桂生教授在发表观点时,强调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必须依据文献,进行探讨。与会同志在讨论刘桂生教授的观点时,一致认为,李大钊研究必须打破框框,实事求是,坚持从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出发,客观地评价李大钊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否则无从研究他的思想发展道路。大家感到,有必要逐篇研读李大钊的文章,为李大钊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姜庆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