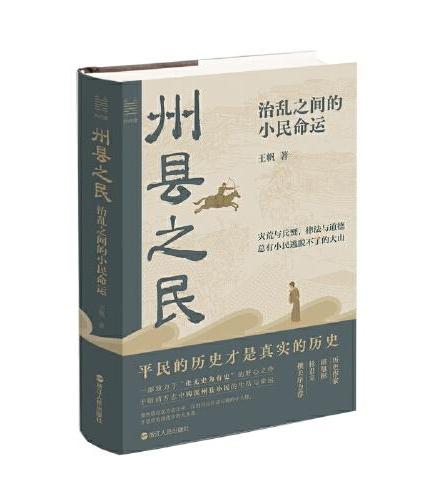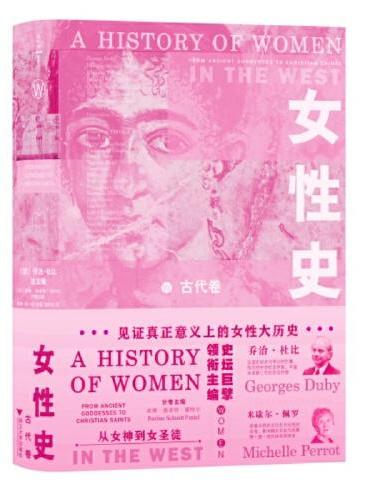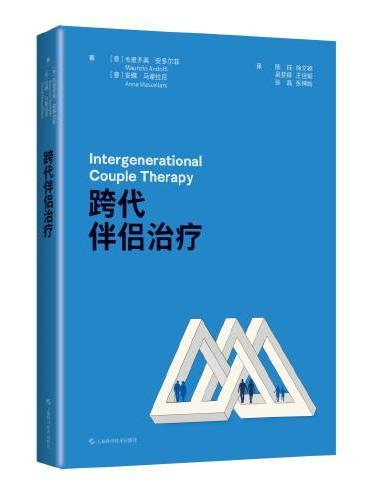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NT$
295.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NT$
440.0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NT$
440.0
編輯推薦:
◆ 关于记忆的绝赞之作,行文激扬流畅、内容引人入胜,作者像侦探一样探寻家族故事,同时将时代的大历史和普通家庭的小历史编织在一起,还原了数千万人如何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犯罪铺平道路、又如何走出“否认”代替“记忆”、“制造神话”代替“事实”的失忆症大流行。
內容簡介:
施瓦茨通过追踪家中三代人的故事,还原了一个昨日世界:德国数以千万计的“随大流者”漠视对犹太人的驱逐、参与对犹太人的掠夺;在战后否认个体责任、造成失忆症蔓延,直至他们的孩子都站出来质疑过去……当德国社会的记忆工作开始显现成效时,法国人民才从抵抗者的幻梦中醒来,那其他国家呢?对于过去的遗忘,是否仍在流行?
關於作者:
热拉尔丁·施瓦茨(Géraldine Schwarz)
目錄
第一章 是不是纳粹
內容試閱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