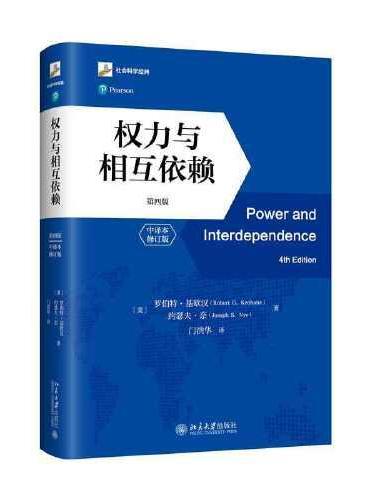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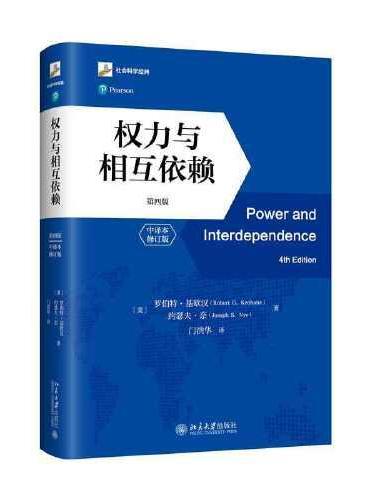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踏上疗愈之旅(修订版)(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
控制权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管理与传承
》
售價:NT$
398.0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
》
售價:NT$
762.0

《
利他主义的生意:偏爱“非理性”的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推荐读物!)
》
售價:NT$
352.0

《
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咨询的顶层设计
》
售價:NT$
454.0

《
FANUC工业机器人装调与维修
》
售價:NT$
454.0

《
吕著中国通史
》
售價:NT$
286.0
|
| 內容簡介: |
《沧浪之水》是当代文学名家阎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小说以池大为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个青年的奋斗和成长历程。从不谙世事、充满理想的学子,到进入社会摸爬滚打,再到面对生活的重压和坚硬的游戏规则,池大为身上发生了许多改变。他不断探寻着关于事业、关于人生的答案。《沧浪之水》是现实的,也是黑色幽默的,作者以犀利的文笔和生动的故事,写出了个人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命运抉择与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
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
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
|
| 關於作者: |
|
阎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1976年起在湖南省株洲市拖拉机厂当工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8年又于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赴加拿大打工、学习。1992年起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副教授。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白雪红尘》《沧浪之水》,中篇小说《佳佳呀,佳佳》等以及论文多篇。长篇小说《曾在天涯》获湖南师范大学1997年作品特别奖,短篇小说《菊妹子》获湖南省建国30周年青年文学竞赛奖。
|
| 內容試閱:
|
《沧浪之水》:
1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我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覆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谁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儿,在门槛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人才能分辨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中问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着,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生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嵇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侯,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了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辨认才看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2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P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