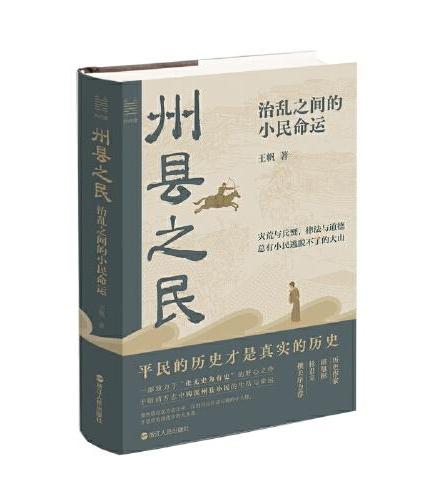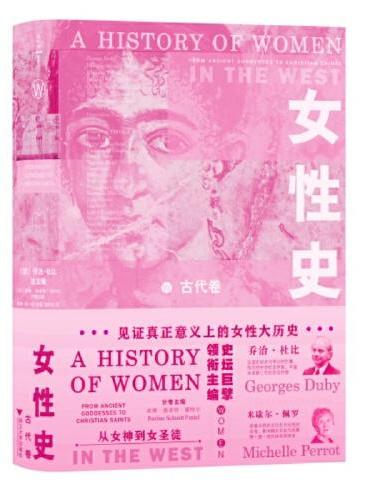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NT$
295.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格罗斯曼“战争二部曲”的第一部,《生活与命运》前传)
》
售價:NT$
84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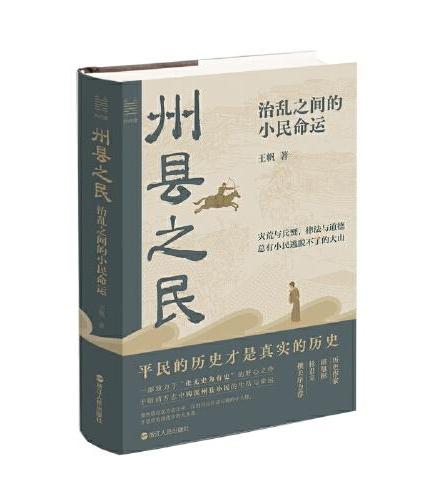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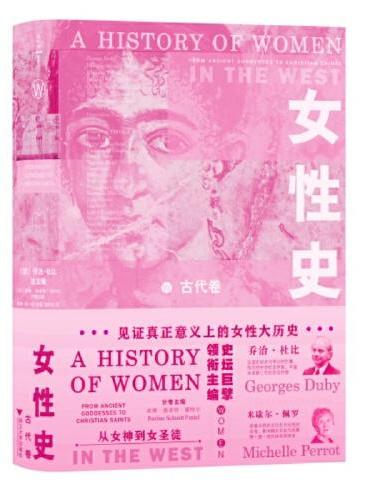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
| 編輯推薦: |
老舍的幻想集。写给成人,是时代的警示录,他笔下的“猫国”,有学校而没教育,有政客而没政治,有人而没人格,有脸而没羞耻,弥漫着他对20世纪30年代初旧时中国的忧心忡忡。写给儿童,则是人性的赞歌,他笔下的“宝船”“青蛙骑手”,都有着淳朴少年的机智和顽强生命力。
幻想集的背后,是老舍先生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沉大爱。
|
| 內容簡介: |
|
老舍是20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有几部带有幻想性质的作品,同样出彩。《猫城记》是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长篇小说。该小说采用游记式的结构展开故事,用第一人称写作,以“我”飞离地球开始,以“我”返回地球结束,描述了“我”在猫国经历的一番奇遇,表达了老舍对社会现实的深思和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宝船》创作于1961年,讲述了贫家小孩王小二偶得宝船、救助弱者,被奸险小人骗走宝船,又在朋友的帮助下重夺宝船的神话故事,颂扬了劳动者勤劳善良、顽强勇敢、团结互助的美好心灵。《青蛙骑手》则是老舍根据藏族民间故事改编,剧中融入了反抗压迫的主题思想,剧情精彩,唱词优美,格调激昂。
|
| 關於作者: |
|
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生于北京,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猫城记》、短篇小说集《赶集》,话剧《茶馆》《龙须沟》等。老舍的文学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
| 目錄:
|
猫城记 ……1
自序……3
猫人……4
迷叶……19
死国……112
宝船 ……141
青蛙骑手 ……177
|
| 內容試閱:
|
我一直地睡下去,若不是被苍蝇咬醒,我也许就那么睡去,睡到永远。原谅我用“苍蝇”这个名词,我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它们的样子实在像小绿蝴蝶,很美,可是行为比苍蝇还讨厌好几倍;多得很,每一抬手就飞起一群绿叶。
身上很僵,因为我是在“地”上睡了一夜,猫人的言语中大概没有“床”这个字。一手打绿蝇,一手摩擦身上,眼睛巡视着四围。屋里没有可看的。床自然就是土地,这把卧室中最重要的东西已经省去。希望找到个盆,好洗洗身上,热汗已经泡了我半天一夜。没有。东西既看不到,只好看墙和屋顶,全是泥做的,没有任何装饰。四面墙围着一团臭气,这便是屋子。墙上有个三尺来高的洞,是门;窗户,假如一定要的话,也是它。
我的手枪既没被猫人拿去,也没丢失在路上,全是奇迹。把枪带好,我从小洞爬出来了。明白过来,原来有窗也没用,屋子是在一个树林里——大概就是昨天晚上看见的那片——树叶极密,阳光就是极强也不能透过,况且阳光还被灰气遮住。怪不得猫人的视力好。林里也不凉快,潮湿蒸热,阳光虽见不到,可是热气好像裹在灰气里;没风。
我四下里去看,希望找到个水泉,或是河沟,去洗一洗身上。找不到;只遇见了树叶、潮气、臭味。
猫人在一株树上坐着呢。当然他早看见了我。可是及至我看见了他,他还往树叶里藏躲。这使我有些发怒。哪有这么招待客人的道理呢:不管吃,不管喝,只给我一间臭屋子。我承认我是他的客人,我自己并没意思上这里来,他请我来的。最好是不用客气,我想。走过去,他上了树尖。我不客气地爬到树上,抱住一个大枝用力地摇。他出了声,我不懂他的话,但是停止了摇动。我跳下来,等着他。他似乎晓得无法逃脱,抿着耳朵,像个战败的猫,慢慢地下来。
我指了指嘴,仰了仰脖,嘴唇开闭了几次,要吃要喝。他明白了,向树上指了指。我以为这是叫我吃果子;猫人们也许不吃粮食,我很聪明地猜测。树上没果子。他又爬上树去,极小心地揪下四五片树叶,放在嘴中一个,然后都放在地上,指指我,指指叶。
这种喂羊的办法,我不能忍受;没过去拿那树叶。猫人的脸上极难看了,似乎也发了怒。他为什么发怒,我自然想不出;我为什么发怒,他或者也想不出。我看出来了,设若这么争执下去,一定没有什么好结果,而且也没有意味,根本谁也不明白谁。
但是,我不能自己去拾起树叶来吃。我用手势表示叫他拾起送过来。他似乎不懂。我也由发怒而怀疑了。莫非男女授受不亲,在火星上也通行?这个猫人闹了半天是个女的?不敢说,哼,焉知不是男男授受不亲呢?(这一猜算猜对了,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证实了这个。)好吧,因彼此不明白而闹气是无谓的,我拾起树叶,用手擦了擦。其实手是脏极了,被飞机的铁条刮破的地方还留着些血迹;但是习惯成自然,不由得这么办了。送到嘴中一片,很香,汁水很多;因为没有经验,汁儿从嘴角流下点来;那个猫人的手脚都动了动,似乎要过来替我接住那点汁儿;这叶子一定是很宝贵的,我想;可是这么一大片树林,为什么这样地珍惜一两片叶子呢?不用管吧,稀罕事儿多着呢。连气吃了两片树叶,我觉得头有些发晕,可是并非不好受。我觉得到那点宝贝汁儿不但走到胃中去,而且有股麻劲儿通过全身,身上立刻不僵得慌了。肚中麻酥酥地满起来。心中有点发迷,似乎要睡,可是不能睡,迷糊之中又有点发痒,一种微醉样子的刺激。我手中还拿着一片叶,手似乎刚睡醒时那样松懒而舒服。没力气再抬。心中要笑;说不清脸上笑出来没有。我倚住一棵大树,闭了一会儿眼。极短的一会儿,头轻轻地晃了两晃。醉劲过去了,全身没有一个毛孔不觉得轻松得要笑,假如毛孔会笑。饥渴全不觉得了;身上无须洗了,泥,汗,血,都舒舒服服地贴在肉上,一辈子不洗也是舒服的。
树林绿得多了。四围的灰空气也正不冷不热、不多不少的合适。灰气绿树正有一种诗意的温美。潮气中,细闻,不是臭的了,是一种浓厚的香甜,像熟透了的甜瓜。“痛快”不足以形容出我的心境。“麻醉”,对,“麻醉”!那两片树叶给我心中一些灰的力量,然后如鱼得水地把全身浸渍在灰气之中。
我蹲在树旁。向来不喜蹲着;现在只有蹲着才觉得舒坦。
开始细看那个猫人;厌恶他的心似乎减去很多,有点觉得他可爱了。
所谓猫人者,并不是立着走,穿着衣服的大猫。他没有衣服。我笑了,把我上身的碎布条也拉下去,反正不冷,何苦挂着些零七八碎的呢。下身的还留着,这倒不是害羞,因为我得留着腰带,好挂着我的手枪。其实赤身佩带挂手枪也未尝不可,可是我还舍不得那盒火柴;必须留着裤子,以便有小袋装着那个小盒,万一将来再被他们上了脚镣呢。把靴子也脱下来扔在一边。
往回说,猫人不穿衣服。腰很长,很细,手脚都很短。手指脚趾也都很短。(怪不得跑得快而做事那么慢呢,我想起他们给我上锁镣时的情景。)脖子不短,头能弯到背上去。脸很大,两个极圆极圆的眼睛,长得很低,留出很宽的一个脑门。脑门上全长着细毛,一直地和头发——也是很细冗——连上。鼻子和嘴连到一块,可不是像猫的那样俊秀,似乎像猪的,耳朵在脑瓢上,很小。身上都是细毛,很光润,近看是灰色的,远看有点绿,像灰羽毛纱的闪光。身腔是圆的,大概很便于横滚。胸前有四对小乳,八个小黑点。
他的内部构造怎样,我无从知道。
他的举动最奇怪的,据我看是他的慢中有快,快中有慢,使我猜不透他的立意何在;我只觉得他是非常的善疑。他的手脚永不安静着,脚与手一样的灵便;用手脚似乎较用其他感官的时候多,东摸摸,西摸摸,老动着;还不是摸,是触,好像蚂蚁的触角。
究竟他把我拉到此地,喂我树叶,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由得,也许是那两片树叶的作用,要问了。可是怎样问呢?言语不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