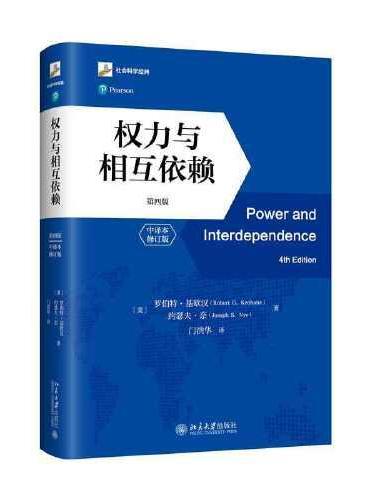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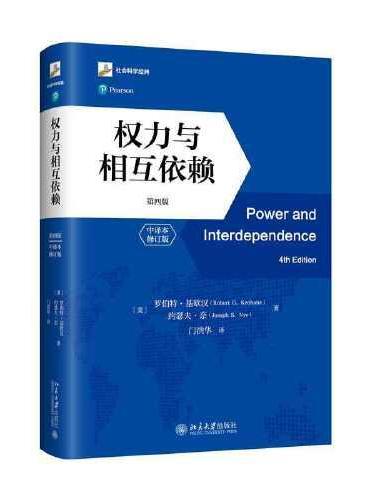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踏上疗愈之旅(修订版)(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
控制权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管理与传承
》
售價:NT$
398.0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
》
售價:NT$
762.0

《
利他主义的生意:偏爱“非理性”的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推荐读物!)
》
售價:NT$
352.0

《
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咨询的顶层设计
》
售價:NT$
454.0

《
FANUC工业机器人装调与维修
》
售價:NT$
454.0

《
吕著中国通史
》
售價:NT$
286.0
|
|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威风凛凛》保持了现实主义小说注重情节的特点,将赵老师被杀作为小说的基本贯穿线索,将“谁是凶手”这一悬念不断浮现在各章节中,使小说具有较强的阅读吸引力。同时又将象征主义的意象化特点和神秘的色彩融进了现实故事情节,创造出一种特殊艺术氛围,使该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揭示现实之外的、暗示人生真谛的隽永审美意味。
编辑推荐
《威风凛凛》以南方闭塞山区的西河镇为故事空间,以一桩离奇杀人案为叙事起点,从耍威风的民间文化心理和处世哲学来观照小镇众生,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数十年的人事纠葛。故事双线交织,情节曲折动人,既塑造了不同程度带有畸形的耍威风心理的众生相,也刻画了赵老师及其学生“我”等不同于小镇众生的新人形象,表达了对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文明和理性的呼唤与张扬。
|
| 內容簡介: |
|
长篇小说《威风凛凛》,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南方闭塞山区,民办教师“赵长子”一夜之间所遭遇的凶杀案——偏偏西河镇的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不值得杀的,该杀未杀的金福儿、五驼子等人继续着金伍两家从解放前就开始的威风之争,而见证并再次结束这一切的正是西河镇“最聪明的人”——爷爷。小说通过与八十岁的爷爷相依为命的少年“我”的视角,交替叙述了“没有一个善人”的西河镇的阴郁历史与现实,以及青葱岁月懵懂爱情所预示的依稀希望,以文学典型赵长子的人生际遇,张扬了一种骨子里的威风凛凛的精神,直面生命的灵魂和血肉。小说《威风凛凛》张扬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骨子里的,是一种能做各种苦役,受各种欺凌折磨都不会改变都会永远存在的精神,这种精神威风凛凛。
|
| 關於作者: |
|
刘醒龙,湖北黄冈人,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一棵树的爱情史》、长篇散文《上上长江》、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各类单行本约百余种。有作品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韩语、越南语、印地语、阿拉伯语、黑山语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获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蟠虺》获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背靠背,脸对脸》曾获国内外多项电影大奖。
|
| 目錄:
|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8
第三章 057
第四章 090
第五章 117
第六章 160
第七章 197
第八章 226
第九章 261
第十章 294
第十一章 328
第十二章 362
后记:失落的小镇 407
|
| 內容試閱:
|
后记:失落的小镇
1
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几乎不能写一个字。那笔对我来说,拿在手里如同拿着一把刀或一支枪,让我去除掉一个谁,当面对纸上许多方方正正的小眼睛时,我却惶惶不知可以在何处落下。那一阵,就连在工资册上签划自己的名字,也觉得疙疙瘩瘩的,笔和纸仿佛存在着一种仇恨,推推搡搡,让我怎么也把握不了。
《凤凰琴》的电影改编者对原著的肆意妄为及相关版权纠纷,单位里人事的角逐,还有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难以对人言的苦闷与痛楚,如山一样压在自己的身上。
当然,也不是没有欢乐的日子,但那时光之短暂,让人更感到痛苦的漫长。这实在又一次印证了那句名言,欢乐是虚无的,痛苦才是实在的。
黄州是个极小的城市,任何一种俗套都企图淹没她的风雅。
身居其中,实实地有万般的无奈。譬如,在黄昏的晚风中,想独自寻一片净土,让灵魂出一回窍,捎一些清凉和宁静给心灵,让星星和月亮抚一抚那许多永远也不会出血的伤口,让无边无际的夜空融合掉那一声声无声的呻吟。可我尚未动步,那几双职业伫望的眼睛,就降落在脊背上,那彻骨的凉意,一瞬间就能冻僵散步的情绪。
在以往,一位学工科才华出众的朋友,常常脱口冒出一句:高处不胜寒。我那时没有站在高处的体会,不知此寒为何物。现在,当我一步一步向着山峰攀去时,回想朋友说此话时的情景,不免慨然、怅然还有惘然。
感谢王耀斌、丁永淮等师长的帮助,我终于请上了三个月的创作假,那个神秘的山里小镇,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它能帮我回到文学的伊甸园。潇洒逃一回,这当然难说是最佳选择,起码它不是那种挑战人生的男性的强悍,但这怪不得我,要怪只能怪生活。拿上行李,就要出门,儿子生病上医院打针去了,过几天他就要满十岁。在他十五岁时,他会责怪我此刻不在他身旁,可我相信等到他三十岁时,他会理解父亲的。所以,我将要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献给年满三十的儿子。
咬紧牙关,逃一回吧!管它潇不潇洒。
2
送我进山的中巴车,在胜利镇街口上扔一样将我洒在一派萧条之中。一扇大门旁不知谁用红油漆写着四个字:胜利车站。我环顾四周,除略显破败的街景与大多数车站一样以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感觉到这就是车站。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慢慢地对此表示出了理解,作为亦迎亦送的车站,它从来不是旅行者的归宿,而永远只是整个旅途的一部分,劳倦与无奈才是它的本色。北京火车站、深圳火车站,在它落成之际是够豪华的了,当匆匆来去的人流一旦涌入之后,那些僵硬的奢侈无论如何也掩不去灰色的苍茫。无处不在的是迷惘,是惆怅,是遗憾的失落的感觉。
不知是哪种原因,在随之而来的那四十多个孤独的日子里,于写作之余,下楼走一走,散散步,放松一下情绪,那脚步便情不自禁地迈向车站。尽管那儿雨天很泥泞,晴天又尘土飞扬,嘈杂与脏乱则是不受气候的制约,每日里都一如既往,可我总是管不了自己的脚步,非要绕着车站走一圈,然后才或是沿着河堤,或是沿着沙滩,或是沿着公路与小街慢慢地走去。
有时候,一边走一边免不了想,如果父亲一直待在这座名叫胜利的小镇,那如今的我会是什么模样呢?那个黑得很深的夜,其实还不到八点钟,老长老长的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着,后来我也停下来不走了,望着大河淌水,听着旷野流风,我无法不想到爱与爱情。就在这种时刻我突然异想天开地意识到,人对历史的关注,更甚于对未来的仰望。在我每天对小站的不自主的回望中,包含着一切普通人的一种共性。那就是对无法拒绝的过去的百感交集。
我在写完第六章中的一个细节后,曾问过自己,你怎么想起要来胜利镇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呢,是一种纪念,还是一种向往?我不愿对自己多做解释,因为这已成为“过去”了,关于过去,是谁也无可奈何的。然而,过去可摸、可看、可怀想、可思考,还可以悔、可以恨、可以欢喜、可以忧。就像眼前的这小站,无论它如何破败,仍是无数旅途所不可以缺少的一环一节。人生也有许多破败之处,包括选择上的失误,过程中的不当,一段痛苦的婚姻,一宗不如意的工作,或者还有受人欺侮,上人贼船。虽然它是那样的不堪回首,可它把你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苦有乐的生命实体,没有它,人生就无法延续下来。就像一件穿了多年的破内衣,由于习惯,自己甚至不能察觉它的坏损。
在后来对小站的回首中,我努力想把它升华到具有文化地位和历史意识的高度,想从中找到一些哲学感来。越是如此越是发觉事情的奇妙,我不但不能抽象出形而上来,反倒变得更加形而下。随着时间的延长,我对小站的回望也越来越多,我很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多日无人与之长谈,许久不知山外消息,我太渴望能见到一个熟人了。每当那驻足不前的大小客车开门吐出一堆堆的人时,我总是希望从中见到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身影来。在一次次的失望以后,我甚至觉得此刻哪怕遇上那种曾让自己恨之入骨的人也行。幸亏我并没有这种机遇,真的那样,我肯定还是无话可说,而只有那种又与自己的历史打了一回照面的感觉。
面对过去,许多人可能都会无话可说。这不是一种无奈,每个人在“过去”面前永远都是一个幼稚的小学生。尽管每个人的过去是每个人造就的,过去仍旧固执地教化着每个人。我从小站来,我记得小站以前的一切的路,但小站以后的路呢?小站只是又一个起点,它不能告诉我什么,可它是我前程的唯一依靠,或者说是离前程的最近之处。人恋旧大概也是这个缘故,旧事再难过,它也是踏实的,而未来总在虚幻之中,缺少一种安全感。我老是回头看小站,一定也是感觉到前面的路太长了。
15
天没亮爷爷就喊醒了我。
上学的行李他都替我收拾好了。
西河镇是客车终点站,容易搭上车。可爷爷非要我走十里路,到一个小站去等车。
我说,你这不是巴不得人死吗?!
爷爷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下一站叫甲铺。
甲铺的招手站牌下别无他人。爷爷掏出一只布包,亲自塞进我的贴身衣兜里。
弄好后,爷爷说,这是一百元钱,好生点用,要管半年啰!
我问,这么多钱,是哪里借的?
爷爷说,你只管多读书,多识字,别的少问。
远处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爷爷说,客车来了,车上可能都是熟人,有人若问,你就说多走几步可以省几角钱。
一会儿,客车来了。
爷爷又说,昨夜听见鬼叫的事,你不要和任何人说。说出去会不吉利。
车停下来后,爷爷将我的行李搬上车,有几个人和他打招呼,他也顾不上回答。
爷爷退到车下时,我想起习文说的,让我走之前到她那儿理个发,就冲着爷爷说,我没有和赵老师告别,回头代我谢谢他。
大概是汽车在呜呜鸣笛,没听见,爷爷对我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
车上果然都是熟人,翠水和蓉儿都在。
蓉儿穿着一身新衣服,眼圈红红的,脸上也阴阴的,几次扭头想和我说话,可嘴唇一动又缩回去了。
蓉儿的母亲和几个婶娘坐在她的周围,身上也都是穿着八成新的衣服,喜气洋洋的脸上隐现着少许不安。
我听见坐在旁边的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窃笑着说些什么,其中一句是,瘸子去相亲,男的怕是个瞎子啵。
翠水坐的双人座上,另一个人是金福儿,她将头靠在金福儿的肩膀上,像是睡着了。
车上的人差不多都没理我。
只有金福儿和我说了一句,问我怎么才去报到,大桥都走一个星期了。还对我说,大桥和我是一个寝室,但不是一个班。
蓉儿一家在一个偏僻山村前面下了车,她们一下去,路边的一群人便围了上来,都是一脸的笑。
蓉儿的母亲接过别人递来的一支烟,叼在嘴上,一个男人连忙用火柴给她点火,划了几根都被风吹熄了,蓉儿的母亲就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机,手指一蹭,火苗蹿出老高。
客车开出老远,我还看见蓉儿母亲的嘴巴仍在冒烟。
我在县一中大门口下车时,翠水仍在金福儿的肩膀上睡着。
我挑着行李去了学校总务科。总务科的会计接过我的钱,说,你是最后一个来报到的。
会计数钱时,眉头一皱一皱的。那钱脏兮兮的,上面有很多油渍。
望着那么多的钱,我心里很奇怪。爷爷去年借钱是那样的艰难,东家几角,西家几块,才将学费凑齐。这一次,挨到最后却如此顺利,眨会儿眼就齐了,简直像去银行里取存款一样。
会计将钱数了两遍后,退回十元钱。
我小心翼翼地问,学费是多少?
会计说,一百元呀,你不晓得吗?
我说,你是不是数错了,这钱正好是一百块。
会计犹犹豫豫地又数了两遍,然后不高兴地说,你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怎么自己没个准数。还怀疑我数错了,是不是想学雷锋,搞捐献,那你就交一百一吧。
我捏着钱不作声,手心却直冒汗。
出了总务科,我看了看手中的十元票子,那汗渍渍的样子,很像昨天赵老师准备送给我的那一张。
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分给我的铺位上,被先到的同学扔满了月饼包装纸。除了过年以外,我和爷爷没有别的节日,我不知道别人的中秋节是在什么时间。
这时,下课铃响了,我赶紧挑上随身带来的柴和米,到事务长那儿换成饭票,我没有钱买菜票,只能吃从家里带来的腌菜。
回到寝室,大桥一脸激动地冲过来,双手抱着我的肩膀,连声说,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我说,闻你妈的屁去。你以为我读不成书了?我偏要读。
大桥说,你读书算什么新闻。赵老师被人杀了,杀成了五马分尸!
我说,大桥,你放屁连臭都不臭。
这时,班里的学习委员苏米进来问,你是学文吧!
我说,是的。
苏米便告诉我,班主任听说我来报到了,让我去领书,下午要上课。我便和苏米一起走了。苏米剪着男孩一样的短发,穿着一件牛仔裙,胸脯也凸起来了,走路的姿势很像电视里的香港女孩。我知道大桥一定在盯着看她,便回头呸了一下。
31
爷爷到家时,已是半夜过后。电灯开关线断了,我摸索着点了半截蜡烛。
大桥一见爷爷手上的衣服就叫起来。
大桥说,学文,别要!这是从外国人的死尸上扒下来的,上面什么病菌都有。有的还有艾滋病。本来工商所要没收,是我妈去担保下来的。
爷爷瞟了大桥一眼,说,你妈真是好干部,待金福儿这样好。
大桥脸上一红,不说话了。
爷爷瞅了瞅那两件衣服,说,管它什么病菌,总熬不住开水烫。
爷爷将两件衣服放进锅里,又舀满了水,盖上锅盖,便去灶后点起火来。
灶火将爷爷映得红通通的。
不一会儿,锅里的水就咝咝作响。
我揭开锅盖看了一下,说,这衣料是化纤的,一煮就没用了。
爷爷一听,忙将灶里的火弄熄,又用手去锅里捞起衣服,扔在脸盆里。
正忙着,外面有人敲门。
开开门,镇长站在我面前。
镇长一个劲向里走,边走边说,大桥在你家吧?
我说,是的。
镇长说,你没听到广播,怎么不去报信?
我说,正忙着将金福儿给的衣服消毒呢,没空出工夫来。
镇长站在屋当中,说,大桥,出来随我回去。
大桥在房里说,我不回去。
镇长正要进去,大桥又说,你别进来,屋里还有个没穿裤子的男人。
镇长稍一怔,还是进去将大桥拖出来。走了几步,大桥一把抱住桌子腿。镇长拖不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
大桥说,要我回去也行,以后夜里你不能将我一个人丢在屋里。
镇长忙说,行行。
大桥说,今天是谁当的叛徒汉奸,出卖了我?
镇长说,是赵长子告诉我的。
大桥说,赵老师太没骨气了。
他们走后,我将夜里的事全告诉了爷爷,爷爷听后,夜里再没有开过腔。
第二天早饭后,爷爷和我一道去找金福儿。走在街上,看见派出所门口贴了一张招领启事,说赵老师昨夜在金福儿家附近,拾到衣物一包,有遗失者来派出所认领。
栖凤酒楼的王国汉和蓉儿的爸正在高声议论。
王国汉说,赵长子这家伙真酸,这大年纪了还想学雷锋,既是捡的东西,拿回去就是。
蓉儿的爸说,衣服不同别的,一穿上身别人就能认出来。
王国汉说,改个样式,或者染个色不就认不出来!
爷爷上去问,国汉,金福儿到酒楼里了吗?
王国汉说,这么早,酒楼还等我去开门呢!
我和爷爷便回头先去金福儿的废旧物资回收公司。
公司里坐着几个人,我们问时,他们指着正在门外踱步的一个人说,县文化馆的小曾也在等他呢。
等一会儿,我坐不住,跑到门外和那个踱步的人搭话。
我说,曾老师,你认识董先生吗?
小曾说,老董和我住一层楼。
我说,他最近在家吗?
小曾说,在家,身体不大好,哪儿也去不了。
我说,是不是在写一本书?
小曾说,一天到晚总见他写,可就是不见发表出来。
我说,那本谚语不知编好了没有。
小曾说,编是编好了,就是没有钱印。
我说,曾老师你也是写书的吧?
小曾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省报,指着一篇报告文学说,这是我最近发表的一篇较满意的作品。
我看见那文章的标题是《新破烂王金福儿》。
小曾又掏出一个会员证给我看,说,我是省青年诗歌学会会员。
正要再问,爷爷喊我去栖凤酒楼看一看。
路过派出所时,正好碰见大桥夹着那包衣物从门里出来。
大桥走到墙边,将那张招领启事撕成粉碎。
栖凤酒楼那儿也没见到金福儿。
再回到废旧物资回收公司,金福儿正坐在那里和小曾谈得热火朝天。
听了一阵,听出了些头绪。小曾写的这篇《新破烂王金福儿》,省报要收三千元钱。小曾是来讨账的。金福儿还想让自己的名字上《人民日报》,问小曾这得花多少钱。小曾答应回县后找朋友打听一下,不过估计不会低于一万五到两万。
后来,王国汉送了一张现金支票过来。小曾接过支票,笑一笑后起身告辞。
小曾走后,没等爷爷开口,金福儿就主动说,我刚才到处问过,找过,实在是一点现金也没有。
爷爷后来站在街中间叹气,险些叫一辆汽车给撞了。
爷爷说,我算是白救了这一对杂种。
93
离开学还有三天,我就去了学校。
一进寝室就发现大桥也到了,只是不见他的人。
我去商店买了一只悬着十字架的金项链,然后到车站接苏米。
十二点刚过,从武汉来的客车到站了。
苏米在车门出现时,我眼前像是升起了一颗太阳。
我们相互笑一笑什么也没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纸包交给苏米,要她回家后再打开看。
苏米的妈没有回,她在武汉还要待一阵子,也没有别的事,就是看看孙子。
回到苏米的家,苏米匆匆擦了一下脸,就钻到房里去了。接着,我听见了一声惊喜的欢叫。
不一会儿,苏米戴着项链走到房门口,说,学文,这真是你送给我的吗?
我走过去,猛地将她拥抱着,说,我能进来吗?
苏米挣扎着说,不,我答应过习文,我不和她争你!
我不理她,慢慢地低下头,对准那绯红的嘴唇深深地吻起来。苏米的嘴唇极柔软,简直可以像水一样融进我的心里,接着她的身子也变成了一团水,从那甜甜的舌头里,一阵阵地冲向我的心里。她的身子变得极薄,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
我说,苏米,我爱你!
声音是那么深沉,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那完全是一种成熟的男性的一种宣言。
苏米哭起来,说,我等这话都快等成老太婆了。
我一点点地将她脸上的泪水舔干。
然后,匆匆地做了一点吃的,接下来的整个下午,以及下午以后的黄昏,我们都是这么深深地吻着。
天黑后,苏米的爸回来了。他一进屋就打开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送本县新闻。屏幕上的两个人是胡校长和金福儿。播音员介绍这条新闻是部分政协委员座谈怎么发展我县的教育事业。
新闻完后,屏幕打出一条广告:值此县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县著名农民企业家金福儿,特独家点播电视连续剧《威镇天河镇》。接下来是一组有关金福儿的镜头画面:金福儿在会上讲话;金福儿拿着计算器算账;金福儿在栖凤酒楼前送客;金福儿对文化馆的小曾说:我的启蒙老师姓赵,可后来我将他教的东西都还给他了,我现在是自学成才……
苏米忽然说,《威镇天河镇》?改一个字不就成了《威镇西河镇》!
我说,这是他的本意!
苏米的爸在厨房里大声说,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的同学大桥,今天中午在公园里和一名妓女鬼混时被当场捉住了!
苏米说,关起来了吗?
苏米的爸说,就算她妈来保,也要关上五至七天。
我说,这都是金福儿害的。
正说着,文所长打来了电话,他替镇长求情,说如果一抓大桥,这对镇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要苏米的爸看在他们孤儿寡母的分上,放了大桥。
文所长说,镇长在到处买安眠药,弄得医院的医生、护士怕得要死,又不敢不给,后来还是他亲自用万能钥匙偷偷打开她的门锁,用维生素将那五十粒安眠药掉了包。
苏米的爸只是嗯嗯地应着,一直到放下电话,也没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电话刚接完,胡校长来了。
胡校长也是为了大桥的事,然而他考虑的是学校的荣誉,真的抓了大桥,一中这几年辛辛苦苦得来的省地县三级模范学校也就完了。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苏米一听,竟是金福儿。她按下免提键,电话里的声音满屋都能听见。
苏米的爸一听金福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来。
于是,苏米便对着电话挑衅地说,金福儿,我爸让我告诉你,他现在不在家!
金福儿在那边愣了一会儿,说,我大小是个政协委员,你爸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请你转告你爸,我已和公安局长谈过了,你们一放大桥,我就赞助一辆三轮摩托给刑侦队。
苏米的爸在一旁吐了一大口痰。
我冲着电话说,金福儿,你的钱怎么这不干净,我在电话里都闻到了垃圾味!
金福儿说,你是学文侄儿?赵长子大概没有跟你讲过,世界上的钱,没有哪一张是干净的。赵长子没有这种体会,你现在多少应该有了。再说广一点,世界上哪一件事物又是干净的呢!
我说,金福儿,你毒害不了我!
金福儿说,我很高兴将来能有你这样的对手,快点长吧!和大桥一样,多与几个女人睡一睡,会长得快一些!赵长子、镇长、五驼子和你爷爷都垮了,我一天到晚闲得慌呢!
我还想说,苏米将电话机上的免提键复了位,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胡校长喃喃地说,我从未见过如此赤裸裸的卑鄙!
苏米的爸说,我们还是换一间屋子谈吧,接触这种事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早了一点!
他们往里屋走时,苏米忽然说,爸,我也求你将大桥放了。
苏米的爸说,为什么?
苏米说,你不是说过,监狱是最坏的一所学校吗!
苏米的爸想了想,回头问我,学文,你说呢?
我说,如果要关大桥,那先得将金福儿枪毙了。
他们进屋后将门关起来。
我对苏米说,我晓得世上最少还有一种东西是纯洁的!
苏米将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我将身子挨近了她。在我们的嘴唇刚一黏合时,苏米的舌尖就送到我的嘴中。
在相拥着走向苏米的房间时,我听到整个世界都在渴望地说,我爱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