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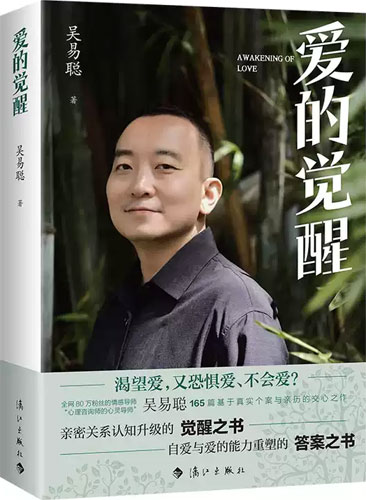
《
爱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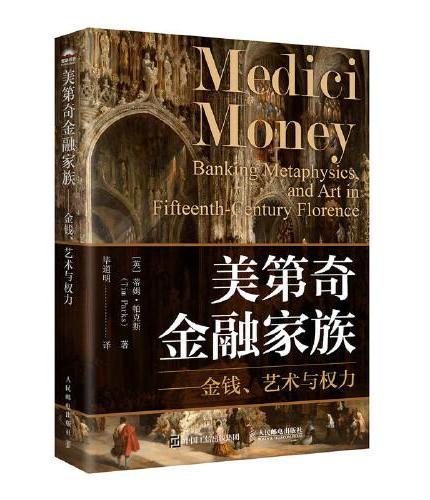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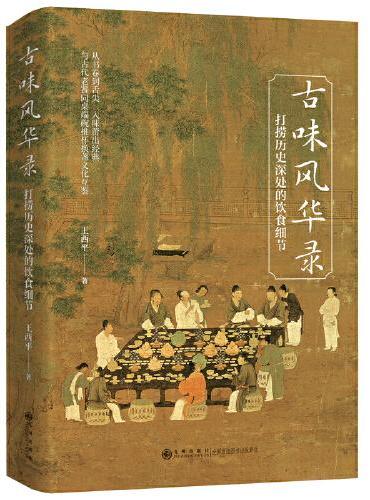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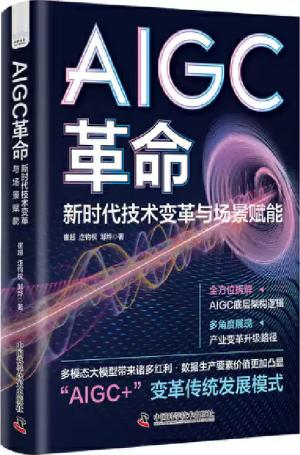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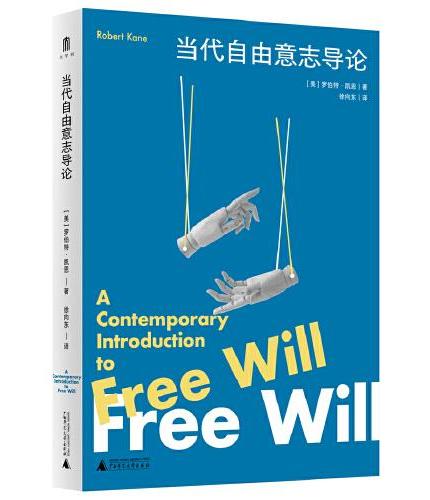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NT$
347.0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NT$
449.0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瑞士]安德烈亚斯· F.克列诺](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5/12/9787111768685.jpg)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瑞士]安德烈亚斯· F.克列诺
》
售價:NT$
454.0

《
中国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报告2025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不负青山和绿水。在时代巨变面前,乡村如何发展,如何进行文化传承,如何让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同步发展?金米村中的追梦者们给出了答案。
从非虚构类作品的角度,温情地观望我的故乡……
|
| 內容簡介: |
|
《山语——金米笔记》是一部纪实文学,重点反映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自脱贫攻坚以来乡村振兴新征程上的可喜变化。作者通过长期的实地采访和驻村工作,以专题故事的形式展现村庄产业带动发展,解放思想,进而带动全村面貌和村民生活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艰辛历程,呈现出一幅山、水、人共兴、共富、共美的和谐画卷。作品以四组独立又相关的故事展开情节,塑造了年轻而富有闯劲的乡村基层干部群像,以及他们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建设新家园中遇到的困难和收获。
|
| 關於作者: |
|
张国宁,现任陕西网总编辑,先后在《求是》《中国组织人事报》《当代陕西》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作为主创人员连续三年获得陕西新闻奖一等奖;荣获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陕西省网络内容建设先进个人等称号。左京,当代陕西杂志社记者,多次获陕西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创作的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入选中宣部第四届“期刊主题好文章”。
|
| 目錄:
|
第一章
耳子
菜园子风波
“倔老头”
咸嫂子
木耳博物馆
第二章
余村取经
“都管”
党员会
田方办厂
火儿入党
第三章
米汤街
老人与牛
茄子栽荚 辣子栽花
敬老院
古寨
第四章
将台子
金米村的“布达拉宫”
撤校
复校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东经108°49′25″—109°36′20″,
北纬30°25′31″—33°55′28″,
“柞水木耳”地理坐标。
耳 子
01
山里的雨脾气烈。
金米村白天还艳阳高照,像是要晒化人,麻影子时才聚了一点儿黑云,一擦黑说发作就发作,闪电像要把天撕裂,雷炸得地都能抖起来。避在大棚里的吊袋木耳还好,就是不知大田里的地栽木耳受不受得住。
我初来乍到,遇上的村支书李正森是个热心肠。
小伙儿30出头,身高一米八,体重超200斤,皮肤黝黑,盯着人说话的时候黑眼仁几乎全露出来,眼皮一个单、一个双。他看起来五大三粗,嗓音却极柔和,喊来两个女村干部帮忙,把我安顿在村委会二楼靠西的一间房。
雨夜闲来无事,便捧起一本《柞水县志》读,想搜寻点与金米有关的文字,不觉越读越入迷。
县志里讲,柞水地貌大势犹如手掌,山脉呈手指状依次向南、东南延伸,流经金米全村的社川河则如指缝由北向南蜿蜒。受东西向和西北—东南向的构造断裂所控制,同时遭受长期风化剥蚀,由此形成山岭纵横、千沟万壑的掌状岭谷地貌。
这种山大沟深、土薄石多的特殊地貌,导致境内耕地面积仅占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且分布流散,形状不整。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地处秦岭南麓,林木与中草药资源丰富,又因地质史上的燕山运动时期褶皱和断裂伴随着岩浆活动,带来丰富的矿液,生成多种多样的矿床,自唐中期便有人来此淘金……
及至夜半,窗外雨声渐小,河水声不绝。迷迷糊糊入睡,直到隔壁院子里两只公鸡争相打鸣方被闹醒。
早起与正森相约,直奔一组财富湾的地栽木耳基地。已经有不少耳农拎着铁桶下到田里。上年纪的坐着小板凳,把木耳菌棒横在腿上,左手转动棒子,右手来来回回地挑大拣小、挑肥拣瘦。
柞水当地老百姓管木耳亲切地称为“耳子”,摘完一茬又有新的生发出来,因此摘木耳又叫“拣耳子”。细看整个劳动场面,不觉令人啧啧称奇,再没有比“拣”字更传神、更贴切的了。
我就近掬起一个菌棒,嗬,分量可不轻。接地气的那一面,木耳朵儿明显更大更稠密。正森眉飞色舞,跟耳农们聊得热络:“耳子这东西喜欢雨水,只要不下雹子,越是电闪雷鸣越能激发出它的灵性,长得越好。”
放眼望去,只见两山对开,一层又一层的山头叠着,山间升腾起雾霭,笼着这条上望不到边、下看不见头的川道。
照正森的说法,柞水的山大多以山形命名。
比方说钟鼓山,山似洪钟矗立,却又有平地一片;再说狮头山,山中间鼓起一个包包,身下好似有两只前爪伸将出来,像极了毛乎乎的狮子头。金米村沟口叫“金龙嘴”,也是这个缘故。
山都是被树盖着的,当中最显眼的自然要数杨树,但村里老一辈的人却最中意耳树。耳树又叫柞树,正森领我上坡看:这种阔叶树树皮糙厚,小时候呈棕色,长大了逐渐变成黑色,连树上的裂纹也跟着狰狞起来。
这树用处却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耳树被山民锯成长短一般齐的木桩,桩身打出一排排小洞,塞入菌种,盖上盖儿捂住,不久就能长出耳子来。当地有文人墨客为木耳写赋,称赞其为树上精灵,“一包贮天浆”。
前些年封山育林,对这种老式的“段木点耳”生产方式有影响。不过山封了,种木耳的营生却没封,而是通过别的山路迂回了——金米村现在搞的是木耳代料栽培,而且不是一家一户在弄,有基地。代料的好处是护了树林而且高产,基地则带来集约与高效。
只是作为大山的馈赠,每年仍有少量耳树通过疏林计划,变身木耳代料中的木屑,“零落成泥碾作尘”,为这川道里蓬勃而出的“大地耳朵”源源不断地供给营养。
02
关于金米村的由来,最流行的说法是“山上有金,地上有米”。
为把这事儿弄确切,正森打算专程带我跑趟火儿家。火儿大名叫尹宇炳,是村委会副主任,村里人喊惯了“火儿”,大名反倒叫得少。他爸是金米村的“活字典”、80岁的老文书尹宏志,对金米的来历知根知底。
逆流而上。一条与社川河几乎完全平行的水泥路贯通整个村庄,中间又有小道从主干延伸出去,如同一棵大树上横七竖八冒出的枝丫。这正应了县志上“掌状岭谷地貌”之说。
不同年代的民居交错在一起,其间夹杂着大大小小、新旧不一的厂房,那是生产木耳菌包的中博公司和20世纪80年代末入驻金米的陕西银矿。民居散漫,厂房高大,很有一种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交融的感觉。
火儿家在岩屋沟口。金米的五个村民小组,分别对应了五个小地名:财富湾、郭家庄、瞿家湾、米汤街和岩屋沟口。显然这些名字的由来都是人类活动与山川自然的结合。五个小组自沟口向沟垴依次排列。
木耳基地的分布也大体与此对应,占的都是村里最平整的耕地,数火儿家跟前这个地势最高,也更靠近水源上游。
我们上了桥,瞅见火儿媳妇正独自一人扯着塑料篷布的四角,从大棚里艰难地往外拉拣好的耳子。见有客上门,她急忙撂下手里的活,一边朝过跑一边拍掉身上的灰。
马上要进6月门了,门前那棵杏树树梢上,杏子皮儿渐渐透出红来。小院里栽着草莓,都藏在叶子下面,个头不大,吃到嘴里却酸甜酸甜。
火儿媳妇麻利地摆好板凳,倒上茶水,又到菜园里随手揪了一把蒜苗,嫩白的新蒜便露出头。一转眼工夫,她像阵风般消失不见了,火儿他爸从旁边的土房里徐徐迈步走了出来。
老爷子眉毛胡子全白了,却耳不聋眼不花,红光满面。他没住在火儿前几年起的二层小洋楼,原因是就喜欢他那睡了大半辈子的土炕,谁也拗不过。
“伯伯,我们来找你谝个帮子。”正森赶忙迎上去,右手拉起老人的左手,又用左手抓着老人的右手叠在一起。
冷不丁被搅了午觉,老爷子原本有些迷糊,一看来人是正森,又问的是“正事”,他正襟危坐,抖擞精神讲了起来。
1960年,金珠社和米川社合并,都采头一个字,叫金米村。最早分12个生产小队,大姓有6个,邹、赵、王、谢、江、陈。
我记得初级社时人口还没过千,有一年收成不好到处人饿饭,又从凤镇迁来好些人,也就有了肖、曹这些小姓。别说这个,年景不好的时候关中道都有人把娃往山里送。
外间传金米“山上有金,地上有米”,现实情况也差不离。从前只要你眼睛能看到的平地,栽的全是稻子。我们的稻子和别处的可不一样,叫个马稻子,白米上面有红道道,适宜半高山种植。河道差不多跟地一样平,引了水渠到地里,金米有这条社川河,再旱再涝不断粮。
山上也确实有金,就是量小,但银多,唐朝时王洪、孟喜在咱这开过银矿,现在那些古矿洞还在。论起来金米前多年的风光、红火都离不开银矿。
20多年前村集体就有自己的百货大楼,四层楼气派得很,卖布的、卖脸盆肥皂的、卖副食粮油的,十里八乡都羡慕。
火儿他爸讲的是方言,连说带比画,我云里雾里跟听天书一样,全凭正森在一旁翻译,才记下这些。老人见状也急,干脆要过纸笔自个儿写了一段。不愧是当过30多年村文书的人,手微微颤抖,落下来的字却骨架不散。
我曾经看过一份史料,柞水县从秦汉时起便有过多次南、北移民,其中,清康熙年间开始的“湖广填陕西”移民政策更是奠定了如今的人口格局。在这一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南来的“下户人”与先迁入居民的语言发生重构,形成了如今“北方音,南方调”的柞水话。
到了正森他们这一辈,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都没问题,但村庄内部交谈多用土话,吐字慢、咬字轻,悠扬婉转,跟唱歌似的,话尾多带“儿”音,而且特别喜欢给名称后加“子”字。
“正森,在这儿凑合吃噢。”火儿媳妇笑盈盈打起门帘,客厅里果然摆上了一桌子菜,还有一把黄铜酒壶。柞水老百姓好客,无论家境贫寒还是富裕,有客来一定要端上自家做的甘蔗酒或是高粱酒,以示尊重。村里现在还常见吊酒的大黑铁锅。
我随火儿媳妇进到厨房帮忙。刚才拔出来的新蒜在臼子里早被砸成一窝蒜泥,她舀了一勺放在胡铁汉上,拌了拌,喷香。只是蒸玉米发糕时添多了水,用筷子捅了一下,心儿倒是熟透了。
大伙一起吃饭,火儿媳妇却再唤也不上大桌,拨了些菜在旁边的矮桌上吃。她时不时抬头望我,不安地问:“你怕吃不惯吧?”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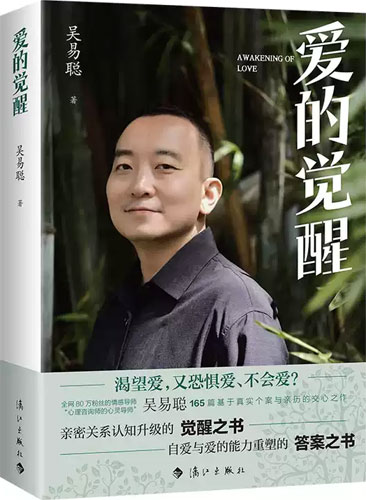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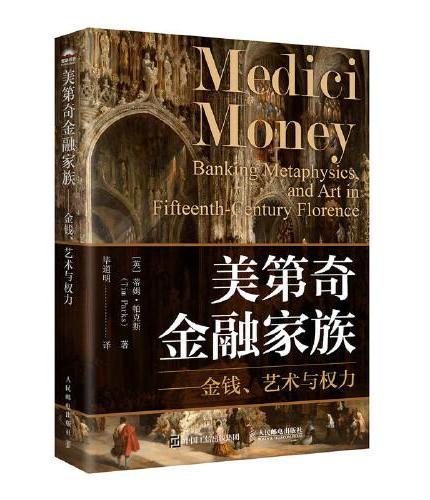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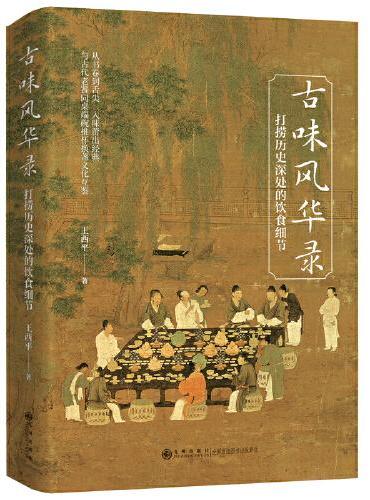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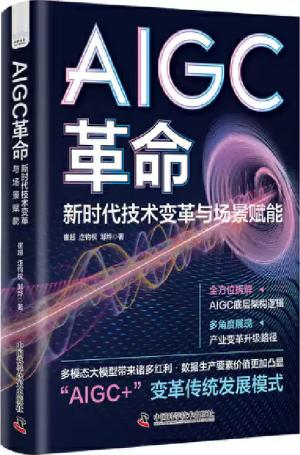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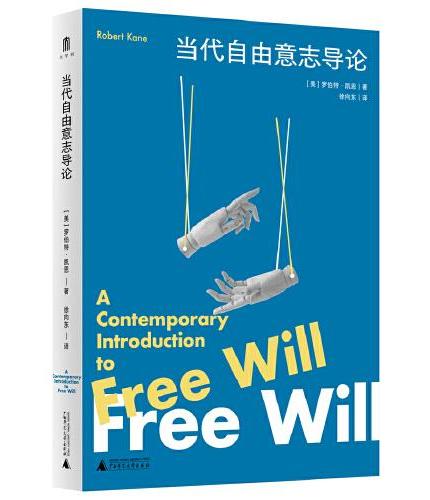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瑞士]安德烈亚斯· F.克列诺](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5/12/97871117686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