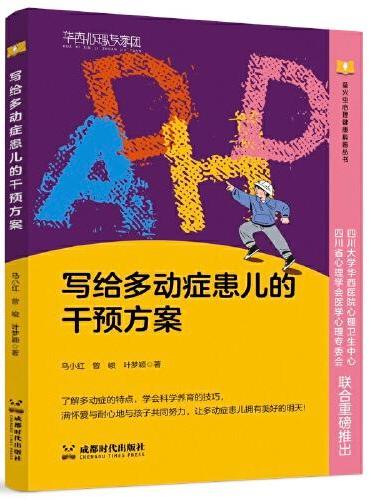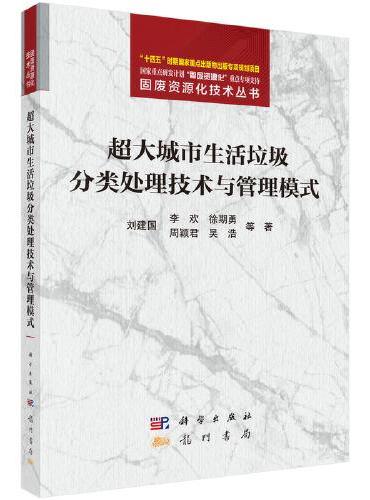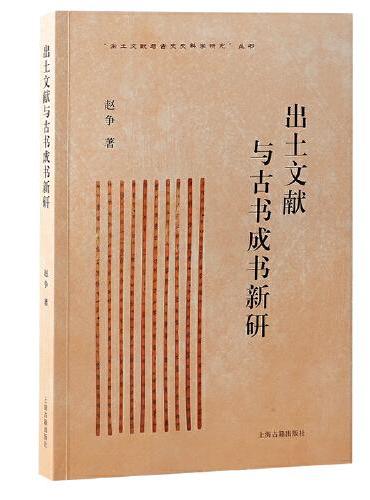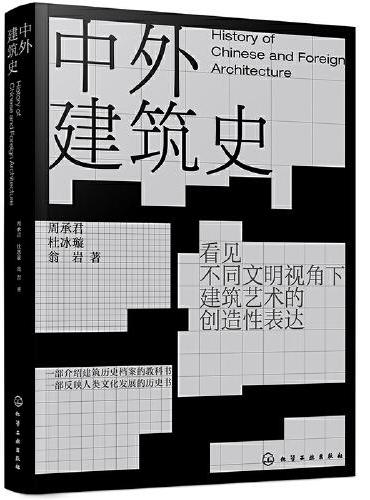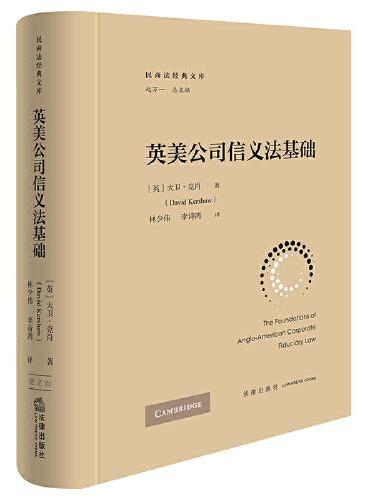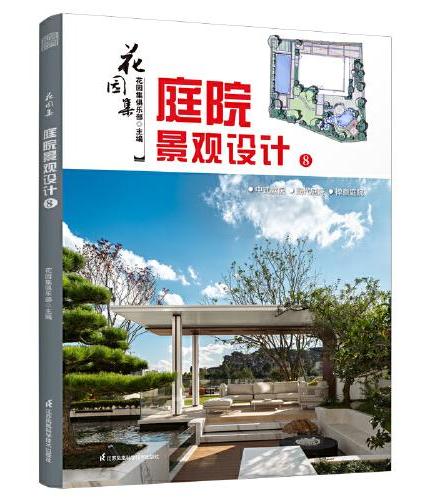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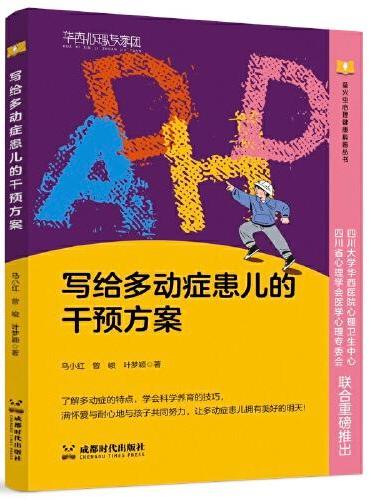
《
写给多动症患儿的干预方案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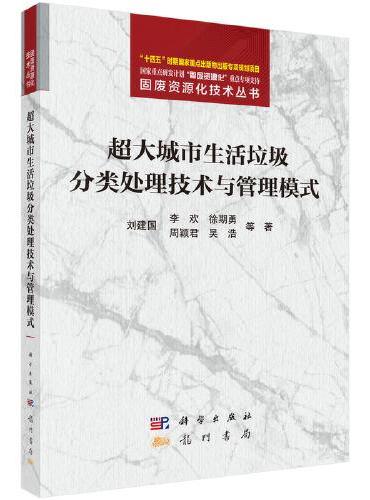
《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技术与管理模式
》
售價:NT$
551.0

《
九色鹿·松漠跋涉:辽金史学步
》
售價:NT$
5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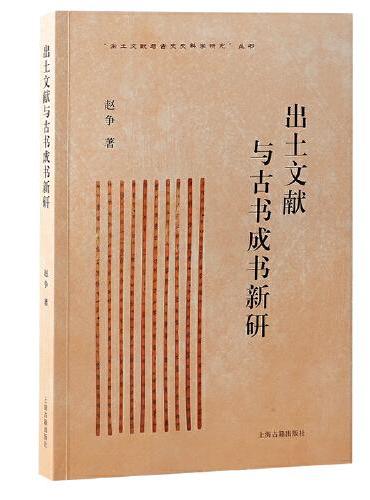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新研
》
售價:NT$
449.0

《
内敛心态与唐末诗风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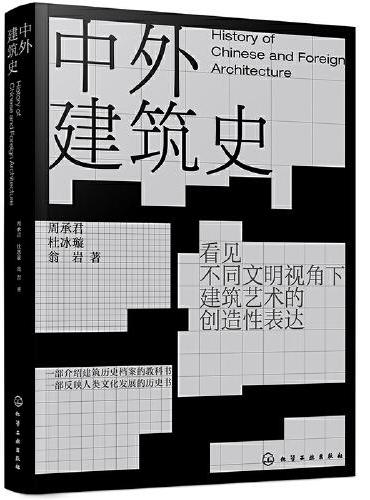
《
中外建筑史(周承君)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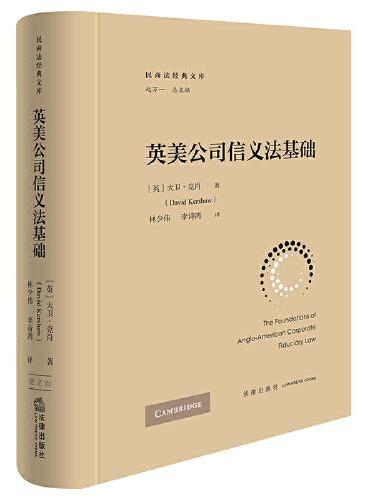
《
英美公司信义法基础
》
售價:NT$
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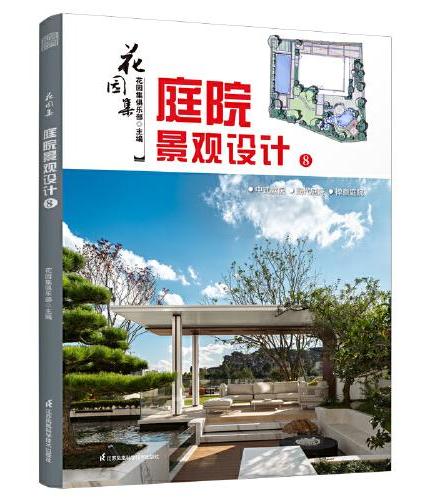
《
花园集 庭院景观设计8
》
售價:NT$
356.0
|
| 編輯推薦: |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跨出封闭的世界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综合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广大区域进行长时段、整体性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经典著作。
袍哥
1.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兼备文学式的描写与严谨的历史研究;
2.微观个案与宏观历史的完美交织,在宏大历史背景之下审视个人命运的沉浮;
3.传奇色彩与历史的深度同时呈现,将对袍哥的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上加以定位,展现更饱满、立体和丰富的川西社会图景;
4.回应大众文化中对秘密社会的猎奇心态,褪去浪漫想象和英雄光环,还原1949年以前影响**的秘密社会——袍哥的真实面貌;
5.以丰富的素材,重建民国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模式,还历史以血肉;
6.图文并茂,栩栩如生地展现中国近代民众生活的种种细节。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综合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广大区域进行长时段、整体性
|
| 內容簡介: |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馆为研究对象,力图以此为窗口,探求20世纪上半叶成都人的生活实态。作者采用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从茶馆的休闲、社交、娱乐、经营、群体、组织、秩序等多个角度,切入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使读者得以真切感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成都城市历史的脉动。作者以丰富的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细节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极佳地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袍哥》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袍哥》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从自然环境、人口状况、农村经济发展、区域贸易与市场网络、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统治结构与地方秩序、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等多个角度,对1644—1911年间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况,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全书综合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广大区域进行长时段、整体性的研究,被学术界视为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本次再版,作者根据近年来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删繁就简,使全书内容更加凝练、清晰。
《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本书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 ,以“叙事”的方式考察公共空间 、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将“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 、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
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当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时,便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随后在革命运动中,民众又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民众和精英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组织自卫活动捍卫他们的生存,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与以往研究的角度不同,本书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
|
| 關於作者: |
|
王笛,1956年生,现任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共同主编。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将在“博雅撷英·王笛作品集”中陆续推出。
|
| 內容試閱:
|
二十年后话街头
——《街头文化》中文版第三版前言
本书英文版是200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文翻译版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第二版。时间过得真快,英文版已经出版20年了,中文版已经出版了17年。这些年我继续以日常生活为中心,以为民众写史为初衷,用微观历史的方法,完成了20世纪茶馆的两本英文专著和一本袍哥的著作。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社将出版本书中文版的第三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对本书出版后学术界和阅读界反响以及一些感想。
令我欣慰的是,这本书在中西方都得到了积极的肯定。英文版在2005年获得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最佳著作奖,中文版在2006年被《中华读书报》选为十佳图书。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这本书一直在学术界、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中,产生着它的影响。当我在大学做学术报告的时候,经常都有学生拿这本书来请我签字。北京大学图书馆 2020年4月18日发布的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2019热门借阅图书”云书展,《街头文化》与《百年孤独》《想象的共同体》《平凡的世界》等我喜爱和崇敬的书同在前十的名单上。对我来说,简直真是难以置信。对于读者的青睐,甚至有点惶恐不安。
这本书引起广泛反响的原因之一,我想应该也是由于中国城市正在发生的重大变迁,许多古老的城市正在一天天的消失,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虽然我研究的是清末民初的成都,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实际上也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以及政治史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在中国仍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的认同。我特别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阵营之中。《街头文化》在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眼光向下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这本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城市规划、大众传播、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家的关注。去年10月,三联人文城市季在成都刚建成的東·壹·美术馆,举办开馆首展“日常史诗:成都市民生活与公共空间”。这个展览便是根据我的四本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 》,从的宏观历史逐渐聚焦到成都市内的具体空间,展示从望远镜到显微镜的四层“成都维度”,由13位当代艺术家和建筑设计师进行再创作,分别对应一个或多个维度,从“西南地区时空”,“成都城市时空”,到“成都室外公共空间”和“成都室内公共空间”,各个维度进行互动和对话。还举行了展览开幕论坛。看到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够走出象牙塔,为现实社会服务,感到是莫大的欣慰和充满着成就感。
为民众写史
本书出版以后,据我目力所及,共有16篇英文书评,对于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在西方能得到这么大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2006年中文版前言中,我对英文世界发表的书评已经有一个概述和评论。在这个中文第三版前言中,我想主要讲讲这些年来中国学者对这部著作的反应。书出版之后,很快成为了当年的“学术畅销书”,出现在各种榜单上,专业刊物和报刊发表了很多书评。就我已经读到过的中文书评便有四五十篇,包括《历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中国学术》《中国图书评论》《读书》等杂志,还有更多的像《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等报纸。
马敏在《历史研究》发表了长篇深度评论,肯定了新著之是由于视角转移所造成的“感觉之新、领域之新、方法之新……著者以非凡的功力,对老成都街头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生动的叙述,对活跃于街头的各种群体也进行了归类描写……显然,王笛新著在风格上的追求,已接近于人文史学的追求,旨在生动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全幅式场景,使历史变成可触摸的、可接近的,能够普及于民众的。但如果细分一下,在叙事风格上,王笛又明显不同于史景迁式的以扣人心弦的人物命运和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为中心线索的叙事,而毋宁更接近于黄仁宇似的徐徐展开、风俗画般的历史长卷。”
任放则从更宏大的背景讲本书的贡献,认为《街头文化》“不仅在学术上完成了自我蜕变,而且颠覆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的叙事结构,确立了一种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尽管这一范式难掩‘西学’本色,但其推陈出新的革命性意义是醒目而深远的。” 王先明等更强调了本书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新的问题的提出,不仅决定了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决定了研究视域的突破与创新。王笛的《街头文化》无疑是这种实践的优秀成果。”
朱英等把《街头文化》与我早期的《跨出封闭的世界》和后来的《茶馆》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并着重讨论了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他们指出《街头文化》是“作为城市社会史研究的著作出版的,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把其与新文化史联系起来,但是其研究视角和方法却都明显地受到当时已经在欧美流行的新文化史的影响,王笛的社会史研究也呈现出较明显的文化转向。”而且书评也表达了对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批评的看法:“大众文化和微观研究虽采用小处着眼的方法,但其方法不仅是史学研究的进步和突破,同时也是史家本身史观的提高和升华,所以一味否定新文化史成果则有妄加批评之嫌。”
谭徐锋则欣赏本书对民众的命运的关注:“王先生心细如发,他发现,在一拨接一拨打乱再造的改良或革命中,民众平静的日子被搅起深深的涟漪,如果说起初他们还比较配合,那么到他们发现涟漪化为回水沱,偌大的成都街头已经放不上一口破旧的饭碗之时,尽管他们面容悲凄地四处述说,然而改良精英往往为宏大的(其实更多是自我的臆想)目标而激奋不已,参与者的民众只好成了历史祭坛的牺牲。” 的确,这个评论,是看到了我力图对历史的拷问。人们引述最多的是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句话其实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句话所得到的启发。我想表达的是,有些所谓的“革命”是打着为民众的旗号,但经常最终的结局,却是民众成为了牺牲品。
甚至直到最近,还仍然有学者就这本书进行的讨论。虽然学界对我在本书中的观点并不完全同意,但是《街头文化》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模式却引发了学者的持续思考,如《读书》2022年第12期发表晋军的《大众何谓?公共何为?》的文章,认为“王笛对成都街头公共空间的研究扩展了‘公共领域’范式的研究视野,不但确认了普通民众同样是公共事务中的行动者,而且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互动之中加入民众的维度,可以探讨其中的多向关系。立足‘公共’,关注‘大众’,是《街头文化》的真意。”因此《街头文化》“翻转了大众反抗范式对现代转型与大众文化的讨论。在王笛看来,即便有大众反抗,也是社会转型的后果,而并非转型的动力。”强调要从下层民众的视角来探讨现代化的社会后果,“而他对现代转型的态度也从积极评价转向了关注转型对民众生活及地方文化的冲击。”
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极大的关注,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一、研究视角转移,从社会底层往上看,了解普通人,关注日常生活,对女性生活变化的考察,描绘了下层民众生活的历史画卷;二、为民众写史,从民众的眼光来看改良与革命,考察民众、精英和国家的互动,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讨论,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弱者的反抗,发现下层民众的微弱的声音;三、具有可读性,叙述的生动,资料的发掘,图像和文学资料的使用,“深描”的运用,是有趣好看的史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城市史;四、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转向,新问题的提出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运用社会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展现复杂的社会现实,重新建构一个城市的微观世界,等等。
读这些书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得到鼓励、受到启发、和自我反思的过程。《街头文化》也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下面我就一些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特别是这20年中我一直思考的与的现实社会有关的问题,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有些观点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才形成的或者是完善的,有些是与在学者讨论过程中或者媒体采访问题的基础上的一个梳理。
国家权力和社会空间
晋军——和一些读者所批评的——认为:“王笛只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分而模糊了国家的位置,也就弱化了国家或者说政治权力在公共空间改造中的力量。” 这个批评是公允的,的确在这本书中,国家(state)只是隐蔽在后面的一种力量,如果说我讨论了国家的话,最多也就是在前台的警察角色,这显然对讨论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角色在这本书中没有在前台被充分展示出来,主要是由于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焦距在地方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如果国家讨论得过多,有可能转移了本书的焦点。当然,我也在不断的思考,怎样能把这种关系处理得更好。也就是说,既能够集中讨论精英与大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同时也更好地展示处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不过,也可能是在冥冥之中试图弥补这种缺陷,我后来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空间和微观世界,1900-1950》那本书中,对国家的角色及其对公共空间的影响,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讨论。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阐述《街头文化》一书中涉及到的城市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整个20世纪,都是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社会空间逐渐缩小的过程,市民的自主性和自治也随之被削弱。过去中国城乡都有民众自己的组织,如看庄稼的护青会,自卫的红枪会,街邻的土地会,从事慈善的善堂,社区的关帝会,等等,还有像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但是它们都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一个个的消失了。当只剩下国家机器的力量时,当国家掌握了一些资源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政治权力的内卷化”。经济学上用“内卷”这个词来表示投入很多,但产出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的状况。国家权力的不断扩张,官员越来越多,就要增加更多的收入来雇佣更多的人。那么增加收入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征税,人们的负担也就越重,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
前现代的中国城市几乎都是自治的,地方精英、士绅、老百姓共同管理社区,官员的角色有限。在成都,到1902年建立了警察机构,才开始行使市政的一些最初功能。一直到了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才有了市政府。晚清新政效仿日本和美国,设立警察,管理城市的交通和卫生,乃至于小商小贩能够在哪里摆摊,什么时候摆摊,都被官府所要求,之后的国民政府也在推动这一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组织不断地被削弱,国家权力也深入了到地方社会。但是问题在于,再大的政府,如果不依靠市民,不依靠社会,不依靠社会组织,不依靠公共领域,也不可能照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国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一个城市的管理不能仅仅是政府的事,如果一切都由政府来包办,是不正常也是不可行的。一个城市要有效的管理好,就应该让社会参与,这个社会的参与包括市民和各种社会组织。政府不应该害怕城市社会组织的普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例如清代,社会组织基本都是和官方合作的,这也是一个异族的统治能维持两百多年的原因之一。那种认为只要社会的发展就是和国家权力的对抗,就是图谋不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现实社会中也是有害的。实际上社会组织越繁盛,政府得到的帮助会越大,社会也因此更稳定。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人的能动性会被调动起来,能够主动参与社会的管理,以及文化和经济活动,反之,社会就会萎缩。社会的每个链条是连接在一起的,当某个链条被人为地切断了,那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整个20世纪,政府都试图按照一种统一的模式对城市进行规范,结果中国城市逐渐变成千篇一律。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多元化是它的生命,无论是城市的管理、城市的文化、还是城市的面貌。我在《街头文化》中提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表现,那么地方的个性如何塑造了街头和公共文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过去地方的区域性和封闭程度较高,而现代社会有着更高的人口流动,这些都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文化。尤为重要的是为发展现代化进程而引进的相应模式,其中包括各种标准、以及卫生、管理、职能部门的设立等等,逐渐改变了各个城市的内在和外在。由于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过去我们可以在街巷、市集、庙宇等看到各种地域文化展现出的地方特点,但是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逐步趋向同质化。由于城市重建,广场大道取代了小街小巷,因此切断了街头文化生存的基础。
现今体制下,国家对于一座城市发展的影响巨大,规范是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主要手段,包括城市土地的公有制也为城市大拆大建大开了绿灯。但这种极端现代主义的规划并不能完全说是中国的特点,法国建筑学家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其《光辉城市》中全面地表达了他“大是美的”的城市构想,哪怕是与原有的城市不协调,甚至新规划完全取代原有的城市也在所不惜。 中国的城市规划从结果上来看几乎反映了柯布西耶的现代化特征:快速交通,城市大道,整座城市划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以及其他功能区。但这种宏大城市愿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已经对城市的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其实城市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应该是有生命的,就如同一个有机体,有生有死,文化就是它的命脉,他强调的是要根据一个城市文化脉络来发展。到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则更进一步,她认为已经成形的旧街区不需要大拆大建或者全面更新,而是在城市建设中针对社区逐步地细化,考虑的中心是居民生活的方便和安全,而非宏大漂亮的建筑和街道。规范化作为一种迷思,大家过分迷信国家的力量,单一的体系下的思想、文化和政策,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同一、呆板、缺乏活力。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那本书,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过分迷信于某一种力量,而经常最后得到的则和人们的期望的相反。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动员社会的全体力量,公民共同参与的,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正常的运作方式。归根结底,自发性组织越多越完善,社会的发展就越健康。
日常的重要
我强调日常,并不是要抛弃宏大叙事,但同时我自己感觉要与宏大叙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宏观经常是看不到个体的。宏观视角看到的都是远景,就像站在高高的山巅上,或者在云层中去看一个城市,怎么能体会到城市中个体的思想、感情和经历呢?研究历史要重视人——作为个体的人,不要总是把人作为群体来看,“人民”“群众”等等都是群体概念,但它们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所以历史研究要关怀个体的命运。如果忽视个人的诉求,那么所谓的群体也只是一句空话。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当一个帝王或者英雄要创造历史的时候,他是豪情满怀,但是那些被裹挟进入的民众,很可能就是血流成河,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千千万万个生命化为尘土。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这不是历史研究应该反思的问题吗?去研究一些小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背后有很大的议题,最直接的就是怎样对待个体的人,甚至我认为,怎样对待个体,是检验我们是否真的关怀人民命运的试金石。
历史写作中有两种历史观:帝王史观和日常史观。在前者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应该围绕朝代和帝王,民众没有什么书写的价值。但是我认为,普通人和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因为涉及到人口的绝大多数每天都面临的问题,因此他们至少应该得到我们历史研究的相应的关注。实际上不仅涉及到我们怎样看历史,而且也是民众怎样看待自己这样重大的问题。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帝王和英雄造成的是更多的是破坏,对经济和文化的损害。而我们的文明发展到今天,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我还想强调的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每天做的一切,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就应当享受人格、尊严和权利。掌权者要让人民的生活保持日常,而不是反反复复地折腾他们。
写作日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日常在历史资料中几乎是不见记载的。过去的一切,就变为了“历史”;还是还有另一种“历史”,就是我们书写的历史——通过查询有限的资料、实地考察等来重构历史。我们重构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重现过去,当我们与历史的时间距离越远,我们所受局限性就越大。既然资料存在着极大的局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现在所能依据的材料只是历史本身非常小的一部分,要依据这么少的资料去重构历史,那么它们有多大程度上是还原了历史本身?虽然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写作历史的时候,要运用“历史的想象力”去填补资料的空白,但是这种填补一定要有历史依据的。历史学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小说家,要在合理逻辑下进行推演。而且写作者必须告诉读者,这是作者在利用有限资料后的一种合理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历史本身。
关于资料,我在导言中已经进行过讨论,这里还想补充几句。我认为,不是说只要找到了这些资料,就可以随便采用。因为资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里面讲的故事和真实历史到底有多远?怎样通过这些文本去分析?过去认为,找到档案、报刊和日记,就等于找到了历史,如今我不这样认为了,这些记载只是一种文本,文本必须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经过分析后才能呈现其中的内涵。
研究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资料的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是运用文学资料就是一个可能的途径。我认为,文学家、小说家写他们同时代的生活,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中国的小说家有采风传统,比如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把接触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记载。其实历史的记录,并不见得比文学更真实。历史学者自身也有局限和偏见,过去的历史写作钟情于大叙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个体,普通人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历史学家不要太瞧不起文学。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Metahistory)中,讨论到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共性,也有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等内在结构。传统的史学训练不赞同使用文学资料,但我越来越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对土改运动的描写,超过了我读过的任何关于土改运动的历史写作;路遥《平凡的世界》对1970年代的黄土高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故事也是非常真实的。因此,文学可以被用来补充历史细节的缺乏,历史和文学其实没有孑然分离的鸿沟,历史要有文学性,文学要有历史感。在没有历史资料的时候,可以用文学来填补缺失的部分。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学完全等同于历史,要有所选取和分析。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冉云飞先生。虽然他的专业是文学,但是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敏锐的阅读。他几年在腾讯《大家》专栏上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篇文章《如何将二等题目做成一流学问》,对我出版的几本书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论。 在这个评论中,他对《街头文化》中若干晚清和民国时期来川的外国传教士中文名翻译进行了订正,这次新版,我都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晗,他负责我这个作品集的各种事务,感谢责任编辑延城城对这本书又进行了仔细的编辑,保证了本书的再版的高质量。
王笛
2023年2月7日于澳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