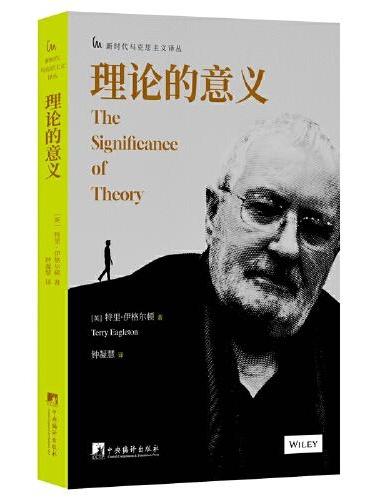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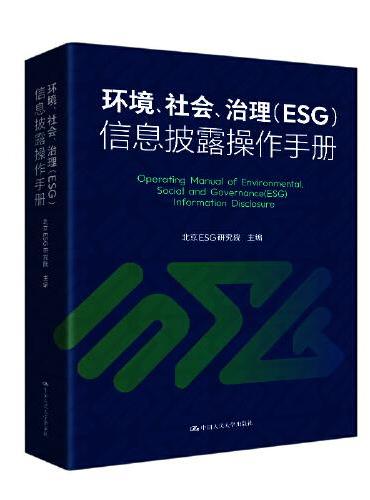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
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
售價:NT$
1190.0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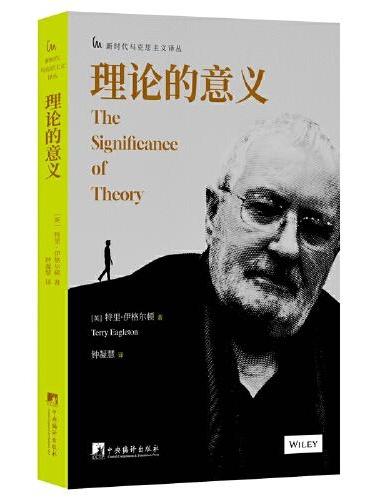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NT$
240.0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 編輯推薦: |
她不属于人类,却仿佛拥有了人类的心。
囊获八项至高大奖的天才科幻小说
横扫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阿瑟克拉克奖、英国科幻协会奖、法国幻想文学大奖、英国奇幻奖、日本星云奖等多项大奖
完整构建了一个人与机器共融共生的未来世界
陈楸帆、程婧波、龙星如力荐
湛庐文化出品。
|
| 內容簡介: |
内战爆发,人工智能布瑞克被任命为舰队长。
布瑞克曾是一艘智能星舰,控制着几千具人类躯体。
然而现在,作为星舰的她早已覆灭,她拥有的只剩一具脆弱的肉体。
她将前往一座位于宇宙尽头的空间站,确保整个星系的安全与稳定。
不过,空间站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样平静……
|
| 關於作者: |
安·莱基
Ann Leckie
美国知名科幻小说家,被誉为“创造了新的科幻小说历史”的作家。
早期主要写作短篇小说,并在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任职。2002年,安·莱基开始撰写《数字星舰》系列的初稿。《数字星舰1:正义的觉醒》于2013年出版,出版后一举拿下了包括雨果奖和星云奖在内的多项科幻大奖,她也成了备受瞩目的科幻女作家。
随后两年,安?莱基完成了“数字星舰三部曲”。该系列的后两部作品同样斩获了包括轨迹奖在内的多项科幻至高奖项。
|
| 內容試閱:
|
玛丽、厄休拉和安
程婧波
中国科幻新生代代表作家
首位同时斩获两大中文科幻奖项
“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的女性作家
《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丛书主编
对中文世界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安·莱基可能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名字。
这是一位近年来风头正劲的女性科幻作家。通过极具先锋气质的写作,安·莱基已经将科幻圈鼎鼎有名的几项大奖——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阿瑟·克拉克奖、英国科幻协会奖、法国幻想文学大奖、英国奇幻奖、日本星云奖收入囊中。
就在安·莱基凭借《数字星舰》获得雨果奖和星云奖的认可的几年之后,一位名叫N.K.杰米辛的黑人女作家,以“破碎的星球”三部曲三度摘得雨果奖桂冠,创造了雨果奖史上“帽子戏法”的奇迹。
而杰米辛也在第三次登上雨果奖领奖台时,贡献出了可能是雨果奖史上火药味最浓的获奖感言。她提到自己曾经因为肤色原因,不得不忍受编辑的退稿和知名作家的白眼。她还无比愤怒地回忆起一些发生在研讨会上的不愉快——连“女性作家的创作有何意义”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也需要与男性作者争辩。
把“平权主义”“女性主义”写进科幻小说,成为N.K.杰米辛的一种生理自觉——作为一位黑人女性,她选择了用科幻小说这种在美国一直被视为典型的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类型文学,来战斗和发声。
巧的是,安·莱基踏上科幻写作的领路人奥克塔维娅·巴特勒,也是一位黑人女性科幻作家。
奥克塔维娅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她在美国科幻界开创了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的新天地。
美国一直都有科幻写作工作坊的传统,奥克塔维娅曾在号角科幻写作班学习怎么写作科幻小说,这对她日后拿下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以及美国笔会的文学写作终身成就奖,并且成为第一位以科幻小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奥克塔维娅后来回到号角科幻写作班授课,足下高徒包括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作者)和中国读者现在或许还不太熟悉的本书作者——安·莱基。
如果要说安·莱基从她的老师奥克塔维娅·巴特勒那里继承了什么最核心的东西,我猜这也正是她从自己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东西——那种被人们称为“xx”染色体的东西,那种使女性有别于男性的东西。这使得她提笔写作时,源自女性身份的思考成为一种无可避免的生理自觉。
这样的一种自觉,我们从安·莱基身上看到了,从在她之前的奥克塔维娅·巴特勒身上看到了,也从在她之后的N.K.杰米辛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自觉使得她们笔下的作品大放异彩,也使得我们从中发现女性科幻作家的写作是一条传承有序的纽带。
如果说母系氏族是由“女性”主导的基因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种传承,那么女性写作则是由“女性”主导的一种精神上的传承。
如果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女性写作的脉络在科幻作品的世界里继续溯流而上,还能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发现:
安·莱基作品中那种女性主义的先锋性,不仅仅是因为她站在自己的恩师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的肩膀上——还因为她同样受到了厄休拉·勒古恩的深刻影响。
说起厄休拉·勒古恩,骨灰级科幻迷想必并不陌生。她是英语世界的“科幻小说女王”,笔下的作品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作者)、大卫·米切尔(《云图》作者)、尼尔·盖曼(《美国众神》作者)、J.K.罗琳(《哈利波特》作者)等人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数字星舰》系列中,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一些向厄休拉·勒古恩致敬的痕迹。
《数字星舰》系列中,绝大多数的性别代词就是“她”。无论是拥有人类的身体加人工智能的大脑的主角布瑞克,还是故事中出现的其他角色,作者往往以“她”称之。
这种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性别思维和阅读习惯的做法,无疑是一招险棋——它会带给读者全然新鲜的冲击力,亦会招来不适、批评,甚至愤怒。如同厄休拉·勒古恩在她的《黑暗的左手》中为消除性别差异的构想所带来的性别思维突破,对20世纪70年代两性文化的冲击。
厄休拉·勒古恩在1969年出版的《黑暗的左手》中,构建了一个叫作冬星的地方。在这里,性别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二元统一的。评论界将其称为厄休拉的“性别思想实验”。格森(Gethen),又称冬星,是一个气候寒冷、生存条件严苛的行星。这里的原住民都是“双性同体”,平时在生理上并无男女之分,仅在每个月一次的卡玛期(kemmer,意即发情期)中,随机分化为男性化或女性化状态。由于卡玛期中会变化为何种性别全无规则可循,一个格森人可能既是父亲也是母亲,因而形成格森社会的特有型态:其成员并无性别习性。
《黑暗的左手》一经出版就产生了轩然大波。人们借主角金利·艾(此人的身份是星际联盟使者,其性别思维与地球人类相近)之眼,走近了一个“性别流动”的社会。厄休拉·勒古恩在书中对所有格森人都以“他”称之,这一方面具有打破性别思维惯性的先锋性,另一方面,也给她招来了一些批评的声音。
严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黑暗的左手》中的主角是男性,而性别未定的角色们也都是“他”,因此,这本书并不能被视为女性的觉醒之书。
1995年,厄休拉在短篇小说《卡海德的成年》中,故意将所有的人称代词写作了“她”。
2013年,安·莱基在自己的处女作《数字星舰1:正义的觉醒》中,也把几乎所有的性别代词写作了“她”。
这是一种以科幻文本完成性别思想实验的传承。
安·莱基在作品中呼应了1995年那个将“他”一律改作“她”的厄休拉,也呼应了1969年那个将所有未定性别的格森人一律称作“他”的厄休拉——女性写作并不是一诞生就完美无瑕的,它是由一位又一位作家、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蹚出来的一条荆棘之路。
对西方科幻世界的女性写作来说,尤其如此。
往这条路的源头走去,或者还能有更有趣的发现。
科幻小说的起始点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尤其是如果这门显然是由男性掌控的文学类型,是诞生于一位女性之手。
科幻史中有迹可循的一个原坐标,是十九岁的少女玛丽·雪莱与她那部具有浓郁哥特风格、阴森诡异又极具大众流行度的科幻小说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
困扰过N.K.杰米辛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在1818年初版时,《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纵使日后被称为“科幻小说之母”,在当时却是匿名的。初版《弗兰肯斯坦》由玛丽的丈夫,知名诗人雪莱作序,使许多人误以为此书是后者的作品。直到五年之后,小说第二版出版,玛丽·雪莱才公开了自己的作者身份。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现在仍然需要去努力证明,但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女性作家当然可以创作出和男性作家一样优秀,甚至不朽的作品。
《弗兰肯斯坦》采用了一种被评论家们探讨了两百年的精巧的“三重叙事”结构。到厄休拉·勒古恩以《黑暗的左手》重新提振女性科幻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声量之时,她采用了“双重叙事”的结构来呼应玛丽·雪莱的古典叙事。而到年轻的安·莱基提笔创作出《数字星舰》时,她采用了一种颠覆式的“一重叙事”——以主角布瑞克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故事,而布瑞克作为一种AI共生体,“她”可以说拥有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
厄休拉所欣赏的中国道家思想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安·莱基的“一重叙事”可以看作是与厄休拉·勒古恩的“双重叙事”和玛丽·雪莱的“三重叙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叙事闭环:
万物生三,三生二,二生一,一生道。
读过或者没有读过《弗兰肯斯坦》的读者,可能都很难不注意到“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字,却忽略了“玛格丽特·塞维尔”这个角色。
“玛格丽特·塞维尔”从来没有出场,却成就了这部小说的“三重叙事”结构:
《弗兰肯斯坦》以书信体的格式,以在北极探险的航海家罗伯特·沃尔顿的口吻,给远在英国的姐姐玛格丽特·塞维尔写信,转叙弗兰肯斯坦讲述给沃尔顿的故事;而在转述之中,还嵌入了一层结构:弗兰肯斯坦讲了怪物对他讲的故事。就如同梦中之梦一样,三重叙事环环相扣,构成了一种叙事奇观。
玛格丽特(Margaret)其名,与玛丽(Mary)肖似。而玛丽这个名字背后,则又藏着许多故事。
婚前的玛丽全名叫作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古德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而这个名字与她的亡母一模一样。
玛丽的母亲并非泛泛之辈,而是世界女权主义第一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书的作者。不幸的是,她在生下玛丽后十一天就因产褥热而逝世。玛丽的生伴随着母亲的死,这似乎也成为《弗兰克斯坦》这部作品绕不开的主题:生从何来?死向何去?
这种关于“生”与“死”的思考,也深深地影响着几乎所有的女性写作。
在两百年前,玛丽·雪莱对于“生育”的恐惧,是与“死亡”紧密相连的。而她笔下的“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则是从拼接的尸体里创造出生命。这是一种互文式的生育恐惧。
玛丽的经历是给予新生,又眼睁睁看着新生凋零;弗兰肯斯坦所做的则是从坟墓中找出那些死者的尸体,将这些残肢拼凑到一起,并赋予其生命。
玛丽和弗兰肯斯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两百年间,无数的女性作家笔下依然在延续着“生”与“死”的永恒母题。
今天,安·莱基所做的,就是在她的前辈们披荆斩棘走出来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勇敢地前行。
人工智能取代了古老的哥特故事,共生体的概念带来新的奇观——安·莱基不仅仅是想要打破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惯性思维,更要使人们对“人”的定义、本源和意义进行重新思考。
“生”与“死”的文学母题还在继续着。剥开《数字星舰》系列那坚硬的表层——人称的先锋性和叙事的颠覆性,触及其内在的柔软,那些更加本源的思考才是女性写作的最最迷人之处。
从玛丽·雪莱到厄休拉·勒古恩,从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到N.K.杰米辛,科幻中的女性写作从未缺席。
女性对世界的观察、感受、认知和构建,就如同女性的存在对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安·莱基和她的作品无疑也是如此。
“鉴于当下情形,你可能需要再添一名上尉。”阿纳德尔·米亚奈说道。阿纳德尔·米亚奈是雷切帝国的在位统治者,这会儿正坐在一把铺着刺绣坐垫的宽大椅子上。阿纳德尔有数千具躯体,跟我讲话的这具大约十三岁,着一身黑衣,皮肤黝黑,脸上带有特有的贵族气质的印记,在雷切帝国,这是最高身份的标志。在这个帝国,通常是不会有这么年轻的领主的,但现在属于特殊时期。
这个房间不大,面积三四平方米的样子,四周是黑木围成的栅栏,其中一个角落里整段木头都不见了。就在上周,阿纳德尔与她的另一个人格爆发了激烈冲突,这段木头可能就是那时被损坏的。在其他几处没有破损的黑木上,几缕植物的卷须蔓延开来,银绿色的细叶子映衬着朵朵小白花。这里并不是宫殿中的谒见室。领主座椅旁放着一把空椅子,两张椅子中间摆放着一张茶几,上面有一套茶具,一个茶壶,还有几个未经雕饰的白色瓷茶碗,摆放极为讲究。乍看上去这些物品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仔细端详就会发现其价值能抵得上几个行星的艺术品总和。
阿纳德尔命令属下给我上茶,并邀我就座,但我并没有坐下。“你许诺过,我有选择下属的权力。”说这话时,我本该加上“我的领主大人”这样的称谓以示敬意,但我并没有,而且在我进门见到领主时,也没有下跪叩首。
“你已经选了两名上尉。斯瓦尔顿是一个,这不用多说。另一个是艾卡璐,原因也是不言而喻。”她话音刚落,两名上尉的形象便条件反射似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用不了十分之一秒,停泊在该空间站约三万五千千米之外的仁慈卡尔号便会接收到我大脑发射的信号,再过十分之一秒,星舰便会把搜索到的关于两位上尉的数据反馈给我。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尝试着改掉这项几近本能的大脑活动,不过效果并不明显。“舰队长有权选择第三位军官。”阿纳德尔继续说道。
阿纳德尔戴着一副黑色手套,手里端着一个精致的瓷茶碗。她朝我打了个手势,仿佛是在指我的制服。雷切帝国的军人统一穿深棕色夹克、裤子、军靴并戴手套。而我的制服却有些不一样,左半边是棕色,右半边则是黑色。我的制服上佩戴舰队长徽章,徽章赋予我的权力包括不仅掌管我所拥有的星舰,还可以向其他星舰长下达命令。我拥有的星舰是仁慈卡尔号,在我所控制的舰队里,只有这一艘归我管辖。
不过,我将要前往的区域,也就是艾斯奥克空间站,并没有其他舰队长驻扎。因此,如果我在那里遇到其他军官,舰队长官衔意味着我的权力会更大一些。但有一个前提,这些军官得愿意承认我的权威。
上周那场长期蓄积的矛盾爆发后,一个军团捣毁了两扇星系间的传送门。如今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做好防御,谨防更多的星系传送门遭到破坏,并严防该军团占领帝国其他星系内部的传送门及各空间站。
我理解阿纳德尔授予我舰队长官职的理由,但仍然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事。“别以为我是在为你服务。”我说道。
阿纳德尔笑道:“我不会这么想。要选第三位军官,还得在本星系或者本空间站找。提萨瓦特上尉刚刚结束训练,她本来接受了第一个任务,当然了,现在看来她是没法执行了。况且,我以为你会希望找一个能按你指令训练的人。”她似乎被自己的这种想法逗乐了。
在阿纳德尔说话的时候,我的大脑出现了斯瓦尔顿的脉搏、体温、呼吸、血氧量以及荷尔蒙水平的影像,我知道她正处在睡眠的第二阶段——非快速眼动睡眠。紧接着,睡眠数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艾卡璐上尉的影像,她此刻正在站岗,因此牙关紧闭、皮质醇升高、注意力高度集中。艾卡璐一直是普通士兵,不过在一周之前,原仁慈卡尔号星舰舰长因叛节被捕,她便升为军官。这是她从未想过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她对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十分自信。
我眨了眨眼,将注意力从大脑图像中拉回。“你不会就给我一个经验不足的军官去应对一场刚刚爆发的内战吧?”我质疑道。
“这总好过没有吧。”阿纳德尔·米亚奈说道,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意识到我刚刚走神了,“提萨瓦特那孩子知道要在一位舰队长手下工作欣喜若狂,她正在港口等你呢。”阿纳德尔放下茶碗,坐直身子,“通往艾斯奥克的传送门已经被毁,我不清楚那个空间站的情况,所以不能给你具体指令。”她举起手,似乎是不让我插话,“况且,要求你一切听从我的指示也是在浪费时间,你还是会自行其是的。你的装备都准备妥当了吗?供应物品带齐了吗?”如此询问无非是装装样子,她心里和我一样清楚星舰的储备情况。我做了个含糊的手势,故作傲慢的样子。“你不妨带上维尔舰长的物品吧,”她说道,好似我刚刚给出的答复很合理,“反正她也用不着了。”维尔·奥斯克一直任仁慈卡尔号舰长,一周前却发生了变故,她不再需要这些个人物品的理由有很多,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她已身亡。阿纳德尔·米亚奈从来都不会半途而废,尤其是对敌作战的时候。毋庸置疑,这次维尔辅佐的“敌人”是阿纳德尔的另一个人格。
“我不想用维尔的东西,送到她家人那里吧。”我答道。
“那我试试看。”但她很可能是做不到的。她又问道:“出发前还需要带些什么吗?什么都行,请尽管提。”我想到诸多物品,但没一个能用得上,便答道:“没了。”“你知道,我会想念你的。”她接着说道,“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讲话,你不害怕冒犯我,这样的人我还没见过几个,而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也没有人拥有你我这样……你我这样相似的背景。”阿纳德尔意指我曾是一艘星舰,是一艘由人工智能掌控的巨型运兵舰,拥有千万名辅助部队士兵,那千万具人类的躯体,都曾是我的一部分。
那时,我并未将自己看作奴隶,而是征战的武器,是阿纳德尔·米亚奈的附庸,而阿纳德尔的千万具躯体亦遍布雷切帝国。
而现在,我只有一具躯体了。“你接下来要我做的,不可能比你已经做的那些事更令人发指了。”“这我知道。”她说道,“而且我还知道,接手这项任务会让你成为危险分子,让你活着可能是愚蠢的决定,更别提给你权力和一艘星舰了,但我从不玩属于怯懦者的游戏。”“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可不是什么游戏!”我愤怒地说道,因为我知道就算我面无表情,她也可以察觉出我的情绪。
“这一点我也明白,我不骗你。只是有些牺牲在所难免。”领主回应道。我脑海中蹦出了六种不同的回应方式,我本可以随便选一种搪塞,但我一句话没说,扭头朝房间门口走去。
一个名为卡尔五号,隶属于仁慈卡尔号星舰的士兵在门外站岗,见我从门内出来,她迅速跟上,没发出一丝声响。如同仁慈卡尔号星舰上的其他士兵一样,卡尔五号是人类,而不是辅助部队士兵。
除了她所在星舰、分队和属于自己的编号外,她还有自己的名字。
有一次我叫了她的名字,她虽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却是警铃大作、焦躁不安,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叫过她的名字。
我还是一艘星舰时,准确地说,当我还是正义托伦号星舰的一部分时,我时刻都能对星舰上军官们的状态了如指掌。她们的所见所闻,她们的一呼一吸,甚至每一块肌肉的抽动,她们的荷尔蒙水平、氧气含量,所有这些我无所不晓,但是我读不透她们的思想。然而,通过经验和对她们的熟稔,我通常可以猜得半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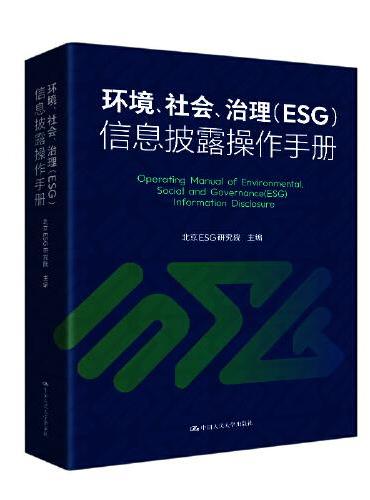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