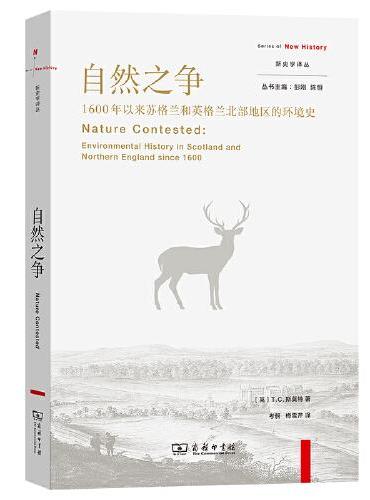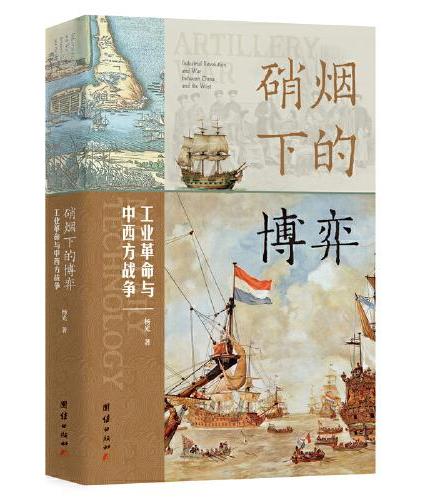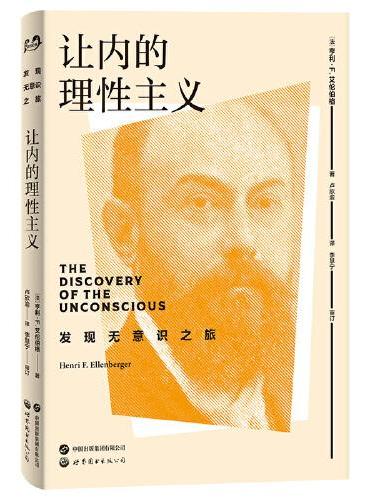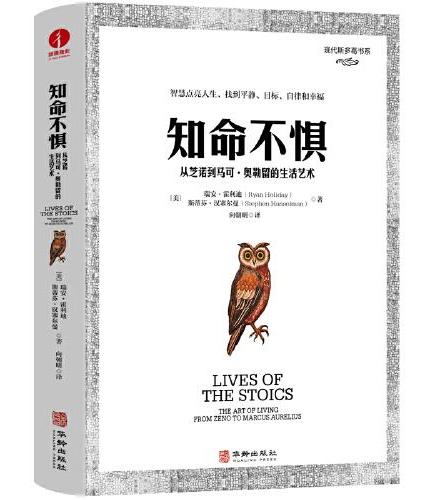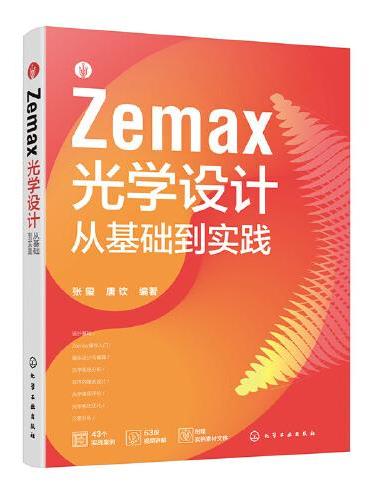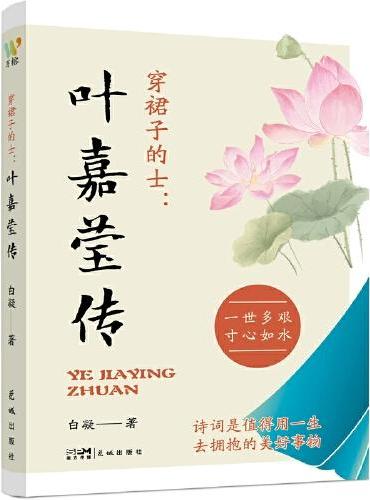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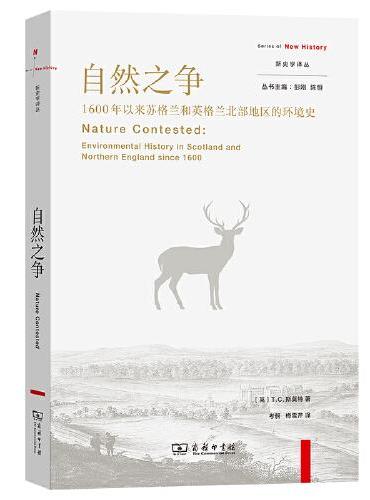
《
自然之争:1600年以来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地区的环境史(新史学译丛)
》
售價:NT$
4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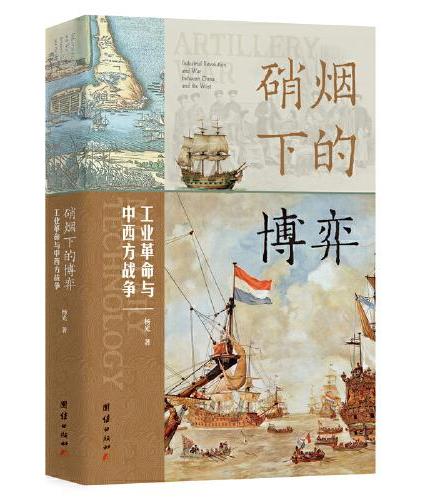
《
硝烟下的博弈:工业革命与中西方战争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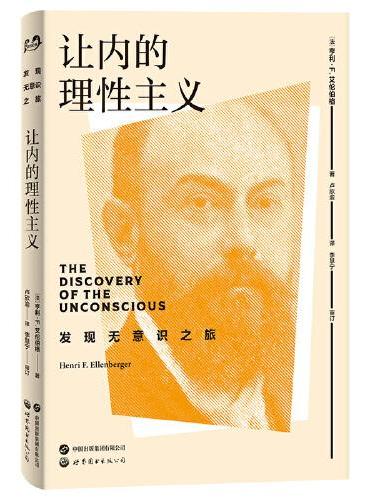
《
让内的理性主义 发现无意识之旅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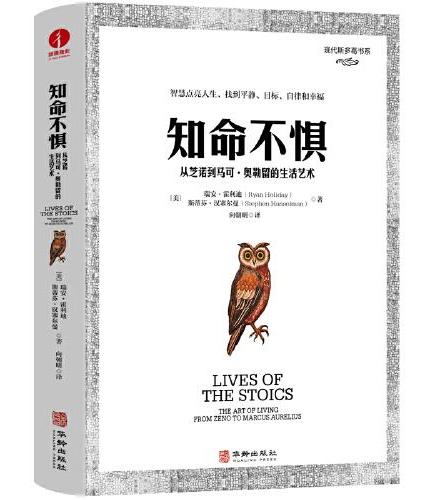
《
知命不惧:从芝诺到马可·奥勒留的生活艺术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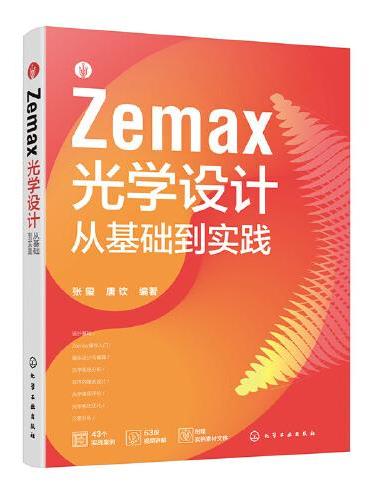
《
Zemax光学设计从基础到实践
》
售價:NT$
602.0

《
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
》
售價:NT$
500.0

《
危局
》
售價:NT$
3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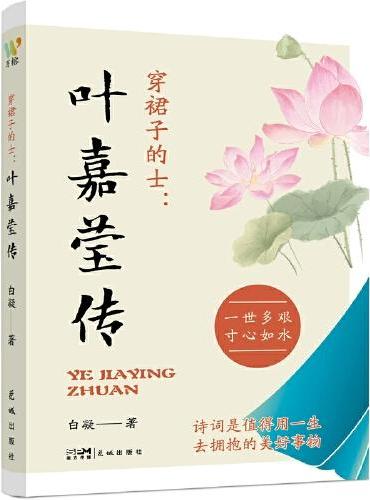
《
穿裙子的士:叶嘉莹传
》
售價:NT$
245.0
|
| 編輯推薦: |
|
19世纪可以说是帝国的世纪,很多个横跨多个大洲的大型殖民帝国得以构建,洲际贸易和人口流动蓬勃展开,这一时期的思潮与知识谱系也围绕帝国生成新的话语和知识体系,有些也成为影响现代社会构成理论的源头。梁展的这几篇论文正是讨论文明、族群的生成和共同体的构建这些帝国体系的基础理论,厘清这些理论的生成和发展,洞察它们殖民话语服务的局限性。
|
| 內容簡介: |
|
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自17、18世纪开启的民族主义浪潮迅速席卷了欧、亚、非和南美洲大陆,帝国的崩解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齐头并进,势如破竹,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方才显出颓势。然而,与其说20世纪是所谓民族-国家的世纪,不如说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相互纠缠的历史。本书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发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几桩案例,采用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构成当今流行的民族主义与帝国理论的诸多复杂的文学想象因素,以及隐藏在这些理论论述背后的、浓厚的殖民主义和自由帝国主义色彩。
|
| 關於作者: |
|
梁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著有《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早期自我观念的形成》、译有《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牛津西方哲学史·第四卷》)、《历史的天使:肖勒姆、本雅明和罗森茨威格》,编有《全球化话语》。
|
| 目錄:
|
导言: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纠缠
一 帝国的崩解与再造: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的政治话语
布拉格的“中国人”
奥匈帝国的神话
“大奥地利”方案
二 政治地理学与大同世界:康有为《大同书》的文明论谱系
文明话语实践与人种学的诞生
政治地理学与体质人类学
晚清外交危机与人种分类的知识与实践
“烟剪人”、鲜卑与康有为殖民巴西的计划
种族改良与大同世界的构想
三 帝国与启蒙的前夜:《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中的土地、财富与东方主义
“莫卧儿-贝尔尼埃”
自由思想者眼中的焚祭礼和日食
印度洋贸易、财富和土地所有制
四 帝国与反叛的幽灵:法兰西革命年代的文人形象
密谋家
浪荡汉或波希米亚文人
幽 灵
五 自由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重思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
来自爱尔兰的中国海关关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
自由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民族主义
|
| 內容試閱:
|
1917年6月,犹太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了摆脱埃及民族主义风暴给外国人带来的不安,母亲带着两岁的艾瑞克乘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赫勒万号”邮轮来到她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故乡——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不久前这座风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刚刚被意大利占领。数月后,霍布斯鲍姆一家移居维也纳郊区,艾瑞克在那里度过了喜忧参半的童年时光。在这个前多瑙河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新的奥地利国家首都,霍布斯鲍姆虽然没有机会亲历哈布斯堡帝国分崩离析的政治悲剧,但是共同生活在帝国内的德裔、斯拉夫人、马扎尔族群以及犹太人之间的政治、文化、语言冲突仍未远去。“假如说19世纪奠定的‘民族原则’曾经在某一时刻赢得了胜利的话,那么这个时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离开维也纳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霍布斯鲍姆带着遥远的童年记忆论道,民族主义在1918—1950年之所以达到了高潮,究其原因,应当是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的崩溃和俄国革命的爆发所致。所谓“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显然是指历时50余载的奥地利-匈牙利帝国(1867—1918)。凡尔赛和会之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楬橥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民族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直绵延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很快成为历史,英、法殖民帝国元气大伤,苏联最终也未能摆脱解体的命运;在中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地区,新兴的民族-_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涌现,这让人们觉得,20世纪仿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纪”。
历史学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叙述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抹去民族-国家的帝国印迹以及它与帝国相互重叠和纠缠的“前史”,来服务于民族主义政治的现实需要。然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则尝试在全球史网络中考察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掘它们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彼此连接构成的复杂关系,并对过度依赖民族-_ _国家视角的历史编纂学原则,即所谓“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做出质疑、反思和挑战。以德国殖民史、东亚(日本)史和全球史理论见长的塞巴斯提安·康拉德指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帝国与民族-_国家泾渭分明,然而将帝国看作是民族-_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向外扩张的结果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对于民族-_国家而言,帝国既是催化剂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碍:一方面,帝国的压迫培养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民族主义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是对“传统的发明”,它将“族裔、宗教、语言和地区的差异与联合人们起来反对外来统治的利益连接起来”。因此,作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本身正是借助基于交流和交换的目的而设立的帝国诸项制度和基础设施才成为可能,而且,作为政治枢纽的帝国中心反过来亦有利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滋生”;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如若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跨越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帝国这一障碍,换言之,如果后殖民国家要追求民族兴盛,帝国也就必须要解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念(即民族兴盛——引者)恰恰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对国内“落后民族”所肩负的“文明的使命”往往也能够使帝国预见到自身会缓慢没落的命运。因此,与其说20世纪是民族-_国家的世纪,不如说它是民族-_国家与帝国相互纠缠的历史。
在中东欧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马扎尔等的民族主义者纷纷指斥奥匈帝国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动员作用,然而,在以民族-_ _国家为中轴线展开的历史叙述中,中性意义上的帝国治理方式对国内族群的政治民族主义发展起到的催化作用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漠视。彼得·朱迪森是在意大利欧洲大学任教的中东欧历史学家,他在2016 年推出的《奥匈帝国史:一部新史》中,分析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帝国境内各个族群“分而治之”的情况,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积极有效地利用帝国的族群治理政策服务于他们各自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选举活动的事实。举例而言,1897年4月5日,帝国总理巴德尼颁布语言法令,要求在政府工作的德裔公务员能够熟练掌握捷克语,这个举措的初衷是要在波希米亚王国境内将捷克语提升到与德语同等重要的地位。感到利益受损的德裔族群立即走上街头,反对该法令的实施,并以言辞辱骂巴德尼本人,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以巴德尼被迫辞职才平息下去。在朱迪森看来,巴德尼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奥匈帝国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国家决策的讨论当中,表明维也纳中央政府对波希米亚王国两大族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受到削弱,遂使波希米亚形成了除维也纳之外的另一个帝国中心。此外,政府为波希米亚王国单独制定法律的做法又为与其毗邻相处的格拉茨或萨尔斯堡所不满,从而激发了当地人的民族平等意识。由此可见,帝国非但没有构成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反而是民族主义的摇篮。
若论帝国对内部民族主义的压迫,与奥匈帝国相比,英帝国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镇压显然更为残酷无情。在奥匈帝国解体100周年来临之际,朱迪森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首先谈到了1916年在都柏林爆发的一次民族起义。4月24日(复活节)清晨,1200多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持枪攻占了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椭圆形地带,驻扎在这里的英军在经历了短暂的震惊之后,迅速从英国各地调集了多达数千名的士兵,甚至用战场上才使用的重炮猛烈轰击叛乱者构筑的街垒。数日后,起义者终于感到寡不敌众,被迫于4月29—30日向英军缴械投降。根据2015年英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这次起义一共造成至少485人死亡,其中有260名平民;2600余人受伤,其中包含至少2200名平民以及40余名17岁以下少年儿童。尽管接受了对方的投降,驻爱尔兰英军总司令还是下令逮捕了3500余名叛乱者,处决了帕特里克·皮尔斯、詹姆斯·康诺利等154位领导者。在讲述这一历史事件时,朱迪森刻意隐去了起义发生的地点。很多人会觉得,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民族起义一定爆发在奥匈帝国的某个边远省份,因为在1916年协约国战败迹象显露之际,奥匈帝国内部的族群冲突正愈演愈烈。
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帝国的末日,对于地方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自治要求,卡尔皇帝也表现得宽容有度。1918年的秋天,在施蒂利亚州首府格拉茨,一批商业名流和工人迫切想要解决当地生活用品的供应问题,于是组成了“施蒂利亚州公共福利委员会”,决心斩断与奥匈帝国的纽带。该委员会同时致电卡尔皇帝和施蒂利亚州州长,请求他们赋予其在当地行使原本属于帝国政府的权力。维也纳方面不但同意了他们的诉求,而且命令州长将涉及当地物资供应和帝国内部贸易的权力全部移交给该委员会执行。朱迪森就此评论道,这一做法体现了善于根据形势灵活应变的帝国传统。
在分析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的原因时,历史学家指出,起义的举动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通市民和公众舆论的支持:无论是英军的亲属,还是英爱联合派,连英国国会中的爱尔兰党派都对起义军心怀敌意,这一现象被朱迪森概括为普通民众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漠视。在奥匈帝国晚期,语言常常被认定为甄别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以及衡量他对本族群是否忠诚的标准。在族群杂居的地方,语言成为政治斗争的“前线”,然而,与当地民族主义政治精英希望看到的态度相反,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朱迪森细致地观察到,当地的农民拒绝将语言的划分转化为在自我认同甚至族群忠诚度方面的差别,相反,“操两种语言、对民族身份的漠视以及利用民族身份投机等现象,表现了双语地区地方文化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无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所谓现代化进程均无法予以摧毁”。因此,族群或民族身份的甄别和归属只是人们看待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而已,民族身份并非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事实,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决定一个人对其民族身份做出选择的因素不是生理特征或者语言特征,而是这个人所处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具体的生活情境。
一般认为,奥匈帝国的崩溃是维也纳中央政府对待各族群的不平等态度以及族群间的政治冲突所致。朱迪森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精心营造出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恰恰是奥匈帝国借以表达其统治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导致帝国解体的原因并非族群政治,而是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在战争期间由大权在握的军官们制定、并得到皇帝和政府高级官员支持的军事管理措施,严重侵蚀了曾经受到普遍拥护的战前体制的合法性;其二是帝国的治理网络濒于崩溃,尤其是帝国中心越过地方政治精英领导人(他们本身往往是民族主义者)直接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的能力下降。
在长篇小说《诉讼》中,卡夫卡描绘了这样一个惨烈的场景:K先生在31岁生日当晚被闯入家中的两名陌生人无故带走,最后像“一条狗”那样被用来剪肉的一把锋利的剪刀插入胸膛而死。K先生的遭遇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作家对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生存困境的表现,以及“现代官僚世界及生活在这个迷宫般的世界当中无法找寻自己主体的一个巨大比喻”。但是,熟悉奥匈帝国历史的读者就会联想到,K 先生正是那些在战争期间普遍遭到通敌叛国指控,从而被当局无端逮捕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当中的一员。如卡夫卡所说,对他们来说,这“耻辱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村民们对言语不通的邻省爆发的叛乱抱以厌恶之情,城里人对地方政治精英被当街处决的场面漠不关心,孔武有力的信使纵使怎样摆动双臂都无法走出京城的尴尬,以及那位终日枯坐在窗边等待皇帝口谕的乡民……史学家朱迪森笔下的奥匈帝国日常生活场景均被卡夫卡嵌入了文学想象的世界,他的小说读起来仿佛是《圣经》中的寓言故事,其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人们分段修建长城的方式。
1918年10月16日,卡尔皇帝在面向全体臣民发表的宣言中说,他决心把奥地利各族群的愿望融会成一个声音,并努力促使它成为现实,“奥地利将满足国内各族群的意愿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族群都要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建设自己的国家式的共同体。奥地利境内的波兰人聚居地与独立的波兰国家统一无论如何也不应是首选,按照当地居民的愿望,的里雅斯特城及其所包含的地区将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卡尔皇帝一方面对刚刚获得独立、尚留在帝国政治版图之内的民族国家许以自治的保障,同时呼吁它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使帝国“共同体成为单个国家的生活所需”。从宣言措辞的谨慎程度来看,卡尔皇帝对类似波兰这样的少数族群有朝一日会从帝国独立出去的前景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而事实上,的里雅斯特(也就是霍布斯鲍姆母亲的故乡)很快就变成了一座意大利城市。本书第一章正是在奥匈帝国晚期的上述政治危机中讨论了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它表达出作家对如何从精神上重建大奥地利帝国以及对普遍意义上的帝国存在理由的思索、困惑和忧虑。
(摘选自本书“导言: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纠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