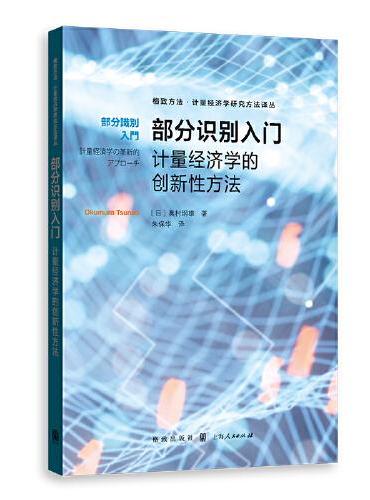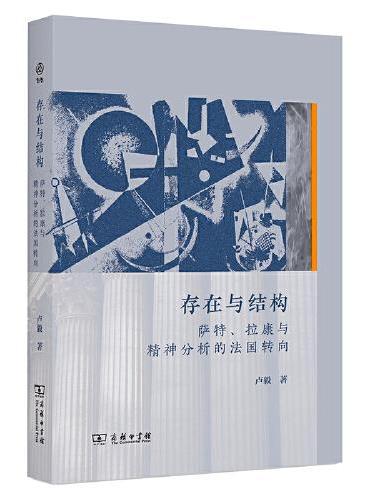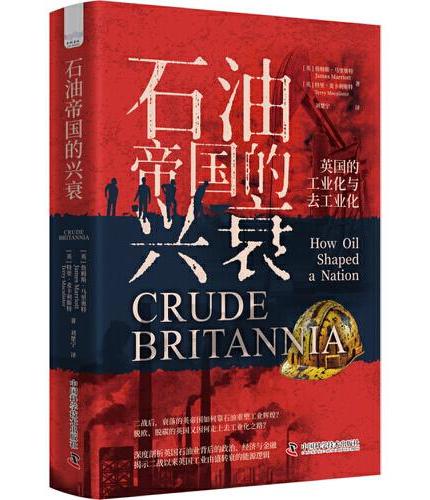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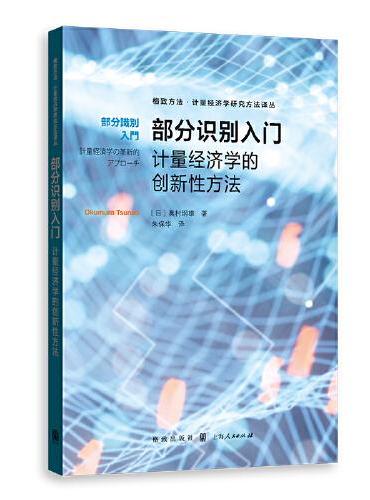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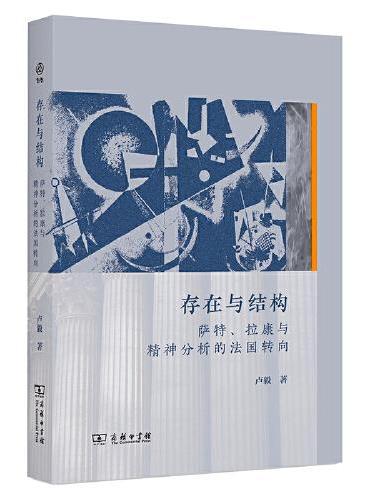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NT$
240.0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NT$
4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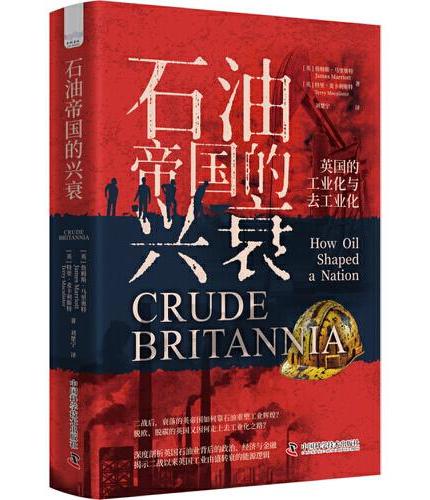
《
石油帝国的兴衰:英国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售價:NT$
445.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
★余光中逝世五周年,缅怀致敬——
余光中家属亲自授权审定篇目,原汁原味完整呈现余光中经典文学。
★梁实秋、莫言、张晓风、韩少功极力推崇的文学大家——
梁实秋赞他诗文双绝,莫言赞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真正高明的继承,张晓风赞他是文字方面的全才……
《朗读者》邀请他亲自朗读《民歌》,因为他,所有人更深刻理解了“乡愁”……
★原来,现代汉语的散文能写得这么美——
他身具士大夫的气质,他的散文处处可见汉赋唐诗的味道,他的散文是对现代汉语华美的极致探索,隽永飞扬,处处透着古典的气息,那是一种极致之美……
★生活不止眼前的内卷,还有偶尔的偷闲——
闲不是懒,而是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就像梁永安说的,“在摸鱼中探索,还算是清醒的人、有真生命的人”,“躺平,是对生活有了新思考”。
★在艺术中,寻找生活的美好——
谈诗律、品画韵、讲文法、评音乐。余光中对古今中外的名人名篇信手拈来,同时还能对其进行一针见血、独有见地的评论。他的评论始于文艺,合于美,止于生活。任何人都可以从他的评论中感受到美的艺术,生活的真谛。
|
| 內容簡介: |
余光中说,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无闲旷之岁月,不能称性逍遥。“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
《游于艺:做个闲人》收录《杖底烟霞》《诗与音乐》《捕光捉影缘底事》《猛虎与蔷薇》等谈诗律、品画韵、讲文法、评音乐的文章和诗歌;还有关于张晓风、徐志摩、凡高、毕加索等的文艺作品之品评。本书堪称美的修养和写作的典范。
阅读余光中,获得智性的幽默、余裕的闲情、无瑕的爱和美。艺术,涵养人心。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余光中
当代知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评论家,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
1928年生于南京,福建永春人。就读金陵大学、厦门大学,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曾获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政治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著有诗集《白玉苦瓜》《藕神》等;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青铜一梦》等;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举杯向天笑》等;翻译《理想丈夫》《温夫人的扇子》《不要紧的女人》《老人和海》《凡高传》《济慈名著译述》等,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秋之颂》等。
余光中,学识渊博、睿智诙谐。其作品文字壮阔铿锵,又细腻柔绵,在华语世界影响深远,被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中。
|
| 目錄:
|
章 无闲旷之岁月,不能称性逍遥
杖底烟霞
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
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
缪思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
现代诗的名与实
中国古典诗的句法
散文的知性与感性
李白与爱伦·坡的时差——在文法与诗意之间
捕光捉影缘底事——从文法说到画法
文法与诗意
诗与音乐
第二章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猛虎和蔷薇
从天真到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
沙田山居
西画东来惊艳记
一笑人间万事
第三章 也无风雨也无晴
何曾千里共婵娟
另一段城南旧事
亦秀亦豪的健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文章与前额并高
狸奴的腹语——读钟怡雯的散文
舞与舞者
徐志摩诗小论
凡·高——现代艺术的殉道者
毕加索——现代艺术的魔术师
|
| 內容試閱:
|
代序:盖棺不定论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位作家,生前蹭蹬潦倒,或遭人误解,或受人冷落,眼看曲士得意,竖子成名,往往只有寄望于历史的评价。丹麦思想家齐克果生前看尽世人的白眼,且以瘦胫的星象家与戴礼帽的公鸡之姿态,出现在哥本哈根报纸的漫画之中。死前不久,他说:“我死后,世人将同声赞美我,而赞美的语气,将使青年误会我生前曾受人尊崇。这,也是真理在现实中蒙受的歪曲之一部分。以卑劣相向的时人,一旦我死了,将一反昨日的议论,而一切陷于混乱。”
一位作家的价值,很难获得定评,生前如此,身后亦然。生前,他容易招人曲解,致天下之恶皆归之;身后,他既已成为偶像,世人对他的溢美,也每每邻于迷信。相反地,也有生前享尽声誉,死后光芒毕敛或恶名横加的例子。而无论是低估(underestimate)或者过誉(overestimate),都不是一位作家应得的报酬,也会导致文学史的混乱。一般说来,我们对一位作家的恶评往往发自内心,但对于一位大师的称扬则往往出于附和,因为无论你如何诟骂莎士比亚,都不能稍减莎翁的权威,相对地,这样做,只能自绝于风雅。因此,在梁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庆祝会上,社会名流,数以百计。其中究有几位能欣赏原文的佳妙,又有几位曾经认真读过中文译本?如果当场举行一次临时考试,恐怕将会证实,大半的来宾仅仅具有看银幕上的《王子复仇记》的资格吧。王彦章所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是另有用意的。对于附庸风雅之辈而言,一位大作家死后,除了名字之外,还留下了什么呢?
盖棺而论不定,于莎士比亚尤然。莎士比亚死后七年,班江生即写了一首长诗赞美他,称他为大师,并说他“不属于一代,属于千秋”。又七年之后,年轻的弥尔顿写了一首短诗献给他,说他的盛名何需金字塔的见证。但三十多年后,进入复辟时期,在法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布瓦罗(Boileau)的影响下,一些平庸的作家,对于不屑遵守古典戏剧格律的莎士比亚,表示不满,甚至视为“野蛮”。日记家皮普斯(Samuel Pepys)对莎翁戏剧的反应,可以代表十七世纪后期的一般态度。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载:“今日同去看了《仲夏夜之梦》,生平看过的戏里,没有比这更乏味更可笑的了,我决不要看第二遍。”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坛,对于莎士比亚不能说不够重视,但是一个弥漫着理性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了解浪漫的莎士比亚的。当时的诗坛泰斗颇普,曾不自量力,编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结果是谬误百出,为专家萧博德所笑。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在柯勒律治、兰姆、哈斯立特、德昆西的批评之中,崇莎热(Shakespeare idolatry)臻于高峰,迄二十世纪而不衰。可是在外国,莎士比亚的股票亦时涨时跌。法国浪漫派的大师们,如雨果、缪塞、德拉克洛瓦和柏辽兹,固然将莎士比亚奉为神明,但是在十八世纪,伏尔泰曾经对莎翁大肆攻击。伏尔泰曾经留英三年,回国后屡在作品中介绍莎翁,但等到法国的文艺界显示崇莎的倾向且将莎士比亚与法国悲剧大家高乃伊相提并论的时候,伏尔泰竟因妒生嗔,讥莎翁粗鄙不文,说“莎士比亚是一个野人,只有几星天才的火花,在可怖的夜里闪现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常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评论莎士比亚。十九年前,我念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患“左”倾幼稚病的同学,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指控莎士比亚为贵族阶级的御用文人,戏院的股东,女皇的佞伶。愤怒的我,立刻和他展开论战,为莎翁洗刷莫须有的罪名。事实上,当时我对于莎剧的种种,并无深切了解。
在“左”倾的浪潮中,我国的古典大师往往成为罪人,被拖出来鞭尸。中年以后的闻一多,生活困苦,情绪紧张,在同情郊寒岛瘦之余,竟然诬苏轼作帮闲文人,充倜傥才子。陶潜的命运,似乎也飘摇不定。台湾诗人邮票四种,有白居易而无陶潜,拥陶派情何以堪?以陶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言,在诗宗词曹之中,难道连四名以内都考不上?白居易固然成就可观,但他那种忧时爱国的写实风格,标出杜甫一人已可概括其余,何必于此风格亮瑜并列,而于高士襟怀则独付阙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自谦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白居易可以说是诗人之中为幸运的一位,不但及身而享盛名,眼见自己的大作,题于“乡校佛寺,游旅行舟之中”,咏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即在千载之后,无论海内海外,亦皆香火不绝。在岛内,他已经上了额的三元邮票。在国外,经亚瑟·魏利(Arthur Waley)等人的再三译介,Po Chu-i的大名,久已凌驾杜甫,媲美李白。
古人棺木已朽,议论尚犹未定。今人坟土未干,评价自然更难一致。胡适去世已经六年,倒胡的遗老宿儒迄今仍喋喋不休,咬定白话文断送了中国的固有文化,而西化思想是中国一切乱源。拥胡人士则趋向另一,犹津津乐道他牙牙学语的白话诗和已经落伍的美学思想。在动荡的现代中国,大多数的名作家,恐怕都要暂时悬在棺已盖而论未定的虚空中,等待尘土落定,历史来为他们从容画像。例如周氏兄弟,今日棺已皆盖,而时论纷纷,就是现代文学史典型的问题人物。
现已八旬有三的美国诗人庞德,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物。但有时,那“问题”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是美学的。从文学史的观点看来,后者毋宁是更为严重。例如五四人物中,徐志摩的诗和朱自清的散文,素为新文学的读者所称道,迄今仍有不少人,言新诗必举《再别康桥》,言散文则必推《背影》,好像自二十年代迄今的四十年中,我国的新文学贫乏得只留下这么两篇小品。事实上,从现代文学的标准看来,徐志摩只能算是一个次要诗人(minor poet)。以浪漫诗人为喻,他的地位大约相当于汤默斯·莫尔(Thomas Moore)或者兰尼尔(Sidney Lanier)。拿徐志摩来比拟拜伦或雪莱,是外行人语,因为他既无《唐璜》那样丰富的巨著,也没有《西风颂》《致云雀》《云》那样精纯的力作。至于朱自清的散文,清畅平易而已;这种只求无过不望有功的文体,比起前贤的前后《赤壁赋》一类杰作,直如淡茗之于醇醪。
文学批评,常有影响力(inflfluence)一说。传统的观念,以为所谓影响,只是前人施之后人,呈单行(one way)状态。事实上,后人对前人,今人对古人,也是有影响力的。文学史的透视,往往因为加入了新的因素,而呈现新的全景。某一时期的文学,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原来秩序井然,尊卑有别,成为一个所谓hierarchy;可是到了下一个时期,由于美学思想变了,或者发现了新的史料,前一时期的文学原有的秩序,便必须加以修正了。例如唐人的文学批评,并尊李杜,到了宋人笔下,便尊杜而抑李;更有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之说。又例如在十九世纪后期,丁尼生几有独步诗坛之概,到了二十世纪,反浪漫运动兴起,便有人将白朗宁置于丁尼生之上,等到霍普金斯的诗集出版,丁尼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压倒性优势,更是摇摇欲坠了。
因此盖棺不定论,可作三解。,伟大并无可靠的标准。文学风气多变,批评思想日新,今日的巨人可能变成明日的侏儒,因为明日的尺寸将异于今日,或因一位新巨人之发现而使旧巨人“矮了半截”。一位名作家,常以另一名作家为“假想敌”,念兹在兹,以为身后与争千秋之名者,当为斯人无疑。结果可能两人都假想错了: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里,忽然闪出一个无名的角色,把桂冠摘去。拜伦一生妒忌湖畔诗人,尝谓诗坛非一家禁地,班主宝座,当有史考特、罗吉士、甘宝、莫尔、克拉布相与竞逐,不料上述五人皆属配角,而真正的主角却是他所忽略的雪莱和济慈。第二,同行相妒,文人相轻。一位作家常会幻想,百年后,历史当是我所是,而非我所非。事实上,历史的演变常由相对甚或相反的力量所促成;在某一时期之内,基督固然取代了恺撒,但从整个历史着眼,则恺撒仍是恺撒,不容抹杀。当时曾是敌人的作家们,在文学史上往往是香火共事,秋色平分的。冤家果然路窄。“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结果仍是王杨卢骆,挤在一间小庙里。革命党的弥尔顿和保皇党的骑士诗人们,不但是文敌,甚至是政敌,而事过境迁,同登十七世纪诗史。伏尔泰和卢梭,一个是古典大师,一个是浪漫鼻祖,生前是死敌,殁后同葬伟人祠中,成为近邻。第三,大众习于权威,安于攀附。除了少数例外,一位大作家,一个新天才的出现,通常皆有赖一小撮先知式的读者,所谓élite者的发掘与拥护。这种情形,不独在作家的生前如此,即在身 后也往往会持续一段时期。甚至于,在那位作家的伟大性已获公认之后,真正能欣赏他的,恐怕还只是那一小撮知音。唐朝的李贺、李商隐,宋朝的陈师道、陈与义,英国诗中的邓约翰、白朗宁、霍普金斯等等,都是这种例子。在所谓“大众传播”日趋发达的今天,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流行的杂志等等几乎垄断了国民的美感生活,成为文艺鉴赏的掮客集团。“报上说那本小说已经在拍电影了!”便是小市民现成有力的引证。把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交给这些文艺买卖的掮客去决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现代作家的孤绝感,一部分因此形成。不过,盖棺虽难定论,得失存乎寸心,文运不绝如缕,一半有赖作家的自知与自信,另一半则有赖那些先知先觉的读者。至于那些掮客,无论喊的是古董或是时装,呼声再响,历史的耳朵是听不进去的。
另一段城南旧事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
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 在六○年代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一九六一,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
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斯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
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的,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Zh、Ch不卷,Sh、S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 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
湾,却来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成为众客共享的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也“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而且决定得很快,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就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大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廿七年,不幸在一九九五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与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人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而在她文学成就的,《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
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辞说:“林海音岂止是常青树,她简直是常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荫
深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
大的男性。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闽南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
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
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痖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纪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