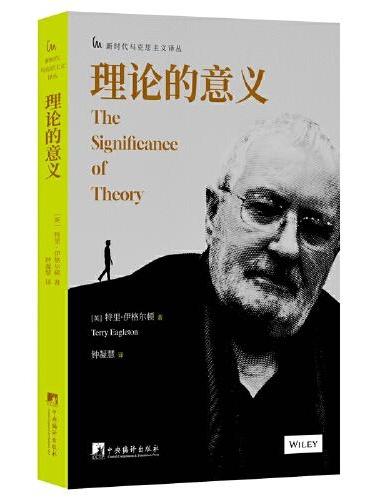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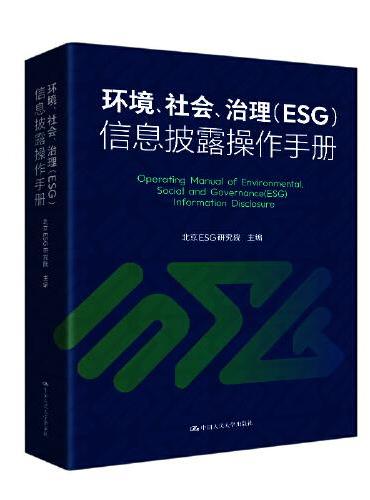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
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
售價:NT$
1190.0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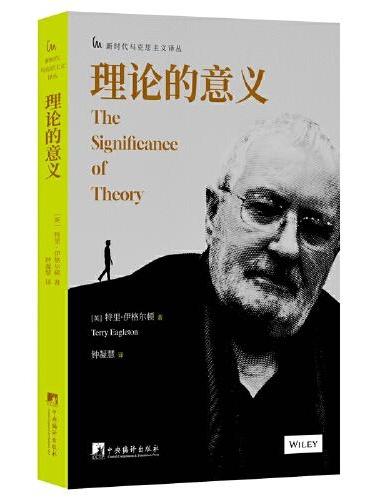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NT$
240.0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
★余光中逝世五周年,缅怀致敬——
余光中家属亲自授权审定篇目,原汁原味完整呈现余光中经典文学。
★梁实秋、莫言、张晓风、韩少功极力推崇的文学大家,央视、新京报、南方周末等缅怀——
梁实秋赞他诗文双绝,莫言赞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真正高明的继承,张晓风赞他是文字方面的全才……
《朗读者》邀请他亲自朗读《民歌》,因为他,所有人更深刻理解了“乡愁”……
★不看不知道,余光中原来这么幽默、犀利——
关于说话:心情好,婉说,心情坏,直说。对聪明人,婉说,对笨人只有直说。
关于开会:世界上无趣的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辨一件议而不决、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方式。
关于借钱:借钱,实在是一件紧张的事,富于戏剧性。借钱是一种神经战,紧张的程度,可比求婚,因为两者都是秘密进行,而面临的答复,至少有一半可能是“不肯”。
★是诗人,也是带着笑意的生活观察家——
他观察朋友圈:朋友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趣,低级而无趣。
他观察出版圈:作家要多出好书,读
|
| 內容簡介: |
内容简介:
余光中说,幽默实在是荒谬生活的解药!凡事过分不合情理,或是过分违背自然,都构成荒谬。荒谬的解药有二:是坦白指摘,第二是委婉讽喻,幽默属于后者。
《宜幽默,宜从容:对抗荒诞的生活——余光中的生活观察》收录了《假如我有九条命》《朋友四型》《借钱的境界》《论二房东批评家》等文化评论文章和诗歌作品,展现了余光中对生活中趣事、新事、奇事的观察、感悟与点评。他以敏锐的双眼观察,以细腻的笔触书写,有辛辣的讽刺、幽默的调侃,也有随性的思考,以及对时代变迁的感悟。
余光中说:“诗歌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写幽默文章,也从王尔德那学到很多招数。”阅读本书,可以看到余光中的渊博学识、睿智观点、绚丽文采和诙谐幽默。
与其活在乏味的人间,不如自成有趣的宇宙。幽默,是荒谬生活的解药。
|
| 關於作者: |
余光中
当代知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评论家,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
1928年生于南京,福建永春人。就读金陵大学、厦门大学,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曾获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政治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著有诗集《白玉苦瓜》《藕神》等;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青铜一梦》等;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举杯向天笑》等;翻译《理想丈夫》《温夫人的扇子》《不要紧的女人》《老人和海》《凡高传》《济慈名著译述》等,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秋之颂》等。
余光中,学识渊博、睿智诙谐。其作品文字壮阔铿锵,又细腻柔绵,在华语世界影响深远,被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中。
|
| 目錄:
|
代序:幽默的境界
部分 幽默实在是荒谬的解药
假如我有九条命
朋友四型
借钱的境界
论二房东批评家
蝗族的盛宴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开你的大头会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鸡同鸭讲
谁来晚餐?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娓娓与喋喋
第二部分 种树的人往往来不及乘凉
两个寡妇的故事
王尔德讲广东话
给抓到小辫子
戏孔三题
当奇迹发生时
横槊酾酒
长未必大,短未必浅
老得好漂亮
与杜十三郎商略黄昏雨
句短味长说幽默
第三部分 只是不甘寂寞
钞票与文化
好书出头,坏书出局
喂,你是哪一派?
笔耕与舌耕
粉丝与知音
莫惊醒金黄的鼾声
传家之宝
专业读者
另有离愁
寂寞与野蛮
绣口一开
第四部分 代差往往成为推动社会的力量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独木桥与双行道
新大陆,旧大陆
后浪来了
难惹的老二
乐山乐水,见仁见智
舞台与讲台
说起计程车
车上哺乳不雅?
环保分等
书斋·书灾
|
| 內容試閱:
|
幽默的境界
据说秦始皇有一次想把他的苑囿扩大,大得东到函谷关,西到今天的凤翔和宝鸡。宫中的弄臣优旃说:“妙极了!多放些动物在里面吧。要是敌人从东边打过来,只要教麋鹿用角去抵抗,就够了。”秦始皇听了,就把这计划搁了下来。
这么看来,幽默实在是荒谬的解药。委婉的幽默,往往顺着荒谬的逻辑夸张下去,使人领悟荒谬的后果。优旃是这样,淳于髡、优孟是这样,包可华也是这样。西方有一句谚语,大意是说: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的浪漫,也是荒谬的一种。凡事过分不合情理,或是过分违背自然,都构成荒谬。荒谬的解药有二:是坦白指摘,第二是委婉讽喻,幽默属于后者。什么时候该用前者,什么时候该用后者,要看施者的心情和受者的悟性。心情好,婉说;心情坏,直说。对聪明人,婉说,对笨人只有直说。用幽默感来评价人的等级,有三等。等有幽默的天赋,能在荒谬当中觑见幽默。第二等虽不能创造幽默,却多少能够领略别人的幽默。第三等连领略也无能力。等是先知先觉,第二等是后知后觉,第三等是不知不觉。如果幽默感是磁性,等便是吸铁石,第二等是铁,第三等便是一块木头了。这么看来,还勉强可以将秦始皇归入第二等,至少他领略了优旃的幽默感。
第三等人虽然没有幽默感,对于幽默仍然很有贡献,因为他们虽然不能创造幽默,却能创造荒谬。这世界,如果没有妄人的荒谬表演,智者的幽默岂不失去了依据?晋惠帝的一句“何不食肉糜?”惹中国人嗤笑了一千多年。晋惠帝的荒谬引发了我们的幽默感:妄人往往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成全别人的幽默。
虚妄往往是一种膨胀作用,相当于螳臂当车,蛇欲吞象。幽默则是一种反膨胀作用,好像一帖泻药,把一个胖子泻成一个瘦子那样。可是幽默并不等于尖刻,因为幽默针对的不是荒谬的人,而是荒谬本身。高度的幽默往往源自高度的严肃,不能和杀气、怨气混为一谈。不少人误认尖酸刻薄为幽默,事实上,刀光剑影当中只有恨,并无幽默。幽默是一个心热手冷的开刀医生,他要杀的是病,不是病人。
把英文humour译成幽默,是神来之笔。幽默而太露骨太嚣张,就失去了“幽”和“默”。高度的幽默是一种讲究含蓄的艺术,暗示性愈强,艺术性也就愈高。不过暗示性强了,对于听者或读者的悟性,要求也自然增高。幽默也是一种天才,说幽默的人灵光一闪,绣口一开,听幽默的人反应也要敏捷,才能接个正着。这种场合,听者的悟性接近禅的“顿悟”;高度的幽默里面,应该隐隐含有禅机一类的东西。如果说者语妙天下,听者一脸茫然,竟要说者加以解释或者再说一遍,岂不是天下扫兴的事情?所以说,“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世界上有两种话必须一听就懂,因为它们不堪重复:是幽默的话,第二是恭维的话。理想也是过瘾的配合,是前述“幽默境界”的第二等人围听等人的幽默:说的人说得精彩,听的人听得尽兴,双方都很满足。其他的配合,效果就大不相同。换了等人面对第三等人,一定形成冷场,且令说者懊悔自己“枉抛珍珠付群猪”。不然便是第二等人面对等人而竟想语娱四座,结果因为自己的“幽默境界”欠高,只赢得几张生硬的笑脸。要是说者和听者都是等人呢?“顿悟”当然不成问题,只是语锋相对,机心竞起,很容易导致“幽默比赛”的紧张局面。万一自己舌翻谐趣,刚刚赢来一阵非常过瘾的笑声,忽然邻座的一语境界更高,利用你刚才效果的余势,飞腾直上,竟获得更加热烈的反应,和更为由衷的赞叹,则留给你的,岂不是一种 “第二名”的苦涩之感?
幽默,可以说是一个敏锐的心灵,在精神饱满生趣洋溢时的自然流露。这种境界好像行云流水,不能作假,也不能苦心经营,事先筹备。世界上有的是荒谬的事,虚妄的人;诙谐天成的心灵,自然左右逢源,取用不尽。幽默忌的便是公式化,譬如说到丈夫便怕太太,说到教授便缺乏知识,提起官吏,就一定要刮地皮。公式化的幽默很容易流入低级趣味,就像公式化的小说中那些人物一样,全是欠缺想象力和观察力的产品。我有一个远房的姨丈,远房的姨丈有几则公式化的笑话,那几则笑话有一个忠实的听众,他的太太。丈夫几十年来翻来覆去说的,总是那几则笑话,包括李鸿章吐痰、韩复榘训话,等等,可是太太每次听了,都像初听时那样好笑,令丈夫的发表欲得到充分的满足。夫妻两人显然都很健忘,也很快乐。
一个真正幽默的心灵,必定是富足、宽厚、开放,而且圆通的。反过来说,一个真正幽默的心灵,不会固执成见,一味钻牛角尖,或是强词夺理,厉色疾言。幽默,恒在俯仰指顾之间,从从容容,潇潇洒洒,浑不自觉地完成:在一切艺术之中。幽默是离宣传远的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和幽默是绝缘的。宁曳尾于涂中,不留骨于堂上;非梧桐之不止,岂腐鼠之必争?庄子的幽默是清远洁的一种境界,和一般弄臣笑匠不能并提。真正幽默的心灵,绝不抱定一个角色去看人或看自己,他不但会幽默人,也会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会释然自嘲,泰然自贬,甚至会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之中,像钱默存所说的那样,欣然独笑。真具幽默感的高士,往往能损己娱人,参加别人来反躬自笑。创造幽默的人,竟能自备荒谬,岂不可爱?吴炳钟先生的语锋曾经伤人无算。有一次他对我表示,身后当嘱家人在自己的骨灰坛上刻“原谅我的骨灰”(Excuse my dust.)一行小字,抱去所有朋友的面前谢罪。这是吴先生二十年前的狂想,不知道他现在还要不要那样做?这种狂想,虽然有资格列入《世说新语》的任诞篇,可是在幽默的境界上,比起那些扬言愿捐骨灰做肥料的利他主义信徒来,毕竟要高一些吧。
其他的东西往往有竞争性,至少幽默是“水流心不竞”的。幽默而要竞争,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幽默不是一门三学分的学问,不能力学,只可自通,所以“幽默专家”或“幽默博士”是荒谬的。幽默不堪公式化,更不堪职业化,所以笑匠是悲哀的。一心一意要逗人发笑,别人的娱乐成了自己的责任,那有多么紧张?自生自发无为而为的一点谐趣,竟然像一座发电厂那样日夜供电,天机沦为人工,有多乏味?就算姿势升高,幽默而为大师,也未免太不够幽默了吧。文坛常有论争,唯“谐坛”不可争论。如果有一个“幽默协会”,如果会员为了竞选“幽默理事”而打起架来,那将是世界上的荒唐,不,的幽默。
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越大越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越小越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
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 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信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 假如有一条命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致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时,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
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之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做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
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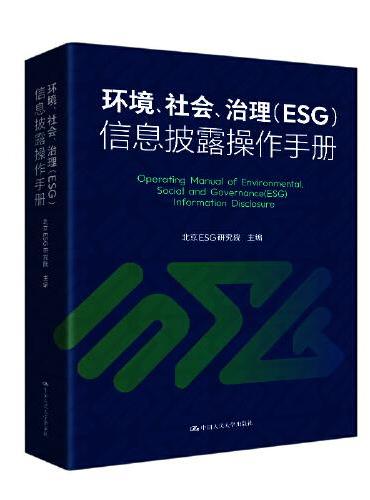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