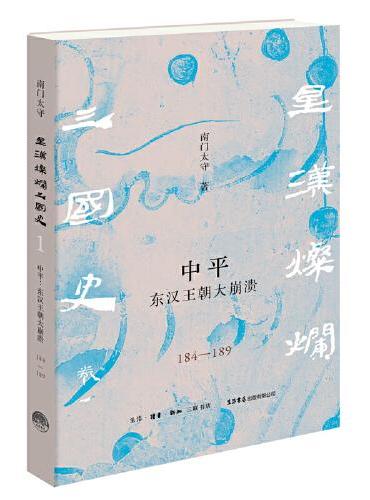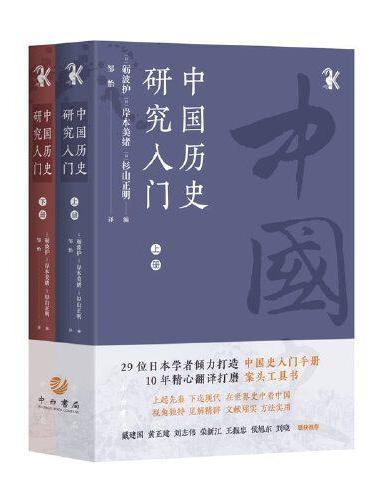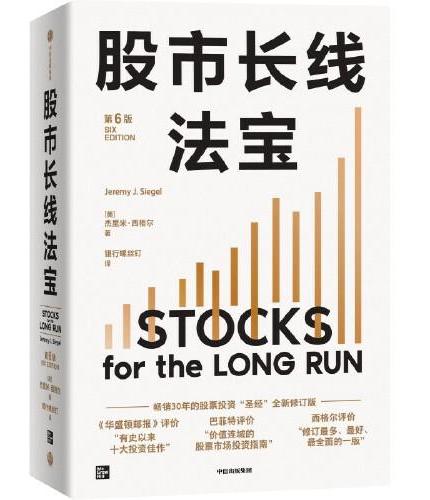新書推薦: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概念与方法 [美]马苏德·索鲁什 [美]理查德·D.布拉茨](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5912.jpg)
《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概念与方法 [美]马苏德·索鲁什 [美]理查德·D.布拉茨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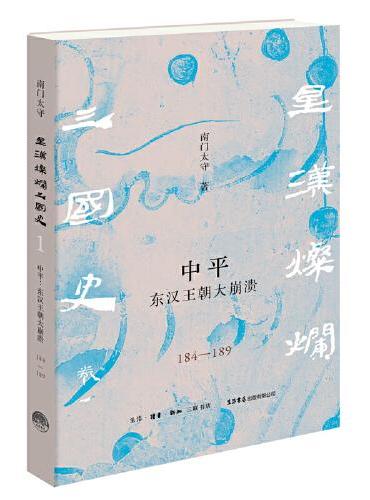
《
中平:东汉王朝大崩溃(184—189)
》
售價:NT$
245.0

《
基于鲲鹏的分布式图分析算法实战
》
售價:NT$
4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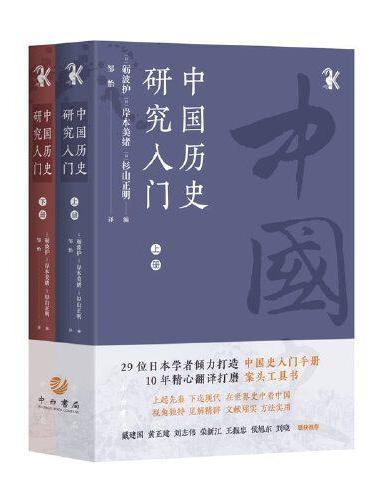
《
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全二册)
》
售價:NT$
1290.0

《
夺回大脑 如何靠自己走出强迫
》
售價:NT$
299.0

《
夏天,19岁的肖像(青鲤文库)岛田庄司两次入围日本通俗文学奖直木奖的作品 ,同名电影由黄子韬主演!
》
售價:NT$
225.0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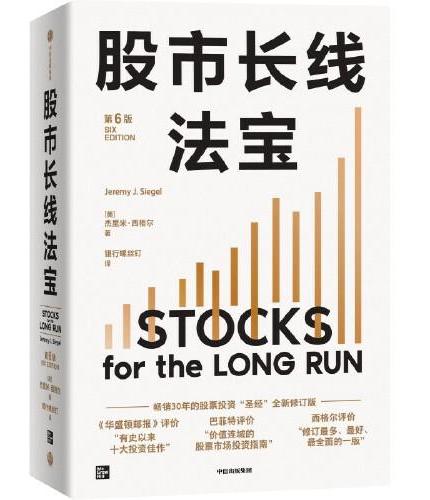
《
股市长线法宝(第6版)
》
售價:NT$
640.0
|
| 編輯推薦: |
|
“爱尔兰短篇小说女王”克莱尔?吉根潜心八年的短篇小说力作,描写了爱尔兰现代社会中的绝望与欲望,精悍之中透着极其克制的冷调,情节起伏出人意料,让人惊叹在短篇格局中竟有如此跌宕的内容。本书出版后获得英国重要短篇小说文学奖“边山短篇小说奖”。中译本获首届爱尔兰文学翻译奖最佳翻译奖。此次新增一则短篇《漫长而痛苦的死亡》,描述了一位女作家失恋后来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故居试图重新投入阅读与写作的一天。
|
| 內容簡介: |
以三部作品跻身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家之列、爱尔兰短篇小说女王
克莱尔?吉根 潜心八年的短篇小说力作
英国重要短篇小说文学奖“边山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中译本获首届爱尔兰文学翻译奖最佳翻译奖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是克莱尔?吉根的第二部作品,描写爱尔兰现代社会中的绝望与欲望,精悍之中透着极其克制的冷调,情节起伏出人意料,让人惊叹在短篇格局中竟有如此跌宕的内容。本书出版后获得英国重要短篇小说文学奖“边山短篇小说奖”。此次新增一则短篇《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
| 關於作者: |
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
生于爱尔兰威克洛郡乡间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是家中小的孩子。十七岁时远赴美国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主修英语和政治学,一九九二年回到爱尔兰后,相继在威尔士加迪夫大学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攻读创意写作硕士课程。
一九九四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部短篇小说集《南极》于一九九九年出版,被认为具有雷蒙德?卡佛、威廉?特雷弗等短篇小说大师作品的神韵,并获得二○○○年度“鲁尼爱尔兰文学奖”和《洛杉矶时报》年度图书奖。其创作极为严肃认真,一直到二○○七年才推出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同样深受英语文坛好评,获得“边山短篇小说奖”。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福特选为个人年度好书。二○○九年出版中篇小说《寄养》,获颁戴维?伯恩爱尔兰写作奖。
目前居住在爱尔兰劳斯郡乡间。
|
| 目錄:
|
001 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021 离别的礼物
034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060 黑马
070 护林员的女儿
115 在水边
127 妥协
143 花揪树的夜晚
|
| 內容試閱:
|
凌晨三点,她总算驱车驶过那座通往阿基尔岛的桥。村庄终于出现了:渔民合作社,五金店,食品店,红砖小教堂,在昏黄的路灯下,每座房子都上着锁,四下里一片寂静。她顺着一条黑黢黢的道路往前开,路两边是高高的杜鹃花篱笆,杂乱疯长,早已过了花期。她看不到一个人,也看不到一扇亮灯的窗户,只看见几只睡熟的黑腿绵羊,后来又看见一只狐狸站在车尾灯里,一动不动,样子有点吓人。道路变得狭窄,接着,拐入了一条宽阔而空旷的大路。她感觉到了大海、沼泽;开阔而广袤的空间。杜格特的路没有明显标志,但是她很笃定地往北一拐,顺着荒无人烟的道路,驶往伯尔故居。
来的途中,她两次把车停到路肩上,闭上眼睛小睡一会儿,但是此刻,到了岛上,她感到十分清醒,精力充沛。就连这条径直坠入海滩的漆黑道路,似乎也充满了生命力。她感觉到了高高耸立、遮天蔽日的大山,光秃秃的山丘,以及在下面的道路尽头,大西洋的海浪拍打沙滩时清脆悦耳的声音。
管理员告诉她在哪儿能找到钥匙,她急切地用手在煤气罐周围摸索。钥匙链上有好几把钥匙,她挑选的把就打开了锁。进去后发现房子重新装修过:厨房和客厅合并,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长房间。房间一头还是那个刷成白色的壁炉,但另一头安放了新的水池和橱柜。房间中间有一个沙发、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配套的硬椅子。她打开水龙头,烧水沏茶,用篮子里的泥炭点了一堆小火,在沙发上临时铺了个床。玻璃窗外,倒挂金钟的树篱在晨曦的微光中颤动闪耀。她脱掉衣服,躺下来,伸手拿过书,读了契诃夫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一章。这章写得很精彩,可是她刚读完,就感到眼皮耷拉下来,她愉快地关上灯,知道明天整个儿都属于自己,工作,阅读,在路上散步,徒步去海滩。
醒来时,她隐约感觉一个梦的尾巴——如丝绸一般——悄然隐去,她睡了很长时间,睡得很沉、很满足。她把水烧开,从车里取回自己的东西。她的行李很少:几本书,几件衣服,一小箱子食物。还有几个本子,几张写了笔记的纸,上面的字迹潦草模糊。天空布满云团,但依稀可见几抹蔚蓝,预示着一个好天气。下面的大海边,一长条丝带般的海水掀起透明闪亮的海浪,在海滩上摔得粉碎。她渴望阅读,渴望工作。她觉得自己可以接连几天坐在这里,阅读,工作,什么人也不见。她在思考手头的作品,琢磨着应该怎么开头,突然,电话响了。响过几声后沉默下来,接着又响。她伸手去拿话筒,与其说是为了接听,不如说是为了让它不要再响。
“喂?”一个带口音的男人说,“我是……”报出了一个外国名字。
“什么?”
“管事的说你住在这儿。我是德语文学教授。”
“噢。”她说。
“我可以看看房子吗?管事的说你会让我看的。”
“说实在的,”她说,“我没有——”
“噢,你在工作吗?”
“工作?”她说,“我在工作,是的。”
“真的吗?”他说。
“我刚搬过来。”她说。
“我跟管事的谈过了,他说你会让我看的。眼下我就站在伯尔故居的外面呢。”
她转向窗户,顺手从纸箱里拿了一个青苹果。
“我还没穿好衣服,”她说,“而且我在工作。”
“真是打扰你了。”他说。
她看着水池里。不锈钢反射着晨光。“你能改天再来吗?”她说,“星期六怎么样?”
“星期六,”他说,“我就走了。我得离开,但是眼下我就站在伯尔故居的外面呢。”
她穿着睡衣站在那儿,手里拿着苹果,考虑着这个站在外面的男人。“今天晚上你还在吗?”
“在,”他说,“今天晚上你合适吗?”
“如果你八点钟来,”她说,“我会等你。”
“我必须那时候再来一趟?”
“是的,”她说,“你必须再来一趟。”
说完她就把电话挂断了。她看着话筒,不明白刚才为什么把它拿起来,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号码告诉别人。这里竟然有电话号码,她为此生了一会儿闷气。这刚刚开始的一天,本来是个好日子,现在仍是个好日子,但是有了变化。既然她定了一个时间,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天就只能朝着德国人来访的方向推进了。她走进浴室,刷牙,心里想着站在外面的他。她可以迅速换掉睡衣,出去叫他进来,那么这一天便又会重新属于她。然而,她坐在炉火边,捅了捅炉栅里的炉灰,盯着壁炉架上的一个玻璃大水罐出神。她要走到海边去,从树篱上摘一些倒挂金钟,在他到来前给水罐里插满那些悬挂的红花。她要好好地洗一个澡。她寻找手表,过了好几分钟才找到,在昨天穿的那条牛仔裤口袋里。她盯着白色表盘看了整整一分钟。表上显示,她的三十九岁生日刚过中午。
她迅速站起身,走进伯尔的书房,这小房间里有一个废弃的壁炉,还有一扇面朝大海的窗户。就在这个房间里,伯尔写了如今已名闻遐迩的那部日记,但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伯尔死后,他的家人把这座房子留作了作家的创作基地。现在,她要在这里住两个星期,潜心写作。她用一块湿布擦了擦书桌,把笔记本、辞典、稿纸和钢笔都放在桌面上。万事俱备,现在只缺咖啡了。她走到厨房,在那箱食物里寻找。她又花了一些时间查看橱柜,但没有找到咖啡。她还需要牛奶——牛奶很快就要喝完了——但是她一心只想投入工作。她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拿起钥匙,开车上路,到村子里去。
她在村里没有耽搁,买了咖啡、牛奶、引火物、一种蛋糕粉、一品脱奶油,还买了报纸。她顺着原路返回时,太阳火辣辣的,因此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往南拐入了大西洋车道。这里没有什么住宅,也几乎看不见一簇灌木。她想象着冬天住在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感觉:大风挟裹着沙子吹过海滩,猛烈地劈砍那些树篱;无情的暴雨;海鸥凄冷的尖叫——想象着一旦冬天终于过去,一切会发生怎样戏剧性的改变。路边,一只胖乎乎的小母鸡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伸着脑袋,脚奋力地攀上那些石子。一只多么漂亮的母鸡啊,羽毛边缘是白色的,就好像它在走出家门前给自己扑了粉。它跳到草地边,既不往左看也不往右看,径直冲过马路,然后停住脚,重新调整一下翅膀,撒腿朝悬崖那儿奔去。女人注视着母鸡埋头冲到悬崖边,毫不犹豫地纵身跃过悬崖。女人停住车,朝母鸡坠落的那个地点走去。她隐隐约约不想从悬崖边往下看,但还是看了,发现那只母鸡和几个同伴一起,在稍稍下面一点的草坡上的一个沙坑里,或用爪子刨土,或懒洋洋地躺着。
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这一幕,觉得很有趣,然后放眼眺望大海。在辽阔蔚蓝的天空下,大海是那么辽阔、那么蔚蓝。前面远远的有个小湾,里面是一池清澈的、幽深的海水,边缘紧贴着一道白色悬崖的底部。她离开汽车,循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小湾走去,然而小道消失了,下坡路变得很陡,令人十分恐惧。她站住脚,这儿能把一切尽收眼底:那一池幽深的海水,水面下的礁石和纠结的黑色水草。她返身顺坡而上,走到小湾的另一边,发现了另一条小道,通往下面一条从沼泽流出的淡盐水小溪。她小心翼翼地踏着那些褐色的石板,顺着湿滑的小路,终于来到了白色阳光照耀下的小湾。
细细的砾石被高高的浪头冲起,但她的周围是一层层亮晶晶的、被漂白的石子。她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石子,每次她移动时它们都在她脚下像陶器一般叮当作响。她真想知道它们在这里躺了多久,是什么种类的石头——但这重要吗?此时此刻,它们在这里,她也在这里。她环顾四周,没有看见一个人,便脱去衣服,笨拙地踏着水边那些粗糙、潮湿的石子往前走。海水比她想象的温暖多了。她在水里趟着走,后来海水突然变深,她感觉水草贴在她腿上,黏糊糊的,令人亢奋。水齐到胸口时,她深深吸了口气,仰面朝天,游了出去。她告诉自己,这才是她,此时此刻,应该做的事情,应该过的生活。她看着地平线,发现自己在默默感谢某种她并不真正相信的东西。
她游到了水域变宽、小湾融入大海的地方。她从未置身于这么深的海水。继续往前游的渴望那么强烈,但是她拼命克制着,顺水漂浮了一阵,就游回岸边,躺在那些温暖的石子上。她躺在那儿,觉得高处的悬崖上似乎有个身影,但是在阳光里看不真切。她躺在那儿,直到皮肤被晒干,然后迅速穿上衣服,顺着那条陡峭的小路,走回到汽车边。
回到房子里,她一边思忖着工作,一边烤了一块黑色的巧克力蛋糕。蛋糕并非完全自制,而是有现成的蛋糕粉。她只需要加入鸡蛋、油和水。她搅拌面糊,把它倒进一个罐子,大脑的某一部分又被德国人来访的事占据。一时间,她猜想那个人是什么模样,身材有多高。他说不定还能说一些关于海因里希·伯尔的趣闻轶事呢。她觉得心中一片茫然,微微有些羞愧,住着这位作家的房子,却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四点钟,她顺着小路,经过新教教堂,朝海边走去。那儿有一所小学,只有一个房间,操场上满是枯死的、毛蓬蓬的蓟花。她站在那儿,突然一阵风吹过大地,几株蓟花的冠毛被风吹散,从她眼前飘过。她继续朝小路尽头走去,那里簇拥着几座不起眼的度假屋,里面没有住人,放炉灰的桶被风吹得干干净净。下面的海边比较冷,于是她转身,返回山丘上,一边走,一边把倒挂金钟从树篱上打下来。几根细细的枝条轻轻一碰就断,发出清脆的折断声;另一些枝条则很顽固,她不得不用手把它们拧断。她喜欢这些鲜红色的、倒挂着的花,喜欢这些硬硬的、带锯齿的叶子。返回房屋时,她停下来看了看那块牌子:请尊重此处居住的艺术家的隐私。她站立片刻,看着那一行字,然后走进院子,关上院门,把那些绵羊关在外面。
进了屋,她往那个大玻璃罐里注满水,把倒挂金钟随意地摆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她用切片的西红柿和奶酪给自己做了简单的晚餐,就着昨天剩的面包和一杯红酒慢慢吃下。盘子洗干净收了起来,她点燃炉火,又看起了契诃夫的小说。
——摘自《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
|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概念与方法 [美]马苏德·索鲁什 [美]理查德·D.布拉茨](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59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