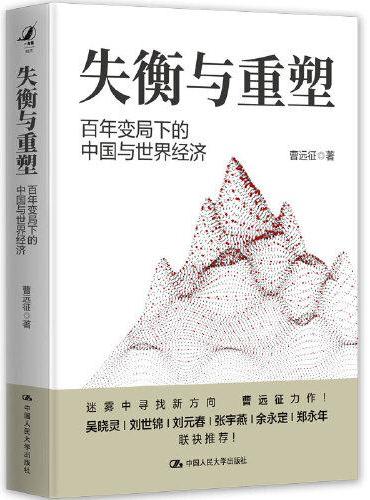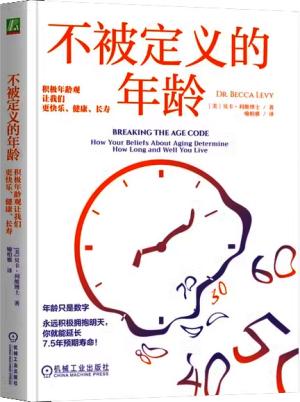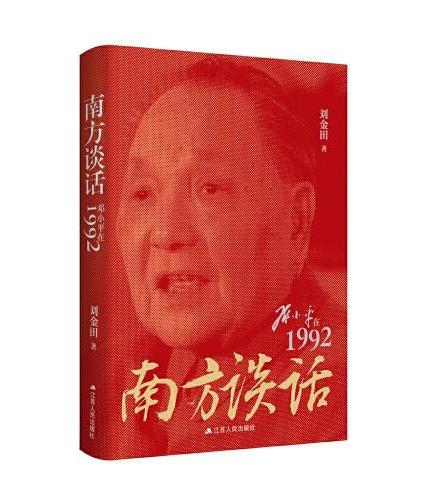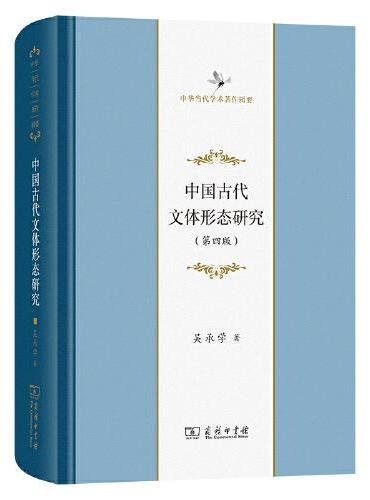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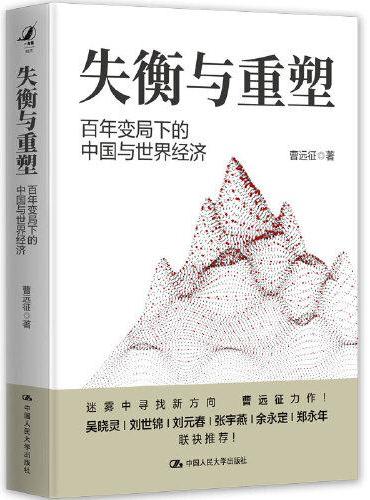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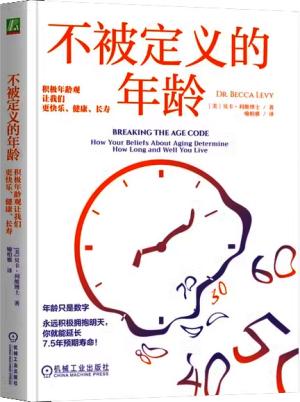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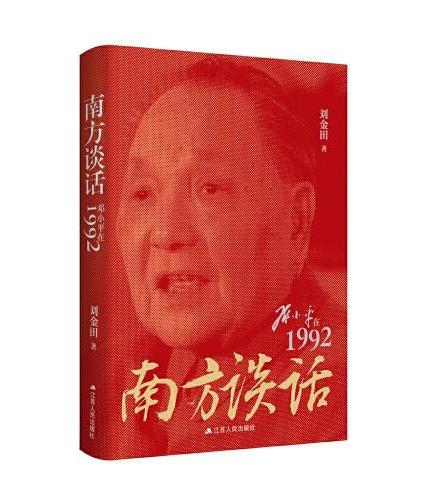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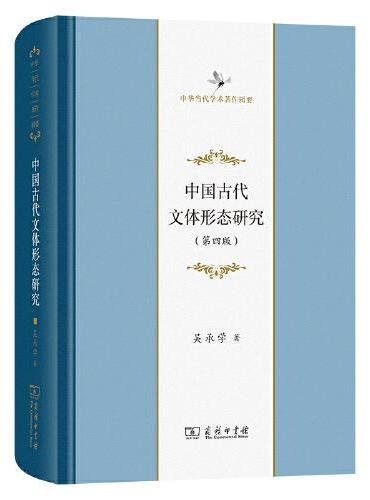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NT$
765.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NT$
403.0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NT$
286.0
|
| 編輯推薦: |
马洛伊?山多尔:描绘匈牙利民族的心灵幽境,见证欧洲市民阶层的兴衰起伏
“欧洲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所属欧洲“市民阶层”☆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马洛伊?山多尔与歌德、托马斯?曼一样,深度地探索市民阶层的精神愿景,讲述他们的心灵成长。
诺奖得主J.M.库切认为,在所有重要层面上,马洛伊都属于一个正在消亡的族类,即“奥匈帝国的进步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代表精神是“勤勉、爱国、有社会责任感、尊重学识”,是马洛伊在它不复存在后仍然孜孜不忘之物。
马洛伊一直恪守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强调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国家与社会使命,诠释出“责任”一词的全部重量。
马洛伊?山多尔自传三部曲:首度引进,代表其☆高文学成就,完整呈现原貌
三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
2015年版《一个市民的自白》:该版本为删节版。2013年底,《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才重见天日,在匈牙利出版。
2023年版《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底本即为匈牙利出版的《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但将其拆分成两部,请译
|
| 內容簡介: |
马洛伊?山多尔的青年时代从德国开始。1919年,他离开考绍,就读于莱比锡新闻学院。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与托马斯?曼和西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此后,他游历欧洲,去往东亚,最终回到布达佩斯。十年间,他是旅人、作家和记者,以冷静理性之眼凝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大陆,于繁华的表象窥见文明的黄昏时刻,揭示被美好掩映的颓然暗面:人文传统日渐式微、道德伦理分崩离析、精神家园不复存在。他更以灼热感性之笔、火烫真诚之心,追怀逝去的昨日世界,让文字成为时间与历史恒久的铭记,为身后的时代留下见证。
从远走异乡到返回故里,始于求索,终于颖悟,马洛伊历经漂泊流离的孤独与迷惘,青春放浪的不羁与浪漫,跨越阶级的友谊与爱恋,最终确认并担荷自己“匈牙利作家的使命”。他所讲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也是欧洲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 1900—1989)
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名门望族,享有贵族称谓,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蕞高荣誉“科舒特奖”。他亦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他的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
他质朴的文字蕴藏着千军万马,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他写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辩证,阶级与文化的攻守,冷静的叙述下暗流汹涌。德国文学批评界认为他与茨威格齐名,另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列。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
他是马洛伊?山多尔。
【译者介绍】
余泽民
作家、翻译家,现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特聘教授。
译有凯尔泰斯?伊姆莱、马洛伊?山多尔、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等匈牙利国宝级作家的代表作,还有道洛什?久尔吉、苏契?盖佐、巴尔提斯?阿蒂拉、德拉古曼?久尔吉等杰出作家或先锋作家的作品。代表译作:《船夫日记》《烛烬》《撒旦探戈》《平行故事》《和谐天堂》(即将出版),以及“马洛伊?山多尔自传三部曲”等。
著有《纸鱼缸》《狭窄的天光》《匈牙利舞曲》《碎欧洲》等。
曾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被誉为“当代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
|
| 內容試閱:
|
流亡的骨头(节选)
余泽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睿智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序言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得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纳道什?彼得、巴尔提斯?阿蒂拉和德拉古曼?久尔吉。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的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这使我彻底成为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十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的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一个市民的自白:欧洲苍穹下》《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的翻译工作,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草叶集》《反叛者》则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引进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曾出过繁体中文版,但是从意大利语转译的,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不免有些遗憾。当然这不是译者
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中文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2
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也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市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市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考绍岁月》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第一章
1
桥上站了两名士兵,他们穿着潇洒的系带式过膝长靴和灰绿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猎装风格的运动装。他们将戴着手套的两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列向西行驶、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货混编列车。
“快瞧啊,”我对妻子说,“这里已经是欧洲士兵把守。”
我异常兴奋地盯着他们,心脏已跳到了喉咙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险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或斯坦因?奥里尔。当时,我们两人都很年轻。我刚满二十三岁,刚刚结婚几个星期。罗拉坐在车窗旁,坐在这列已被法国人淘汰的列车上,这列火车曾经跑过巴黎沿线,如今被流放到临近德国和比利时边境的穷乡僻壤—亚琛。包厢里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被扯断的橡胶封条耷拉着,破旧的行李网低垂着,座椅里头露出了弹簧。“给他们用这个就不错了。”当这列旧车被调到亚琛时,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办事处的人这样想。的确,我们能搭乘这列火车旅行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坐在没有玻璃的车窗旁,冻得浑身哆嗦,盯着那两位“欧洲”士兵(从德国边境起的几公里路程,火车由英国人开),一想到这个我就牙齿打战。 噢,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上,我们就像没见过世面的非洲人!
在我们眼里,这一切是多么“欧洲”啊:这列气味酸臭、颠簸摇晃的火车,那位挺着啤酒肚、穿着印有银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浑身盖满邮戳似的比利时检票员,那盏挂在车厢棚顶、光亮微弱、咝咝作响的煤气灯,那张可以从考萨旅行到波普拉德菲尔卡的火车票……毫无疑问,车厢破烂座位上垂下的穗子,还有我们在沿途火车站购买的烟灰色、很难吃的法国巧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欧洲”。夏末带着尖酸烟味的“欧洲”空气吹进了包厢,包厢内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焦虑和自我意识,都让我们感到自己非常的“欧洲”。我们咬紧牙关,内心坚定,我已经感觉到巴黎正在向我们招手……(后来,在所有误入巴黎的中欧人身上,我都能体会到这种浑身发抖的优越感)我们是多么的好奇啊,激动得感觉脊背发凉。那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全部的法国文学”——我读了左拉的书,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几部小说,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译本的作品我都读了;多多少少我听人讲过一点柏格森,我“了解”法国历史,但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到现在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法国香水和头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读过波德莱尔的几首诗。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奥迪曾在那里驻足徘徊,咀嚼他那类人命运的痛楚,与此同时,他们肯定喝了许多苦艾酒,搂抱过许多“穿蕾丝袜的法兰西女郎”。是的,我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预习了许多西方的功课。瞧我们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扮得比法国人“更优雅”,我们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是否拜倒在法国女郎的石榴裙下,过着优越、舒适的市民生活?我们是否跟女教师克雷门汀女士学习法语?我们的女士们是否紧追“最新潮的法国时尚”?……没有,但我们确确实实地了解了西方文化,我们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们的阶层和我们的教养不会让我们在那里感到自惭形秽。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西方人派来接我们的冰冷、腌臜的车厢里?为什么我们怀着羞怯与惊恐坐在这儿,就像乡下的亲戚进城拜访有钱有势的大人物那样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来,“西方文化”套在我们身上有点松松垮垮,就像让非洲人穿燕尾服。我们的神经出于自罪感而进行反叛。我们在欧洲的大门口开始忏悔,“西方”毕竟不同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著作的蹩脚至极的匈牙利语译本,不同于奥迪的巴黎印象,不同于法国时尚杂志和法国刮胡刀,不同于在学校读的历史课本,不同于在家乡日常会话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顶的法语发音。我们开始猜测——其实只是出于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上对周围氛围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们国家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它不只意味着四个房间都有蒸汽供暖,有雇用的仆人、书橱里的歌德著作、优雅的绅士谈吐、对奥维德和塔西佗作品的了解,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一种文化最表面的接触,跟我们现在前去造访的另一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只存在皮毛的联系。我们通过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经感觉到困惑,感觉到在南特做一个市民跟在我们的“大城市”考绍不完全一样;在我们家乡,市民们感到尴尬内疚,我们试图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地履行市民阶层的义务,不遗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们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并没有特别的阶层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环视四周。我感到恐惧和紧张,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一遇到某道难题,就想通过自身的勤奋和让他人敌视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符合欧洲气质。
罗拉聪明地坐在车窗旁,望着欧洲沉默不语。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说话,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们相识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话般的童年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只使用符号性的语言;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阶层、同一个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气,当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她用聪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为她带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来到欧洲,她知道,“她必须格外小心”。我则左顾右盼,坐立不安,口无遮拦地喋喋不休。她静静地听着,偶尔说一句这类的话:“在柏林要多买些漱口水。现在那里肯定会便宜一些。”我在过边境时想到的是,柏林的烟斗或长筒袜吊带会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说的要买的是这些东西,会更合我意。
“欧洲士兵”走到车窗前,他们踱步的样子,就像家乡的老爷们晚上打完猎回家。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车厢,不给凭据。我问他们,到了巴黎我怎样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时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显得非常惊诧。
“他们会相信吗?”我问。
那人从嘴里取下叼着的烟卷。
“您说什么?”这位欧洲士兵不解地反问,带着诚实的想象和不大友善的傲气反问,“您总不会撒谎吧……?”
他用英语跟同伴说了几句什么,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不时怀疑地扭头看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