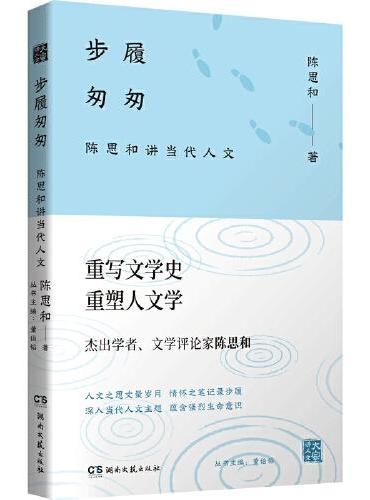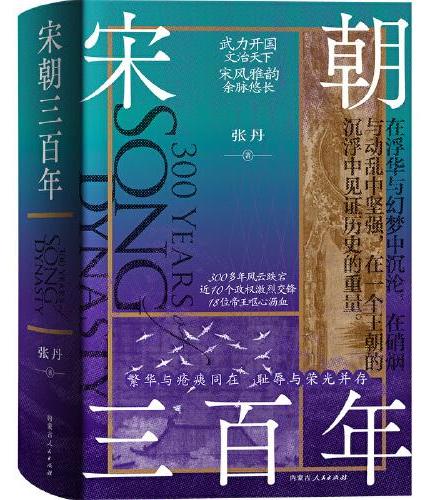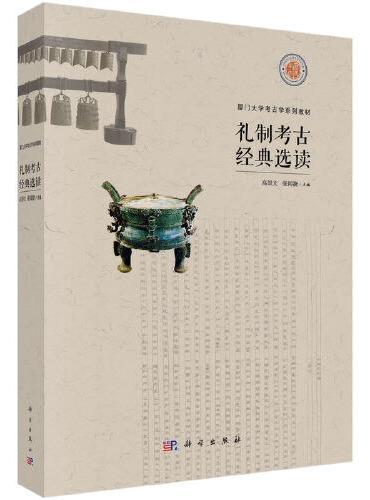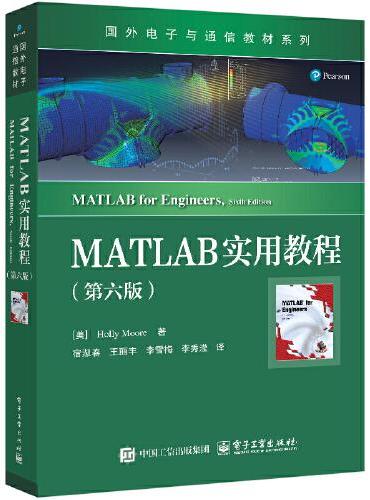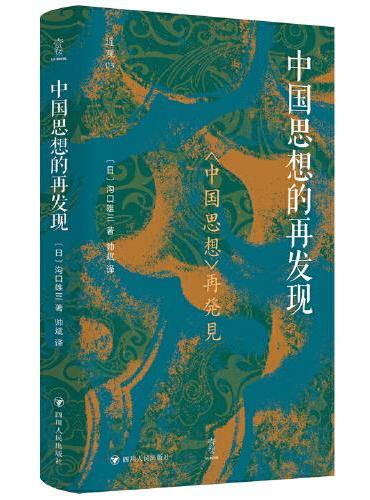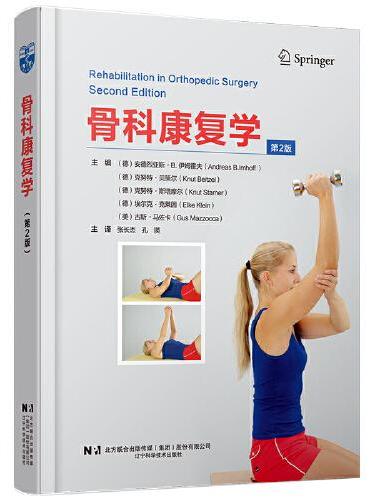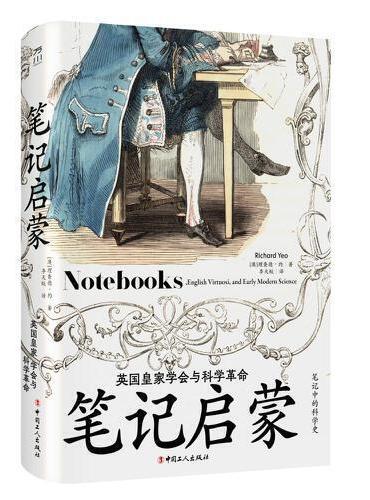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战争事典085:德国人眼中的欧战胜利日:纳粹德国的最终失败
》
售價:NT$
4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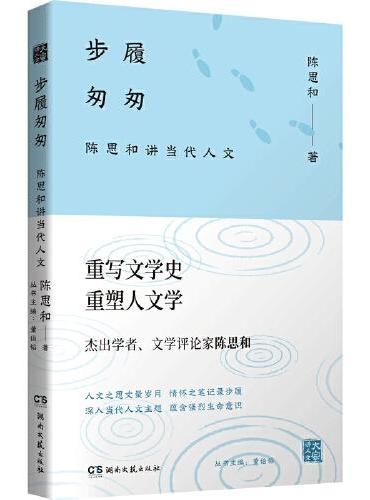
《
步履匆匆:陈思和讲当代人文(杰出学者陈思和的人文之思、情怀之笔!)
》
售價:NT$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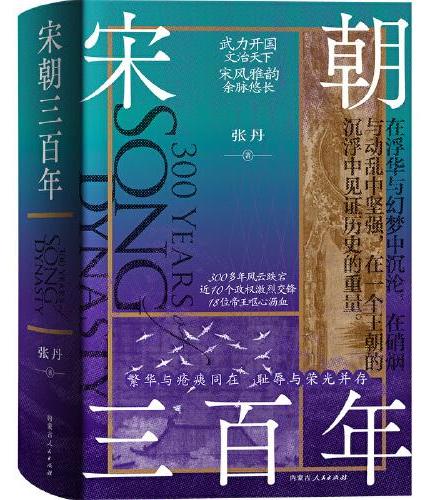
《
宋朝三百年
》
售價:NT$
7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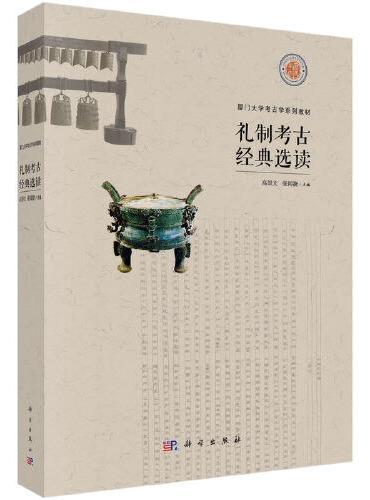
《
礼制考古经典选读
》
售價:NT$
1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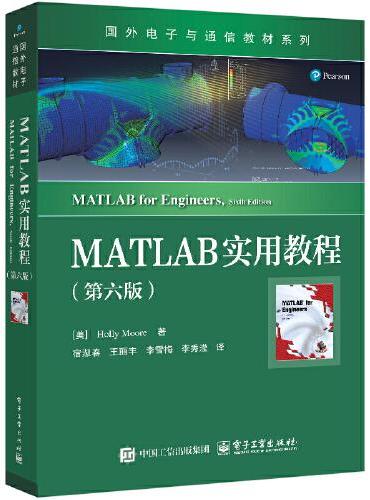
《
MATLAB实用教程(第六版)
》
售價:NT$
6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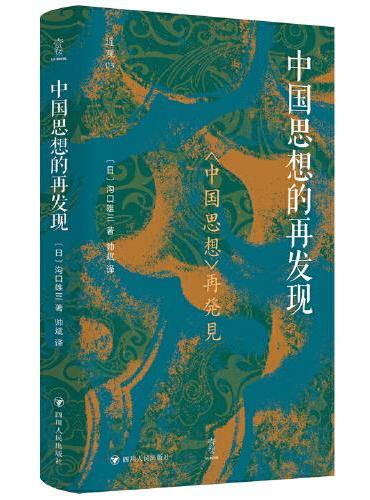
《
中国思想的再发现(壹卷:近观系列,沟口雄三教授以其精湛的学术洞察力,旨在呈现一个全面而立体的中国思想图景)
》
售價:NT$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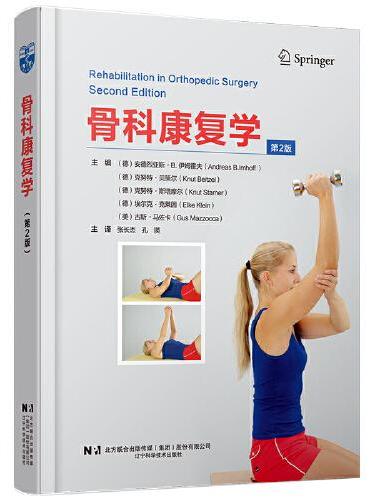
《
骨科康复学(第2版)
》
售價:NT$
11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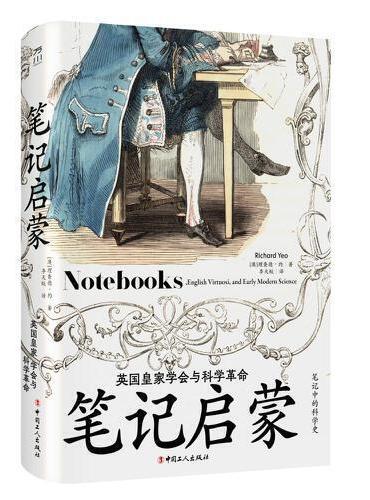
《
笔记启蒙 : 英国皇家学会与科学革命
》
售價:NT$
390.0
|
| 編輯推薦: |
李俊玲的散文以细腻、深刻而见长,体现了一位女性作家对于人生世事的温馨情怀。在她的散文中,边地生活的诸多物象携带着某种陌生气息进入读者的视野,既生动、新鲜,又充满阅读的吸引力。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适当的距离可以创造更好的阅读效果。散文中纷繁的物象,还体现了作家与大地的亲密关系。
——黄玲
|
| 內容簡介: |
|
《隐秘的人间》收录了作者近三年来所创作的二十五篇散文。共分为四辑:一、故园风脉,二、眼中世象,三、生命道场,四、栖身生活。本书依从个人经历与感受,书写出滇西小城施甸特有的乡俗民情,体现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人居形态。从一棵树到一片丛林,从一瓢一饮到人间万象,作者着力于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感受,从个体命运中去反映地域的总体风貌和全景气象。一座城、一群人、一种风俗以不同的方位烙印在作者的喜怒哀乐里。作者之所以用其中一篇书写鬼神的文章《隐秘的人间》作为文集的标题,是因为她觉得我们所处的红尘人间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人间,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人间,比如我们的内心世界,比如“举头三尺有神明”。作者想以这个标题作为这么多年来对写作的一种敬拜。
|
| 關於作者: |
|
李俊玲,女,布朗族,70后,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7届高研班学员。出版诗集《流水飞花》,散文集《另一种抵达》《跳跃的河山》。
|
| 目錄:
|
序 黄玲 /1
第一辑 故园风脉
小城人物 /3
面相 /19
有龙在侧 /28
祭忆贴 /40
人间炊米 /48
第二辑 眼中世象
大地之子 /59
人在深秋 /76
地球上最纯净的一滴水 /81
院落的世界 /89
隐秘的人间 /96
秋风恸 /108
第三辑 生命道场
宝藏丛林 /121
火语者 /131
食事记 /140
夏至 /151
庙宇 庙语 /158
第四辑 栖身生活
素时光 /173
尘世的隔离 /182
李劳动的幸福 /188
你好,黑豆! /197
距离 /204
父亲的习惯 /210
在心内科的日子 /214
见字如面 /225
小恙小记 /229
|
| 內容試閱:
|
序
黄 玲
李俊玲的散文集《隐秘的人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值得祝贺!这个项目旨在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中青年作家,推出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这是一项卓有成效的工程,对各民族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俊玲是布朗族作家,布朗族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主要分布于云南保山、临沧、西双版纳等地。布朗族还是跨境民族,其在境外主要分布于缅甸、泰国、老挝。布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民间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诗和抒情叙事诗,题材广泛。布朗族还是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和种植茶的民族,有“古老茶农”之美称。但是布朗族的作家文学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一些50后写作者,李俊玲这批70后写作者属于布朗族第二代书面文学作家。她毕业于“211”大学,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是新一代布朗族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她因为热爱文学而走上创作之路,多年来,她写诗,也写散文,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很快成长为布朗族作家群的中坚力量。
我“认识”李俊玲,是从她的获奖散文《怒江,原来我属于你》开始的,那一年,我应邀担任云南省滇西文学奖的评委,在众多作品中对这一篇留下深刻印象:散文以潞江坝为起点,沿着怒江之水一路向北逆流而上,追溯着这条搅动作者思绪的著名江流的浪花,写出了作者的灵魂和怒江之间密切而深刻的缠绕,文风朴素而又灵动。我后来才知道这位70后的布朗族写作者,2005年就开始发表汉语文学作品,其诗歌、散文已经走出云南,在全国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几十万字的作品,出版有诗集《流水飞花》,作品多次获过各种文学奖项。而且她是布朗族为数不多的几名中国作协会员中的一名,鲁迅文学院第37届高研班学员,施甸县作家协会主席。如此成绩,来自她对文学的热爱,对故土的深情。她的散文多以施甸这个小县城的民族风情、风土人文为写作背景。以小见大,开掘出丰富的人文地理内涵;切入时代,对人生世态有深入透视,使她的散文体现出独特的文风。
几年前,我参加施甸举办的一次采风活动,终于在施甸见到李俊玲。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皮肤白净的女子,面相端庄,性格温婉,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她身上有一种属于散文的婉约气质。记得那一次简短的交谈,谈的也是她的散文写作,我建议她多写她的民族和故乡,期望读到更多她的新作。她说她正在写,不久会出版一部散文集。那几年我在研究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对布朗族作家也多有关注。一个人口只有十二万的民族作家要在文学上出成绩,多出作品才是关键。之后听到她先后出版散文集《另一种抵达》和《跳跃的河山》,很是高兴。现在她又出版了《隐秘的人间》,可以让喜欢她散文的读者大饱眼福。
李俊玲的故乡施甸,其实是一座有故事的边地小城,它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保山市南部、怒江东岸,与缅甸相距二百六十公里。八千多年前,“姚关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元初,契丹人南下至此定居。著名的“永镇驿道”穿境而过,滇缅公路从北部过境六十五公里,历史上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滇西抗战,这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与日军对抗的前沿阵地,无数抗战英烈长眠于此。这块土地上的二十四个民族水乳交融,谱写着灿烂的历史文化。
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厚重的人文地理,理应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记录和展示,这是本土作家身负的重任。好在有李俊玲携她的散文新作《隐秘的人间》向我们走来,正好满足了读者对这块土地的期待心理。
《隐秘的人间》收录李俊玲近三年来所创作的二十五篇散文,书名便透露了作家的文学审美追求,她希望从个人经历与感受出发,书写出滇西小城施甸特有的乡俗民情,体现出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形态。作家力图通过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去反映地域的总体风貌和全景气象。每个作家笔下都有自己不能忘怀的故乡,这是作家生命成长的摇篮,也是散文写作的基点。同时,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也可以通过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描写,实现对精神原乡的追求和建构。让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升华为精神之境的家园,这样的散文才具有审美的价值和意义。
翻开《隐秘的人间》这部散文集,滇西小城丰富的人间万象扑面而来。这是一个地处边境、多民族共居的小城,这就注定了它的人文地理和民风民情的与众不同。在李俊玲笔下,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小城。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与她的生命成长有关,“一种风俗以不同的方位烙印在我的喜怒哀乐里”,那些记录着她生命过往的人和事,带着回忆进入文字,犹如干花在温水中一点点复活,缓缓绽放出动人光彩。在《小城人物》中,那些穿过时间迷雾向读者走来的,都是在作者心灵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和事,李俊玲把自己和小城的关系生动地比喻成植物与土地的关系,她说:“一个人在一座城待久了,便会成为这个地方的一株植物,知晓着这方土地的温度、湿度、酸碱度,以及风向、水位、日照时长,以自身特有的姿态融入在这些看似恒久却不断变幻的指数中,成为它细微而不易察觉的一部分。”作为一名70后作家,李俊玲为我们展现的是80年代的成长记忆,一座小城的历史通过她的记忆在文字中复活,鲜活而生动。照相馆的马师傅,老中医赵医生,“叫客的”老朱丸,身带巫性的钳婆,送报纸的老张头……李俊玲以一个成长中女孩的眼光,透视人世间来来去去的人影,写出了一座城的时代面貌,一群人的丰富多姿,笔触真诚,文风朴素,温情而不失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
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的感受和思考、淳厚的亲情、深刻的生命体验,构成了这部散文集丰富的内容,为读者打开一扇扇独特的窗户。
散文需要哲理的思考,它可以让读者透过事物的表象,抵达作家心灵深处洞见她灵魂的波澜。充满智慧的思辨,可以为散文增加内涵和深度。《有龙在侧》中展示了边地小城丰富多姿的龙文化,也思考着人与自然与生俱有的默契,对民间智慧进行礼赞。《大地之子》写出了边境文化的独特,作家坦陈自己的美学理想,就是希望看到“人充满劳绩,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像虫鱼,像草木,始于大地,终究归于大地。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人在深秋》是一篇写意式的散文,看似散漫的思绪,却渗透了作家对人生世事的体悟。从北京到边城,从自己的童年到女儿的成长,作家用水墨画式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广袤的人世秋景图。而生活的琐碎与具体,则冲淡了自古以来秋的萧杀之气,染上了几许尘世的温馨。它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作家心灵世界的起伏跌宕。
如何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接通一个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这是近年来散文写作界许多作家正在思考的问题。李俊玲在《隐秘的世界》中,也在进行思考和探索。她的很多篇章中,都是以自己的主体视角切入对世界的观照,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布朗族相信万物有灵,民间信仰对李俊玲的写作有潜在的影响。她相信除了红尘人间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人间,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人间存在,比如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民间才会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说法。这大约就是她选择其中一篇书写鬼神的文章《隐秘的人间》作为这部散文集标题的理由。她还想通过书写,传达出一个写作者对文学的崇拜。她认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应该对身处的生存处境永怀好奇之心和敬畏之意,为乡土赋形,为众生代言。这样的写作理念决定了她的散文是有温度的写作,她是怀着对故土和亲人的热爱,去书写这块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的。
李俊玲的散文以细腻、深刻而见长,体现了一位女性作家对于人生世事的温馨的情怀。在她的散文中,边地生活的诸多物象携带着某种陌生气息进入读者的视野,既生动、新鲜,又充满阅读的吸引力。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适当的距离可以创造更好的阅读效果。散文中纷繁的物象,还体现了作家与大地的亲密关系。作为边地小城的施甸具有丰富广袤的自然特色,它已经与作家的生命形成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也是一名写作者可贵的地理和精神意义上的家园。通过诸多边地风情的生动描绘,李俊玲的散文逐步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原乡,呈现出独特的文学
风貌。
我写故我在,这是李俊玲散文所追求的目标。如她在散文中所言:“当我的脚再次踩到乡间松软的泥土时,仿若自己也是一株稻米,把生命中每个特别的瞬间都一一呈现给了这个纷繁的人间。”同时,她的散文也丰富了布朗族当代作家文学,为文坛奉献了一束美丽的花朵。祝愿她在散文的道路上一路畅行,佳作连连。
是为序。
(作者为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第一辑
故园风脉
小城人物
一
一个人在一座城待久了,便会成为这个地方的一株植物,知晓着这方土地的温度、湿度、酸碱度,以及风向、水位、日照时长,以自身特有的姿态融入在这些看似恒久却不断变幻的指数中,成为它细微而不易察觉的一部分。
说是一座城,勉强得很,城池城墙皆无,那些依附于一座城上该有的冷硬与守护毫无可寻,尊贵、抵御、拒之门外皆坍塌一片,“城”便丧失了历史应有的印证与筋脉。四通八达的包容,毫无戒备的进出,显得质朴而平民化。当然,这个像被弄丢在丛山之中的、面积不过十多平方公里的施甸坝子,本不应是版图之上被锁定的关隘与要道,仅仅是偏远地域人们休养生息的家园而已。远离富庶,自然远离纷争,天赐的便是坦然与随意,这座城的人也与他的附属物一般,与世无争,惯于接纳,善于付出,地域的闭塞使得人性相对简单纯善。
几百年前踏入这里都得需要有被遗弃的勇气,明代时的戍边者大多是不得志的军士与被贬的官员,流放在这些山高皇帝远、无价值可取的地域方能让当朝权贵安心。所以,我所住的地方只能称之为小县而已,这里曾经有一个傣语的称谓——“勐底坝”,意为温暖的地方,因傣族先祖白夷踏足这里的第一感受而得名。这里也因热气和水草丰茂而瘴气肆虐,“如要下坝,尸骨先放”说的就是曾有瘴气密布坝中,使得人们不敢轻易涉足,唯恐尸骨无存,下坝就意味着赴死,让人胆战。大自然总会用它的双手对入侵的人类制造追魂索命的魔障,我无法想象脚下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曾充斥着魔鬼般的凶险,是祖先们的梦魇之所,远古在我们眼中总是那么鬼魅,神秘,魔性十足。直到后来,植被的砍伐,自然的改变,人迹的踏入与开辟,才使得勐底坝有了人气。炊烟是号角,吹响了这块土地的所属权,最早的人类生存痕迹是八千年前,姚关智人头骨化石的发掘,把怒江边这块蛮荒之地的文明史推高了一个高度。这块土地,因早有人类活动而彰显出它的宜居性。的确,历经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依然觉得施甸坝子是如此地四季如春,舒适安逸,冬天没有凛冽之感,夏天也无酷热之苦,以至于来这里工作的北方朋友对季节有种不信任感,怀疑时间是凝固的,感知不到它们该有的更迭。我把自己半生的时光奢侈地抛在了这里,这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是多么巨大的消耗,而对于八千年来说,却是瞬息之事。我与这块土地上的那一茬又一茬的庄稼一样,抽穗,拔节,灌浆,随即成熟,低垂,
死去……
二
对它的描述,那些留存的遗迹,印刷的史志是冰冷和疏离的,资料在我心中仅仅是图片和数字而已,触及不到该有的质感和温度。我必须凭借着自身的感官,从一个孩童有记忆那天起,搜索与它依赖相处的点滴,掏空我的内心,描摹出它该有的姿态和容颜,这样安静地细细回想,我熟悉它竟胜于熟悉自己,熟知一座城,其实是熟知城里的那些
人和事。
这座小县城四十年前仅有一条街,街两边都是重要的店铺和单位,百货公司,公安局,供销社,理发室,商业局,印刷厂,大食堂……街道是这座城的生活命脉,民居如大树延伸出的枝丫般顺着这条命脉四散开来,生发出许多的巷道,马篮巷,米糠巷,菜秧巷,猪羊巷……名字里充溢着生活原汁的味道。我的家就在国营照相馆后面的一个大杂院子里,这个院子属于饮食服务公司的家属区,在街道的中心,地理位置较为显著。80年代初时,前来拍照的人总能排成长龙般的队伍。每到赶集天,照相馆就挤满了许多山上乡下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小马师傅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他是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那时,摄影师这个词似乎还没有流行,我们都称这些能操持相机的人为师傅。师傅,这个称呼不轻易落在一个人身上,得身怀普通人没有的技艺、富含技术的重量、引领时代滚动潮流的人才可担当。印刷厂、机械厂、制糖厂是师傅们云集的地方,其次便是理发馆、食堂、照相馆,各种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的场所。马师傅便是照相馆的一张招牌,进入照相馆的大厅,他的那张自拍特写就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用手拄着下巴,侧脸以45度角朝上作远眺之势。俊朗的眉宇之间透出非凡的自信,虽然是黑白照片,你仍能看得出那皮肤的润泽和衬衫的质地。高端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吸引着诸多女人发亮的眼光。他相片下的那块水泥地,总是大厅最干净的地方。
在镜头前,马师傅就是统帅,让你做什么动作,穿什么衣服,拿什么表情,他说了算。你唯一可以做主的就是选取背景图,可他也能按照你的衣服款式和色调告诉你,这个背景不搭,需要重换。我总记得他钻到摄影机的黑布里,调好焦距,又伸出头来,像一个将军,指着对方交代着:头左侧一点点,手自然下垂,对了,微微一笑,不要眨眼!语调霸气侧漏。有时遇到局促不安的顾客,怎么摆都显得动作僵硬,马师傅会走过去,做个示范,或者捏雕塑一般,给他们归置手脚,抬高下巴。腼腆的姑娘们总是推推搡搡,不愿意第一个去照相。这时,马师傅就说:赶快了,第一个站在我镜头前的人,我就好好地拍啊。有时插科打诨:好呢,笑起一点,想着这块表是你对象买的啊,看着镜头,想着你对象正向你走过来!哦,露出羞涩的微笑,对了!咔嚓一声,一道白光闪过,那些镜头下的姑娘们都笑成一片灿烂的山花。一块上海表,被不同的“主人”佩戴着,千篇一律地展现在搭于窗沿的手腕上,在无数的手腕穿梭和取戴下,它是最繁忙的道具。那时候,有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拥有一块手表,哪怕这样的场景是虚拟的,也能满足人们短暂的快乐。马师傅交代,挽起袖管,露出表来,还有微笑。每个人都是春风满面,一脸富足的表情,我不知道这样的场景有多少次在同样的背景下反复地上演、定格。在那个年代里,相同是大众一致的追求,相同的表情和姿势,相同的审美取向,相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被一一封存在那张张相同的黑白影像中。
马师傅有着一双白皙的手,纤细的手指注定是为艺术而生的。他总会在歇息时,到水管边用肥皂细心地清洗指缝,一洗就是半晌,仿佛手刚刚触碰了不洁之物,洗得血丝全无,苍白脱皮。院里的老奶奶们总说他有心魔,其实就是洁癖。他的房间我只进去过一次,有人等着照相,央我跑去喊他。房间在楼的尽头,门开后,一股雪花膏的香气迎面而来,涂着红色油漆的木地板干净得泛光刺目,让人晕眩。他的床头有一张女人的照片,细瞧,是山口百惠,美得不可方物。我匆匆一瞥,心里暗叹,这哪是男人的房间啊,和电影里那些水袖飞舞的小姐闺阁一样整洁。有一次,我无意中把那张女人的照片告诉隔壁阿婆,她为此担忧了好多天:唉,喜欢一个东洋女人,造孽啊。
马师傅是照相馆的一张招牌,他在,顾客蜂拥而至;他休息,顾客也莫名消失了。他的颜值和手艺让他成为这条街上的人物,只要提到照相,谁都会想起马师傅来。县里有位很严肃的领导,有一天去照相馆,点名要马师傅拍照,马师傅正准备洗手,同事催促,快点,别让领导久等。马师傅依然不紧不慢,按部就班,把他那双苍白的手反复揉搓、冲洗。同事催了三次,马师傅才洗完。照相时,领导的头老是偏朝一边,马师傅上前去,习惯地用手扳正,不想,这一幕让街上的王走嘴看到,一下子,传遍了大街小巷——马师傅真有胆,敢随便摆弄领导的脑袋。这话传的,像马师傅在领导头上拉屎一样。马师傅的“英名”一时激起千重浪,佩服的,戏谑的,打击的,惊讶的,中伤的,人们的情绪被这样的一句流言一时激荡。以至于单位领导找到马师傅特意交代,让他以后给领导照相时,不能动手动脚,以免让领导威信扫地。马师傅傲气一来,从此拒绝给领导拍照,这又掀起一轮风波,人们茶余饭后新增了一项谈资。而单位领导最终还是在他的拍照水平之下妥协了,谁让马师傅有能耐呢。岁月总会淘汰掉许多英雄好汉,随着相机的普及,摄影行业的日益兴起,拍照成为人人皆可为的一种技能。马师傅的手艺自然也被这样的时代大潮所冲淡和淹没。当我再见到他时,是在县城较为偏僻的一条巷道,一间逼仄的小铺面,门楣上那块陈旧的“老马相馆”的牌子被挤在各种广告牌间,落寞而固执。年过半百的他也失去了当年的风华,坐在店铺里低垂着头颅正打盹,瘦弱的脊背佝偻着,像一个无力的问号。
三
我小时候一旦病了,母亲总会背着我去赵医生家看病。赵医生是县里闻名的老中医,听说承袭祖上技艺,弟兄两个都靠着中医起家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赵医生是弟弟,我小时候感觉他已是老人家了,而我人到中年时,他依然是从前的模样:长长的眉毛下双眼慈善,嘴角似乎永远挂着微笑。他性格极好,说话温和,仿佛来自云端般轻软。遇到哭闹的孩子,他总是不急不躁地说等等吧,等孩子安抚好了再把脉看病。他从不穿白大褂,总是一身蓝布衣裳,手捧着一个茶罐。我看着他拿出一个小软枕,伸出那双清瘦而修长的手来,用三个指头轻轻按住我的手腕。指尖的温暖传递过来,让人心安。把脉时,他侧耳低垂着眉眼,沉寂如被某种力量钉住一般,似乎在倾听着来自患者体内的声音。把脉结束,他便细细端详着你的脸庞,片刻,让你张开嘴巴,伸舌观察。然后问话:大小便情况,睡眠如何。接着简单地总结病症,内寒外热引起的感冒啊,胃火太重导致的病症啊,气血两虚引发的疾病啊,等等。每次总结之后,他便用征询的口吻轻问:“开一小服中药先吃吃看?不好再来。”大多数人一服药以后基本不会再登门了。有些小毛病,他并不抓药,告诉你回去自己找点食材吃吃就行。鸡胗皮焙黄,捣碎后吞水服用治消化不良,甘蔗在炉火里烤熟吃治咳嗽,姜葱煮水喝祛风寒,香蕉烤脆了碾碎吞水治小儿腹泻……他总爱说,食疗胜于药疗,是药三
分毒。
看开处方时,我觉得自己不是来看病的,仿佛是来看表演的。准确地说,他不是写字,而是画字。只见他拿着笔,开始了龙飞凤舞的描绘。除了你的名字和年龄可辨析得出,其他的字是无法看懂的。他的笔犹如神器,落笔之后一气呵成,绕来勾去,跌宕起伏,高低错落,峰回路转,一个个字悄然游入纸间,那些字仿佛带着某种神力,让人看了就觉得莫测高深,也深信这样的药方一定会拔除病根。有人戏说,赵医生开方子就是画符,神药两医,病怎么可能不好呢。末了便是签名,他的签名简直就是一直在画圈,一圈,两圈,三圈,无数个圈中间嗖地穿过一条剑一样的直线,开方结束。这个过程很奇幻,让我感觉那是一种孩童才有的绘画方式,带着恣意的随性。没有人可以辨析出这些方子里到底写了哪些味药,字写得密密麻麻,而这些药藏得极深,极隐蔽。只有负责抓药的他的二姑娘看得懂,她接过父亲的单子,一言不发就去药房。一会儿工夫,一包梯形四角尖的纸包已递到眼前。赵医生家抓药一直用传统的粗纸和麻线。就是到了塑料袋横行的当下,也不丢失这个传统。小城里的人们喜欢这样的包装,亲切、古朴,带着老旧的信任。
赵医生的哥哥叫良渚,两兄弟看病各有千秋。他们的诊所紧挨着,在一条街道。要论医术谁最高明,还真不好说。看病也讲究缘法,在赵医生这里一次看好的,到了他哥哥那里也许两次也不行。而在哥哥那里的病人也认准了门道似的,不会轻易过去找赵医生看。大家心照不宣,各入各的门,各看各的病。我少时和良渚医生的外孙女是同学,有一次去她家做作业,楼上就是安放药材的地方,那些木屑和杂草一样的草药大袋小包,堆满了房间。我们两个小姑娘就在木楼上写字,一股股中药的气息弥散在四周,闻着闻着竟然觉得异常舒心,脑袋空前地清新。一道道平时解起来费力的数学题,鬼使神差地被我轻轻松松解答出来。那些药味难道也有通窍之神力?良渚医生笑了:中药就是辅养以通,通则畅,畅无病也,很多中药有提神开窍之能。我懵懂点头,却深深记住了这几句话。看着进进出出看病抓药的人,我坚信那些杂物一样的草药熬煮出的浓汤会像血液一般流入他们的体内,将病痛清扫干净。
县城在几十年的光景里拓展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这条老街的这两间中药诊所,成为一辈辈人不朽的记忆活物。女儿只要有任何不适,我也会像当年母亲带着我一般,领着她去找赵医生看病。女儿趴在赵医生看诊的桌前,睁大着眼睛,专注地看他开处方,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有时女儿偷偷伏在我耳边说:妈妈,这个医生爷爷在写外星文。我听了哈哈大笑: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觉得呢,就是这些奇怪的外星文医好了多少人的病啊。每次女儿发烧,只要一服药便痊愈,我们母女俩都与赵医生有着奇妙的医缘。那间小小的诊所就坐落在老旧的街边,却无人知道,它其实一直安放在我生命里那个充满信赖而安全的角落,让我有所依托。女儿大了,外出求学,我去诊所的次数也少了。赵医生已步入耄耋,还在为患者看病。他的动作迟缓了许多,而语调依然那么地轻软。有一次出差归来路过诊所,店门紧闭,才知道赵医生已经作古。他女儿说,去的那天早上,老爷子还给病人看诊,饭后喝了一口茶,靠着椅子就驾鹤西去了,安详得如睡了一般。兄弟俩一前一后相继去世,哥哥享年九十九,弟弟享年九十七。良渚医生的诊所还在,由他的儿子继续坐诊,而赵医生的诊所已关闭。没过多久,铺子变成了“绝味鸭脖”。每次路过,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朝铺子多看一眼,老楼仍在,人间流徙,在往来的人群中,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将目光和思绪在此驻留呢?
四
“来来来!这里有三个位子,远客先坐,寨邻朝后……好喽,人齐上菜!麻利点!烟酒跟上!”这一声近乎爆破的招呼,带着金属的质感,那嗓门一开,就像刚发动的拖拉机一样呼啸倾轧,让人退避。出口之声来自负责叫客的“老朱丸”,不知这名是不是他的绰号。只要有人家办客,他就是主角,张罗宴席,安排座次,迎来送往,全凭一张嘴。酒席办得要热闹,全靠叫客叫得好。叫客是施甸的一种习俗,谁家要办宴席,无论婚丧,首先都得请一个叫客人。他得熟知礼俗,得弄清主人家的三亲六戚,得会察言观色,注重细节,调度有方,最关键的是得有一副好嗓子。这些特质,老朱丸都具备了,他叫客时,肥厚脸颊的肉随着声线上扬而抖动,有时,强大的气门喷涌出骤雨般的唾沫星子,而这些不雅都淹没不了他叫客的才华。他提着酒壶穿梭于席间,目的是不让一个座位有空缺,不让一桌的酒水斟不满。让客人吃好喝好的同时让主人家少浪费,是叫客人的本分,他恪守本分。
每到一桌前,他三言两语就会撩起一浪又一浪的笑声。他提着酒壶,对着有些拘谨的男人们开嗓:“酒水粮食酿,三年吃味香,今天你不尝,就是怕婆娘!”“吃肉不放盐,吃着也不甜,做客不沽酒,白来世上走!”叫客时,他的声调爬坡下坎一般顿挫:“来的远客——贵客——稀客——座上客,吃好喝好耍好啦——不要怕主人家饭少,谷子堆得有四大山高——不要怕主人家肉不够,肥猪比虼蚤还要多——”“见官罢(罢,不要的意思)在前,吃饭罢在后,脸皮厚厚,吃得够够。三步并两步,动作不快,洗碗水招待!”他脱口而出的戏谑,让喜宴的热闹沸腾了好几度。有老朱丸叫客的宴席,才让人欢乐。遇到丧事,他也能将悲痛化解掉那么一两分。“穿破才是衣,到老才是事,世上多少人,活得过百岁。”“三更鼓四更锣,人人迟早见阎罗,不要气不要哭,黄泉路上无老少。”在农村,这样的“出口成章”让大家都觉得他像个通晓俗世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他只小学毕业。
做客场上,他是众目追随的至尊宝,而平时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邋遢懒汉。他家的田地四季荒芜,院落杂草横生,他讨生活的方式仅仅是靠养狗卖猫而已,还有叫客时主人家给的几文钱和少量的物资,日子过得滴汤掉水。媳妇早年不堪忍受他的穷困潦倒而离婚了,耍了多年光棍的老朱丸喜欢四处游荡,走东家串西家瞎聊,身后如影随形的是一条脏兮兮的黄狗。小县里的新闻总是第一时间从他的口上揭开,经过他的那么一加工,再加上表情和声调的处理,哪怕不起眼的一件事情都让听者咋舌。他超强的编撰能力加上放肆的渲染,让人在惊诧之余加重了质疑,知晓底细的人都说,老朱丸一开口,牛统统都被吹上天了。瞎混和练嘴,成了他的生活日常,哪里有酒哪里醉,哪里有铺哪里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浪荡而恣意,也被周围那些务实而本分的庄稼汉所鄙夷。农忙时,几乎无人家办客事,老朱丸如同被闲置的器具一般,沉寂下来,而他不甘于这样的冷遇,只要有人在村前休闲,他便跻身其中开始神侃。这时通常被那些轻视他的农人戏耍:“你那么能说会道,骗个女人焐焐脚嘛!”“他脚臭,哪个婆娘敢挨着!”“头发可以搭雀窝了吧,老朱丸。”“听说你又去隔壁寨子吹死了几头老母牛了?”……在大家的言语漩涡中,他岿然不动,嬉皮笑脸地开始了粗俗的回击:“你们这些狗日的,要婆娘搞么?像你们一样受窝囊气啊!老子一个人,快活似神仙!你瞧瞧你,花几块钱都要看婆娘的脸色,老脸都丢尽了。还有你这烂杂种,老鸹不要说猪黑,懊糟堆起一墙厚,还有脸说我。老子吹死牛不算,等哪天去你家,吹死你养的那群老母猪才实在!”话音未落,他扣起脚趾,作出鄙视的姿态。唇枪舌剑下,往往是他一马当先,杀得众人片甲不留,老朱丸沾沾自喜,对大家的故意消遣他全然不在乎,此刻他又成了焦点人物,仿佛自己又置身在热闹的办客场中,是那“战场”上调遣千军的大将。
直到有一天,他酒后摔跤引发脑出血,也跌断了腿,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有人说他瘫痪了,说话也不利索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每到冬腊月,小城里就又迎来了嫁娶的高峰期,客事依然一拨接一拨地举办,叫客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大家觉得宴席上似乎寡味了许多,而谁也说不清究竟少了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