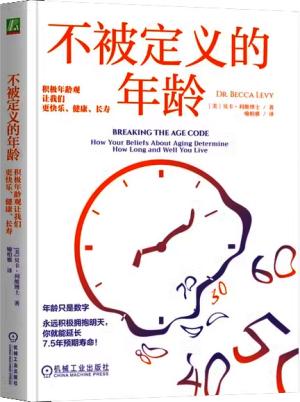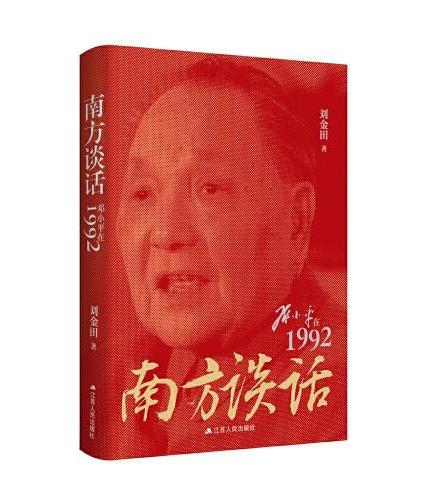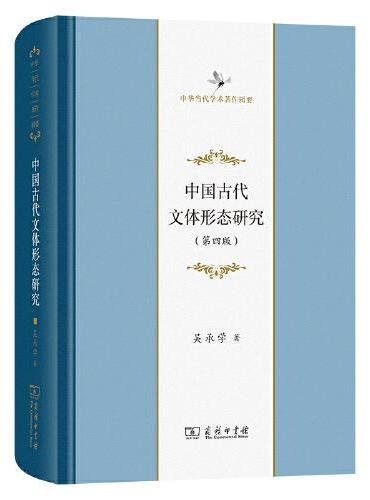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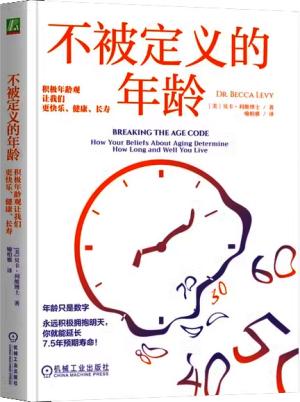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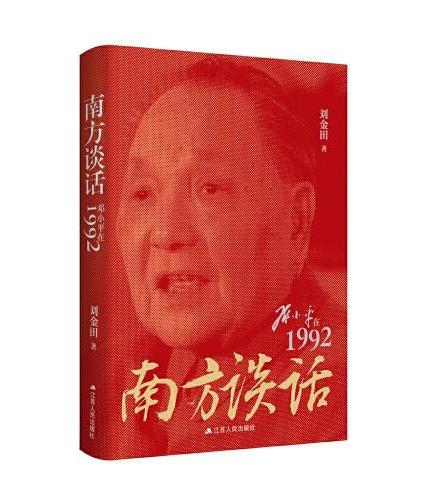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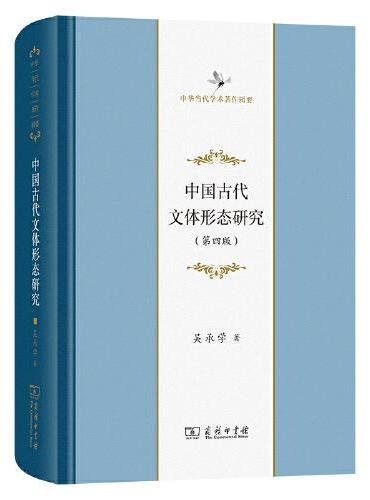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NT$
765.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NT$
403.0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NT$
286.0

《
台风天(大吴作品,每一种生活都有被看见的意义)
》
售價:NT$
245.0
|
| 編輯推薦: |
★时代的沙粒,历史的莽原——知名历史学者马勇再次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诉说中国近代史学历次转型的来龙去脉!
明夷:意为不论情况多么艰难,我们还是应当坚持下去,才能走向光明的前途。本书以大开大合的学术姿态,祛魅、存真,重新构建近代历史历次转型的整体脉络。
★郭世佑、王奇生、余世存、张宏杰——推荐!
★致敬前辈,辨章学术,反本开新。
★历史体系与逻辑体系的完美交融,以力透纸背的书写,实践新史学宗旨。
★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断代体、大事记、通志、图表、点评、史论……但凡能想到的体例无一不被发明。幽微形式下,史学家如何改造旧史,编订新史?
★追述旧史研究的窠臼,探明外部史学的影响。揭示甲午战后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变动。
★因循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邓实、王国维的脚步,理解新旧时代转换之际学术进步的可能、力度与局限。
★求新求变,研究互联网时代的历史研究与书写,探讨大众历史写作的意义与方法。
★重建“五四”历史叙事,阐明史学本质和史家责任。
|
| 內容簡介: |
本书为马勇老师梳理史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文章的集合,分为“老辈史家的经验”和“我的史学研究”两大部分。“老辈史家的经验”,介绍章太炎、蒋廷黻、张荫麟、范文澜、胡绳等前辈从事史学研究的经历,他们进行史学研究时受到的一般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秉持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等,分析《訄书》《清代学术概论》等史学名著的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我的史学研究”则介绍了马勇老师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和心得,可供相关专业的读者学习和借鉴。
本书以大开大合的学术姿态,祛魅、存真,重新构建了近代历史历次转型的整体脉络。
|
| 關於作者: |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以及《激荡:晚清二十年》《回望:近代一百年》《中国儒学三千年》《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华文明通史》等。
|
| 目錄:
|
老辈史家的经验
老辈史家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调整 / 3
《訄书》与中国史学转型 / 45
《清代学术概论》说了什么? / 53
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叙事 / 62
张荫麟与中国历史重建 / 71
吕思勉与中国通史研究与写作 / 80
范文澜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构建 / 93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 102
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 110
唐德刚先生逝世十年祭 / 118
我的史学研究
六十年近现代中国人物研究 / 131
“历史三调”——甲午战争百年研究史的简述与思考 / 166
所谓新旧——重建“五四”历史叙事 / 178
新文化史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 / 217
史学本质与史家责任 / 229
学科渗透与历史学本质 / 234
作为艺术的历史学 / 244
大众历史写作的意义与方法 / 249
互联网时代的历史研究与书写 / 260
马勇书房,保持精神与文化的流动 / 269
|
| 內容試閱:
|
《訄书》与中国史学转型
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是学术成就斐然的大家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和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刘知幾、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
章炳麟生于1869 年,卒于1936 年,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余杭区)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本名顾绛),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在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整天忙于科举考试的同龄人,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
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二十八岁的章炳麟,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乃至其他时代学者都很难做到的。
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见识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
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借着酒劲儿发生肢体冲突。
《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传播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了维新时代的思想家和新派学者。
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通友好相处,只有几个高度宽容的朋友能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足以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其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彼此相安无事。
章炳麟只是在行为上显得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毫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处发表,在它们的基础上后来编成《訄书》。
《訄书》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集子的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 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 年前将《訄书》改编成《检论》,经过了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 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 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时,中间所收篇目,乃至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
《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1895 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到1898 年的政治变革时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
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舆论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
关于清廷的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
马勇书房,保持精神与文化的流动
一、我的阅读启蒙从地震棚开始
绿茶:您的书房是怎么样一个成长过程?
马勇:我是农村出来的,父亲读过私塾,对孩子读书还是很支持的,我们小时候,如果你愿意读书,就会给你创造条件。印象中,20 世纪60 年代,邢台地震,我们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个地震棚,在里面读书,我的阅读启蒙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
但那时我们能读到的东西很少,印象中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巴金的作品。大概在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我到新华书店买过一套鲁迅的单行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白皮本,后来我把它们装订成册了。
1986 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来的时候,我带的全部资产就是十二个纸箱的书。我为什么能够在七年读书期间积累那么多书呢?因为我是带工资上学。像有一套《中华大词典》,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买的,当时大概就三十来块钱。
刚来北京,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东四头条社科院宿舍院内,给我的是一个二十平方米的里外间,根本谈不上有书房。但我们宿舍离单位近,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2005 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前,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是个内外间,但因为书增长得太快,很快被我一个人占用了。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十点多才从办公室出来回家,第二天送完孩子又去办公室。2005 年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
2005 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后,有了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书房,但实际上家里每个房间都是书,楼下还有一个地下室也是书,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册。去年退休前,又把办公室的书都搬回到家里来。
二、从读书开始,专心读了十几年
绿茶:除了做书房的办公室,你们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吧。
马勇:对。我1986 年毕业,到1991 年才发第一篇文章。我的老师朱维铮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发文章,要多读书。所以,那些年我每天就是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再借再还。当时做的第一个课题是梁漱溟研究,我做了很多前人没做过的材料挖掘工作。后续又做了几个近代人物研究,比如蒋梦麟,在我做之前,内地找不到一本关于蒋梦麟的书,我从香港、台湾等地方收集、挖掘了很多材料。
我是学古代思想史的,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当时的研究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刚来,老先生不让我们写东西,也没那么大压力,就静静地读了五六年书,算上本科,专心读了十几年书。
等到后来开始写东西时,脑子里对历史有无数种自由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儿,随时可以调动这些资源。我写东西面比较广,得益于当年阅读比较系统,可以从古至今打通。
注:2000 年时,近代史所承担了一个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的课题。之前马勇发表过关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文章,所长就让他负责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的写作。2013 年,由近代史所中青年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
三、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
绿茶:在书房和图书馆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哪些书要收在家中,哪些去图书馆阅读?
马勇:我的书基本是一个流动状态,我正在做的题目,要用的书,都在我的书房,暂时不用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参考和补充其他资料,基本是去图书馆,但很多时候,做研究需要借助更多的地方。比如我当时做蒋梦麟的研究,内地各图书馆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什么材料,就需要去台湾、香港等地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而我的书房本身,我保持它是流动的状态,随着自己的研究变化而变化。我的书房是用的书房,而不是藏的书房,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是为藏而买的。
造成我书多的原因是,我原来做古代史,所以积累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书,大学毕业后做近代史,又大量购买近代史方面的书。加之三十多年来,我的书都跟着题目走,为不同的题目又增加了不同的书。
比如,刘大年找我合作做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因此就增加了大量抗战史的书。后来做严复的研究,关于严复的书我基本上都收齐了,还去沈阳看严复的资料、手稿等。之后又做章太炎的研究,用三年的时间读章太炎的资料,《章太炎全集》最后就是我参与一起合拢的。
还有由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研究”,这项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我参与其中“中国文明的研究”,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围绕这个主题,又扩充出很多书。这些年来的课题经费,基本上都换成书了。
到目前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选的,还有几本论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20 世纪90 年代初,庞朴主持“中国儒学”项目时,曾约我参与,第一卷《儒学简史》就是我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