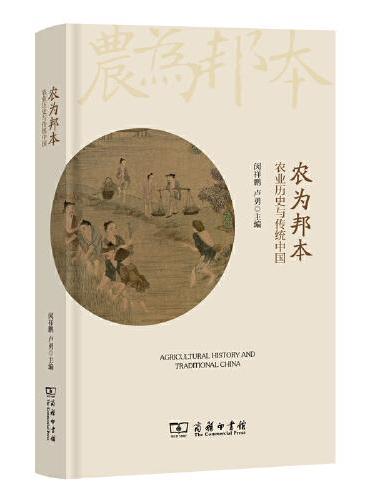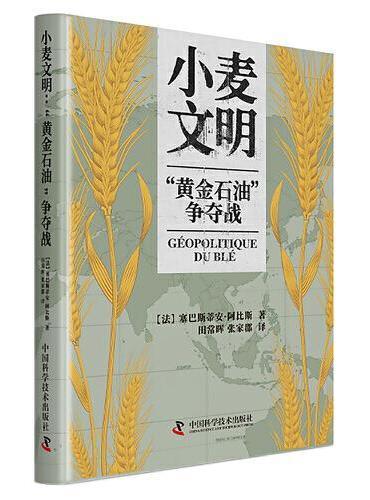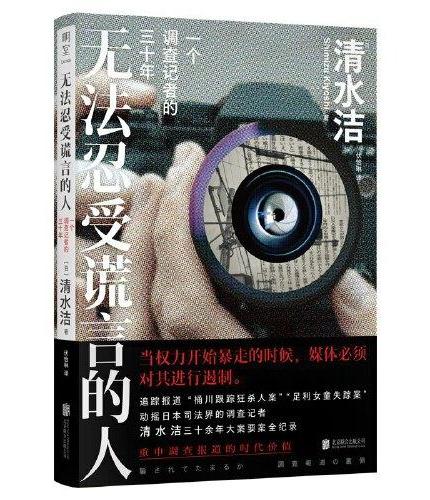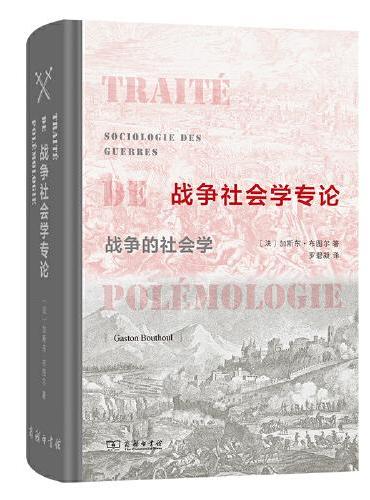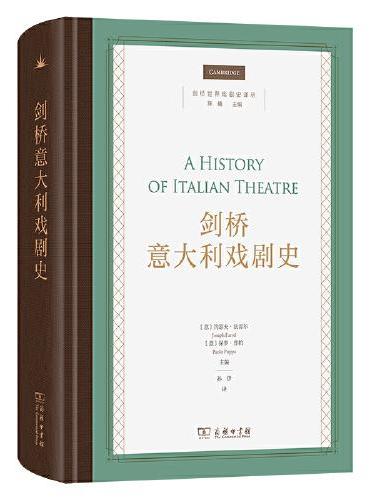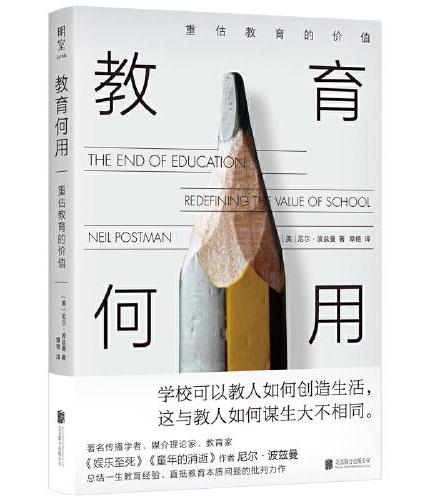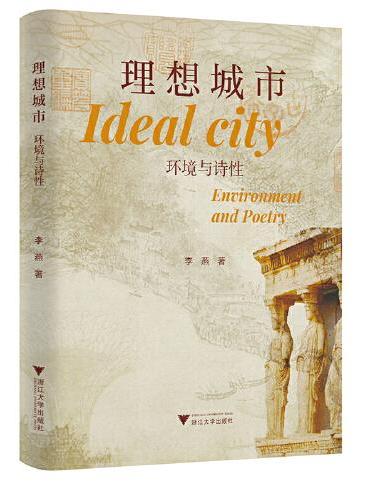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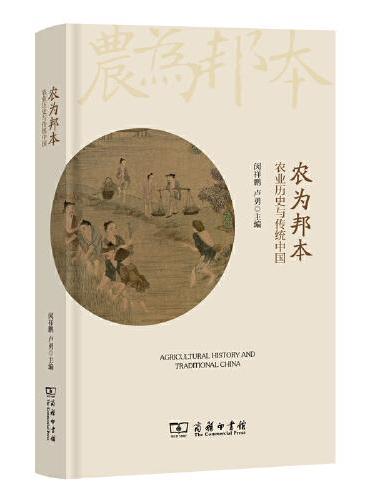
《
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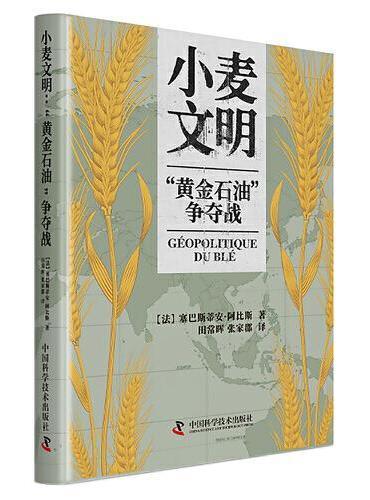
《
小麦文明:“黄金石油”争夺战
》
售價:NT$
445.0

《
悬壶杂记全集:老中医多年临证经验总结(套装3册) 中医医案诊疗思路和处方药应用
》
售價:NT$
6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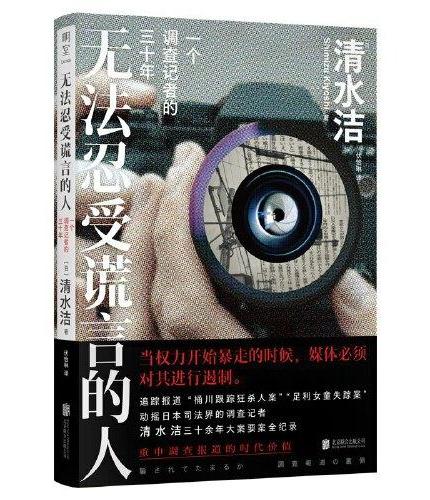
《
无法忍受谎言的人:一个调查记者的三十年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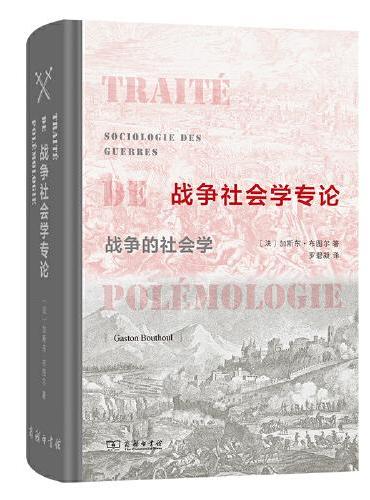
《
战争社会学专论
》
售價:NT$
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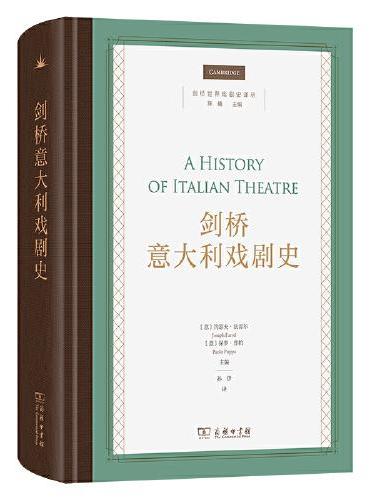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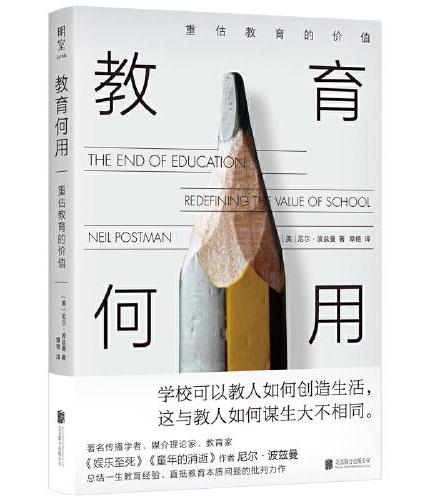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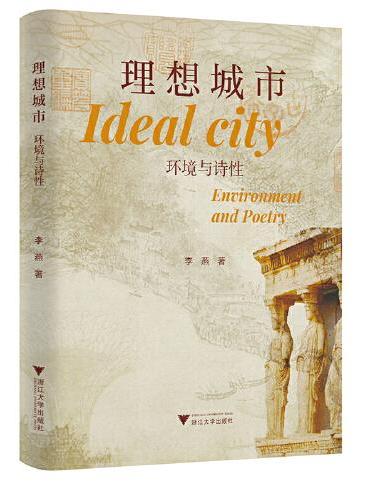
《
理想城市:环境与诗性
》
售價:NT$
390.0
|
| 編輯推薦: |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文学巨匠福楼拜代表作,被许多作家视作“写作教科书” ,“新艺术的法典”,一部“完美的小说”。
★《包法利夫人》以优美译笔展现思想精华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标杆,启发智慧的同时,带给读者美的享受。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包法利夫人, 19世纪文坛不可绕过的一部小说, 一本值得反复诵读的文学经典。
★雨果盛赞“一部真正的杰作”,左拉眼中“确而无疑的典范”,米兰?昆德拉认为它让小说赶上了诗歌。
★《包法利夫人》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一个多世纪,更是一本对人生有重大启发的经典。
|
| 內容簡介: |
小说《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1821—1880)的代表作,初次发表于1856年。
爱玛是农庄主的女儿,在修道院受过教育,也偷偷看过不少浪漫小说。她怀着对爱情的美妙憧憬结婚,成为包法利夫人。嫁给乡镇医生夏尔?包法利以后,爱玛的幻想很快成为泡影,因为丈夫才不出众,思想平庸。爱玛偶然参加了一个贵族舞会,便对上流社会的奢华羡慕不已,强烈的反差使她觉得现实生活十分无聊。夏尔为了满足爱玛,迁居荣镇行医,与药剂师奥麦为邻。爱玛在荣镇遇到青年书记员莱昂,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莱昂为了摆脱精神苦闷,决定去巴黎深造。百无聊赖的爱玛又认识了附近的农庄主鲁道夫。在情场老手鲁道夫的勾引下,爱玛成了他的情妇,她向鲁道夫提出私奔要求,但鲁道夫由热而冷,终于弃她而去。爱玛为此大病一场。夏尔为让爱玛散心,陪她进城看戏,偶遇爱玛一度心动的莱昂。两人旧情复燃,爱玛每星期都要借故进城同莱昂幽会。爱玛为偷情而挥霍家产,并常常向奸商勒赫赊账举债,勒赫捏住爱玛的把柄,逼债未果,便通过法院张贴布告,宣布爱玛再不偿还,就要扣押其财产。陷入困境的爱玛四处求助,包括两个情人,岂料他们无不推诿搪塞。爱玛走投无路,吞服从药店弄到的砒霜,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小说通过爱玛的婚姻—堕落—死亡的悲剧经历,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19世纪法国的外省风俗。它熄灭了让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环,令人看见底下黯然的真相。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和残酷的现实。严酷的写实服从现实,它并不创造升华,也不将一切美化成浪漫诗歌,它将现实的精髓搬上纸面,铺排得和谐有序,在此和谐之中,生活的本来面目便裸露出来。比现实中的更加严密、结实和触人心弦。它是一部艺术上完美、精致的法语典范作品,是继《红与黑》《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杰作。
|
| 關於作者: |
\福楼拜(1821—1880年),生于法国鲁昂,终生从事文学创作。被誉为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20世纪法国“新小说”派。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的老师。作者生前则“拒绝一切派别”。主要著作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等。
译者简介:
陈艳,1978年生,1996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法语语言文学专业,2003年获该校法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赴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二大学求学,2006年获该校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3年至2014年,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意语系。曾出版译著《社会学有什么用?》《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等
|
| 目錄:
|
章 002
第二章 012
第三章 020
第四章 026
第五章 032
第六章 037
第七章 043
第八章 049
第九章 059
第二部
章 072
第二章 082
第三章 089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05
第六章 114
第七章 128
第八章 137
第九章 160
第十章 172
第十一章 181
第十二章 194
第十三章 208
第十四章 219
第十五章 230
第三部
章 240
第二章 256
第三章 266
第四章 269
第五章 273
第六章 291
第七章 309
第八章 323
第九章 343
第十章 352
第十一章 358
作者年表 369
|
| 內容試閱:
|
我们正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个新生和一个校工。新生没有穿校服,校工搬着一张大课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都立刻醒了过来,一个个站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示意我们坐下,然后对班主任低声说道:
“罗杰先生,我把这位学生交托给你,他先跟着五年级上课。如果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合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新生坐在门后边的墙角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这是个小乡巴佬,十五岁上下,个头比我们都高。他前额的头发剪得很齐,就像乡村教堂的歌童,看上去又懂事,又十分拘谨。他的肩膀并不宽,但却被黑扣绿呢上衣箍得很紧。从袖口能看到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背带裤高高地吊在身上,露出了穿着蓝色袜子的小腿。皮鞋没有擦亮,鞋底打了钉子,看上去很结实。
我们开始背书。他竖起耳朵来听,就像在教堂听布道一样专心,身子坐得笔直,既不敢跷腿,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课桌上。两点钟的下课钟敲响的时候,还是在班主任的提醒下,他才跟我们一起排队走了出去。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就是进教室的时候会把帽子扔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碍事;一进教室门槛就把帽子往凳子下面投去,帽子得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为一种规矩了。
但是新来的这位也不知道他是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做法,还是不敢跟我们一样做,总之,直到祷告做完,他还一直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属于混搭风格,兼有毡帽、军帽、圆顶礼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质睡帽的风格,非常寒碜。它那副不声不响的丑样子,就像傻子的表情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帽壳下部被三道环形的粗鲸骨撑得像鸡蛋一样圆鼓鼓的;中间一层由红带子、菱形丝绒和兔毛混编在一起形成;帽顶装饰着复杂的刺绣,呈不规则多面体状,像个歪歪扭扭的纸袋子扣在上面;帽顶垂下一根又细又长的绳子,绳子末端挂着流苏状的帽穗,由金色的丝线编织而成。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闪放光呢。
老师说:“你站起来。”
他站了起来,帽子就掉在了地上。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拿帽子。旁边的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弯腰捡了一次。
老师打趣说:“把你的头盔搁到一边吧。”
全班同学又是一阵爆笑。可怜的新生手足无措,不知道是该把帽子拿在手里,还是放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他终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了膝盖上。
老师又说道:“起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口里像含了萝卜似地说了个名字,大家都没听清楚。
老师说:“再说一遍!”
他还是说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名字,但是声音完全淹没在众人的哄笑里。
老师喊:“大声点!大声点!”
新生下足决心,张大嘴,像呼救似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叫道:“夏包法利。”
学生们又开始闹腾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有的声音尖得刺耳,有的像狼嚎,有的像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夏包法利,夏包法利。”喧嚣像零散的音符逐渐减弱,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突然又从某排学生中间传来压低的笑声,就像一串没有燃尽的鞭炮。
老师以罚写作业相威胁,课堂总算逐渐恢复了秩序。老师让新生重复、拼读、再重复,总算听清楚了是“夏尔?包法利”。然后老师就让这个可怜的家伙坐到讲台下边的懒人专座上去。新生准备过去,却又站住了。
老师问他:“你在找什么?”
他不安地四下看看,怯生生地说:“我的帽……”
全班哄然大笑。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愤怒的叫喊就像海神镇压风浪时喊出的Quos ego 一样,遏制住了新一轮的喧闹。“安静!”老师一边怒吼着,一边从帽子里掏出手绢擦着额头的汗水。“至于你,新来的,你得写二十遍ridiculus sum 的变位法。”接着,老师稍微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你会找到你的帽子的,它不会被人偷走。”
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到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女子身穿蓝色的美利奴羊毛长裙,上面镶着三道褶边。她领包法利进了厨房。火烧得很旺。大大小小的罐子里饭菜正在沸腾。炉灶内壁烘着几件湿衣服。铲锹、火钳、风箱口都是大个儿的,像抛光的钢铁一样锃亮。靠墙放着成套的厨具,反射着灶膛的火光,还有从玻璃窗透进来的曙光。
夏尔上到二楼看病人。病人躺在床上,蒙着好几层毯子,出了很多汗,棉布睡帽远远地扔在一边。这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白皮肤,蓝眼睛,前额秃顶,戴着耳环。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大瓶烧酒,他不时喝上一口,振奋一下精神。但是他一看到医生,立马就泄劲了,原本骂骂咧咧了一夜,立时就只能有气无力地哼哼唧唧起来。
骨折的情况非常简单。夏尔不敢指望还能有比这更好治的。他回想着当年老师在病床前的样子,说着各种好话宽慰病人。这样的安抚对于外科治疗来说就跟给手术刀上抹油一样重要。病人需要上夹板。仆人从车棚里找来一捆木条。夏尔挑了一根,砍成几小块,用碎玻璃磨光。女佣撕着被单准备绷带。爱玛小姐准备缝几个小靠垫。她找针线盒的时间长了点儿,她的父亲就不耐烦了,她也不回嘴;但是,她缝靠垫的时候一不小心扎到了手指,就把手指放到嘴里,嘬了两口。
她的指甲很白,白得令夏尔惊讶;指甲光亮,指尖细小,形状像杏仁,看起来比迪耶普的象牙还要光洁。但是她的手并不算美,也许还不够白,指节瘦得有点露骨;手显得太长,轮廓不够柔和。她的眼睛很美,虽然是棕色的,但在浓密睫毛的映衬下,显得很黑。她看人时很大方,目光既天真又大胆。
伤腿一包扎好,鲁奥先生就邀请医生吃点东西再走。
夏尔来到楼下的房间。一张小饭桌上面摆着两套餐具和几个银质的杯子。饭桌摆在床头。一张华盖大床,挂着印花帐子。窗户对面是高高的橡木衣柜,散发出鸢尾草和湿布的气味。墙角的地上有几袋小麦,靠墙竖着,排得很整齐。这是谷仓装满后多出来的。谷仓就在隔壁,上三级台阶就到。硝石墙面的绿漆已经开始剥落,墙中央用钉子挂着一幅智慧女神的头像,是铅笔画的,裱着镀金的画框,头像的下方用哥特式字体写着“献给我亲爱的爸爸”。
两个人先是谈病人,然后谈天气、谈严寒和夜里在田野奔跑的狼群。鲁奥小姐在乡下并不开心,尤其是现在,整个农场几乎都得靠她一个人来管。屋子有点冷,鲁奥小姐一边吃一边打着寒噤。她的嘴唇很厚,她不说话的时候习惯咬着嘴唇。
她白色的衣领向下翻着,露出了脖颈。头发乌黑油亮,顺着纤细的发线从中间往两边分,随着头顶的轮廓呈现出自然的曲线,在脑后梳成一个大大的发髻,略微露出耳朵尖,鬓角的发丝像波浪一样卷曲。这种发式夏尔这个乡下医生还是平生头一回见到。她的两颊粉红,像男人一样在上衣的两个纽扣中间挂了一副玳瑁眼镜。
夏尔上楼跟鲁奥老爹告辞,然后回到一楼的房间,看到爱玛小姐站在窗前,额头贴着窗玻璃,正往花园里看:花园里的豆角架被风给吹倒了。她转过身,问道:“您找什么东西吗?”
夏尔回答:“打扰小姐了,我找马鞭。”
夏尔开始在床上,门背后,椅子底下寻找。不料马鞭却掉在小麦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爱玛小姐眼快,就俯在口袋上够马鞭。夏尔出于礼节,也赶紧跑过去,伸长胳膊去够。他感觉到自己的胸膛蹭到了她伏在口袋上的背脊。小姐直起身来,涨红了脸,回头看了他一眼,把牛筋鞭子递给他。
夏尔原本答应病人三天后来复诊。事实上他第二天就又来了,然后除了每周两次的定期复诊之外,他还时不时地“顺道”上门探访。
病人情况很好,按部就班地康复着。四十六天之后,人们就看到鲁奥老爹一个人在屋子里试着自己走路。大家都认为包法利先生是个很有本领的人。鲁奥老爹说,就算是伊夫托甚至是鲁昂的一流名医都不会看得比他好。
至于夏尔,他并不深想自己为什么这么乐意去贝尔托。当脑子里掠过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要不就把自己的热情归结为伤情的严重性,要不就认为自己是为了多挣诊金。难道仅仅这些原因就能使去贝尔托成为他贫乏生活中的乐趣吗?那些日子,他一大早就起床,一路快马加鞭,到了地点后,先下马在草地上擦干净靴子,戴上黑手套,然后再进去。他抵达院子,用肩膀顶开栅栏门,看到公鸡在墙上打鸣,小伙计们出来迎接,这一切都令他感到喜悦。他喜欢这里的粮仓和马厩。他喜欢鲁奥老爹拍着他的手,叫他救命恩人。他喜欢看到爱玛小姐穿着小巧玲珑的木底鞋走在厨房洗过的石板地上,高高的后跟把她的身材托得颀长。她走在他前面,鞋底急促地起落着,牵动皮质的鞋帮,发出吱吱的响声。
她每次都会把他送到级台阶,一直待在那里等伙计们牵马过来。告别之后,他们不再说话;四面都是风,吹乱了她颈后新生的细发,吹起了腰后围裙的带子,像飘带一样卷着。有一次赶上化冻,院子里的树皮渗着水,屋檐的雪正在融化。她走到门槛,又回屋找出自己的阳伞撑开了。阳伞是绸缎面的,颜色像鸽子的脖颈,蓝灰色夹杂着紫色,阳光穿透伞布,在她白皙的脸庞上闪烁。空气带着暖意,她在伞下微笑,雪水滴滴答答地落在紧绷的伞面上。
夏尔这么频繁地往贝尔托跑。起初,他的太太爱洛伊丝少不了要问病人的情况,甚至还在账本里挑选了一页空白纸专门用来记鲁奥先生的账。但是后来她知道了鲁奥先生有个女儿,她就四方打探。她打听到鲁奥小姐是在乌尔苏拉会 的修道院里长大的,据说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会跳舞,懂地理,会素描、刺绣和弹钢琴。她受不了了!
她琢磨着:难怪他每次去贝尔托的时候都容光焕发,连下雨天都要穿上新背心!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
她出于本能恨上了这个女人。起初,她话里话外地试探夏尔,夏尔听不懂;后来,她指桑骂槐,夏尔怕她吵闹,不想接茬,只当没听见;后,她索性把话挑明了,问得夏尔无言以对:既然鲁奥先生腿已经好了,而且还没付钱,他为什么还要去贝尔托?啊!是因为那边有个人能陪他聊天,那个人能说会道,还是个才女。他就爱这样的!他需要的是城里的小姐!
她接着唠叨:“鲁奥老头的姑娘也算是城里的小姐?去她的吧!她的爷爷就是个放羊的,还有个亲戚跟人打架差点吃了官司。她至于摆出一副城里大小姐的派头吗?星期天去教堂还穿着丝绸的裙子,把自己当成伯爵夫人呢!那个可怜的老头,去年要不是收了油菜,连账都还不上呢!”
夏尔实在是被她吵得烦,就不去贝尔托了。爱洛伊丝还逼他把手放在弥撒书上发誓,以后决不再去。她哭着亲他,用疯狂的爱情肆虐他。夏尔顺从了。可是行动上虽然屈从了,内心却在抗议,想去看鲁奥小姐。他心里宽慰自己,太太虽然能禁止自己去看她,但是却禁止不了自己爱她。寡妇消瘦了,牙显得更长了。她一年到头都披着一件黑色的披肩,披肩的角一直垂到肩胛骨。裙子套在干瘦的身子上就像剑鞘似的;裙子太短,露着脚踝,宽大的皮鞋还有灰色袜子上交叉系着鞋带。
夏尔的母亲时不时地来看他们;但是过不了几天,就像被媳妇传染了似的,也变得尖刻起来。婆媳两张刀子嘴,你一言我一语,比着挑夏尔的毛病。他为什么吃得这么多?干嘛谁上门都要拿酒招待?怎么死活也不肯穿法兰绒的衣服?
开春的时候,安古镇的一个公证人,也就是迪比克寡妇财产的托管人,卷走了事务所的所有钱财乘船逃跑了。爱洛伊丝除了价值六千法郎的船股之外,还有圣-弗朗索瓦街上的一处房产。不过,这份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产业,也就有一点家具和几件衣服搬到了包法利夫妇家中,其余的可没人见过。事情必须要弄清楚。原来,迪耶普的房子早就什么都不剩了,连柱子都被抵押出去了。至于她在公证人那里存放了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而且所谓的船股也决计超不过一千埃居 。这样看来,这个女人先前撒谎了!老包法利先生一气之下,把一张椅子都摔坏了,他怪老婆害了儿子,给儿子配了这么一匹瘦马,马鞍都没有马皮值钱。老夫妻俩来到托特兴师问罪,跟儿媳吵了几架。爱洛伊丝哭着扑到夏尔怀里,求他在公婆面前帮自己说话。夏尔想为她辩解几句,结果老两口一怒之下走了。
但是爱洛伊丝的病根已经种下了。一个星期之后,她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时候,吐了口血。第二天,夏尔正转身去拉上窗帘,她说了句:“啊!我的上帝!”叹了口气,就昏了过去。她死了!真是意外!
下葬之后,夏尔回到家里。楼下没人。他来到楼上卧室里,看到她的裙子还挂在床头;夏尔在书桌前双手抱头一直坐到晚上,沉浸在痛苦的思绪当中。毕竟,她曾经爱过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