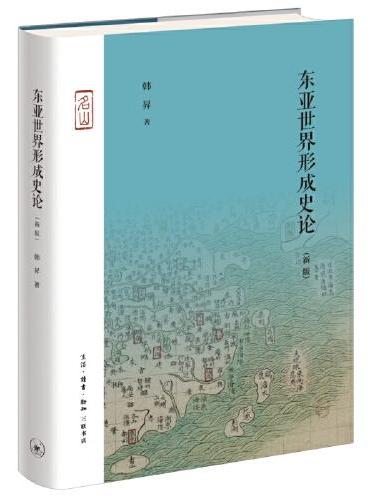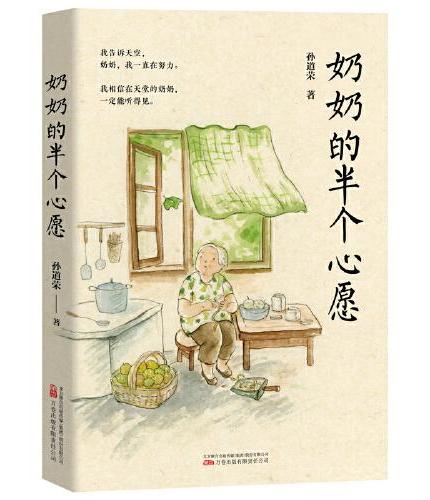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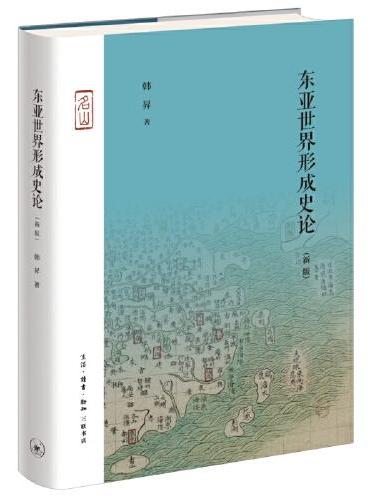
《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新版)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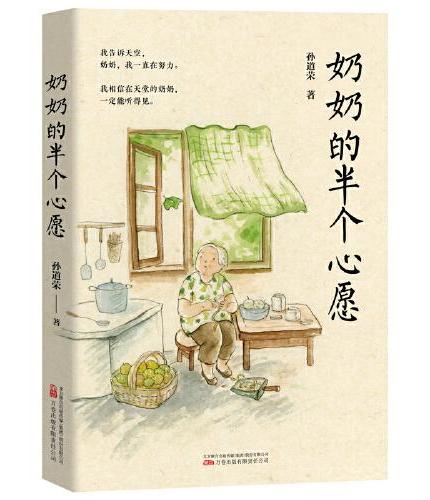
《
奶奶的半个心愿 “课本里的作家” 中考热点作家孙道荣2024年全新散文集
》
售價:NT$
190.0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
| 編輯推薦: |
|
用辛勤的思索去耕耘凡俗的荒原。亲善和坦诚的彩虹跨越在欺诈和奸险的深渊与泥潭之上,向未来输送彩梦。幸福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的专利,她属于芸芸众生的每个分子。跟着简·爱去获得你崇高的人格、完美的人性和非凡的人生,幸福会拥抱你。痛苦与磨难是简·爱的道路,孤独与抗争是简·爱的脚步,搏击与真善是简·爱的性格,美满与幸福是简·爱的归宿。有了简·爱所拥有的,才会拥有真正的人生财富和生命的辉煌。简·爱的精神生命不朽!
|
| 內容簡介: |
|
出身贫寒的简·爱在做家庭教师时,与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就在两人的婚礼上,简·爱发现罗切斯特家的阁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而她竟是罗切斯特的结发妻子。简·爱愤而离开。不久,疯女人火烧庄园,罗切斯特双目失明,并陷于贫困。就在他对生活感觉绝望之际,简·爱回到了他的身边……
|
| 關於作者: |
|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父亲是一名牧师。母亲玛丽亚于1821年因病去逝,夏洛蒂先被送到姨妈家寄养,后来又被送到科恩桥女子教会学校生活。因为学校爆发疫情,导致了夏洛蒂的两个妹妹玛利亚与伊丽莎白的死亡,于是夏洛蒂重返家中,并在这里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出版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简?爱》,轰动文坛。其后,又陆续出版了《雪莉》《维莱特》《教师》。夏洛蒂?勃朗特与其姐妹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作者)、安妮?勃朗特(《艾格妮丝?格雷》作者)并称为“勃朗特三姐妹”,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 內容試閱:
|
《简·爱》版不必写序,因此我没有写;这第二版需要几句致谢的话和零碎的评论。
我应该向三方面表示感谢。
感谢读者,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感谢报界,用真诚的赞许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进取者敞开了公正的园地。
感谢我的出版商,用他们的机智、他们的精力、他们的求实观念和坦率的慷慨为—个未经推荐的无名作者提供了帮助。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只是模糊的人物,我只得用模糊的话来感谢他们;可是我的几位出版商却是明确的,一些宽大的评论家也是明确的,他们鼓励我,只有宽宏大量的人们才懂得那样鼓励—个在挣扎中的陌生人。
对于他们,即,对于我的出版商和卓越的评论家,我诚挚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在这样向帮助过我、赞成过我的人致谢以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就我所知,这类人人数虽少,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过去。我是指少数畏首畏尾或者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怀疑《简·爱》这类作品的倾向。在他们眼里,凡是不平常的事都是错误的,他们的耳朵在针对偏执——罪恶之母一的每—个抗议中都觉察出一种对虔信——上帝在人间的摄政王——的凌辱。
我要向这些怀疑者指出一些明显的区别,我要提醒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袭击后者。揭去法利赛人上的假面具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
这些事情和行为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悬殊正如善恶之间的悬殊—般。人们过于经常地把它们混淆起来,它们不应该混淆,表面现象不能误认为真相;狭隘的世人的说教,只能使少数人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却不应该用来代替拯救世界的基督的教义。我再重复—遍,这之间是有不同的,在它们之间醒目而清晰地划一条分界线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分开,因为已经习惯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觉得把外表的虚饰当作真正的价值、让刷白的墙壁证明洁净的神龛是方便的。世人也许憎恨那个敢于探究和暴露、敢于刮去镀金展现下面劣质金属、敢于进入坟墓揭示里面的尸骸的人,可是,恨尽管恨,世人还是受惠于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对他作预言从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也许他更喜欢基拿拿的爱谄媚的儿子;但是亚哈如果停止听奉承而听听忠告,他倒可能逃过一场流血的惨死。
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人,他的话不是说出来去取悦娇嫩的耳朵;我认为他应该站在社会上的大人物之前,就像音拉的儿子应该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之前一样;他说出的真理同音拉的儿子的一样深刻,他的力量同音拉的儿子的一样像先知、—样强大,他的神态同音拉的儿子的—样无畏和大胆。写《名利场》的那位讽刺家在崇高的地位中受到赞扬吗?我闹不清,不过,我认为,被他投射讽刺的燃烧剂、被他照射谴责的电光的那些人,如果其中有几个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那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许还可以逃脱致命的基列的拉末。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人呢?读者啊,我提到他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比他同代人所承认的更为深刻、更为独特的智者,因为我把他看做当代位社会改革家,看做要匡正时弊的工作者的首领;我认为评论他的作品的人还没有找到适合于他的比喻,没有找到恰如其分地刻画他的才能的言语。他们说他像菲尔丁;他们谈论他的才智、幽默和诙谐能力。他之近似菲尔丁,犹如老鹰之近似秃鹫;菲尔丁会扑向腐尸,而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的才智是杰出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是两者与他严肃的天才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夏云边上嬉戏的片片闪电与孕育在云中可以致死的带电火花之间的关系。后,我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把这第二版的《简·爱》奉献给他一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献礼的话。
柯勒·贝尔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她以前从没这样过,”临了,白茜回过头去对使女说。
“可是她一直存着这个念头,”这是回答。“我常常跟太太说起我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同意我。她是个贼头贼脑的小家伙。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居然会这么狡猾。”白茜没有接口;但是不久她就冲着我说道:“你该放明白些,小姐,你受着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在养活你;她要是把你撵出去,那你只好进贫民院了。”听了这些话,我无话可说;这些话对我说来并不新鲜;我早的生活回忆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暗示。’这种指责我靠人养活的话,在我耳朵里已经形成了意义含糊的陈词滥调了,叫人非常痛苦,非常难受,但又只是使人似懂非懂。阿葆特小姐也附和道:“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里德少爷一块儿扶养长大,你可不该因此就以为自己和他们地位相等。他们将来都会有不少钱,而你连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就得低声下气,顺着他们。”“我们跟你说这些话,是为你好,”白茜补了一句说,声调并不粗暴,“你该学得有用一些,学得乖巧一些,那样的话,你也许还能把这儿作为家住下去;不过,要是你再发脾气,再粗暴无礼,我敢说,太太准会把你撵出去。”“再说,”阿葆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叫她在发脾气的时候突然死去,那时候,看她能上哪儿去?来吧,白茜,咱们走吧,别管她,我决不会得到她的好感。爱小姐,等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做做祷告吧。你要是不忏悔,准会有样什么邪恶的东西从烟囱里下来,把你抓走。”她们走了,关上了门,随手上了锁。
红屋子是备用的屋子,难得有人在里边过夜;真的,我可以说从来没有人睡,除非是偶尔有大批客人拥到盖兹海德府,才有必要利用里边所有的设备。然而,它却是整所房子里宽敞堂皇的一间屋子,里边摆着一张有粗大的桃花心木架子的床,挂着绛红色锦缎帐子,像一个帐篷似地立在屋子中央。两扇巨大的窗户,窗帘永远垂下,也用同样料子做的花彩和窗帘半掩着。地毯是红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一块鲜红的桌布。墙是淡淡的黄褐色,稍微带点儿粉红色。大柜、梳妆台、椅子都是乌黑油亮的老桃花心木做的。在周围这些深色的陈设中,床上的褥垫和枕头堆得高高的,蒙着马赛出品的雪白床罩,白得刺眼。同样醒目的是床头边一张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也是白色的,前面还放着一张脚凳,我想,它看上去就像一个苍白的宝座。
屋子里很冷,因为里边难得生火;它也很静,因为离婴儿室和厨房都很远;很庄严,因为大家知道很少有人进来。只有使女在星期六来擦擦镜子,抹抹家具,除去一星期来的积尘。里德太太自己要隔好久才来一次,查看一下大柜里某一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她在那个抽屉里收藏着各种羊皮纸契据,她的首饰盒,还有她那亡夫的一张小像。这间红屋子的秘密就在于她的亡夫身上。这秘密是一种魔力,正是它使这间屋子尽管堂皇却显得那么凄凉。
里德先生故世已经有九年了。他是在这间屋子里断气的,也是在这里人殓的;殡仪馆的人就是从这里把他的棺材抬走的。从那一天起,屋子就由一种哀伤的神圣感保护着,以至于不常有人闯进来。
白茜和恶毒的阿葆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在上面的那个座位,是一张软垫矮凳,就搁在大理石壁炉架附近。床就耸立在我面前。右手边是高高的、黑糊糊的大柜,黯淡的、不完整的映像使嵌板的光泽有点儿变化。左边是遮蔽起来的窗户;两扇窗户之间,有一方大镜子,重现了大床和屋子的空虚肃穆的景象。我不很肯定,她们是不是把门锁上了;等我敢走动了,我就起来,走过去瞧瞧。天啊!真锁上了,从来没有哪个牢房比这儿关得更紧了。我走回原来的地方,不得不经过那方大镜子;我的眼光被它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向它显示的深处探索。在这空幻之中,一切都显得比现实更冷酷、更阴暗;里面那个瞪眼盯着我的古怪小家伙,在黑暗里显出苍白的脸庞和胳臂,在那一切都静止不动的地方转动着明亮的恐惧的双眼,看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幽灵。我想,这小家伙就像那些半神半妖的小鬼中的一个,白茜在晚上讲故事的时候说过,这些小鬼会从沼地上荒草萋萋的幽谷里爬出来,在走夜路的人面前现形。我回到了我的矮凳上。
我那忽儿很迷信;但是迷信还没到它完全胜利的时刻,我的血液还很激奋·反抗的奴隶的心情还在气势汹汹地激励着我,我得先和激流般的回忆搏斗一下,才会在可怕的现实面前屈服。
约翰·里德的种种暴虐专横,他姐妹的种种骄傲冷漠,他母亲的种种憎恶,用人们的种种偏心,一古脑儿都像积聚在浑浊的井里的污泥沉渣一样,在我混乱的脑海里翻腾起来。我为什么老受折磨,老受欺侮,老挨骂,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呢?我为什么会从来得不到别人的欢心呢?为什么我竭力讨人喜欢也没有用呢?伊丽莎又任性又自私,却受人尊敬。乔奇安娜脾气给惯坏了,凶狠毒辣,吹毛求疵,蛮横无理,大家却都纵容她。她的美丽、她的红喷喷的脸蛋和金黄色的鬈发,似乎叫看着她的人都感到愉陕,都能因此而原谅她的每一个缺点。至于约翰,谁也不会去违拗他,更不会去惩罚他,虽然他扭断鸽子的脖子,弄死小孔雀,放狗去咬羊,摘掉暖房里葡萄藤上的葡萄,采下花房里珍贵的植物的苞蕾;他还管他妈妈叫“老姑娘”;有时候还辱骂他母亲那和他一模一样的黑皮肤,对她的吩咐公然不理不睬。还时常撕破和毁坏她的绸衣服,而他却仍然是她的“心肝宝贝”。我不敢做错事,我竭力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而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整天都有人骂我淘气、讨厌、阴险、鬼头鬼脑。
我被他打倒,头还在痛,血还在流;约翰粗暴地打了我,没有人责备他,而我,为了叫他以后不再干出这种荒唐的暴行,却受到了众人的许多责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