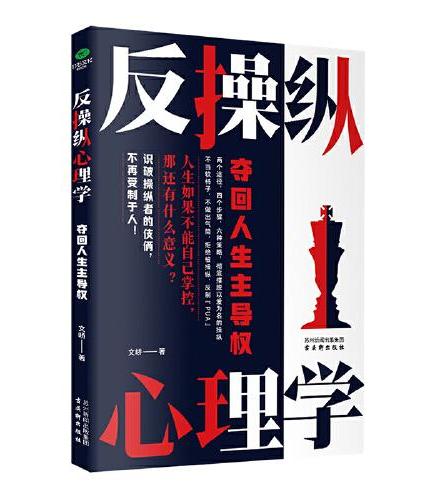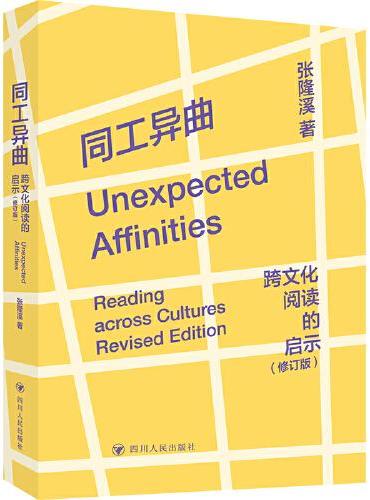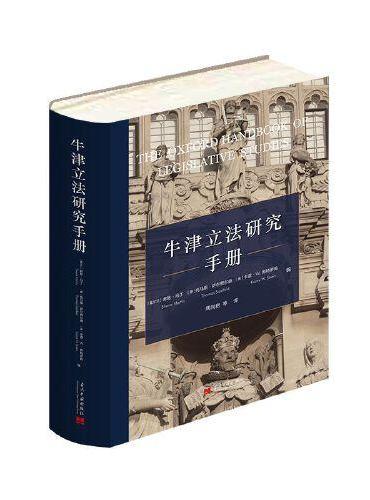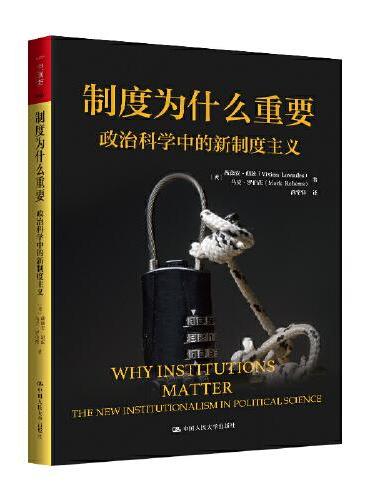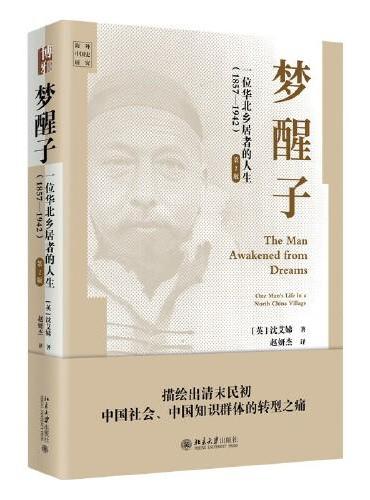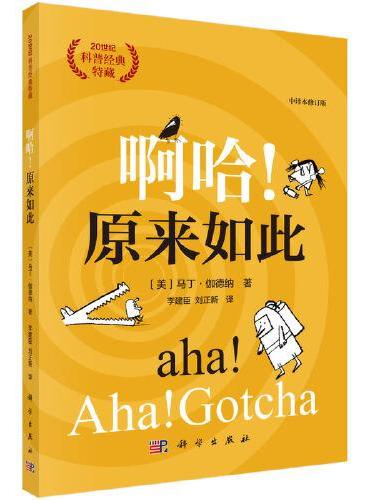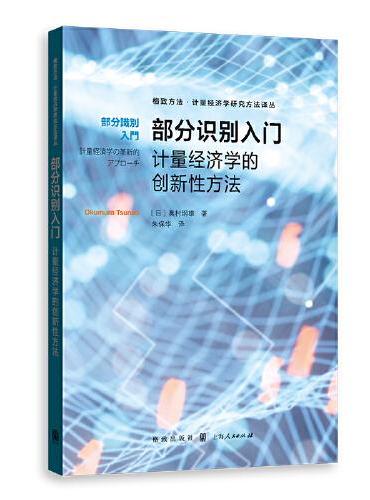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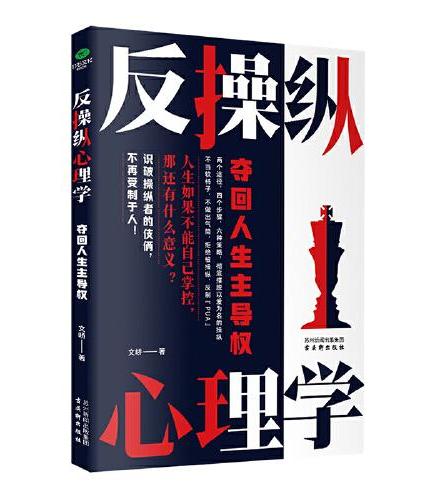
《
反操纵心理学:夺回人生主导权 拒绝被操纵
》
售價:NT$
2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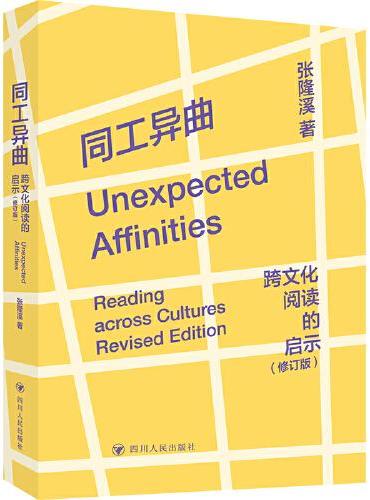
《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修订版)(师承钱锺书先生,比较文学入门,体量小但内容丰,案例文笔皆精彩)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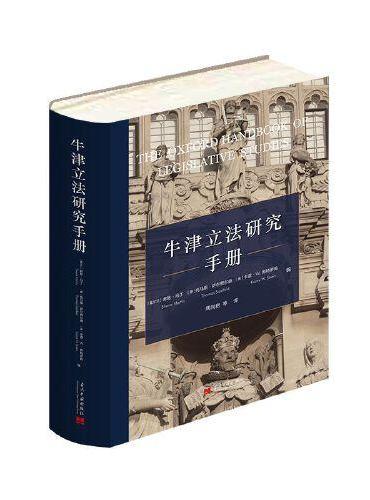
《
牛津立法研究手册
》
售價:NT$
16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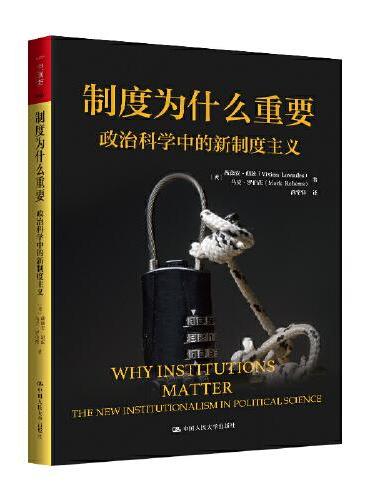
《
制度为什么重要: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人文社科悦读坊)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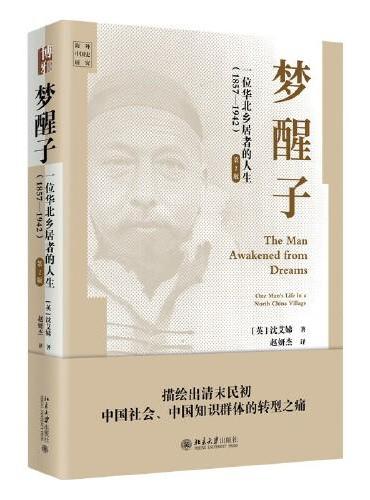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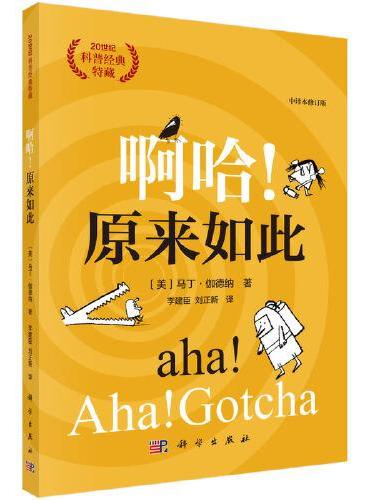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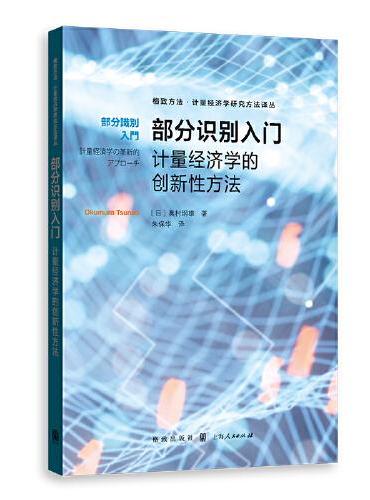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 編輯推薦: |
|
收录函札一千四百余通,是较为全面的俞樾函札总集整理本
|
| 內容簡介: |
|
俞樾(1821年12月25日-1907年2月5日),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城关乡南埭村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所著凡五百余 卷,称《春在堂全书》。除《群经平议》五十卷、《诸子平议》五十卷、《茶香室经说》十六卷、《古书疑义举例》七卷外,其《楼丛书》三十卷、《曲园俞楼杂纂》共百卷。本 书为俞樾经典著作之一种,为《春在堂尺牍》的整理,以人名为次序,共收录俞樾函札一千四百余通,是为当今能见到的现存俞樾函札之总集。整理者对每封信札的相关信息如人物、 事件、写作事件都予以考证,对于研究俞樾交游,有着重要的价值与作用。
|
| 關於作者: |
俞樾(1821年12月25日-1907年2月5日),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城关乡南埭村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
张燕婴,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编审。从事俞樾研究多年,出版有《俞樾函札辑证》等多部著作。
|
| 目錄:
|
春在堂尺牘目録
前言一
凡例一
致白曾烜(一通)
致鮑晟(一通)
致北方蒙(十四通)
致卞寶第(一通)
致曹元弼(一通)
致陳方瀛(九通)
致陳漢第(一通)
致陳豪(十通)
致陳夔龍(二通)
致陳鼐(一通)
致陳祖昭(一通)
致程先甲(一通)
致崇厚(一通)
致村山正隆(一通)
致戴啟文(二通)
致戴清(一通)
致戴望(十一通)
致戴咸弼(一通)
致戴湘(五通)
致丁立誠(六通)
致丁立誠、丁立中(一通)
致丁日昌(四通)
致杜聯(二通)
致杜文瀾(四通)
致端方(一通)
致恩壽(三十四通)
致樊氏(一通)
致方濬頤(一通)
致費念慈(十一通)
致馮桂芬(五通)
致馮焌光(一通)
致馮崧生(一通)
致馮一梅(二通)
致馮譽驄(一通)
致傅觀海(一通)
致傅雲龍(三通)
致高保康(一通)
致高均儒(一通)
致龔照瑗(二通)
致顧成章(一通)
致顧文彬(一通)
致何兆瀛(一通)
致洪爾振(七十通)
致洪子靖(四通)
致胡俊章(三通)
致胡澍(一通)
致胡元鼎(一通)
致黄以周(三通)
致江瀚(三通)
致江清驥(一通)
致蔣光焴(二通)
致蔣清瑞(一通)
致蔣益澧(三通)
致金安清(一通)
致金文潮(一〇二通)
致金吴瀾(三十四通)
致金武祥(三通)
致金詠榴(三通)
致景星(一通)
致蒯德模(一通)
致勒方錡(三通)
致雷浚(一通)
致李濱(二通)
致李超瓊(八通)
致李慈銘(一通)
致李瀚章(十七通)
致李鴻藻(一通)
致李鴻章(二十二通)
致李桓(八通)
致李嘉樂(一通)
致良揆(一通)
致廖世蔭(一通)
致廖壽豐(四通)
致凌霞(二通)
致劉炳照(四通)
致劉秉璋(一通)
致劉恭冕(一通)
致劉汝璆(一通)
致劉瑞芬(二通)
致劉樹堂(三通)
致柳商賢(一通)
致陸潤庠(一通)
致陸樹藩(一通)
致陸心源(五通)
致陸元鼎(二通)
致羅豐禄(一通)
致馬新貽(五通)
致毛子雲(四十八通)
致冒廣生(五通)
致梅啟照(三通)
致孟沅(一通)
致繆荃孫(六通)
致聶緝椝(二通)
致潘大人(一通)
致潘衍桐(二通)
致潘曾瑋(四通)
致潘祖同(十通)
致潘祖蔭(七通)
致潘遵祁(二通)
致彭見貞(三通)
致彭生甫(二通)
致彭玉麟(十四通)
致祁寯藻(三通)
致錢應溥(一通)
致喬松年(一通)
致秦緗業(一通)
致瞿鴻禨(七通)
致如山(一通)
致三多(二通)
致沈秉成(一通)
致沈鳳士(一通)
致沈光訓(一通)
致沈夢巖(二通)
致沈能虎(一通)
致沈三三(一通)
致沈善登(二通)
致沈樹鏞(一通)
致沈玉麟(十通)
致盛康(八通)
致盛宣懷(三十三通)
致施則敬(二通)
致壽錫恭(一通)
致崧駿(二通)
致宋仁壽(一通)
致宋恕(五通)
致孫殿齡(八通)
致孫同康(一通)
致孫憙(一通)
致孫衣言(六通)
致孫詒讓(一通)
致譚獻(二通)
致譚鍾麟(一通)
致談文烜(十一通)
致唐翰題(一通)
致唐樹森(八通)
致陶然(一通)
致陶甄(一通)
致童寶善(五通)
致汪丙照(一通)
致汪芙青(七通)
致汪鳴鑾(三十通)
致汪曰楨(一通)
致汪宗沂(三通)
致王棻(二通)
致王繼香(十通)
致王凱泰(十四通)
致王韜甫(一通)
致王廷鼎(十六通)
致王同(二十九通)
致王同、許祐身、俞祖綏(一通)
致王文韶(一通)
致王修植(一通)
致王豫卿(七通)
致王原讓(一通)
致魏錫曾(一通)
致翁同龢(一通)
致鄔銓(二通)
致吴昌碩(一通)
致吴承潞(十一通)
致吴承志(一通)
致吴存義(二通)
致吴大澂(二通)
致吴大廷(一通)
致吴康壽(一通)
致吴慶坻(四通)
致吴紹正(三通)
致吴棠(一通)
致吴雲(十三通)
致謝增(一通)
致徐琪(一五五通)
致許庚身(二通)
致許國瑞(一通)
致許景澄(一通)
致許引之(三通)
致許應鑅(二通)
致許祐身(二十五通)
致嚴辰(一通)
致延清(一通)
致楊昌濬(八通)
致楊以貞(一通)
致楊子玉(一通)
致姚文玉(一通)
致易佩紳(二通)
致應寶時(五十通)
致英樸(一通)
致瑛棨(四十三通)
致于鬯(四通)
致俞陛雲(四十五通)
致俞波文(二通)
致俞林(三通)
致俞繡孫(十九通)
致俞祖綏(一通)
致袁保恒(一通)
致惲炳孫(五通)
致曾璧光(三通)
致曾國藩(七通)
致曾國荃(一通)
致曾紀澤(四通)
致章梫(二通)
致張楚南(十七通)
致張大昌(一通)
致張縉雲(一通)
致張森楷(一通)
致張樹聲(一通)
致張文虎、唐仁壽(一通)
致張應昌(一通)
致張豫立(一通)
致張之洞(一通)
致趙寬(一通)
致趙烈文(二通)
致趙舒翹(一通)
致鄭文焯(二十三通)
致鍾文烝(一通)
致周學濬(一通)
致朱澄瀾(一通)
致朱福榮(一通)
致朱欽甫(二通)
致朱泰修(二通)
致朱宜振(三通)
致朱振聲(一通)
致朱之榛(六十三通)
致竹添光鴻(四通)
致宗源瀚(二通)
不詳姓名者(九通)
缺上款者(十一通)
參考文獻
|
| 內容試閱:
|
前言
俞樾是晚清時期‘有聲望’顧頡剛《秦漢的方士和儒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二頁。的經學家之一,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清政府重建文化秩序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一位通儒。《春在堂全書》是他的著作總集。其中有尺牘六卷,收入信札二百餘通,然而這遠非俞氏所作書信之全部。
近年來,分藏於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臺灣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杭州岳廟管理處、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等國内外多家典藏單位的俞氏尺牘稿本或原札漸次以各種方式公布如國圖的一些藏札可在‘中華古籍資料庫’中檢索到,上圖、浙圖、北大與港中大藏品多已影印出版,臺圖與日本兩家圖書館的藏品可在網絡上獲取,南圖藏品也已有掃描件可到館閲覽。所有這些無不説明,海内外圖書館都抱持著越來越開放的態度,服務讀者。,海内外多家拍賣公司的各場次拍賣會上也常有俞札現世‘雅昌藝術網’爲檢索各家拍品提供極大方便。截止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可通過該網站檢索到的俞札拍品,本書已盡可能予以輯録(所遺漏者,多因網圖過於模糊或未能尋訪到拍賣圖録)。二〇一八年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洪晨娜整理的《俞樾函札輯補》,主要收録見於(本人二〇一四年整理本之外的)各家拍賣品二百五十餘通。由於本人的整理在《輯證》一書出版前後長期持續進行,本書中與《輯補》重合者,實係本人采擇自網絡圖片、拍賣圖録或衆友好之見示。。本人又曾走訪國内多家藏有俞札的博物館觀摩展覽或藏品,更因種種機緣有幸得見一些私人藏家手中的俞札其中之大宗,如俞氏後人家藏信札,有本人親見者;亦有趙一生先生見示者。杭州岳廟文管會所藏俞樾信札,爲俞氏後人捐贈,亦蒙趙一生先生見示複印件。。今將這些資料搜集起來,輯成此書本書輯録之俞札,以信札原件爲首選。一些刻入六卷本《春在堂尺牘》的信札,經查原件尚存的,均據原札予以整理,以見俞氏書信之本真。。
鳳凰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曾影印《春在堂全書》,《尺牘》六卷在影印本第五册中,不難獲見。故此次整理未沿用刻本《尺牘》的編例。二〇一四年,鳳凰出版社曾出版本人整理的《俞樾函札輯證》(收入《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輯】中)。該書爲簡體字版,有考證信札繫年或本事的按語。此次整理,沿用此前整理俞札的體例(詳參凡例)。
本書輯録的俞樾信札,或鋪陳日常行止,或關照文化大業,或探究故實,或切磋學藝,或吟詠贈答,或披露心性,或評騭著述,或臧否人物,從中可以窺見俞氏之學識、品格、胸懷與情趣,亦有助於探究清末政治、社會、經濟、學術狀況之實態。
一、 考察其生平行事之細節
人都是社會的人。考察個體人生的狀態,對於了解其所生活時代的實態,是一種有益的補充。
俞樾的人生,始於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終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七年二月五日),幾乎貫穿清末這一中國社會發生變局的時期。他身居江浙,曾親身經歷次、第二次鴉片戰争、捻軍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等時事;家人中則有多人受到主要發生在北方的義和團運動的影響。這些歷史事件以及當時的世況民情,都嘗在其筆端積爲‘實録’支偉成總結俞樾‘爲學固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違實録者’(《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二三〇頁)。:如致李鴻章札第四、第五通、致應寶時札第五、第三十九通,致廉翁札等均提及捻軍起義;致洪爾振札第十至十三通、致盛宣懷札第二十九通、致汪鳴鑾札第十四通、致徐琪多札等均作於義和團運動期間,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對於民生的影響,札中都有細膩的記述。
俞樾是清末傳統教育的體驗者與實踐者。他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取得進士出身,又有近五十年的時間從事教育:這其中既包括他早年爲了生計授館的經歷,也包括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起他歷主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上海詁經精舍、上海求志書院、歸安龍湖書院、德清清溪書院的歷程。他的信札中多有相關的教育史料,如致費念慈札通、致馮焌光札、致高保康札、致龔照瑗札通、致廖壽豐札第二通、致劉樹堂札第三通、致孟沅札、致聶緝椝第二通、致瞿鴻禨第五通、致孫衣言札通、致陶甄札、致王同諸札、致王豫卿多札、致應寶時多札、致惲炳孫通等。
故研究俞樾生平,對於晚清社會生活史、學術史、教育史都是有意義的。
了解一個人的生平行事,直接的資料,當然是日記。已經刊刻行世的俞樾著述接近五百卷,其中只有一卷是日記:即記載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八日赴閩省親行程的《閩行日記》一卷(收入《曲園雜纂》卷四十),可知俞氏對日記這類‘私著述’的公開,是相當審慎的。故至今可見完整的日記手稿僅存同治六年至光緒二年十年間的今藏杭州岳廟管理處。二〇一八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俞樾全集》第二十七册收入整理本。;另有《俞曲園先生日記殘稿》民國間排印本一種,爲光緒十八年二月初十日至四月初三日蘇滬往返的經歷(此種又存抄本一種,與排印本文字小異)。三者所存日數加起來,仍不足其人生的八分之一(俞樾一生共計八十六春秋,三萬餘日夜),故仍需要其他相關史料予以補充。
而信札恰恰是一種富有‘日録’意味的資料。從《春在堂日記》的記載來看,收寫信件本就是俞樾日常行事的重要内容:一天來往三五通信件,是常有之事;一日十來通也不稀罕如同治六年六月十八日、同治八年九月十四日、同治九年三月初八日、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同治十一年十月三十日等。;有些日子俞氏僅記載下‘得某書’‘與某書’這樣簡要的文字,因此信札的内容就對還原俞氏當日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所作所爲顯得尤爲重要。
本書輯録的俞樾手札一千四百多通,其中署有日期者超過半數,可作爲與其日記互證或補充其日記缺失部分的直接資料。如俞氏日記載,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壬子‘與戴子高書’,僅從日記看,難明其詳。本書所輯俞樾致戴望札第十一通則説:子高老表阮足下:
得十一月十六日書,知所患未全癒,明年擬來吴下就醫。而吴下亦無良醫,岐黄一道似乎失傳。費伯庸輩盛名卓卓,實無所有也。大著《論語注》,陳意甚高,即以文字論,亦千數百年來無此作矣。日置案頭,思有所獻替而卒不得,亦見其義也堅确也。吴承志字祁甫,馮一梅字孟香。吴長於小學,馮富於詞藻。兩君皆可喜,而吴已娶,而馮則今年未之見,聞其館上海,不知其曾娶不也。此外殊無佳士,未敢以冰上人自任也。紹萊尚在大名任所,一時未即交卸,然薄宦天厓,亦殊乏味。望其明歲能補一官,未知得否。僕雖托林泉之名,而無閑適之樂。著述之事,久已輟筆。前寄上《群經平議》,知爲胡君乞去,兹再寄奉經、子兩《平議》及詩古文詞,求收存。此外,《樓叢書》尊處計已有也,其《随筆》《尺牘》等,瑣瑣不足觀,或有便再寄,此時案頭適無單行本也。别紙所示,處之善。明年酌予紫米之資,亦事也不可少者,毋使作《漢學商兑》者埶爲口實也。尊三叔母厝處在德清何處?望示知其詳。僕明年至德掃墓,或與内人偕,擬至其棺前焚一佰紙錢。外家姊妹,相處多年,至今思之依依也。於此敬問起居,不盡所言。
十二月二日,樾顿首再結合俞氏日記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己丑‘得戴子高書,子高言:其叔母、仲蘭外姊之棺厝於德清銘道基,問蔡氏名亭者可得其處’的後續記載,可知是札即作於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者。俞氏在札中問候戴望之疾、稱贊戴著之優、説明兩位門生的婚姻情況(當是戴望有所問詢)、長子俞紹萊的任職、臚舉自己已有之著述、詢問戴望叔母(即俞氏外姊)棺厝所在,内容可謂豐富。
而一些未署日期的信札中也往往有可資利用的時間信息,如:樾于三月八日還吴下寓廬,頃又買舟至浙,開詁經之課。(致卞寶第)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聲中,又交六九。(致崇厚)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書……今年二月十三日曾致一函,未知收到否?(致戴望札第二通)
自正月廿一日如滬、二月十三日還蘇以至於今,無須臾之暇……僕寓蘇平順,已于二月廿日開課。(致戴望札第六通)
僕于九月初攜老妻至湖上小樓,倚檻坐對,全湖晴好雨奇,隨時領略……前日乘籃輿至天竺、靈隱禮佛……是日爲月盡日,香客稀少,游屐亦罕……(致杜文瀾札通)
二月七日曾布一箋,未知已達典籖否?(致蔣益澧札第三通)
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致李鴻章札第二通)
九月廿六日得六月四日書,雅意拳拳,讀之增感。七月廿七日曾肅寸箋,奉賀金甌枚卜之喜,託禹生中丞作寄書郵,未知已達典籖否?(致李鴻章札第八通)
今年八月又值老母九十正壽,以在國恤之中,乃借七月十二萬壽蟒服之期稱觴一日,雖止一日排當,頗費兼旬料理,故久而不及函也。(致李桓札第四通)
二月之末曾寄一書,未知到否?弟于三月二十日自杭還蘇。(致俞林札通)以上僅列舉有明確時日信息的俞札十通,這些内容對於豐富俞樾生平細節的描述同樣具有補充作用。
本書輯録的俞札,收信人計有二百二十多位,或是家人親戚,或是業師門生;既有科舉同年,亦見鄉黨官長。在通訊不便的年代,魚雁往還本就是俞樾與他們重要的交往方式之一:從本書的整理實踐看,有些人與俞樾從未見過面,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之間有相當熱絡的書信往來如本書收録俞樾致金文潮的信札一〇二通,而金氏逝後,俞樾致其子金詠榴的信中有‘久不得尊大人書,甚以爲念。欲俟拙刻《雜文》第五編八卷印釘齊全再作函奉寄,不料今日接令叔來書,驚悉尊大人已於本月十三日仙逝,痛哉!十載神交,未謀一面’(第二通)的説法,可知俞樾與金文潮從未見過面。。即使是那些僅記録了饋贈(致恩壽、汪鳴鑾諸札)、請托(致盛宣懷、朱之榛諸札)、慶吊(致金文潮第五十一通、致毛子雲通、致小樓札等)等生活瑣事的函札,亦無不真實反映俞樾日常生活的面相,也都是研究俞氏生平與交往情況的珍貴資料。
二、 展現其情懷與心緒
信札‘是文學中特别有趣味的東西,因爲比别的文章更鮮明地表出作者的個性’,‘文章與風月多能兼具,但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周作人《知堂書話》之《日記與尺牘》,嶽麓書社,一九八六年,第七六、七七頁。。俞樾寫給其摯愛親朋的信札,常常流露出深沉的關愛與無盡的思念(詳見與夫人姚文玉札、與親家翁彭玉麟札、與次女婿許祐身札、與次女俞繡孫札、與獨孫俞陛雲札等)。
如果説上述感情尚屬人之常情的話,下面這幾通手札中所反映的思想内涵與感情特質,則需要通過考察俞樾的人生經歷方可更好地予以把握。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俞樾在河南學政任上。因出題不慎,爲御史曹登庸參劾,罷職事見《清文宗實録》卷二百三十一。。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五月,俞樾作《曲園自述詩》一百九十九首,其一曰:‘命宫磨蝎待如何,唤醒東坡春夢婆。已到神山仍引去,蓬萊亦是有風波。’小注曰:‘丁巳秋,因人言免官,即移寓挑經教胡同度歲。’對罷官之事諱莫如深。又一首曰:‘嶽色河聲無古今,使臣仗節遍登臨。力除蕭艾求蘭蕙,此事當年過用心。’小注曰:‘丙辰二月,始出棚考試。學使之職,當以求才爲主,而以防弊爲賓,果拔得一二真才,便爲無忝厥職,小有冒濫,無傷也。余當年轉以防弊爲主,此乃少年用意未當,奉職不稱,正以此也。’將自己早年罷官之由歸爲防弊過度咸丰七年七月初六日曹登庸參劾俞樾的奏摺中稱其‘覆試一人一題’,當是俞氏防弊之舉措。。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八月,弟子徐琪拜廣東學政之命,致信俞樾請教施政之方。俞樾在復信中寫到:粤東材藪,亦弊藪,尤人人畏之。兄謂,弊亦防其在我者而已,如幕友、家丁,皆在我之人也,關防宜密,稽察宜周,聽言宜慎,家丁尤宜少用,少一人自可少一弊矣。至於代槍頂替,乃在人之弊也。我場規嚴肅,彼自無所施其技,即察出一二,亦不必嚴辦,蓋嚴辦而求其淨絶根株,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徒使其人播散蜚語壞我清名而已。(第三十通)札中俞樾提示徐琪取士需要防弊,但因從自己身邊著手,精選幕友、家丁,嚴控關防,嚴格考紀;至於考生的作弊行爲則不必嚴辦。特别是此札中還有‘如兄者,但可借鑒以爲覆轍之車,非可倚重以爲識塗之馬也。既承問及,輒貢其愚’,結合俞樾罷官的經歷來看,他顯然是以自身所遭遇移作徐琪居官的借鑒。
事實上俞樾的内心并不以出仕爲重,他早年的創作就時時流露出歸隱山林的願望:人生束髮事名利,何異牛馬居闌牢。即使百齡守簪笏,未若半席分漁樵。題詩并與山靈約,他年築屋名雲巢。(《春在堂詩編》卷一《七里瀧》)
世間名利豈不好,一骨投地萬犬。不如歸掃子斗室,左右圖史如排衙。他人入室詫不識,但見束束籤紅牙……鄙人十夜九此夢,所苦有願囊無鎈。獨坐千山萬山裏,不覺心緒紛如麻。安得一稜兩稜地,去與鄰父同耕。他年有田不歸隱,請即此歌盟以豭。(《春在堂詩編》卷二《丁未秋周雲笈下第歸,寄詩慰之》)
自拋簪笏奉潘輿,又見春風到敝廬。牲醴不豐因歲儉,光陰好是家居。(《春在堂詩編》卷三《除夕口占》)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之業《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立德’實難,而俞氏又不以出仕爲意,則能够使其‘不朽’的亦唯有著述一途。事實上,俞樾自幼即對著述之事非常在意《春在堂全書録要·序》中俞樾自謂‘九歲時剪紙成書册之形,自爲書而自注之’。,六十歲已有將著述‘藏之名山’的規劃與舉措《春在堂詩編》卷九有《余於右台仙館隙地埋所著書稿,封之,崇三尺,立石識之,題曰‘書冢’。李黼堂方伯桓用東坡〈石鼓歌〉韵爲作〈書冢歌〉,因依韻和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又曾請人鑿造‘書藏’(詳參本書中輯録的致毛子雲札第二十至三十五通)。因爲有著强烈的以著述傳世的意識,俞樾的著作常常隨作隨刻,如致陳方瀛札通稱‘今年又刻《曲園雜纂》五十卷……弟今年新刻《游藝録》六卷’,致丁立誠札通有云‘拙作《銷寒吟》,已刻入第十七卷詩’,致恩壽札第二十八通稱‘近作又刻成十葉(廿九至卅八)’,致傅雲龍札通稱‘日前惲太夫人曾以《落葉》詩索和……因索觀者衆,遂付剞劂,以代胥鈔’,致金吴瀾札第二十三通稱‘又有《題故人孫蓮叔翦燭談詩圖》一詩……弟擬假尊處活版排印一百紙分布同人’,致徐琪札三七通有‘去年詩尚未刻成,今年詩亦循去年之例絡續付刻’,致朱之榛札第四十通稱‘今作一詩聲明之……又近作二首……此三詩皆用鋼版摹印,但不甚清晰耳’等等。且因爲對自身著述的自信,俞樾又常常將新刻成的著述饋贈友人,如致陳鼐札稱‘拙著各種,年前又刻成三十九卷,并前所刻,共一百二十六卷,兹一并寄呈是正’,致戴望札第七通中説‘閏月之朔曾寄一書并《諸子平議》之已刻者’,致孫憙札中説‘外附去《春在堂全書》二部,一以奉贈,一請留存九峰書院中,妄借名山,希圖不朽’,致張之洞札曰‘拙著已刻者,一百四十二卷,此後有便,擬寄呈一二部,即求存貯書院中,雖不足質院中高材諸生,亦古人藏名山、傳其人之意也’。這樣的内容在本書所輯函札中甚夥,讀者自可留意。
著述一方面可以揚名,另一方面也可能致禍,俞樾對此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寫給曾國藩的信中提到: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而比年譔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雖然‘花落春仍在’是俞樾成名的基礎(其著述總名亦爲《春在堂全書》),但‘花落’之詞,終非春風得意中人所宜有《春在堂詩編》卷十七《八十自悼》其三曰:‘已分青氈了此生,蹉跎三十幸成名。置身瀛閬雖堪喜,回首窐衡轉自驚。月下吟情仍賈島,花前詩句竟韓翃。也同入夏春猶剩,偷領春風一日榮。’小注曰:‘余進士覆試,以“花落春仍在”句爲曾文正所賞,遂忝。此事屢見余詩文矣。後觀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載六安陳鼇,嘉慶丙辰進士,覆試。詩題“首夏猶清和”,陳詩云“入夏初居首,春光剩幾分”。不數日竟卒,人以爲讖。余詩雖稍勝,要非春風得意中人也。’,無怪俞樾以之爲讖語。‘花落’一詞僅僅使俞樾禄命不佳,尚不致送命。前面提及的導致俞樾罷官之事,實際上也是文字惹的禍。所以俞樾後半生的寫作是非常謹慎的如致李鴻章札第四通中説:‘樾非不知儒者讀書當務其大者,特以廢棄以來,既不敢妄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并不屑雕琢詞章以媚俗,從事樸學,積有歲年,聊賢于無所用心而已。’,他在考據學領域取得的成就,當與考據學問遠禍的性質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第二二至二九頁)有較詳細的分析,可參看。不無關係。
除了考據經書的名著《群經平議》之外,俞樾的説經之書還有光緒十三年撰成的《茶香室經説》十六卷《茶香室經説序》葉一。和光緒二十年的《經課續編》八卷《經課續編序》葉一。。認同自己經師身份的俞氏,對兩書中的説解頗爲自許,故常常持以贈人:附去拙刻《經説》,與賢喬梓共質之。(致金文潮第二十一通)
所刻《經説》十六卷,記已奉覽矣。(致繆荃孫第三通)
附去近刻《經説》十六卷,聊酬雅意,兼求是正。(致孫同康)
冬寒杜門,仍以書籍自遣而已。偶解得《論語》‘有婦人焉’及‘瓜祭’兩條,自謂發千古所未發,附聞,一噱。(致李超瓊第三通)
鄙人新刻《經課續編》四卷,印釘甫成,謹寄呈一部,以備啟發。(致金文潮第九十九通)
又《經課續編》第四卷,皆説經之作,近時所吐棄者。然‘有婦人焉解’一首,自謂極確,並以呈教。(致繆荃孫第四通)
又《經課續編》第五卷亦於年下刻成,一并附呈。(致王同第十五通)以上各札分别作於光緒十四年、光緒十六年柳向春《俞曲園致繆筱珊手札六通考實》,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録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四六四至四六五頁。、光緒十七年札中提及孫同康的《師鄭堂集》,是書爲光緒十七年末排印。、光緒二十年札中有‘弟八月回杭爲孫婦營葬’之説。、光緒二十一年、光緒二十二年柳向春《俞曲園致繆筱珊手札六通考實》,《版本目録學研究》第四輯,第四六五頁。和光緒二十二年,可知俞樾持續推廣自己的説經之作。然而當光緒十八年,時任廣東學政的弟子徐琪想要謀刻《經説》一書時,俞樾却勸阻道:初擬縮刻拙著《茶香室經説》分貽士子,今則改縮刻爲翻刻,此意良是。袖珍之本,非使者所宜持贈也。惟兄則又有一説:學使者當堂給發,必須官樣文章,近時有奉發之世祖御製《勸善要言》。若以此等書給發多士,庶幾正大得體,人無異言;若私家著述,大非所宜。拙著《茶香室經説》成書較後,王逸吾學使纂《皇清經解續編》不及著録,得老弟爲我張之,大妙。然不過攜數十部於行篋中,考試經古,遇有佳士,以此贈之,或可示以塗畛,濬其心源,此則於理可行,於事亦或有益。若人人給以一函,則徒費紙札之資,而適以啟揣摩迎合之私,且或以成口舌異同之辨,萬萬不可也。兄意如此,幸老弟從之。(致徐琪札第三十三通)札中力阻徐琪縮刻袖珍本的《經説》,認爲袖珍本不是學政所宜持贈者;至於翻刻書,則當以‘官樣文章’(如世祖御製《勸善要言》之類)爲首選,而《經説》這樣的‘私家著述’,贈與個别喜好經書古文的士子即可,實無需廣爲散播,以免招致‘口舌異同之辨’。綜合以上諸札觀之,對於文名之傳或不傳,其中的尺度當如何,俞樾顯然有著細心的揣摩,這恐怕也是罷官一事的‘遺産’。
本書所輯俞札,頗多此類透露其委曲心緒之作,需要細細體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