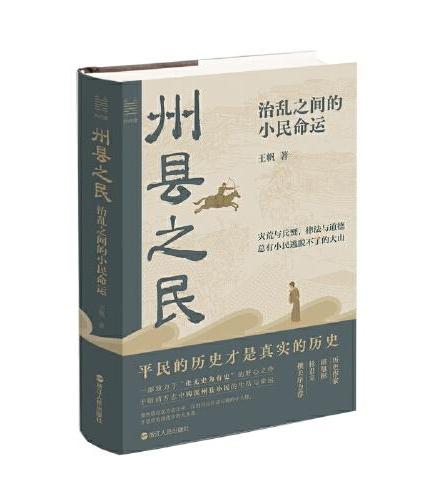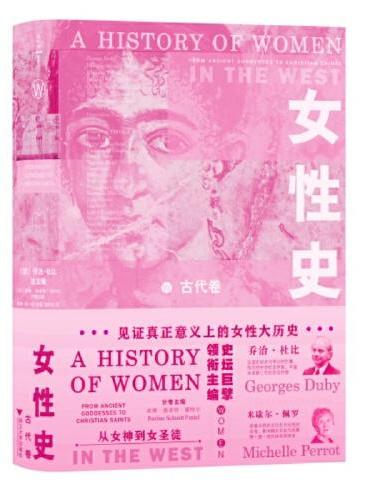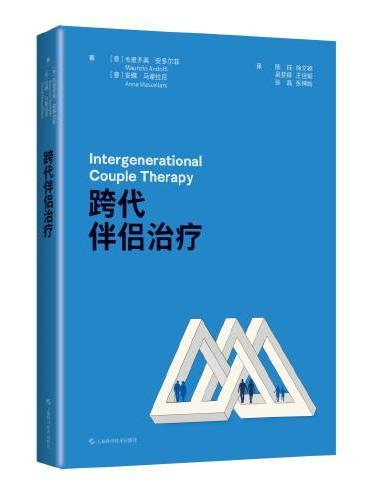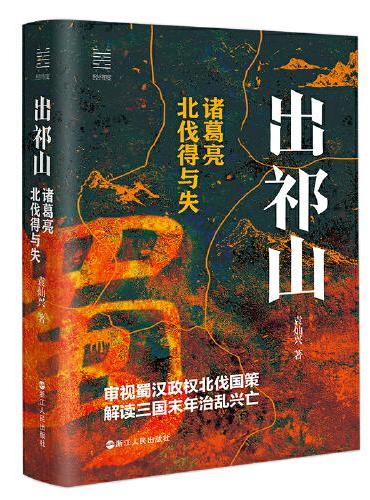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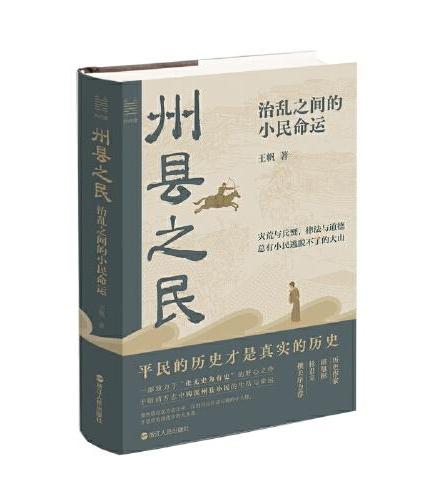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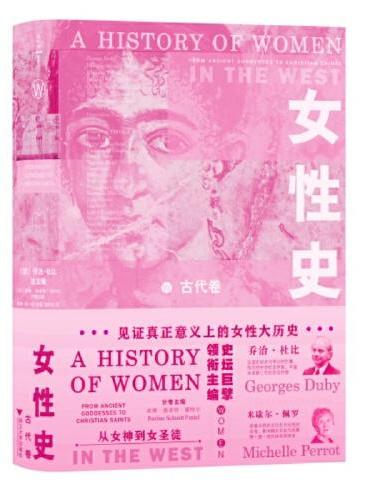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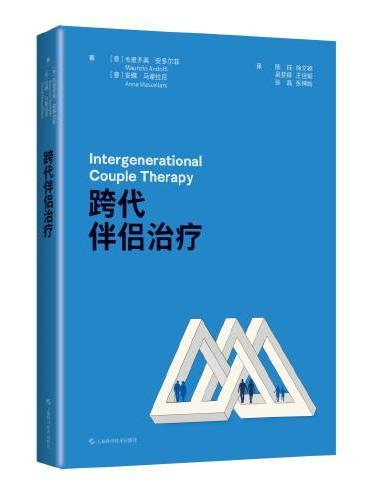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NT$
440.0

《
精华类化妆品配方与制备手册
》
售價:NT$
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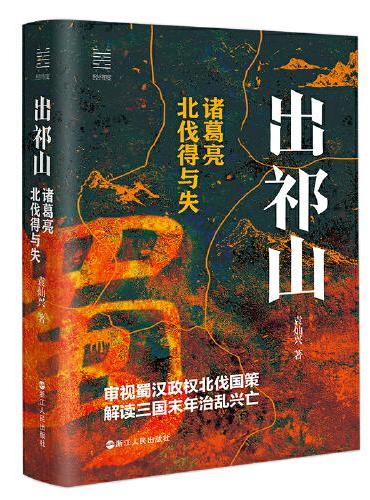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出祁山:诸葛亮北伐得与失
》
售價:NT$
440.0
|
| 編輯推薦: |
|
“牛津通识读本”被誉为真正的“大家小书”。作者均为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重要和知名的专家学者,对相关领域有深入研究。译林出版社自2008年初开始推出“牛津通识读本”中英双语版,截至目前,出版已达100种,特制作百种精美礼盒套装以飨读者。
|
| 內容簡介: |
|
“牛津通识读本”丛书由译林出版社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被誉为真正的“大家小书”,内容涵盖文学、宗教、哲学、艺术、历史、法律、政治、管理、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南京大学前校长陈骏院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万立骏院士等近百位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作序推荐,现已成为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通识教育图书品牌。
|
| 關於作者: |
|
迈克尔·费伯 1966年获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学士学位,1975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新罕布什尔大学英语教授,研究生教育主管。学术兴趣包括浪漫主义、诗歌、希腊文学、莎士比亚、诗学、象征主义、语言学、翻译以及战争文学等。著有多部关于布莱克和雪莱的作品,另著有《文学象征辞典》(2007)、《欧洲浪漫主义指南》(2005)等。
|
| 目錄:
|
牛津通识读本·第五辑
浪漫主义
批判理论
德国文学
儿童心理学
电影
戏剧
时装
俄罗斯文学
腐败
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古典文学
医事法
卢梭
大数据
癌症
隐私
洛克
植物
电影音乐
幸福
|
| 內容試閱:
|
第三章 诗人
早逝诗人
浪漫主义诗人或艺术家英年早逝依旧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他们多死于肺结核、自杀、决斗或是饿死在阁楼里或流放途中。英语世界里,尽管代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终其天年,济慈、雪莱和拜伦这些“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仍将英年早逝的印象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之中。济慈25岁时因肺结核病逝于罗马,雪莱29岁时溺亡于勒瑞奇海湾,拜伦36岁时因高烧死于希腊,普希金37岁时在一场决斗中受伤而亡。卡罗利妮· 冯· 冈德罗德26 岁时,被她所爱的男子拒绝,开枪射向自己的心脏。但是,这些浪漫主义者自己生前已经前往那些早逝诗人的墓前进行祭拜。
现今几乎已被遗忘的法国诗人查尔斯· 洛森(1791—1820), 在英年早逝的前一年写下了《临终卧床的年轻诗人》(1819),从而在法国掀起了阅读早逝诗人诗歌的热潮。但是,他的其他事情更值得我们关注。正如圣伯夫在1840年一篇随笔中写到的那样, 洛森在西班牙有处城堡,城堡带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树林。
在树林僻静的地方,种植了一小片柏树、桦树和常青树,用来悼念那些英年早逝的年轻作家们。洛森为此所设置的细节也很引人入胜。一簇草丛上摆放着骨灰瓮,瓮上刻着提布卢斯的名字,在附近的桦树树皮上,我们能看到多米提乌斯· 马尔苏斯的两行诗句:
你也一样,提布卢斯,维吉尔的挚友,不公地死去;在花样年华去往极乐世界。
不远处,紫杉之间黑色大理石金字塔唤起人们对于26 岁早逝诗人卢坎的记忆。人们认为他是其打破常规思想的受害者,又或许是暴君忌妒心的牺牲品。碑上,我们可以读到《法沙利亚》中的几句诗行:
……用你的剑攻击我吧,
我,这无用法令和虚空权利的守护者。(2.315—316)
垂柳下的两只鸽子,再现了24岁早逝的让· 塞孔作品《吻》中的意象。我们领悟了其中的思想,这个思想一直被人们所遵循和丰富。我们也没忘记去马尔菲拉特和吉尔贝的大理石墓碑前祭拜。打翻的一篮花象征着米勒瓦英年早逝的命运。早年自杀的查特顿的坟墓前只有一块光秃秃的石头。随后,我们参观了安德烈· 谢尼埃的墓,这是美的地方之一。洛森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的结局,因此,提前与他钟爱的诗人们居住在他极乐世界中的秘密树林里。
洛森翻译过提布卢斯的很多诗歌。古代世界伟大的哀歌,即奥维德的《恋歌》第三卷第九节中曾经称赞过提布卢斯。在那首挽歌中,奥维德声称吟游诗人是神圣的,受到诸神的关注;他想象着提布卢斯和其他诗人一起隐居在极乐世界的山谷里,就像是在洛森的小树林中一样。卢坎曾著有《法沙利亚》, 该44 诗被誉为维吉尔《埃涅阿斯》之后伟大的拉丁语史诗;他迫于尼禄的压制,自杀而死。在雪莱悼念济慈的挽歌《阿童尼》中,很多已故诗人,“一些未成就的声誉的继承者”都站起身来迎接济慈,其中之一就是“卢坎,死使他受到称赞”。让· 塞孔(即亚努斯· 塞昆德斯,原名扬· 埃费拉茨)是16世纪荷兰用拉丁语进行创作的诗人。其作品《吻》主要模仿了卡图卢斯的诗作。接下来谈到的是三位法国诗人,他们均受伤而死。我们很快会在下文中谈到托马斯· 查特顿和他那块光秃秃的石头。1819 年浪漫主义重新兴起时,人们再次关注到安得烈· 谢尼埃的诗歌。他在1794年“恐怖统治”期间被送上断头台,而几天之后,“恐怖统治”就被推翻了。维尼将小说《斯岱洛》(1832)中长的部分献给了谢尼埃(和另外两位诗人查特顿和吉尔贝);普希金1826 年也以他为主题创作了一首诗歌。
洛森在其后院(仿照奥维德)再建了一个极乐世界,是热切推动年轻诗人崇拜的人。很多法国诗歌中均可以找到他心中所有的崇拜对象和其他伟人。托马斯· 查特顿是其中有名的一位,也是离世时年轻的。当时,他正要凭借自己的非凡才华大展宏图,却被蒙上“骗子”的名头。他1752 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尔,从孩提时起就常去圣玛丽雷德克里夫大教堂拜读乔叟、斯宾塞和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12岁时,他用古英语创作诗歌来冒充中世纪的诗歌。1770年,他搬到伦敦,他那些假托15世纪托马斯· 罗利修道士之名的“罗利”诗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赞美。当时,他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可能不久之后,有人揭穿了他的骗局。因为这些或是其他别的原因,他服毒身亡,时年17 岁。
柯勒律治大约在1790年,仅比查特顿早逝时的年龄大不到一岁时,写下了一首《哀查特顿之死》。诗中,他将这个男孩悲惨的命运归咎于“贫困和冷漠的无视”以及“恨麻木的心投来无尽的侮辱,/ 悲无望尘世间浅薄之徒”,世人和出版商的思想过于呆滞而未能识别他的天赋异禀。但是,现在他已是“天佑亡魂”,在天使中传播他的圣歌,“圣歌飞越极乐之地,/ 天使为之狂喜”。柯勒律治和他的朋友骚塞迎娶弗里克家两姐妹时,就是在圣玛丽雷德克里夫大教堂举行婚礼的。
华兹华斯在1802年创作的《决心与自立》中抒发了他行走荒原时的凄凉感受:
我忆起查特顿,那优秀的大男孩,
那不眠的灵魂,枯萎在鼎盛之年;忆起他,他自豪快乐地行走,
走在犁地后,走上山腰[罗伯特· 彭斯,逝于37 岁]:
我们的精神将我们奉若神明;
我们这些诗人年轻时以欢愉开始,
但是到头来总变成沮丧和癫狂。
和柯勒律治一样,玛丽· 鲁滨逊也写了一首悼诗《追忆查特顿》(1806),哀悼贫穷困顿和怀才不遇给查特顿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她将他比作一朵被扼死在萌芽期的花朵:“淡白色的报春花,五月美的蓓蕾,/还未绽放美丽就已枯萎。”济慈喜欢放声朗读查特顿的诗句,他似乎与查特顿感同身受,都是那凋零的希望之花。济慈在一首组十四行诗《噢,查特顿!》(1815)中写道:“你却已凋零,/初开的蓓蕾。”但正如柯勒律治和鲁滨逊一样,济慈也将查特顿安置于天堂,“对着旋转的苍穹,/你甜美地歌唱”。三年后,济慈尝试写作了他的首史诗《恩底弥翁》,并将其献给了查特顿。威廉· 亨利· 艾尔兰德创作了组诗《被忽视的天才》(1812),分别讲述斯宾塞、弥尔顿、德莱顿、汤姆森、哥尔德史密斯和其他数名诗人的杰出和不幸,并以查特顿结束组诗:
杰出的查特顿唤醒我悲伤的歌,
诗人群体中非凡的年轻小哥;
幻想的子宫孕育出多产的神童,
生而发光,随之腐朽在坟墓中。
这些诗句或许揭示了威廉· 亨利· 艾尔兰德自身才华遭到忽视的原因,但其将可怜的托马斯· 查特顿视为典范,并能对他作出这样心领神会的解读,这更加值得关注。与柯勒律治和济慈的诗句相比,这些诗句或许才气不足,却能凸显出对查特顿的狂热崇拜。似乎所有这些诗歌(还有更多的诗歌)都是供奉在神殿上的许愿烛,用来阻挡沮丧和疯狂,又或者是在无情的批评家的弓上鸣枪示警。
受难诗人
如果说相较于“早逝诗人”,“被忽视的天才”是一个更大的群体,那么,比它还要更大的群体便是“受难诗人”了。无论他们是否被忽视,浪漫主义者们用一首接一首的诗歌、一部接一部的戏剧作品来振奋精神,激励自己或同龄人。乌戈· 福斯科洛独力将朱塞佩· 帕里尼因尖锐讽刺贵族而招致的艰苦生活谱写成神话;他在其为著名的诗篇《墓地哀思》(1807)中,用一个章节生动描述了帕里尼遗体被扔进一个普通坟墓时所遭受的侮辱。拉马丁将其《光荣》(1820)献给长寿诗人弗朗西斯科· 马诺埃尔· 多· 纳西门托(1734—1819)。纳西门托被驱逐出葡萄牙,不久前刚刚去世。诗中,拉马丁追忆起荷马:
这里,正是那位老人,忘恩负义的爱奥尼亚
看见他四海漂泊,历经苦难,
双目失明的他竟以自己的天才作为代价
乞食一块被泪水浸湿的面包。
接着,又追忆起塔索:
那里,塔索,充满着致命激情,
为荣耀和爱情而身陷囹圄,
在即将获得辉煌的胜利之际,
却坠入了黑暗。
然后,又追忆起被雅典流放的将军阿卫斯提得斯和被罗马流放的英雄科里奥兰纳斯。在后一节中,追忆了被流放至黑海托弥的奥维德:
在坠入死亡之岸前,
奥维德向天堂举起哀求的双手:
他把遗骸留给了野蛮的萨尔马提亚人,
却把荣光留给了罗马人。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托尔夸托· 塔索( 1544—1595)创作了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多首十四行诗。根据传说,他爱上了费拉拉公爵的妹妹利奥诺拉,并被视为疯子监禁了七年。塔索获释后,教皇克莱门特八世计划在朱庇特神庙将其加封为桂冠诗人,但他在加封大典举行之前就去世了。不正当的爱情、盲目的疯狂、极权统治者的残暴、太晚才受到认可的天才—这些均是极为诱人的浪漫素材。歌德用戏剧作品《塔索》(1790)掀起了一股“塔索风”,斯塔尔夫人在影响广泛的著作《论德国》中对该作进行了解读。拜伦在1817年发表的《恰尔德· 哈罗德游记》的第四章和《塔索的悲哀》中均对诗人塔索进行了描述。后者是写给利奥诺拉的长篇书信体诗文,在信中,有“儿歌之魂”美誉的诗人塔索为自己长期身陷囹圄而感到悲哀:但是在费拉拉政权瓦解后得知“诗人的花环应是你的王冠,/诗人的地牢应是你远的名望”时,他感到些许安慰。1818年,雪莱计划以塔索为主题创作一部戏剧,后来写了一个场景并且谱了曲。弗雷西亚·海曼斯创作了《塔索获释》(1823)和《塔索和妹妹》(1826),其中《塔索和妹妹》借鉴了斯塔尔夫人的作品《柯丽娜》。在俄罗斯,巴丘什科夫创作了《垂死的塔索》(1817)。拉马丁又重新以塔索作为主题创作了多首诗歌;他晚年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1821年早期在那不勒斯因阅读塔索传记、思索塔索疯病而引发的神经崩溃。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拉克洛瓦绘制了不同版本的《疯人院中的塔索》和一幅《狱中塔索》。1833 年,多尼采蒂以该故事为原型创作了一部歌剧。1849 年,李斯特创作了交响诗《塔索》。塔索不幸的一生历经的场所变成了圣地。1817年,拜伦拜谒了费拉拉,一年后,雪莱也前去拜访并参观了塔索被幽禁的牢房。1831年,柏辽兹和门德尔松一同到达罗马瞻仰了塔索的墓地。
著有《变形记》(和《提布卢斯挽歌》)的诗人奥维德的部分诗歌可能触犯了凯撒· 奥古斯都,因此被流放至黑海之滨人迹罕至的罗马前哨,周围生活的是锡西厄人或萨尔马提亚人。他把自己的诸多诗歌都寄给了在罗马的朋友,并被收集在《哀怨集》和《黑海书简》中,但是这些诗歌却未能让他得到赦免,终客死他乡。在《哀怨集》第三章第七节中,奥维德认为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将会永存,并以此来安慰自己:“只要从她那胜利的七丘,/罗马俯瞰被征服的世界,我的诗歌就会被人诵读。”普希金因为触犯他的凯撒而从圣彼得堡被流放,途中,他拜访了托弥并忆起这几行诗,这比奥维德所希望的更有先见之明。罗马的灭亡甚至也未能撼动奥维德的名声!但普希金自己却被淹没在人潮中,注定默默无闻,无人聆听他“粗俗”的吟诵(《致奥维德》,1821)。在澳大利亚,弗朗茨·格里帕泽没有像普希金那样遭受流放,但他自1826年便开始创作《哀怨集与黑海书简》,一组关于绝望与艺术贫乏的组诗。德拉克洛瓦被失去自由的塔索吸引,也被这一主题吸引,他两次绘制了《锡西厄人中的奥维德》。
注意到有多少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流亡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要么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要么是嫌自己国家专制与残暴而流亡。普希金曾被流放至克里米亚半岛或被限定于自家田园。莱蒙托夫被流放至高加索地区一年。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被捕后流放至俄国,尽管可以自由游历,但是他自此再也没回过波兰。意大利诗人乌戈·福斯科洛出生于希腊的扎金索斯岛,当时该岛受威尼斯人控制,他因自由倾向的政治观点而逃离威尼斯。后来,出于相同的原因,他又逃离了米兰, 在瑞士待了一段时间后移民到英国,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直至去世。维克多· 雨果在泽西岛和根西岛度过了20年才等到拿破仑三世政权垮台。拜伦和雪莱逃离英国,到了“流亡者的天堂”意大利(尽管这不是乌戈·福斯科洛的天堂)。海涅离开德国去了巴黎。这些诗人各自的情况和他们的性格一样,差异很大,因此我们不能确定是否能通过流亡轨迹找到他们的共性,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诗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亡有助于浪漫主义运动发展为国际性的运动。所有这些诗人均能说两至三种语言,可以读懂更多种语言。密茨凯维奇曾在巴黎以斯拉夫文学为题发表演讲,海涅也曾在那里以德国文学为主题写作;福斯科洛曾在伦敦评论意大利文学作品。但是, 这些流亡者似乎也体现了我们在本章中探讨过的主题:在祖国不受敬重的预言者、因说着奇怪话语而隐居的人。这被驱逐的、受难的或是疯狂的诗人形象拥有美好的未来:例如,19世纪70 年代,兰波和魏尔伦在法国过着奢侈的生活;近一个世纪后,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和其他“垮掉一代”的作家们在美国总是不停漂泊,享受着药物所致的幻觉。
在所有这些强调诗人崇高和不幸的断言中,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发觉这些显然是浪漫主义诗人为了得到更多尊重、让其作品更为畅销以及为宣传他们的群体而发出的诉求。这一观点的确不无道理。当时,诗人的主要谋生手段正由接受赞助转向向普通民众销售书籍,而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过渡时期的一种回应。取悦贵族或者收取昂贵的订阅费,通常需要谦逊和礼貌;而要引起购书中产阶级的兴趣似乎需要更为大胆甚至令人震惊的某种东西。正如丑闻缠身的拜伦所知道的那样,负面宣传也是一种宣传。讽刺作品是贵族赞助时代的一种诗歌典型,而这些讽刺作品可能有些大胆,但是因为赞助人们自己会陷入派系斗争,因此掌握讽刺的技巧也是这些雇佣文人的长期饭票。另一方面,单凭宣称自己是先知或是立法者不大可能赢得很多贵族的支持,当然,也有例外。夜莺本身无可厚非, 但它若非要假扮成鹰,那就会像诗人假扮成贵族一样荒谬可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