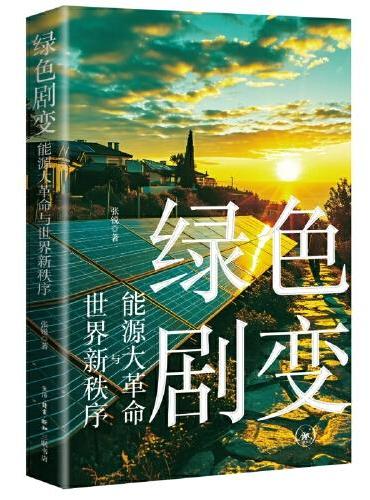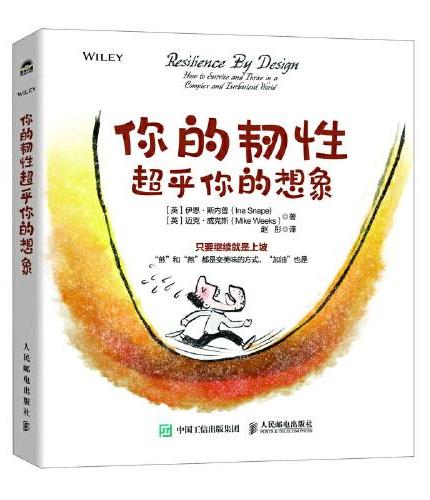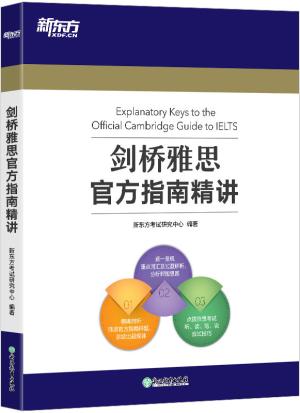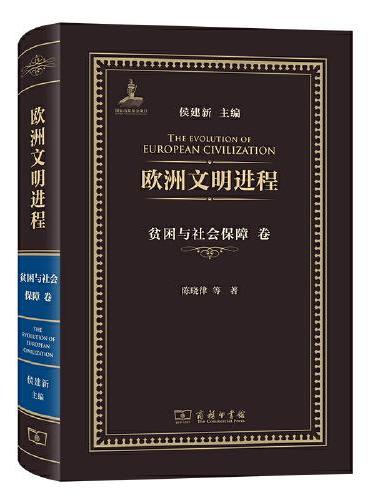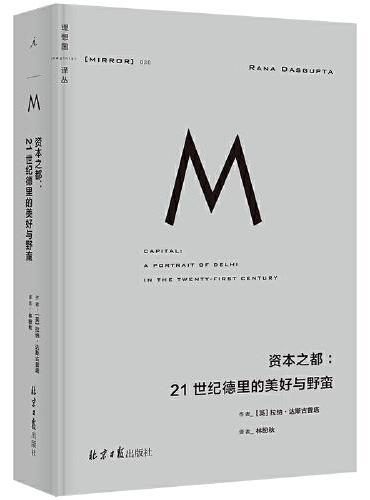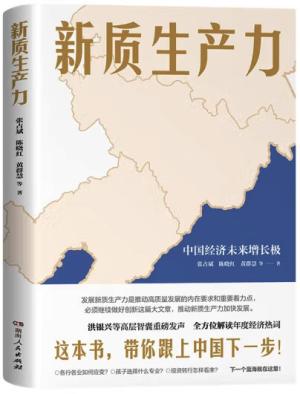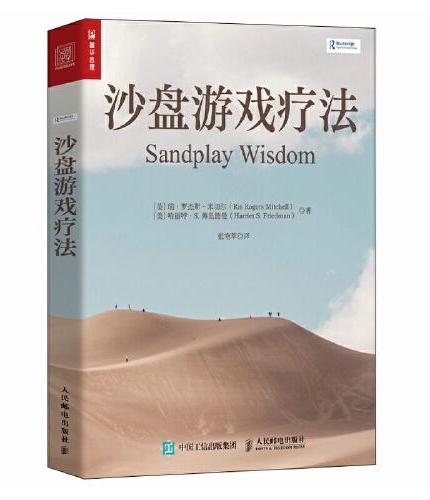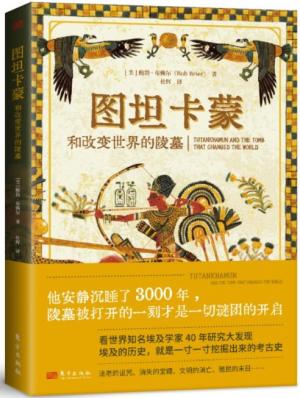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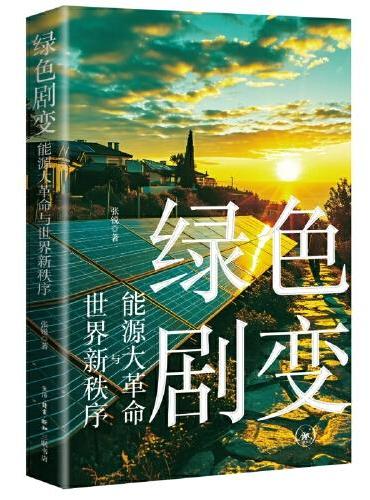
《
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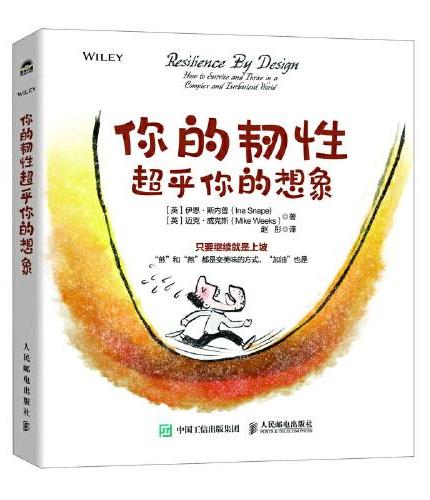
《
你的韧性超乎你的想象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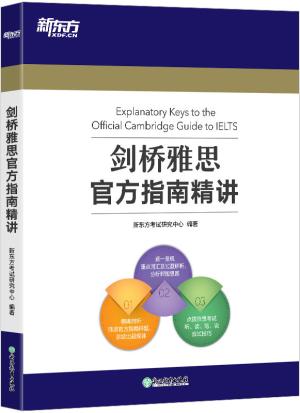
《
新东方 剑桥雅思官方指南精讲 精确剖析官方指南样题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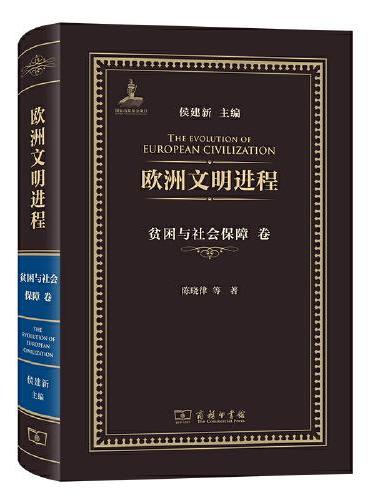
《
欧洲文明进程·贫困与社会保障卷
》
售價:NT$
9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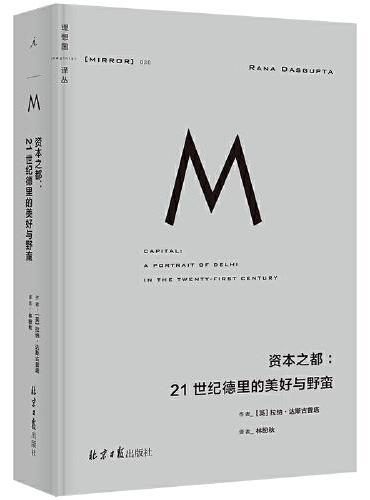
《
理想国译丛030: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
售價:NT$
5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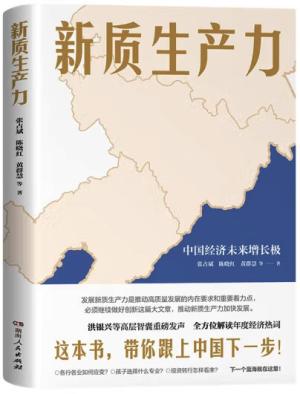
《
新质生产力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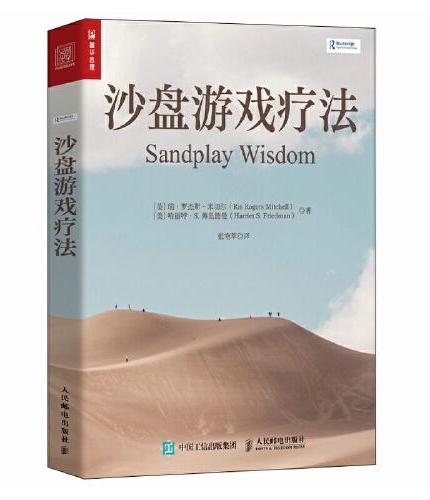
《
沙盘游戏疗法
》
售價:NT$
4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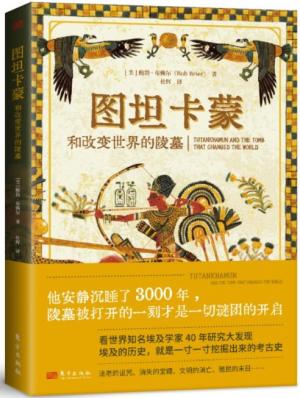
《
图坦卡蒙和改变世界的陵墓
》
售價:NT$
447.0
|
| 編輯推薦: |
鲁迅文学奖、女性文学奖、全国图书奖、加拿大华语文学奖、英国笔会文学奖得主迄今为止*精*全文集
莫言 李敬泽 陈晓明 戴锦华 联袂推荐
她被誉为后社会主义中国*出色的小说家澳大利亚著名女性文学研究学者Kay Schaffer );
她是高度技巧化地传达被遮敝的声音的小说家(世界著名出版社西蒙舒斯特Atria Books副总裁Judith Curr语)
她是飞翔的姿态越来越优雅的小说家(莫言语)
她是守护着超验的神性的迷幻花园的小说家(李敬泽语)
她是把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的小说家(陈晓明语)
她是站在中国文坛金字塔*上的小说家(戴锦华语)
|
| 內容簡介: |
|
徐小斌经典书系之一种。著名作家徐小斌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在海外发行。这本书是她的经典短篇小说集。收录《蜂后》《银盾》《清收下这束鲜花》《密钥的故事》《阿迪达斯广告》等二十篇短篇小说。
|
| 關於作者: |
|
徐小斌,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画家、刻纸艺术家。自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德龄公主》《双鱼星座》等。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均有藏书。2014年入选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著名女作家。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三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加拿大第二届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2015年度英国笔会文学奖等。代表作《羽蛇》成为首次列入世界著名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国际出版计划的中国作品。部分作品译成英、法、意、日、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巴西、希腊、阿拉伯等十余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
|
| 目錄:
|
001蜂后
022银盾
033女觋
045蓝毗尼城
054阿迪达斯广告
070若木
090古典悲剧
100无相
121无执
141美术馆
155图书馆
162密钥的故事
171黑瀑
184请收下这束鲜花
197过门儿
207黄和平
217青芒果
231花瓣儿
241亚姐
258雾
279能人之外
293写作是最好的礼物(代跋)杨庆祥
299徐小斌作品系年
302徐小斌文学活动年表
|
| 內容試閱:
|
写作是最好的礼物(代跋)
读徐小斌的短篇小说
杨庆祥
年轻的男孩卷入了一场不愉快的三角恋:他爱上的美丽纯洁的女孩丽冬居然是自己姐夫的情人。而更让他伤心的真相是,丽冬不过是一个在夜店酒吧寻欢作乐的风尘女子。这是徐小斌短篇小说《蜂后》讲述的故事,仅仅是上述情节对于一个短篇来说已经足够复杂,但有意思的是,这一切才只是个引子,真正的故事,要等到男孩在郊区碰到一个长相怪异的女人才开始,这个女人是一个养蜂者,猛一看像一个非洲土著,更奇怪的是她的头发像一个蜂巢,里面居然养着一只可以通灵的奇大无比的蜜蜂
《蜂后》是我近几年读到的最为诡异的短篇小说之一,如果非要作一个类比的话,似乎只有安吉拉卡特的《烟火》系列才可与之媲美,但安吉拉卡特以英国人的视角描写日本的经验,同时又融入土著者的神话,对于一个中国的读者来说其诡异情有可原。但是徐小斌以本土作家身份书写当下中国故事,居然也能营造出这种阅读的效果,让我觉得非常诧异。我不太清楚徐小斌的写作资源,但是至少在《蜂后》这篇短篇小说里,一种非常复杂的主题和类型被恰当地融合在了一起。对于那个男主角来说,这是一个成长型的故事,他在目睹纯洁外在背后所潜藏的污秽猥琐后获得了一种心理性的成长;如果从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来看那个养蜂女居然是丽冬的养母,并在抚养丽冬的过程中对其造成了某种弗洛伊德式的童年阴影,最后,她又帮助丽冬来处理感情和生活中的危机这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式的世俗传奇,而这种传奇,又寄生在中国当下非常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传奇与现实构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现实感。但徐小斌显然不是一个世俗小说的热衷者,与中国大部分作家处理此类题材时候的局促逼仄相比,徐小斌的作品始终有一个超越的层面,这不仅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是奇怪的巫妖人的结合体,更表现在她的小说总是在最接近日常生活之时又突然腾空而起,高蹈虚步,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在《蜂后》中,随着养蜂女人的出现,小说明显指向一种类似于哥特小说的场景,阴郁的气氛和压抑的叙述烘托出一种只有在中世纪城堡中才出现的气息,而在小说的结尾,复仇以一种中国《聊斋》式的神秘方式得以实现,即使这种复仇遵循的并非现实的逻辑而是故事的逻辑更严格来说,遵循的只是徐小斌个人智力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徐小斌的作品有一种智力和想象力得以释放的快感。
这种智力的操练最典型地表现在《图书馆》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故事极其简单:一个老教授在图书馆看一本希伯来文的《死亡之书》,然后猝死,然后连同书籍一起火化。这个故事简单得几乎可以说没有故事,但毫无疑问,这并非重点,重点是徐小斌试图通过这种去故事化的方式为短篇小说局促的篇幅腾出叙述空间,利用这些空间在小说中填入一些看来不是那么小说的东西。在《图书馆》中,这些东西由以下一些片断组成:铅字,字母,数字,乐谱,子宫,魔咒,等等。这些片断并不构成情节、冲突和结构,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灵感突现,比如1是站着的女人,2是跪着的女人,3是舞蹈着的女人,4是一条腿跷起来的女人,5是飞翔的女人,比如子宫是地狱的通道,等等。这种碎片化的叙述构成了一篇散文化十足的短篇小说,在这样的小说中寻找一切现代的主题是徒劳的,现实、历史和主体在这里都被思维的跳跃性所解构,这里呈现的仅仅是游戏式的表达,为了表达而表达,为了一种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心灵的表达。我在阅读徐小斌晚近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想起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有意识地摈弃现代写作的范式,把轻作为未来写作的首要命题,在卡尔维诺的很多作品中,故事和主题都让位于作者的奇思妙想,这些奇思妙想构成了小说一副轻巧的面具,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徐小斌的作品也隐隐吐露出这种趋向。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徐小斌的很多作品中,其人物似乎都带有一种神秘性,或以奇怪的装束示人,或藏身于某处与世隔离的处所,即使不得不进入世俗生活,也总是带有一种幽灵的气息。在这种设置中,人物的精神层面代替了人物的世俗层面,或者说,人物的行动更多地服膺于自我心灵的准则而非世俗生活的原则。在我看来,这正是轻的重要含义即以精神性来超越物质性,以审美来超越世俗。在这一点上,徐小斌有些艺术家的气质。
如此并不是说徐小斌就放弃了对于历史和现实关怀,恰好相反,无论是早期的《羽蛇》,还是后期的《敦煌遗梦》,历史和现实的幽灵就一直在徐小斌的作品中游荡,并构成一种背景式的存在。这一存在通过两个切近的主题反复出现:宗教的堕落和女性的自救。在短篇小说《蓝毗尼城》中,女人梦幻般地来到了传说中的蓝毗尼城,才发现这里已经被一群干瘪的木乃伊控制,他们违背宗教的信条,放纵罪恶的欲望,女人面临的抉择是,想活下去,就不能反抗这种罪恶,如果要坚持人性的良知和宗教的戒律,说出这些罪恶,则要面临不知名的恐怖刑罚。这个女人选择了不妥协,她最后是否受到了惩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把上述的两个主题结合到了一起,圣城的堕落暗示了一种后宗教时代的普遍现实,在《敦煌遗梦》中,这种堕落以更复杂的悬疑故事展示出来,面对这种现实,女性为了实现自身清洁的愿望,不得不作出自我的牺牲。徐小斌对现代女性面临的这种生存困境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她没有化装为某一类女权主义者做一些表演化的抵抗,而是直面这种困境,由此可以说,徐小斌的写作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同时又是一种非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是指她始终尊重自己的女性身份这一基本的物质事实,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书写的视角,非女性主义则是指她没有拘囿女性主义在现代语境中的庸俗政治指向,她意识到了并试图呈现一种复杂性。在《蓝毗尼城》中,那个陌生的拯救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以一种折中的方式来化解这种困境:她从那些行尸走肉那里获得食物,同时在另一个荒凉之地洗净自己的身体,以此保持心灵的高洁,灵与肉在此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多么温婉而又尖锐的妥协和牺牲,但事实是,正如徐小斌借文中女人之口所言她如此生活了三千年!在《敦煌遗梦》中,女性的命运与更遥远神秘的历史勾连到了一起,在围绕佛像所展开的争夺和权谋之中,女性自身的丑陋和局限也被和盘托出。我想说徐小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残忍的书写者,她没有含情脉脉地去以简单的善恶来区分男性和女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她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她忠实于自己深切的体验和感受,《敦煌遗梦》其实有一个更现实的背景,那就是所谓的知青经历。作为这一运动的亲历者,徐小斌没有陷入滥情的苦难叙述,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开始,徐小斌就回避了那种简单的叙述,那种将自我经验无经艺术转化的日记式的文学。徐小斌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具体的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背后所呈现的普遍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规范。对于真正的文学来说,具体的苦难都是浅薄而容易过去的,对象过于明确的反抗和讽刺也是不长久的,徐小斌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但不管如何,她感受到了普遍性。在短篇《古典悲剧》中,徐小斌将这种普遍性编织到一段宫廷斗争中,与《羽蛇》描写血缘关系密切的女性群体相比,《古典悲剧》中的女性基本上都没有血缘关系,她们经由某种偶然的命运而落入黑暗的陷阱,而这种偶然的命运,却正是这些女性普遍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宿命。但是在这一宿命中,却有不屈服者的隐忍的反抗顺儿这一并非主角的女性为了拯救另外一位女性选择了死亡,通过这种自我牺牲,她完成了某种抵抗仪式:她像原谅母亲那样原谅世人的堕落,她独自走向通向死亡的回廊,用只有十九岁的年轻身体去填补深渊中那个阴暗的缺口。这是一则还没来得及展开的寓言,它的寓意是,面对无边又无望的阴暗,面对英雄(男性)的缺席,女性惟有通过自我牺牲来获得自我拯救。这种拯救的维度是多方面的,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拯救,一个女性对一段黑暗历史的拯救,一个女性对书写和讲述的无畏坚持。
即使在众多的小说中徐小斌都暗藏批判的锋芒,但让人惊讶的是,她始终有一种发自本性的隔绝能力,让她和那些过于残酷的历史存在保持必要的距离而不至于降格为一种悲情的叙述,事实是,即使在她最阴郁的小说里,也会出现大量如巴洛克风景画式的明丽色彩,这些色彩构成了她小说中最耀眼的一部分,带有绘画的质感和通灵性;在她那些巫妖一体的女性人物身上,往往又有一种少女式的天真和童贞,善与恶,美与丑,忠与不忠,奇怪地扭结在一起。徐小斌将这种天性发挥到了极致,并在其作品中构建了双重的维度,一种形式、叙述、修辞的轻和一种历史、现实和宗教的重,这两者并置而生,互为视域,在这个视域中,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被呈现出来。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反驳徐小斌的警句:女人写到最后并非一无所有,因为当写作成为一种天性和命运,它本身已经是最好的礼物。
2013.1.20于北京
2013.1.21再改
2013.3.4三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