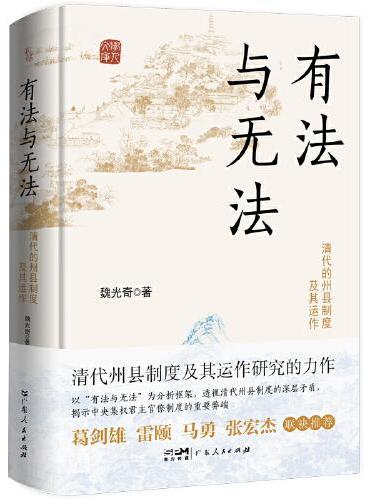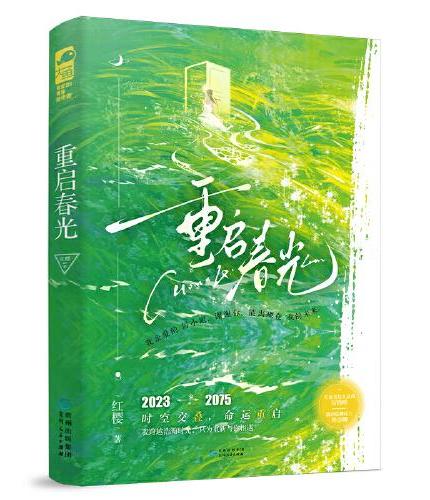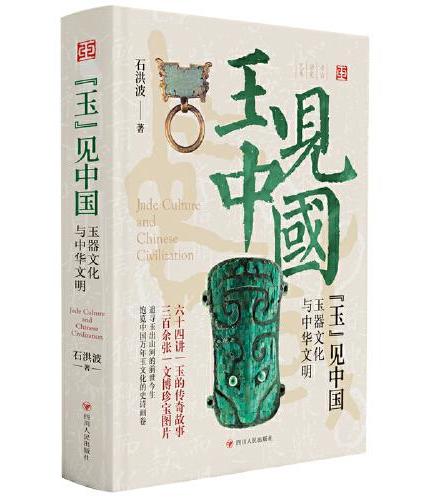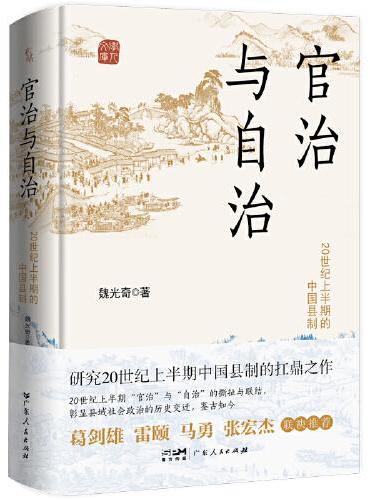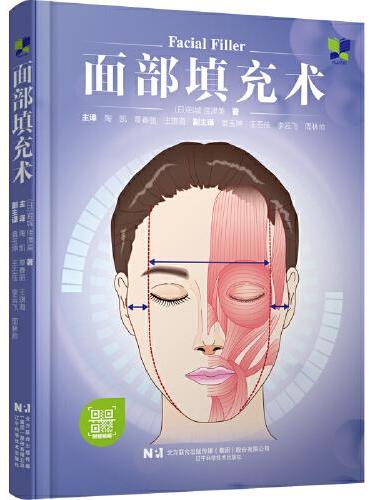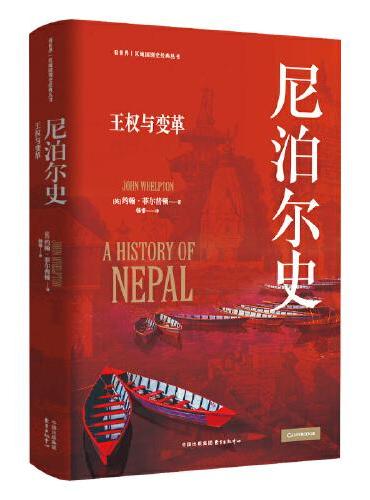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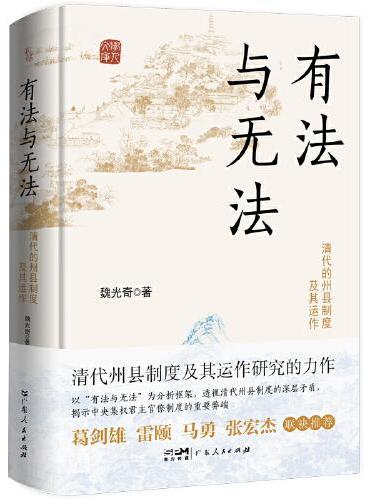
《
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 最新修订版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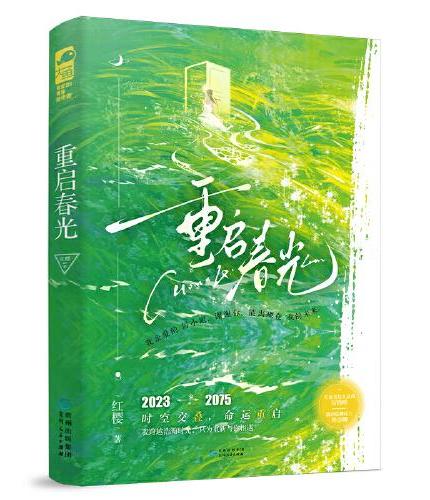
《
重启春光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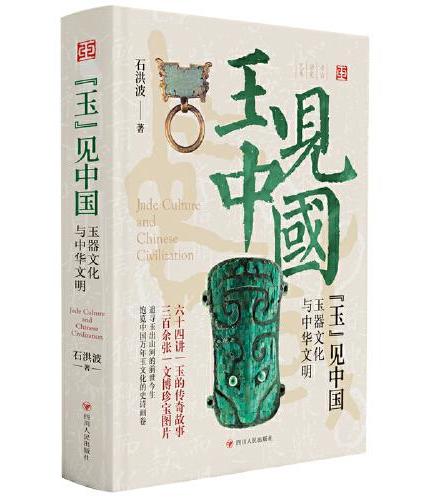
《
“玉”见中国:玉器文化与中华文明(追寻玉出山河的前世今生,饱览中国万年玉文化的史诗画卷)
》
售價:NT$
6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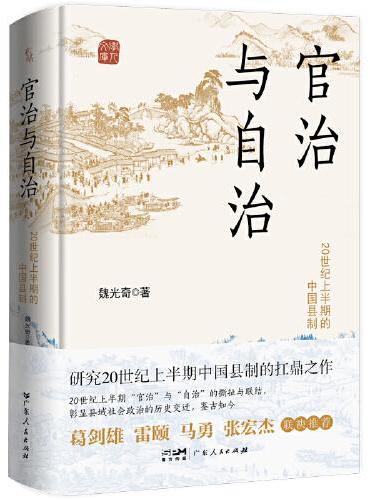
《
官治与自治: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最新修订版
》
售價:NT$
640.0

《
迈尔斯普通心理学
》
售價:NT$
7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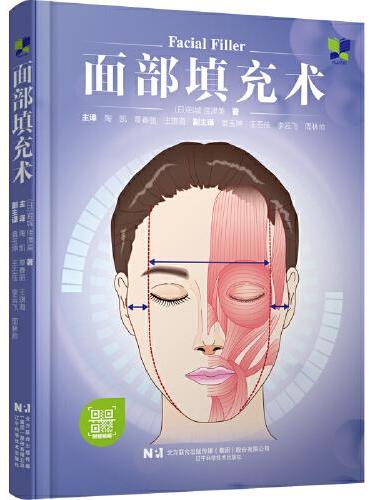
《
面部填充术
》
售價:NT$
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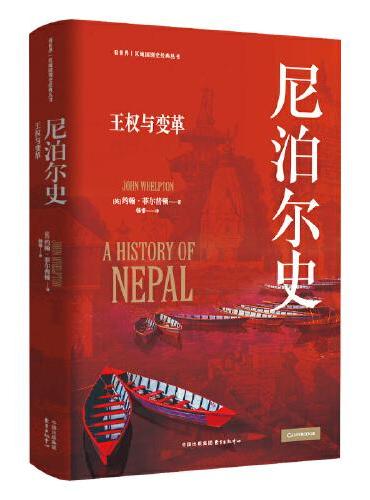
《
尼泊尔史:王权与变革
》
售價:NT$
430.0

《
战争事典085:德国人眼中的欧战胜利日:纳粹德国的最终失败
》
售價:NT$
499.0
|
| 編輯推薦: |
|
巴金所经历的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zui为迅疾的百年,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
|
| 內容簡介: |
|
巴金所经历的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zui为迅疾的百年。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概括巴金。有时他如电,如雷,如激流;有时又如阴云,如浓雾,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他为百年中国贡献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一个伟大作家的生命,永远存在于作品之中。巴金,永远与读者同在。
|
| 關於作者: |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4年到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湖北加油泵油嘴厂子弟学校教师。随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要方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黄苗子与郁风》等。巴金写意
引子
热情是火,
痛苦是云,
云与火的景象下,
走着一个真实的人。
这位老人,与世纪同行。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4年到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湖北加油泵油嘴厂子弟学校教师。随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要方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黄苗子与郁风》等。
巴金写意
引子
热情是火,
痛苦是云,
云与火的景象下,
走着一个真实的人。
这位老人,与世纪同行。
照片重叠,重叠起岁月沧桑,重叠起多彩人生。
他热情而真诚。热情是心中永远燃烧的火;热情是他作品的力量。他热爱读者,他说要把心交给读者,他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一代代读者,影响一代代读者。他真诚袒露心灵,无情解剖自己,把说真话作为晚年反省的核心。人们说:他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敏感而忧郁。生活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矛盾,感受痛苦。然而,痛苦是他的动力。没有痛苦,他就不会走上文学之路。忧郁,痛苦,把心中的激情烧得更旺。冰心说他:我看他在痛苦时才是快乐的。说得真好。
他坚韧而执着。一个瘦小的身躯,却充溢着巨大的生命力。生活坎坷也好,疾病折磨也好,从不会让他在命运前屈服。他的生命与思想同在,与文学同在。只要有可能,他一刻也不愿意停止思考和写作。他相信,作家的生命靠作品的力量来体现,而不是任何外在形式的打扮和炫耀。这是真正有价值的生命。
他便这样与世纪同行。
他便这样写下自己真实的人生。
门
这是新近落成的现代文学馆。从20世纪80年代发出倡议那天起,修建一个现代文学馆,集中展现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的历史,就成了巴金晚年最大的心愿。
病中的巴金,每天牵挂着它,期盼着它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变为现实。题写馆名,四处呼吁,审阅图纸
如今,这里的大门随时等待着它的构想者巴金前来推开。
现代文学馆的设计者很高明。他们在大门上设计了巴金的手模。今天或者未来的人们,都将与巴金的手触摸,在他的导引下,走进历史场景之中。
一扇非同凡响的大门。
一扇把文学巨匠与读者连在一起的大门。
一扇把历史与未来衔接起来的大门。
病中的巴金,多么想来到这里,用自己的手推开这扇门。哪怕不再能写一个字,哪怕不再能说出一句话,但他只要健在一天,他的心就一定与这扇大门连在一起的。他一定会在梦中走进这里。
一生走过多少路,一生推开多少门。
一扇门,可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
一扇门,可能改变过他的命运;
一扇门,可能留给他或者幸福或者痛苦的回忆。
这是巴金在上海武康路的家,从50年代初至今,他在这里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跨过大门,穿过草坪小径,走进客厅,走进书房,走进卧室。在这里,他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这是一个大舞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探望慰问,外国总统授勋,友人相聚,文革红卫兵野蛮的抄家、批判,灰溜溜地接受改造,妻子萧珊被迫害致死,诸多的荣耀、苦难、屈辱、困惑,从这座大门走出走进,也在巴金心里走出走进。
这座大门让巴金最难熬、最难受,也最难忘的日子是在文革中。
大门前发生的一切,折磨着巴金和妻子。
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口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这是巴金不堪回首的回忆。
妻子被罚扫街。
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只有走进这座大门,回到妻子身边,磨难中的巴金才会感到一点儿解脱。
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诉。
萧珊最终凄惨地死在医院,留下巴金一个人从这个大门里孤独地走出走进。
时间回溯。贵阳秀丽幽静的花溪公园。
相识相爱历时八年,巴金与萧珊终于在1944年5月8日旅行结婚从桂林来到这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一桌酒席,只是印上一份简单的旅行结婚的通知,寄给亲戚朋友。推开位于公园里的花溪小憩宾馆大门,这里便成了他们安安静静两人相对的地方。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黯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当年,满怀激情和热望,年轻的巴金走出了大家庭。如今,在滚爬摔打将近二十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他走向未来。
当然,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恐怕只有家乡故居的大门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常常到门房找听差、到大门口找看门人李老汉闲谈,其实是请他们讲讲各自的经历。
大门是童年巴金瞭望世界的窗口。
大门更是巴金认识封建大家庭的窗口。大院里的生活,对于他,简直就是噩梦。
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的、一时的人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
在这座大门里长大,睁开眼睛打量身边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让他最终成为大家庭的叛逆者,成为社会革命者,成为一个用笔来呼喊的战士。
故居的门,成为他的作品中屡屡出现的场景。
《家》《春》《秋》里的大门。
《憩园》里的大门。
说是没有留恋,这当然是巴金小说中人物的一种激愤。1941年,在离开家乡十八年后,巴金重返成都。他又走到故居的这条大街,再次以一种悲哀、以一种忧郁,细细端详变化了模样的大门。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九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前的遥远的旧梦。
时间总是不断地过滤情感,包括爱和恨,包括留恋与厌烦。中年后的巴金,老年后的巴金,谈到家,想到童年的大门,自然会是一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感受。
这扇门,毕竟决定了年轻巴金未来的道路。
三峡夔门。这不是通常所说的门。可是自古以来人们称它夔门。当年,年轻的巴金坐船离开家乡,就是跨越这道门,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未来。
他知道,走出这里,也就意味着走进如江水一般跌宕起伏的人生。
死
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
我自小就见过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给我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问: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
巴金从小就对死很敏感。一次次生命的毁灭,改变着他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巴金第一次注意到死亡,感受到死对自己心理的影响,是一只公鸡的被杀。那时他很小,是在四川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令。现在这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生长的地方,据说就是当年县衙门的所在地。巴金和父母便住在这里,与他相伴的有兄弟姐妹,也有一群鸡。
大花鸡、小凤头鸡、麻花鸡、乌骨鸡巴金可以叫出它们一连串的名字。他最爱的是大花鸡。
养鸡就是为了吃,小小的巴金还无法理解。眼见着鸡一天比一天少,眼见着自己喜爱的大花鸡也难逃厄运,巴金央求母亲留下大花鸡。大人笑笑,很不理解。
大花鸡最终被厨师杀了。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却让敏感的巴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深深的记忆。
让巴金对死亡敏感,对人的生命被蹂躏、被毁灭感到痛苦,是封建大家庭里的悲剧。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一个个熟悉的生命在眼前消失。可恨而可怜的祖父,可悲的叔父,可爱的用人,无辜的轿夫死亡让他震撼,死亡让他不能不鞭挞造成这些悲剧的制度。
一部激流三部曲,写出了一个个美丽生命被毁灭的悲剧。
鸣凤之死。
瑞珏之死。
梅之死。
蕙之死
高老太爷之死。交织着作者的爱与恨,生发出另外一种复杂的意味。
一次次对死亡的描写,成了巴金作品中的精彩篇章,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
改变巴金人生走向的却是意大利工人凡宰地、萨柯的死。
那是在1927年的法国。寂寞,孤独,感伤,因牵挂凡宰地、萨柯的命运而不再显得重要。他们因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在美国被捕,受到诬告而被判处死刑。刑期临近,全世界都在声援他们。留学巴黎热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也参与进去。他给狱中的凡宰地、萨柯写信。
我不再徒然地借纸笔消愁了。我坐在那间清净的小屋子里,把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全写在信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我给美国死囚牢中的犯人凡宰地写了一封长信。
狱中的凡宰地给巴金回了两封信。青年巴金为之兴奋。
然而全世界的声援没有改变凡宰地、萨柯的命运。他们被绑在电椅上处死了。巴金陷入愤怒和痛苦之中。
我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提出我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是我仍然无法使我的心安静。我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我的心情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面我写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三章,又写了一些我后来没有收进小说里的片段。
巴金此时写的就是他的处女作《灭亡》。《灭亡》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巴金,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文坛。他绝对没有想到,投身社会革命的热情和初衷,会因此而改变。
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将近八十年后,凡宰地、萨柯冤案在美国平反,他们的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他们生命的毁灭,意想不到地点燃了一个中国青年心中的文学激情,从此,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一个文学巨匠的诞生。
生
巴金这样说过: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从第一眼看到死亡的阴影那天起,巴金就更加珍爱生命,他一生探索着生的意义。他用笔,用一点一滴的身体力行,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一步一步向自己确认的人生目标走着。
对生命意义的最初教育来自母亲。
巴金把母亲称作我的第一个先生。母亲教他爱一切不管他们贫或富,母亲教他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亲教他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仆人巴金记忆中,母亲永远对他温和地微笑,让他感受爱的温暖。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爱是根底,一切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由此展开。
1937年,美丽的西湖,一条小船上坐着几个焦虑的男子。他们中有巴金。此行不是为了欣赏美景,而是为营救一个姑娘而来。几天前,巴金在上海收到姑娘的求救信。信中说,她读了巴金的作品,离开了家庭来到杭州,投奔一位亲戚。谁知她发觉这位亲戚却与庙中的和尚私下串通,她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她希望巴金假装她的舅舅来搭救她。
巴金一直在想用作品温暖读者,一直希望把心交给读者。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向一个弱女子伸出援助之手。
假舅舅成功了。他们一行人带着那位姑娘回到上海,把她交给了另外一位亲戚。他在用行动来体现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教育: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为此而问心无愧。
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
从母亲那里,从卢梭那里,从克鲁泡特金那里,从托尔斯泰那里,从许许多多思想家、人道主义者那里,巴金学会了如何认识生命的真谛,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
广东的这棵大榕树,因巴金的描写而出了名。20世纪30年代初,巴金来到这里,游览之后创作了那篇著名散文《鸟的天堂》,从此,这里的人们便称它鸟的天堂。在那次旅行中,巴金来到朋友们主办的乡村师范学校,与学生们举行了一次谈心会。看着这些年轻的学生,巴金倾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他不善演讲,但他的真诚仍然感动了学生。
他说到自己的生活态度: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严格地批判自己,忠实地去走生活的路,这就会把你引到真理那里去。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这正是巴金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态度。难免会有过失,难免会有缺点,但真实地做人是第一位的。文坛中人,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样拥有广泛的朋友,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样充满忏悔意识,在自我反省中完成人格的塑造。
坦荡而不掩饰,真实而不虚伪。这便是巴金。
1985年,年过八旬的巴金,收到了江苏某乡十位小学生的来信,他们向敬重的巴金老人询问寻找理想的问题。很巧,这与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次谈心会,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连接。
虽然年老体衰,巴金仍如当年一样对理想充满激情,甚至显得十分浪漫。他在与孩子们平等交流,实际上,他的一席话,可以看作他对自己漫长人生道路的历史总结。
还是那个真诚、热情、浪漫的巴金,还是那个用生命拥抱理想、拥有信仰的巴金。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承认自己人生的坎坷和艰难,但支撑他与命运抗衡、执着地走向生命终点的,永远是对理想的热爱和坚信:
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它有时离我很远,有时仿佛近在身边;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有时我竭尽全力,向它奔去;有时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就永远给我指路。
梦
无论年轻时,还是晚年,巴金总是处在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中。爱做梦,爱写梦也就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1934年他这样说:
近来我常常做噩梦,醒来后每每绝望地追问自己:难道那心的探索,在梦里也不能够停止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严酷地解剖自己?
不妨把梦看作是巴金的忧郁、敏感气质的外在表现。梦是清醒的延续,梦是心灵的反射。
1937年,巴金在上海梦见自己被判决死刑,应该是被押到一个岛上去登断头台。他却主动前往,一个友人陪同他。他被投进地牢,友人不知去向,整天听到的只有修建断头台的声音。他等待着死亡。一天,他被带出来,他看到天井里绞刑架已经矗立起来。他用憎恨的目光看着。突然,他看见了那位友人。她惊恐地叫着他的名字,眼里含着泪花。已经失望的他感动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居然还有一个关心他的人。他坦然走向绞刑架。
这个梦很长。最终,那位友人用飞机把他营救了出去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巴金没有说。不过,他说过这样一段关于梦的话:
我在生活里找不到安宁,因此才到梦中去找,其实不能说去找,梦中的安宁原是自己来的。然而有时候甚至在梦中我也得不到安宁。我也做过一些所谓噩梦,醒来时两只眼睛茫然望着白色墙壁,还不能断定是梦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实地感觉到的。但是等到心跳渐渐地平静下去,这梦景也就像一股淡烟不知飘散到哪里去了,留下来只是一个真实的我。(《梦》)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上海奉贤的五七干校,文革中巴金和上海文艺界的同行在这里接受监督改造。
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
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80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被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诵最高指示。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于是,在巴金这里,叙述梦不再是写作的一种技巧,也不是文学想象的补充,而是痛苦心灵的真实再现。
因为梦,他的心更敏感,也更充实。
对于晚年的巴金,梦无疑是一种生活的补充。重病缠身,行走不便,言谈困难,他越来越难于与社会交往,这样,他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任思绪飞翔。
晚年梦中不断见到萧珊,成为他们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场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病中的巴金。
|
| 目錄:
|
巴金写意 001
为电视专题片而作
永远的家,永远的爱 021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037
沈从文与巴金五十六年友谊漫谈
与冰心谈巴金 046
与巴金聊天 053
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072
读萧乾书简随感
巨星陨落,光还亮着 094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102
文革小报上的巴金 112
巴金的交代 123
与大众共享 127
《百年巴金》后记 132
《巴金研究论稿》序 135
德文版《巴金小说选》序 140
《随想录》三十年 146
思想史上的《随想录》 150
《随想录》就不如《思痛录》? 160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巴金 16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