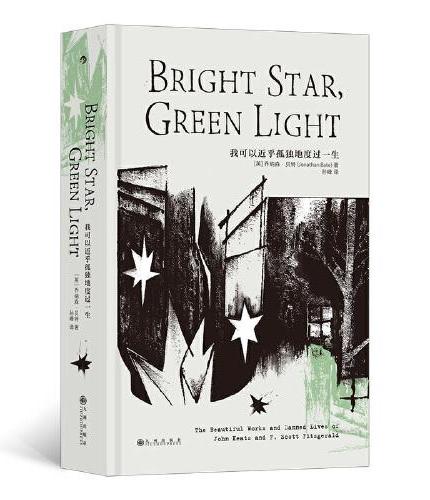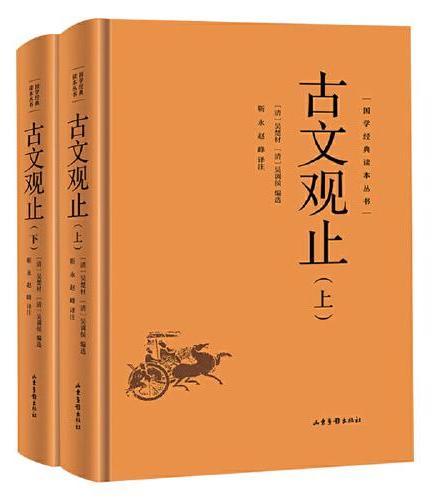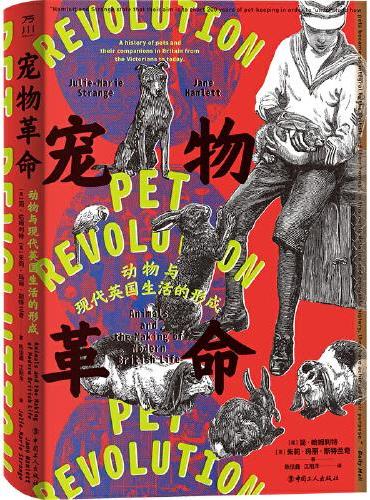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量价关系——透视股票涨跌脉络
》
售價:NT$
340.0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
《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
》
售價:NT$
295.0

《
复原力
》
售價:NT$
345.0

《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9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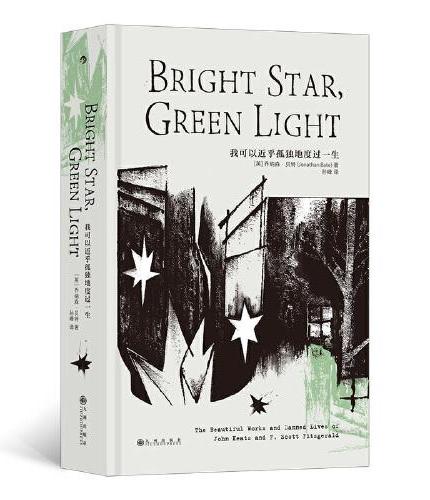
《
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
》
售價:NT$
440.0

《
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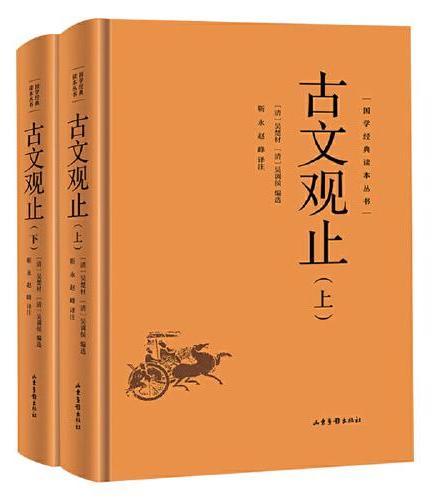
《
古文观止(上+下)(2册)高中生初中生阅读 国学经典丛书原文+注释+译文古诗词大全集名家精译青少年启蒙经典读本无障碍阅读精装中国古代著名文学书籍国学经典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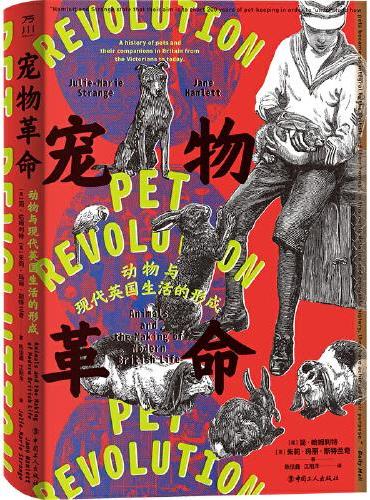
《
宠物革命:动物与现代英国生活的形成
》
售價:NT$
360.0
|
| 編輯推薦: |
|
太阳鸟文学年选,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开始创建的文学品牌,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丛书主编,本套丛书大体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六大分卷,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的厚望,每年都将发表的原创文学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这些选本追求精品,但更多体察了民众的心理,内容贴近大众化的生活,行文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风格。至2017年,这套文学年选已经连续出版了20辑,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这套文学年选,也将在大众读者的支持与陪伴下、逐步深入,越走越远。
|
| 內容簡介: |
中篇小说的选本,较多地关注了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心理冲突的作品。
二十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
|
| 關於作者: |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林建法,男,汉族,1950年11月出生,福建连江人。1982年1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91年1月始为《当代作家评论》法人代表,主持编辑部全面工作至今。2000年5月为主编。先后荣获1995年辽宁省十佳编辑、1996年东北三省优秀社科编辑称号、2006年第四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2006年辽宁省首届辽宁期刊人奖、2006年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 目錄:
|
001 花满月 方 方
032 红豆生南国 王安忆
071 水 墨 尤凤伟
119 大乔小乔 张悦然
155 一 天 田 耳
223 在豆庄 方格子
|
| 內容試閱:
|
悄悄的,不知不觉的,又是一年沉落到永恒中去了,好像一滴水落在大海里!1 别林斯基回望一八四五年的俄国文学,以如诗的语言开篇。2017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如果以文学史为度量,几近滴水入海。但检阅年度作品未必没有意义,还是别林斯基说的,当前正是归结过去、筹划未来的时候2,哪怕在后人眼中,这项工作如同王安忆小说中所言,海湾已成回音壁
1
198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的专家们联合推出《新时期文学六年》,如同一部微型的文学断代史,对1976年至1982年的文学流程作基于一定的研究之上的鸟瞰与评论。该著中篇小说的章节内,以三页的篇幅介绍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坛新秀王安忆。当时王安忆发表了《尾声》《归去来兮》《流逝》等六部中篇,作者以单纯的、善良的心和敏锐的目光,去感知生活和探索人生的命运,用她的客观、冷静、细腻、含蓄的笔触写她独特发现的生活,但如果在她固有的风格中增添一些炽热的因子,其作品必将加强那种如同醍醐灌顶的撼人心灵的艺术力度1。抚今追昔,重读上述评价,着实让人感慨。如果站在1983年的时间节点上展望未来,估计很少有人会预见,日后王安忆会写出《小鲍庄》、三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天香》这是一位创造力多么丰沛的作家,永远向着未来敞开不可预见的可能性。2016年,她以《匿名》登临抽象叙事的巅峰,而2017年又通过以《红豆生南国》为代表的三部中篇,重回日常生活叙事的绵密与细水长流。
不过且慢,上面这样的说法也不稳当,似乎强行将形上与形下、超越与日常、抽象与具体、历史社会与个人生活断为两截,这并不符合王安忆的创作图景。伍尔芙早就提示过,现代文学日益朝着散文的方向发展,须知散文是如此地位低下,因为能够走到任何地方去,没有一个地方是那么低下那么污秽那么简陋,它能够用它长长的粘胶似的舌头把事实的最微小的碎片舔干净。然而伍尔芙追问散文是否能够说出那些巨大的简单事情,比如我们对于像玫瑰和夜莺、黎明、日落、生命、死亡、命运这样的事情所怀有的情感。我们并非完全忙碌于个人的关系,并非我们的所有精力都被用于谋生。我们渴望获得思想、获得梦想、获得想象、获得诗的意境。在散文与诗意之间,我们是否能够获致一种中道、均衡的现代小说,它长长的粘胶似的舌头扫向人世间的泥沙俱下,但同时又可以对生活的某些重要面貌获得一个更大的视野2。
《红豆生南国》第三章,写主人公他与劳拉母亲见面,从三件头洋服的装扮、半岛酒店的环境,到谈话时你来我往的词锋这一路写来,巨细靡遗。然后写见面后心情失落的他,暴躁地脱下西服外套,扯去领带,坐上海边的水泥台,这时,风吹着脸,渐起凉意,平静下来,从先前密密实实物质的、散文的世界中超脱出来,举目望去,开始抒情(不要忘了,他本是文艺青年,而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填地日益增阔,地上物堆垒,天际线改变,变成几何图形,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此刻还封闭在新型建材的灰白里。汽笛声被夹岸的楼宇山峦吃进去,吐出来的是回声,海湾已成回音壁。这是香港吗?他都不认识了!他似乎身在异处,连自己都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人当年随养母偷渡香港,最初的落脚点即新填地街,那是五六十年代的晦暗困顿岁月,但晦暗中也有百废待兴的勃勃生机;而现在已是世纪末,天际线被拔地而起的楼宇不断切割、改变,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那是人人惯见的繁华夜香港。可这还是他的香港吗?往昔与今日之间,终于化作沧海桑田的一声喟叹。他前番还斤斤于世俗儿女情,一转身就生出近乎子在川上般的省悟这是王安忆的艺术手段,每每从市井烟火气的散文世界中兀地转上一层,透出精神性的庄严。
王安忆的小说有一种整体性,接近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包含辩证的整体观:生活环境、社会和个人都不占据优先地位,而彼此之间又有着内在统一,在完全是个人的领域里,整体生活恰恰显得最为重要。我们全力以赴地关注整体生活的每一方面,而价值的中心却总是落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不是任何一个孤立的人,而是构成整体生活实体的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在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持续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小说的形式才真正成熟起来。然而威廉斯指出,在1900年之后,现实主义传统分裂成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 在社会小说中,有着对整体生活亦即作为聚合体的人群的精确观察和描写,但因为欠缺血肉丰满的人物,整体生活也往往沦为抽象的存在;而在个人小说中,有着对单位个体的精确观察和描写,但因为社会总是割裂般地外在于人物,从而认识不到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地影响到最内在的个人经验。总之,以上两类小说中,个人和社会被割裂成了截然相对的两极。想想当下的中国文坛,触目可见的不就是这两种类型的小说?然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努力是为各种关系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努力是全体性的,可以认为它既是个人的努力也是社会的努力,是在实践当中学习如何扩展各种关系。有着伟大传统的现实主义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因为它具体地展现了那种生气勃勃的互相贯通1 王安忆小说的整体性,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生气勃勃的互相贯通,诚如论者所言:在五十年代南来难民的困苦生活,六七年的反英抗暴,八四年签署的中英协议,九七金融风暴与楼市崩盘,究竟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香港回归之外,对于香港左翼运动的浮沉,报纸副刊文化与本土文艺的观照,皆以更加隐晦的方式编织进来。这些绵密的人文历史,与主人公的少年心事和罗曼蒂克消亡史暗中精密贴合,读来让会心者惊喜;但又能在讲故事的表面做到不着痕迹。1《红豆生南国》写一位文艺青年,在被刻板目为文化沙漠物质丛林的香港社会中的有情一生。在个人与社会背景之间,既有艰难的损耗、磨合,对应一段香港左翼从广场隐入民间的心史;也有如盐入水般的融合,正因为有一个个他,才支撑起市井社会的情义天地。小说卒章点题,他来到台南丛林中,此生的恩欠愧受困囚最终化作相思,其实可以再直截了当地化作一个字报,这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2。我们读到小说结尾,再回想起小说中时常出现的语句(自己何德何能,得这一份馈赠),不难明白《红豆生南国》的主题便是恩欠与报还,由此组织出来的伦理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小说起首第一句是身前身后都是指望他的人),要他担负义务。联系到小说中地域的流转(大陆,中国香港、台湾,为什么最后要跑到台湾才明白相思呢?),这义务,是否已可从个人过渡到家国认同了?
在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作家中,哪一位接近前辈王安忆的气象?这个提问或许显得粗率,但我还是愿意给出一个答案张悦然。当年和张悦然一起横空出世的那批少年成名的作家,有的早已转行,有的在文坛销声匿迹。张悦然不同,她没有在挥霍完青春才气之后小成即堕,在写作历程的关键节点上,总能再提起一口气,奋力上出,和王安忆一样,张悦然也是长跑型选手。我认同大多数论者的看法,以长篇《茧》、中篇《大乔小乔》为标志,张悦然的创作发生了某种转型;但我并不认同那种在《茧》中只看到文革、在《大乔小乔》中只盯住计划生育的读法。卡夫卡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大多数作家都卷入了社会事件之中,卷入了外部世界的活动。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成为见证,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这种东西1。写作的成熟、作品的优秀和题材选择没有关系。小说挂靠重大历史事件,未必能给文学自动加分,甚至处理不慎,一来会沦为上文所引分裂的社会小说,二来容易限制住作家的创造力,如同布罗茨基认为,巨大的悲剧经验、叙述一个大规模灭绝的故事,往往会限制作家的能力与风格,悲剧基本上把作家的想象力局限于悲剧本身,削弱了,事实上应该说取消了作家的能力,使他难以达到对于一部持久的艺术作品来说不可或缺的美学超脱。事件的重力反而取消了在风格上奋发图强的欲望2。计划生育也许比不上战争的酷烈惨重,但作为一项得到严格执行的基本国策,显然影响到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样具备事件的重力。以此而论,我认为《大乔小乔》实则比《茧》更为出色。《茧》中的文革,如同小说中那枚钉入人脑的铁钉,还只是符号般的抽象的存在。而计划生育所引发的原罪与宿命、荒诞(多余的人)与错位(合法生的姐姐死了,不合法出生的妹妹倒是活下来),通过张悦然与事件重力的美学搏斗,如盐入水般化入小说内在的艺术构造。
最让人动容之处,莫过于乔琳逝后,许妍躺在乔琳床上,发出可以撤销那个愿望吗的忏悔,以及最后的洗心革面(她想,现在她有机会做另外一个人了)。张悦然在《大乔小乔》中拒绝任何来自外力的救济,权贵阶层的良心发现无法挽回乔琳的生命,而法制建设又总是迟滞(所以小说中人才会说犯不着打官司,这种事找对了人,就是一句话的事),不借助于任何外在的、客观力量的解救之道,而执意地内在化,磨难在此,救赎也在此。从先前的生冷怪酷3,走到今天对生活中的款曲委婉有更复杂的理解,对人性幽微的皱褶有更温厚的体贴与善意相比于题材的转型,我更愿意将此视作张悦然的成熟。
|
|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