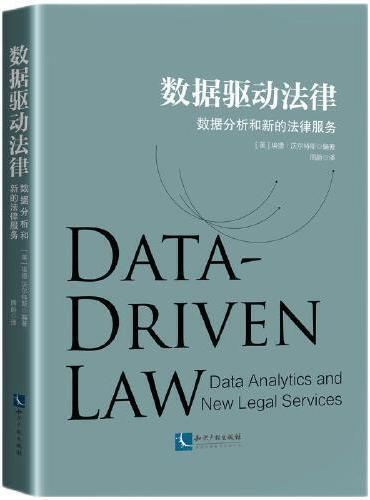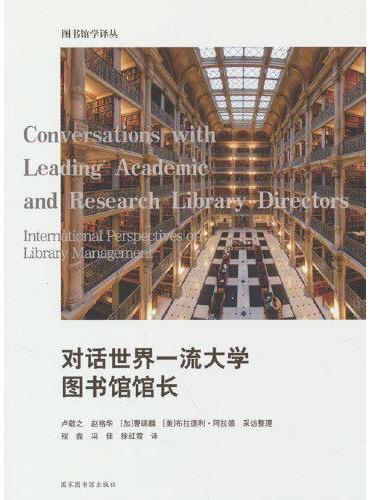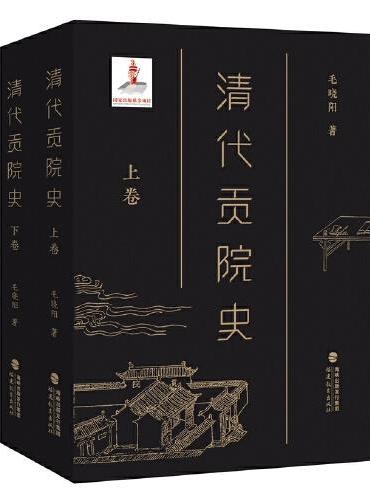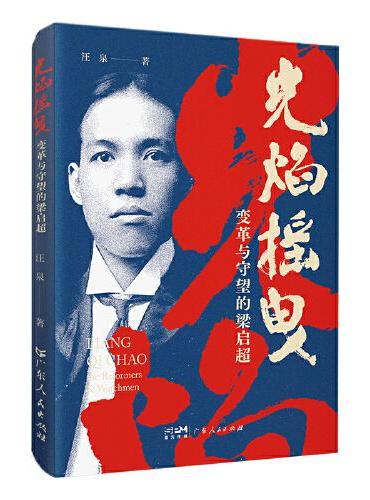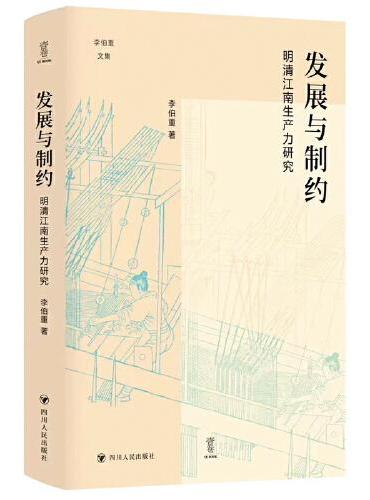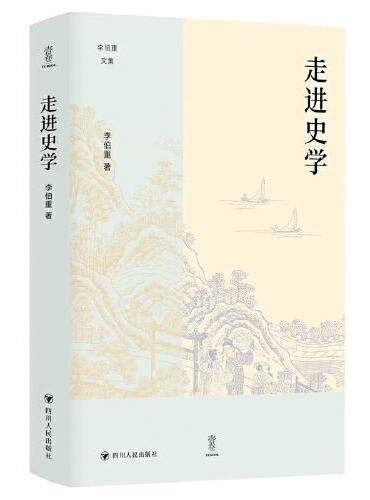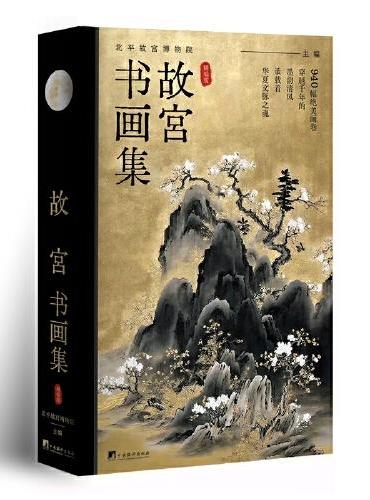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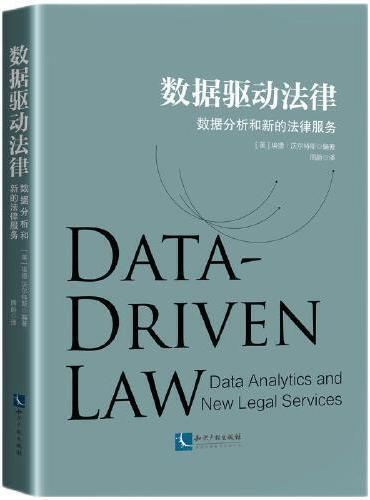
《
数据驱动法律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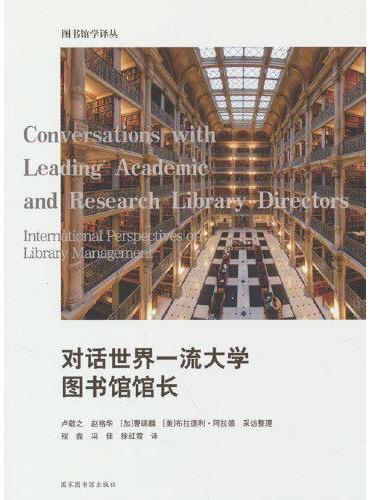
《
对话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馆长
》
售價:NT$
995.0

《
揭秘立体翻翻书--我们的国宝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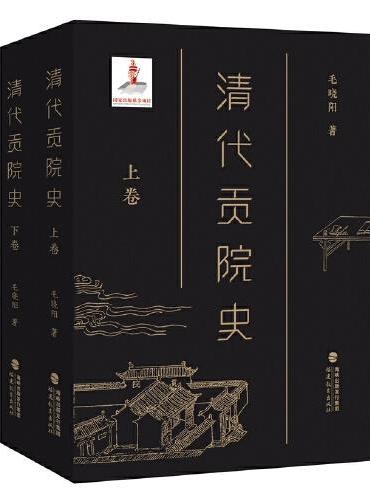
《
清代贡院史
》
售價:NT$
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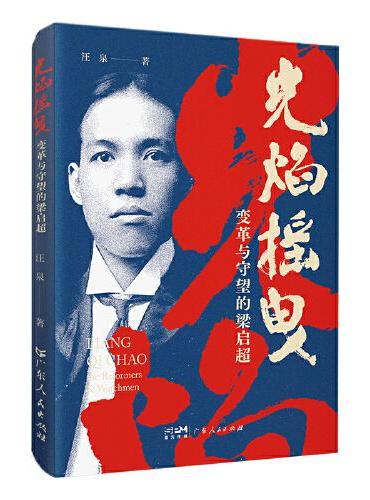
《
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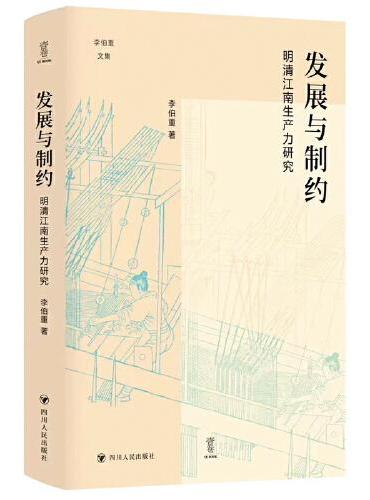
《
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壹卷李伯重文集:江南水乡,经济兴衰,一本书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
》
售價:NT$
4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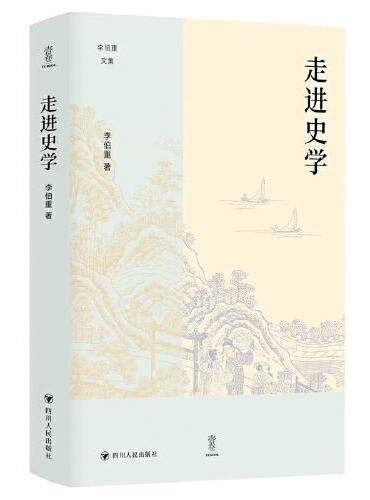
《
走进史学(壹卷李伯重文集:李伯重先生的学术印记与时代见证)
》
售價:NT$
3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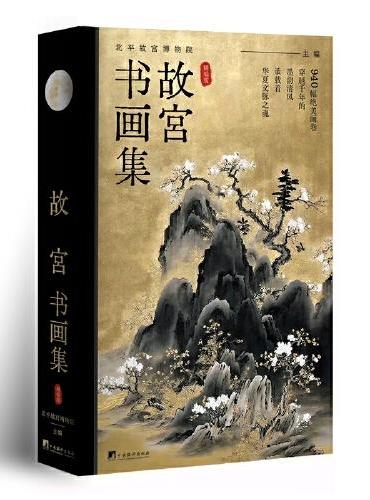
《
故宫书画集(精编盒装)版传统文化收藏鉴赏艺术书法人物花鸟扇面雕刻探秘故宫书画简体中文注释解析
》
售價:NT$
1490.0
|
| 編輯推薦: |
|
《民主的古代先祖:玛里与早期集体治理》通过考证出土于古玛里王宫遗址的3000多封书信文本剖析了古代近东的政治传统。这些书信向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参与者,他们生活于大王国、小王国、抑或各类部落城镇之中。玛里古代文献证据的特殊价值在于其部落组织的视角,玛里王辛里-利姆首先是一位部落统治者,玛里既是其执政基地,又是其声望之源。这些古代政治传统与希腊前民主时期的政治形态本质上并非不同,为我们确认爱琴海古典时期与更古老的近东之间的文化连续性提供了zui新证据。
|
| 內容簡介: |
|
《民主的古代先祖》一书从玛里文书档案、部落城市关系、国家与麻敦、集体治理方式等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古代政治世界图景。全书逻辑严密、论据充足,涉及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包括考古学、早期中东和近东史,以及政治与社会史。本书中译文忠实、严谨、流畅和自然,且无论是注释、译注还是索引等内容,均极具学术前沿性,为民主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来源等研究做出了关键贡献,相信能给后来学者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参考。
|
| 關於作者: |
作者 丹尼尔E弗莱明,纽约大学斯格鲍尔希伯来语和犹太学系副教授,美国东方学协会会员,美国东方学研究院会员以及圣经文学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希伯来圣经和亚述学研究。
译者 杨敬清,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已出版译著《古希腊简史》。
|
| 目錄:
|
导读
民主不是希腊的专利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玛里文书档案
第二节
玛里历史概况
第三节
关于重要术语的注释
第四节
玛里文书档案与政治史
第五节
基于文本的研究:研究方法说明
第二章
辛里利姆的部落世界
第一节
游牧民与亚摩利人的部落组织
第二节
部落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西米莱特伽羽分支和亚米纳特里穆部落
第三节
部落与城市的领导者:为玛里王国效忠的头领
第四节
牧场首领
第五节
帐篷居民哈奈人
第六节
另一个部落联盟:亚米纳特
第三章
古代国家和麻敦(mātum)国
第一节
城市生活与古代国家
第二节
麻敦:公元前两千纪初区域政治的基本单位
第三节
麻敦的细分:行政区
第四节
不受政体限制的人口术语
第五节
辛里-利姆与帐篷居民王国
第四章
集体与城市
第一节
玛里文书档案中的城市
第二节
集体政治传统
第三节
城市或者王国的集体面貌
第四节
长老们
第五节
头人们
第六节
表示议事会的词语
第七节
伊玛、图特尔和乌吉斯:具有强大集体政治传统的古代城镇
第八节
公元前三千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玛里
第九节
关于集体权力的解释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玛里文书档案呈现的政治世界
第二节
民主的古代先祖
古代词汇表
专有名词表
索引
参考文献
|
| 內容試閱:
|
导读
民主不是希腊的专利
阮炜
一个谬误存在已久,流传甚广,那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代民主或democratia只是古希腊才有的一种独特现象,而其他民族的早期政制都是专制主义。然而这是一个谬误,一个并不难证明的谬误。可是晚至1980年代,西方学界仍有人坚持希腊民主独一无二。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丹尼尔E弗莱明(Daniel E. Flemming)本着实事求是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在其《民主的古代祖先:玛里与早期集体治理》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即古代两河流域不仅存在着民主,而且在时间上比希腊早一千多年。在其论述中,玛里王国的政制也许并非十分明显地具有人民大会、民众法庭一类雅典式的制度安排,但非个人专断的集体决策或协商决策机制是确然存在的,而由资深者组成的议事会来决定共同体重大事务的做法,更是一种标准的希腊民主制度。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实际上,氏族形态的民主并非某个民族所独有,更不是希腊人的专利,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19331934年,安德列帕罗(Andre Parrot)领导的一个法国考古队开始对两河流域西北部的玛里王国遗址Tell Hariri进行了发掘。1935年,一座巨大的宫殿被发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部分已知玛里王国档案已经出土。激起学界极大兴趣的,是大约两万件楔形文泥板中的三千多封多书信(用阿卡德语写成,该语言为通行于古代两河流域东部的一种闪米特语)。其中不少是玛里国王与其他地区或城镇的统治者的通信,更有高级官员、地区总督、将军和部落首领写给玛里国王的数以千计的报告。
这些通信和报告提供了有关公元前18世纪早期两河流域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情况,其中就包括大量有关古玛里地区集体政体(collective polities)的情况。弗莱明《民主的古代祖先》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即便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政体已然在当地产生(毕竟两河流域享有一个适合农耕的大型陆地板块,很容易开出这样的政体),民主性的集体治理仍然是两河流域西北部乃至整个两河流域的通行的政治模式。
也就是说,在实际政治管理模式上,被很多西方人视为专制主义典型的东方帝国实行的是双轨制:一方面是帝国式的权力集中,或者说,各地方城镇或部落统统臣服于一个中央王国,有义务向王国统治者纳税并提供军役;另一方面各地方城镇、部落或小王国依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其内部运作并非采用权力集中于个人的专制主义模式,而总体上遵循了一种以共同体意志为转移的集体治理原则。
这种看法有何具体依据?作为一个专治古代两河流域史的学者,弗莱明给出了语言、宗教、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证据。
一个极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者说证据,是专有地名GN(Geographic Name,地理名称)加上词尾ites以构成诸如Imarites(伊玛尔人)、Tuttulites(图图尔人)或Urgisites(乌尔吉斯)一类的词。这种用法的出现频率极高。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出现频率不太高但十分相似的表达法,即the sons of NG,即专有地名加上儿子们。例如the sons of Imar即伊玛尔的儿子们,或the sons of Tuttul,即图图尔的儿子们。玛里地区的人们用这两种表达法来表示一个城镇、部落在与毗邻的城镇、部落的战争、和平或冲突中的集体行动。
这些表达法虽能表示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却并不能够明确表示该共同体的集体决策行为。从出土文献看来,进行集体决策的人常常是长老们。长老并非头衔,更不表示任何官职,而只泛泛地指共同体的资深者和年长者。他们不仅集体决策,也代表城镇或部落进行一般的对外交涉,尤其与西姆里-利姆(Zimri-Lim)的中央王国的代表交涉。跟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样,这里的长老除对外交涉外,也负有司法和宗教职能。
然而地名加词尾ites最多只表示一个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及其集体行为,长老多用来表示代表一个共同体进行对外交涉的资深者,而更能确切体现集体治理原则的,既不是地名加词尾ites,也不是长老,而是塔赫塔蒙(tahtamum)议事会。这种议事会只见于幼发拉底河中游河谷的伊玛尔镇和图图尔镇文献中。由于证据不足,其包容程度到底多高仍不清楚,但它是一种具有较大代表范围的集体性的决策机制,却没有疑问。
从一封图图尔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头人拉那苏姆(Lanasum)召开一次塔赫塔蒙会议之后,该镇的儿子们决定提供三十名人员参与当地的治安保卫工作。从设好的座位或席位来看,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所以塔赫塔蒙应是一种长老议事会之类的机构。
从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西姆里-利姆的中央王国想以掳掠罪逮捕一些图图尔人时,却发现不通过塔赫塔蒙会议,就根本办不到。从另一封信中还可以看到,西姆里-利姆想要图图尔人提供劳役,但被图图尔头人以人手不足为由拒绝了,所给的解释是:我召开了塔赫塔蒙会,跟他们讲了此事,但他们不从。更有证据表明,伊玛尔镇和图图尔镇召开这种会议是自主行为,而非出于强迫。
除塔赫塔蒙议事会外,文献中还常出现puhrum和rihsum这两个表示会议的名词及相关动词形式。后者尤其被用来指镇与镇(或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协商或会谈(talks)。
此外,在玛里地区,围绕伊斯塔尔女神节的一系列祭仪也有强烈的团体色彩。祭仪包括伊斯塔尔庆典本身、拉蒙姆(ramum)祭礼(以一块纪念性石头为标志)、奈加尔(Nergal)祭礼,以及其他祭礼。这些活动鼓励全体成员参与,不仅仅有缅怀国王的祖先的意思,更有缅怀整个共同体的祖先的意思。节日的主要庆祝活动被认为最初是由共同体的儿子们即全体成年男性发起。这完全可以视为集体治理政制在文化意识上的表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主的古代祖先》并非只讲公元前18世纪早期两河流域西北部玛里地区的集体治理传统。从该书引用的其他研究成果来看,集体治理的政体并非局限于18世纪早期两河流域西北地区,其时间和空间范围要大得多,可以说存在于文明萌生以后整个两河流域和古叙利亚社会。
弗莱明提到,雅可布森早在1943年的研究便表明,在苏美尔(位于两河流域东南部,这里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存在的文明为最早的人类文明)时期,各城镇中心便已开出了这样的政治样式:其最高权力并非被少数精英所垄断,而不论财产、地位和阶级,掌握在所有自由的成年男性成员手中。此即雅可布森所谓原始民主。
另据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出现了强大的民间贸易力量,有商人把锡和纺织品运到今日土耳其地区贩卖,以换取黄金白银。经济力量往往意味着政治力量,拥有雄厚财力的商人很可能也要分享政治权力。另外还有证据表明,议事会一类机构不仅裁决案件,还有立法甚至行政的职能。
里查德布兰顿及其同事有关古叙利亚(古代叙利亚地区很大,除现叙利亚版图以外,还包括向伊拉克北部、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北部的研究(1996)也很值得注意。他们认为该地区一直以来有着一种强大的集体决策传统。这种传统沿自氏族制度,但晚至前3000年至前2500年之前(此时国家已经产生),仍在国家而非氏族部落的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序和跋。从中可以看到,巴比伦王国最高统治者汉谟拉比不仅是一位君主,也是王国内各主要城市及其神祇的看护者。这些主要城市包括他刚刚从西姆里-利姆手中夺取的玛里。《法典》给人这样的印象:巴比伦国王竭力要在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小王国、城镇或部落间建立广泛共识,因此与其说汉谟拉比是一个令人畏惧、至高无上的征服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受欢迎的神遣的保护者。
然而两河流域早于希腊一千多年便有民主,并不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看法;而民主不是希腊人的专利这一点,也不是什么伟大发现。早在《古代社会》(1877)中,摩尔根便基于人类学规律否定了希腊独特论。他认为在国家形成之前的原始条件下,氏族民主是古代人类群落普遍实行的制度,易洛魁人、阿兹台克人甚至有发达的前现代民主。
易洛魁人的国家或部落联盟由五个地位完全平等的同宗部落组成,虽统辖在一个共同政府之下,但各部落内部事务均由它们自行处理。联盟设立一个首领全权大会或联盟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各部落选举产生的五十名首领组成,名额分配有限制,但其级别和权威是平等的。这与前5世纪雅典十部落各选五十名代表轮流主持五百人政务会相似。
在联盟大事上,首领全权大会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投票,每个部落都可以对其他部落的动议投反对票,但各个部落在投票之前必须举行一次内部会议,也可能以投票的方式来做出在全权大会上持何种立场或如何投票的决定。联盟层面的公共法令必须得到联盟会议的一致通过方才生效。任何人都可出席全权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讨论公共问题,但最终决定权却在大会。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至于阿兹台克人的民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国家或部落联盟层面的酋长会议。这是一种随氏族产生的集体决策机制,代表各氏族中的选民,自古以来就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统治机构。
像希腊城邦有军事统帅巴赛勒斯那样,阿兹台克联盟设有吐克特利即军事酋长的职位。吐克特利是酋长会议的一员,有时被称为特拉陶尼或议长。出任此职者由选举产生,也能通过选举罢免。这意味着,最高军事权力仍掌握在人民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吐克特利在战场上的权力虽很大,但重大战略决定则仍由酋长会议决定。
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一书中便记载,前8前4世纪的迦太基便实行与希腊相当的有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民主。亚氏固然对贵族政体情有独钟,但在他笔下,迦太基政体不仅是一种选贤任能的良好政体,而且是一种集贵族制、民主制和寡头制优点于一身的混和政体;当偏离走向民主政体时,人民大会的权力非常大,即便王者和长老两方面意见一致,也有权将其意见抛在一边,自行做出最后的决断;甚至人民大会任何成员都有权反对王者和长老提出的议案。今日标准看,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对文革仍然心有余悸,因此有一种倾向,即不承认19世纪以来人类学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承认中国史籍中明明白白记载的事实,而一口咬定夏、商、周早期国家全都是专制主义,全然不顾夏之前曾长期存在禅让制。
只要不拘泥于形式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而是将民主理解为一种协商和分权机制,或一种集体性质的决策传统,而非一种个人专权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则不仅早期华夏根本不缺乏民主,而且晚至春秋早中期,议事会、人民大会之投票表决意义上的氏族民主仍然存在于华夏世界,尽管很可能没达到前5前4世纪雅典式民主的激进程度。
儒家强调尊卑上下,君臣秩序,但即便在《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之类被视为上古文献的文典中,也不难发现华夏早期国家统治者聚在一起,和谐平等地集体决策的记载。从这些文典中,可以看到他们召开政务会,畅所欲言地商讨邦国大事;看到他们审慎考察、议定共同体最高职位即元后继承者的人选,用心良苦地举贤任能;议事者们表达自己意见时无需看帝之脸色,而帝之采纳他们的意见也并无居高临下之意。这难道不可以视为一种协商民主?
以上只讲到汉族的古代民主。我国少数民族有没有他们的民主?
当然有。晚至20世纪初,鄂温克人仍保留着氏族形态的原始民主:凡属公社内部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要由乌力楞会议来商讨和决定;会议主要是由各户的老年男女所组成,男子当中以其胡须越长越有权威。很明显,这里的乌力楞会议就是长老议事会,是一种许多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过的典型的氏族民主机构。
凉山彝族社会的民主更值得注意。1956年民主改革以前,凉山黑彝社会明显存在氏族形态的民主:
每个家支都有数目不等的头人,彝语称为苏易和德古。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或任命的,因为他们精通习惯法,善于权衡阶级关系和家支势力的消长,所以他们被黑彝奴隶主拥戴出来不论苏易和德古,如果排解纠纷一旦显出不公允,就会失去威望,也会失去头人的地位。头人没有固定的薪俸,也没有高踞于一般家支成员之上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也不世袭家支除头人外,还有家支议事会。议事会分为吉尔吉铁和蒙格两种。凡是几个家支头人的小型议事会,或邀请有关家支成员商讨一般性问题的会议,称为吉尔吉铁;家支全体成员大会称蒙格。蒙格由黑彝家支中有威望的头人主持,与会者都可以发表意见。当发生争执时,头人和老人的意见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凡经会议决定的事项,家支成员都得遵守。
事实上晚至1950年代中期,凉山彝族社会不仅仍有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议事会即吉尔吉铁,甚至仍有完全意义上的人民大会或公民大会即蒙格大会。从每个家支有不止一个头人和与会者都可以发表意见来看,召开蒙格大会时,家支成员的参政程度完全达到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激进民主中人民大会的水平。
所以应当承认,在现代资产阶级和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较小的政治单位开出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共同体 -- 由氏族而部落,则部落而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由较小的早期国家而较大的国家,直到最终开出跨地域、跨文化的地缘共同体或超大帝国以因应政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求得越来越大范围的和平与安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意味着越来越高水平的政治整合,而更高水平的政治整合又意味着个人和较小社群必须向国家交出越来越多的自由。这当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去(氏族)民主化过程,一个从较低社会发展水平到较高社会发展水平演进的过程。
然而,在18世纪末以降的欧洲,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民主迅猛推进,致使欧洲人将现代民主意识形态化,以为只有欧美样式的民主才具有普世性,才是唯一正确或正宗的民主,并且顺带衍生出一种罔顾事实、非常片面的古代民主观。清末民初,似是而非的欧美民主观播散到中国,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持续至今。
因时代局限,五四一代人汲汲于救亡图存,来不及深思西方民主观,来不及详察古典时代直至19世纪末欧美民主话语的历史背景和实质,便将其全盘接受,以至于流毒至今,很多人仍分不清真假是非。现在,是时候纠正谬误了。
1933至1934年间,由安德烈帕罗特(Andr Parrot)领导的一支法国考古队对古玛里(即哈里里丘,Tell Hariri)遗址开始了考古挖掘工作。1935年他们发现了一座巨型王宫,并很快挖掘出了大量的楔形文字粘土书板及碎片(Margueron 1997,143)。虽然绝大部分已知的玛里泥板文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被发现,但帕罗特于战后又重返该考古现场,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74年。最近几年的考古挖掘在让-克劳德马古隆(Jean-Claude Margueron)的主持下进行,对该遗址的挖掘至今仍未完结。
像Tell Hariri(哈里里丘)这类地名中的tell一词通常被称为城,但是使用此称谓需谨慎,因为我们目前对其所包含的具体意义仍然一知半解。古玛里城由呈三分之一弧形的土墙围合,距离今天的幼发拉底河航道大约3至4公里,属于该河流泛滥平原的一部分。出自古玛里的所有楔形文字书板几乎均属玛里历史上最后几位国王统治的五十年间,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元前18世纪早期。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出自这一历史时期的玛里遗址大多显示为王室和仪式服务的建筑遗迹,其中包括行使管理职能的主王宫,国王的妻妾们居住的后宫,各式各样的庙宇,以及执掌大权的玛里官员们的官宅。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使用,但古玛里城的某些部分似乎从未动工兴建,严格意义上的住宅区至今尚未被发现。未来考古挖掘的最新成果必会令如今的妄下结论者难堪,不过就目前来看,我们可以断言古玛里城的土墙之内似乎不太可能有大量聚居人口,那里仅仅住着一些可以直接亲近国王的人员。
1. 玛里文书及其出版
玛里楔形文字王室档案揭示的正是如上所述的公众与王室的背景,其中绝大多数文书出自玛里末代国王辛里-利姆Zimri-Lim统治时期。辛里-利姆从他的前任来自另一王朝的敌手那里继承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多数玛里文书具有实际用途而非用于抄写训练,因此,我们几乎无法从中领略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文学的特色,也几乎没有找到词汇集或者专门记载有关预言或咒语的文本档案。不过,我们发现已经记录在案的近两万块楔形文字泥板及碎片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揭示宫廷各种机构日常事务的行政文件,另一类是史无前例的书信集。作为王宫管理细枝末节的文本证据,玛里文书档案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在这些楔形文字文书档案中,王室往来书信则最为独特且珍贵的。多达三千多封的信件数量已足以令人瞩目,不过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更在于书信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范围和写信缘由。我们发现了玛里王与其他统治者们或其它城市的信件交流;我们还发现了由以下人员提交的数千份报告:宫廷高官、地方长官、将军、效忠王室的部落领袖,以及外交官、代表王室的驻外使节等等。另外,官员之间也有书信往来,甚至还有一些被截获的敌军情报。有些信件简洁扼要,其目的纯粹是为了传达信息;但也有许多信件采用的是谈话方式,而且从现代读者的欣赏角度来看可以说十分罗嗦。凭借着历史的连贯性优势,从如此众多的信件中了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纷繁的方方面面并非不可能。这些信件以独特的书面表达方式向我们呈现了如此久远的一段历史时期,而就在这里精彩纷呈的往事相互交织着。
虽然大多数的玛里楔形文字泥板是在几十年前被发现的,但是随着玛里文书档案的公开发表,其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新的证据纷至沓来,而且似乎又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即使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的玛里泥板文书还未达其总数的一半,重要资料可望陆续面世。对玛里文书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的已有两代人,因而凡是需使用玛里文本证据的研究者们必定都会特别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有关文本原文的还是考古学的。玛里楔形文字泥板于1934年首次被发现之后,其整理出版工作最初由德高望重的亚述学家弗朗索瓦特罗-丹金(Franois Thureau-Dangin)负责,之后不久乔治﹒道森(Georges
Dossin)接替了他的工作。1980年以前大部分玛里文本的出版由道森及其同事共同完成,与帕罗特的考古挖掘工作大约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
1980年以前玛里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出土甚是轰动,但当时出土的仅仅是其中的极小部分;尤其在莫里斯佩罗(Maurice Birot)的帮助下完成过渡工作之后,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担负起了研究重任。1982,让-玛丽迪朗(Jean-Marie Durand)组织了一支新的研究队伍。领导人的更换不仅使玛里文书档案的出版工作得以重新开展,而且还引领了一个对文本原文进行分析的全新研究视角,迪朗和多米尼克夏宾(Dominique Charpin)是这一研究方法的积极推动者。
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20多年里,玛里研究硕果累累,大批新出土的文本及一些解读性的评论纷纷面世,更多的文本证据也即将出版。不过,这批新资料多数尚未被美索不达米亚专家们完全解密,更毋庸说该研究领域以外的那些学者们了;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便是尽可能扩大最新研究成果的影响。我对玛里文书档案的研究始于19971998学年,当时我正荣幸地在巴黎享受着学术假期。在巴黎逗留期间,玛里文书档案的研究小组成员(特别是迪朗,夏宾和贝特朗拉封)令我获益良多,他们热情好客且才智横溢。在对玛里文本证据以及法语版解读性论著进行批判性阅读之后,我积极尝试开辟一个独立的研究视角,不过对上述研究者的学术成果相当熟悉的读者们一定会发现我的研究能做到目前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学者们。当然,我们在许多观点上是存在分歧的。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他们的结论极具说服力,本书中的引文主要出自他们最新版本中的解读。当我的法国同行们的分析结果至关重要但却可能引起争议时,我会明确说明自己有着同样的论断,这样做既方便了读者同时又能重申其重要性。
有关玛里文书档案的研究已持续多年,现已出版的玛里文本也分散于不同地点。特罗-丹金以和他之后的各个考古研究小组的早期发现往往被记录在了研究者个人发表的论文中,要想全部找到难度颇高。道森发起出版了研究玛里泥板文书的系列文集(即《玛里王宫档案(ARM)》)的第1卷,目前共已出版了28卷。随着玛里泥板文书的研究在迪朗主持下得以重新开始以及玛里的历史环境逐渐变得明朗化,早期的分类方法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彰显,迪朗因此采用了新的分类方法。近年来,玛里楔形文字书板资料主要以小型系列专刊的形式出版,如玛里研究法语版系列刊物Florilegium Marianum(FM)。最近迪朗又重新整理出版了在他担任领导工作之前所有已发表的玛里书信,共三卷;新版中增加了译文及注释(这些注释是基于对楔形文字书板的亲自考证)。这新版三卷被收录为法文版丛书《近东古代历史文献》(Littratures Anciennes du Proche-Orient)(LAPO)的第16至18卷,卷名为玛里王宫书信原本(Documents 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I-III)。想要真正理解并正确使用玛里文书档案的书面证据,没有足够的法语知识还真不行。
2.了解专业领域:语言及书写系统
本书对古代政治生活的研究是以那些参与玛里文书档案分类和解读的学者们的著作为依据的,因此,本书有很大一部分篇幅将围绕有关字词及文本原文进行评述。这就意味着还得烦请对古代语言陌生的读者们忍受一下些许古代文字的干扰,因为这些文字提供的证据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研究人类社会。下面我将做一些介绍说明,希望本书中古代文字的出现不要令大家望文生畏。
玛里文书档案中集体政治传统的证据线索几乎均出自王宫书信。整体来看,信件采用的是阿卡德语即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地区使用的塞姆语的一个分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期时的巴比伦、埃什努纳(Enunna)、亚述都讲阿卡德语。这一时期使用楔形文字书写系统的地区以阿卡德语作为信件交流的书面语言。在采用楔形文字的中心地域如伊拉克和叙利亚,即使外来居民的信件往来也用阿卡德语。如同其它塞姆语的语言分支一样,阿卡德语中多数的动词和名词源自三连辅音串词根(triconsonantal roots),词根的不同组成方式表达不同的意思。例如,阿卡德语中顾问(counselor)的名词是mālikum,与其动词形式imlik及其另一名词形式milkum紧密相关。在玛里文书档案所属历史时期之后不久,名词后缀字母-m消失了,而-m前面的元音-u-则可根据它在词组和从句中的功能变换形式。
该时期大多数叙利亚人讲的是与阿卡德语截然不同的西塞姆语的好几种方言,但是我们仅仅掌握了被当作是阿卡德语的个别词汇。要想将玛里文书档案中阿卡德语与西塞姆语词汇区别开来,只有尝试去对比这一时期大量的文本证据中它们各自的使用模式。本书中的所有塞姆语词汇均采用斜体字。词汇将被完整呈现,如sugāgum(头领);而在对文本原文的引用中,我将区分书写词语时所采用的不同楔形文字符号,如引文中头领一词的呈现形式是su-ga-gu-um,每个楔形文字符号都包含了它本身的音值。
在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之后,楔形文字书写系统仍保留着其发展初期时的主要语言特点。最早的楔形文字系统几乎没有包含可识别的语法标志,它采用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符号表示简单的物品或动作,所以要举例说明最初的创造者所使用的楔形文字到底有何特点绝非易事。不过,楔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苏美尔人那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苏美尔语是一种粘着性语言,它与塞姆语毫无关联,也不与任何其它已知语言相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时,苏美尔语似乎就不再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了,这是社会动荡带来的变故。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期,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都讲西塞姆语。8这一时期,尽管苏美尔语已不再作为口语使用,但却是极受欢迎的书面语;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对楔形文字学者以及书吏们而言,苏美尔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由于一直用于抄写和速记,苏美尔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书面语言,因此掩盖了当时实际用于说和读的语言的基本形式。遗憾的是,要分辨清楚这一特殊语言系统造成的混乱,现有的众多解决方法都不尽相同。而我做了如下区分:塞姆语词汇的苏美尔语书面语形式采用大写字母表示(如URU,其阿卡德语是ālum(音译阿卢木),意思是城、镇等定居点),苏美尔语词汇则以小写字母表示(如城市或定居点一词uru)。亚述学者在引用塞姆语词汇时通常采用斜体字,引用苏美尔语词汇时则不然,以示区分;当然,目前更广为采纳的惯例是将所有外语词汇斜体排版。
在本书中,读者们会接触到两类古代词语:特定词汇和专有名词。处理特定词汇时,我依据亚述学的标准惯例,将特定词汇的元音长度变化完全标记出来,如sugāgum头领或mer?m 牧场首领)。长元音以长音符号作标记,由两个元音紧缩成的长元音则以音调符号作标记。我将辅音字母按照楔形文字音译惯例来表示,读者们需识别-? -kh,-?-ts,以及--(sh)。强调辅音-?-通常发t的音。我将喉头音辅音都以-?-表示,当然我很清楚楔形文字符号可能代表着各式各样的其它塞姆语喉音。比如,书面形式为mer?m(牧场首领)的名词实际包含了塞姆语辅音?ayin音译为mer?m,但我们却无法凭借其书写形式加以识别;而我本人则依据此类词语的楔形文字拼写法将其表达了出来。这样,玛里文本中的那些词源尚不确定的词语和名称的呈现方式将保持一致。9
至于专有名词,我决定遵循音译的惯例保留辅音和元音的基本形式,但有一个例外,即地名、人名及神的名字中的简单长元音将不采用长音符号作标记(如Qu??unan 表示Qu??unān,Saggaratum表示Saggarātum)。我仅在词语末尾的紧缩元音上标注了音调符号,以此表明词语末尾音节的重音变化(如Kurd)。专有名词中元音的特点通常难以确定,而我的策略使我无需对每一个专有名词作关于释义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