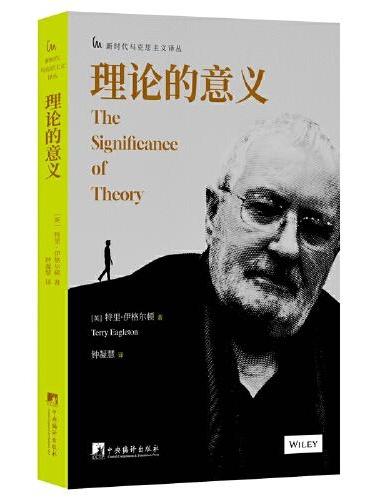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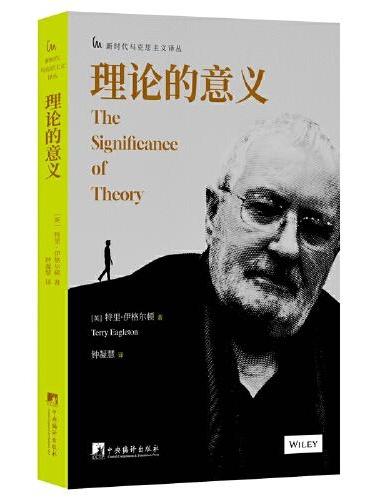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NT$
240.0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NT$
299.0
|
| 內容簡介: |
|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航海探险小说的先驱。小说的主人公鲁宾逊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生志在遨游四海。一次在去非洲航海的途中遇到风暴.只身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开始了段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凭着强韧的意志与不懈的努力,在荒岛上顽强地生存下来,经过28年2个月零19天后得以返回故乡。这部小说是笛福受当时一个真实故事的启发而创作的。1704年9月,一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苏格兰水手与船长发生争吵,被船长遗弃在大西洋中,在荒岛上生活4年4个月之后,被伍兹.罗杰斯船长所救。笛福便以塞尔柯克的传奇故事为蓝本,把自己多年来的海上经历和体验倾注在人物身上,并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文学加工,使鲁宾逊不仅成为当时中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而且成为西方文学中一个理想化的新兴资产者形象。
|
| 關於作者: |
|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笛福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个特殊的位置,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18世纪,长篇小说兴起,笛福作为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创作开辟了以写实为风格、追求逼真效果的现代长篇小说发展的道路,他的小说表达了要求个性解放、勇于冒险的进取精神。由于生有着不平常经历,59岁时他写出了杰作《鲁滨逊漂流记》,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又写出了《杰克上校》《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罗克查娜》等几部小说;晚年又创作了《不列颠周游记》《英国商业计划》等著作。
|
| 目錄:
|
译者序1
序5
鲁滨逊漂流记1
笛福年谱255
|
| 內容試閱:
|
译者序
丹尼尔.笛福生于1660年,此时正值英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然而笛福生性又极不平和,所以一生的经历正如他笔下的鲁滨逊那样,可以说是起起伏伏。大体来说,他的一生是充满灾难的一生。
笛福属于不信国教的异见派,在信仰上备受官方教会的压迫,他撰写的讽刺文字《对付宗教异见派的简便之道》,曾招致了官方的忌恨,他本人也因此入狱;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的三个臣民各自信奉自己的宗教,鲁滨逊则不加干涉,这一笔,可以说是饱含着笛福本人的身世之痛和对信仰自由的憧憬。笛福的生涯是以商人开始的,但和他笔下的鲁滨逊一样,他行事鲁莽,曾经两次破产,并负债累累,又曾因还不起债务而被捕入狱。鲁滨逊失之东隅,后来却得了意外之财,成了富家翁,笛福则没有他笔下的主人公这般幸运,他至死都是贫困潦倒的。在政治上,笛福属于新兴的辉格派,他反对王权专制和宗教压迫,曾写了大量的文章和小册子来攻击时弊,并曾因此入狱。光荣革命之后,笛福有过一段风光日子,他做了威廉三世的政治顾问,但好景不长,威廉去世后,他再次陷入困境。在安妮女王统治期间,他因言论不慎而再次被捕,后经权臣罗伯特哈利的斡旋,才被释出狱。此后,他和《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一道为哈利效力。到了60岁的高龄,笛福开始了小说的创作,《鲁滨逊漂流记》(后简称《漂流记》)便是笛福新生涯的开端。这部书为他争得了名声和读者,甫经出版,便流传开来,并引发了大量的仿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人用这部作品的主题写了一部名为《星期五》的小说,但其中的鲁滨逊却是接受了野人星期五的教化。这大概是宗教上正确之一例吧。此后,笛福一鼓作气,又创作了多部冒险小说,最著名的如《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其中的《罗克珊娜》近年来颇得好评,有许多英国文学选本便舍《漂流记》而取《罗克珊娜》的。
以出身、所受的教育和职业论,笛福都称得上当时文坛的外来户。《漂流记》出版时,正是新古典主义文学盛行的时代,这种文学推崇趣味的典雅,迎合的是上层口味;作家的衣食所资,也多来自贵族的赞助。但由于文化的普及,读书识字的人日渐增多,从而为出版商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到了18世纪中期,文学靠贵族赞助的历史接近尾声,按第一部英语字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的说法,书商成了文学的赞助者。《漂流记》出版于1719年,正处于文学摆脱贵族的控制而走向中下层读者的关头,所以此书出版后,立即在中下层读者中传播开来。当时的小说受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其标准是描述事物之当是,而非事物的所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漂流记》则与此相反,它追求的是客观真实的效果,甚至不惜流于细节的琐碎,这也正是日后小说的发展趋势。所以19世纪的柯勒律治才说,写小说应该像笛福那样,使人有读历史之感,而不能像菲尔丁那样以寓言笔法来写小说见柯勒律治《文学传记》,万人文库版,256页。笛福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也正是由于此。
《漂流记》之成为经典的少年读物,则开始于19世纪。随着人们意识到了少年与成人的差异,儿童文学在19世纪发展起来。《漂流记》中的冒险故事,以及它那栩栩如生的笔法,对于少年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其中的道德灌输也为家长们所乐见。所以自19世纪以来,《漂流记》便成了少年读物中的经典,即使在父亲的督课下,非圣贤书不读的约翰穆勒,也从父亲手里得到了一本《漂流记》见穆勒《自传》,哈佛古典丛书本,13页。但作为成人读物来看,《漂流记》的情况则有些复杂。大概由于《漂流记》本身的一些缺点,再加上成人不及少年那样心口如一,所以尽管大多数成人喜欢阅读这部书,但并非所有的成人都说它的好话。最著名的如狄更斯,曾说自己从未见过这样一部书,其中没有引人落泪之处,而居然成了经典。但这些评价,大多是依据个人的文学见解做出的,并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评价这本书的标准。
但无论如何,《漂流记》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在我们普通读者看来,最主要的是笛福的粗心,以至小说读起来偶有不连贯之处。比如在鲁滨逊第一次登上破船时,笛福已经声明他脱下了所有衣服,但不过一页的篇幅,鲁滨逊居然又有口袋来装船上的面包了;鲁滨逊在岛上生活的年代,也显得前后不一。这些粗心的例子书中还有一些,细心的读者可以一一找出来。至于对《漂流记》的其他指摘,则多显得有些学究气,是与我们普通读者无关的。
《漂流记》在我国流行日久,即使没有读过这部书的人,也可以说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所以关于这部书的内容,笔者不再饶舌。翻译此书所依据的版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的唐纳德克劳利编辑本,并曾参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方原译本,谨在此致谢。
我是约克城的一个良家子,生于1632年,我家并非本地人,家父是外乡人,来自德国的不莱梅,他最早在赫尔落户,靠着经商,挣得一份不小的家产,以后他收下了摊子,来约克城住下,并在当地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在本地也算得家道殷实,由于我母亲的缘故,我本名鲁滨逊克劳茨纳尔,但由于英语的讹误,乡里人都叫我们克鲁索,我们入乡随俗,也这样称呼并且书写我家的姓氏,于是我的同伴们也这样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英军驻佛兰德步兵团的中校,曾效力于大名鼎鼎的洛克哈特上校麾下,后来战死于和西班牙人在敦刻尔克进行的那场战役;我的另一个哥哥下落如何,我一无所知,就如同我父母如今不知我的下落一样。
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儿子,又没学过手艺,所以从很小开始,我脑袋里就想入非非。家父那时年事已高,他在家中督课我,又让我上了乡村免费小学,叫我薄有学识,并立意要我做律师。但除了去海上,我对一切都不中意,这种偏好使我执意违抗家父的心愿和命令,全然不顾母亲朋友的乞求与劝告,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非要把我行将遭受的那种悲惨生活塞给我。
家父为人明智而稳重,他预见了这计划的结果,对我好言相劝。因为痛风他不能出屋,有天早晨便把我叫到他房间里来,就这事热心地劝我。他问我犯了什么混念头,居然不顾事理,要离开自己的家和生身的国土,在这儿我本可以很好地跨入社会,靠着刻苦勤奋,大可以发家致富,活得逍遥快活。他对我说,只有贫困潦倒的穷人和野心勃勃的富人,才涉险去海上,靠冒险发迹,靠非常的举动扬名。而这两者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了。他说我属于中等阶层,或者说,是下层人的上上者,而据他的阅历,这是最好不过了。这阶层最幸福,既不像卖体力的,得忍受不幸、艰辛、劳累和痛苦,也不像上层人,备受傲慢、浮奢、野心和嫉妒的攻心之累。他说,其实我自己也能看出这一阶层的幸福来,只要我明白,别人都很羡慕这一阶层,即使贵为国王,也常常感慨生于帝王之家所尝的苦果,总盼着自己落在这两极之间,既不贵盛,也不寒贱;还说那个智者,曾祈求上帝让他不富不穷,由此可见,这一阶层是真正幸福的标准。
他说你睁眼一看就知道了,生活中的灾难,下层人和上层人都有份儿,唯独中间地位的人却很少赶上,而且不像贵人和贫民那样大起大落、荣枯不定的。不但如此,他们还没有被不良生活,被穷奢极欲搞得身心交困,也没有因为劳累、匮乏、缺衣少食而病恹恹;还说各种德行和快乐,就是为中等地位的人准备的,平静和富裕是中产之家的女仆;克己、适度、健康宁静、乐朋好友、所有可人的娱乐、所有赏心乐事,这些福分都属于中等阶层的人;又说在这个阶层,人在世界上是来得安稳,走得舒适,不至于心为形役,搞得身心交困,也不至于为了每天的面包卖给生活去做奴隶,或整天苦于世道险恶,弄的身心不得安闲;嫉妒的怒火、想成大气候的野心,都燎不着他,只是乐悠悠地过完一生,尝尽生活的甜味,与苦无缘,觉得幸福无比,而且快乐每天都不离左右。
说到这儿,他诚恳而慈祥地劝我别耍孩子气,别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按道理,按我的出身,事情都不该这样;说我没必要自己去找饭碗,他会好好替我找的,他会尽量让我进入他向我推荐的那个阶层;而如果我不能幸福安适,那全怪我命不好,或我本人的过错妨碍了它,与他是无关的,因为他已经尽了义务,他看到了这一步的害处,并且警告过我。一句话,我要是听他的,在家里安顿,他会助我一臂之力,可我要想毁自己,那他绝不来凑一手,所以我想远游的话,则别指望他的鼓励。最后,他要我以哥哥为戒。他当年也曾这样苦口婆心地劝他,让他别掺和低地国家的战争,但说不动,非要一逞少年狂去参军不可,结果死了。如果我非要走这愚蠢的一步,他固然还为我祷告,但上帝却不会保佑我了,当日后我求救无门时,我自会闲下心来,想到我当初是如何不听他老人言的。
我日后才觉得,家父的后一半谈话,可算有先见之明,只是照我看来,当初他并未料到这一番话会谶语成真。我看到家父老泪纵横,尤其是提到我那被杀的哥哥时,当他说到我日后会悔恨,会求告无门时,他大伤感情,突然中断了谈话,告诉我说他心乱如麻,无能为言了。
当时,这谈话深深感动了我,谁又是铁石心肠呢?于是我决定不再想出海的事,听老父的,在家里安身。可不消几天,这决定就被我忘在了脑后;长话短说吧,几周过后,我决定自己溜走,免得父亲再来纠缠。可我却没有趁这决心的热乎劲儿立即行动,我逮了个母亲比平时高兴的当口,对她说,我就是想出去见见世面,在别的事上安身,我是没心干到底的,所以父亲最好是同意,免得我不告而辞。我都已经18岁了,去做什么学徒,或给什么律师做秘书,都嫌太晚。我敢说即使我去了,也干不长久的,不等出徒,我肯定要背着师傅跑去出海。可她要是跟父亲谈谈,让我出一次海,等我回得家来,不喜欢这事了,我就再不出去,我保证以双倍的勤劳,追回我失去的光阴。
这话惹恼了我母亲。她告诉我,她知道拿这类事跟父亲去说肯定没用,事关我利害的事,他很清楚,绝不会同意这种害我匪浅的事。而且她真纳闷了,在和父亲谈过话之后,在父亲情深意切地待我之后,我居然还在想这事,别说了,我要成心毁自己,那别人也没办法,但别指望他们的同意。至于她,才不帮我自蹈绝路呢。以后要提起这事,说父亲不同意,可母亲同意,那是没门儿。
尽管向父亲提建议的事遭到母亲拒绝,可我日后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父亲,还听说,家父显得很焦虑,然后叹口气对她说,这孩子要待在家里,他会很幸福的,可要是出海的话,他可是天底下最命苦的人了,我不能同意这事。
大约事过一年之后,我便自己逃走了。而在这期间,对于要我定个行当的所有建议,我一概装聋作哑,而且不停地纠缠父母说,既知道我如此想出海,就别再断然反对了。可有一天,我去了赫尔城我时而去那里逛逛,只是没有逃走的打算,在城里碰到我的一个伙伴,他正要坐父亲的船出海去伦敦,他使出招募水手的老圈套,鼓动我随他们一起走,说此番航行,不用我花一个大子儿,我没有再和父母商量,连个口信也没有捎给他们,管他们听着听不着呢;没有求上帝的祝福,没有求父亲的祝福,更没想什么前因后果,在那个倒霉的时辰,去听天由命了。1651年9月1日,我踏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我想普天之下,还没有哪个年轻的冒险者,赶上灾祸比我早,忍受不幸比我长了。船刚刚开出亨伯河,就赶上了风暴,海浪连天,异常吓人。我从没有去过海上,所以身体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心里也很害怕。我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心想我这么离家出走,不尽子职,真算是造孽,老天惩罚我,也是罪有应得。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哀求,这时一齐涌进我的脑子。我的良心,由于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达到顽梗的顶峰,于是也责备我无视忠告、背弃我对上帝对父亲应有的忠节。
说话之间,风暴越来越猛,海浪掀起老高来。这一场风暴,固然不及我以后多次经历的那些,也不及几天后我见过的那次,可对一个初见风涛的新水手来说,这已是够惊心动魄了。我觉得每个浪头上来,都要把我们吞掉,而每当船跌进了浪底,我总觉得是再也上不来了。我心里很痛苦,发了好多誓言,暗下决心说,上帝要是让我在这次航行中苟全性命,我的脚要是再能踏上陆地,我就直接回家见父亲,有生之年再也不上船了。我会听他的话,绝不再这样自找倒霉。现在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他那些关于中等生活的言谈,真是信然不虚。他这一辈子,活得是多么自在舒服,既没在海上经过风暴,也没在陆上遭过麻烦;我像一个回头浪子那样,决心回家去,守在父亲的膝下。
这些明智而冷静的念头,在风暴持续的当口一直在我心里盘桓,而且还盘桓到了风暴过后。但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我开始对大海稍稍适应了。尽管一整天我有点儿闷闷不快,而且还有点晕船,但临近傍晚,天气变得晴朗起来,风也完全停了,随后,就是一幅美丽动人的黄昏景色。太阳晴朗地落下,第二天又晴朗地升起,见不到一丝风影,阳光照在水平如镜的大海上,这景色,我平生真是未曾得睹。
头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如今也不再晕船,所以心里乐颠颠的。我看着这片刚才还狂暴可怕的大海,一时间竟变得平静可爱,不免满心惊诧。那个把我诱来的伙伴,大概怕我回家的决心还在,于是走到我跟前,拍着我肩膀说道:嗨!伙计,现在怎么样?昨天那一帽底风把你吓着了吧。你把那叫一帽底风?我说道,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呀!别傻了吧,什么风暴,他回答说,你管那叫风暴,这可奇了。要是船坚海阔的话,我们才不理睬这样的小风。不过你还没见过盐水嘛,也难怪。来吧伙计,咱们去弄碗甜酒喝喝,然后把这事忘他个干净,你瞧天气现在多棒。我这一节伤心的故事,还是长话短说吧,我们步了所有水手的后尘。酒调好后,我喝了个酩酊大醉,那一宿的混账行为淹掉了我的所有悔恨,我对过去行为的一切反省,以及对未来的所有决心。总之,当浪静风平、海面回到了往日的平静,我那腔纷思乱绪,就统统没影了,生怕被大海吞掉的担心和恐惧也全部忘光了,以前的欲望又倒流回来,我在危难中发的誓言,做的许诺,如今忘得一干二净。那些反省和正经的念头,倒也总想卷土重来,可都被我撵了回去,我像躲避瘟神那样躲着它们,只顾着狂饮滥喝,呼朋引友,很快就把这一腔心病我当时就是这样称呼它们压了下去,没叫它们再犯。五六天过后,我像一个决心不叫良心打扰的毛头小子那样,大胜了自己的良心。可我因此还得遭一场磨难,对我这号人,老天自是要弃之不顾的。既然我不把这次脱身当成上帝的一次宽释,等到了下一次,他自然不再手软,就是人群里天不怕地不怕的恶棍,遇上它也会告软讨饶的。
在海上的第六天,我们开进了雅茅斯锚地。天气虽然晴朗,但风向是逆吹的,所以风暴之后,我们只走了一小段路。我们被迫在这里抛锚,锚抛下之后,风向还是逆吹,从西南方向刮过来,持续了七八天。在这一段时间里,纽卡斯尔来的许多船也开进了这片锚地,这里是往来船只的必经港口,船都得在这里等候顺风,以便开进泰晤士河。
其实,我们不该在这里漂这么久的,要不是风力太猛,我们早趁着潮水开进泰晤士河了。在这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却愈发见凶了。但这个锚地向称良港,再加上我们锚坚索固,所以大伙都无忧无虑,毫不担心危险,只是以海上的方式休息玩耍。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风力加剧,大家都上手去放中桅,把一切捆紧扎牢,好使我们的船尽量漂得安稳一些。到了中午,海水拍得很高,我们的船头几次进水,海水漫过了甲板,有那么几次,我们都以为是锚脱了;因此船长命令大伙把副锚也用上。结果,我们的船头沉下了两只锚,锚链则放到了最长度。
这时,风暴刮得吓人极了,甚至从船上水手的脸上,我都看出了一股恐惧和惊慌之态。船长虽然行事机警,极力保存着这只船,可当他从自己的舱里出出入入、经过我身边时,我几次听见他低声自语主啊,可怜可怜我们,我们要没命了,我们要完蛋了诸如此类的话。在第一阵慌乱的当口,我傻呆呆地躺在尾仓里,心里说不出的糟乱。我既然已经铁下心来,把前番的悔悟踩在了脚下,现在就不该吃那口回头草了。我觉得死亡的苦况已经过去,这次不过和上次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当船长走过我身边,像我刚才说的,说我们全要完蛋时,我登时给吓呆了。我走出船舱,向外望去,只见一幅我从未见过的惨象。海浪卷得像山一样高,不出三四分钟,就在我们面前冒起一次。我看看四周围,满眼是海滩的惨景。漂在我们旁边的两条船,由于负载过重,甲板上的桅杆已全被砍掉;只听得大伙又高声叫喊说,我们前面一里处的那条船已经沉了。另有两只船则脱了锚位,从锚地冲出去,没有一条桅杆,漂进汪洋里去听天由命了。那些轻便的船只情形最好,在海上颠簸得不算厉害,但也有两三只开过来,从我们船旁擦过,只有斜杠帆斜矗在风里,一头漂离了锚地。
临近黄昏时分,大副和水手长来乞求船长让他们把前桅砍去,船长却不舍得。水手长抗议道,如果他不肯,那么船会沉的,他只好答应了。他们把前桅砍掉之后,主桅又晃起来,把船摇得厉害,他们只好又把主桅砍掉,这样甲板上就空了。
作为一个新水手,前不久又遭那么场惊吓,我当下处境如何,人人都能猜到。但事过境迁,要是今天我来讲讲当时的心情,那死的恐惧倒在其次。想我前番悔罪,今朝故态复萌,不改最初的顽梗,由此而来的恐惧,是胜过死十倍的。这些恐惧,加上风暴骇人,搞得我心迷意乱,非笔墨可以形容。然而最糟的还在后面:风涛狂暴不止,即使水手们也连连承认,今生今世,还从没见过这么糟的天气。我们的船固然是不错,可负载过重,深深吃进水里,所以水手们不时大声嚷叫说,它要没了。由于不懂得没是什么意思,我算小沾了点便宜,后来我才搞明白这话的意思。且说风暴越刮越凶,最后到了这少见的一幕:我看见船长、大副、水手长和一些稍懂事理的人,都做起了祷告,觉得这船随时就要没入深渊了。到了午夜,尽管已是灾祸四起了,可有个想下去瞧瞧的家伙又大声喊道,我们漏水了;另一个又说,船底的水已经有四英尺深了。于是大家都被喊去抽水泵。一听这话,我的心凉了半截,刚刚还坐在床上,这时却一个后仰翻进了船舱。可人们把我弄起来,对我说,我以前不能做什么事,现在倒可以和别人一样去抽水泵了。听到这话,我打起精神向水泵走去,一心一意地抽起水来。正在我们抽水的当口,船长看见几只小煤船,被风暴打得倚里歪斜,不由自主地滑向汪洋,此时正靠近我们,于是他命令鸣枪,作为海难的信号。我对此一窍不通,所以大感惊慌,还以为船破了呢,或又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总之,我这惊吃得不小,竟晕倒在地。在这人人自危的当口,自然没有人会想到我、看我出什么事了。倒是有人跨到了水泵跟前,一脚把我踢开,随我那么躺着去:他以为我早死了。过了好一阵子,我才醒过魂儿来。
我们接着抽水,但船底的水却只涨不减,事情明摆着,这船要沉了。虽然风暴开始稍稍减弱,可也别指望这船能把我们拖进港口,于是船长继续鸣枪求救。漂在我们跟前的一艘轻船这时冒险放下一只小艇,前来搭救我们。它冒了好大险才靠近了我们,可我们却无法上去,它也无法拢近我们船侧,这些人只好狠命摇桨,拼着自己的性命来救我们的命。最后,大伙终于从船尾把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抛向他们,然后放长,他们费尽力气,冒了好大险才抓住了它,我们把他们拖到船尾下面,便一齐上了他们的小艇。上去之后,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觉得无望追上他们的大船,所以只好由它漂去,只是想法让它靠岸就行了。我们的船长对他们许诺说,要是小艇被海岸撞碎,他一定赔偿他们的船主。就这样,我们的船半摇半漂着,斜滑向正北海岸,几乎是到了温特顿岬角。
弃船之后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眼看着它沉了下去,这时我才第一次明白海上所说的没是怎么一回事。说实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它在沉的时候,我真是无心去看,因为从我迈进该说被人架进才好这只小艇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好像就死了,这一半是惊吓,一半是念及此后生死未卜,不免心里发虚。
虽然我们处境险恶,可人们还是拼命摇桨,好使它靠岸。每当小艇浮上浪尖,我们就可以看见海岸,一大群人正在沿岸奔跑,好等我们靠近时过来帮我们,但靠岸又谈何容易。一直过了温特顿灯塔,到了海岸向西凹进克罗默,烈风因陆地的阻挡而势头稍减时,我们才上得岸来:虽然又费些力气,但大家总算安全登岸了。此后,我们步行去了雅茅斯,那里的人对我们这些落难者大加体恤,镇上的官员派给我们好房子住,一些有头有脸的商人和船主赠给我们足够的盘缠,随便我们去伦敦还是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省事理的话,就该回赫尔、回老家去,这样我会很幸福的。我父亲,也会像我主基督寓言里的那个慈父化身一样,为我宰杀一头肥牛;因为他听说了我搭乘逃走的那只船,已在雅茅斯锚地被毁,但得到我没给淹死的准信儿,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但命运却不依不饶地跟我犯难,这真让人没办法。有好几次,我的理性和那颗还算冷静的大脑,都大声叫我回家去,可我无力这么做。冥冥之中,也真是有天数,我不知该怎么叫它,也不想深究,只知道它要是想把人送进毁灭之手,就是绝路摆在眼前,我们也会眼睁睁地一头撞过去。我这次可算倒了大霉,撞在了它手上,那就甭想逃脱,它赶着我一头走到黑,全不顾我那理性的冷静告诫,以及我在这初次尝试中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
我的伙伴、也就是那位船主的公子,上次曾帮我横下心来,这次却缩得比我还快。我们在雅茅斯住了两三天之后,他才第一次得机会跟我说话,因为我们分住在镇上不同的地方。他一见我,好像声调也变了,一脸沮丧,还不住地摇头。他先向我问过安,然后把我介绍给他父亲,说我这次出航,只是想试试身手,也好以后出远海。他父亲拿出严肃和关怀的口气对我说:小伙子,你可不该再出海了,事情这不明摆着,你当不了水手,这你该看得出来。可是先生,我说道,那您以后还出不出海?那是另一码事,他说,这是我的天职,也算我的义务。可既然你想拿这次航行尝试一下,那你该看到了,如果你要一味坚持的话,老天会给你什么果子吃;也许我们这场倒霉事儿全怪你,你就是他施船里的约拿。他又接着说道,你小子是谁?你干吗要出海?既然他问到这儿,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事告诉给他,不料我刚一讲完,他突然起了邪火,瞧我都干了什么!他说,怎么能叫这个倒霉蛋上我的船?就是给我1000镑,我也不会再跟你同上一条船了。叫我说,他这通火实在发得没有道理,不过是自己受了损失,一时想不开,心火邪发罢了。然而火发过之后,他又认真地跟我谈话,力劝我回到父亲膝下去,别自找死路;他说我该看出来了,上帝明明是跟我作对的。想想吧小伙子,你要是不回家,那不论你走到哪儿,你只会碰上灾难和失望,直到你父亲对你的预言完全应验。
|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