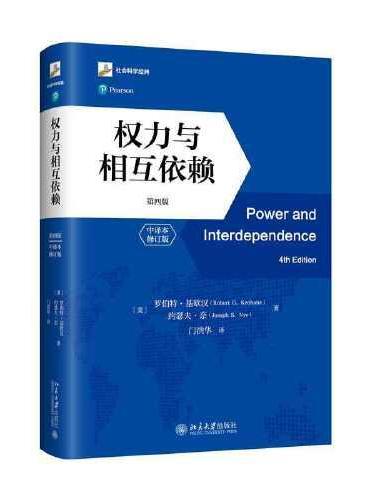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瘦肝
》
售價:NT$
454.0

《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
售價:NT$
254.0

《
秩序四千年:人类如何运用法律缔造文明
》
售價:NT$
704.0

《
民法典1000问
》
售價:NT$
454.0

《
国术健身 易筋经
》
售價:NT$
152.0

《
古罗马800年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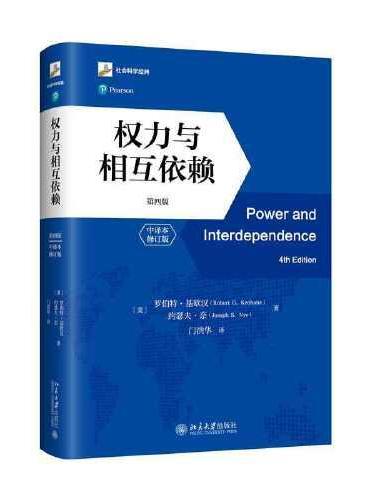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踏上疗愈之旅(修订版)(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
| 編輯推薦: |
☆ 反映夏衍从事文学创作、文化工作的一手资料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夏衍的书信是了解夏衍一生的创作、工作、交游、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 在95年的人生路上,夏衍对自己、对家人、对时代和国家的感想和反省
夏衍活了95岁,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自身也经历了文革的打击,落下残疾。在给亲人、朋友、老部下的书信中,处处可见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反省,对家人、朋友的关爱、挂念,对整个时代的思考、反省,是20世纪新中国文化建设者的自我总结,从中也可见老一辈作家、文化工作者的朴实、平和的优秀品质。
|
| 內容簡介: |
在给宋振庭的信里,夏衍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一辈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夏衍的书信,正是反映这个大转折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夏衍的一生,经历了赴日留学,经历了新文学运动,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可说是曲折的一生。夏衍的书信除写给家人之外,更涉及邓小平、周扬、潘汉年、钱歌川、黄苗子、李子云、王元化、陈白尘、于伶、洪深、萧乾、陈子善等等,是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本次出版在《夏衍全集》书信卷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新发现的夏衍佚简若干,可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材料。
|
| 關於作者: |
|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革命文化翻译工作,曾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抗战胜利后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文革期间受尽折磨,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历任政协常委、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
| 目錄:
|
出版说明
我们的爸爸夏衍(代序)
1931年(1封)
1939年(1封)
1940年(1封)
1941年(1封)
1947年(1封)
1948年(1封)
1951年(3封)
1952年(2封)
1953年(1封)
1954年(2封)
1955年(1封)
1956年(2封)
1959年(1封)
1962年(3封)
1963年(1封)
1964年(1封)
1975年(9封)
1976年(8封)
1977年(14封)
1978年(13封)
1979年(10封)
1980年(6封)
1981年(13封)
1982年(24封)
1983年(21封)
1984年(24封)
1985年(9封)
1986年(18封)
1987年(28封)
1988年(14封)
1989年(26封)
1990年(16封)
1991年(10封)
1992年(2封)
未署年(57封)
|
| 內容試閱:
|
致沈祖安
祖安同志:
沈宁告诉我你打来了电话。承关注,甚感。
关于捐献文物的事,以及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给奖状,这是我的宿愿。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比留给子女好些。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
我收藏东西很杂,不成体系,所以汪济英同志来时,我谈过是否展出,一切由浙博酌定,我没有意见。因此,文物局的《情况反映》所说的准备出版选集,我看没有什么必要。
您如方便,请和文化厅或浙博的负责人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目前出版事业困难很多,千万不要让他们背这种赔本的包袱。
还有一件事,即我的收藏今春中国画院借去展览过一次,后来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要和我合办展览,也有人希望我捐献给这个馆、那个社的,所以浙博入藏之后,是否可以通过新华社发一条消息,让人家知道我已经捐出了,省得别人再来打主意周培源的文物捐献给故乡之后,也是这样办的,是否可行,
请酌。
至于浙一师之事,我的确和汪济英同志谈过,现在有点后悔,我太多管闲事了!管多了,不仅干涉内政,这类事甚至有地方主义之嫌也。所以你知道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您的健康情况如何,入冬务希珍摄。匆此问好!
夏衍 十一月八日(1991)
致陈白尘
白尘同志:
柯灵同志来信,奉呈一阅,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越计较就会越麻烦,于公对此也有过分之处,但我也无法劝阻。除复柯公一信,劝他息事宁人之外,望你也能在适当时候婉言几句,同时,对史的写法分寸上,盼能严守实事求是方针,千万不要受双方意气之争的干扰为好。匆匆问好,在苏、在宁都承照拂,甚感。遇刘、惠、匡、陈时,乞代致谢。
嫂夫人均此。
夏衍 五、七(1984)
附录:
夏公:
姑苏一面,看到您好精神矍铄,十分高兴。现在您想已安返北京了。
这次开会,有一件我万万料不到的事,就是于伶同志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我觉得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些情况,通一通气。
1981年12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参加现代文学研讨会,写了题为《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的论文(后来收在《剧场偶记》一书中)。我作此文,原因是(一)中文大学的讨论题明确规定为四十年代华东华南文学,因此我只能谈沦陷期间的戏剧文学。(二)我只在沦陷期间参加戏剧活动,自然只能谈我所知道和熟悉的。而且孤岛时
期和沦陷时期情况不同,各有特点,也不宜混为一谈。(三)孤岛时期的戏剧,谈者已多,而沦陷时期的戏剧,从来无人谈过,我觉得有谈一谈的必要。当我定题和写作时,也曾
考虑到:孤岛剧运是于伶领导的,不提于伶和孤岛剧运,他可能不高兴。因此我在论文里开宗明义,说明论述的范围,限于沦陷时期,而且强调指出:话剧的繁荣和职业化,孤岛时期奠定了基础,沦陷时期是它的继续和发展。指明沦陷时期的戏剧,遵循的是中国进步话剧运动的轨道。丝毫也没有抹煞孤岛话剧成就的意思。原文俱在,可以复按。而且我本身亲历孤岛风雨,所写宣扬党领导孤岛战绩的文字,就有多篇。最近为阿英的剧本《海国英雄》作序,就特别提到《阿英剧作选》:篇首有夏衍和于伶同志的序文,他们或是阿英同志的世纪同龄人,或同为孤岛剧运的创导者,长期并肩作战的生死患难交,序文中对阿英同志有周详恳切的介绍,读者可以参阅。还特别将此事告诉了于伶。我对孤岛文学、戏剧的论点,白纸黑字,深信绝不会引起任何误解,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谈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会招来于伶如此强烈的不满。
我和于伶素无芥蒂,一直把他当革命前辈看待,而且因为您和他的关系,我特别对他尊敬,表示亲近。但在一年多以前,我逐渐感到了他对我的隔膜和嫌隙。去年春,白尘来信约我到南京参加《中国现代戏剧史》编写讨论会,信里明说,他已请于伶通知我,但于伶对我只字不提。后来我到于伶家里看望他,他不在,我问柏李,老于去了哪里,柏李含糊其词,不肯告诉我。事后我知道,是因为迎取潘汉年同志的骨灰,去了湖南。于伶去哪里,当然没有告诉我的必要。但运骨灰并非什么机密事,我专程登门拜访,而竟采取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这就充分证明了对我的有意冷淡。此外我又看到,于伶写回忆文章,谈到三十年代的影评小组,遍提所有的成员,就是不提我;他谈孤岛剧运,说得到文艺界的支持,当时在上海的作家几乎都提到了,就是不提我,而那时上海剧艺社主持的《戏剧周刊》,就是在《文汇报》发刊的,有些重要的戏剧评论文章,就发表在我编的副刊《世纪风》里。我绝不是要借重于伶替我作政治或业务鉴定,我深信这是您可以理解的,但于伶这样的故意抹煞事实,却分明地表现了他对我的不友好态度。最奇怪的是,他对我出版作品和发表文章,也表示不快,告诉凌鹤说:柯灵一年要出几本书(这不是事实),有人要他的文章,也有人要出他的书。但于伶虽然这样对待我,我一直不以为意,并且将信将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这次去苏州以前,我又特别跑去看他,送给他《散文选》,希望消除隔阂。我扪心自问,从来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他一到苏州,我就看出他对我的抵触情绪,形诸辞色,已经到了爆发点。四月二十六号晚间,我和白尘等六人到南林宾馆看您的时候,谈到上海筹开文代会的事,于伶就一再指着我说:你不是去参加了吗?意在向你暗示,我是参与其事的。第二天下午,有您参加的戏剧史编写讨论会上,他索性借题发挥,什么论客,两面派,挑拨是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混骂。我耳聋,听不大清楚,这类污水,也泼不到我身上,我只是不明白,他何以如此激昂。后来忽然听到说:有人说只有1941年以后才有话剧。 这才起了疑心,立刻问在我身旁管录音机的陈雪岭(编写组成员),于伶说的确是这句话。我感到奇怪,谁能发表这样缺乏常识的议论呢?会后我问了葛一虹,他是否看到过这类文章,他说没有。因为他刚读过我的《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问他此文论点是否有什么错误偏颇,他认为论点是公允的。我另问熟悉戏剧界情况的编写组成员马明,他也说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文章或议论。我再次向陈雪岭了解,据说于伶当时说的是:有人说三十年代上海没有文学和话剧,只是到了 1941年以后,有了钱钟书和杨绛,才有文学和话剧。 当天晚上,陈雪岭为了核实材料,专访于伶,了解这种议论或文章的出处。于伶说不出来,但又大骂了一通费穆。这样一来,谜底揭晓,事实就非常清楚了:我在《管窥》一文中赞美了杨绛,在《散文选》中又有一文揄扬钱钟书,这就是于伶歪曲为有了钱、杨,才有文学话剧的由来。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捧钱钟书,夏是反共的,所以于伶在会上又攻击说:已经知道他是反共的,还多说什么呢?我在《管窥》中肯定费穆的爱国主义,于伶就在会上和会后骂费穆。这实际都是拐了弯骂我。我这才完全弄清楚,于伶深文周纳,指桑骂槐,目标是针对着我的。
我历尽沧桑,余年无多,只想写点东西,他无所求。而这种事情,完全是非所逆料的。但于伶这样捏造事实,公开攻击的场合是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编写讨论会上,而且当着您(左联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当着几位左翼戏剧运动的前辈,和当代专业话剧史研究者的面,真可谓辣手辣脚了。根据于伶善于冲动的习惯,估计他还不会善罢甘休,可能到处乱说,弄得飞短流长,在不明真相的人中间,无端陷我于不义。我考虑再四,临离苏州前,和白尘谈了,并向他表示,也将和您通一通气,目的是息事宁人,希望不再节外生枝。白尘分析说:于伶对我不满,可能有历史原因。那就是说,于伶对黄佐临和苦干不满,我偏偏参加了苦干,而又写文章肯定了苦干和黄佐临的艺术成就。这大概是实情,但这也未免太使人作难了吧!白尘又说:我们还以为你耳聋,听不见,也就过去了。不幸我恰巧听到了关键性的一句话。世上的事,有时也真不可究诘。
您这次在苏州会议上的讲话,普遍的反应是胸襟开阔,立论公允,雅有老革命和艺术家的气度,感到很受教育。于伶已到望八之年,长期追随着您,而竟如此褊狭和不近人情,我真代他感到遗憾。
附呈《剧场偶记》,备参阅。为了这无中生有的烦恼,累您花宝贵的时间精力来读这封信,我很抱歉。
此致
敬礼,并祈
珍摄
柯灵上 1984.5.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