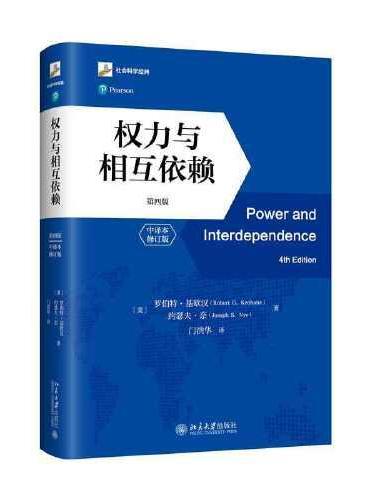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瘦肝
》
售價:NT$
454.0

《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
售價:NT$
254.0

《
秩序四千年:人类如何运用法律缔造文明
》
售價:NT$
704.0

《
民法典1000问
》
售價:NT$
454.0

《
国术健身 易筋经
》
售價:NT$
152.0

《
古罗马800年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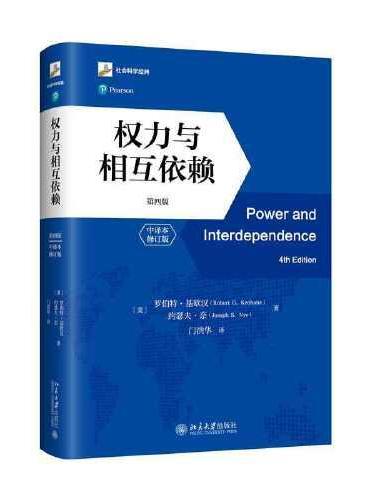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踏上疗愈之旅(修订版)(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
| 編輯推薦: |
推荐一
「果仁」APP原创短篇小说精选集。由阿乙、余西、阿丁、野夫、巫昂、曹寇、盛可以、任晓雯、于一爽、双雪涛、孙一圣等当代作家联袂呈现。
推荐二
被权威忽视却又值得被热爱的小说作品;现代文学小说的延续,当代短篇小说的范本。
推荐三
15篇风格迥异、内容新奇的小说,给人另类的阅读快感,极富冲击力;
故事荒诞却不荒谬,传奇却让人唏嘘,平淡中透着诡异,无奇中又见神秘。
|
| 內容簡介: |
15位当代作家联袂呈现出的一场文学盛宴,讲述15个不同的故事。
《猴者》,一位父亲用尽各种办法向村民证明一只猴子会说“喂”,并告诉我们“人哪,只是猴子直立起来的痛苦”;
《我的朋友卡夫卡》,看余西笔下的卡夫卡经历一段怎样的青春往事;
《弥留之际》,当眼前的苍蝇变成蚊子后,他再也没有掌掴过其他人,而是反复的画一个女人,画一具丑陋的身体;
《老同学》,毕业多年,与初恋重温旧日情怀,却发现人、事、物早已面目全非;
《有人迷醉于天蝎的心》,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看似是一场意外,却隐藏着诸多谜团,到底是谁杀了她?丈夫、情人,还是雇佣的女员工?看私家侦探以千计带你抽丝剥茧找出真凶;
《空房子》,本欢欢喜喜装修房子准备结婚,可是女友小蒋却不声不响地离开,皇甫失魂落魄下,发现女友从没有对自己坦诚过;
《时间轴上的一点》,一位算命先生带你解开“什么是命”的谜题。
……
故事荒诞却不荒谬,传奇却让人唏嘘,平淡中透着诡异,无奇中又见神秘。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想象,却会让你觉得比真实更加真实。给人另类的阅读快感,让你在大呼过瘾之时,又不乏刺痛感与感动。
|
| 關於作者: |
阿乙作家
曾为警察、编辑,代表作《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鸟,看见了我》《寡人》。
孙一圣 前农药厂实验员、酒店服务生
作家、“果仁”编辑,代表作《爸你的名字叫保田》《倒退》。
余西青年作家、编辑
代表作《另一个世界的花朵》。
盛可以作家
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代表作《北妹》《水乳》《道德颂》《死亡赋格》。
瓦当青年作家、诗人、出版人
代表作《到世界上去》
任晓雯作家
代表作《她们》、《岛上》、《飞毯》。
阿丁作家、“果仁”主编
前麻醉师,后弃医从文,代表作《无尾狗》《胎心、异物及其他》《我要在你的坟前跳舞唱歌》。
于一爽青年作家
现任凤凰网文化频道副主编,代表作《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巫昂作家、诗人
创办手工品牌SHU。代表作《春药》《爱情备胎》《什么把我弄醒》。
双雪涛80后作家
台北文学奖得主,代表作《翅鬼》《融城》。
李晁编辑、80后青年作家
《青年文学》杂志长期撰稿人,代表作《男孩与辣椒》《四季》《本命年》。
曹寇作家
被誉为最具才华和潜力的当代青年小说家,代表作《割稻子的人总是弯腰驼背》《我和赵小兵》。
北影摄影师
水鬼机械类工作者
野夫作家
中国自由作家,代表作《乡关何处》《1980年代的爱情》《父亲的战争》《丘陵之雕》。
|
| 目錄:
|
胆怯者
猴者
我的朋友卡夫卡
弥留之际
织女牛郎
我的妈妈叫林青霞
天注定
老同学
有人迷醉于天蝎的心
荒冢
空房子
她是如何治愈我的
时间轴上的一点
水乳记
国镇往事之蛇神牛鬼
|
| 內容試閱:
|
胆 怯 者
阿乙作家
一准下雨,中午或下午,顶多下午,届时,我们的影子消失,像有无数黑黢黢的坦克、舰队开到天空,停在那儿。
(清晨,漫长的关于宏阳的讲述暂时告一段落,宏梁摁停电风扇,关好窗户,给伏案而眠的许佑生盖了件衣服。地面有些返潮。在听讲时 许佑生差不多翻完那本《爱经》。上面画满横线,页面空白处做了大量批注,全是宏梁对自己的训诫与激励。当许佑生认真地看着这些龙飞凤舞的字时,宏梁也在跟着一行行地看。“这里都是男欢女爱的技法,就你还问我。”许佑生说。宏梁发出准备已久的叹息,说:“只是看着玩, 包括我问你,也是问着玩。它是写给罗马上层社会看的,教导贵族如何去剧场、廊庑、跑马场、筵席勾引名媛贵妇,跟我们乡下人没关系,它没有提供如何在牛棚和田埂示爱的技巧。它没有用具体的言辞侮辱乡下 人,但正是从它的不置一词里我看出,它认定乡下人和牲畜一样,没有 资格谈情说爱。”)
你应该问我一句,可我们不就是渴望这样的女人吗?然后我会回答,癞蛤蟆不能因为肩部长出两个翼尖便认为自己有资格占有天鹅。我们得明白这个事理。伊莲,光听名字你就明白她是城里人的后裔,悄无声息地降临时,我正背对大门修理那台随时可能爆炸的电视机,我将显示屏拆下来,小孩子们如风般自门前掠过,他们比谁跑得快好获得将新的信息传播出去的优先权。“村里来了个洋气女人呢。”他们喊。这和我没任何关系,我继续用起子猛戳主电路板。这时与其说我是在尽一切可能 拯救它,还不如说是在愤怒地捣毁它。就像医生看不见手术成功的希望,举起手术刀戳烂病人的胸腔。就是在这烦躁的声响中我听出一阵异常:一层薄纱或者说一层雪轻盖于地上。我们在农村活久了就会对空间变得异常敏感。阴影是有质量的。一截阴影轻盖于我身后的地面。它同时有着味道,我闻到林间河水那特有的阴凉味道。我听见十几米外的邻居停下“嘁咔嘁咔”的脚步声,他扛着锄头屏住呼吸望向这边,在我和他之间一定有位陌生人。我转过身来,看见伊莲活生生地站在那儿,胸脯平静地起伏,嘴唇微微颤抖,一颗汗珠沿着腮部滑落,一只大脚趾从她的平底凉鞋里探头探脑地翘起来,放下去,又调皮或者说羞涩地翘起来。我脸色通红,看着这从虚无、虚构或者说是意念中走出来的人,束手无策。就好像只有几粒小石子在蹦蹦跳跳地朝下滚,我的身体空如山谷就像有一场大雨要在其间歪歪斜斜地下起 来。我在幸福地受罪。
我愿人生永远停驻于这一刻,不再倒回去,也不往下走。我们看见幸福的热浪正翻滚着朝我们奔来,这就够了。我们不应该再往下走。不应该让这还活在谎言中的女人亲眼看见马尔克斯在小说里写的:厕所里,那股浓烈的氨水气味真是呛人、催人泪下。这是像固体一样凝结在半空中,让人不得不屏住呼吸的气味。而在居所之中,在人类足迹不能到达、在手也够不到的角落,老鼠任自己极其腐烂地死掉。尚在昨日,它可能还矫健地跃上餐桌,钻进纱罩,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你三分之一 剩菜。草席之下是干燥的稻草。锅内有擦不完的黄锈。开水总有一股让人想到癌的味儿。姑娘啊,这和你想象中的田园风光是两码事,在你的想象中“穷”是清淡雅致的,但你不知道那穷也是由富裕搭建起来的穷,而我能提供给你的便只是实打实的像铁一样硬的穷。是杨白劳那种穷。是连一块牛粪也要珍惜的穷。
伊莲是换乘多辆客车从修水县城赶来的,临行前既未通知其父母也未通知我。从这种不打招呼甚至是自作主张的特性里,我看出她“原教 旨主义者”的一面,也许在很小时因为看见某篇杂志的文章她便坚定自己对爱情的看法并一直让自己活在这种信仰下,我们知道,那时的媒体 总是鼓吹爱情面前人人平等,有时候为了故意平等不惜制造出一些残忍的佳话,以至有不少心地简单的姑娘就此得出“爱情=献祭”的公式,认定凡不做出牺牲的爱情便不能称之为爱情。因此有不少人跳水式地下嫁给肢体残缺者,也许她们要嫁的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人,而只是心中的一个理念吧。
现在,当伊莲踏入我家门槛,我在她眼睛里看见的也正是这种过 于神圣、过于残忍同时过于虔诚的光。她太单纯同时也太自以为是了。可是用不了多久,不是吗?很快,非常快,随着越来越多地接触 到现实,她准会后悔自己的一时头脑发热,而这是她的父母早就预料 到的。他们预见她会这样反思自己,她会沉浸于一种蒙难的情绪中不能自拔而终日以泪洗面,她会以这种方式抗议将要度过的漫长而恐怖的一生。
(许佑生呜咽着,用普通话说梦话:想你,当然想,好想。)
几天后,我将伊莲连人带皮箱推出门,她显得悲伤,脚步却没停下来,就像发动机不灵的汽车在人为地推了一段路后打着火自己行驶 起来并且再没停下来。我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那几天,她在我面前并未表现出什么不满或者说为难,然而我却觉得越来越受用不起她。此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而说起来我之所以要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将她赶走,也仅仅只是因为一个梦。就像佑生你现在在做的梦,入睡前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醒来后却可能变得异常坚决。是 的!一个梦!而与其说它是个梦,还不如说是一位理性的智者将我单独唤过去,向我交代这场爱情很快便会迎来的结局,这位智者就像你死去的外公,他总是对我负责,在他的教导里没有一丝诳欺、遮蔽和夸大其词。相比之下,我和伊莲待的那几日倒更像是个梦,那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女人(她会懂的,而且很快)和一个有意欺瞒自己的男人联手上演的一出戏。
在我做的那个梦里,阳光真是好极了,我和伊莲走进范镇街,阴影像一层透明的纱罩在我们身后。而根据我们十指紧扣的情形判断,我们的关系已发展到极为稳固的阶段,可能还会登记结婚。但这并不能保护我。去趟镇上是她反复提出的要求,我总是有不好的预感,但不好违逆。我对她说,好,我们这就去镇上,我尽量显得真诚却在心里企盼着能早点归来。阳光是银色的,像一整块镜子摔碎在地面,塞满建筑物间的空隙。在进入集市前我有意和她说着情话,因为她的回应总是让人不 尽满意。我反复说着那些情话,我在试探她,直到我自己也厌烦了:有谁在即将走进热闹的集市时还顾得上全心全意地回答“你爱不爱我”的问题呢?那天的阳光真是好极了,佑生,特别清晰特别光明,事物简直纤毫毕现,然后因为她买来一件又一件明显是用来过日子的商品(包括 喷着“囍”字的洗脸盆、痰盂,以及绣着小宝宝图像的童衣),我不禁羞愧难当。我越是羞愧,对她的爱意便越是汹涌,我差不多要捧住她的 脸狂吻。然后,我就像是惴惴不安的毕业生抚摸着盖过章子的录取通知书,抚摸着那些作为证据的货物,目送她走向厕所。我被一种踏实的感觉包围着,坐在石头上。
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话,声音里夹杂着一股吊儿郎当的气息,你可以理解他是在表达熟人间的亲昵,也可以理解他本性就很轻浮。我感到慌乱。“过来了啊?”他说。“嗯。”我说。“这些都是什么?要生 孩子吗?”他拨弄着我手上的东西。“在计划。”我说。“哦,”他的眼睛 在集市转了一圈,“你的女人呢,我还没见过呢,听说她很漂亮。”我像是饿极了,想回答,却缺乏气力。我怕他看见我在发虚。啊,这就是一个色狼在问一个男人你的妻子呢,对他来说这是不用忌讳的事,他色胆包天可是出了名的。而让人奇怪同时气愤的是,那些女人在察觉到自己被他关注了后,就像遇到什么了不得的奇迹,一个个呼吸不过来,就快要晕倒过去。他确实和这里的男人不同,他穿着奇装异服,言行举止装腔作势,他就像是被临时贬黜到此地的王子,从不为生计发愁,一门心思只想捣毁号称是这镇上最坚固的几样东西之一的道德,就像要捣毁一个鸟窝。他简直坏透了。他直白地向猎物(女人)表达好感,与此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存在什么长久的契约。按理说,这样的男人没办法赢得女人的心,可事实是,只要他的目光在她们身体最骄傲的部位逡巡几遍,她们便马上软下去,就像那眼睛是一剂春药,我就是喜欢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就是喜欢,我现在就想亲近它。他的眼睛说。她们诚惶诚恐地点头,宁可第二天被他踹出门来并接着被自己的丈夫或父亲反复鞭打。他用魔法唤醒她们身体内可怕的欲望,有几个女人已经疯掉,开始没日没夜地在他的窗外,脏兮兮地裸奔。
现在,他沿着伊莲走过的方向走去,我祈祷那想象中可怕的事不要发生:一、按照这个速度走下去他将在伊莲走出来之前走过厕所,你也知道女人在厕所待的时间总是很长;二、即使他们打了照面,他也可能会在最后时刻停止罪恶的念想,总会有底线的,无论是多么糟 糕的人,我和他是熟人不是吗?我们多少算是兄弟或朋友,他知道那就是我的妻子。但我还是感到痛苦,我清楚这不过是自我安慰。我不能过去推着他的肩膀让他走快点,也不能朝他的脚底扔一块石头让他跳着跑开,我只能揪着头发反复祈祷,并不时抬头瞅向那边。他走近厕所时,脚步忽然奇迹般地在一两尺长的地面来回滑动,就像那块地面是跑步机的滚送带,他不停地走着,而人却一直滞留在原地,他优雅得像是走太空步的迈克尔·杰克逊。他知道传说中的美人就在厕所,他刚从我的话里嗅出来了。然后,在我重新抬起头时,虽然对不幸的结局早有准备但还是差点惊呼出声来——他已经抓住她的手!而她的手就像一只安顺的小鸟眯着眼躺在他的手里。刚刚它还在我的手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对自己大声说,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这只是他在习惯性地占便宜,这个便宜说大不小说小不大,她不想将事情闹大,很多女人面对这种情况都会选择忍让。是他捏紧她的手!你瞧,她的手并没有反握过去,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果然,几秒钟后,在他的手稍微放松时,她迫不及待地抽回它。他显得很失落。这是他头一回经历这样的事故吧。他的那只手被迫空着,醒目地抬在半空,就像龙虾僵硬地举起螯足。但是我没高兴多久。她从包里翻找出一面小镜子,旁若无人地照起来,她侧过左脸又侧过右脸,刚才她预感到有什么不妥,现在就是在找出它好对之进行修补。他像斗败的公鸡,虽然 披着华贵的斗篷,却是沮丧地站在一旁,他还沉浸在这罕见的失败中,直到她将镜子塞回包内,摁上子母扣,像瞎子一样将手向后伸去。在没得到回应后,她晃晃它,意思是你来抓住啊,他便乖乖地抓住。然后,他拉着她,他们,手拉手,欢快地走进阳光深处。我坐在那儿无法动弹,感觉自己正被沉默地杀害。
我在梦里沉默地哭泣了很久,才醒来。我看着熟睡在一旁的她,眼神贪婪而悲壮。她是沿着一条脆弱、单薄、摇摇欲坠的管道侥幸走到今天,走到我身边的,她侥幸保住处女之身以及像处女一样的思 维,而所有像她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都早已被两个强盗绑架、占有并 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侍妾和性奴,他们一个叫权,一个叫钱,他们不会受到历史制裁,就是连起码的抗议也看不到。她们的家人也不会 感到痛心(要我说,这些家人还会感到荣幸)。她伊莲迟早也会变成这样。她来到艾湾并不是什么奇迹,奇迹是她到这么晚还没接受到那全 体人民都已获知的信息。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那些过去是女孩现在是女人的人,已经知道用手臂或乳房擦碰那些就像电梯一样能将 她们捎到社会顶层的成功男士。当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吭哧吭哧” 地扑上来,心急火燎地解她们的裤带并仓促且认真地发誓时,她们还 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做个爱吗?所有的道德、情感与理想都在覆灭,只有权力与货币是坚固的。我们这些鱼,在权力与钱这个杠杆的 驱赶下,呈放射状地朝社会游去。伊莲迟早是别人的人。一件衣服打 动不了她,十件也许可以;十件不行,一百件就会。只要她一出现在 那男人较多的场合(她总会在那儿出现的),那所有人便都抛下他们诚 意的钩子来。我们不要以为那就是在侮弄她,不,相比他们的挥金如土,清贫的我才更像是骗子。我悲壮地看着这迟早要滑向名利圈的女人、这巴黎明天的交际花,束手无策,心如刀割,然后我开始扒她的 裤子。此前我一共扒过三次,均未成功。这一次也没成功。她仍然在说:“你急什么,我迟早会给你的。”唉,我真想摇着她的肩膀,疯狂地说:“怎么不急,你叫我怎么不急?”我开始生闷气,然后趁着这股气没消,让她收拾东西走人。
然后,就像要将一件事完成一样,我去嫖娼。我低着头跟着那分 不清年龄的妓女走,往后我将知道她有着一具童稚的身体而在性爱上 却是我的祖母。我控制不住紧张的情绪,虽然我喝了很多酒而且仍在喝,我提着酒瓶。我躁动得难受。倒不是害怕被抓住,而仅仅只是意 识到那件事注定要发生,而她痛苦地闭上眼,我的心情很复杂,这是 我第一次干这事儿。当我走向那孤独而荒凉的房间时,我感觉快要爱上对方了。以前这里是一排活动工房——建筑工的宿舍,也许只用了一个下午便建好,然后也只用了一个下午便拆毁,但不知为什么就留下这一间。我们踩着瓦砾走过去,推开门时,那些气味儿像是长了脚扑过来。没有窗户,没有枕头,只有一床破棉被以及一张与其说是白还不如说是黑的床单,我感到头昏脑涨,无数个老男人曾躺在这里,毫无疑问。有的得了疝气,全身的斑点,到现在还能闻到他们的烟味,他们坐在这里,用铁钳般的手抓住她的头发让她低下头。我那缥缈的爱好像在这里稍稍得到依附,我忧伤地看着这个从阳光中走进室内的可怜的人的阴影。但是她熟练的动作惊醒我,就像扯掉一根线,那些衣裳便全然滑落,她的臀部移动着,将身体移到床中央,然后像是递一盘瓜子那样将自己递过来。我还在错愕之时,听到她沙哑地说:“脱呀。”我脱了,悲哀地躺在她身边,任由她爬上来对着我碾来碾去,她带着极大的嘲讽哼叫着:“啊——啊——啊。”谁知道她脑子 在想什么呢?她的身体在我身上心不在焉地碾动着,嘴巴在无聊地哼 叫着,就像一只磨盘将我的大腿骨压得很痛,“啊——啊”就像是在早晨的山坡上练嗓子,直到她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才茫然地看我一 眼,然后从床边抽来一张纸扔给我。这他妈的和卖一碗面卖一碗豆腐脑卖一根油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一门生意!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 嘴上却忧伤地说:“你应该去念书。”她说:“念过。”我说:“你可以好好做点别的,比如去当一名家庭主妇。”她说:“你们怎么都喜欢说这个,你们可真好玩儿。”我沉默下来,她接着说:“不就是一道缝儿 吗?”这句话让我惊愕很久,佑生你跟着我念,你念着念着就一定能念出深意来。
( “不就是|一道|缝儿|吗?”宏梁比画着念,“不|就是|一道缝|儿 吗?”一阵风将沙土吹到窗户上。光线晦暗不堪,一点朝气也没有。大 半天都会这样,直到雨下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