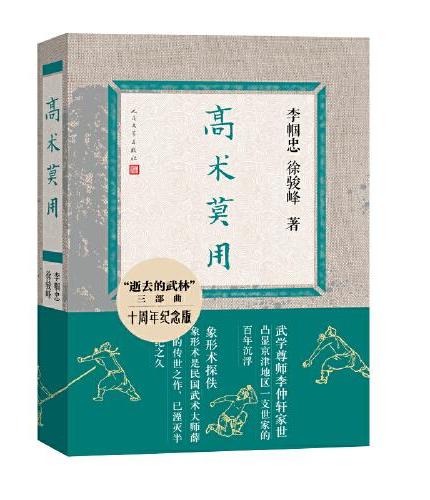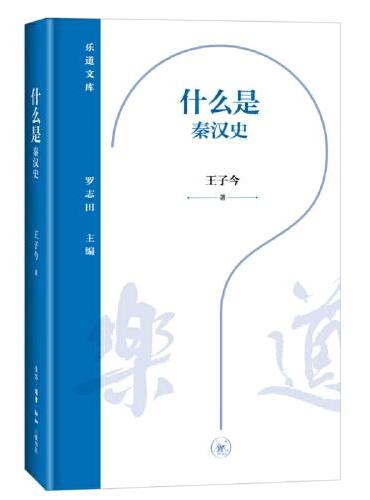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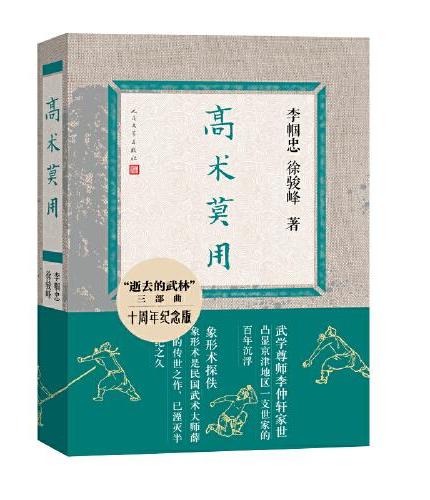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NT$
250.0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NT$
449.0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NT$
352.0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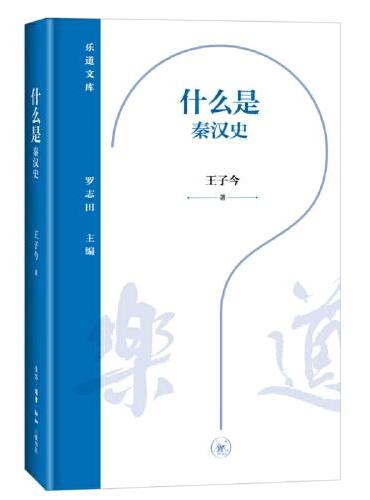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NT$
367.0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NT$
500.0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NT$
500.0
|
| 內容簡介: |
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大家席慕蓉最新散文集。
席慕蓉用一颗澄澈的诗心,来体认生命中幽微辽远的感动与牵挂;用温润入心的文字,讲述时光长河里绵长的喜悦与哀愁。童年动荡年月里的辗转与彷徨,初踏蒙古原乡的悸动与澎湃,与灵魂相契的友人的倾心与交流……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她与时间握手言和。
|
| 關於作者: |
席慕蓉,祖籍蒙古,生于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于台湾。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赴欧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
在国内外举行个展多次,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金鼎奖最佳作词及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担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授多年,现为专业画家。
著作有诗集、散文集、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读者遍及海内外。近十年来,潜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乡为创作主题。现为内蒙古大学、宁夏大学、南开大学、呼伦贝尔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校的名誉(或客座)教授,内蒙古博物院荣誉馆员,鄂温克族及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
诗作被译为多国文字,在蒙古国、美国及日本均有单行本出版发行。
|
| 目錄:
|
辑一短歌
琴声3
邂逅4
偶遇5
画笔6
孕妇8
伴侣10
我的支持者11
哀伤的时代13
冬日的午后14
麻叶绣球16
短歌18
小笔记之一19
小笔记之二20
信仰22
晓风23
秋天的晚上24
李安26
小笔记之三28
小笔记之四29
主客易位30
别离32
小笔记之五34
仰望35
丝36
诱惑38
阴山下39
草原骗局40
洛阳李家营41
老课本·新阅读42
辑二关于挥霍
关于挥霍49
追寻之歌56
如花的绽放61
线索64
舞者·阿月71
初老77
诗人与写诗的人81
寄友人书87
秋月90
谢函94
玫瑰的灰烬102
相见不恨晚114
太平洋诗歌节124
生命的撞击147
辑三真相
有一首诗155
天穹低处尽吾乡161
心灵的乡宴168
记忆广场178
真相184
寻找鲍尔吉188
暗伤191
重返湾仔194
古蜀三日行203
一生的专注210
真实的人生213
圣诞夜225
一如天唱228
系斜阳缆233
辑四春日行
春日行245
辑五草木篇
草木三篇305
无题315
神圣的人320
诺门罕战争326
曼德拉山岩画333
杨老师的美术课338
回望344
城川行352
附录长城之外的草香——鲍尔吉·原野371
读书记——陈丹燕385
|
| 內容試閱:
|
辑一
短歌
·
好像是在极缓慢的行进中忽然感觉到了那一闪而过的什么——诗,是与生命的狭路相逢。
琴声
站在巷口,在不知道究竟是该向左还是向右转去的时候,我听到琴声。
从绽放着深红色九重葛花簇的门庭上披洒下来,生涩而又迟疑的琴声,想必是个初初开始弹奏舒伯特的人。
在遥远的不可预知的未来出现之前,此刻,一双年轻的手,一颗年轻的心,正在试探着舒伯特曾经走过的路径。
而现在是我的下午,天空澄澈无云。
邂逅
他的米白色西装上衣在后,她的黑色连身衣裙在前,紧紧贴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仿佛有一种无言的呼应,当她从镶着金边的镜子里瞥见这幅画面的时候,不禁屏息。多么像是赫奈·马格里特(RenéMagritte)的一幅画啊!
许多隐秘的愿望,许多无法宣泄的情绪,竟然会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这象征完全符合超现实主义的要求,尤其是赫奈·马格里特的绝对真实和绝对荒谬的搭配。
室外有人在轻声催促,于是,她对镜涂上口红,然后微笑着打开了门,该她上场了,舞台下众多的观众正在等待。
更衣室里,那两件悬挂着的衣服也在安静地等待着落幕之后的离别。
偶遇
两个女孩坐在巴黎歌剧院门前的石阶上,聊得正欢。
一个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一个是黑发棕眸的印度人,却有着极为相似的气质,应该是学艺术的学生。年轻的像小鹿一般削瘦而又结实的身体上,都穿着相同的衬衫和牛仔短裤,一样把头发梳到脑后扎成辫子,露出光洁的额头,双眼也和小鹿的眼睛一样,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热情。
在石阶上,其实散坐着一大群花花绿绿的观光客,但是,在众多的人群里,我只看见了她们两个。
应该是同学,也是相交甚久的好朋友了,乘着暑假,结伴远行,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可是,然后呢?
再相似的气质,再相似的热情,却有着太多不能相似的背景,年轻时如此心契如此亲密同行的朋友,再过几年,也只能各奔东西了吧?
缓缓行过这两个女孩的身旁,我心疼痛,强烈地怀想着当年我的那些同学和朋友,不知道她们此刻身处在什么样的城市里,有着什么样的心思?
画笔
画了几十年油画,却始终不能忍受洗笔剂的强烈气味,会引发头痛,所以,我只好养成了在每次画完之后才用肥皂洗笔的习惯。
这样本来就会使得用笔的数量增多,再加上我又有点洁癖,只要颜色或者笔触的大小轻重稍有不妥,就想换笔,好像必得要手握一支洁净又合用的笔,才可能面对新的改变,因此,往往一天画下来,光是在水龙头下清洗那大大小小几十支画笔,就要用上一两个钟头。
我当然知道还有不少比较省时省事的方法,奇怪的是我也并不想改变。好像多年以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洗我的笔,一面回味和反省这一天的工作成绩,这种在疲倦中掺杂着少许亢奋,有时懊恼有时自豪的状态,竟成为生活里只有自己才能品味的享受了。
这或许可以算是一种职业上的怪癖,我因此而很爱买画笔,每次遇到机会就要挑选,在画室的角落里总是摆着过多的笔,轮替着使用,装笔的陶器,也都是朋友们给的。
不过,其中有一把洗得干干净净的画笔,是少年时一起习画的朋友在多年之后转送给我的,我却始终舍不得用,只好变成收藏品了。放在画室一角,我常常揣想,在学画的这条长路上,到底还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在中途偶然放下了笔,以为只是暂别,却没想到从此再也回不到原处来了呢?
孕妇
火车从列日城开出之后,大概半个钟头,就到了鲁汶,因为是国际快车,所以并不停靠,小小的车站很快就落在后面,远远望去,一切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包括那些空寂的月台。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宝芬在月台上等车回布鲁塞尔的时候,看见一位孕妇也在等车,她身穿黄色露肩薄纱衣,那天虽说是夏日,温度依旧偏低,少妇却不以为意,神情自若地站在我们侧前方。
宝芬转头告诉我说:“听说孕妇就是这样,特别不畏寒,刀枪不入的。”
那时的宝芬要去美国做新娘,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带着维平刚穿过的新娘礼服,我留她在宿舍住了几天。那一阵子,我也刚开始和海北约会,所以周末才会到鲁汶大学来玩。
我们对着那个容光焕发的孕妇看了又看,有生命在体内孕育着,是无法想象的事,却似乎也离我们很近了,是令人又害怕又受它引诱的渴望。
在那天以后,我常常揣想,我可能也会结婚,结婚之后,也会有小孩,推着婴儿车在街上走,也会在路的转角遇见了朋友,彼此寒暄一下。
地点当然是在台北,也许是在福州街口的树荫底下(那是我上大学时惯走的路,再往前去就是外婆住的厦门街),朋友当然会低头端详我的孩子,婴儿车是深蓝色的,篷罩边上镶着白色的蕾丝花边……
想象的画面总是到这里就停了。
因为,不知道未来的婴儿是男是女,所以只能到此为止——会有个婴儿,睡在小小的缀着花边的推车中。
而我,就穿着黄色的薄纱衣裙,在树荫下容光焕发……
伴侣
从美术馆出来,独坐在布鲁塞尔市区的咖啡店里。对面一对老夫妇坐定了,正商量着要点些什么,妻子把菜单拿在手中研究,丈夫就斜靠着过去一起看。我想他们在家大概也是这样,她习惯在小事上做主,而他总是在旁边跟着凑兴吧?阳光从嵌花玻璃窗照了进来,红色橙色的光点晕染在他米白的西服外套上,再反映到两人微微笑语着的面颊之间,忽然觉得幸福就是这样,就在眼前。
听口音是美国人,鬓发都已花白的夫妻来欧洲度假,觉得什么都很有趣却又不会太惊奇,两个人坐在一起所散发出来的喜悦与从容,好像是一杯好茶入喉之后的甘香,一杯好酒饮尽之后的温醇,都是岁月的累积和沉淀吧?
我忽然想回家了,回家去和他慢慢过日子。
我的支持者
海北过日子很有规律,一直是个早睡早起的人。可是,近几年来,不知道是否近朱者赤,他也逐渐越睡越晚,反倒是我这个夜猫子却不太能熬夜了,于是,总有几个晚上,我们夫妻二人差不多可以同时上床。
有天夜里,从浴室出来之后,我就顺手把卧室的大灯关掉,只留下两张床中间那个床头柜上的一盏台灯,人就钻进被窝了。
海北手上拿着干净的换洗衣裤,本来已经准备要去洗澡了,走了几步,忽然折回到床头柜前,俯身伸手,很仔细地把这盏台灯的光度调到最低,然后才转身走进浴室,把门关上。
屋子里顿时变得极暗,只剩下枕旁床头柜上的那一点点微光,我却全无睡意了。
这就是我的丈夫,虽然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里,他在有些地方对我几乎是处变不惊因而也好像是视而不见了。可是,从刚才他慢慢捻弱了灯光的那种无言的体贴里,又一次向我证明,他其实还是那个当年被我爱上的男子,在生活的许多细节里,总是充满了温柔的关怀。
有张相片是在新疆天山巴音布鲁克草原上,与我的卫拉特蒙古朋友们合照的(一九九二)。他因为接纳了我,也就欢欢喜喜地接纳了我的朋友和我的族人,支持我的一切,我感激他。
哀伤的时代
——读《阳春白雪集》
凡是认识李霖灿先生的朋友都知道,这位故宫的学者只要一谈起玉龙山,那原是温和从容的长者风范,就马上转变成只有年轻人才可能拥有的勃发狂热,开始无限神往地追述四十多年以前,八千里路之外的那座太古雪山的种种美丽与惊奇。作为读者与听众之一的我,在敬爱仰慕的同时,每次心里总会掺杂着几分不忍与同情,是很难说清楚的矛盾情绪。
想不到,这种矛盾,如今却让李霖灿先生自己在书里说出来了,是在第九十三页的最后一行,先生对他的朋友李晨岚所下的一句评语:“真是一个对雪山有深眷的画家,却遭遇了这么一个哀伤的时代。”
就是这句话!正好也可以完全包含了李霖灿先生对雪山钟情一生,却不得不分离了一世的哀伤故事。
然而艺术家是绝不屈服的!所以他以文字、图画,以自己和许多人对玉龙大雪山的种种痴情完成了这本《阳春白雪集》。(书名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决定,书成却已是一九九二年。)用五十多年岁月完成的这本书,是李霖灿先生向我们提出的证明——即使整个时代都哀伤如此,人,也绝对可以用艺术品和文学创作来反击和抗衡。
冬日的午后
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自己认定的专业是绘画,也可能是要闪躲诗集畅销所带来的一些困扰,有几年,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是在向谁和向什么赌气,竟然不再提笔,硬生生地把想要写诗的渴望压抑下去。即使后来慢慢开始再写,也发表得少了,而且,不管是人前人后,都很不愿意被归类为“诗人”。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八十八岁的父亲在德国逝世,我在整理他的藏书时,意外地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英美现代诗选》,六百多页的平装袖珍版本,还留有翻读过的痕迹。
父亲生前在波昂大学的中亚研究所里教了多年的蒙古语文,平日自己也喜欢钻研蒙古的历史与文化,却从没听他谈起过现代诗。因此,在满书架的蒙文或者汉文的文史书籍之中,忽然出现了这样一本英文的现代诗选,的确让我觉得有些惊讶。
是不是因为女儿出了诗集,才让父亲在书店浏览时偶尔起意买下这本书,好看一看别人是如何下笔的呢?
原来,平日不动声色的父亲,对于女儿忽然成了“诗人”这件事,还是很欣慰的。
书在手中,很小很厚很温暖,几十位诗人的肖像印在封面和封底,每个人所占的地方小得不能再小,显得模糊而又拥挤。然而,翻开书来,他们印在书页上的诗句却清晰无比,每一首诗几乎就是一个浩瀚深邃的宇宙。
诗,是何等神秘神奇神圣的事物!可以让我们在瞬间进入一个原本是完全陌生的灵魂深处,隔着那么遥远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和诗人素面相见,却发现那其实就是遍寻不获的另一个自己,在那一刻,心中难以言说的了悟和满足,伴随着如闪电般战栗的狂喜。
对诗的渴望,是生命本身最纯净的企求,任何附加的解释,都是多余的。
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了进来,手中握着这一本诗集,我忽然发现自己正在不断地轻声自语:“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是的,我愿意。
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了进来,父亲已经走远了。在满满的书架上,都是他曾经带引我去认识的原乡故土,而此刻握在我手中的这本小书,怎么却像是他特意为我留下的轻声提示?
“要珍惜,要好好珍惜啊!”
是的,父亲。对诗的渴望,是生命本身最纯净的企求。能够进入这个自给自足的世界,真是上天赏赐给我的福分!怎么可以不去全心全意地接受和感激呢?
是的,我愿意。
麻叶绣球
在三月,你需要一棵花树。
生命要与生命互相对话,我向你保证,麻叶绣球开花的三月,必定是让人最愉悦的时光。
由许多细长枝条所组成的整丛灌木,远远望去,本身就像是一把花束。
然而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是那越追究越令人惊叹的细巧和精致。每一朵盛开的麻叶绣球都是由十几朵各自独立的白色小花所组成的,靠近细看,这些花朵虽然小如珠粒,却美得不可方物,是一朵微型的重瓣芙蓉或玫瑰,有时更盛放得像一朵重瓣的白莲,十几朵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饱满的花球,就像是一把微型的新娘捧花。然后,再细看,从枝条上伴随着嫩绿的新叶斜斜伸出的,还有更多更幼小的花蕾,有些在蓓蕾边缘已经绽出白色的花瓣,有些还只是青绿色的小花苞,顺着枝条一路寻找下去,总有比原先看到的更为细小更为嫩绿的蕾与叶,几乎是无止无尽,却又都在精神抖擞地准备着。
整个三月,如果你有一株麻叶绣球,就好像在你的院墙边上,住着一位古波斯的画匠,一丝不苟,精确而又细致地,用工笔淡彩慢慢在勾勒和点染,为你描绘出一幅蕴藏着无限惊喜的细密画来。
此刻在我的书桌上,有一个细长透明的玻璃瓶,瓶里正插着三枝细长的枝梗,以难以形容的优雅在空中横伸或回转,那许多朵饱满的白色花簇偶尔因为碰触的缘故,就会在枝梗的尖端微微颤动,让我不得不为此而分心停笔,细小的花瓣落在稿纸上,我怎么也不舍得拂去,这就是每个生命都应该珍惜的当下吗?
生命与生命需要互相对话,在三月,最好的倾诉对象是一株麻叶绣球。
短歌
木化石切割而成的桌与凳就摆在我们的樱花树下。花开正盛,桌面与地面之上却已铺满了一层绯红的落英。
今天早上刚开门去拿报纸的时候,有几朵离枝的樱花,就轻轻轻轻地落在我眼前的石桌之上。
深灰和浅灰色夹杂的桌面,一圈又一圈斑驳的年轮犹在,却已转化成石,是要经过多少万年的侵蚀与渗透才会转变成如此坚硬的质地?
那几朵樱花落下之时,颜色还是娇嫩的水红,如此湿润柔软的花瓣在轻触这木化石冷硬桌面的那一刻,彼此会有怎样的迷惘呢?这样的相遇使我着迷。
“好像是在极缓慢的行进中忽然感觉到了那一闪而过的什么——
诗,是与生命的狭路相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