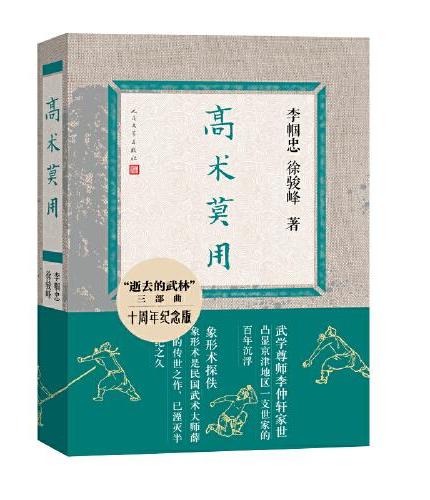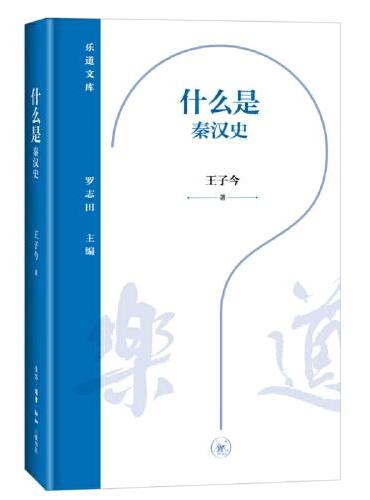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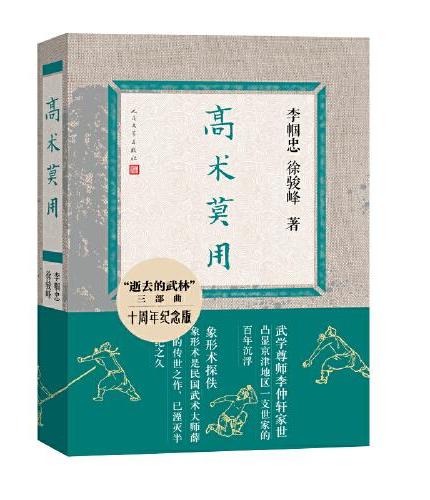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NT$
250.0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NT$
449.0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NT$
352.0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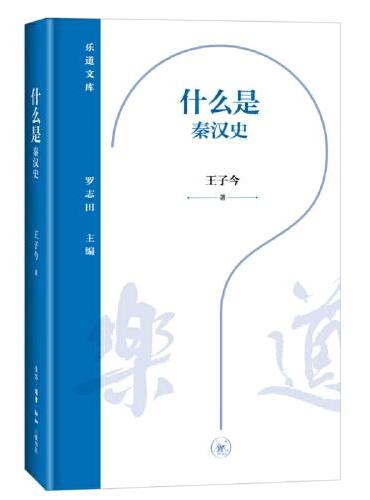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NT$
367.0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NT$
500.0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NT$
500.0
|
| 內容簡介: |
《与大师一起读历史:李鸿章结论》从梁启超一生所著千余万字作品中,精选各个时期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各类文章,从中可管窥中国近代史上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伟人渊博的学问与卓越的贡献。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广涉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学贯中西,囊括古今。一生著述甚丰,影响不止一代人。
|
| 關於作者: |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
| 目錄:
|
导读梁启超——一部读不完的书
第一部分 政论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公德
论自由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少年中国说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论正统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新民议
论进步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痛定罪言
复古思潮平议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呵旁观者文
拟讨专制政体檄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人生观与科学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第二部分 随感
成败
惟心
慧观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破坏主义
善变之豪杰
豪杰之公脑
答客难
忧国与爱国
傀儡说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倡设女学堂启
干涉与放任
中国之社会主义
三十自述
第三部分 亲历
戊戌六君子传
《李鸿章》结论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人权与女权
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
附录:梁启超生平大事记
编者说明
|
| 內容試閱:
|
论不变法之害
(1896年8月19日)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订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薾蘼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徧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岛,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懵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时募集,半属流丐,器械窳苦,馕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猬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敝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跸,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扶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相、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龂龂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威廉第一、睦仁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飏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已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砮,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余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浡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痒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扆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衂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衂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械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其彼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远猷,乌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乌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责以治兵,欲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乌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专,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欲其有成,乌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欲其振厉,黾勉图功,乌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官层累,非奔竞末由得官,非贪污无以谋食,欲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于公义,自非圣者,乌可得也。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肖,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华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法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已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于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去岁李相国使欧洲,问治国之道于德故相俾士麦,俾士麦曰:“我德所以强,练兵而已。今中国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练,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于此二者,中国不足强也。”今岁张侍郎使欧,与德国某爵员语,其言犹俾相言。中国自数十年以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众口一词,不可胜辨。既闻此言也,则益自张大,谓西方之通人,其所论固亦如是。梁启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无义战,墨翟非攻,宋钘寝兵之义,以告中国,闻者必曰:以此孱国而陈高义以治之,是速其亡也。不知使有国于此,内治修,工商盛,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彼美国是也。美国兵不过二万,其兵力于欧洲,不能比最小之国,而强邻眈眈,谁敢侮之?使有国于此,内治隳,工商窳,学校塞,才智希,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陆军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战而土三胜焉,而卒不免于今日,若是乎国之强弱在兵,而所以强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则必涤其滞积,养其荣卫,培其元气,使之与无病人等,然后可以及他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以甲胃,予之以戈戟,而曰尔盍从事焉,吾见其舞蹈不终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
然则西人曷为为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启封疆以灭社稷者,何国蔑有?吾深惑乎吾国之所谓开新党者,何以于西人之言,辄深信谨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于中国者,若练兵也,置械也,铁路也,轮船也,开矿也,西官之在中国者,内焉聒之于吾政府,外焉聒之于吾有司,非一日也。若变科举也,兴学校也,改官制也,兴工艺、开机器厂也,奖农事也,拓商务也,吾未见西人之为我一言也。是何也?练兵,而将帅之才,必取于彼焉;置械,而船舰枪炮之值必归于彼焉;通轮船、铁路,而内地之商务,彼得流通焉;开矿,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无不仰给之于彼,彼之士民,得以养焉。以故铁路、开矿诸事,其在中国,不得谓非急务也;然自西人言之,则其为中国谋者十之一,自为谋者十之九。若乃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强也,宜其披肝沥胆,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权、沾大利于中国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乌肯举彼之所以智所以强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为中国谋者,实以保护本国之权利耳,余于光绪十年回英,默念华人博习西学之期,必已不远,因拟谒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示振兴新学之道,以储异日传播中华之用。迨至某国,投刺晋谒其学部某大臣,叩问学校新规,并请给一文凭,俾得偏游全国大书院。大臣因问余考察本国新学之意,余实对曰:欲以传诸中华也,语未竟,大臣艴然变色曰:汝教华人尽明西学,其如我国何?其如我各与国何?文凭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见华官,每以谀词献媚,曰:贵国学问,实为各国之首。以骄其自以为是之心,而坚其藐视新学之志,必使无以自强而后已。今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为谰言以污蔑西人,无可疑也。而其言若此,吾欲我政府有司之与西人酬酢者,一审此言也。李相国之过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厂主人,盛设供帐,致敬尽礼,以相款宴,非有爱于相国也,以谓吾所欲购之船舰枪炮,利将不赀,而欲胁肩捷足以夺之也。及哭龙姆席间一语,咸始废然,英、法诸国,大哗笑之。然则,德人之津津然以练兵置械相劝勉者,由他国视之,若见肺肝矣。且其心犹有叵测者,彼德人固欧洲新造之雄国也,又以为苟不得志于东方,则不能与俄、英、法诸国竞强弱也。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德以后起,越国鄙远,择肥而噬,其道颇难,因思握吾邦之兵权,制全国之死命。故中国之练洋操、聘教习也,德廷必选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习而兼统领之任。今岁鄂省武备学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只任教习,不充统领,而德廷乃至移书总署,反复力争,此其意欲何为也?使吾十八行省,各练一洋操,各统以德弁,教之诲之,日与相习,月渐岁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国绿营、防勇,一无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号令之是闻,如是则德之所获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诸国下,此又德人隐忍之阴谋,而莫之或觉者也。当中、日订通商条约之际,德国某日报云:“我国恒以制造机器等,售诸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得制造之要领,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国,恐德国之商务,扫地尽矣。”去岁《字林西报》载某白人来书云:“昔上海西商,争请中国,务须准将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则谓此事非西国之福,今按英国所养水陆各军,专为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起见,所费不赀,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
呜呼!西人之言学校、商务也,则妒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则爱我如彼。虽负床之孙,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不此之务,而惟彼之图,吾甚惜乎以司农仰屋艰难罗掘所得之金币,而晏然馈于敌国,以易其用无可用之物,数年之后,又成盗粮,往车已折,来轸方遒,独至语以开民智、植人才之道,则咸以款项无出,玩日愒时,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万也。吾又惑乎变通科举、工艺专利等事,不劳国家铢金寸币之费者,而亦相率依违,坐视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机会,而不肯一导之也。吾它无敢怼焉,吾不得不归罪于彼族设计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诗》曰:“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1896年10月27日)
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各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补破衲,愈补愈破。务治事者,用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务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及其究也,有不受节制,出于所防之外者二事:曰彝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汤沃雪,遂以灭亡。于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则适足为自敝之具而已。
梁启超曰:吾尝读史鉴古今成败兴废之迹,未尝不悁悁而悲也。古者长官有佐无贰,所以尽其权,专其责,易于考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露》所述官制,莫不皆然,独《周礼》言建其正,立其贰,故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复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凡正皆卿一人,凡贰皆中大夫二人,此今制一尚书、两侍郎之所自出。《周礼》伪书,误尽万世者也。)汉世九卿,尚沿斯制。(汉、晋间太常等尚无少卿,后魏太和十五年始有之。)后世惧一部之事,一人独专其权也,于是既有尚书,复有侍郎,重以管部,计一部而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之诚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诿,无一事能举也。古者大国百里,小国五十,各亲其民,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之地,犹今之县令而已。汉世犹以郡领县,而郡守则直达天子。后世惧亲民之官,权力过重也,于是为监司以防之;又虑监司之专权也,为巡抚、巡按等以防之;又虑抚按之专权也,为节制、总督以防之。防之诚密矣,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长官,犹惧不得当,无暇及民事也;朘万姓脂膏,为长官苞苴,虽厉民而位则固也。古者任官,各举其所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汉、魏之间,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书,而天下号得人;毛玠、崔琰为东曹掾,而士皆砥砺名节。后世虑选人之请托,铨部之徇私也,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年劳资格之法,孙丕扬定为掣签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而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古者乡官,悉用乡人,(《周礼》《管子》《国语》具详之。)汉世掾尉,皆土著为之,(《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可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盖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后世虑其舞弊也,于是隋文革选,尽用他郡,然犹南人选南,北人选北。(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明之君相,以为未足,于是创南北互选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可到官,非贪污无以自存也。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而官为缀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汉世三府,开阁辟士,九卿三辅郡国,咸自署吏,(顾氏《日知录》云: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职不举。)所以臂指相使,情义相通。后世虑其植党市恩也,于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诚密矣,然长佐不习,耳目不真,或长官有善政,而末由奉行,或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见也。古者用人皆久于其任,封建世卿无论矣,自余庶官,或一职而终身任之,且长子孙焉。
爰及汉世,犹存此意,故守令称职者,玺书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终不迁其位,盖使习其地,因以竟其功。后世恐其久而弊生也,于是定为几年一任之法,又数数迁调,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礼者使之掌刑。防之诚密矣,然或欲举一事,未竟而去官,则其事废也;每易一任,必经营有年,乃更举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盘踞不去,世其业者,乃在胥吏,则吏有权而官无权也。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汉世亦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属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议国政,(余别有《古议院考》。)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后世恐民之讪已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耎,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其权重大,其体尊严。(三公者一相、二伯。)汉制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盖君则世及,而相则传贤,以相行政,所以救家天下之穷也。后世恐其专权敌君也,渐收其权归之尚书,渐收而归之中书,而归之侍中,而归之内阁;渐易其名为尚书令,为侍中,为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平章政事同三品,为大学士;渐增其员为二人,为四人,乃至十人;渐建其贰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协办大学士。其位日卑,其权日分,于是宰相遂为天子私人。防之诚密矣,然政无所出,具官盈廷,徒供画诺,推诿延阁,百事丛脞也。古者科举皆出学校,教之则为师,官之则为君,汉、晋以降,犹采虚望。后世虑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于是为帖括诗赋以锢之,浸假而锁院,而搜检,而糊名,而誊录,而回避。若夫试官,固天子近侍亲信之臣,亲试于廷,然后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严封其宅焉;所至严封其寓焉,行也,严封其舟车焉,若槛重囚。防之诚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筹赌戏,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而关节请托之弊,卒未尝绝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雕落,士气不昌,徒使无忌惮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古者疑狱,泛与众共,悬法象魏,民悉读之,盖使知而不犯,冤而得伸。后世恐其民之狡赖也,端坐堂皇以耸之,陈列榜杨以胁之。防之诚密矣,然刁豪者益藉此以吓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会例案,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时巡,与国人交,君于其臣,贱亦答拜,汉世丞相谒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恐天泽之分不严也,九重深闭,非执政末由得见。防之诚密矣,然生长深宫,不闻外事,见贤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则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也。凡百庶政、罔不类是,虽更数仆,悉数为难。悠悠二千岁,莽莽十数姓,谋谟之臣比肩,掌故之书充栋,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谬种流传,遂成通理,以缜密安静为美德,以好事喜功为恶词,容容者有功,峣峣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禄保位为第一义,缀学者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大本既拨,末亦随之,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改科举,必曰恐开躁进之门也;语以铸币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辙也;语以采矿产,必曰恐为晚明之续也;语以变武科,必曰恐民挟兵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纪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张。譬之忡病,自惊自怛,以废寝食;譬之痿病,不痛不痒,僵卧床蓐,以待死期。岂不异哉!岂不伤哉!
防弊之心,乌乎起?曰:起于自私。请言公私之义。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虽然,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言公之为美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虽然,向者众人所失之权,其不能复得如故也,于是乎不知权之所在。故防弊者,始于争权,终于让权。何谓让权?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曰议以闻,是让权于部院;部院议可,移文疆吏,是让权于督抚;督抚以颁于所属,是让权于州县;州县以下于有司,是让权于吏胥。
一部之事,尚、侍互让;一省之事,督抚互让;一君之事,君国民互让。争固不可也,让亦不可也。争者损人之权,让者损已之权。争者半而让者半,是谓缺权;举国皆让,是谓无权。夫自私之极,乃至无权。然则防弊何为乎?吾请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