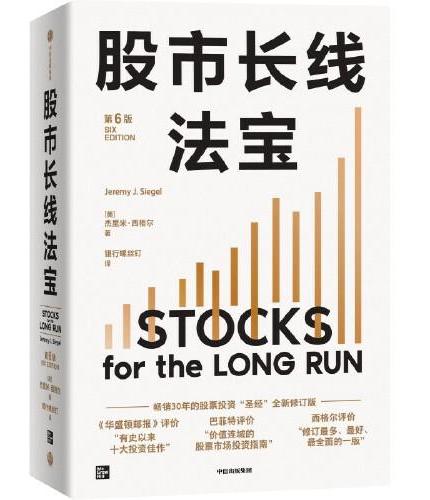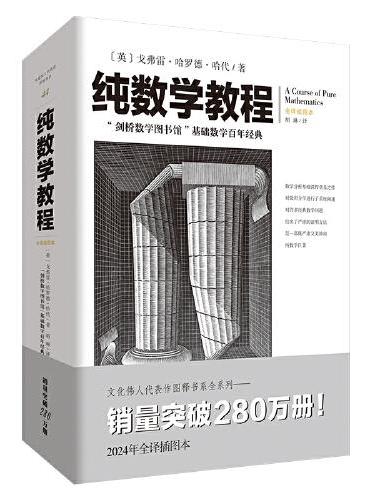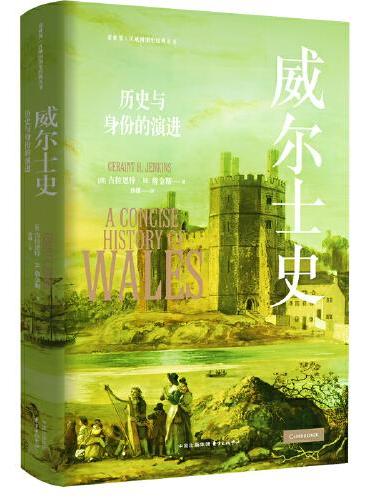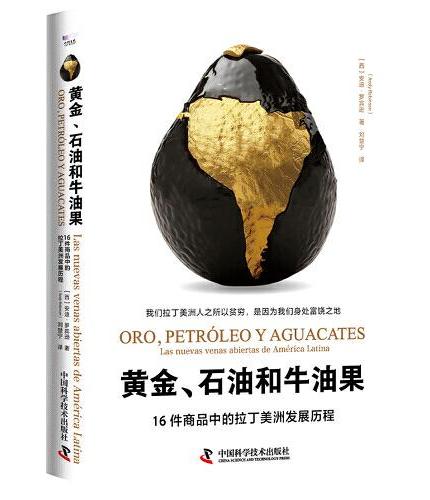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夺回大脑 如何靠自己走出强迫
》
售價:NT$
299.0

《
夏天,19岁的肖像(青鲤文库)岛田庄司两次入围日本通俗文学奖直木奖的作品 ,同名电影由黄子韬主演!
》
售價:NT$
225.0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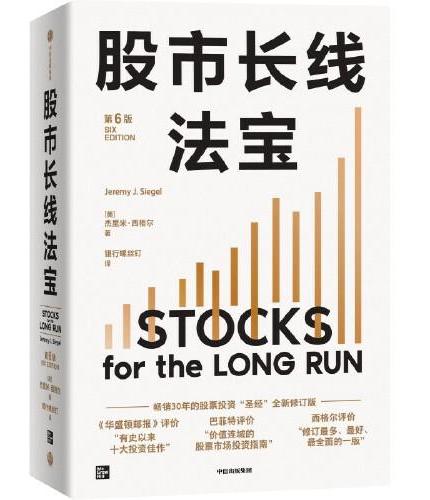
《
股市长线法宝(第6版)
》
售價:NT$
640.0

《
中文版SOLIDWORKS 2024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实战案例版)
》
售價:NT$
4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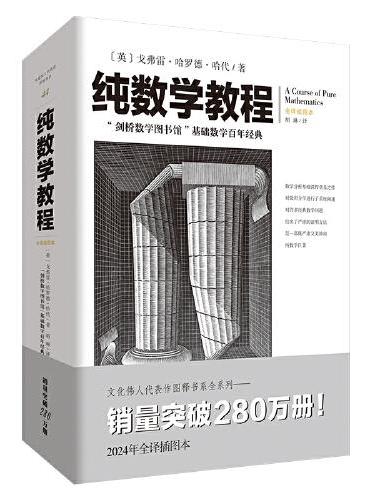
《
纯数学教程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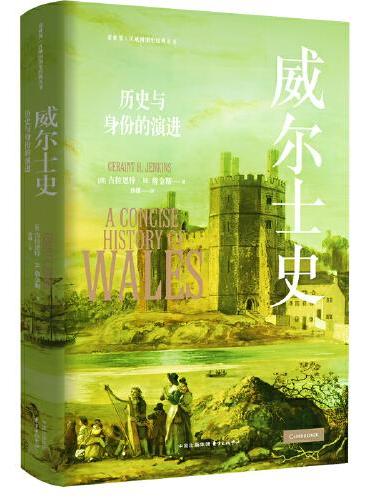
《
威尔士史:历史与身份的演进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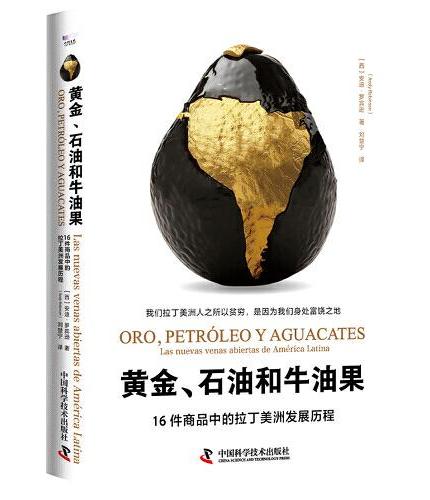
《
黄金、石油和牛油果:16件商品中的拉丁美洲发展历程
》
售價:NT$
395.0
|
| 編輯推薦: |
回望俄罗斯被战争、饥荒、革命和集权统治笼罩的残酷历史。
大清洗中,莫洛托夫一人就签署了43569份死刑判决书。
十二月党人雅库什金:“在西伯利亚的矿坑里,请坚持你的尊严。”
索尔仁尼琴:“25年间,我们竟然没有追捕任何一个人,没有让任何人出庭受审。”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以莫洛托夫的居所和其藏书室中的藏书为起点,以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地点为线索,追索俄罗斯历史中光辉与黑暗时刻。作者不仅关注这个国家被战争、饥荒、大屠杀和集权统治笼罩的过去,也同时挖掘伟大作家、诗人的宝贵遗产——他们高尚的人道主义、被扭曲的视野、民族主义的幻梦、史诗般的对战争和恐怖的回应,以及他们对精神价值和自然科学的笃信。
|
| 關於作者: |
蕾切尔·波隆斯基 (Rachel
Polonsky),剑桥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讲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观察家》、《新政治家》等杂志专栏作家,另著有《英语文学与俄国美学的复兴》(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Russian Aesthetic Renaissance)。
|
| 目錄:
|
前 言
第一章 罗曼诺夫巷
第二章 61号房
第三章 蒸气浴
第四章 卢奇诺
第五章 莫兹辛卡
第六章 诺夫哥罗德
第七章 旧鲁萨
第八章 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第九章 塔甘罗格
第十章 沃洛格达
第十一章 阿尔汉格尔
第十二章 摩尔曼斯克与巴伦支堡
第十三章 阿尔善与伊尔库茨克
第十四章 乌兰乌德与恰克图
后 记
译名对照表
|
| 內容試閱:
|
前言
这是莫洛托夫曾经住过的一套公寓。客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一台老式幻灯机。
背对着一扇能俯瞰罗曼诺夫街的窗户,我扶着幻灯机上的铜质提手,眯起眼睛,透过齐腰高的桃木镜筒上的玻璃镜头,伴着胶片传送架“咔嚓咔嚓”的运转声,看到了一张张模糊的图片。先是一户人家在克里米亚海滩上度假的情景,女士们穿着旧式泳装坐在海边的石头上,支着手遮挡阳光;一暗一明,画面换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萨满巫师;然后是一群农村妇女跳舞的样子;再后来又换成了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美丽的广场和木头房子??
“好好研究吧,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知道该怎么做。”我的这位银行家朋友手上提着一串钥匙,操着一副慢条斯理的迷人腔调说道。
昨天,在这条街上另外一间罗曼诺夫公寓里专门为欢迎他来到莫斯科而举办的酒会上,我俩刚刚见过一次面。与他碰杯之时,我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其实我并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写小说的氓流学者??而他也像某些投资银行家那样,坚称自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而不是黑心资本家。他对我说,他真正的志向在政治上。他曾经怀着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花费十多年时间,在故乡美国德克萨斯州为民主党工作。
然而当他对我提起莫洛托夫的藏书室之后,我们的谈话立刻就热络起来。我知道,他刚搬进的这所公寓(就在我家楼上),曾是斯大林的最忠实追随者莫洛托夫晚年的居所。但之前我并不知晓,莫洛托夫的孙女在将这所公寓出售给外国人时,居然将一些财物也留在了其中,包括数百本书籍。这些书中,有的是别人送给莫洛托夫的,有些他还亲手批注过。然而,现在它们却尘封在公寓后廊的书架下层,被彻底遗忘了。
我的这位银行家新朋友在递给我那串钥匙的时候,一定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怎样的大礼。当我第一次独自待在莫洛托夫这富丽堂皇的故居,环视精心粉刷雕琢过的四壁和高高在上的天花板时,心中有一种到达了目的地的感觉。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自打在剑桥大学那个忙碌的春天,我突发奇想地要搬家,并最终制定了一个搬到莫斯科的计划之后,这里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之一。
问题是,我该怎么对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这间废旧的藏书室呢?我到莫斯科来,并不是想要这样研究书籍的。从小到大,长辈们一直教育我要珍惜书籍。但眼前的这些败章残卷,却来自一个至今依然影响深远的邪恶时代。它们过去的拥有者,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间,曾是约瑟夫?斯大林最信赖、最亲密的同志,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脑。他是斯大林一系列罪行的帮凶,也是制造了无数残暴屠杀惨剧的刽子手。当我从摇摇欲坠的架子上往下搬书的时候,却忽然回忆起少年时代自己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夜莺狂语》(Nightingale
Fever)。那本书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由牛津大学学者罗纳德?辛格雷编纂的,关于四位俄罗斯诗人作品和生平的研究性书籍。安娜?阿赫玛托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夜莺”们即便在莫洛托夫参与创建并长期主政的红色帝国里受尽最残酷的迫害,依然在不断“歌唱”。当时的我倍感震撼,不仅因为在俄罗斯这个国度诗歌的力量居然得到了政治上的确认,更是由于克林姆林宫高墙里的大人物们对这四位诗人行为的反应。但是在我看来,在父亲给我的那本关于诗歌的书里,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历史的人只不过是些幽灵、野兽罢了。
我读过这四位诗人的诗。然而除了各种韵脚和节奏的堆砌,以及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诗词艺术谦逊外表下所隐藏的“荒唐现实的缩影”之外,当年的我几乎读不出别的内涵。我清晰地记得一些诗句,比如曼德尔施塔姆首部诗集《石头》中某首诗的前两句:
肉体给了我——我拿它怎样处理,
如此完整又分明是我的肉体。
我初读这首写于1909年的诗歌就觉得它简单而又意味深长。而我接触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是因为得知他在写下此诗30年后死于古拉格集中营。诗人继续这样问道:
为了享受这生活的安静的快乐,
我该感激谁呢?请您告诉我。
我既是园丁,也是花朵。
在世界的牢狱中不止我一个。
历史总是很诡异,充斥着无数离奇的因缘际会。斯大林曾说:“如果世界上没有莫洛托夫,那么很有必要创造一个出来。”而恰恰是这个莫洛托夫造就了这几位“夜莺”诗人充满悲剧色彩的伟大成就。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曾在她的回忆录《对抗希望的希望》中提到,曼德尔施塔姆在他讽刺斯大林的诗(正是这部作品导致他1934年第一次被捕)中描写的“细脖子官僚”形象,来源于“莫洛托夫伸出衣领的细长脖子上顶着个小脑袋”的样子。曼德尔施塔姆曾指着莫洛托夫的画像说:“他就像个色鬼。”然而莫洛托夫却鬼使神差般地对曼德尔施塔姆发了一番善心。曼德尔施塔姆20世纪20年代后期居住在亚美尼亚,当时他正处于才思枯竭的状态之中。莫洛托夫曾以个人身份探访那里,并交待当地党组织要妥善照料这位诗人及其家属。娜杰日达回忆道:“在亚美尼亚,曼德尔施塔姆的才华得以恢复,于是他开始了人生中的一个全新阶段。”
回望历史就仿佛是在观看一幅幅幻灯片。阿赫玛托娃曾说:“记忆如同幻灯片,凸显着那些彼此互不相关的片段,却留下了许多无法照亮的黑暗。”其实在来莫洛托夫故居的路上,我的脑中便已经在回忆一些往事了。
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曾经睡在父亲书房里的一张行军床上。我想到了父亲书架上尼古拉斯?博雅耶夫的《历史的意义》书脊上那一行金色的小字。当时我并没有去读那本书(后来我才知道,该书是1937年我的祖父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购买的),但书脊上那句关于“历史有它的意义”的断言,与作者的俄文名字一起,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春天一个干燥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来到了莫斯科。那一天,我与一位15岁的校友一起,从普希金美术博物馆一路走着去河对岸的布加勒斯特饭店。其实我们当时也有些辨不清方向。我们从一个冷饮摊买了冰淇淋,那是一种被称作“拉克木齐”的巧克力酥皮奶油冰淇淋,我俩都觉得它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我们走过克里姆林宫墙下的亚历山大花园,穿过红场和莫斯科河,其间还有过一段关于立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认为高明的对话(那是我这辈子经历的第一次关于这些内容的讨论)。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这两者之间某些重要的联系,并且这一讨论将一直持续下去。整个城市都给人一种空廓生硬的感觉,似乎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感觉莫斯科充满了各种被深深隐藏的秘密,而我们像是盲目的探访者,四处乱撞却无法触及它真正内在的东西。
我曾经有那么几次在附近的街区闲逛的时候经过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那天是第一次。我和朋友走着走着,就路过罗曼诺夫公寓附近,那时它里面的上百套房间还是苏联权贵阶层、政界精英和高级军官们专享的住所。记忆,此刻仿佛并不受我主观意识的支配,而是有着它自己的直觉一般。仿佛那时我记住这里的景象,就是为了与今天透过莫洛托夫故居的窗户所看到的画面作对比。此刻,我能看到窗外的克里姆林医院和莫哈瓦亚大街(当年称“马克思大街”),当时我俩一定到过这里。从后窗看出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百货公司。1986年,我曾经在那里的货架上找到一张唱片,里面是阿赫玛托娃在吟诵她那首影射斯大林时代社会恐怖的诗歌——《安魂曲》。当时莫洛托夫葬礼的守灵仪式刚刚在这套公寓里完成不久。克格勃特工们已经把当局认为重要的私人文件和照片全部查抄走了。那张唱片上阿赫玛托娃因衰老而颤抖的嗓音,似乎宣示着庞大的红色帝国正走向衰败。这样的结局与莫洛托夫毕生信仰的马列主义愿景截然不同。
我也还记得,当年自己与现任丈夫的一次毫无意义的争执。那一次,我俩与朋友们一起,待在帕什科夫大楼穹顶下的列宁图书馆地铁站。那天很冷,大家都饿着肚子(当时不比现在,没有咖啡屋之类的地方可去),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充满未知感的体验;虽然只要再走一段路就能到家,孩子正在等着我们回去享受天伦之乐。
还有一些后来的回忆。在我拿到剑桥大学奖学金几个星期前去世的那个俄语讲师的书房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曾在向苏联摩尔曼斯克运送援助物资的盟军部队中服役,也是在那时学会了俄语。后来二战结束,当俄语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阅读和俄国文学教学中去了。这位老学者以其高超的学术水准、犀利的讽刺文风、渊博的学识以及对19世纪保守思想家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的特殊兴趣而闻名。他生前没有立下任何遗嘱,除了一本对屠格涅夫《父与子》的批注之外,也再没发表其他著作。也许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能用同样的时间阅读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浪费精力撰写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学术文章呢?
在他死后,学校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房间里那些与鞋子和药瓶之类的杂物堆放在一起的书籍和论文,那都是他在充实自己的过程中留下的残迹。财务主管让我去看一眼。于是,我花数天时间作了一番整理,将它们分门别类收进了图书馆。剩下那些该扔的或是该送人的,我都可以保留下来。你知道独自一人处置逝者的这些书籍意味着什么吗?曼德尔施塔姆曾说过:“如果要我写一部自传的话,我会告诉你我读过哪些书。”那位俄语老师的藏书室告诉我他是个极富修养、深爱书籍、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的真正的学者。阿尔汉格尔斯克、莫斯科、赫尔辛基、巴黎、伦敦??他从各地购买了那些书籍,并且把购买日期和他的名字“E?桑德斯”一起写在上面。比如,有一本简装企鹅版的《犹太问题》上面写着“购于1939年”;而一本黑布封面的俄语《新约圣经》上则写着“1942年11月购于剑桥”。当年押运物资去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之时,他是不是也随身带着这本《新约圣经》呢?他在那上面写满了注释,一半法语,一半拉丁文。书中夹着一些飞虫的残骸,仿佛书签一般。还有写便条之类的东西,颇有生活气息,有老教授逝世的讣告、书店的单据、学生们的作业和退学申请、朋友们寄来的明信片,还有加瓦尔尼讽刺小说《巴黎的女同性恋们》的摘抄??很多书上都有桑德斯的批注,其中大多数都是指出排版错误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他偶尔也会做一些交叉引用,以阐释俄罗斯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我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下午,桑德斯先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双腿交叉,一边听着楼下的车来车往,一边用铅笔批注着手上的书籍。他收藏了很多苏联版本的法国文学作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还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所多玛和蛾摩拉》俄语译本,做了大量批注。
从一个人的藏书之中,能否找到一条揭示其性格本质的道路呢?《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有这样一幕描写:奥涅金离去之后,深爱着他的达吉亚娜独自待在他的书房里。她伴着墙上拜伦的肖像画和桌上拿破仑的雕像,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伴着奥涅金留在书页上的指甲印记和每一条潦草的脚注,达吉亚娜发现自己正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到处,不自觉地,
他把心灵流露在自己的笔下:
这里一个问号,
那里一个简短的词,
或者一个十叉??
旧书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总能勾起人们情不自禁探究过往秘密的欲望,仿佛其中有他们非常关注的深层含义或者精神方面的东西。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书籍是折射人们自身命运的舞台。每次看书的时候,我们总能超越其内容,领悟到更多的东西。虽说那位名叫桑德斯的俄语讲师并不是要留给我什么遗产,但那个下午我在他房间里看到的书籍足以构成一部传记了。我把其中两本出版时间隔了半个世纪的书并排放在桌上。一本是由政治流亡者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科特连斯基编纂、封面印有橙白相间图案的简装企鹅版《俄国小说选》,封面和书的侧面都被桑德斯用俄语写满了“再见”,(就像另外一本普希金作品一样)扉页上写着“1941年购于俄罗斯”。1941年,那正是英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第一年,当时代号“苦行僧”的首批援助物资到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摆在它旁边的,是桑德斯藏书中最新的一本,同样大小的简装版《北方护卫队》,1991年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版。而恰是在这一年,苏联解体了。
我自己留下了一本“异见”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关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哲学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很薄的书,一本反沙皇斗士伊凡?雅库什金在斯大林时代后期的作品集,一本契诃夫的讲演集,一套标注为“1944年购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缺少一卷的普希金全集。还有一本关于在巴伦支海惊涛骇浪中为斯大林而战的海军歌曲集,其中桑德斯夹进了一张印有苏联国歌歌词“牢不可破的联盟永远围绕在伟大的俄罗斯周围”的纸片。为了避免被学校里那些好事的财务管理员看到,我把在一箱文件中找到的几封桑德斯的情书随手夹到了几本书里。其中有一封写给一位相识几十年后再次重逢的法国女人的情书草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时光荏苒,你却从未改变??”当年他真的寄了这封信吗?我还发现了一张印着玛丽莲?梦露形象的颇有情趣的黑白明信片,画面上的梦露赤身裸体,只穿了一双透明高跟鞋,戴着钻石耳环和圆点图案的丝巾。明信片上写着一些诸如“你不要生气”之类的话,寄信人署名“蒂朵?D小姐”,日期是情人节,却不知何年。
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发现了一张护照大小的照片之后激动得够呛。那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的摩尔曼斯克,那上面的桑德斯戴着一顶俄式羊皮帽。(那个冬天正值莫洛托夫秘密乘坐一架四发动机的轰炸机飞越德占区到英国商讨英苏联盟事宜之后。当时温斯顿?丘吉尔在花园门口握住莫洛托夫的胳膊并端详了一下他的面容,顿时觉得这人似曾相识。)正是这张桑德斯年轻时代的照片,让站在他房间里踌躇许久的我,决定打扫掉盖在这堆没人要的东西上的灰尘,然后立刻乘船奔向那个极地港口。
三年之后,我那四海为家的丈夫因法律事务第一次到莫斯科出差时,用街头糟糕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我的号码。自从苏联解体前夕我们从列宁格勒毕业之后,他这还是第一次回俄罗斯。
“如今莫斯科是一个世界大都市,越来越像一座真正的城市了。”即便信号质量很差,我也能听得出他话音里的兴奋。
于是,我也决定去莫斯科一趟。不过,到了莫斯科之后,夫妻二人总不能一直住在古色古香的博雅尔饭店或者美丽的大都会酒店吧。于是我们借了一辆汽车,花费一整天在泥泞的冰天雪地里跋涉,穿梭于那些依然带着浓重苏联气息、卫生间铺着黑色大理石的公寓楼之间。晚上,在恍惚之间,我忽然发现一个穿着老式俄罗斯皮大衣的艺人坐在路边,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唱着老掉牙的民歌。为什么这些陈辞滥调依然让我感到狂喜呢?难道是因为1990年我在列宁格勒看了太多蹩脚的苏联电视节目,所以每次听到斯拉夫风格的小调都会想到月光下宽阔的河流、白雪皑皑的森林和春日阳光下的草原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沉浸在这美好的想象之中。
离开英国之前,收拾完学校里的东西,我把一些书籍和论文封进几个纸箱放到了地下室里,对自己也对同伴说,我一年半后就会回来。到莫斯科之后,我打算找个大图书馆工作,研究俄罗斯诗歌中的东方元素。可结果,一年半却变成了十年。
事实上,没过多久我就改主意了。我并没有利用这些时光去研究那些关于东方风格的学术巨著,而是写下了这本书。书中模糊地记述了我过去读过的书和去过的地方。在地图上看,克里姆林宫似乎是一个指南针的圆心,通过指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道路,掌控着周围轮廓模糊的土地。每次一有机会,我都被一时的兴致和浪漫的书生气驱动,凭直觉从家中走到克里姆林宫墙下。我也随心所愿地去过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列宁图书馆(即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号阅览室,与那些拿着塑料放大镜、衣衫褴褛的老人们坐在一起。
这座图书馆遵照总统令于1992年废弃了其名称中的“列宁”二字。历史上,它曾一度被称为“鲁缅采夫博物馆”。该图书馆最著名的馆长,被称为“俄罗斯的苏格拉底”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据说对馆藏所有图书的内容都了如指掌。关于这位馆长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学识,曾有过这样一段轶事:一群负责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程师向他展示了穿越广阔原野的工程地图,而从未去过西伯利亚的费奥多罗夫居然纠正了图上一些山峰高度的错误数据。费奥多罗夫坚信,书籍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传达了作者的思想和灵魂。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在他1903年逝世后以《共同事业的哲学》为题结集出版)中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与死亡妥协的拒绝。在他看来,人类在地球上的任务就是使逝者在肉体上复活。而那些智慧都被分门别类地尘封在图书馆中,期冀后人重新赋予它们生命(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疯狂”。博雅耶夫曾说:“人死之时的这种悲哀,世间无人能懂。”)。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费奥多罗夫一直与鲁缅采夫博物馆的藏书为伍,废寝忘食,甚至都不愿坐下。俄罗斯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来馆里跟他切磋交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罗维耶夫(曾将费奥多罗夫称为他的“导师和精神之父”)都将他视为一位天才哲学家。费奥多罗夫很反感别人为自己画像,因为他觉得从哲学的视角看,被画像的人面部表情都是装出来的,非常虚伪,只能算是艺术品,却不能体现本真。于是艺术家里昂纳德?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只能偷偷躲在阅览室书架后面,为费奥多罗夫画了一张速写肖像。
费奥多罗夫是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他认为藏书是一件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工作,而图书本身应该按照作者的生卒年月归类,就像撰写一部圣人编年史一般。在他看来,书籍是历史长河中最高尚的遗产,以最具人性的方式传承着前人的思想和成就。对他来说,要想战胜死亡,唯独唤醒先辈们的智慧才是王道。按照费奥多罗夫的理论,“学习,非责难亦非褒扬,而是回归生命本真”。
如今,列宁图书馆的管理员们正在恢复无数曾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被“镇压”(逮捕、枪毙、神秘失踪)的前辈的名誉。而在1928年10月,《红色晚报》报道称,这家图书馆已经成为“反革命学术集团”和贵族后代的“庇护所”。伟大的图书管理员、书志学家、编辑,在十月革命后担任图书馆馆长,并在1927年为图书馆新楼奠基的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于1935年被捕,受审时公开抨击老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布哈林,最终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最为血腥的1937年被枪毙。对无数起类似死亡案件负有责任的莫洛托夫,在其晚年时常会来第一阅览室消磨时间。被自己终身侍奉的苏共贬黜之后,他深入研究历史,维护着那些掌控他一生的意识形态,仍然相信它们可以指引未来。
透过阅览室巨大的边窗朝莫霍瓦亚大街望去,越过20年代海外共产主义者(诸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库恩?贝拉、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胡志明等)为世界革命工作过的前共产国际总部,可以看到山上克里姆林宫的三一门、塔楼和金顶。图书馆临近沃斯季申卡大街一侧的前庭有一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型雕像,是我们来莫斯科那年立起来的,替换掉了之前的列宁雕像(列宁曾经很讨厌这位作家)。近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年轻支持者们会聚集在雕像脚下,为电视节目拍摄表忠心的示威画面。如今被当成普京“新拜占庭帝国”先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被雕刻成了一个弯腰驼背、将最后一丝健康都献给书桌、几乎无法忍受自己写作欲望煎熬的形象。
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一座城的轮廓和形状,取决于真实的人们的所想所欲。波德莱尔也曾写道:“唉,一座城的外貌改变得比人心更快。”其实,城市的外貌不仅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神秘感和失落的痕迹。我探访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促使我去追寻下一个目标,追寻更多地点、政治和神秘事件,并在这本行纪中加以梳理。我的探索之旅,皆是追随莫洛托夫古旧藏书中别人的足迹,去那些属于流放、探险和犯罪的地方。我所获知的那些故事,皆与罗曼诺夫巷这座宏伟的公寓有关,始于斯,或终于斯。
虽然我对桑德斯的了解仅限于他的藏书、一些碎纸片和一封电报,但我还是在一个白夜乘火车一路向北,去了他曾经为军队和情报部门服役过的地方。那是在莫斯科以西、兹维尼戈罗德附近、伊尔门湖北岸的一片区域,是基督徒们第一次挑战并安置河神、雷神和树神等异教神明的地方。我探访了许多荒芜的所在,如修道院、研究站、乡间别墅、疗养院等??在这些地方,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曾经相互纠葛不清,生物化学家和核物理学家们或曾饱受意识形态压迫,或曾在复杂扭曲的建筑物中艰苦工作,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圣水的力量和异教祭司的教义为这里带来了智慧和慰藉。
在西伯利亚大草原,贝加尔湖以南的地区,那个寒冷而荒凉、到处都是干草和泥土的地方,空间本身已经成了政治镇压的工具。但是,这片空间从未丧失其召唤自由希望的魔力。在那里,无论国家还是个人,仿佛都迷失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同时又似乎浮现在苍白的地平线上,变得愈发明晰、愈发真实。那些挑战当权者而获罪受罚被流放至俄罗斯疆域尽头的人们,虽然已经湮没无闻,却真正创造出了一片属于“内心自由”的圣地。
莫洛托夫故居的幻灯机为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一开头便让焦虑的小马塞尔登场——仿佛用遥不可及的彩虹代替了“密不透风的墙”,用传说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刻折射着历史。在我阅读与旅行的过程中,遥远时空的情景闪现在我的眼前,无数幻象引领我超越理解力的极致,深入渺茫的人心,深入我们一度认为自己了解的事物的本质。就像那部老式幻灯机狭小镜头里闪过的褪色胶片,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向我掀开了它的一角——我自己的过往片段,陌生人记录下的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瞬间,都仿佛被魔法召唤般在黑暗中一幕幕浮现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