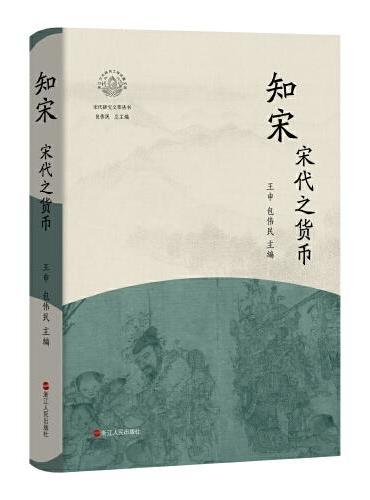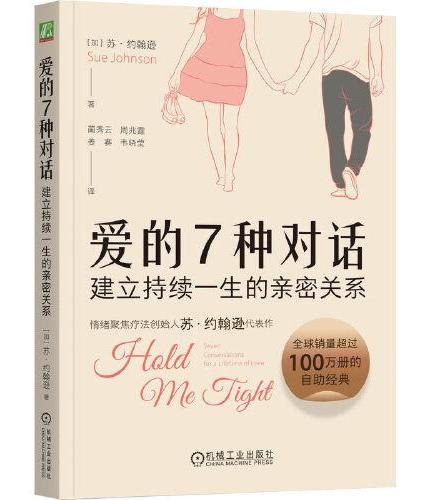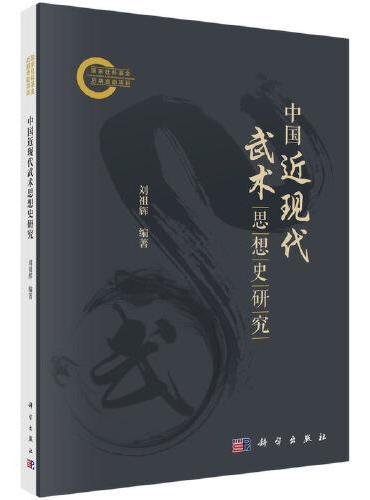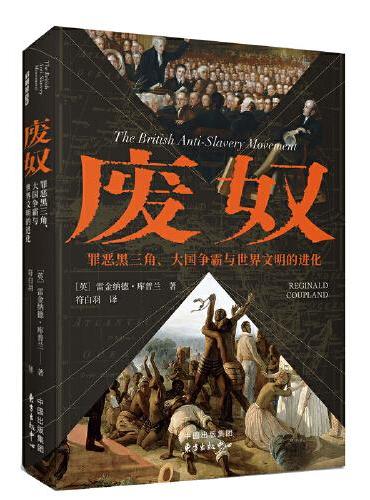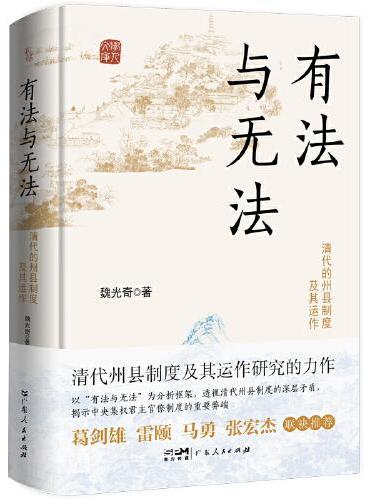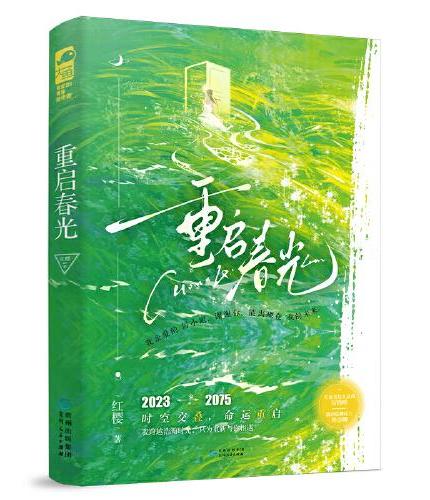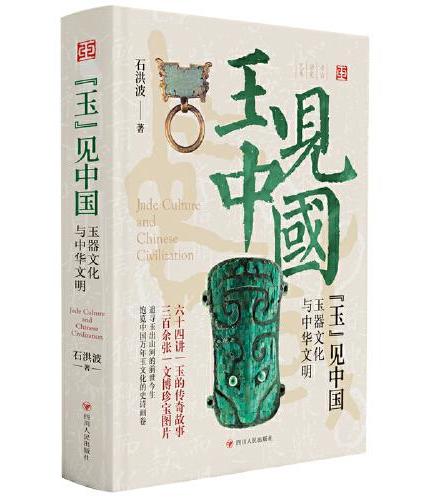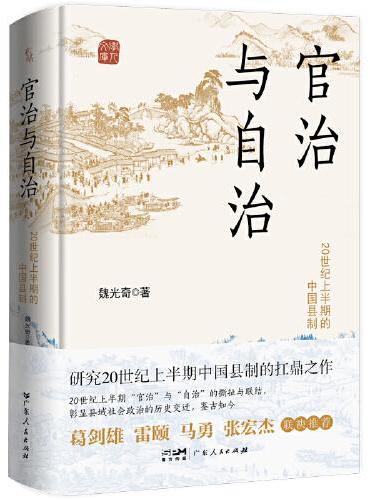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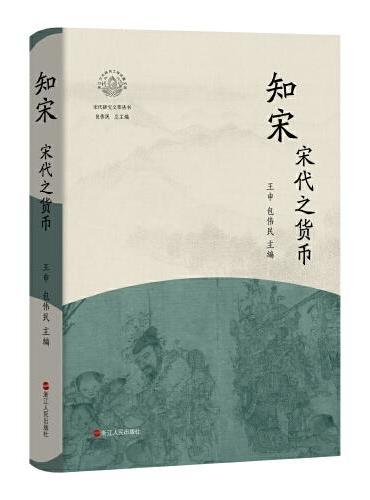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货币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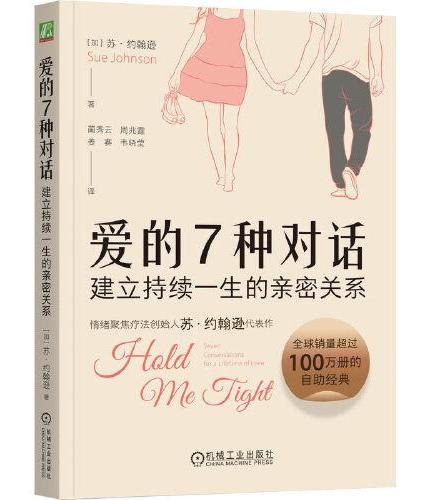
《
爱的7种对话:建立持续一生的亲密关系 (加)苏·约翰逊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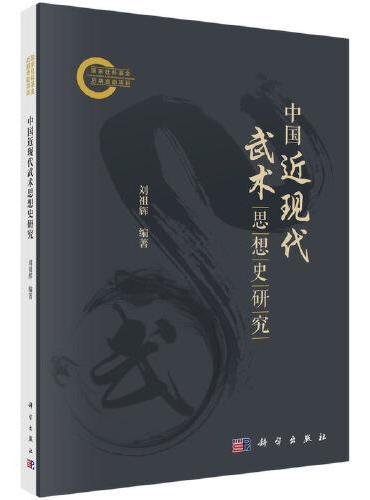
《
中国近现代武术思想史研究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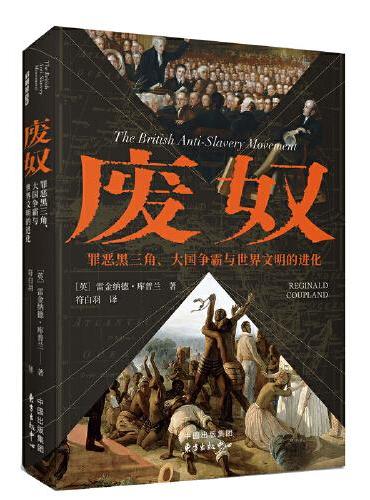
《
废奴
》
售價:NT$
3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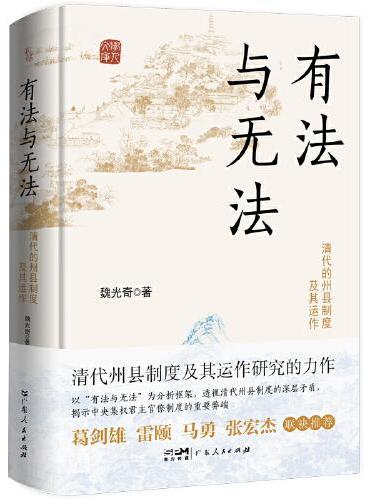
《
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 最新修订版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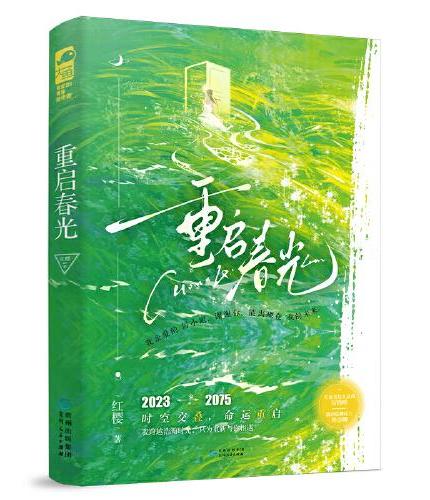
《
重启春光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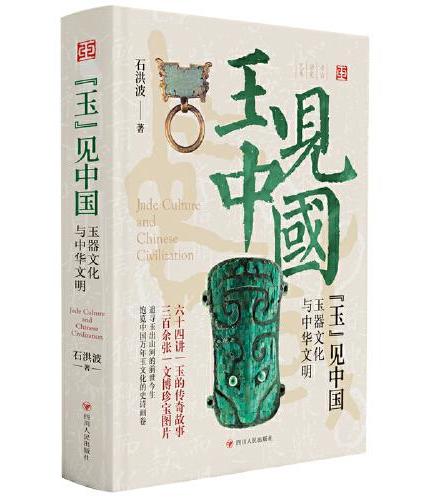
《
“玉”见中国:玉器文化与中华文明(追寻玉出山河的前世今生,饱览中国万年玉文化的史诗画卷)
》
售價:NT$
6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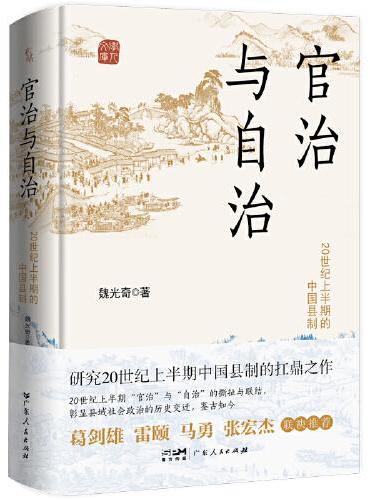
《
官治与自治: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最新修订版
》
售價:NT$
640.0
|
| 編輯推薦: |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作品集首次登陆中国
十部作品,震撼上市!
翻译阵容超级豪华,齐集全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
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你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
《心兽》是赫塔•米勒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
——赫塔•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父亲在园子里锄着夏天。孩子站在菜畦边想:父亲懂得生活窍门。因为父亲将他的愧疚植在最蠢的草里,然后把它们锄掉。
○卫兵手中的青李子乌黑如夜空。
○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
|
| 內容簡介: |
米勒的长篇代表作,台湾的译法是《风中绿李》。
1980年,年轻女孩萝拉离开了贫穷偏僻的小村庄,去大城市上大学,和五个女孩住在拥挤简陋的宿舍里。为了逃避灰暗现实,她随意与各种男人发生关系,有工人,有体育老师。但是,她最终没能逃出她的生活,某一天她被发现自尽于宿舍。她的朋友不相信她会自杀,想找到事实真相。
他们成立秘密小组,写诗,记录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日常生活。不久他们也被盯上,暴力逐渐降临…
|
| 關於作者: |
赫塔•米勒
女,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移居西德,现常居柏林。1982年,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她曾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
|
| 內容試閱:
|
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埃德加说,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面对照片在地上坐得太久。我的双腿坐麻木了。
我们用口中的词就像用草中的脚那样乱踩。用沉默也一样。
埃德加默然。
今天我无法想象一座坟墓。只能想象一根腰带,一扇窗,一个瘤子和一条绳子。我觉得,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
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埃德加说,准以为你疯了。
在我看来,每一个死人仿佛都留下来一袋子词。我总是想起理发师和指甲剪,因为死人不再需要。还有,死人永远不会再掉一粒纽扣。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死去的人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许跟我们不一样,埃德加说。
他们有证据,因为我们甚至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直到重新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行走、吃、睡、爱一个人而制造坟墓,埃德加说,那么他的错比我们的还大。他是一个对所有人的错,一个主宰一切的错。
脑中长草。我们开口说话,草就被割。我们沉默,也一样。一茬又一茬,想长就长。然而我们还是幸运的。
萝拉从南边来,从她身上可以发现一个没有脱贫的地域。我不知道从哪里,或许从颧骨上,嘴边,眼睛里。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白,一个地域也罢,一张脸也罢。这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没有脱贫,每张脸上也一样。可是萝拉来的地方,一如人们从她的颧骨、嘴边和眼里所看到的,也许更穷一些。地域多于风景。
贫瘠吞噬了一切,萝拉写道,除了羊、瓜和桑树。
但不是贫瘠驱使萝拉进城来的。我学什么,贫瘠无所谓,萝拉在本子里写道。贫瘠察觉不到,我知道多少。只知道我是什么人,也就是说我是谁。在城里一定要有所作为,萝拉写道,四年后返乡。但不是走在下面尘土飞扬的路上,而是在上面,穿行于桑树的枝间。
城里也有桑树。但是外边街上没有。桑树在内院里。在少数内院里。只有老人的院子里有桑树。树下搁着一把原是屋里坐的椅子。丝绒软垫的椅座。可那丝绒上斑斑点点的,撕破了口子。一束干草从下面将破洞堵住。草被坐扁了。椅座下面像是拖着一条辫子。
走近这把被淘汰的椅子,辫子上一根一根的草茎依稀可见。而且它们曾经绿过。
在种着桑树的院子里,阴影如同一片闲静,罩在椅子上坐着的那张苍老的脸上。说如同闲静,是因为我不期而至来到这些个院落,而且难得再来。难得的是一缕阳光从树梢笔直地照在那张苍老的脸上,一个遥远的地域。我的目光沿着那束光移下又移上。一阵寒意袭上脊背,因为这份闲静并非源于桑树的枝条,而是来自脸上眼睛里的寂寞。我不想让人看见我在这些院子里。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干的不比我眼前的这些东西多。我久久凝视着桑树。然后,在我离开前,又看了看坐在椅子上的脸。脸上写着一个地域。我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或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那个地域,扛着一根装在袋子里的桑树。我在城里的院落中见过不少带出来的桑树。
后来我在萝拉的本子里读到: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
萝拉想学四年俄语。入学考试不难,因为名额足够,大学里的名额跟全国学校里的一样多。俄语是少数人的志愿。志愿很难,萝拉写道,目的比较容易。一个上大学的男人,萝拉写道,指甲干净。四年后他跟我同行,因为这样的人明白,到了村里他就是个人物。理发师上门来,到了门口脱鞋。永别了,羊,萝拉写道,永别了,瓜,只要桑树,因为我们都有树叶。
一个小小的四角形作为房间,一扇窗,六个女孩,六张床,每张床下一个箱子。门边有个壁橱,一个扩音器安在门上方的天花板上。工人合唱队从天花板唱到墙,从墙唱到床,直至夜幕降临。然后他们安静下来,就像窗前这条街以及外边那个无人穿越、乱蓬蓬的公园。每个宿舍里像这样小小的四角形房间有四十个。
有人说,扩音器看得见听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
六个女孩的衣裙紧紧地挤挂在壁橱里。萝拉的最少。她穿大家的衣服。女孩们的长统袜躺在床下的箱子里。
有人唱道:
妈妈说
如果我嫁人
她就给我
二十个大枕头
统统装满蚊子
二十个小枕头
统统装满蚂蚁
二十个软枕头
统统装满败叶
而萝拉正坐在床边地上开箱子。在长统袜子堆里翻寻着,把搅作一团的大腿、脚趾和脚踵举到面前,一松手,任其散落在地上。萝拉的手颤抖着,眼睛不止脸上那两个。两手空空,手也不止空中这一双。空中林立的手几乎和地上躺着的长统袜子一样多。
眼睛、手和长统袜无法在一首隔着两张床的歌声中相容。一个前额上有一道愁纹的小脑袋,轻晃着站在当地唱歌。愁纹顷刻间又从歌中消失了。
每张床下面立着一个箱子,里面是乱成一团的长统棉袜。全国都管这叫专利长统袜。这种专利长统袜是给那些想要光滑、薄雾般的连袜裤的女孩们穿的。女孩们还想要发蜡、睫毛膏和指甲油。
床上枕头底下放着六个睫毛膏盒子。六个女孩子吐一口唾沫到盒子里,拿牙签搅一搅,搅到烟炱糊糊粘到牙签上为止。然后她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牙签在眼帘上摩刮着,睫毛变得又黑又粗。可是一个小时后,睫毛上就显现灰色的缝隙。唾液干了,烟炱落到了颊上。
女孩们要颊上的烟炱、脸上的睫毛烟炱,可是再也不要工厂的烟炱了。只想要很多很多薄雾连袜裤,因为这种袜子太容易抽丝了,女孩们不得不在脚踝和腿部将漏针捉住。用指甲油将漏针捉住、粘住。
一位先生的衬衫要保持洁白不容易。如果他四年后跟我回贫乡,那就是我的爱了。如果他穿着白衬衫在村里行走有本事让路人艳羡,那就是我的爱了。如果他是一个体面人,理发师上门来,到了门口脱鞋,那就是我的爱了。在跳蚤跳来跳去的脏地方保持衬衫的白净不容易,萝拉写道。
萝拉说,连树皮上都有跳蚤。有人说,那不是跳蚤,是虱子,蚜虫。萝拉写入本子:木虱更可怕。有人说,它们不犯人,因为人没有叶子。萝拉写道,它们什么都犯,太阳热辣辣一晒,连风也犯。而叶子我们都有。如果人不再长个子了,就掉叶子,因为童年过去了。如果人干瘪了,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叶子想长就长,萝拉写道,像深草。村里有两三个孩子没有叶子,他们有一个大童年。他们是独生子女,父母都念过书。木虱让大孩子变成小孩子,让四岁的变成三岁的,三岁的变成一岁的。还有一个半岁的,萝拉写道,还有一个新生儿。木虱造的兄弟姐妹越多,童年就越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