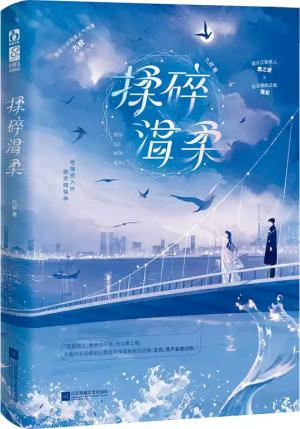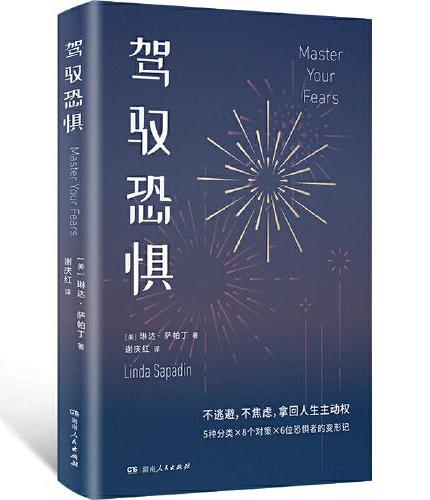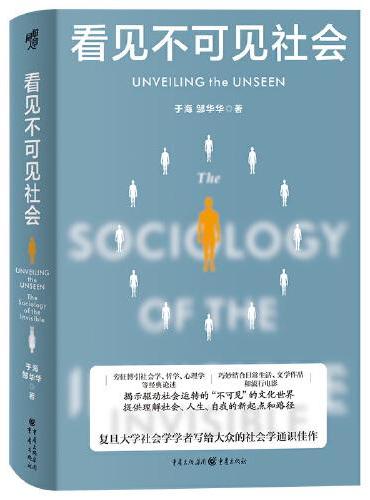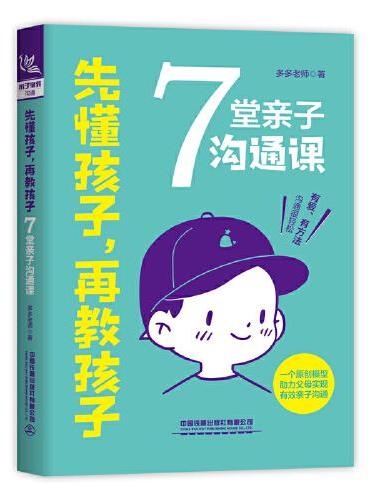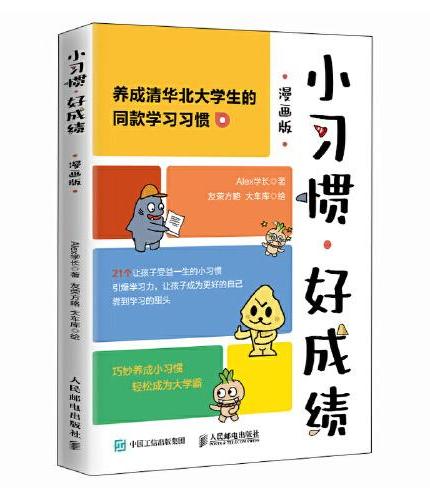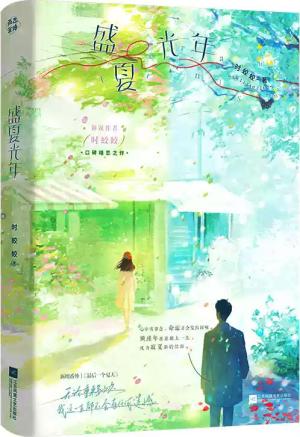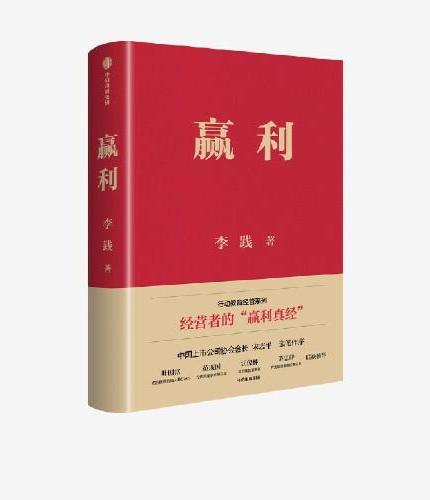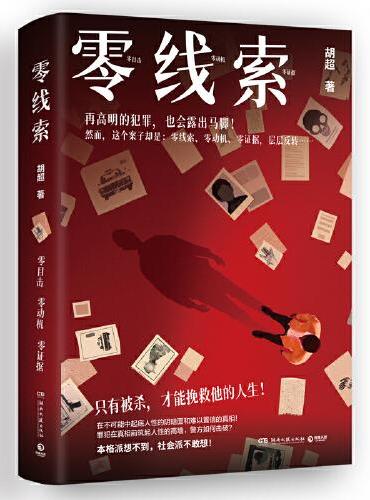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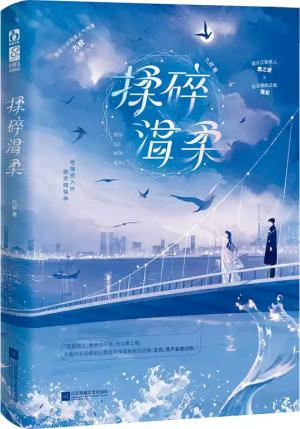
《
揉碎温柔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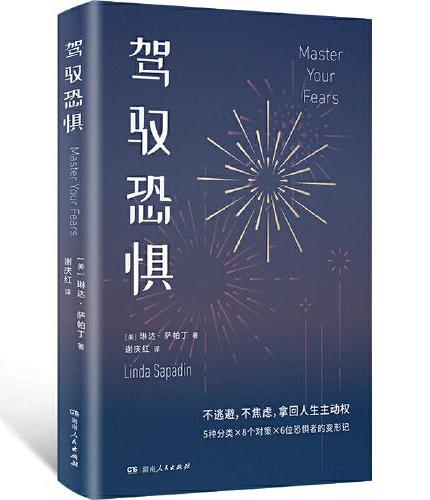
《
驾驭恐惧(菲利普·津巴多力荐的时代读本!减少焦虑、控制情绪、一键重启人生!)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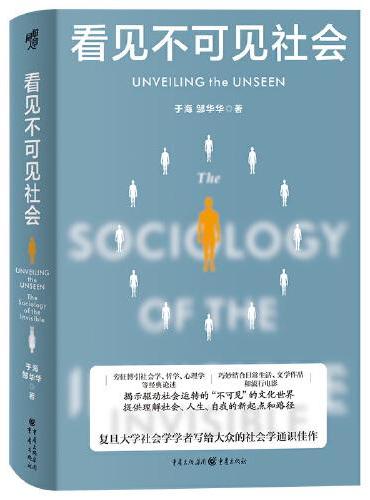
《
看见不可见社会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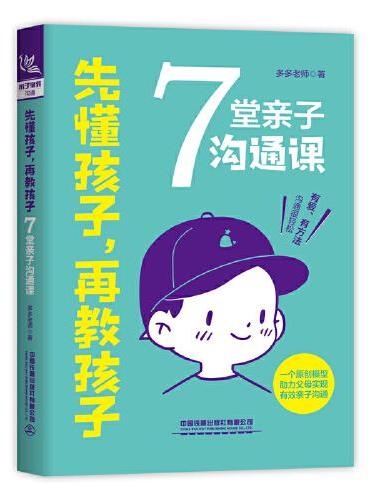
《
先懂孩子,再教孩子:7堂亲子沟通课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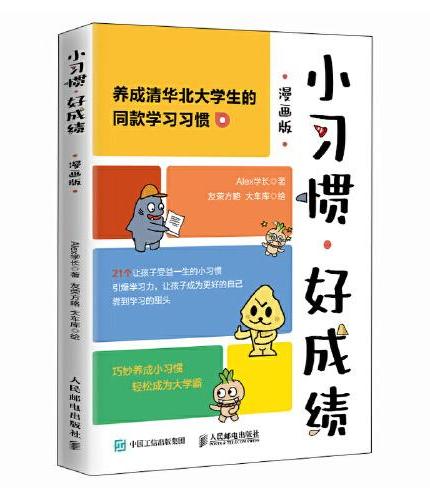
《
小习惯,好成绩(漫画版)
》
售價:NT$
2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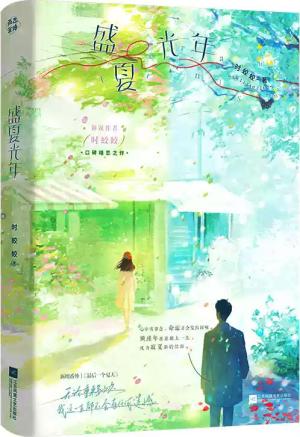
《
盛夏光年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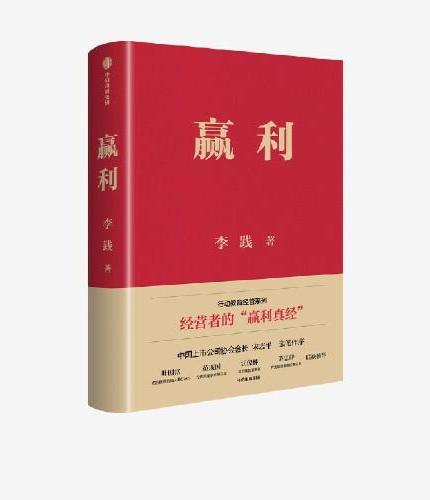
《
赢利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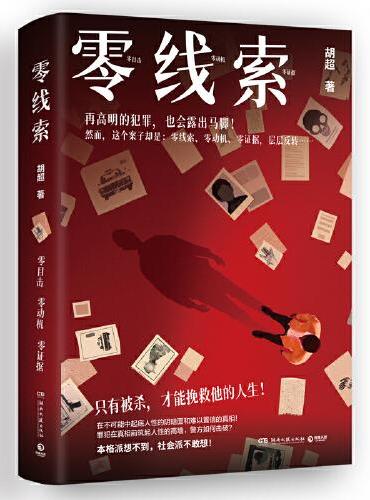
《
零线索(只有被杀,才能挽救他的人生!)
》
售價:NT$
305.0
|
| 編輯推薦: |
作者稻泉连在即将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之际,为解答自己对就业的疑惑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完成了这本《我们工作的理由、不工作的理由、不能工作的理由》。
受访者有缺乏求职热情的高材生,有就业后为工作所苦的职场新人,有自由职业者、创业者,有选择音乐家、渔夫等“另类”职业的人,也有茧居者。他们的经历与心声,展现出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中,年轻人对于择业的种种困惑、思考和选择。
选择一份工作,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由此产生的思索不会停止。在本书的姐妹篇《工作漂流》中,稻泉连又探讨了职场年轻人跳槽的现象,以及他们各自对工作意义的理解。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属于译文纪实下的日本现场观察支线。 “工作”究竟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抱着不安摸索着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有着怎样的烦恼与困惑? 本书采访了八名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小一帆风顺,顺利拿到名校的入场券,一些人一度辍学又重返校园,也有人退学后一蹶不振。不同的经历和背景塑造了不同性格与人生观,也让他们在走出校园之后做出了不同的职业选择。作者通过采访,结合自身的经历,用真实的案例向读者展现了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在就业道路上的种种困惑、思考和选择。
|
| 關於作者: |
|
稻泉连,1979年生于东京。1995年高一时退学,1997年通过大学入学资格检定,考入早稻田大学,2002年从第二文学部毕业。2005年凭借《虽然我也在战时出征:竹内浩三的诗与死》,获得日本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时26岁)。已出版作品有《我的高中辍学手册》《工作漂流》《做书这件事》《重生的书店》等。
|
| 目錄:
|
序章
第一章 希望自己被劝服——暮气沉沉的大学生,模糊不清的未来
第二章 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对“营销”职位的焦躁
第三章 把一切献给音乐——从精英路线到音乐人
第四章 寻求朋友圈——快乐的飞特族生活
第五章 摆脱“茧居”状态——直到他接受让自己苦恼的那段岁月
第六章 工作意味着坚持——选择成为一名护理员
第七章 我在为何而活?——校外补习机构年轻经营者的内心纠葛
第八章 在石垣岛寻得归宿——成为冲浪者、海人
尾声
后记
文库版后记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前言/序言】:
序章
在新宿站南口下车后,我朝着高岛屋的方向走去。整幢建筑矗立在青空下,有力地彰显着它的存在感。走着走着,转眼间,我便被吸入了人潮漩涡之中。
从检票口出来的人络绎不绝,前方等待红绿灯的队伍也眼看着壮大了起来。大家都在等待横穿跟前的甲州街道。来来往往的轿车、卡车、出租车等各类车辆也一直排着队列,川流不息,仿佛是在传送带上被运送着。
交通信号灯一变,车辆便停下,行人则涌出。接着,一分钟过后,车辆开始移动,行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斑马线前堆积起来。这般场景宛如工厂的流水线,抑或说,像是遵循着自然规律在同一个地方循环往复着似的。
我突然在想:倘若自己逆着这样的人流而行,又会如何呢?
在顺势而行的人群洪流当中,一旦有人想要沉思而止步,走在其后的工薪族便会冷不丁地打个趔趄。他应该会摆出一副明显厌烦的表情,仿佛要让你听到他的咂舌声,然后迅速避开障碍物,若无其事地继续急匆匆地前行吧。
停下脚步者会变成扰乱人潮的异物。
在新宿街头,人们看似融合在了一起,以一个毫无个性的集体为单位流动着。然而有一天,我陷入了烦恼之中,独自一人呆立在那里。所谓“社会”究竟为何物?“长大成人”又意味着什么?
对于尚未踏入社会的人来说,“社会”就像是一口巨大的锅,在墙的另一边咕嘟咕嘟地煮着。而对于这口未曾见过的大锅,尽管我们可以透过升腾的蒸汽和轰隆的声响来推测一二,但它绝不会将其全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听到有人在墙那边发出安抚的声音:“这不是什么需要让你如此烦恼的事情哟。你来到这里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在内心深处思考着:或许是这么回事吧,可是……
还有别的人在墙那边焦急地叫喊:
“你怎么这么天真!大家都是这么活过来的!”
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些人马上就能去到另一边。可是,如果你突然回首身后,也会看到去不了的人们又排起了长队。
如今,不能融入社会的年轻人、不去融入社会的年轻人确实在增多。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飞特族、不登校、茧居族等,被视作“问题”。有时,甚至有人说这属于“异常”现象。他们在被视为问题的同时,也被当作社会中的异类,遭受着众人不理解的目光。
据说东京都内某所高中的毕业生中约有一半为飞特族。该校对这个情况抱有危机感,于是组织了指导活动以防止学生成为飞特族。
其校长曾公开表示:“我们希望成为一所在消灭飞特族方面知名的学校。”
2000年3月29日,《朝日新闻》晚报报道了“日本劳动研究机构(JIL)”整理的实况调查中期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飞特族被分为三种类型:“延缓型”“追求梦想型”“不得已型”。其中,尤其是“延缓型”的年轻人多表示“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处于焦虑状态”。
报道的最后这样写道:
“就是否对飞特族的生活感到‘有界限’或‘想逃离’这一问题,有回答称‘一旦过了25岁就会被要求有社会工作经验’,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
截至1997年,全国飞特族人数已多达约151万人。1982年时约为这一数字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其上升势头相当迅猛。
瑞可利调查公司(Recruit Research)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大学生中,31.5%认为“毕业后不用马上就业”,50.9%认为“就业是理所当然的”,剩下的17.6%认为“不好说”。2000年3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55.8%(据文部省调查),创历史新低。按理说,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接着,我们来看看不登校的情况。
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的一项调查显示,1999年度请假不去学校30天以上的中小学生人数超过13万人(其中约八成为初中生),刷新了历史最高值。这一数字几乎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两倍。此外,高中辍学人数每年保持在10万人左右,其中一半以上在高中一年级时辍学。
这种情况的余波似乎也影响到了那些顺利从高中毕业的人身上。最近,成为大学生之后开始拒绝上学的人也有所增加。而且,从一流大学进入大企业,被认为突破了艰难就业战线的人,在进入公司的第二年左右就突然辞职的事例似乎也很多。
目前(即2000年),茧居族的总人数据说多达50万甚至上百万人。
看到这些调查数字,我深切地感受到,对当代年轻人而言,走向社会已经成为人生的一大课题,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将无法跨越。我们也可以说,与人口总数相比,被具体分类为飞特族、不登校等的总人数是个小数目。然而,如果把后备军也算进去,情况又会怎样呢?即使是那些看似走着寻常路线、顺理成章地步入社会的人,或许内心深处也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不安吧。
在这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潮流的正中央,年轻人被卷入人潮漩涡当中,他们会突然停下脚步,有时还会呆立着不动。
我也是一个对踏入社会感到恐惧和害怕的21岁年轻人。而且,我高中一年级时辍学,一度从学校这个框架中逃了出来,属于应该会被我们父母那一代的许多人说成“软弱青年”的一员。同时,我还想着,尽管自己现在还是一名大学生,但再过一年,必须要作为社会的一员融入墙那边的大锅里。
我不知道其他年轻人在这之前处于怎样的环境中,带着怎样的思考成长起来的。但是,作为同一代人,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产生共鸣的。
例如,在我结束青春期成为一名大学生时,我开始听到有关因受欺凌而自杀的报道,以及大量的少年犯罪案件。得知这些事的时候,我是否感到惊讶?想来,我当时的内心状况并不能简单地用“惊讶”来形容。不仅如此,我内心深处甚至萌生出一种达观的心态,认为“或许那样的事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这其中存在一种共鸣,即我自己也曾在同辈年轻人所在的那个共同的世界里生活过。
我高一辍学,因此,在学校度过青春期的时光要算到初中为止。尽管如此,我还是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曾旁观正在受欺凌的同学,甚至参与其中,还曾感觉自己被当成攻击的目标。我觉得这并不是谁的错。只是欺凌者占多数,被欺凌者占少数。仅此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害怕暴露自己。我尽量让自己在班里不显眼,但同时又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渴望展现自己,希望别人听自己说话。
然而,尽管在这种夹缝中饱受煎熬,但我从未感到怀疑。我想这一定是正常的。就像是在游泳池里要溺水了一样,我拼命地让自己的手脚乱动起来,却没有看到在旁边泳道游泳的人同样被卷入青春期的漩涡中拼命挣扎的样子。因此,我觉得自己说了很多无心之言,也同样被说过多次。我无暇思考这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后果。为了过这样的日常生活而去学校是件痛苦的事,但直到初中为止,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不去上学这一选项。
然而,当我感觉到原本以为上了高中就会改变的日常生活并不会有任何变化时,我放弃了高中的学业。我觉得自己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那时,在我看来,世界开始变成了灰色。我感觉路上的行人、车辆、建筑似乎都失去了真实感。我的视线边缘变得越来越暗,不想看的东西绝对不会映入眼帘。我想这大概是自己经常低着头的缘故吧。即便是在天空湛蓝、万里无云的日子里,我的眼里也依然黯淡无光。
高中辍学——对我来说,就是从大家都应该会去往的世界中脱离出来。
我有时会想,自己之所以没有对那些令人悲痛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涌起惊讶之情,是因为我曾经隶属于那个世界,哪怕只是暂时的。尽管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教育现场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我还是觉得那些令人厌恶的事件一定和自己曾经身处的世界存在着关联。
我从高中脱离出来,而同龄人几乎都留了下来。至于这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我不得而知。后来,我就这么懵懵懂懂地考入了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然而,我甚至不用看那些关于欺凌、不登校、飞特族、茧居族的调查结果就知道,其他年轻人确实也曾以与我不同的方式拼命地在青春期里挣扎求生。
然后接下来,我必须完成起飞奔赴社会的任务。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安,为什么社会对自己来说会成为如此巨大的障碍堵在面前?换言之,可以说那是对社会产生的一种极其强烈的违和感。然而,这种违和感只存在于我一个人身上吗?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疑惑在我心中一点点地滋长,我才想就“对走向社会所感到的不安”这一问题,尝试咨询一位已经确定工作的前辈。
作为早稻田大学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这位前辈获得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录用通知。在高中辍学的我看来,出身重点高中的他似乎是毫不犹豫地按照“高中→大学→就业”的线性轨迹一路前行。我想,对于“走向社会”这个问题,他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然而,当我问他找工作进展如何时,他的回复中带着点想开了的口吻。
“我感觉找工作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直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当然,我也没想过会得出答案。自己本来也没有对从事特定的工作抱有什么希望,就是想着反正暂且必须找份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找工作本身是最重要的目的。嗯,我想不论谁都是这样吧。毕竟,还是得不断挣钱啊。”
他这样谈论着找工作的事,让我感到很意外。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走向社会,我本以为他可以用更加积极乐观的语气来谈论。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工作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不讨厌工作和学习。如果不这么想的话,也没法坚持下去,对吧?因为在日本社会,积极、诚实被说成是一种非常好的美德嘛,所以,还是必须要让自己接受那样的价值观才行啊。渐渐地被这些影响也是没办法的事吧。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比起去做街头无差别杀人狂魔那类的事,还是前者更好,对吧?这就是所谓的长大成人吧。尽管说实在的,我并不想长大,但也不想做太过孩子气的事。”
“暂且”“在一定程度上”“不讨厌”“没办法”,他接二连三地说出的这些词让我觉得胸口有一种压迫感。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说得如此达观。
他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而且,也承认自己走的是所谓的“精英路线”。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为了小升初考试去上补习班。当小学里的其他人都在玩乐时,只有我一个人坐公交车去补习班……”
在那样的日子里,他被灌输了一种思想:“读书就会有前途”。他说自己一直认为,要想获得社会地位,首先需要学历。而想要找到好工作,就必须考上好大学。他的确信了这些,并付诸实践。
“因为那时候学习还算过得去吧。”他回忆起过去说道。
“我小学的时候比较喜欢理科,所以那时一直很想成为医生,或者是技术人员。读了爱迪生等人的传记后我挺感动的,而且说白了,我当时在理科方面还挺擅长的。后来,之所以改读文科,是因为初二、初三的时候开始看报纸、读论文什么的,对文学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于是,我就觉得还是文科好。毕竟还有所谓的‘理科书呆子’存在嘛。看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我当时有瞧不起理科的想法。高中的时候,我甚至还想过要当报社记者呢。
“我初高中上的是东京都内有名的私立学校。那里以学习为最高目的,一般会有50人左右考上东大。在那所学校里,大家都说东大很了不起。其实,我曾经也以东大的文学院为目标(笑)。从初中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那会儿我经常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不过,我对社会正义之类的东西也很感兴趣,对于读法学院,也不是绝对不愿意,所以觉得也不错。最终,我报考了东大的文科三类和早庆的法学院。回想起来,高中快结束时,我还想成为一名学者呢。但是,那个时候我处于摇摆的状态,不确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我对表象文化之类的东西也很感兴趣,想对影像文化进行学术性研究。还有,我当时真的很想成为一名动画导演。只是,在这个社会里说自己喜欢动漫是需要勇气的,就算说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所以在高中时我隐瞒了这一点。而在大学里我毅然抛开这些想法,开始果断地告诉周围的人,不过,进了公司我大概就不会说了吧。”
聊着聊着,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误解了他。
在大学里的他,平时给我的印象是个不可捉摸的人。而这种印象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即他考入早稻田法学院,工作也定在了一家大公司,是一个从未经历过挫折的优等生。这是因为,当周围的同学们都在谈论对未来的不安或脱离现实的话题时,只有他无论是对找工作的事还是上课的事,总是很轻松地一笑而过,不会让人有丝毫严肃的感觉。当其他的朋友或前辈谈及未来或求职时,哪怕是想轻描淡写地说“明天又要面试了,真麻烦”,也还是会闪现一丝情绪的波动或瞬间的阴影。但是,从他的身上,可以说我完全看不到他的真实想法。
然而,其实他也曾有过诸多不安和内心纠葛。我不禁愕然,这么显而易见的事自己居然都没有注意到。就像我过去所做的一样,他也一直在反复地尝试消除自我,再创造一个新的自我。
“或许我的人生的确看起来不错,但也经历过不少挫折。不如说,我倒觉得自己总是处于愿望无法得以实现的状态,所以我尽量把人生想作玩笑。虽然我本来性格就认真,怎么也开不了玩笑,但就算遇到不好的事,也就想着把它当作噱头应付过去吧。比如,用幽默蒙混过去,或者一笑了之。
“我并不认为进入一家好公司是件幸福的事。学了这么多年,考上大学,然后进入一流企业,我完全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好的,反而认为或许自己原本还可以有更快乐的人生吧。”
从上补习班到进入重点高中,从重点高中再到“好的大学”。
拿到特快“精英号”单程票的他终于要到达“大企业”这一站了。从车窗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风景——有时非常迷人——然后便飞驰而过。
换句话说,那些“迷人的风景”无疑就像禁果一样。如果伸手摘了一个看起来很甜的果实吃下去的话,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了。
……他忍住了。
然后,在终于接近了“就业”这一自己所坚信的目标的当下,有时会突然清醒过来,想着“或许自己原本还可以有更快乐的人生吧”。
于是,他说道:
“不过,我无法想象另一种活法下的自己。”
我从中感受到他似乎想表达“不想自己后悔”的心情。
可是……我又想了想。
当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只是对走向社会的一种达观。“A其实是最好的。不过,换作B我也不是不想干。”他这样自我说服的结果意味着走向社会,还是长大成人?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让自己这么认为。
而且,当想到自己对社会的那种极其强烈的违和感时,我突然开始在意起身边其他年轻人的存在。我很想知道,切身感受着与自己同一时代和同一世界的他们过去经历了怎样的童年和青春期,今后又将如何走向社会。他们也会对我说些达观的话吗?还是别的什么?
此刻,我正站在社会这片汪洋大海的边缘,还没有下定决心跳入其中。于是,在这之前,我想稍微看看其他人的人生。去观察他们走过的路,确认一下那里有过什么样的障碍,他们又有过怎样的想法。
我下定决心,将对其他年轻人的人生观察作为自己踏上社会之前的最后之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