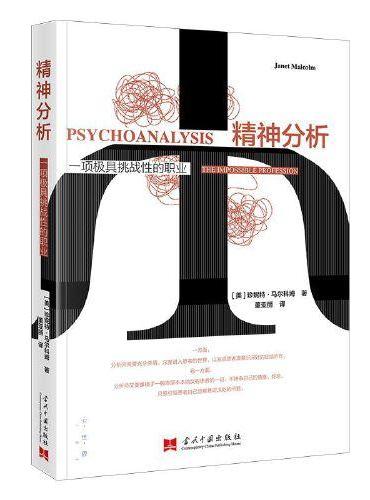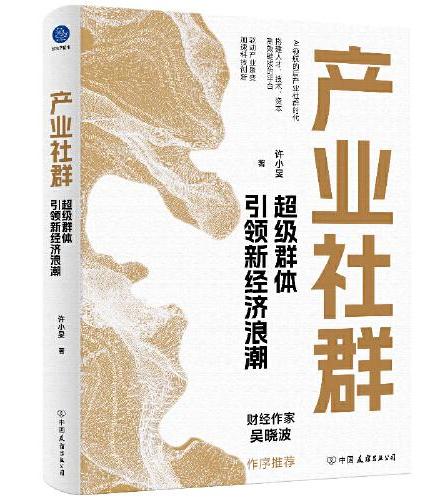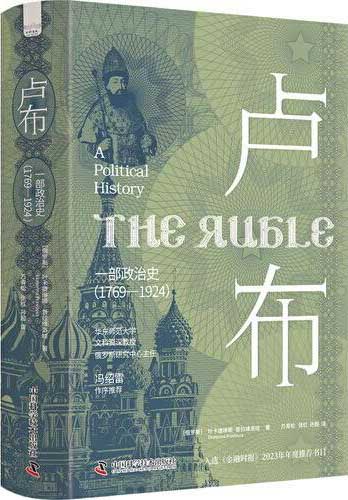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NT$
959.0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NT$
407.0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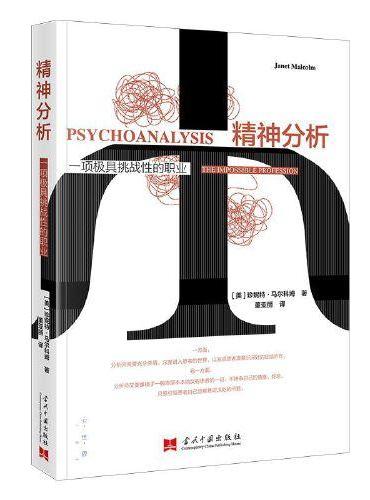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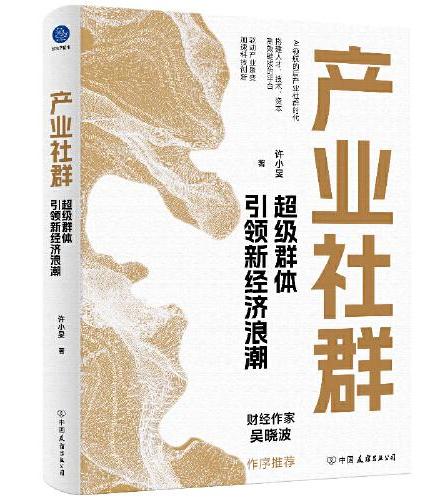
《
产业社群:超级群体引领新经济浪潮
》
售價:NT$
3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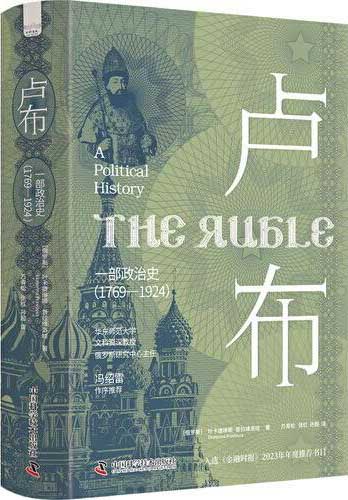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NT$
556.0
|
| 編輯推薦: |
1.福建客家叙事,因其族群聚居、乡村日常、平民书写,以及南方丘陵气候自然,使其与潮汕地区的新南方文学,既有南方诡谲想象的一致,又有所现实群落意义的区别,而与台湾、马华的南方文学更为接近。
2.福建客家地域文学独特价值之处,在于其内陆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历史上少经战乱,这使得其文化与秩序具有延续性、而其变革的议题,常涉内部困滞与自我更迭。本集多篇小说的背景或主旨即生发于此。
3.青年作家林为攀,自“新概念”作文奖、休学、离家,漂泊十余载,重返客家精神原乡、扛起人生搭萨——“童年与故乡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它们会让你在社会上走投无路之际给你一记闷棍,让你突然浑身一个激灵,想起隐藏在大脑褶皱里的往事”。
4.回望故乡的山川日月和客家的婚丧嫁娶,寻找生命的滋味与力量,重新扛起人生重担。
|
| 內容簡介: |
客家人把结婚、生子、盖房视为人生三大搭萨。扛起这三大搭萨,便是扛起生活的酸甜苦辣咸。
《搭萨》是青年作家林为攀的客家叙事中短篇小说集,收录《玲珑七窍心》《搭萨》《沙漏》《梵高马戏团》《胡不归》五个故事。离家少女拜师学艺,却沦为木偶,命运难以自主;游神的荣光背后,兄弟阋墙的无奈悄然蔓延;老无所依的祖母严守昼伏夜出的生存法则……这些故事以客家原乡为起点,书写客家人在传统与现代、故乡与他乡中的挣扎与坚守。在出走与安顿间徘徊迷茫时,故乡的山川日月总能给予生活滋味与力量。
|
| 關於作者: |
林为攀,福建上杭人,九〇后青年作家。高中时以处女作《作家之死》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大二选择退学,随后周游全国。曾从事广告、编剧等工作。自十九岁立志写作,迄今矢志不移。工作挣钱,辞职写小说,周而复始二十余次。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合同制作家。
出版有长篇小说《追随他的记忆》《万物春生》《梧桐栖龙》和小说集《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驯小说的人》等。入选二〇二○年《小说选刊》与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委员会联合推出的“新锐小说家20强”。
|
| 目錄:
|
玲珑七窍心—————————————————————— 001
明明是在用傀儡演戏,实际上演的却是人的感受。文人用文章托物言志,艺人则用傀儡寄意于物,写文章可以泪洒纸上以示激愤,可吊傀儡不能泪洒当场。
搭萨 ————————————————————————— 069
打醮搭菩萨便车,别称“扛菩萨”,有求财祈平安之意。后指滋味,生活有滋味是有搭萨,无滋味便是冇搭萨。客家人把结婚、盖房、打醮称为人生三大搭萨。
沙漏—————————————————————————— 141
祖母把昼伏夜出当成自己晚年最重要的生存法则。
凡·高马戏团—————————————————————— 167
老莫正把动物从笼里放出来。我站在废墟上看着老莫的背影,跑过去。
我说:“老莫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走?”
胡不归————————————————————————— 221
台风顷刻之加大了。这回它将抹掉地上的屋顶、庄稼、牲畜等一切脆弱的生命,只有躲藏在丘陵褶皱里的蚂蚁、蕨类、苔藓等坚强的生物将幸免于难。
|
| 內容試閱:
|
玲珑七窍心(节选)
松姑后来很怀念雾岭的杜鹃花。年幼的她在房里待腻了,就推门出去,推门声像竹子断裂。她一下子看尽万山红遍,杜鹃花没有洛阳城的牡丹富贵,也没有平阴的玫瑰浪漫,可她却偏爱这种山花。不管过了多少年,她都记得当年出走雾岭的那天。她用花汁涂艳了自己的脸,正式开始了向儒释道借饭吃的傀儡师生涯。
做傀儡师并没有死规定,它不像中医要求能认出百草,也不像木匠得知道哪种树能用来做栋梁。做傀儡师没有那么复杂,它的关键不在隔着一层肚皮的心里,而在一眼就能瞧出俊丑的脸上。也是天生该她吃这碗饭,她的五官就像一截最适合拿来做木偶的香樟木,几乎不用怎么动刀,就能立在四角台上,或为人偶中的十八罗汉,或为动物偶中的龟、蛇、鸟、兔。可惜,她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娃娃。做傀儡师的,古来皆跟神怪打交道,不会看不起女性,也不敢看不起,即便真的看不起,也不会在脸上露出来。他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只能放在手里操纵的傀儡身上。主要是,傀儡师需要走南闯北,怕女儿身吃不了这种苦,培养半天别到时跟哪个登徒子跑了,班主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损失。别看傀儡师常放豪言只跟儒释道借饭吃,但仍要看东家脸色,没有东家请,整班的傀儡师和傀儡都只能跟成仙成圣的孔夫子、释迦牟尼和老子喝西北风去。因战乱,看傀儡戏的人本就少,若再被别人知道傀儡师中还有个女娃,说不定整班都要关门歇业。理是这个理,可眼前这个女娃又实在宝贝得紧,蔚南班的老傀儡师哪里舍得放她走。
老傀儡师姓关,单名一个通字。眼前的这个女娃娃看五官就是吃傀儡师这碗饭的,他则是三界通关的姓名里就注定了该他端这碗饭。但他老了,操纵起傀儡有心无力,眼看三界日益脱离掌控,他急需一个徒弟承继衣钵。他一眼相中了这个出走雾岭四处乞食的女娃娃。他知道班主不愿意收留女流之辈,便让她顶替那个坏了的木偶,随蔚南班水宿山行。整班都没人发现她,她也很懂事,只在夜深后吃几口老傀儡师给她留的剩饭。吃完又站到那些木偶中去,浑身不敢擅动,仅一双眸子在滴溜溜偷转。闲时,蔚南班上到班主,下到掌锣鼓的帮腔,都爱去赌坊赌一把,只有老傀儡师不去。待到整班无人,只剩老傀儡师和一个暂时成为傀儡的女娃娃,老傀儡师就会让她活动活动筋骨,但不敢抹掉她脸上涂的粉彩,还会抽空教她吊傀儡子,即传授傀儡戏。
女娃娃这时才知道,她能留下来不是这个老爷爷看她可怜,有心抬举她半碗饭填饱肚子,而是看中了她的五官。吊傀儡子不在手指是否灵活,也不在力气够不够足,虽然这两点也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五官能不能做出万般变化。照理说,傀儡师不需要自己做表情,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演员,而且表情自有那些傀儡承担,不过老傀儡师老早就打量着革新傀儡戏了。多年来,他先后革新了向无曲谱、只沿土俗的唱腔,可让句调长短、音的高低随心入腔;还托人写了几折新传本,不再是《败走麦城》《桂英挂帅》等老古董。可仍旧欠点儿火候,原因不是唱腔不动听、新传本不曲折,也不是伴奏的西皮二黄不够活泼和婉转,而是充当演员的木偶表情僵化。看到这个女娃娃,老傀儡师心里咯噔一下,像挂钟里面的齿轮终于咬合了时针、分针和秒针,他放弃再去借鉴戏台上演员失真的表情,准备让她变身傀儡。
三教九流,诸行诸业,都能在年关歇几天肩膀,但傀儡师不行,年关正是最忙的时候。哪怕一年没开张的末流傀儡班,这个时候都能接到几单活儿,更不用说名头比锣鼓还响的蔚南班。傀儡师有专门休息的日子,每年七、八两个月,他们才能补过没过上的节假。
这年七月初七,到了开镰割禾的季节,老傀儡师难得放假,有时间慢慢把傀儡行的“四字口诀”授给她,并让她往后在台上一一温习。
老傀儡师郑重对她说,松姑,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吊傀儡子?
想。
以后会很辛苦,怕不怕?
不怕。
那我现在就把本行的四种表情教给你,正式收你为徒。
好。
第一种:吞。
吞
雾岭,岭陡云低,走在路上,常会撞见云,入到家门,地上一片水。进门的是松姑的父母,他们把云里的水带进了家门,跟抱着碗舔碗底的松姑说,又像在跟彼此说:再由她这样吃下去,我们这座山岭迟早会被她吃空。松姑放下碗,用手捏起嘴角的饭粒,抹进嘴里,没看她吞咽,就说起了话:“饿死了,还有吃的没?”
松姑的饭量很大,家里本就困难,每顿还要多做几碗饭,这几碗饭在她肚子里也撑不到吃晚饭的时候,几乎刚吃完中饭,在地里卖汗水的父母都还没感觉到饿,松姑就又想吃饭了。她小小年纪,也知道不在饭点的饥饿就像突然上门的客人,一时拿不出好东西招待对方。不过她总有办法跟门外的雾岭打牙祭,她的食禄不在家里逢年过节买的几两肥肉上,而是在这座终年弥漫着雾水的岭上。只要眼睛够好使,她就能看到挂在松柏之间的各色野果;只要腿脚够有劲,她就能逮到被困在陷阱里的小兽。可是时间一久,即便这座山岭仍有浓雾伪装,一听到小松姑的口哨声,整座山岭就会头皮发麻:跑不脱的野果会祈求落一阵急雨,好让它们能从枝头坠下来,躲到厚厚的松针底下;跑得脱的小兽只希望她手里没有弹弓或者鸟铳,否则它们就要全部进到她的肚子里。小松姑占不到雾岭的便宜,便拿出了父母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的耐心,躲在一棵腐朽的松木旁,等待雨后斑斓的蘑菇像酒席上被端出来的七荤三素的十大碗。可是蘑菇也不想被她吃,它们宁愿错过这一季,也不想在刚冒头的时候就被她连根拔起。小松姑的肚子就像一个无底洞,存不下能转化成营养、供她快快长大的饭菜。假如她吃完饭乖乖在家里待着,说不定肚子还能多扛一会儿,可她偏偏撂下饭碗走进了雾岭深处,因此她比平时更早饿了。
父母在雾岭下干活,这几亩梯田就像雾岭吃饱喝足松开的腰带,松姑没出生前,勉强还能养活两口之家,在松姑出世后,就显然喂不饱多出来的一张嘴了。再说,松姑还比其他小孩饭量大。愁,愁的不只这座雾岭,她的父母更愁,每天出门干活眉头都像挂了一副无菜可夹的筷子,每天干完活儿回家眉间愁仍未卸下。饭还没做好,就看到松姑抱着碗准备上了,愁便加上了长吁短叹,又不想被她听见,只好不停说话,可是说出的每一句仍然加了愁,就像做的每一顿饭都少不了盐一样。小孩子饭量大,不是调皮就是有病,可是松姑并不调皮,只要她肚子里有食,就会帮父母干活,几乎把家里能干的活儿都给干了,也是现在手脚脆,下不了地,不然她估计还会帮忙犁田或者脱粒。每次留在家里喂鸡,她就会看着那只三黄母鸡流口水,还会看看草垛里有没有鸡蛋,有时摸到了几颗鸡蛋,刚想下锅全煎了,想起在地里流汗的父母,又不舍得了,强行把口水咽回去。她也没病,除了老是喊饿,没见有别的症状,吃了这么多饭,还是瘦,如果真是有病,也是吃病,或者富贵病。这种病在大富人家,好医,也能医,但在穷人家,就比绝症还棘手。
松姑吃东西不是吃,而是吞,但她的口却不大,反而还有点儿小,不认识的人看到她,就会误以为她撒把米就能养活。她的吃相,或者说吞相并不难看,不像别的饿死鬼吃起来不顾形象。她吃饭时不出声,还会细嚼慢咽,这本来跟吞毫无关系,但因嚼的时间久了,咽的东西多了,细嚼慢咽也变成了狼吞虎咽。没东西吃的时候,她还会不停吞口水,口水吞干了,又站在门口吞空气。父母只要看到她在吞空气,就会怪她吞掉了雾岭的太阳,让雾岭每天都湿漉漉。太阳很大,假如真能吃下肚,或许松姑一整年都可以不吃米饭。她吞空气吞累了,就会活动腮帮子,鹄立岭上,可是太阳在浓雾中就像火候不够没煎熟的鸡蛋,她看清它都费劲,更不用说把它摘下来一口吃了。脚下的松针在动,仿佛她踩住了雾岭所有生灵共同的被子。她松开脚,白高兴一场,脚下不是能吃的蝉和鸟,而是从松树枝头小心翼翼掉落的松果。她捡起一颗松果,松果表面皱皱巴巴,丑陋的表皮里面却不是清甜可口的板栗。松果长得跟毛栗子很像,可也只是外表像,内心差别很大,对,就像一把钝刀和一块嫩豆腐的区别。
她把松果往低处抛,惊动了蛰伏在雾岭四处的飞禽走兽。飞禽在潮湿的天空扇累了翅膀,走兽在无路可走的岭上撞破了脑袋。松姑看到天空与大地都在响亮地拍肚皮,就像是在收拾饭桌准备吃饭了。过了一会儿,飞禽就消失在了可以揉出一江水的天空,荆棘丛生的岭上也没了那些走兽的踪影。锅底灰的天空已经把饭桌清洁干净了,可还是有一朵纯白的羽毛像朵白云一般成了阴天里的不速之客。松姑饿了,她又饿了,她已经很努力了,可是饿意今天只比昨天和前天迟了不到一刻钟。她饿着肚子走下雾岭,不用她张口,树梢的雾水就会自动滴到她嘴里,可是雾水跟空气一样,对饥饿的肚子没有任何帮助。她只好闭上嘴巴,任由雾水在嘴边凝成珠,然后她像在荷叶上打滑一样跌倒在层林尽染里。天空是锅底灰,可是雾岭在浓雾之下却百花盛开。不管是红色的杜鹃花、紫色的通泉草,还是白色的莲子草,松姑都一一用嘴尝过。酸,涩,苦,她的空肚子登时就像打翻了一个调料罐。她摇摇头、耸耸肩,慌忙啐掉,舔叶上的露水漱口。此后再怎么饿,也不敢再吃任何野花野草了。
父母还在岭间劳作,用火烧出的一寸荒,用刀砍出的一片地,把种子撒下去,不求能有好收成,只求一百棵稻子里有一半能抽穗,抽穗的里面再有一半能结粒,就满足了。跟地抢食,也是在跟天夺食,地薄、天恶,太阳老不出来,难有好收成。松姑赶回去做饭,担心饭还没熟生米就全进了自己肚子,哪怕尽力在忍了,饭香也会像捕兽夹子,让她犯下一人吃饱饿到全家的过错。父母又每次都晚归,她既要保证不偷吃,又要保证不让饭菜凉,只得再生火温饭。夜空没有星光,只有火灶里饥饿的蓝色火苗在舔锅底。
父母回家后,不先忙着吃饭,他们要先掸掉身上带回来的落叶,还要脱下鞋子放在门边,因为鞋底的春泥很厚,会把客厅和厨房的地面踩出许多收拾不了的鞋印。第二天,等鞋底的春泥稍微干了一点儿,他们才会用一根树枝把泥揩掉,就像在切一块肥肉中没有多少的瘦肉。那时还在点洋油灯,光亮不足,几乎照不亮桌上的饭菜和挨在一起吃饭的三颗脑袋。有时松姑的筷子误夹到父亲或母亲的碗里,有时米饭吃完了,桌上的菜却没夹几筷子。不过也好,只要剩菜能扛过一宿不馊,第二天还可以拿来吃。夜晚吃饭难,洗碗筷也难,松姑负责洗碗。屋檐下有口大缸,破了个口子,所以这口大缸装的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多,缸口上还盖了一片枯荷叶。这片荷叶刚摘下来的时候还很新鲜,松姑带它回家的时候把它盖在头上,天上没落雨,荷叶上的露珠却争先恐后地落下来。松姑顶着雨帘回家,把荷叶盖到大缸上,忙躲进厨房烤火去了。出来一看,身上的衣服干了,缸上的荷叶也没那么水灵了。她算是看出来了,美好的东西总是短命。她揭开枯荷,舀水洗碗,天黑看不清碗底有没有吃干净,好在她的小手能摸出来碗里还有没有饭粒。她倒一点儿水在碗里,然后用手在碗底捞,就像在淤泥里捞泥鳅一样,终于被她捞到了一粒米饭,二话不说就往嘴里送。大缸有些裂,夜里看不清,白天才能看到缸身上那道像闪电一样的裂纹,松姑有时想着它快点儿破,好让她悬着的心落下来,有时又不愿意它破,害怕缸里的水会漫到屋子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