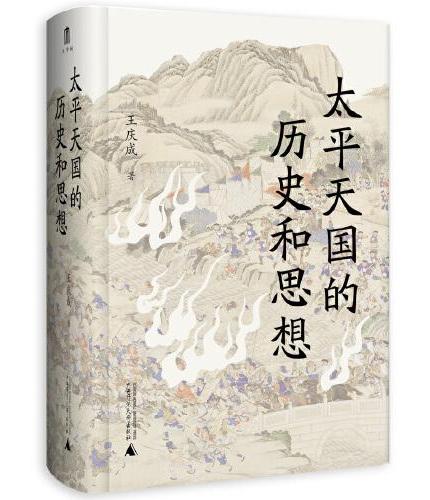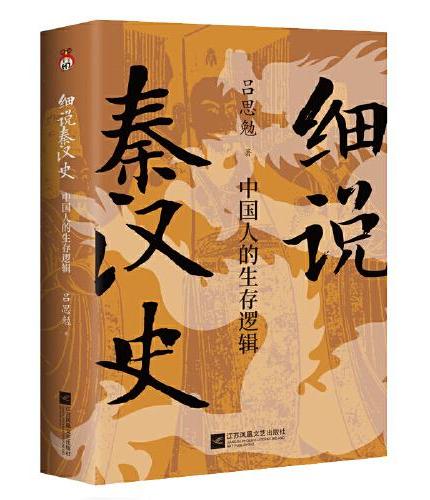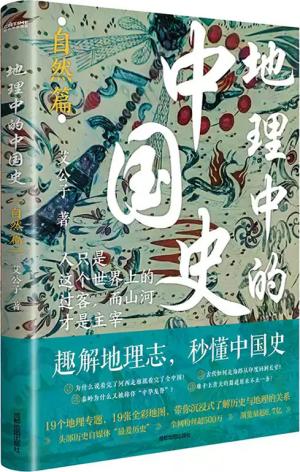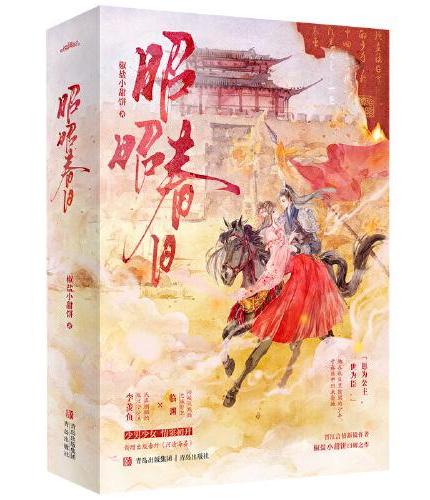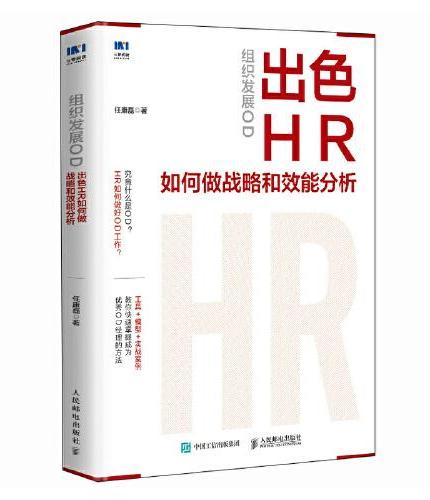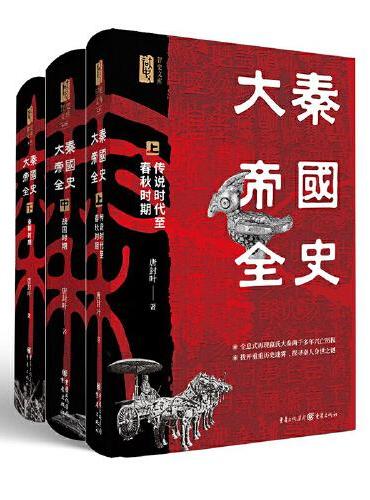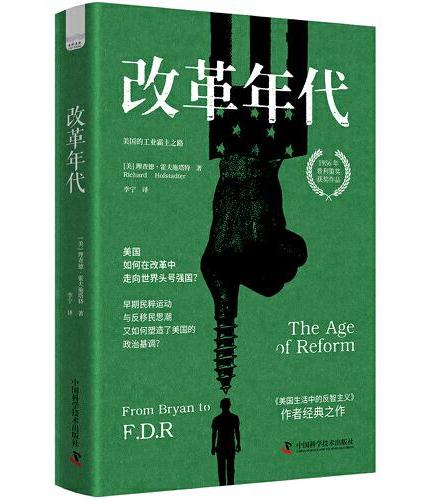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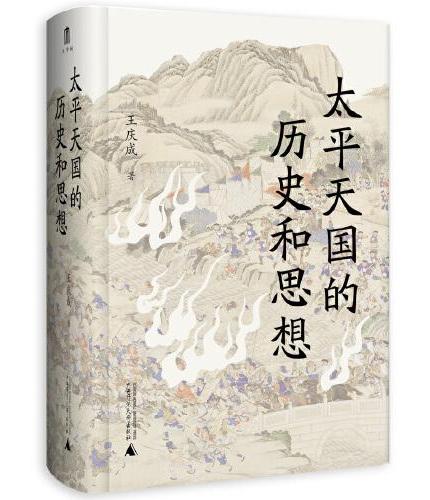
《
大学问·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部研究太平天国的经典著作)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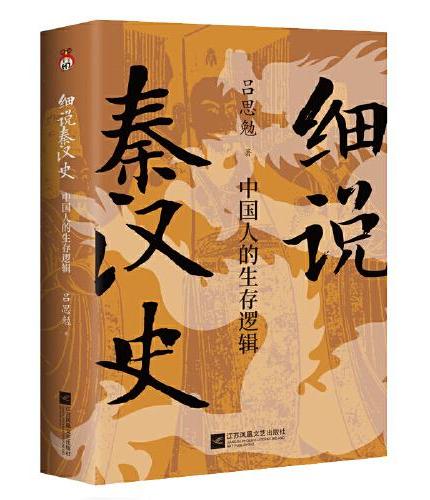
《
细说秦汉史:中国人的生存逻辑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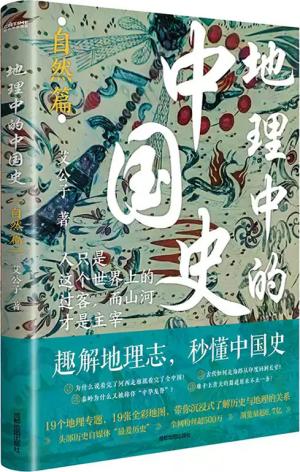
《
地理中的中国史(自然篇)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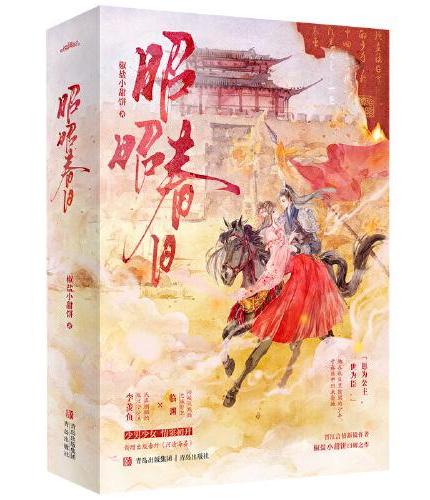
《
昭昭春日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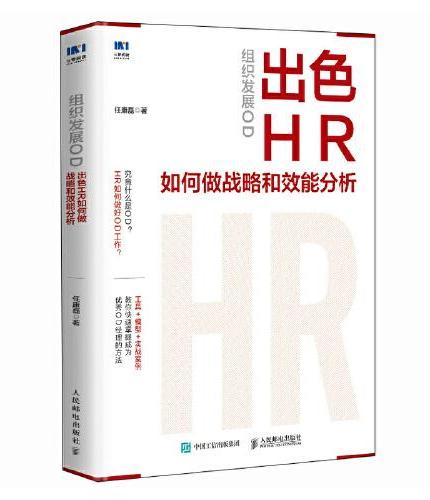
《
组织发展OD:出色HR如何做战略和效能分析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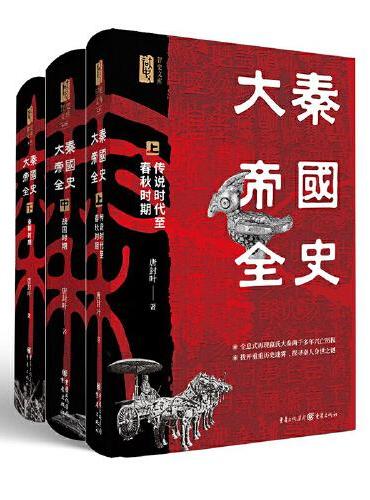
《
大秦帝国全史
》
售價:NT$
1015.0

《
孟浩然(英语世界中的*一本孟浩然传记)
》
售價:NT$
3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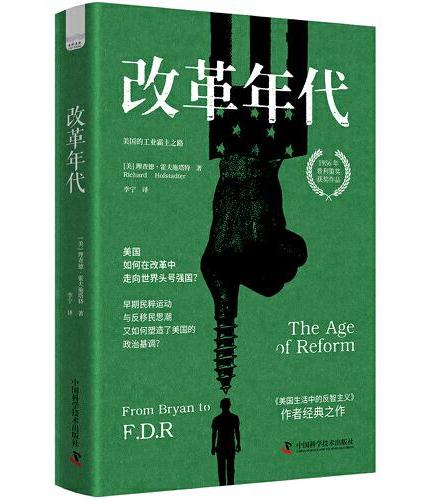
《
改革年代:美国的工业霸主之路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2 2023年新选编,广纳近两年中国小小说名篇。
2 收录冯骥才、梁晓声、刘亮程、石舒清、路也、石钟山等名家作品。
2 行文优美流畅,内容贴近现实,可读性强,能够令人感受文学魅力,提高思想深度、提升自身涵养。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撷集新近小小说佳作,作品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对生命的体悟,为读者提供关照社会、探微人性的一扇窗口。个人叙事的篇什或唯美沉静,或于灵动处见文学元气,多漾溢哲学意味,有的佳构尺幅千里,有家国命运之开阔,得大叙事之魂魄,还有不少篇幅在进行文学叙事的同时携载文化含量,用小小说诠释属于中国的一些文化因子,体现出文化传承的力道,体现出那些已融入国人血脉的文化精神在当下的生命力。该文集作者以小小说作家中坚力量为主,他们的作品具经典性、垂范性。
|
| 關於作者: |
|
王彦艳,《百花园》执行主编,编审。策划、主编小小说类图书百余本,有文学评论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文学报》等,出版有评论集《体验小小说》。
|
| 目錄:
|
万年青
白先生与黑勇士
开满窗户的山坡
马 氏
分手信
一棵树
站 岗
临窗的位置
老那的旗
丑 鬼
爷爷的往事
六谷糊
一条大鱼
幸 运
方 言
舞 台
不见不散
女人善良
收 官
墨 镜
坤 叔
立 誓
腊月廿四
桃花铺
拜 年
蔡 爷
一 切
小小理发店
月亮豆与玫瑰花
大 哥
隔壁的秋生
活着的人
丧 宴
当人老了
一把手
他站在丁字路口
喜 子
坤 车
借 钱
地震波
三个相框
岁月忽已暮
奶奶的寿衣
马 车
急诊室的故事
黄金盏
食菌记
王秀娥
轻舟已过万重山
赤 脚
一次不受控制的死亡
前 妻
不等流星了
还是有家好
伴 儿
杏 核
红头纱蓝头纱
绿 萝
供销社往事
头上喜鹊叫喳喳
五 玉
暗 恋
鸡蛋面
箭 头
追死一只戴胜鸟
知 了
能滚多远滚多远
村庄那些事
惊落的桂花
八 哥
拳 击
鼓 魂
水田衣
鹰 · 醉酒
关于抚摸的秘密
键 盘
雨从天上来
第八音符
城里的麦子
就是你了
张叔,刘叔
我还没有对象
完 善
向阳村的伊芝花
杀 驴
兰婶婶
蒋赖货
黄山甲家的苦楮
茶 商
四下无人
放鹿归山
序言/后记
|
| 內容試閱:
|
小小说的2023
1986年,小小说文体蔚成风气之际,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小小说是什么》,对小小说的文体定位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独到而精当的论述。其中写道:“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本色天然,充盈完美。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脱水蔬菜。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干了水分,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变成一篇小小说。……小小说自成一体,别是一功。小小说是斗方、册页、扇面儿。斗方、册页、扇面的画法和中堂、长卷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布局、用笔、用墨、设色,都不大一样。”他提出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要注意“留白”,讲究“句有余味,篇有余意”。作为小小说写作的早期实践者,汪曾祺先生的《陈小手》《陈泥鳅》等经典之作践行了其艺术理论,在小小说这一文体的少年时代为其树立了审美标杆,是小小说发展道路上明亮的灯盏。时至今日,小小说文体已然成熟,成长为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并立的中国小说文体的支柱之一。
小小说是小的,篇幅就那么长,不仅不可能像长篇或中篇小说一样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在一部作品中勾勒数十甚至数百个人物,即便只写一个人,也多只写其一面。然而一面写到位,便可使人物立得住,使读者有所共鸣,读后有所思,因而小小说可以成其“大”,以其言有尽而意深远。一个小斗方或者小扇面儿上固然不能塞得下《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这样的宏幅巨制,但足以从容地描摹汴京一二人物,展现秀丽江山一隅。惊涛骇浪有惊涛骇浪的雄壮,微风细波有微风细波的优雅。即便只描摹一二人物,假以时日,聚沙成塔,连缀成册,却也能得万千气象,终成蔚然大观之势。这是小小说的另一种“大”。冯骥才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俗世奇人》(足本)便是以数十篇刻画清末民初天津奇人的小小说,勾画了一幅20世纪初天津卫的市井生活画卷,堪称“系列小小说”的典范。2023年,冯骥才的新作《万年青》延续了《俗世奇人》(足本)的气韵,续写着“市井人物列传”的新篇章。
本选集中收录了梁晓声、刘亮程、石舒清、石钟山、路也等人发表于《百花园》上的最新作品。他们都早已凭长、中、短篇小说或是散文、诗歌等扬名文坛,在小小说的选集中看到他们的作品令人欣喜。其中石舒清、石钟山等人的作品近年来多次出现在专门发表小小说的杂志《百花园》上,很明显,他们是在严肃地有文体意识地进行小小说写作。以诗集《天空下》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诗人路也,其小小说《分手信》也像诗歌一样呈现出一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高贵格调,颇具现代气息,既有对俗世悲欢离合的脉脉温情,又怀着一颗恬淡不羁的心灵随时准备放下、离开这一切。这些文坛大将们的小小说创作实践一再说明,小小说不是轻的、快的、浅的小说,“小”只是它的外在形式。像一切文学体裁一样,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作品的气质。
2023年,从当代小小说发轫之时便投身其中、数十年来耕耘不息的“小小说专业户”,如聂鑫森、谢志强、刘国芳、侯德云、于德北等仍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孜孜不倦地探索小小说的新写法,拓展新的写作空间。陈毓、陈敏、安石榴、袁省梅、吴卫华、朱雅娟等人是小小说女性写作的主力军,然而她们的作品并没有囿于女性视角或女性经验,而是以宽广的胸怀书写人性,关怀生命。张望朝、汪菊珍、朱赞军、岑燮钧、王在庆等是近几年开始主攻小小说写作的。他们的叙述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如张望朝的自然朴素、汪菊珍的细腻深情、朱赞军的京味儿、岑燮钧的严整、王在庆的沉静忧伤等。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文学性,创作中有“严肃文学”的自觉,属于雅俗共赏的小小说中偏雅的一类。
2023年,青年作家们也为我们带来了风格迥异、意象纷呈、品位不俗的小小说作品,如本选集中80后的何君华、刘晶辉、阿痴、九峰云、莫小谈、解飞扬、邢东洋、塔娜、飘尘、达瓦次里等,90后的包文源、刘佳、李森等。青年作家们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往往“不按套路出牌”,比如九峰云的《关于抚摸的秘密》以抚摸引发的神奇体验描摹人与人之间奇妙的情感连接;刘晶辉的《键盘》中那个失意的作家在听到妻子咒骂他“跟你的电脑过去吧”之后,真的像跳水一样钻进电脑,逃离了现实;飘尘的《雨从天上来》中的雨不是滴落,而是以手指般粗细的雨柱的形态固定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因而孩子们可以顺着雨柱爬到白云之上。另一些青年作家则立足于现实,如何君华的《老那的旗》、阿痴的《五玉》、莫小谈的《一次不受控制的死亡》等都以稳健的笔力书写了厚重的人文关怀。青年作家们在继承小小说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没有拘泥于传统,他们的写作是多彩的、自由的,同时也是认真的、诚挚的。《易传》曰:“修辞立其诚。”文学的未来属于怀着赤诚之心的青年们。
四十年前,小小说开始流行之时,固定电话都还远未普及,然而当时人们已经察觉到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与小小说文体广受欢迎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处在智能手机时代,正在进入全面的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生活相比四十年前可谓飞速运转,人们的闲暇时间是碎片化的,专注力已成为“稀缺资源”。今天,对于文字阅读来说,小小说不仅是读者的选择,可能也是时代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小说是游戏娱乐式的“快餐文学”,如同你可以利用等公交车的时间读完几首诗却不会认为诗是“快餐文学”一样。小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以“小说”的文学面孔走向读者的,和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一样发挥着启迪、温暖人心的文学功效。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阅读,感受小小说送给人间的小小温暖吧。
1000字内文
分手信
路 也
我住在雷克雅未克的Radisson 酒店,我的房间号是405。
在地球的这个位置,经线们就要收拢起来了,纬线的周长已经递减了很多,让人猜想,是不是正由于经线纬线变得紧凑逼仄的缘故呢,才使得这里的天空相应地看上去那么低矮而且阴沉?天空闷闷地罩在头顶上,似乎踮起脚尖抬起手来就能够得到了,而阳光几乎是贴着地面斜射过来的,坚忍,清亮,无声无息。这气氛给人以压迫感,仿佛有什么事情接下来就要发生了。是的,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从这里再继续往北去不远,经线和纬线将统统聚缩成一个点。
这里是世界上最靠北的首都。在酒店房间里,透过落地窗望出去,近处原本就已稀稀落落的植被现在变得萧瑟和枯黄,街道几乎是空的;远处有一个野湖横在那里,跟寂寂的天空相对痴望,而更远处黑色火山的轮廓隐约可见。有谁会在这样的初冬无缘无故地跑到这世界的尽头来呢?
我渐渐地感到有点儿无聊,开始翻腾写字台的抽屉。我在中间的大抽屉里看见一些风景画册,上面写的是这个岛国自己的文字——往往在一个单词中会夹杂着一个头顶着小撇的字母,如同扎了一个朝天辫儿,这是我第一天到来时就发现的新奇事。
我又打开右上角的小抽屉,里面有一本厚厚的时装杂志,看样子是供客人阅读的。拿起那本杂志来的时候,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抽屉底部,看见了一张写了字的纸——字是用黑色圆珠笔写的,纸用的是酒店里提供的窄小的便笺,有成人的手掌大小,上面的题头是酒店的矢量图和logo。看那文字的格式,分明是一封短信。信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如下:“我爱你,我心爱的Lizzie,很遗憾我们今生再也不能相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字写得有些匆忙,笔迹柔弱,但单词排列得间隔有致。
我愣了一会儿。
再去望窗外的时候,低低的天空似乎在轻轻颤动,景物在它之下仰卧着,使人有了恍惚之感。高纬度是孤独的,一切都在接近极限,似乎一切也都在逼入内心。
此刻我在哪里?为何这样一封分手信偏偏落在了我的手上?
信中没有日期和署名。想必那样一个特定情境是无须写日期和署名的。想必那个人匆匆写完,就拉起行李箱去了飞机场,而那个叫Lizzie 的人还在酣睡之中。
这封信是原本放在桌上或枕边,被看过之后又扔进抽屉里的呢,还是一开始就放在抽屉里,因而没被发现、压根儿不曾被读到过?如果这封信被阅过了,却没有被带走或者留存起来,当事人是出于忧伤痛悔还是心不在焉?
下楼用餐时,我顺便找到前台服务员,指着信笺上的“Lizzie”这个名字,问这究竟是男人名还是女人名,还有,是否会是这岛国的人名。前台小伙子认真地看了信笺上的字迹,很肯定地告诉我,一定是女人名,而且一定是英文名字。
来这个酒店住宿的大都是度假的外国人。那么,他们是谁?他们从哪个大陆哪个国家来?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情感迫使他们必须跑到这世界尽头来完成一个分手的仪式,在这世界地理版图的穷途走完那爱情的末路?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象这封小信背后的故事——在我住着的这个房间里曾经上演过一出分手的剧目。
从直觉上,先排除露水情缘,因为信的语调是那样诚挚、怅惘和哀伤,不是处于那种随便的男女关系中的人可以写得出来的。如果不是《断背山》里那样的同性恋,如果不是《罗马假日》式的童话故事,如果不是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打算跑到天尽头来殉情而未遂,那么极有可能是一个《廊桥遗梦》式的故事,是罗伯特·金凯和弗朗西斯卡从美国、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跑到这里来,进行了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
还有一个更凡俗的可能:从字迹来分析,这个写信的人——确切地说是这个写信的男人——应该是一个温存软弱之人。他缺乏行动力的性格,使得他与女友之间有了难以弥合的矛盾,于是就有了这次遥远到天边的旅行。他们寄希望于极地这令人屏神静气的纯粹和肃然,寄希望于极昼时那似乎永不会完全落下的太阳或者极夜时那永不会完全升起的太阳,能让他们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看清这爱情的真面目,要么挽回要么永诀。而最终的结论却是,他们彻底明白过来,人永远都是孤独的,就像这邻近极地的高纬度一样孤独。
我在脑子里编出了四五个版本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和发生在邻近北极圈的地方,意味是很不相同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一个爱情故事添加了孤绝感。
一个偶然读到他们的分手信的人,在作为这个故事的阐释者的同时,其实也成了这个故事的参与者。冥冥之中觉得,当我在试图描摹这两个素不相识者的故事的时候,一定有另外的什么人也在暗处读着我,就像那种安排了叙述者在镜头中出现的电影,观众同时也在看着那个同样是剧中人之一的叙述者。
说不清出于什么心理,我把这封短笺塞进了自己拉杆行李箱的某一个小夹层,跟一些零散纸质物品放在了一起。接下来,我离开了冰岛。
后来,这只行李箱又跟随我去过很多地方。我越来越喜欢独自旅行,一个人在地球上云游。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
某天下午,我在泰国清迈的酒店里,收拾行李箱,准备去机场,回国。我往行李箱某个小夹层里塞东西时,忽然从里面掏出了一张折叠着的纸片,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封英文短笺:“我爱你,我心爱的Lizzie,很遗憾我们今生再也不能相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于是一下子回忆起了十年前我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情景。
正值二月,现在北极圈内应该是极夜吧。在国土北部紧贴着北极圈的冰岛,太阳依然挂在地平线上,天和地离得那样近,像是终生相依,又像是永远分离。而此时此刻的我,则一个人旅行在北回归线以南。北纬18度,艳阳高照,花木扶疏,火红的凤凰花映着蓝天。
我把那张短笺拿在手里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并没有放回行李箱夹层,而是顺手扔进了清迈酒店房间的床头柜抽屉里。
接着,我拖起行李箱,离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