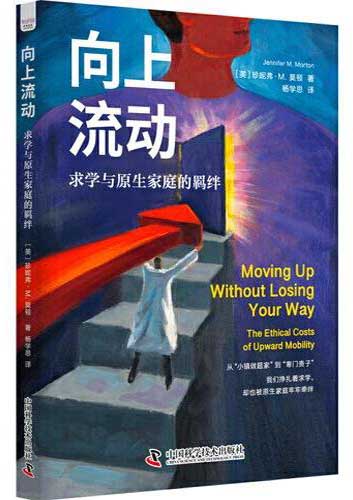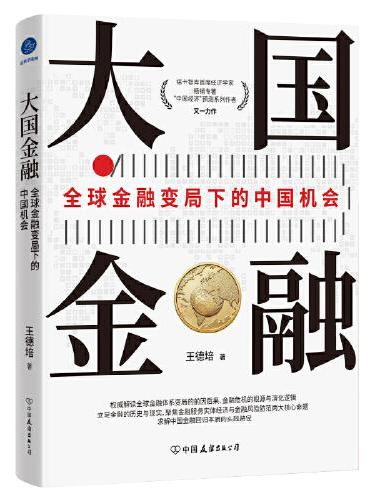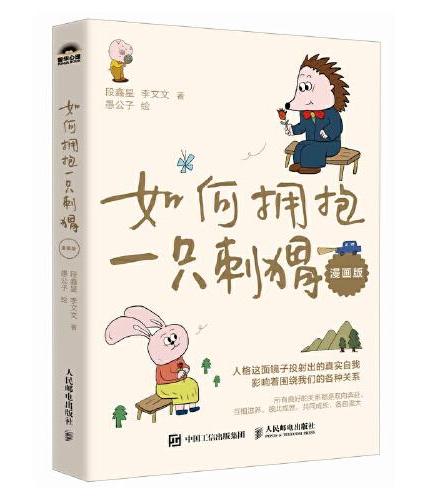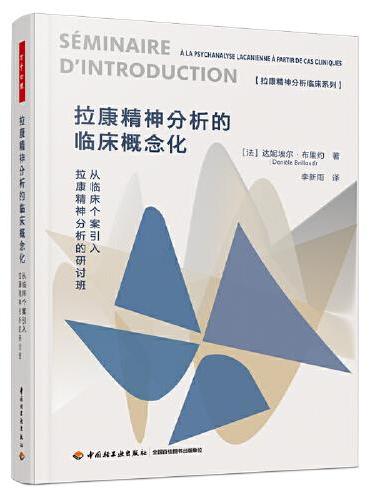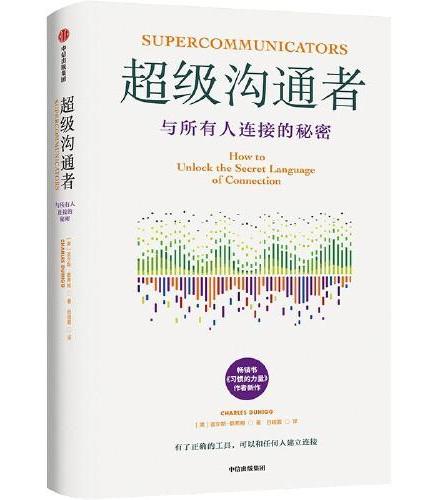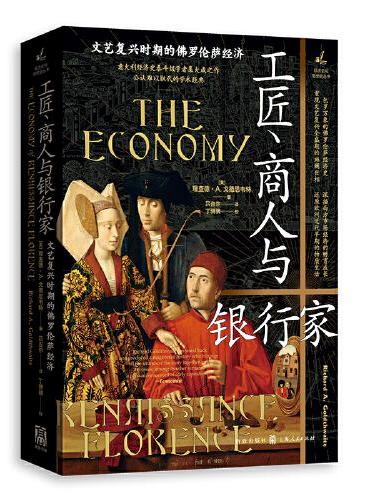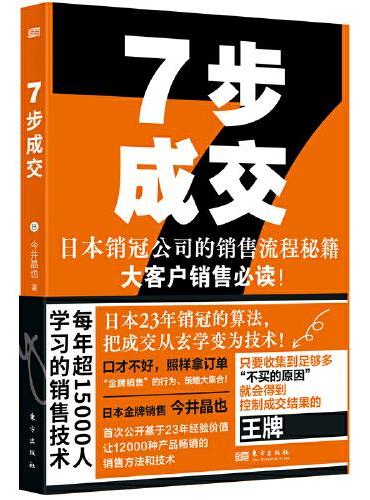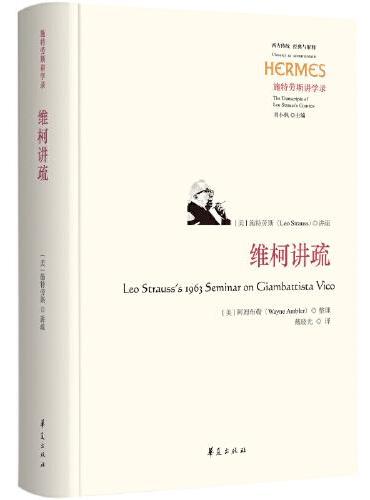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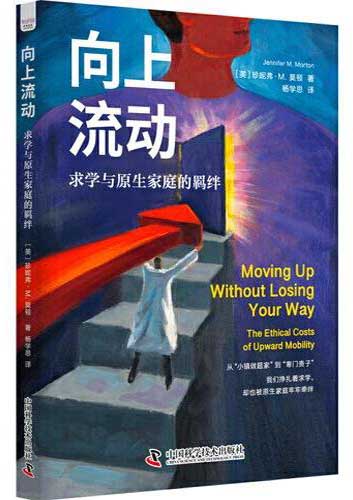
《
向上流动:求学与原生家庭的羁绊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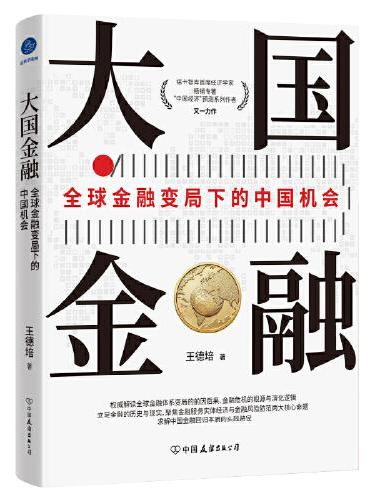
《
大国金融:全球金融变局下的中国机会(解读全球金融体系,变局前因后果,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演化逻辑,中国特色金融,现代金融体系)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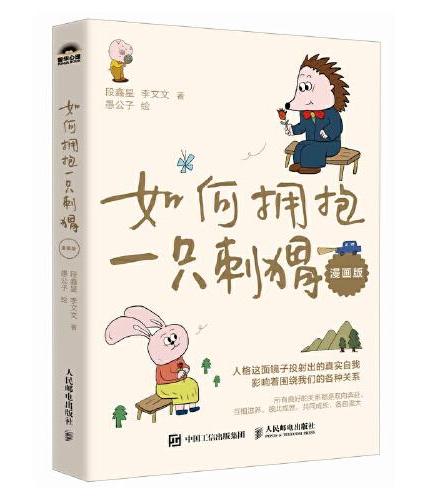
《
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漫画版)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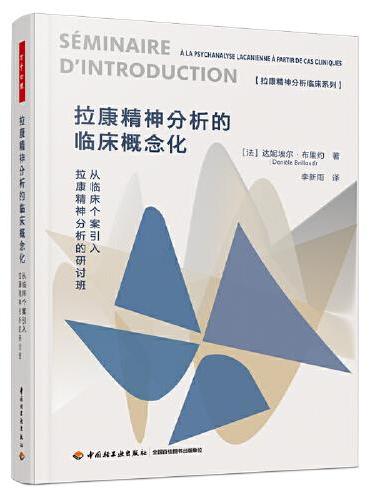
《
万千心理·拉康精神分析的临床概念化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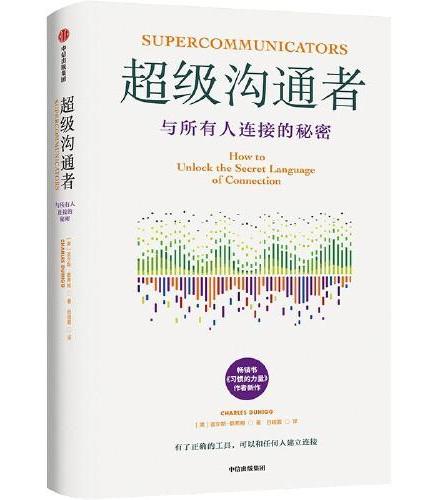
《
超级沟通者 与所有人连接的秘密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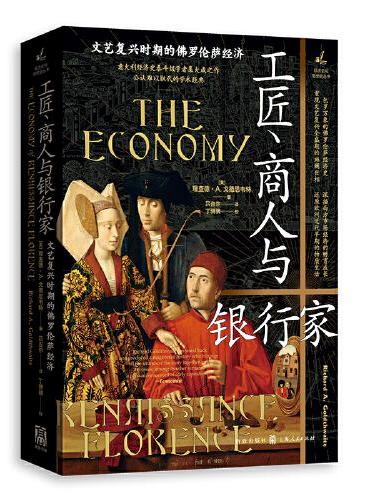
《
工匠、商人与银行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经济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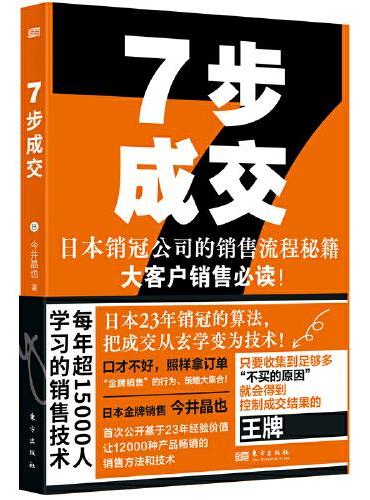
《
7步成交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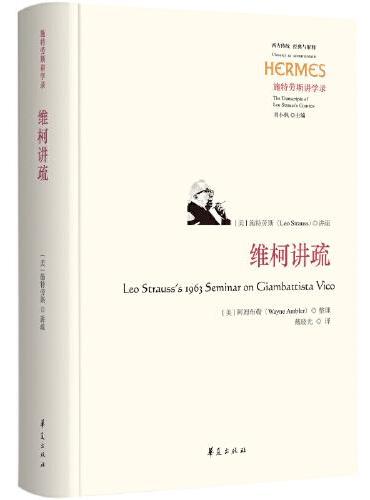
《
维柯讲疏
》
售價:NT$
607.0
|
| 編輯推薦: |
|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虽主要针对19世纪英国国内的一些社会弊病,但却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阿诺德在本书中提出的“野蛮人”“非利士人”“群氓”“希伯来精神”“希腊精神”等术语,已经跳出了具体的文本和学科,在西方人文学科甚至广义的西方文化中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而其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对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强调,不仅为英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奠定了基础、为利维斯的道德—文化批评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原初的理论范式,而且也经由白璧德等人传入中国,影响了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学者的文化观。
|
| 內容簡介: |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主将,阿诺德对其时充斥于英国社会的机器崇拜和功利主义深恶痛绝,同时也敏锐地指出国民对个人自由无限度的追求极容易导致社会陷入一种混乱、分裂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严重妨碍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他高举古典文化的旗帜,呼吁用“文化”统合分裂的社会阶层,从而用健全理智引导全体国民摒弃物质至上的庸俗风气、追求本民族“最优秀的自我”。
本书首次出版于1869年,作为阿诺德在文化批评领域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以文化代宗教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显示出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和高瞻远瞩的预见性,成为对20世纪英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名著。
|
| 關於作者: |
|
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1841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后担任英国教育调查委员会巡视员,奉命考察德国、瑞士、荷兰、法国等国的教育制度,1857年被选为牛津大学诗歌讲座教授,写过大量诗歌和文学、社会评论,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批评集》(1865)、《新诗集》(1867)、《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等。
|
| 目錄:
|
译本序
附:关键词
引言
第一章 美好与光明
第二章 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第三章 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
第四章 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
第五章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第六章 自由党的实干家
结论
序言(1869)
第十章 现实主义与后续传统:一则笔记
修订译本后记
|
| 內容試閱:
|
阿诺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具有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
* 本文节选自《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译本序,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文丨韩敏中
中国读者可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也听说过其代表作,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但是有兴趣翻开这部译著的读者可能会感到迷惑。首先,作品的副标题为“政治与社会批评”,可是它不像当今的社会科学著作那样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没有对“理论体系”的界定和阐述,甚至一再声明自己不讲体系;与此相关的是,行文的语言风格和现在我们通常读到的社会学、政治学或史学的著作也很不一样,几乎从头到尾用一种讥嘲、挖苦的口吻,时而也带着自嘲,况且将“文化”“意识”等当作人那样对待的修辞手段(如“文化说”,“文化要求我们”,“我们深入意识,意识就会告诉我们”,等等),也不大合乎现在人们对政治批评的期待。另一个可能的阅读障碍是,这部著作似乎沉浸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具体问题的争执之中,它大量地应答报纸杂志的报道和评论,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同当时的宗教纷争有关;这些具体问题似乎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更不用说当时的许多具体争端和具体看法早就过时(就像任何涉及时下热门话题的内容、见解都会过时一样)。对此,阿诺德自己早就有言在先。关于他所经常引用的18世纪英国神学家威尔逊主教的语录,他说:“我们应该像于贝尔所建议的,用读尼科尔的方法那样来读这些格言,即学以致用。由于时世变迁及因此必然引起的观念变化,其中有些内容已不再适用,读者可以将这些搁置一边。”
阿诺德去世时,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主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阿诺德在介入具体论争时所表现的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因为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也因为他发明的不少标语式词语早已进入核心英语,成为英语世界受教育者的常识性认识。例如,在英语中,阿诺德对英国中产阶级多少带有贬义的指称“非利士人”,大约就像中文里鲁迅笔下的“阿Q”或“阿Q精神”一样,已成为一个丰富的语义场。
有意思的是,从阿诺德写作的时代至今,一百多年来,他的巨大影响往往通过同他的争论体现出来,例如,《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就对后来有关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辩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说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当然不会感到陌生。我们的许多政治运动,包括现在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一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大到文学巨著《红楼梦》,小到普通电影《武训传》或《苦斗》,都可引发政治运动或成为运动的焦点;整个20世纪,我们感受政治风云、路线斗争、风云突变的神经已修炼得无比发达。但是,阿诺德所说的“文化”及其同政治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上述情况。“文化”应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这种宽阔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应成为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它在承认变革的同时讲究权威性和秩序,“文化”应体现出超越阶级、宗派、个人小利益的力量,其化身应是能够传承人类优秀思想遗产、整合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权威”或“中心”。阿诺德的“文化”所提倡的,是一种“学习”文明(而非颐指气使的“教导”文明),它讲究慢功夫,讲究沉下心来学习、思考,而且强调全社会、全民性的启蒙益智教育。阿诺德所说的文化的“敌人”,恰恰是埋头苦干,只管低头拉车、不管抬头问路,只讲实践出真知的实干家。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诺德一直被视为英美知识思想传统,或曰其“主流文化”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有“保守”的一面,但他所坚持的理想具有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总是如此黑白分明地定义和区分“保守”与“进步”,乃至“保守”总带着贬义,成为抱残守缺、进步的绊脚石的同义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我们一向较多地引进、吸收启蒙运动以来具有革命性能量的思想和著作,而对阿诺德这样的思想家却知之甚少。即使不谈我国的近现代史与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偏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就以我们处在日益向西方和全世界开放、经济实力飞速增长的时代而言,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价值理想,耐心地听一听我们所不习惯的话,或许会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
阿诺德主观上不想采取你来我回的论争姿态,只想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包括讽刺、挖苦、嘲弄等刺激人们认识现状之不足与荒诞的方式),不厌其烦地说理;但客观上他还是卷入了有关国家政治、政策、社会各阶层动向、宗教、国民性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论辩。《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在对论敌的回应中成书的,阿诺德也是借此机会对自己所坚持的思想又一次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尽管这部重要著作已一版再版,但当初在报章杂志上论争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阿诺德在某个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起报纸和其他杂志的关注和评论,他根据反应再写文章,报纸和其他杂志再评论,如此往复的过程最生动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界的实际情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阿诺德的论敌们都参与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以下简称《文化》)的写作,他们的批驳帮助他将思想整理得更加完整,阐述得更加充分,而且如他所愿地帮助扩散了他的思想,使其为触动大众而选用的词语(“美好与光明”“完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野蛮人”“非利士人”等)不胫而走。阿诺德虽然严厉批评了英国的自由至上主义,但是他能写出并发表这样的文章,本身也得益于英国论坛比较自由的、严肃的批评空气。杂志上对新书、文章的赞扬、好评当然是有的,但一般来说不大有恶俗的吹捧,相反对自己尊重的人也常有批评、评论(如阿诺德对卡莱尔等),看法可以很尖锐、不留情面,却是对事不对人。阿诺德的论敌尽管不接受他的见解,可仍尊敬他的人品、文才,有时二者还不打不相识,彼此生出一些好感,如他在《文化》中的主要批评对象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就对他赞赏有加。
《文化》的正文部分写作历经13个月,实际上从酝酿到最后出书的时间还更长。《当今批评的功用》于1864年11月在《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发表后,《星期六评论》有长文《马修·阿诺德先生与国人》评论该文,虽是匿名发表,但大家都知道作者是一直同阿诺德打“堑壕战”、信奉功利主义的菲茨詹姆斯·斯蒂芬。阿诺德静观事态,收集反应,心里已准备回敬;因1865年大半年在欧洲大陆考察,无暇顾及,他1866年2月方在《考恩希尔杂志》发表《我们英国人》(My Countrymen),正式转向政治批评。是年5月在牛津完成了《凯尔特文学》的最后一讲,因忙于写欧陆考察报告等,无法完成原定的诗歌讲座,一直到一年后,于1867年6月7日凌晨方完成在牛津告别演讲的讲稿,下午演讲,题为《文化与其敌人》,不久后按讲稿形式在《考恩希尔杂志》发表,这就是《文化》成书后的第一章“美好与光明”。此后阿诺德听从《考恩希尔杂志》主编史密斯的意见,仍静观事态发展,不忙于回应,待报纸和杂志的反应集中起来再写。到12月初,阿诺德已写好《无政府状态与权威》(Anarchy and Authority),但意犹未尽,不断要求“再加一篇”,一直到1868年7月共写就5篇,这便是成书后的第二至第六章以及结论。在写《无政府状态与权威》第5篇时,他已考虑将牛津讲座和这些文章,加上《我们英国人》等结集出版。
在出书前,阿诺德尚需为书作一序言,一方面对社会反应做进一步的回应,同时也为下面要写的《圣保罗与新教》做一过渡。1868年是阿诺德的伤心年,他的幼子巴西尔不到两岁就夭折,长子汤姆一直身体虚弱,就在阿诺德开始为《文化》写序言的时候病故,年仅17岁。但阿诺德仍完成了序言,并确定书名,1869年1月《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正式出版,不过章节号和各章标题是1875年出第二版时才加上去的,这些标题本身大都已成为名言。出第二版时还删去了一些指名道姓、过于涉及个人的文字。阿诺德生前还出过第三版(1882),1883年由纽约的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美国版的《文化》与《友谊的花环》合订本。20世纪上半叶的版本中,比较著名的是多弗·威尔逊教授编的1932年剑桥版。
维多利亚时期的杂志文化为思想的阐发和交锋提供了舞台,促成了思想的活跃;阿诺德在陆续发文时引起了很多关注,或许因为人们已熟悉了他的意见和文风,所以《文化》首次作为书籍出版并没引起什么反应,反而是后来的《文学与教义》(1873)等宗教方面的著作曾成为最热销的作品。但《文化》却始终能引起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和生命力,成为阿诺德著作中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也被看作阿诺德思想的核心。
……
阿诺德严肃检讨英国的国民性、习惯、心理定式,找出英国最缺乏的东西,提出人类全面、和谐、整体地走向“完美”的目标和标准,提倡以“文化”,或曰广义的教育作为走向完美的途径和手段,学习、研究自古以来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价值资源,从中补充、汲取自己所缺乏的养分。这些都不是当时务实的、性急的英国社会所熟悉和能够会心接受的东西,因此他被指责为不懂实际、超验主义、不着边际、高头讲章、玩弄精英主义、不关心不同情人民疾苦、长外国人的志气、灭英国人的威风,被人讥讽为“文化先知”,他的“权威”和“国家”论更是被说成专制主义。阿诺德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着什么样的力量,他想撼动的是什么样的痼习,因此从不存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然而,正是他那大量的、长篇的演讲和著述,将英国有识之士的思考推向空前的新高度和深度。人们的具体关注总是时时变化的,但在针对一时一事的具体意见被历史洗淘后,阿诺德讨论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宽阔深厚的关怀,以及切入问题时的视角,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在论争中,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他的思想不断发酵,他的名字已成为英语国家文化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标志,代表了对现行的一切和对习惯势力进行批评性审视,同时进行深刻内省的文化立场和文化姿态;而他的一些论敌,当时或许名声很响,但现在只是因为他的缘故还会被提到。他的思想的生命力还在于其“灵活性”:那种坚决反对机械、孤立地看问题,要看到事物的方方面面和看到事物之间潜在联系的思想方法,正是自由人文教育之根本。阿诺德的广阔视野和他的思想的开放性,使《文化》及他的其他著作具有了后来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和“对话”的性质,产生了“长效”;后人也确实始终在与他对话。可以说,“阿诺德已经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我们的观念形态的一部分。……在力图达到全面综合的视域方面,在试探性地提出文明的希望和出路方面,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反过来说,不懂得阿诺德,那么我们对当前世界上主要文明的了解就会显出莫大的欠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