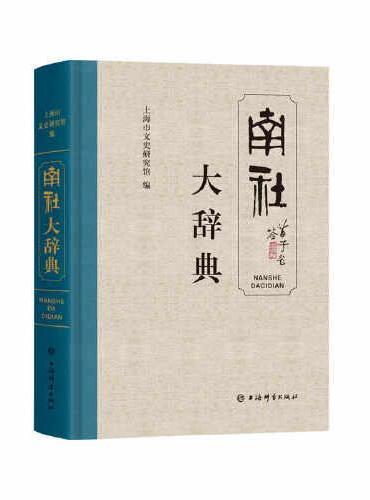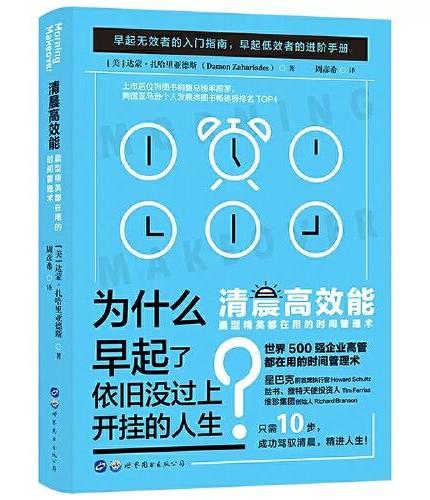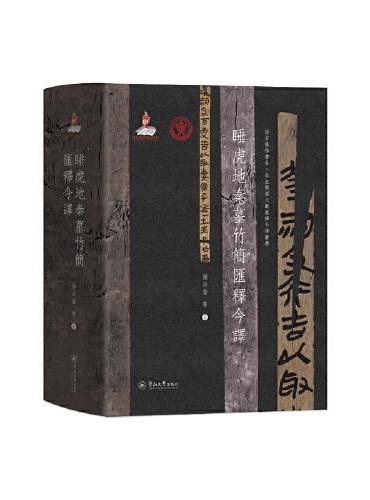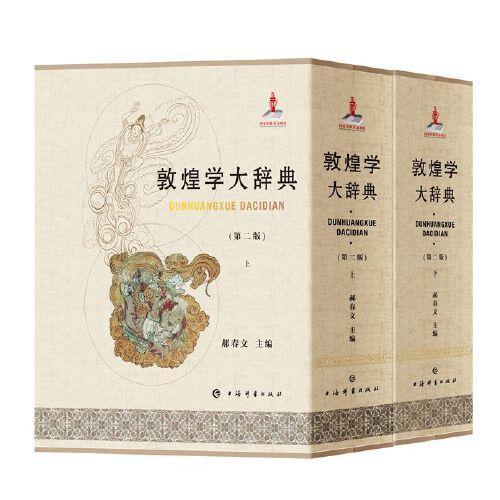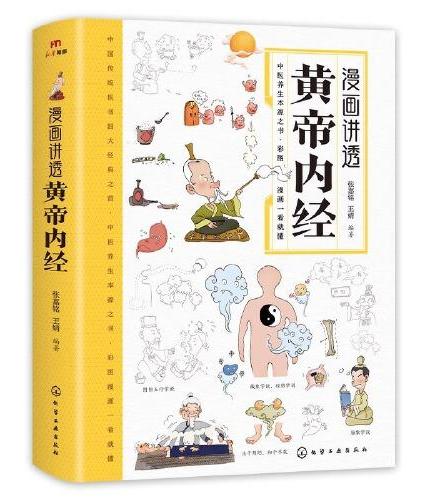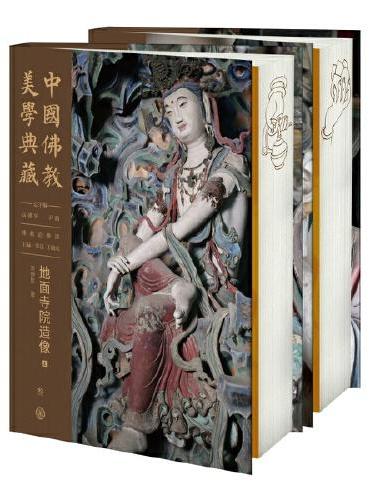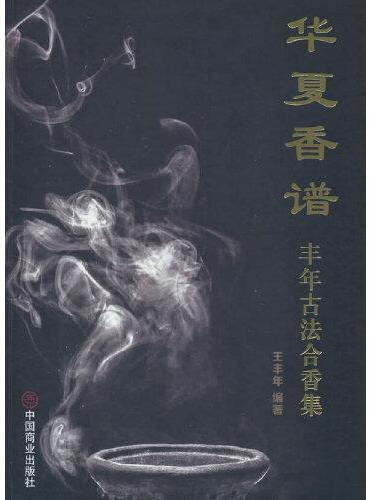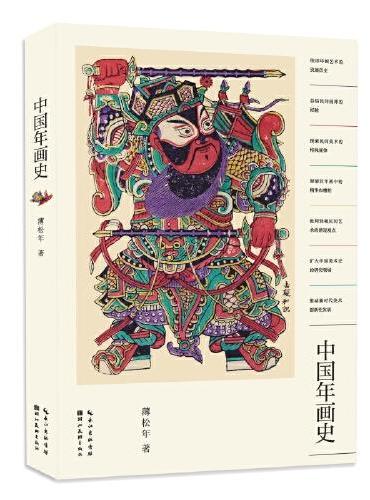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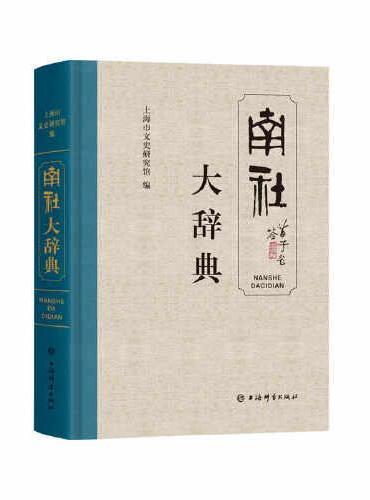
《
南社大辞典
》
售價:NT$
2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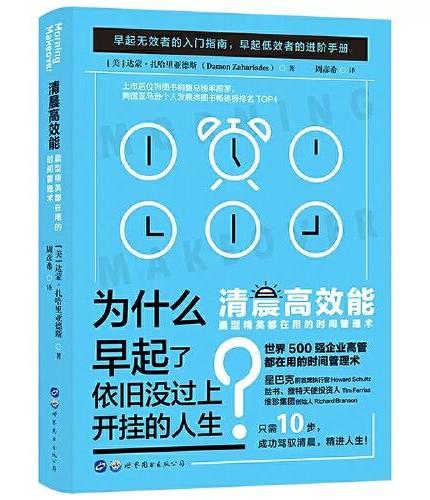
《
清晨高效能+掌控清晨(2册)晨型精英都在用的时间管理术 中小学课外阅读
》
售價:NT$
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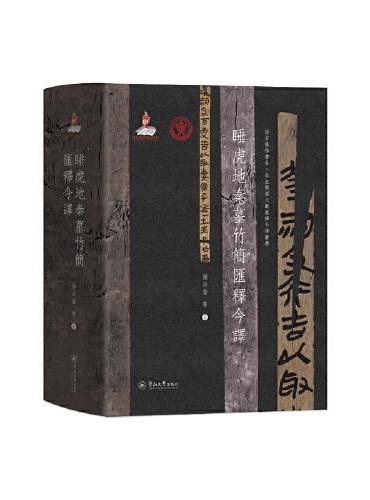
《
睡虎地秦墓竹简汇释今译(语言服务书系·出土战国文献汇释今译丛书)
》
售價:NT$
2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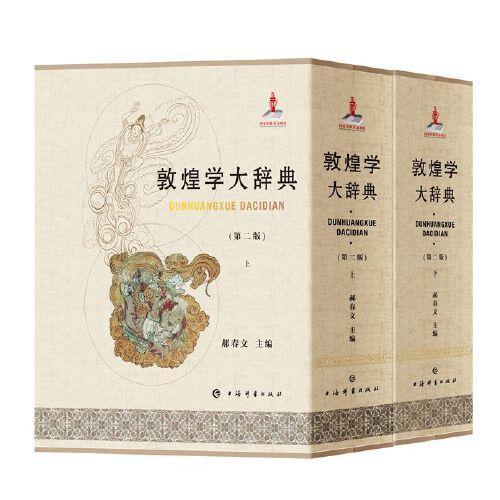
《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
》
售價:NT$
95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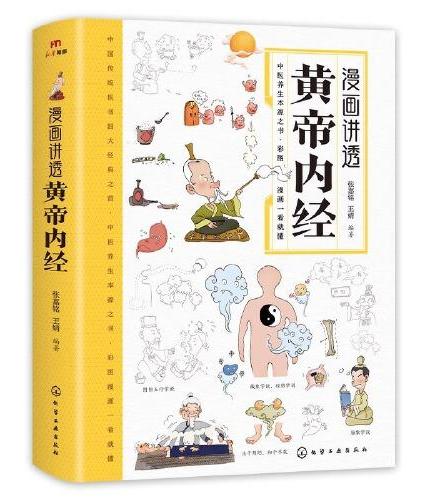
《
全2册图解本草纲目漫画讲透黄帝内经正版白话文彩图版中医书籍皇帝内经大字体全集食疗养生书籍大全
》
售價:NT$
6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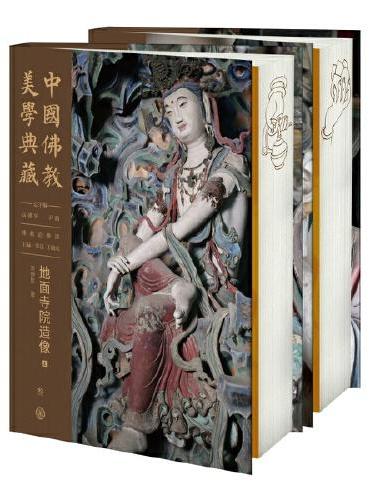
《
中国佛教美学典藏·地面寺院造像(上、下)
》
售價:NT$
6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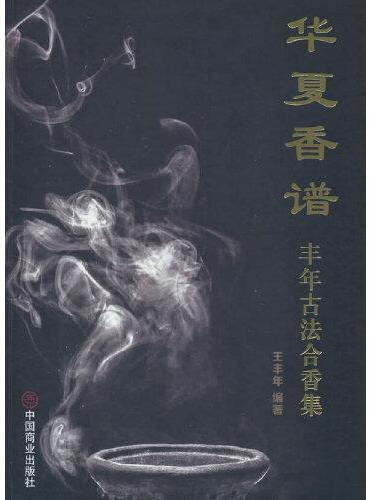
《
华夏香谱:丰年古法合香集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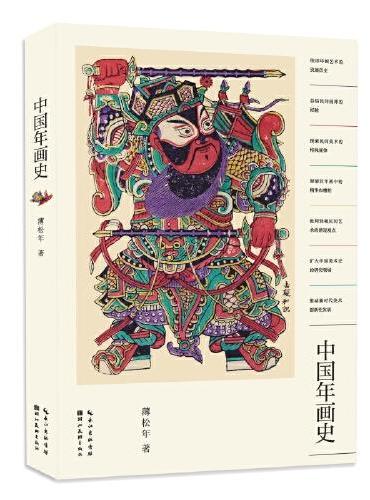
《
中国年画史
》
售價:NT$
857.0
|
| 編輯推薦: |
|
本书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在“说清楚”三个字上下了功夫,说清楚了四个问题:第一,朱熹的“中庸之道”在《中庸》原著里没有依据,它是曲解《中庸》原著并且通过修改原著才形成的理论。第二,厘清了《中庸》原著脉络,揭示了《中庸》原著的“中庸之道”,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联系社会实际对此中庸之道做了必要补充。第三,说清楚了朱熹所注释的《中庸》与《中庸》原著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它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特征,《中庸》是主观唯物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两者差别十分明显,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一目了然。第四,《中庸》的哲学特征是主观唯物主义。如作者说,之所以定名为“杂议”,取其议论角度之广。本书既有对朱熹中庸理论之矫正,此为一议;又有对《中庸》原著正确理解之阐释,又是一议;还有在看待若干社会问题上朱熹理论与中庸的差别,又是一议;等等。如此构成杂议。虽曰杂议,并非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
|
| 內容簡介: |
|
《〈中庸〉新解杂议》为湖北工业大学退休副教授张之权撰写的学术新著。全书分十四章,十三万余字。书中分析批判了南宋学者朱熹提出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中庸之道”背离了《中庸》的原意,是通过修改版本提出的错误主张,揭示了《中庸》原著的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种“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求真(或求实)之道。
|
| 關於作者: |
|
张之权,男,1933年5月出生,湖北仙桃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曾任连队文化教员和空军文化学校专职语文教员。恢复高考后,为湖北工学院中国革命史教师,并担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98年退休。参与撰写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湖北工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教程》等书。发表了《“游必有方”的本义及其社会意义》《〈中庸〉哲学意义溯源——学术界〈四书注释〉中修改〈中庸〉版本之误探析》《〈中庸〉断句,千古一憾》等学术论文。
|
| 目錄:
|
目录
第一章 《中庸》的历史地位及注释概况
第二章 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代尧舜立大统
第三章 朱熹的“不偏之谓中”是大杂烩
第四章 朱熹面临的鸿沟和版本的修改
第五章 修改版本没有依据
第六章 “中庸”本义之探讨
第七章 朱熹两个不能成立的论据
第八章 《中庸》前半部分几个重点内容梳理
第九章 修道的几个内容解析
第十章 真正的“中庸之道”
第十一章 《中庸》的哲学特征
第十二章 《中庸》和朱熹哲学思想之比较
第十三章 朱熹的天理、人欲观摭拾
第十四章 对朱熹天理理论的研判
|
| 內容試閱:
|
自 序
本书所述内容,主要是对朱熹注释《中庸》时对“中庸之道”所做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解释提出异议,从这个角度说可以称为“中庸新解”。但是,本书对“中庸之道”的解释,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忠于《中庸》原文,恢复《中庸》自身的定义和郑玄的注解,从这个角度说又谈不上“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早先是北宋学者二程(程颢、程颐)提出来的,不是朱熹的原创。但是,朱熹是二程学术上的继承人,他在注释“四书”时,完全继承了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就主要说朱熹。
“中庸”二字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至今找不到明晰的判定。这两个字最早见于《论语》。《论语·雍也》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不过,通观《论语》,并没有对此语的解释。什么是“中”?什么是“庸”?不知道。“至”是“来到”的意思呢,还是“最好”的意思?不好确定。
《中庸》一书,虽然以“中庸”为名,但全书对“中庸”二字也没有专门解释。书中有“中庸”10处,另有含“庸”的2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对于“庸”字,没有专门解释。
“庸”本是个多义词,它的内涵是附在“中”字上的。先确定“中”的含义,再对它进行恰当的匹配,朱熹说的“不易之谓庸”和郑玄说的“庸者,用也”都是这么做的。对于“中”,《中庸》第一章有两句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也不算明确的解释。正是因为《中庸》对这两句话没有明确解释,留下了理解空间,所以发生了歧义,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庸”。一个是《中庸》原文和郑玄注释的中庸,一个是朱熹的中庸。这两个中庸的存在人们是知道的,但从南宋以后学界只宣扬朱熹的中庸,而完全抹杀了郑注中庸。
这种修改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庸》原文明确认定小人有中庸,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认为小人不配有中庸,两方面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小人也有中庸,是不利于朱熹的中庸之道存在的,因此必须修改。不是近义词的调整,是反对关系的变更。在现代这种事是谁也不敢做的,必然招致口诛笔伐,因为,在逻辑上保持论说概念的同一性是必须遵守的准则。在古代,朱熹他们没有这个约束,极具随意性。
事实上《中庸》是对的,这种修改是不能允许的,必须批评朱熹。
批评的矛头直指朱熹是很难被中国儒学界接受的。朱熹被学术界推崇为孟子以后(也有人说是孔子以后)的大儒,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朝被奉为圭臬,直到现在,绝大部分注释“四书”的学者仍将其视为金科玉律,不曾有任何怀疑。但在“不偏之谓中”这个问题上,朱熹的许多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是牵强附会的,可是学界发出的赞许性议论文字,用“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其多。在这种环境下批评他的错误,如果没有高度的唯物主义精神,人们就很难接受。
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家,著述甚多。朱熹于宋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在今福建尤溪县,家境不好。祖父朱森“是一个只读经书,不问生计的酸腐士子,一生潦倒不得志”[1]。父亲朱松于政和八年(1118年)戊戌擢进士第,授福建政和县尉。其祖父朱森随子入政和县传授理学,宣和七年(1125年)不幸病故,因家贫而不能归葬江西婺源原籍。朱松在赵鼎任宰相时,“除校书郎、迁著作郎”,又以御史中丞常同荐,“除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2],可见其积有一定人脉。朱松诗名重当时,亲自培养了朱熹写诗的才能。
为了开拓沋郎(朱熹小名,因其出生于沋溪河畔而得名)作诗文的眼界,朱松常携带他出访名公硕儒和诗友,绍兴十二年九月他携沋郎有福州之游,是因为他的好友程迈来帅闽,但也是为了拜访归居长乐的著名诗人芦川居士张元干(幹)。张元干在胡铨上书乞斩秦桧被谪新州时,曾以一阕气壮山河的《贺新郎》送行曲而名垂青史,同朱松是志同道合的诗友。[3]
朱熹13岁时作诗已是“运笔生风,力能扛鼎”[4]。朱熹受父亲和家族的影响,年轻时究心于佛老之学。朱熹参加礼部试,用禅学的意思回答《易》《论语》《孟子》之义竟高中进士,后来师从李侗才弃释就儒。因而,朱熹对释、道、儒都有深刻研究,学识渊博。
朱松因秦桧决策议和而与同列上书皇帝表示反对,遭秦桧打击,便离开朝廷,“出知饶州”,未到任,47岁就去世了。这时,朱熹才14岁,家贫,依朱松遗嘱,奉母率妹赴福建崇安县五夫里投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在那里定居下来。他父亲的另一个朋友刘勉之“爱之甚厚”,把女儿嫁给了他。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受学于李侗。李侗也是他父亲的朋友,为程颐的三传弟子,对他十分器重,把贯通的“洛学”传授于他,可说李侗是朱熹成为理学大师的领路人。
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治、人民的疾苦、父亲的社会关系、贫寒的家境和良好的教育,是朱熹理学观形成的客观条件。
朱熹19岁登进士第,22岁授福建泉州同安县(现属厦门市)主簿。他历经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活了71 岁,《宋史》称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就是说他为官不到十年,其余四十年都从事讲学和著作。朱熹著作之多,在中国哲学家中少见。他自己撰写的和经他编定的著作有数十部之多,在其壮年,年年有著作,有时一年完成两三部,即使在为官任上也笔耕不辍。但是,涉及古书注释,亦有贻误。不过,这也在所难免,因为深思熟虑不足故也。
我们读书常有这样的体会:对同一本书,隔段时间再读,领会又不一样。朱熹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他曾说:“旧尝看《栾城集》,见他文势甚好,近日看,全无道理。”[5]
朱熹特别钟爱《四书章句集注》,注释了一生,修改了一生。有人要拿他的《中庸解》去刻印,他说:“切不可!某为人迟钝,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不可知。”[6]有人问他:“《大学解》已定否?”他说:“据某而今自谓稳矣,只恐数年之后又见不稳。”[7]一直到庆元六年(1200年)临终前,他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8]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朱熹留世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应算“盖棺论定”。他在世时不断修改,今次之改,必因于前注之失。难道因他去世,后人就无权质疑他的前注之失?显然没有这个道理。朱熹所注“四书”,未能忠于原文的地方多有出现,“不偏之谓中”是影响最大的一处。本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2013年,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出了一本新书《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书中列举朱注之失数十处。傅佩荣先生有这样两段话,我极为赞同。他写道:“我们对朱注求全责备,实因其六百年以来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所有念书人首先接触的注解。其影响深入而广泛,甚至掩盖了原文的意思。许多学者先入为主,认为朱注的说法即代表孔子原意,而其实未必如此。”“他的说法若有值得商榷之处,就须以合理的思维去验证。”[9]
傅佩荣先生说得很对,朱注《中庸》,有些地方确实“掩盖了原文的意思”,而学者们还以为它“代表了(中庸)原意”,连篇累牍歌之颂之,顶礼膜拜,取的却不是真经。
“不偏之谓中”,这句话没有错误。笔者批评的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说这句话是朱熹等人硬塞给《中庸》的,不是《中庸》原文的精神。朱熹的“中庸之道”,美则美矣,说起来好听,其实从来没有人实践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到底什么是“中”?他们的解释太玄,绕来绕去,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也不一定能被大家接受。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释《中庸》时,理学系统已经形成,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庸》注释中表现明显。他极力推崇《中庸》,要求人们读“四书”时,先读《大学》,次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10]。而他在注释《中庸》时,社会已前进了1000多年,社会生活的积淀,他的学识的增广,已经超过了《中庸》的承载范围,所以,他在注释中,就不自觉地在许多地方不顾及《中庸》的“古人之微妙”而塞进他的理学思想。于是,他所推崇的《中庸》就成了被他用“不偏之谓中”改造过的《中庸》。这种痕迹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他注释的《中庸》与原著《中庸》的多处矛盾。这种矛盾的消极一面是朱熹的“硬伤”,给朱熹造成了很大被动。研究朱注《中庸》,看不到两者的差别,只给朱熹唱赞歌,是没有读懂《中庸》,也是不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硬伤”。
朱熹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发展到宋代的表现形式,它的出现和存在有其合理性。简而言之,学术的抑扬兴衰都离不开政治。赵宋新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五代那种政权走马灯式的更迭,自然会谋求经济发展的稳定和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每一个政权都是要有理论为其服务的。北宋前期就有一批有才能、有建树的知识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从传统的儒家学说中找出思想武器为巩固北宋王朝的政治服务。二程理学就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
学术有从属于政治的一面,具有了一定规模之后,其“从属”的一面有时会变成强烈的政治诉求。朱熹与程颐相差90多岁,是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出生时,北宋已亡,南宋偏安,秦桧当权(朱熹出生第二年秦桧为相),岳飞被害(是年朱熹13岁),官员腐败,生民涂炭,加上贫寒的家境,使其更了解民间疾苦,这些都反映到了他的思想里。他为人耿直,在为官任上,能体察民情,抑制豪强。他一方面不断给皇帝上书,揭露官场和社会弊端,一方面研究学说,并和其他学派的学者辩论、切磋,所以朱氏理学有反映社会要求的一面,这就是政治诉求,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进步是忠君的,是维护三纲五常的一种呼喊,是人为设计的皇帝和平民之间的一种平衡。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几样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计,是天子的专利。《中庸》又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意思是说,身居下位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获得君王的信任,不然你就得不到治国的授权,当不了官。它还说“天下之达道五”,其中第一个就是君臣之道,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是“达道”之中最重要的“道”。这些话都是皇帝最喜欢听的,如此,哪个皇帝不喜欢《中庸》?
儒家学说里面还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慎独”“中庸”“民贵君轻”等思想。这一类话,似乎对皇帝也是有制约性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喜欢这些话,尽管不起作用,士大夫们却陶醉其中,民众也乐意接受这些思想。朱熹专门提倡“四书”,这些东西都被从“四书”里发掘出来,成为全社会都能接受的东西。再加上他反复论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所以朱熹的学说能被当朝统治者欣赏,被抬到很高的地位。皇帝抬,知识分子也抬,社会各界都抬,于是越抬越高。
哲学来源于对世界的认识,也是解释世界的学说,具体而言是解释人和客观事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时代不同,解释的水平也不同。《中庸》作为哲学著作,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及《道德经》,但它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度优于《道德经》,这跟它比《道德经》晚很长时间有关,也跟它的内容单一且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
《中庸》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它承认事物的真实性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对于这种客观的真实性如何认识?它提出了一套“诚之”的方法,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归纳起来这是一套“求实”的方法。真正的“中庸之道”是求实之道,说得非常明白,比《道德经》明晰许多。只是被朱熹的“不偏之谓中”掩盖了光芒。
《中庸》的哲学特征是,观察事物的态度有唯物主义成分,而认识事物的方法基本是主观体验式的,合起来是一种主观唯物主义。它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却靠主观体验去认知事物的规律性。如果用在社会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社会实践作基础,它就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时,它的认识是否正确,可以由事情发展的结果予以证明。如果用在自然科学领域,它不强调物理、化学方法的验证,对很多问题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将问题刨根到底。
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面的,人们在实践中取得的认识是否正确,还需在以后的实践活动中进行检验。而正确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实践就能取得的,必须经过多次实践、多次修正错误才能取得。凡属科技方面的认识,必须有科学实验的验证才能算数。
朱熹晚年,程朱理学曾被彻底否定。朱熹得罪权臣韩侂胄,皇帝对他的“聒噪”也厌烦了,在他67岁的时候,“程朱理学”被朝廷定为“伪学”,还有人上书要求斩杀他。是时,“四书”等儒学书籍被列为禁书,被列入“伪学逆党籍”的官员有名有姓的达59人,其中宰相就有4人[11]。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朱熹仍然讲学不辍,处之泰然。他去世后不久,即全面翻案,学说被尊崇,人也被抬高,朝廷追赠的名号有“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太师”“信国公”“徽国公”“齐国公”等。朱熹被否定得彻底,翻身得也彻底,打而不倒。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政治因素,也是他的学说的内在因素决定的,具体内容许多研究朱熹的著作对此都有详尽记载。
本书不是研究朱熹的专著,之所以较多联系朱熹,是想通过他注《中庸》之失这个窗口认识朱熹学说的特点,进而正确认识《中庸》。
中国两个“中庸之道”区别的源头在于对“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个判断中的“发”与“中”的解释不同,两者相去较远,不能互相参照,互相补充。它们只能“共存”,各说各的,各行其是。
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严谨的风气,有些学者在其著作中直接修改了原文,写成“小人之反中庸也”,开始只有少数几人,现在则比较多见了。
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有完整的体系。他学问高深,当时的人们没有能力批评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朱熹,而在于弄清楚他所主张的究竟是什么?他的中庸之道和《中庸》原著究竟有何区别?他的理论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多远距离?这些,对我们才是最有益的。
朱熹对《中庸》的注释,学界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人数不多,都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论述。论述稍为具体一些的是卢元骏的《五经四书要旨》(台北三民书局,1972年 )。
该书第94页说: “程、朱解释‘中庸’二字,‘中’字的意义与郑氏所解虽难同,而‘庸’字的意义则仅取‘常’而忽去‘用’了。我们试从《礼记》中使用‘中庸’一词的文句会拢来看,从‘常’与‘用’两种解释来加以选择,似乎解作‘用’字更易获合理。”“《中庸》这一部书命名的含义,还是以郑玄的‘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较为中肯。”
如此寥寥数语,远远达不到将问题“说清楚”的要求。
本书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在“说清楚”三个字上下了功夫,说清楚了四个问题:
第一,朱熹的“中庸之道”在《中庸》原著里没有依据,它是曲解《中庸》原著并且通过修改原著才形成的理论。
第二,厘清了《中庸》原著脉络,揭示了《中庸》原著的“中庸之道”,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联系社会实际对此中庸之道做了必要补充。
第三,说清楚了朱熹所注释的《中庸》与《中庸》原著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它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特征,《中庸》是主观唯物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两者差别十分明显,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一目了然。
第四,《中庸》的哲学特征是主观唯物主义。
本书为什么侧重于“议”,有两个原因:
其一,关于《中庸》章句注释的书籍汗牛充栋,除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元、明、清三朝以及民国时期的千百种注本,现在的注释本也有数十种,我们无须再着力。
其二,是正确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需要。
我们知道,《中庸》原著的本意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它在多处按照古人的——实际是儒家的准则进行了议论。这些议论经过朱熹等人之手被奉为金科玉律,人们必须无条件地遵照执行。这些准则是服从于、服务于“三纲五常”的,千百年过去了,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无议不足以明理;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恰当的议论就会沦为封建文化的贩夫走卒。所以,本书联系《中庸》原著中的某些内容进行了适当议论,以期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例如,《中庸》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这句话被很多人强调为做人要循规蹈矩。这显然是片面的,是不利于创新的。我们要重新审视“素隐行怪”,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
次如,《中庸》是提倡孝道的, 而儒家的孝道是服务于封建生产关系的,现在正在消亡过程中。这个消亡过程很快,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就不能正确认识这种历史现象。
之所以定名为“杂议”,取其议论角度之广。本书既有对朱熹中庸理论之矫正,此为一议;又有对《中庸》原著正确理解之阐释,又是一议;还有在看待若干社会问题上朱熹理论与中庸的差别,又是一议;等等。如此构成杂议。虽曰杂议,并非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请读者鉴察。
本书只是笔者多年来读《中庸》获得的一些心得体会,抛砖引玉,难免贻笑大方。
00笔者读过几本水平很高的研究朱熹的专著,得到很多教益。这些著作都是从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的,对朱熹多有赞美之词,无可厚非。像朱熹这样的大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该赞美的应该赞美。本书所论“中庸之道”只涉及其学说的一个点,不是面,完全是个人一孔之见,没有针对任何学者的意思,我对这些作者皆充满敬意。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湖北工业大学汉语言传播系原系主任张剑平教授诸多帮助,无任感怀,谨致谢忱!
张之权
2021年2月2日于湖北工业大学
第一章 《中庸》的历史地位及注释概况
《中庸》出自《礼记》,这一点从东汉郑玄注“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以后一直是明确的。但在西汉初年并不明确,《中庸》最初是以独自成篇示人的,与其他书籍并列,地位很高。《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下面,笔者来说一说这个情况。
首先,是礼籍的毁灭严重。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从“礼”的功用方面,论述了“礼”的来源。在周王朝的贵族教育体系中,礼被当作“六艺”之首,足见礼之重要。礼者,礼节,与乐、射、御、书、数,被认为是“养国子以道”(《周礼·保氏》)。 只是由于周王室衰败,各诸侯要扩张,《礼》的规定限制了他们的手脚,“乱臣贼子”的帽子有损于他们的名声,他们将众多礼籍毁灭了。到孔子时《礼》就已残缺不全,到秦统一时就“大坏”了,所谓“王纲解纽”“礼乐崩坏”。《汉书·艺文志》是这样说的:
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至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
这里说的“皆灭去其籍”,不是一个诸侯这样做,而是诸侯都这样做,自然损毁严重。
其次,秦朝灭亡后,《礼》是从哪儿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 言《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则鲁高堂生……”这两种说法中,“鲁高堂生”是吻合的,不同之处是,《汉书·儒林传》直接将《士礼》说成了《礼》。
《汉书·艺文志》在总结时也肯定了“鲁高堂生”,它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这就是说,到汉宣帝时传到了后仓。实际上中间还有萧奋和孟卿两人,高堂生传萧奋,萧奋传孟卿,到宣帝时孟卿传后仓,由后仓传到了戴德、戴圣及庆普。 后仓很权威,他解说《礼》的著作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汉书·儒林传》)。以后的脉络就清楚了。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由于有官爵和禄利的刺激,“五经”的传习十分昌盛。武帝至平帝一百多年间,一部经的解说可以至百余万言,大师多达一千余人。《礼》的传习从最初的鲁高堂生一家,发展到13家,555篇(《汉书·艺文志》)。
再次,《中庸》是怎么提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对13家,555篇文的分布列了一个表(数字略有出入):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 石渠。
“《中庸说》二篇”就是在这里单独列出来的,看不出它和其他篇目的联系。现在所传的《中庸》全书3568字,不算大著作,秦以后能在第一批有关“礼”的著作中被单独列出来,足见它的地位之高。
对于《中庸》与各篇的关系,有关专家做了如下梳理:
《礼古经》十七篇,即《仪礼》的前身。各类有关《礼》的《记》一百三十一篇,加上《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乐记》十一篇,《月令》一篇,即《礼记》的前身。[1]
这样就把《中庸》和《礼记》联系到了一起。
东汉以后又有人将它单独挑出来进行宣传和学习,南朝宋戴颙和梁武帝都注过《中庸》,但没有版本留传下来。《中庸》地位提升的关键因素是唐朝的科举考试制度。2018年8月25日,《光明日报》曾载杨少涵《〈中庸〉与科举》一文,对此论说颇详:
科举制度肇兴以后,《礼记》的地位继续巩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考定《五经》,贞观十二年(638)又诏孔颖达等人撰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卷一九六)。唐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最后刊定,“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需要指出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经”增列为“九经”,《周礼》《仪礼》才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唐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侧重于识字记诵,进士侧重于杂文策论。唐制规定无论是明经还是进士,都要加试“帖经”。帖经相当于今天考试中的填空题:给出一行经文,贴住其中三字,让考生填写。这就要求全国考生对“五经”的全部经文必须烂熟于心。从这时候开始,《中庸》逐渐为天下读书人所熟知。
中唐以后,《中庸》频频亮相科举考试中。首先,科考试卷从《中庸》出题。贞元十九年(803),明经科策问第二道题中有“蹈白刃或易于中庸”一语,即出自《中庸》第九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十五)。其次,考官策问使用《中庸》词语。贞元二十一年(805),权德舆策问考生时曾使用了“尽性”“不敢作礼乐”“哀公问政”“文王无忧”“凝道”等词语,这些词语皆出自《中庸》(《钦定全唐文》卷四八三《明经策问七道》)。最后,考生答题引用《中庸》内容。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二十六岁的韩愈二度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作《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其中就引用了《中庸》第二十一章“诚明”“明诚”和第八章颜回“择乎中庸”的相应文句。[2]
到了北宋,由于君臣竞相推崇,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中庸》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玉海》卷三十四记载,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年)在皇家琼林苑赐新科进士王尧臣等377人闻喜宴于琼林苑中。宴会中赐每人御书《中庸》篇一轴,从此“遂以为常”。对于仁宗如此重视这一措施,《玉海》还有一段生动的记载:起初,仁宗想赐《中庸》,先命中书抄录完成,呈上以后,他就命宰臣张知白来诵读,读到“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复陈之,仁宗听完终篇才停止。宋仁宗13岁登基,这一年才18岁。一个如现在高中毕业生年龄的青年已经有了5年当皇帝的经验,他的好恶取舍是皇帝的身份决定的,对于《中庸》的修身治人之道,他自然喜欢。《中庸》第二十八章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第二十章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还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哪个皇帝不喜欢这样的话?宋仁宗在位42年(1022—1063年),在皇帝中是不多见的,他赐《中庸》之举在皇帝中也是罕见的。天圣五年(1027年)宴赐《中庸》之后,过了7年[景祐元年(1034年)],他又赐新第张唐卿《中庸》。又过了8 年[庆历二年(1042年)],赐杨寘《中庸》;又过了7年[皇祐元年(1049年)]赐冯京《中庸》;又4年[皇祐五年(1053年)],赐郑獬《中庸》。26年间五赐《中庸》。
说这些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再看下面的列举:
宋仁宗生于1010年,范仲淹生于989年,只大仁宗21岁,仁宗亲政时他正当盛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只大仁宗3岁。其他几位当时的著名学者都比仁宗略小,司马光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程颢生于1032年,程颐生于1033年,沈括生于1031年,苏东坡生于1037年。他们都在仁宗执政时期或稍后成长起来。皇帝如此重视《中庸》,朝廷考试出题有的也来自《中庸》,《中庸》对他们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
除了朝廷的导向,学者们对《中庸》的研究、发掘,应该说作用更大。著名哲学家张载“少喜谈兵”,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张载曾去晋谒。范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而劝他去读《中庸》。后来,张载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3]到了二程,他们给《中庸》定了调:“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4]从此以后,《中庸》研究就一直沿着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到了南宋朱熹时期达到顶峰。朱熹专门为《中庸 》及《大学》《论语》《孟子》四本书作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集中宣扬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因此在元、明、清三朝备受推崇。由于科举考试试题很多出自“四书”,《中庸》里也曾出过考题,因此,不少人能将“四书”背得滚瓜烂熟。
民间读“四书”之风,在清朝被推翻之后很多年仍很盛行。1938年的时候,我们乡下(江汉平原)还办私塾,当时乡下没有新式学堂、新式教师和教材,私塾学堂只得还教“四书”。
《中庸》如此受到关注,研究者云集,注释名目之繁多达到惊人的地步。朱熹以前,学界对《中庸》的注释仍是夹在《礼记》中进行的,只有注、音义、正义、疏等几个层次的梳理文字。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出现以后,对其注释的名目日益增多,常见的有:(四书)集注、集解、集成、义、要义、精义、疑义、释义、解义、译注、通论、道贯、读本、窜释、说略、要旨、章句、或问、语类、 训诂、本旨、衍说、喙鸣等;将《中庸》单列进行注释的名目又有:(中庸)注、论、解、义、义解、解义、大义、广义、讲义、篇义、辑义、新义、析义、口义、讲疏、 顺讲、直指、辑略、研究、精注、类释、今译、质疑、探微、新解等,这些名目共计超过50种。
看看这些名目,就可得知人们对它重视的程度了。注释文字中对“中庸”是什么,说来说去只有那么几条。 程颐以前,学界对《中庸》的注释比较单一,基本上墨守郑注。即使程颐以后,歧见也不多。
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曾概括出四种说法:
郑玄《目录》云: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礼记正义》引),此一说也。
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杨时:《中庸解》自序)此又一说也。
程颐为《中庸》作解,自以不满其意而焚稿焉,遂以属门人郭忠孝。忠孝《中庸说》谓,“中为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国家”。又云:“极天下至正谓之中,通天下至变谓之庸。”(朱彝尊《经义考》引黎立武说),盖中之训,本诸师说; 而庸之谊,兼采郑玄,折中二家之间,此又一说也。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此又一说也。
钱基博先生虽然列出了四种说法,其实在郑玄以后的三种说法中,合起来还是一种,就是程朱的见解,并无什么新意。[5]
直接置疑朱熹“中庸”二字注释的人不多,都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论述。阐述得稍为具体一些的是卢元骏的《五经四书要旨》(台北三民书局,1972年)。
该书第94页说:
中庸二字的含义,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的解释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引郑玄这一段话,但郑玄在中庸著作中又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所以郑玄对中庸之解释是兼具用与常两种意义,因此就合成为“用中为常道”。但是程颐却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也持相同的意见:“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氏所说庸为不易,庸为定理,也便是常。是则程、朱解释中庸二字,中字的意义与郑氏所解虽难同,而庸字的意义则仅取“常”而忽去“用”了。我们试从礼记中使用“中庸”一词的文句会拢来看,从“常”与“用”两种解释来加以选择,似乎解作“用”字更易获合理。中庸这一部书命名的含义,还是以郑玄的“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较为中肯。
这些话仍是在兜圈子,对于剖析朱注《中庸》之失没有什么作用。
《中庸》这本书,被朱熹抬得很高很玄,他引用二程的话说《中庸》一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等等。由于太过痴迷,按《中庸》本义注释不下去,就曲解《中庸》本义,进而修改了原著。
这本来是个明显的事实,可是继朱熹之后为《中庸》作注的人不讲原则,迷信权威,几乎都顺着朱熹的路子走,人云亦云。
按朱熹所注,“中庸之道”就是求中之道,就是不偏不倚,结果被误解为折中主义,形象很不好,伤了《中庸》元气。朱熹对《中庸》的曲解危害很大。《中庸》全书的宗旨是“用中以求实”,“求实”主旨在《中庸》里很明确,它用大量篇幅进行了论证。坚持求实思想,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认识《中庸》?“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庸》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它算不算优秀文化遗产?这些问题还是要搞清楚的。为此,笔者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庸》这个问题,希望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章 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代尧舜立大统
朱熹在注释《中庸》时,写了《中庸章句序》,对《中庸》的作者、写作目的、《中庸》的内容及意义作了全面介绍。这个序是朱熹理学思想成熟以后写的,反映了一部分朱熹的理学观点。现将此《中庸章句序》介绍如下。
《中庸》的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朱熹也是这个意见。关于《中庸》的写作目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什么是“道学”呢?朱熹没有直接回答,按他的论述,这来源于“道统”。
尧舜时期的思想,与孔子时期是有区别的,与朱熹时期更不可相提并论。
按现在史学界的说法,尧舜时期可算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私有制正在形成,但没有最后形成。尧和舜之间,有帝位“禅让”的做法,他们的那个“帝位”和孔子、朱熹时代的“帝位”不是同样的概念,他们的“帝”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有“禅让”的可能。私有制引发的斗争已相当激烈,但不如后世的不可调和。
这里,可以引用司马迁《史记》的材料。《史记》的描述,在秦汉以后的封建帝王的眼里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绝对不能允许的,但尧舜时期却没有掀起血腥大浪。这反而可信:
舜的父母(后母)想害死舜,只有一个条件的存在才讲得通,就是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舜的家中有牛羊、仓廪,自家还能打井,后母生了兄弟象,父亲喜欢继妻及象,待舜不好。舜却孝顺不减,名声传到尧那里去,尧就培养他,给他牛羊、仓廪、絺衣和琴,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可舜的父亲还想害死他。舜上房修仓库,其父从下面放火要烧死他,他抓住两顶斗笠跳下逃跑了。舜挖井,其父和象又给井填土要活埋他,舜早有预防,在井下面挖了个斜洞逃了出来。井填好了,象得意地说,这都是我的好主意!他占有了尧赐给舜的所有财产及两个妻子,家里的财产给了父母。《史记·五帝本纪》就是这么记载的: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
“舜父瞽叟顽,母嚚(yín,蠢而奸诈),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想杀他,不得手;要找他,他又常在身边)。”
“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为舜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
舜的父母和弟弟象阴谋杀死舜及霸占财产的过程,《孟子·万章》有同样的叙述,可能《史记》取材于《孟子》。 他们这样做是很嚣张的,如果不是为了财产,就不可能这样。这些记载有一定可信度。
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在朱熹时代,就是皇帝将两个公主同时下嫁给一个平民,完全不可能。尤为严重的是,象不但害死了驸马,还霸占了两个公主,而公主的父亲尧还在帝位,那岂止要诛戮他全家,还得夷灭三族!司马迁没有说,意味着此事没有发生,平和地过去了。这也说明时代不同,观念不同,没有相同的“道统”。而朱熹硬要说其中有“道统”相承,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再比如说,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被舜杀了,史称“殛鲧于羽山”。舜杀死了禹的父亲,最后又将帝位传给禹,而且是被杀者的儿子,这在朱熹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有什么“道统”可以相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