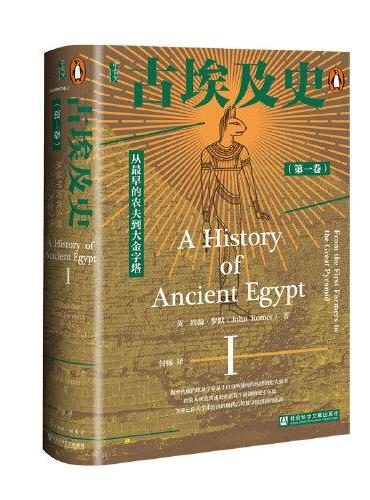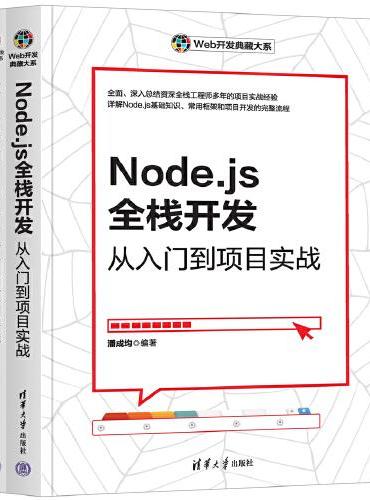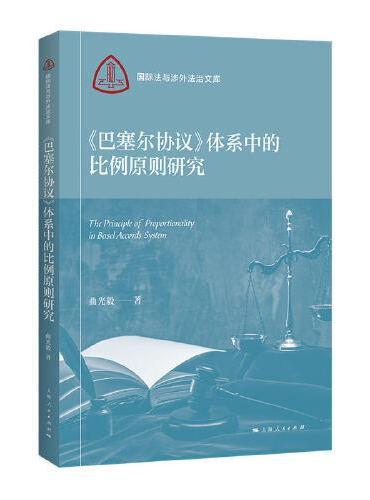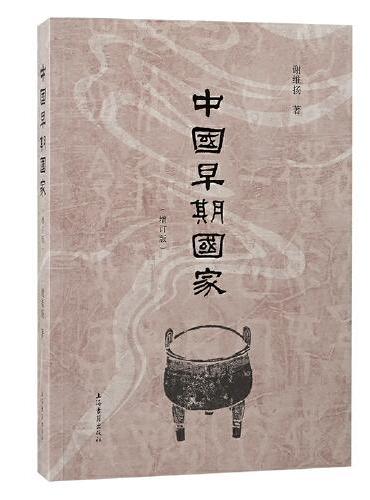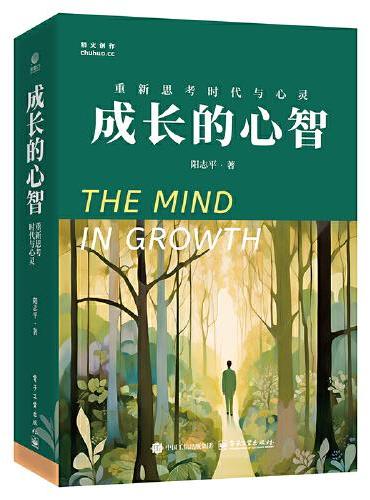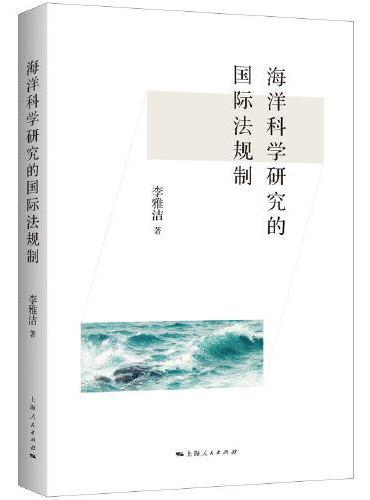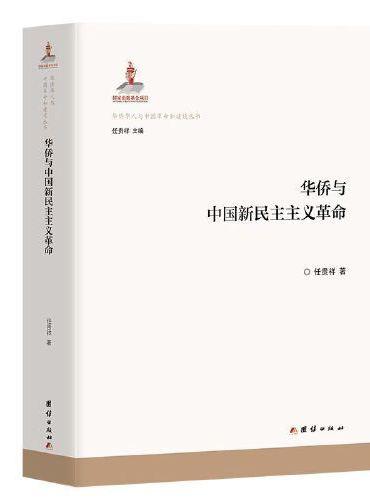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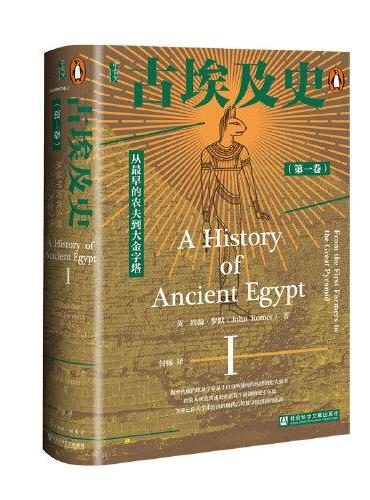
《
甲骨文丛书·古埃及史(第一卷):从最早的农夫到大金字塔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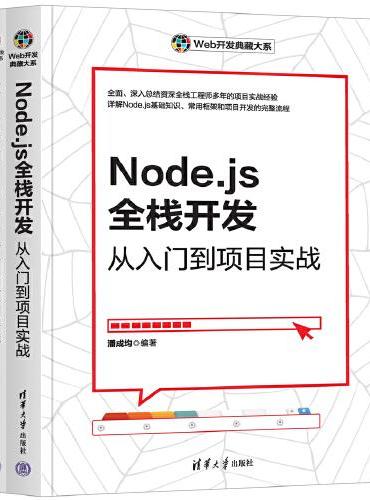
《
Node.js全栈开发从入门到项目实战+Vue.js 3+TypeScript从入门到项目实践(套装共2册)
》
售價:NT$
10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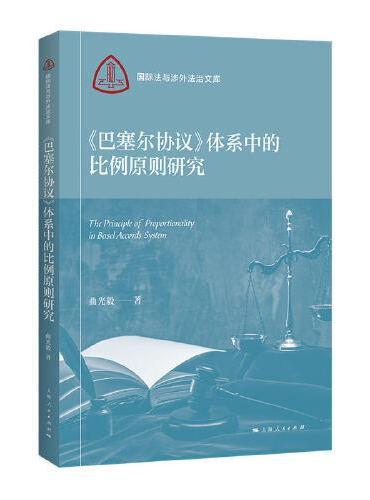
《
《巴塞尔协议》体系中的比例原则研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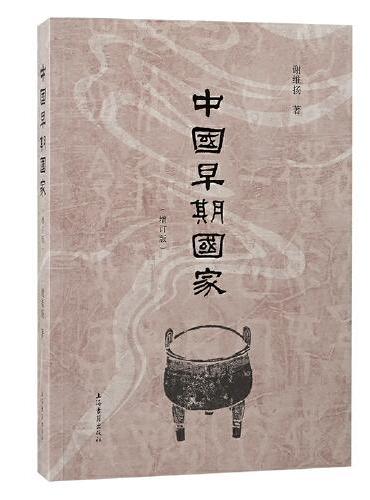
《
中国早期国家(增订版)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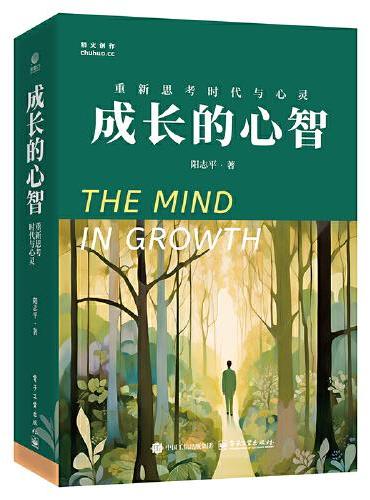
《
成长的心智——重新思考时代与心灵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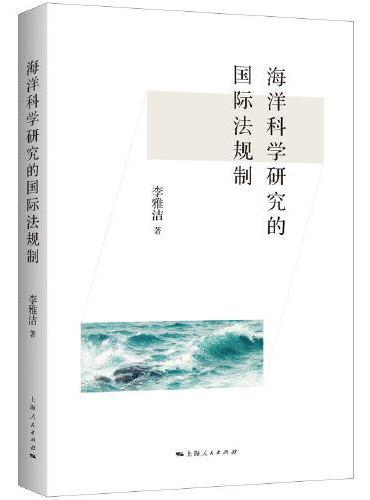
《
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法规制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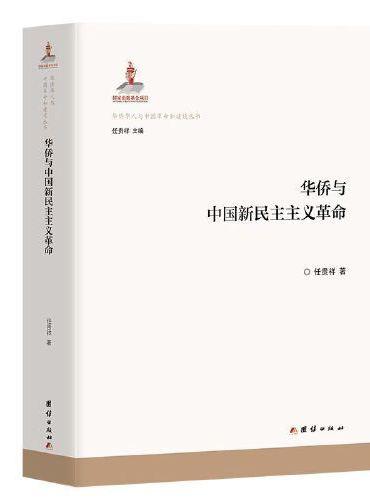
《
华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
售價:NT$
509.0

《
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修订版)
》
售價:NT$
704.0
|
| 編輯推薦: |
★托宾带你citywalk,漫步王尔德、叶芝、乔伊斯的都柏林街道
★三位充满魅力又制造混乱的父亲,以及他们大放溢彩的儿子——是父亲的缺席,铸造了儿子们的惊人成就?
★托宾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的笔触,让三位父亲形象跃然纸上
★张芸译文优美、熨帖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源于科尔姆?托宾受邀在埃默里大学做的讲座,讲稿也刊登在《伦敦书评》上。托宾透过三位男性??威廉?王尔德、约翰?巴特勒?叶芝和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生活和作品,以及他们与复杂的儿子们之间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关系,对爱尔兰文化、历史和文学进行了近距离而充满启发的阐释性研究。透过这三家父子的故事,托宾叙述了爱尔兰人对英国文化霸权的抵抗,现代爱尔兰文化认同的诞生,以及这些复杂而杰出的作者为文学世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
| 關於作者: |
|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自199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三度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他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2014年,当选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外籍荣誉院士。
|
| 目錄:
|
自 序 ……001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闻人:威廉·王尔德爵士 ……001
约翰·B.叶芝:西二十九街的浪子 ……065
两位男高音:詹姆斯·乔伊斯和他的父亲 ……131
致 谢 ……180
|
| 內容試閱:
|
自序
都柏林的有些街道让人觉得格外厚重,在这座城市生活得越久,零散的回忆和联想累积得越多,这份厚重感就变得越具层次。内心的想法随时间而渐趋复杂丰富,发生更多关联。有时,都柏林的这种氛围会因历史和书本而大大加剧。
不过,在忙碌的日子里,人们依旧可能走进位于奥康奈尔街的邮政总局,去寄封信或买张电视许可证,而起初压根儿没想到把这间邮局当作司令部的一九一六年起义,或是领导这场起义的麦克多纳和麦克布赖德、康诺利和皮尔斯,抑或叶芝的诗:
当皮尔斯把库丘林召唤到他身边,
什么人阔步走过邮政局?什么才能,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然后我转身,看见神话中的爱尔兰勇士库丘林的雕像,这座雕像出自奥利弗?谢泼德之手,竖立在这间邮局里,我记起塞缪尔?贝克特曾请他的朋友康?利文撒尔亲自“去都柏林邮政总局,测量从地面到库丘林屁股的高度”,因为在贝克特的小说《莫菲》里,尼瑞想要以头撞击库丘林铜像的屁股。这样一来,那颗无所事事或只琢磨着日常生活之弊病的头脑,可以因英雄、历史和疯子而伤伤神。
沿韦斯特兰路走到头,在皮尔斯街和隆巴德街相交的拐角有一间现已关闭的爱尔兰银行分行,我在那儿开有账户,所以以前经常走着去那儿。有些日子,我在途中路过位于基尔代尔街的国家图书馆,脑中会闪过利奥波德?布卢姆、《基尔肯尼人民报》、斯蒂芬?代达勒斯和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的两年间,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国家图书馆学习,因此我会沉思,是谁在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偷了我的黄色自行车,继而好奇,他们现在是不是还生产一种名叫“哈姆扎”的保加利亚葡萄酒,当年,马路对面的巴斯韦尔斯旅馆以很便宜的价格按杯供应这种酒。或者我会记起有一日,我和一个朋友站在图书馆的大门——就是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所写的大门——外抽烟,我的朋友望着爱尔兰国会下议院的停车场,形容当时一位声名显赫的政客布赖恩?勒尼汉的头发像是被用某种古老的工艺手法烫出的名副其实的波浪卷。抑或我会回想起,一九七八年我从西班牙归来,发现整个都柏林只有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咖啡机,在位于南安妮街的咖啡小馆,心中觉得不可思议。
接着我转入南莱茵斯特街,一九七四年发生爆炸案的地方,我试图回忆那起事件造成的确切死亡人数,纳闷那儿为什么没有纪念碑,然后又试图回忆那个星期五下午的向晚时分,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时,听到的爆炸声是怎样的。事实上,我没有听见什么;我听到更多的是事后的沉寂,留在我记忆中远更清晰的是那晚余下的时光,全城陷入狂乱、恐慌,我用夹杂了怀疑、惧怕和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视每一辆停放着的汽车,然后在位于巴戈特街的托纳酒吧喝酒喝到清晨,电台里播着大提琴的音乐,每当有新闻简报出来时,乐声停止,一片安静。
然后,当南莱茵斯特街变成林肯巷的拐角映入眼帘时,我隐约注意到马路对面那栋建筑山墙上的招牌,上面写着“芬尼旅馆”。说来奇怪,那个招牌并未褪色。詹姆斯?乔伊斯有两本书出自于此,或至少第二本的书名源于此。芬尼。芬尼根。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他正是在这儿邂逅了在这家旅馆工作的诺拉?巴娜科。两个年轻的陌生人四目相对,停下交谈,他们约定四天后再见,地点在威廉?王尔德爵士和他妻子斯佩兰扎曾经居住的宅第外,他们的儿子奥斯卡也是在那栋房子里被抚养长大,逝于乔伊斯和诺拉相识的四年前。
六月十四日,诺拉没有如约和乔伊斯见面,乔伊斯热切地写信给她,恳求再约一次:“我也许是瞎了。我盯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看了良久,终于确定那个人不是你。我沮丧万分地回家。我想再约个时间,但那么做恐怕不合你的意。但愿你能大发善心,与我定个约会——若你不曾忘记我的话。”那日晚些时候,他又写道:“我的耳边全是你的声音……我真希望感觉你的头靠在我的肩上。”六月十六日,他们第一次外出约会,他们的故事从这天开始,《尤利西斯》的时间也是设定在这一天。我想,幸好他们约会的日子不是在十一月中;那样的话,这本小说估计会薄很多。也幸好不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时候这一天酒吧通常关门。想到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酒吧关门、禁止卖酒,我脑中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没酒喝,真是渴死人了,堪比耶稣受难。尤其像临近终了时。从他肋部伤口流出的只有水了。
*
从诺拉工作的旅馆到王尔德的住所之间的那条街叫克莱尔街。塞缪尔?贝克特父亲的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就开在这条街六号,但这儿没有牌匾。一九三三年父亲死后,塞缪尔?贝克特的哥哥接管了事务所,而当时游手好闲的贝克特本人则住进那栋房子的阁楼。和每个游手好闲的人一样,他立下许多承诺;这些承诺既是对他自己,也是对他母亲立下的。他向自己保证,他要写作,他向他的母亲保证,他会教语言课。可他基本什么也没干。若有一块牌匾,或可贴切地写上:“此处是塞缪尔?贝克特无甚作为的地方。”
贝克特是和王尔德、叶芝一样的新教教徒中的天才人物,在他们那些拥有土地、权势和金钱的同仁接连离开爱尔兰或学会缄口不言之际,他们却决意要写下内心的想法。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最高的是格雷戈里夫人,她有一栋大宅和众佃户;其次是约翰?米林顿?辛格,和贝克特、王尔德一样,他有一小笔非劳动收入,加上一段记忆中辉煌的过去;再次是W.B.叶芝,他一辈子辛勤工作;同样还有清贫的布拉姆?斯托克和萧伯纳。最后是肖恩?奥凯西,他家境贫寒以致差点失明。他们全都受洗加入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而严格奉行新教的教会。但他们根本不信那套东西,除了可怜的格雷戈里夫人,她的确期盼有天堂的存在,以及奥凯西所持的共产主义,类似森严的教派——例如,他支持镇压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起义——也算一种宗教。不信任何教义、却让自己的同胞村民恰恰因为那套你所不信奉的宗教而想把你赶去英国,这种经验想必怪诞。
大概正因为如此,他们中有几人对故作姿态、曲解事情、培养他们雄辩的文采和致力于保持沉默产生兴趣。奥斯卡?王尔德喜欢找出一组公认的事实、然后将这些事实猛地反转,萧伯纳喜欢悖论,比他们晚离乡去国的伊丽莎白? 鲍恩更钟情爱尔兰海,原因想必正出于此。
我转入韦斯特兰路,经过斯威尼药房,然后继续朝银行走去。我以前的银行经理比米什先生现已退休,他在别人都不肯借钱给我时向我伸出过援手。塞缪尔?贝克特也有一个姓比米什的朋友,诺埃尔?比米什,战争期间,这位爱尔兰妇女与他住在法国的同一个村子,把她长长、实用的大裤衩与比她年轻的情人的带褶边的小内裤并排晾在一起。
好多东西消失不见;好多东西留在记忆里。那间银行不在了,那栋楼被用作他途,同样还有昔日的学院电影院,曾经是老音乐厅,乔伊斯在那儿唱过歌,他的短篇小说《母亲》以那儿为背景。一九七五年春,我和我的朋友格里?麦克纳马拉在那家电影院看了费里尼的《阿玛柯德》。那年头,爱尔兰电影审查局惯常用剪刀剪去影片中的色情场景,因此直至数年后,我才得以看到片中意大利男孩人人自慰的片段。这一情节在当时被认为不适合我们观看。
格里在二十余年前已去世,我的朋友安东尼?克罗宁两年多前也走了,正是他推荐我去那家银行,并提醒我,假如比米什先生贷款给我的话,不要再得寸进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与作家安妮?哈弗蒂——他们后来结了婚——从伦敦归来,在离此处几步之遥的莫根尼斯坊住过一段时间。他钟情于这儿的街道和巷弄,尤爱街角。他早期有一首诗,名叫《喜欢街角》,这首诗歌颂的场所
有角落收集灰尘和阳.光——
温暖的砖、温暖的平行交错的石块和玻璃碎片
整个下午的微小细节……
在此居住的那些年里,他写了一首情诗给安妮,名叫《幸福》,描绘他沿韦斯特兰路回家的情形。那首诗的开篇:
有时,沿韦斯特兰路一边走
一边想着安妮就在他前方
他感到幸福无.比,
他宛如一个行走的水罐
满得快要溢出来。
我思念他的怀疑主义、他的独立思考精神、他有多么风趣。一次,在看了一出甚是热闹、没什么情节也无幕间休息的戏——一场人人盛赞的演出——后,他对我说,这出戏给他的心灵蒙上了永久的阴影。“永久的?”我问他,“你确定?”他坚称他确信无疑,他敢打包票:那伤害是永久性的。接着他的眼中露出一丝慢慢浮现的笑意,庆祝至少我们现在已走出剧院,告别那从头至尾糟糕的编舞和在台上四处乱跑的演员。“噢,当我发现没有幕间休息时,”他呵呵一笑,“我便知道这伤害将是永久性的。那出戏给我的心灵蒙上了永久的阴影。”他假装绝望地摇摇头。
我在距此地往南两小时车程的一座小镇长大,那儿也是安东尼?克罗宁的家乡,我小时候,从罗斯莱尔出发的火车在韦斯特兰路和这座城市北面的亚眠街有停靠站。因此这条路是我走进都柏林的入口。我不记得当时我到底几岁,但应尚年幼,相信要过马路,必须先朝左看、再朝右看、然后再朝左看,却被我的父亲在正要横穿韦斯特兰路时告知,这条规则在都柏林并不适用,假如车子在很远处,那么即便是冲着你驶来,事实上也可以快速地穿过马路。
韦斯特兰路也是从都柏林南面到市中心上班的那些人的一个通勤停靠站。这些通勤者中有诗人托马斯?金塞拉,他在梅里恩街的财政部工作。他的诗《韦斯特兰路》收录在他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诗集《梦游者》里,这首诗刻画了从车站月台下来、走到下面街上的感觉:
我们沿坡道,穿过一阵阵打转的寒风和沙子
在昏暗中朝外面的亮光走去,我们的耳朵
被噪音堵住。
金塞拉注意到老式的内燃机火车从头顶喧嚷的高架桥上行过:
启动的火车头在头顶缓缓敲.打。
尘土飘落到桥下,我们微微弓身
夹着公文包和书,走入风中。
多年前,应该是一九七三年或一九七四年,我寄给金塞拉几首我写的诗,他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虽然那封信已经找不到,但我记得里面的几句话:“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或实际条件下选择你的生活方式,不妨留意一下美国的诗歌,借此了解其他人时下在做什么。”
近四十年后,有人要拍一部有关托马斯?金塞拉的电视纪录片,我与他同行,站在我家乡镇外一栋房子的大门口。他的妻子埃莉诺即出生在这栋房子里——我记得她的母亲魅力十足,很会玩惠斯特牌。金塞拉的诗《另一个九月》即以这栋房子为背景,这首诗收录在他一九五八年的同名诗集里,我们驻足凝望“苹果树,/成熟的梨树,黑莓,被风吹落的果实使土壤有了甜味”,一幅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生动刻画的图景。
我沿韦斯特兰路往北,中途调头,朝克莱尔街走去,空气中有某些东西变得凝重起来。这条路的很多地方显得肮脏昏暗,有些路段甚至破败不堪。这样一条市街,可能出现在英伦三岛各地——格拉斯哥、利物浦、纽卡斯尔、伦敦——任何一处民生凋敝的城区。街道两旁的建筑——大部分建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多为三层楼加一层地下室。右手边的那些楼现属三一学院所有。我知道乔伊斯的父亲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还有奥斯卡?王尔德的父母,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此地,王尔德夫妇比他早二十年。在大饥荒过后的年月里,都柏林这座首府城市辉煌不再,很难不去想象当时这儿必定十分冷清。根据一八〇〇年的联合法案,爱尔兰当时仍由英国下议院直接管辖,因而没有自己的议会。在贝尔法斯特逐渐成为一座工业城市之际,都柏林停滞不前,起码看起来是这样。
罗伊?福斯特在他的著作《现代爱尔兰》里写道:
到十九世纪末,缺乏工业基础是都柏林的无产阶级处境朝不保夕、一贫如洗的主要原因之一……市中心代表穷得一无所有的生活境遇,南面中产阶级聚居的开阔郊区与市中心密集的贫民窟之间日益严重的分化加剧了这一问题……
在《一六六〇年至一八六〇年的都柏林》一书的后记开头,作者莫里斯?克雷格写道:
要耐着性子描写十九世纪的爱尔兰是件难事。那一时期,缓慢的衰落中夹杂着间歇的发展……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一切混沌不明……虽然到处是群众运动,但它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时代,发生的种种事件明显是孤立的、明显没有共同目标……这座首府城市已开始透出轻微的忧郁气息:六十年后,政治地位的丧失开始引发一股明确无疑的乡土情绪……维多利亚王朝中期时都柏林的风貌,在我们眼里是个谜:我们知道,在那儿,有很多东西正蠢蠢欲动,表面则风平浪静,至少我们觉得如此。
不过,大卫?迪克森在他的著作《一座首府城市的形成》里说明,市内下层中产阶级的兴起源自好几个因素,但主要是由于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城市经济的结构变化,就业人员从制造业转向商务贸易,都柏林重新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批发交易中心……到一八八一年(詹姆斯?乔伊斯出生的前一年;叶芝全家从伦敦回到都柏林、居留六载的那一年),八分之一的男性劳动力从事与运输相关的工作。零售业的就业情况,不论规模大小,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八六二年,当局新开了一个牲口市场,迪克森写道,这个市场“据说是欧洲同类市场中最大的……结果是,在夏末和秋季时,每天有几百头养得肥肥的阉牛和羊被赶上运牲口的船送到这儿,成群结队地行过北环路。”迪克森还记录了市内文职人员的扩张:“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以十年为单位——教育界和警界,监狱、医院和福利机构,市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与维多利亚王朝时期的英国相比,爱尔兰行政上的高度集中化管理使都柏林受益无 穷。”
十九世纪期间,市内还大造教堂。迪克森提到,位于韦斯特兰路的圣安德鲁教堂——《尤利西斯》里,利奥波德?布卢姆逗留过的教堂——“可同时容纳三千两百名教徒站着参加活动”。从韦斯特兰路出发、向南行进的那条郊区火车线,托马斯?金塞拉进城搭乘的那一条,是乡间修筑的第一条铁路线。它比伦敦的首条郊区铁路早两年建成,于一八三四年临近岁末时开始定期运行。它把人们从罗伊?福斯特所称的“南面中产阶级聚居的开阔郊区”载往市中心。
当时,在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W.B.叶芝的父亲、詹姆斯?乔伊斯的父亲居于都柏林的年代,这座城市贫苦、破落。上述发展势头的出现不是靠工业或制造业;它以运输业和文员数量增长的形式出现。尽管郊区扩建,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都柏林给人的印象仍是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地方,整个城市的氛围在某种意义上杂乱无章,一个没有找到自我的地方,神秘而忧郁,保持原状,足以让詹姆斯?乔伊斯本人把这座城市视为“瘫痪中心”,让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他于一九〇五年离开都柏林后没再回来——在自己的书《看守我兄长的人》里哀叹这座城市不像别的地方,它缺乏传统意识,那种意识给许多小说家的作品提供了养分,让小说人物可以面对选择和机会,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寻求自己的命运。
斯坦尼斯劳斯写道:
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代达勒斯谈到爱尔兰作家发现自己在使用英语时处于某种劣势。对英国人来说,英语单词含义上可能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在我看来,恐怕只有像叶芝或我哥哥那样对语言的敏感程度达到最高检验标准的人才会推敲斟酌。我以为,爱尔兰人真正的劣势在于截然不同的天性。爱尔兰这个国家,虽然每一代人都经历过革命,但确切来讲,并无民族传统。在这个国家,一切动荡不安;在民众的心目中,事事反复无常。当爱尔兰的艺术家提笔写作时,他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从混乱中为自己创造一片属于他的精神天地。然而,虽然这一点对许多才华中上的作家来说是一大劣势,但事实证明,对像萧伯纳、叶芝或我哥哥那样天赋异禀的人来说是莫大的优势。
我在冬日稀薄的日光下沿韦斯特兰路而行,奇怪的是,若不细看,这条路可能让人觉得十分空荡荡,平凡普通极了。砖砌的房子,铁轨,一间酒吧,一家小超市,爱尔兰皇家音乐学院,一座现今大而无当的教堂、宛如一个两头通风的老箱子,还有几栋废弃的大楼,连归三一学院所有的建筑也显得阴沉寂寥。我们从克罗宁和金塞拉的诗中读到的韦斯特兰路的面貌,仿佛并非出自人们的共识,仅是某些孤家寡人在走路回家或上班途中的有感而发,这种情感与他人无关,他们身处的年月依旧是莫里斯?克雷格所称的“一个属于个人的时代”,用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话来说,一段尚“无民族传统”的年月,每个从事写作的人必须凭空创造一个世界。
【在线试读】:
詹姆斯?乔伊斯和他的父亲
理查德?艾尔曼在他的书《叶芝真人与假面》里引用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话:“谁不盼着自己的父亲死呢?”艾尔曼写 道:从乌拉尔山脉到多尼戈尔,这个话题反复出现,在屠格涅夫笔下、在塞缪尔?巴特勒笔下、在戈塞笔下。这个话题在爱尔兰尤为突出。乔治?摩尔在他的《一个青年的自白》里公然宣称,在他父亲死后,他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和解脱。辛格把一次未曾发生的弑父作为他《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主题;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描写斯蒂芬?代达勒斯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找寻另一个父亲……叶芝先是在一八八四年写的一部未发表的剧作里述及这个问题,后在一八九二年的一首诗《库丘林之死》里再度提起,一九〇三年将库丘林之死的故事改编成一出剧,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二七年分别翻译了两版《俄狄浦斯王》,并于去世前不久写了另一出含有弑父情节的剧《炼.狱》。
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作品里试图重塑他的父亲,重新想象他,唤起他丰满的形象,置身于他的生活圈子,但与此同时,从二十二岁起,除了几次在都柏林短暂逗留外,他确保自己不与父亲多见面。想到都柏林,他的心中赫然出现他父亲的身影,因此他的背井离乡不仅是要逃离他出生的这座城市,也是为了让都柏林和这个赋予他生命的男人可以变得虚而不实。
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开始做他自己、约翰?B.叶芝以背井离乡的方式象征性地弑杀了他的儿子一样,詹姆斯?乔伊斯也以让他的父亲在都柏林过着听天由命的生活而实现弑父,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他不仅试图打造他血统里未生成的良心,还设法理清他父亲的经历,让其获得重生,使已成幻影的东西变得真切实在。
那样一来,在只有儿子的这片天地中,父亲变成幽灵、影子和杜撰。他们活在记忆里和书信里,变得更加复杂,满足他们儿子作为艺术家的需求,不碍手碍脚。诚如斯蒂芬?代达勒斯在《尤利西斯》里讲的:“父亲……是一个不能不要的祸害。”讲到后来,他又声言:“父子关系也许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谁是儿子应该爱他,或是他应该爱儿子的父亲呢?”
不过,乔伊斯与他父亲的关系比王尔德的或叶芝的更为复杂。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在《看守我兄长的人》里沉吟他哥哥与他父母的关系:“每个体会过思考之苦的人都在精神上依附他父母中的某一方……假如此人是作家,这种亲和力深刻影响着他的艺术创造。”在他哥哥的例子上,他写道,依附的对象是他父亲。
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将文学和生活区分开:
在《尤利西斯》里,以我父亲为原型的赛门?代达勒斯是个酒鬼废物,在他身上,连想活得无忧无虑的愿望也成了模糊的回忆,但若说呈现在书中的他多方面的性格特点使这个人物成为鲜明醒目、滑稽好笑的文学形象,那大概仅是因为文学的宽容度远超过实际生活的宽容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