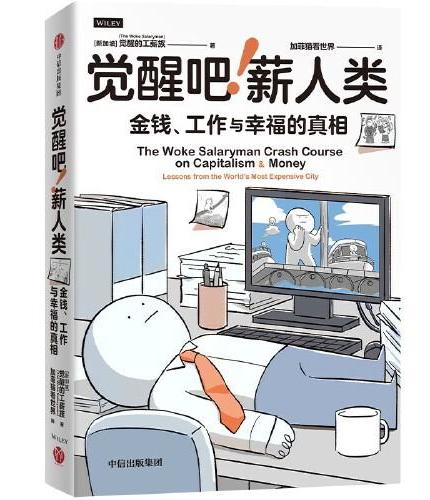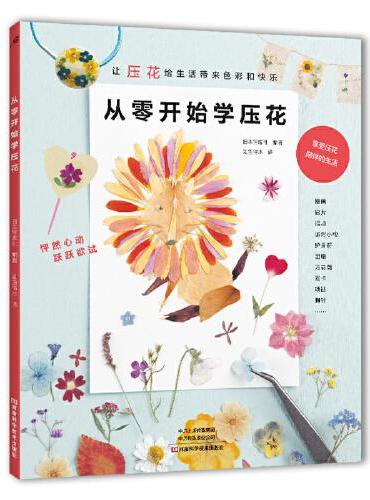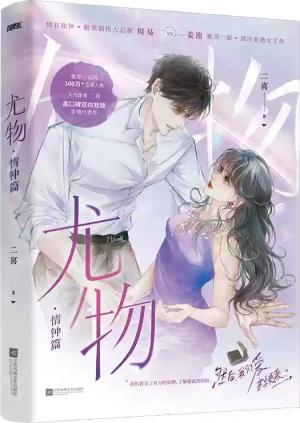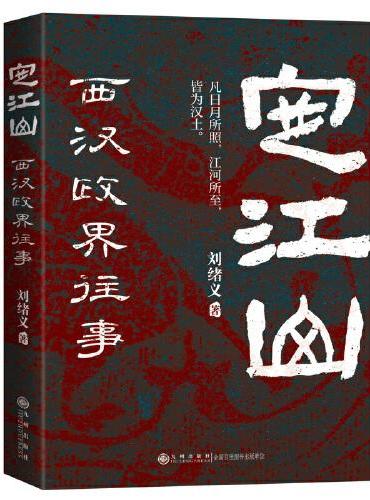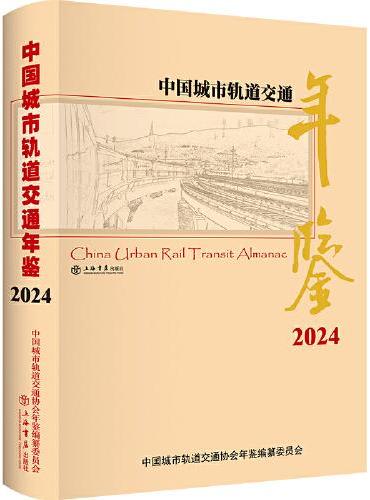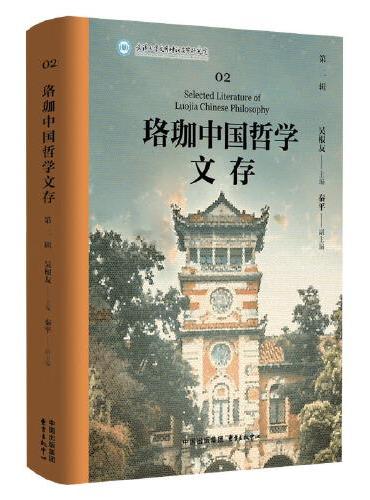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苏联出兵东北始末
》 售價:NT$
500.0
《
日本央行的光与影:央行与失去的三十年 [日]河浪武史
》 售價:NT$
301.0
《
觉醒吧!薪人类
》 售價:NT$
301.0
《
从零开始学压花
》 售價:NT$
301.0
《
尤物·情钟篇
》 售價:NT$
230.0
《
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
》 售價:NT$
347.0
《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鉴(2024)
》 售價:NT$
2448.0
《
珞珈中国哲学文存(第二辑)
》 售價:NT$
500.0
編輯推薦:
▲ 传奇性:纸片儿里的学术记忆,美术史的“考古学”
內容簡介:
人们不可把自己灵魂的居所只当作私自的占有品。人们要把它当作一个世间的奇
關於作者:
王 涵 文化学者,艺术鉴赏家,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国际教育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编著有《中国历代书院学记》《王逊年谱》《王逊文集》。
目錄
为了永不失忆(代序)/ 余辉
內容試閱
写在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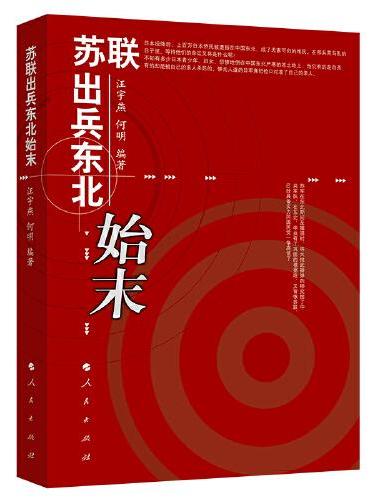
![日本央行的光与影:央行与失去的三十年 [日]河浪武史](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5/5/978711176228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