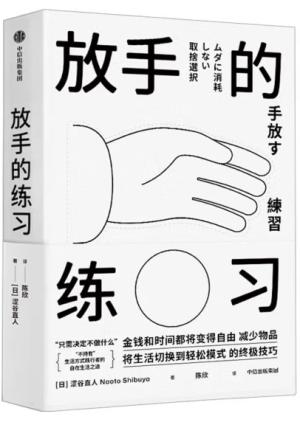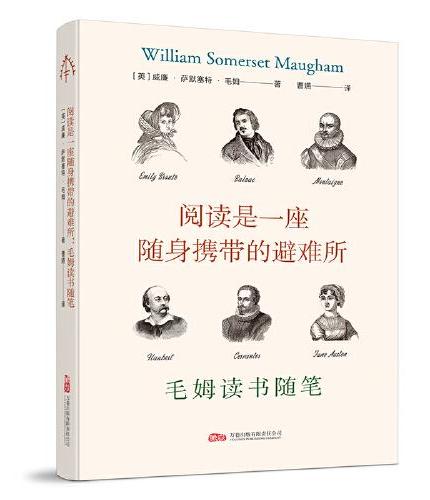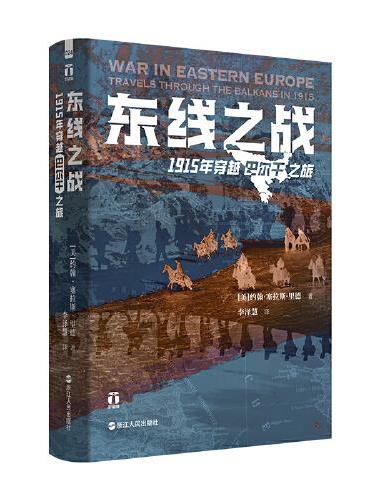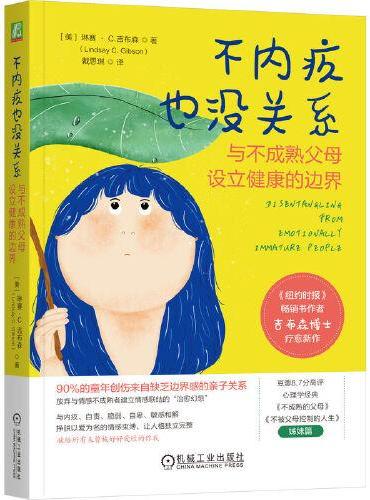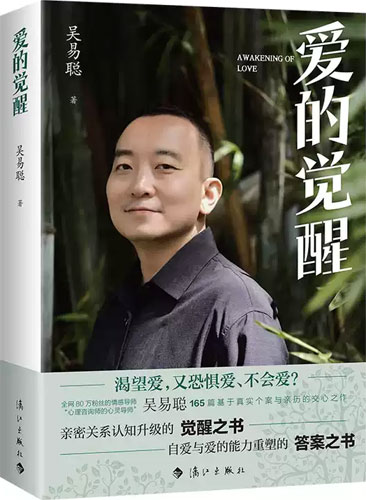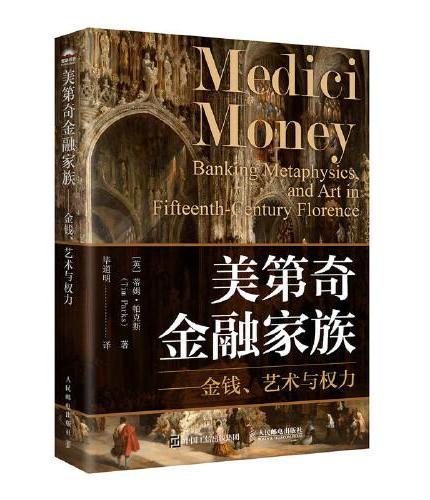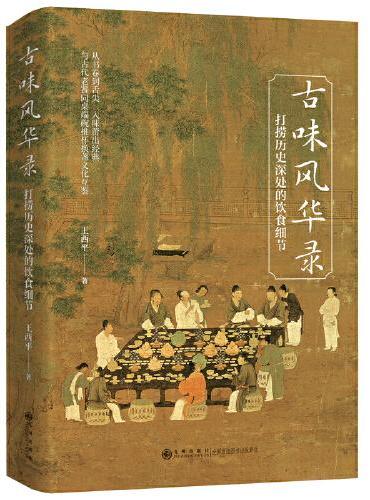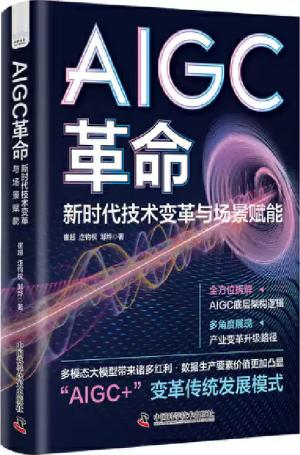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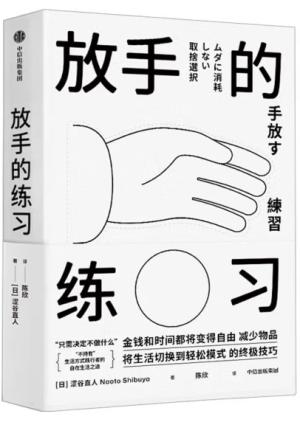
《
放手的练习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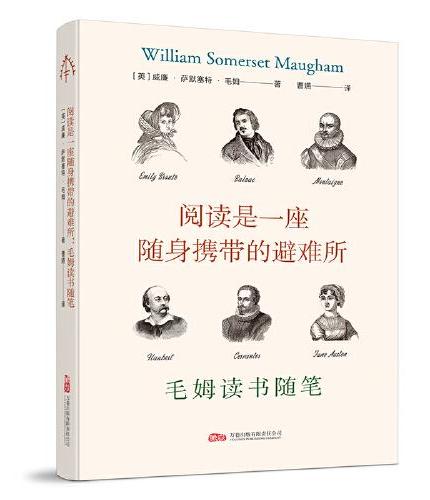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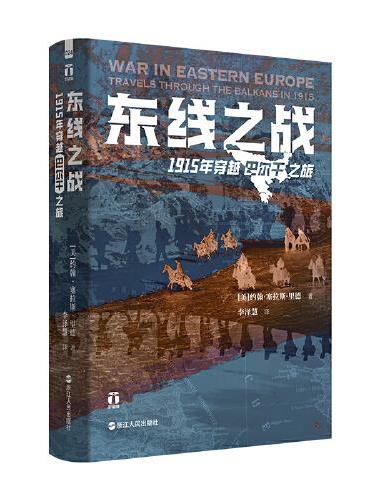
《
好望角系列·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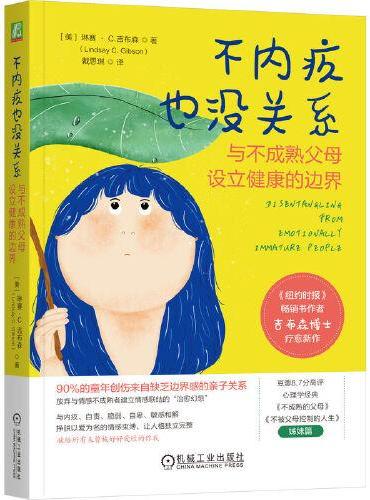
《
不内疚也没关系:与不成熟父母设立健康的边界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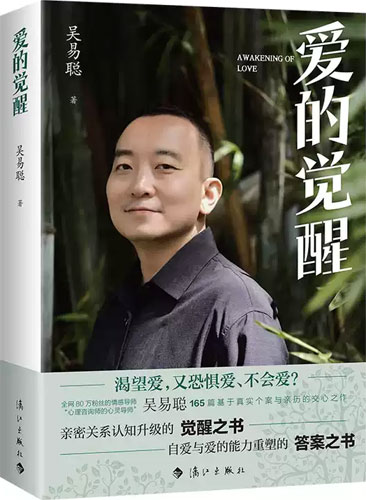
《
爱的觉醒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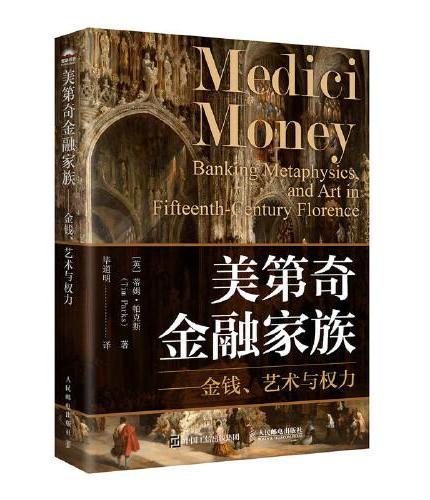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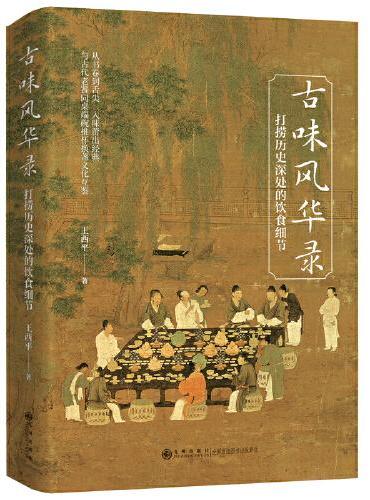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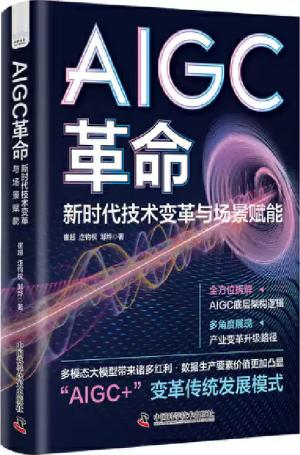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霍勒斯·麦考伊的笔锋冷酷而辛辣,小说披露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人们所面临的艰难困苦与狡诈人性。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可谓罗伯特的个人回忆录,形式和内容都近似本人的反刍式思考。
《孤注一掷》当属存在主义先锋作品。一场骇人听闻的舞蹈马拉松,编织起男女主的荒诞命运,为读者勾画出一个绝望与激情共舞的世界。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罗伯特梦想成为电影制片人,却屡屡受挫,濒临破产。走投无路之下,他孤注一掷,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给风靡当时的舞蹈马拉松。一百对各怀心思的参赛选手,一场出人意料的夺命舞会。这场绝望的豪赌似乎注定要以悲剧收场。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罗伯特又将何去何从?
|
| 關於作者: |
|
霍勒斯·麦考伊(1897—1955),美国作家,著有五部小说,《孤注一掷》在其离世后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
| 目錄:
|
第一章 枪杀 1
第二章 判决 3
第三章 初遇 4
第四章 共舞 12
第五章 意外 19
第六章 日落 28
第七章 悸动 38
第八章 苦战 48
第九章 暴乱 58
第十章 停赛 68
第十一章 淘汰 83
第十二章 婚礼 96
第十三章 枪响 109
|
| 內容試閱:
|
名家导读
/ 蒋向艳
蒋向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法国汉学。在《中国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文艺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程抱一的唐诗翻译和唐诗研究》《唐诗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英文专著Famous Chinese Figures and Their Stories;出版译著“鸡皮疙瘩”系列丛书《金字塔咒语:隐身魔镜》(英译中)、《亚瑟与迷你墨人》(法译中)、《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法译中)。
一
霍勒斯·麦考伊(1897-1955),美国小说家、剧作家。麦考伊一生中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短篇故事;与此同时,他还在好莱坞担任编剧,与尼古拉斯·雷、拉乌尔·沃尔什、威廉·迪亚特尔等知名导演共事,参与创作了约四十部西部犯罪题材的情景剧与电影。麦考伊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孤注一掷》(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于1935年出版,无疑是其最知名的作品。1946年,这部小说被译介到法国,伽利玛社出版了法文译本。1969年,由西德尼·波拉克执导的同名电影在美国上映,该电影获得了九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麦考伊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佩格拉姆,家境贫寒。十二岁时,他就上街售卖报纸;到了十六岁,他便辍学做工挣钱,从事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如维修工、推销员、出租车司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军入伍并在空军服役。一次飞行任务中,在同行飞行员身亡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驾驶轰炸机成功返航,因而被法国政府授予十字勋章。退伍后,他在达拉斯担任体育新闻记者。20世纪20年代末,他开始尝试写作,并在通俗杂志上发表了早期的短篇故事。此时,他的文笔简洁生动,颇有海明威之风。1929年,大萧条时期伊始,他便失去了工作。以谋生计,他先后做过季节工、服务员和保镖。1931年,他来到好莱坞,先参演了几个小角色,后来才有机会成为编剧。在经济大萧条的阴影笼罩下,好莱坞电影产业也未能幸免。进入大萧条时期,麦考伊的笔锋转而变得冷酷与辛辣。他的小说与剧本披露了大萧条时期人们所面临的艰难困苦与狡黠人性。当时,人人都崇拜“美国梦”,将好莱坞的价值观奉为圭臬,因而麦考伊的作品显得格格不入。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寿衣无口袋》(No Pockets in a Shroud)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法文版于1946年出版,收入伽利玛社第四期黑色小说系列。直到1948年,该书的修订版才在美国出版。1955年12月,他因突发心脏病在比弗利山庄去世,享年58岁。
彼时,麦考伊逝世,人们漠然置之。如同他的文学作品,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重视。不过,当作品译介到欧洲后,他在法国获得了一批拥趸。如今,麦考伊被视为与达希尔·哈米特、詹姆斯·M·凯恩比肩的作家。不仅如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洛杉矶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而麦考伊与凯恩当之无愧为开拓先锋。在《论洛杉矶文学创作先锋:詹姆斯·凯恩和霍勒斯·麦科伊》一文中,学者王琳认为,他们的作品与雷蒙德·钱德勒、纳塔纳尔·韦斯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巴德·舒尔伯格的代表作一同,在南加州地域文学的审美特征定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
《孤注一掷》的故事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麦考伊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海滩码头的舞蹈马拉松比赛,而故事主人公正是比赛中的一对搭档,罗伯特·西弗顿和歌洛莉娅·比蒂。男主人公罗伯特是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青年,怀揣着“导演梦”来到好莱坞。罗伯特天性淳朴,活脱脱一位乐观主义者。虽然在好莱坞屡屡碰壁,但他仍坚信自己能够梦想成真。和罗伯特相同,歌洛莉娅也有着“好莱坞梦”,只是当下只能担任临时演员勉强糊口。两人有着相似的背景,都出生在南方小镇,闯荡好莱坞,寻求名利,但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歌洛莉娅性格忧郁,内心充满痛苦与失望。歌洛莉娅的父亲在战争中牺牲,来到洛杉矶之前,自己在家乡遭受残酷对待,也让歌洛莉娅一度想过自尽。他俩刚见面,歌洛莉娅就向罗伯特吐露心声:
“……告诉你,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会从窗户跳下去,或者跑到电车前自杀什么的。”
“我觉得很奇怪,”她说,“每个人都无比关注活着,很少人在意死亡。为什么伟大科学家们总是一番折腾试图延长生命,而不是寻找愉快的方式结束生命?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想死却没胆——”
歌洛莉娅说服罗伯特成为她的搭档,一同参加娱乐码头上的舞蹈马拉松比赛,正是在那,两人遭遇了一场噩梦。这场马拉松比赛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参赛,但必须成双成对。比赛的奖金是一千美金,在当时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过,要拿到这奖金并不容易。比赛要求选手连续不停地在舞池里跳舞,每隔一小时五十分钟,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选手在这十分钟内吃饭、洗澡、睡觉。一旦选手停止跳舞,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只有坚持到最后的那对舞伴才能获得奖金。主办方免费为选手提供住宿和伙食,同时设置了观众席,观众可以为自己心仪的选手提供赞助。诚然,如此高强度的比赛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住,正如罗伯特回忆:“144对选手参加了舞蹈马拉松,61对在第一周就退出了。”
比赛发起人洛基并没有将选手们的身心健康放在心上,那一千元奖金或许也只是空头支票。食物很糟糕,所谓的免费住宿形同虚设。场上虽然有医生和教练,但是,选手昏迷后也只会被投到水箱中,惊醒后继续参加比赛。除此之外,洛基热衷于制造各种噱头,榨干所有选手。卢比与詹姆斯是夫妻,也是一对选手。卢比怀有身孕,即将临盆,参加如此剧烈的比赛却无人阻止;另一位选手马里奥被发现是越狱的杀人犯,被警察缉拿归案后,这一插曲却成了比赛的卖点;还有选手公然在比赛场地行凶,却没有被取消资格。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洛基和另一位推广人索克斯在比赛原有基础上推出了“德比大赛”(Derby races),让选手每晚绕椭圆跑道跑上十五分钟,并淘汰最后一名。不仅如此,他们还怂恿选手们虚假结婚,并在舞厅里办一场公共婚礼,制造更多热点,以吸引观众前来。此举效果显著,许多好莱坞的大腕慕名而来。对选手而言,这可能会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因为“很多制片人和导演都会观看这种舞蹈马拉松比赛,有可能把你挑出来,给你安排一个电影角色”。因而,面对残酷的赛制,大多数选手没有提出异议,仿佛只要有足够的观众,自己的未来便仍有希望。比赛摧残人的身心,选手们却日渐麻木不仁。比赛的结果唯有淘汰、崩溃或死亡,并没有真正的赢家。正如小说的结尾,酒吧里响起不明枪声,观众雷登太太不幸身亡,比赛被匆匆叫停,真正的问题却悬而未决。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切入,罗伯特作为“我”向读者叙述这场荒谬且剥肤锥髓的舞蹈马拉松比赛。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罗伯特的个人回忆录。小说的原标题“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是一句反义疑问句,实际上这是罗伯特在故事里的最后一句话,因而使得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近似罗伯特本人的反刍式思考。小说一开篇,我们便知道了罗伯特因谋杀歌洛莉娅而被判处死刑,这就足以吸引眼球。作者的行文方式别出心裁,法官宣判、舞蹈比赛与罗伯特本人的心理描绘交织在一起,三条时间线并行。然而,小说虽然以罗伯特的口吻叙事,但重点并不落在罗伯特身上。相反,小说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歌洛莉娅的画像。读者通读完小说,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歌洛莉娅是位愤世嫉俗者。实际上,歌洛莉娅在故事里展露出了不少温情时刻,比方说,她是唯一一个提醒卢比不要生下孩子的选手。固然,对于“死亡”这一问题,歌洛莉娅曾有多次表态,我们也不难看出她有着比较强烈的自杀倾向。甚至,她来洛杉矶之前便曾尝试服毒自杀。因而,若将歌洛莉娅的“死亡欲念”简单归咎于残酷的比赛机制或经济大萧条下的忧郁心态,便忽略了麦考伊的用心。
作者对歌洛莉娅的过去着墨不多,但这对理解歌洛莉娅的动机至关重要。不幸的家庭、糟糕的情史、屡屡碰壁的工作,这些都使她更加坚信生命不过是一连串的荒谬事件。她曾调侃自己:
“你这样嘲笑我不太好吧,”我对歌洛莉娅说,“我从没取笑过你。”
“你也不必,”她说,“我被厉害的人取笑过,上帝取笑了我……”
歌洛莉娅应该早已看清了人类生存状况的无奈,深知人世间的痛苦不能寄托于不存在的救世主。在她眼里,上帝或是救世主不过是死亡的“替代”。她选择参加舞蹈马拉松比赛,不过是孤注一掷,试图找寻生存下去的理由。她在比赛中自述:“我厌倦了活着,又恐惧死亡。”她邀请罗伯特作伴参加比赛时,读者还能够感受到她对比赛的期待,而随着比赛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插曲出现,歌洛莉娅也意识到这场比赛和她人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荒谬,正如她的评述:“你总要见不想见的人,总要跟讨厌的人假装友好,我很高兴我不做了”。在最后三章,读者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歌洛莉娅剧烈的态度转变。
“多希望是我们,”歌洛莉娅抬起头说,“我输掉比赛就好了——”(第十一章)
歌洛莉娅一整天都无精打采,我问了她一百遍在想什么,她总是回答“没事”。(第十二章)
反正这一天歌洛莉娅没有无精打采的理由,可她却比以往更没有精神。(第十二章)
“打中的要是我就好了——”歌洛莉娅压低声音说。(第十二章)
“你用不着那样看我,”她说,“我知道自己不好——”(第十三章)
“真希望我当时就死在达拉斯,”她说,“我一直认为医生救我的命只有一个原因——”(第十三章)
“我是个格格不入的人,给别人带不来任何好处……”(第十三章)
“不管怎样我都完了,世界很烂,我受不了了。我死了会更好,对其他人也是,我把周围一切都毁了……”(第十三章)
歌洛莉娅既然拥有了对人间事物的彻悟,那么她自然不会处心积虑,计较比赛结果,去寻求出头的机会,她也能够对生死问题保持最冷静的态度。比赛结束后,她寻求罗伯特的帮助,请求他用她口袋里的手枪杀死自己。“这是让我脱离痛苦的唯一办法。”她说道。在她看来,自杀早已不是一件荒谬的事情。罗伯特困在舞蹈比赛,期望有朝一日能借此出人头地,到头来不过是画饼充饥。相较之下,歌洛莉娅企图通过自杀来摆脱人间的苦难,反倒凸显出主动的反抗精神。麦考伊对两位主人公的刻画别出心裁。歌洛莉娅的名字“Gloria”,来自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意为“荣耀”;而罗伯特的名字“Robert”,源自日耳曼语“Hrodebert”,该词由“hruod”和“beraht”构成,分别意为“名声”和“闪耀的”。显而易见,这两个名字颇具讽刺意味。在经历一系列荒谬痛苦的事件后,歌洛莉娅的死确是对她名字最好的注解。
三
《孤注一掷》其主旨和描写手法和同时期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存在不少神似之处。
首先,这两部小说都成功刻画塑造了女性角色。《白象》里的年轻女孩吉格、《孤注一掷》里的歌洛莉亚。吉格和美国男友在西班牙某地的火车站候车,候车之际,两人在火车站旁边一家酒吧喝啤酒,一边交谈,看似随意的交谈其实涉及关系两人未来的重大事件,就是男人不停地劝吉格去把腹中的胎儿打掉。吉格在这番交谈中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就是男人并不在乎她,他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感受;吉格怀孕会破坏他想要过的那种自由自在、漫游享受的生活,而他唯一想让她去做的事,就是堕胎。年轻的吉格醒悟到这个事实,这反而让她变得坚强。小说最后,吉格向男人投去一个微笑,说:“我觉得好极了。”不管结果如何,吉格已经准备好面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一个年轻女孩,从天真稚嫩走向内心坚定的过程,在两人的对话中跃然纸上。这一成长历程与歌洛莉娅相似,歌洛莉亚的悲剧看似由罗伯特造成,而实际上赴死的动力是她自己,是她那愤世嫉俗的性格,和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绝望。如果说吉格从内心坚强起来体现了她的成长,歌洛莉亚以死对抗这个无望的社会则是更决绝的抗争,是真正觉醒了的极致表达。海明威和麦考伊都塑造了显然更加光辉的女性形象,更充盈、更多层次,也更丰富地展现了时代、社会中卑微个体隐微的努力、抗争乃至自我放弃。
其次,两部小说都非常典型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在《白象》中,小说题名本身“白象似的群山”就是最大的象征:“白象”在英语里有“大而无当”的寓意。养一头大象需消耗大量粮食,这个词便衍生其他意义,代表某种不想要的礼物,而这象征着吉格腹中的胎儿。“白象似的群山”则是怀了孕的吉格身体的象征。两人的对话也充满了象征意味。吉格温情地向男人说起远处的群山就像一群白象,男人却回答他从来没见过象;象征吉格对自己腹中孕育的生命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而男人对此无动于衷。故事发生的地点,火车站上即将到来的火车,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吉格是否堕胎的决定。火车只往一个方向开,象征着决定一旦做出,结果便不可逆。同时,数字“二”也是一个象征,小说里吉格和美国男人是两个人,点了两大杯啤酒、两杯饮料,服务员拿来了两个毡杯垫,男人把两只旅行包拿到站台上,火车只在站台停靠两分钟。“二”象征着吉格和男人的二人世界,但这两人世界可能会被正在孕育中的胎儿打破,男人愿意维持这原来的二人世界,吉格内心则起了波澜,因为她和胎儿也是二人世界。这原先的“二”因为胎儿的存在而有了微妙的变化。吉格和男人都口口声声说着“我们”,但这“我们”的所指却已不同。男人说,“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吉格却说,“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因为男人放弃了胎儿。
与《白象》相似,《孤注一掷》也大量运用象征。英文题名“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中的“马”在小说最后部分出现,罗伯特在歌洛莉亚要求他拿手枪打死她的时候,回忆起小时候在祖父农场里看到的场景:老母马内莉摔断了腿,祖父为了让内莉脱离痛苦,无奈开枪打死了它。书名里“被枪杀的马”就是女主人公歌洛莉亚的象征:一个深陷人生的淤泥、痛苦异常、生不如死的女性,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内莉摔断了腿,无法继续劳作,也已经年老,不能再生育,被“榨干”了有用价值的内莉只能面临被枪杀的命运;歌洛莉亚星途无望,也找不到理想的结婚对象,更不愿沦为男人偷情的对象,她作为“女人”似乎已毫无价值,因此早就有了自杀的倾向,只是自己下不了手,让罗伯特一枪了结是她必然的结局。
此外,《孤注一掷》里也有数字“二”的象征,尤其是舞蹈马拉松的参赛者必须是一男一女的二人组合;小说中多名人物都以二人成对的方式出现:罗伯特和歌洛莉亚、詹姆斯和卢比、马里奥和杰基、基德和玛蒂……但除了詹姆斯和卢比是一对夫妻,其他都是临时组合起来的“二人世界”;当马里奥和玛蒂因故退出比赛后,基德和杰基迅速组为新的一对;即使詹姆斯和卢比也是在一次舞蹈马拉松比赛中结合的,象征这看似和谐幸福的“二”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充满了讽刺意味。就像在《白象》里,男人要吉格堕胎,在《孤注一掷》里,卢比怀着身孕参加舞蹈马拉松,歌洛莉亚看不下去这非人道的场景,“多管闲事”地怂恿卢比堕胎。在绝对的悲观主义者歌洛莉亚看来,维持这虚幻缥缈的二人世界已经足够艰难,何必再带一个生命来这世界受罪?当最后歌洛莉亚让罗伯特拿枪打死自己,也是以这种决绝的方式宣告了这虚假的“二”的破产。
其三,两部小说都运用了反讽。《白象》里,一个美国男人在西班牙某火车站旁的酒吧,坐在露天的桌子边,公然劝说他的年轻女友堕胎,这是一个极大的反讽,因为在西班牙这个有着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堕胎是非法的;而男人可能以为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可以抛开道德约束和女友来谈论这个话题。《孤注一掷》里,罗伯特和歌洛莉亚是舞蹈马拉松的舞伴,虽然歌洛莉亚个性有些古怪,但罗伯特却能理解她,总是安慰她“我了解你的感受”“我明白你的意思”,认为自己是她最好的朋友、唯一的朋友,但最后因帮助歌洛莉亚自杀而被法院起诉,被判定为一级谋杀罪并执以死刑。这对好友舞伴共同走向死亡的结局,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四
读者应该也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位文学人物,那便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两者身上体现的“异己感”,以及他们面对社会而产生的“陌生感”,均有共通之处。事实上,麦考伊的作品与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书在1935年出版,就引起了法国存在主义者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一批文学大家,如加缪、萨特等,他们各自的代表作《恶心》(La Nausée)与《局外人》(L’étranger)分别在1938年和1942年出版。法国评论界将麦考伊视为存在主义的开拓者,而该书自然也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奠基之作。麦考伊一度是法国被人讨论最多的美国作家。鉴于这部小说的出版时间,很多读者会不自觉地将其与经济大萧条背景相勾连,认为作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讽刺,对好莱坞“梦工厂”的讽刺,但这样的解读忽视了作品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内核。
毋庸置疑,小说中的舞蹈马拉松赛有其寓意。歌洛莉娅曾将整个舞蹈比赛比喻成旋转木马。对参赛者来说,比赛犹如参加一场永不停歇的旋转木马,身体在永恒的摆动中,奔向的却是永恒的重复,没有未来的未来。这舞蹈马拉松象征着灰色绝望、没有出路的人生。人,无论谁,都处于这永劫不复的旋转木马式的、陀螺般的、无止境无目的,却不得不非如此不可的荒谬而尴尬的境遇之中。在罗伯特的叙事视角中,我们几乎没什么机会看到除了舞厅以外的场景。所有选手都被困在码头舞厅中,无休止地进行舞蹈比赛,这一叙事场景可以构成对人生的隐喻。舞蹈马拉松赛最后没有了赢家,正如人生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胜者,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愿望之间必然存在断裂。在舞厅里比赛时,所有人都不知道外边的天气,仿佛里面是无尽的黑暗。而罗伯特曾在短暂的休息时间偷偷跑去欣赏日落,“日落”这一意象则与罗伯特的导演梦对应起来,两者都无比美好,最终烟消云散。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罗伯特言语里体现出的乐观心态。但到了最后一章,作者的笔锋一转,罗伯特也逐渐意识到这一切的荒谬。他感受到了和歌洛莉娅相同的精神倦怠,正如他并没有拒绝歌洛莉娅的请求,反而对其表示认同,“这是让她脱离痛苦的唯一办法”。而在这部分,如同电影里的闪回镜头,罗伯特回想起了少年时在阿肯色州农场里的经历。老马内莉受伤后,祖父用枪了结了老马的生命。这一画面与罗伯特枪击歌洛莉娅相对应,祖父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或许也是罗伯特当下的心理写照。
最后一幕,面对警察的拷问,罗伯特只是淡淡地回答道:“人们也会射杀老马的,对吧?”如果说歌洛莉娅早就识破社会的悖谬,那么荒诞主义思想在罗伯特身上觉醒则发生在他枪杀歌洛莉娅之后。小说开篇,他面对法庭的审判时,内心告诉自己,“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唯一的朋友。她怎么可能会无依无靠呢?”此时,罗伯特逐渐接受了歌洛莉娅对待人生的否定态度。因此,他也拒绝为自己辩护,“只能站在那里,望着法官,摇着头,根本无力反驳”;面对刑罚,他和默尔索一样,冷漠且无动于衷:
现在我感觉莫名其妙,百思不解。这不是谋杀,我只是想帮忙,结果却害死了自己。他们要处决我,我非常清楚法官会怎么说。从他的神情中我可以看出,他很乐意宣布这个处决;而从我背后人们的反应也可以感觉到,听到法官的判决他们会欣喜若狂。
最后,罗伯特和歌洛莉娅都沦为虚无主义的皈依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考伊的《孤注一掷》更容易和二战后法国兴起的存在主义哲学、荒诞剧等思想和文学发生共振,在法国读者中引起更多共鸣。贝克特《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 1952)里关于人生荒诞、戈多永远不会到来,象征救赎的希望始终不会抵达等理念,麦考伊通过这场骇人听闻的舞蹈马拉松,也通过歌洛莉亚的自绝行为表达得淋漓尽致。
麦考伊的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在有限篇幅里,作者勾画出了两位典型的存在主义人物形象,小说也超越了对单纯的历史现场简单概括,具有更广阔的意义。麦考伊用最短的篇幅,达到了最大的效果。书中除了对“荒诞”“疏离”等主题的表现,作者的写作手法也颇具“零度写作”的雏形。《孤注一掷》可谓一部存在主义先锋作品,如今首次在国内译介,实在不容错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