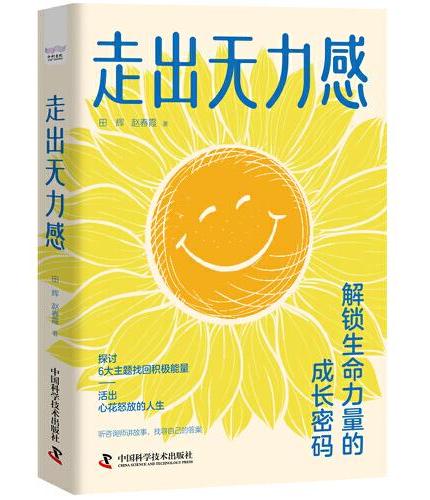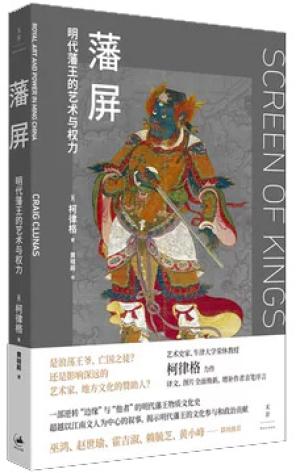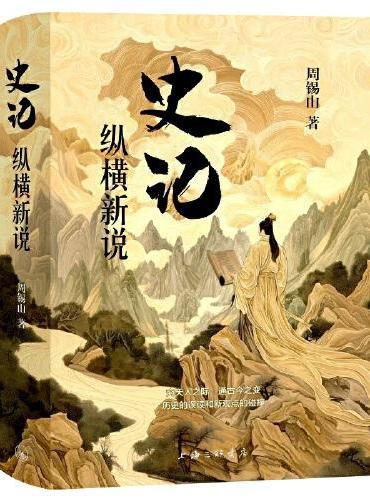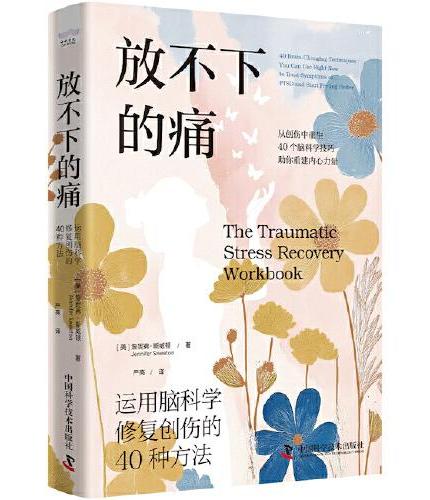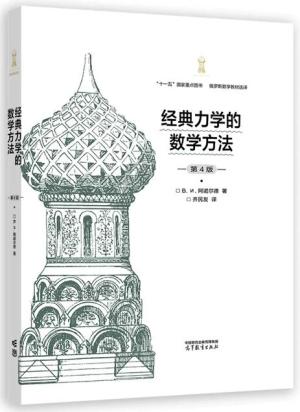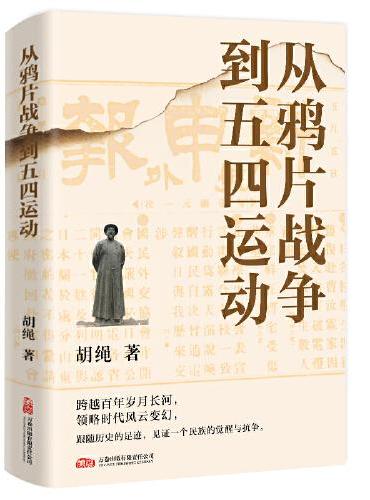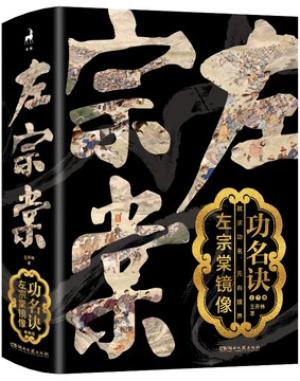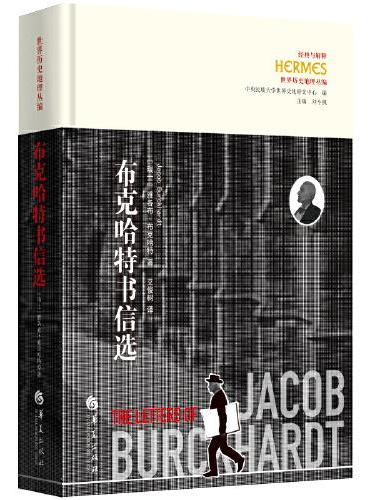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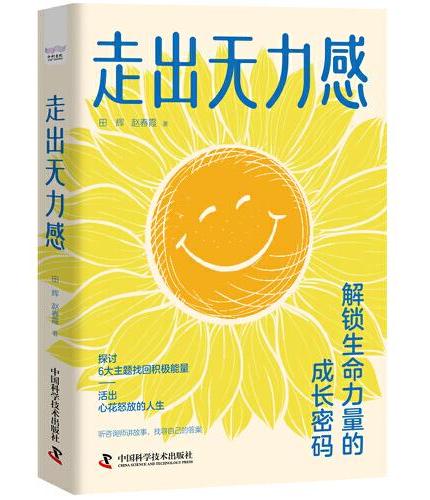
《
走出无力感 : 解锁生命力量的成长密码(跟随心理咨询师找回积极能量!)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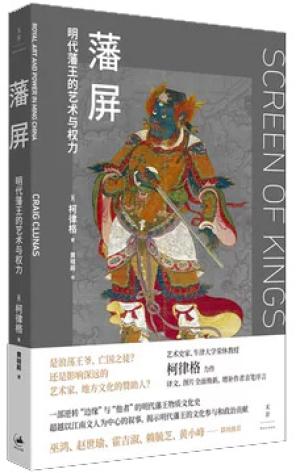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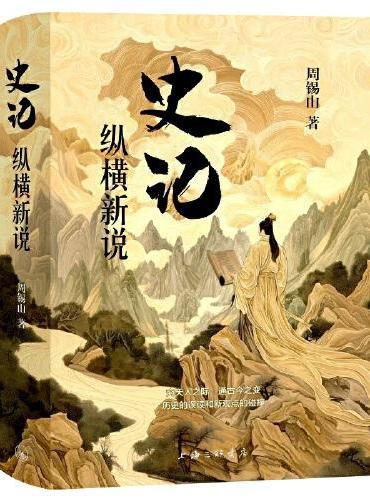
《
《史记》纵横新说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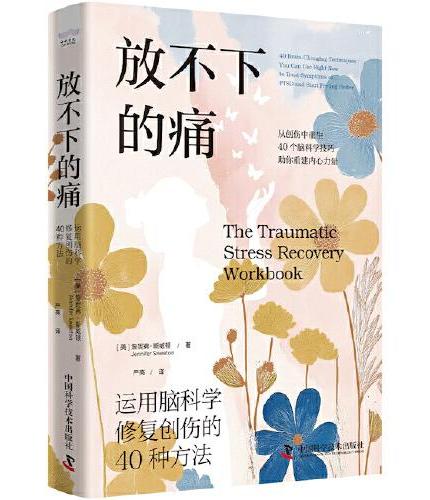
《
放不下的痛:运用脑科学修复创伤的40种方法(神经科学专家带你深入了解创伤背后的脑机制,开启全面康复之旅!)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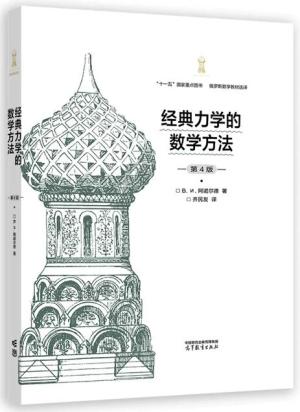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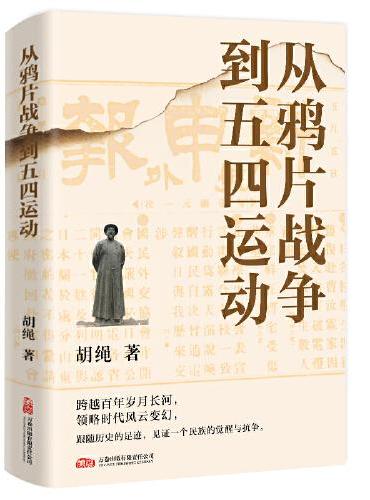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跟随历史的足迹 见证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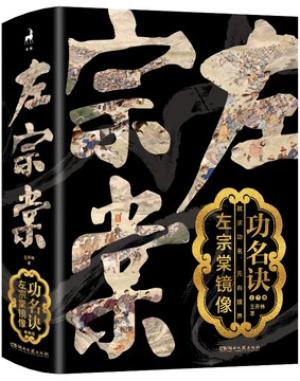
《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
》
售價:NT$
9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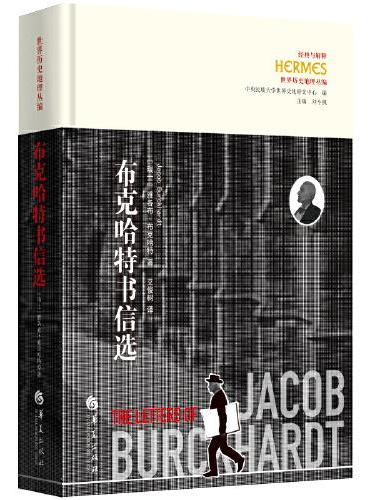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 編輯推薦: |
陶渊明之隐的性质是儒家还是道家,是逸民还是隐者的问题,历来备受关注,其中的分判关节,在于确定他是否承认君臣一伦。作者在细究《形影神》《饮酒》《桃花源记并诗》三组诗文及历代注解后,依据陶氏自然之说上的神不灭论、感应论、委运顺化观,历史之说上的大道沦丧-存亡续绝论,及其生平行状,社会之说上的桃源虚实论、贤者避世论、士人弘道论,等等,以“亦儒亦道”“亦逸亦隐”定位诗人的归隐形态,而更加贴近他的精神本色。
本书以哲学尤其是儒门的出处之道切入陶学研究的深层问题,勾连经典文本、义理考据、学说脉络、历史现实与人物行状,深察渊明诗文与传世评释;作者功力深厚而思路清晰,问题独特而阐述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在现代视野下激活与理解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与政治伦理的佳作。
|
| 內容簡介: |
出世与入世既是面对现实政治的选择,也是面向内心价值的抉择;不同的历史环境、文化身份和各异的出处态度交织,共同塑造了古代文人的传世形象与精神气质。晋人陶渊明以诗文与不仕闻名,影响贯穿古今;而陶氏之隐属儒家还是道家,为逸民还是隐者的问题,历来备受关注。
本书围绕《形影神》《饮酒》《桃花源记并诗》三组诗文及历代诠注,揭开陶渊明思绪流连的独特地带与深邃旨趣,及其由儒而隐的心路历程。作者从哲学的角度将他的精神世界关联于原始儒学的核心义理,又将其人格行状放入所处的生存处境与政治现实,从而把陶渊明思想定位在“隐逸之间”:以儒者为底色,以隐者为归宿。
|
| 關於作者: |
唐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政治哲学与中国哲学。
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任教清华大学哲学系至今。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及学术译作若干篇,主编《公共儒学》。
|
| 目錄:
|
引言 逸民还是隐者——陶渊明的思想定位问题
渴望不朽与纵浪大化——从《形影神》组诗看陶渊明的自然观念
形、影之苦与陈寅恪的新自然说
陶渊明的神不灭论
陶渊明的反报应论
《神释》正解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从《饮酒》组诗看陶渊明的历史哲学
写作背景与文本结构
说避世之缘由
明归隐之志趣
申不就之主意
陈饮酒之隐情
表弘道之初心
虽有父子无君臣——从《桃花源记并诗》看陶渊明的社会理想
仙与隐
隐与儒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的谋篇布局
余论 儒教隐逸主义的另一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逸民还是隐者
陶渊明的思想定位问题
*本文系《隐逸之间》引言,注释从略
人的思想离不开其生活处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处境自有其复杂性与艰难性。按照目前多数学者的认知,陶渊明既在桓玄手下干过事,也在刘裕手下干过事;而桓玄与刘裕,先后都成了东晋的篡臣。可以想见,对于注重名节的陶渊明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降志辱身而保全性命,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陶渊明,发现陶渊明躺在床上,因贫困挨饿已多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遗以粱肉,麾而去之。
说实话,这则对话看得我心惊肉跳,我甚至试图想象陶渊明回答檀道济时的表情。陶渊明肯定会认为用“天下无道”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非常恰当,而这当然也是他决意归隐的原因所在;不过,当面对由新朝任命的地方官将篡夺而立的新朝称为“文明之世”,他是无法与其理论一番的。对于地方官给他的馈赠,他表面上接受,等其走后又“麾而去之”,这正是其态度的鲜明表达。
陶渊明的政治处境如此,他的文化处境又如何呢?魏晋时期玄学大盛,其主题或可概括为“课自然以责名教”。而名教与自然之争到了西晋一统时期,也逐渐倾向于像裴 、郭象那样的调和立场。到了东晋,尤其是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一个新的变化是佛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史之学、玄学与佛学,构成陶渊明生活世界中三种最重要的思潮。就这三种思潮对于陶渊明思想的影响而言,我们应当有如下基本认识。首先,陶渊明是在经史之学的浸润中长大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是陶渊明最清楚不过的自我道白。陶集引用《论语》的次数仅少于《庄子》,这是陶渊明“游好在六经”的显著表现。而《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事迹、思想观念不时地出现在陶渊明的笔下,这也表明陶渊明深深浸润于正统经史之学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中。其次,陶渊明对《庄子》相当熟稔,其思想观念深受《庄子》的影响。至于魏晋时期的玄学讨论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陶渊明,我们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无法获得清晰的判断,但不难看到的是,在玄学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时代性的思想主题同样也出现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最后,陶渊明与慧远、刘遗民、周续之、颜延之等人的交往足以说明佛学在陶渊明的生活世界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且,陶渊明受佛学影响极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慧远等人从佛学立场上开展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思想主题也是陶渊明感兴趣或必须面对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晋、宋易代之际复杂而艰难的政治处境,再加上儒、道、佛三教思想交锋、交流的文化处境,使得陶渊明在直面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时产生的思想也呈现出复杂的面向。真德秀说:
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自老、庄;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
这是以陶渊明自始至终为名教中人,且理由不限于“耻事二姓”一事。以渊明之旨出自老、庄,这当然是更为常见的观点,毕竟归隐不肯出仕的行为往往被关联于道家。过去也有人说渊明“早会禅”,乃至誉渊明为“第一达摩”,这当然是完全不顾历史而进行的纯粹思想性的解读,与陶渊明自己的心路历程完全无涉。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该如何定位,让我们先来看朱子的两处说法:
陶渊明,古之逸民。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因言:“《国史补》称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阁而坐。’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当爱之。”问:“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做不着处便倒塌了底。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
朱子一处说他是逸民,一处说他是隐者,其实若以《论语》为依据,则逸民与隐者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语·微子》记载了楚狂接舆、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等几位隐者的事迹,然后说到逸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此章在理解上有难点,此处我们仅就“逸民”概念做一说明。对于孔子说自己“无可无不可”,朱子引用孟子说孔子的话来解释:“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然后引用谢良佐的话来说明七人何以为逸民:“七
人隐遁不污则同,其立心造行则异。伯夷、叔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盖已遁世离群矣,下圣人一等,此其最高与!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伦,行能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
而不污也,权而适宜也,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是以均谓之逸民。”其中“乱大伦”一语,正来自《论语·微子》中记载的子路对隐者的批评: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由此可见,逸民与隐者的区别在于逸民不废君臣之伦而隐者相反。于是问题就是,既然逸民与隐者一样隐居不仕,那么,何以言其不废君臣之伦?说逸民不废君臣之伦,意思是说,就人类实现其本性的积极生活而言,逸民承认君臣一伦的重要性,认为君臣一伦与父子一伦皆属于自然,皆出于人的本性。而隐者则否认君臣一伦在人类实现其本性的积极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父子一伦属于自然,出于人的本性,君臣一伦则出于人为,不属于自然。对君臣一伦的肯认与否弃正是儒家与道家在人伦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从基本立场上说,逸民属儒家,隐者属道家,这是区别逸民与隐者的要点所在。由此亦可推知,逸民与隐者虽然在行为上都表现为隐居不仕,但其理由并不相同。逸民选择逃逸于政治之外,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在一个乱世中保持其品节,或者有激于世无明君而逃逸,或者眷念于旧君之谊而逃逸,其隐含的信念却是承认君臣一伦乃人之大伦,是有君主义。而隐者却认为君臣一伦的存在或相应的人为主义正是世道浇漓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选择隐居,其隐含的主张其实是无君主义。
那么,陶渊明到底是逸民还是隐者?此一问题的提出显然与过去学术界讨论陶渊明到底是儒家还是道家的问题类似,只不过我们这里对问题的提法更切近陶渊明自己的精神生活。直观地看,无论是像伯夷、叔齐、柳下惠等孔子所说的逸民,还是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论语》中记载的隐者,以及孔子之后的历史时段中出现的一些隐逸之士,都多次出现在陶渊明的笔下,且对于这两类在基本立场上并不一致的高洁之士,陶渊明都给予了由衷的赞扬。或者,从陶渊明引用最多的两部著作是《庄子》与《论语》这一点上,似乎也能看出,他的思想里既有儒家的面向,又有道家的面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需要避免标签化的解读,因为实际的情况正是,陶渊明内在于自身的政治与文化处境,对他所遭遇的一些人生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探索。虽然他并未写作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种哲学性的议论文,而是通过诗歌和散文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既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的那些主流的哲学性讨论不了解,也不意味着他通过自己的强力探索所达到的思想境界不深刻。可以说,在玄学早已开辟的儒、道互质与会通的历史背景中,又直面佛学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陶渊明忠实于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旨趣的深邃思想。
本书从《陶渊明集》中精心挑选了《形影神》《饮酒》《桃花源记并诗》这三篇作品,从哲学的进路展开深入、细致的解读,并将这三篇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关联于陶渊明的其他作品,充分揭示陶渊明精神世界中的自然、历史与社会。《形影神》组诗的主题是自然,这可以从这首诗简短的序言中明显地看到:面对形、影各自所遭遇的苦,神试图通过辨析何谓自然以开释二者。而贯穿于《饮酒》组诗的一个核心看法是“道丧向千载”,这是陶渊明历史哲学的一个精炼表达,对于我们理解陶渊明的归隐行动与思想定位至关重要。至于《桃花源记并诗》,王安石一句“虽有父子无君臣”,准确地道出了桃花源里的社会秩序,而这正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正是从对这三篇作品的深度解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陶渊明由儒而隐的心路历程;对陶渊明所流连的思想地带和其独特的思想旨趣,我们也能够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看法。而且,将陶渊明具有独特旨趣的深邃思想关联于原始儒学的核心义理,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儒教隐逸主义的另一种可能性。
*节选自《虽有父子无君臣》篇,注释从略
陶渊明自唐代始得到较普遍重视。桃花源的意象,亦成为唐人诗画中的重要题材。唐人对桃花源的理解,以神仙说为主。王维《桃源行》一诗,中有“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之句,末有“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之句,是以桃花源为避地成仙者所居之地。刘禹锡《桃源行》一诗,中有“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之句,末有“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水流山重重”之句,亦是以桃花源为仙家之地。韩愈有《桃源图》一诗,首句是“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末句是“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或以为韩愈此诗虽直辟神仙实有之论,但亦是以神仙所居之地理解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宋人王龟龄有《和桃源图诗并序》,为此专做辨正。《和桃源图诗序》云:“世有图画桃源者,皆以为仙也,故退之《桃源图》诗诋其说为妄。及观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乃谓先世避秦至此,则知渔人所遇乃其子孙,非始入山者,真能长生不死,与刘阮天台之事异焉。东坡“和陶诗”,尝序而辨之矣。故余按陶记以和韩诗,聊正世俗之谬云。”王龟龄的意思是说,韩愈一诗所诋排的,并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是后来图画中的桃花源,故其《和桃源图诗》中有“后来图画了非真,作记渊明乃晋人”之句。这个辨正显然与韩愈排佛老的思想和行为是符合的。
宋人对陶渊明推崇更甚,尤以苏轼、朱熹为最。在对桃花源的理解上,如果说韩愈开启了对神仙说的批评,那么,宋人大多承续韩愈的批评而明确提出了避世长子孙的隐居说。王安石《桃源行》一诗云: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此诗对桃花源故事的重述紧扣《桃花源记》,其要旨在于以桃花源中人为秦时避乱来此之人的子孙后代,并以“虽有父子无君臣”点出桃花源中社会秩序之特点。苏轼《和桃花源诗》有“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与“桃源信不远,藜杖可小憩”之句,更在《和桃花源诗序》中明确以《桃花源记》为纪实之作而反对神仙说,认为桃花源如南阳菊水、青城山老人村之类乃实有其地,并指出天地之间类似于桃花源者很多: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亦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思天壤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唐人的神仙说与宋人的隐居说都承认渔人所见桃花源中人为秦时避乱来此之人的子孙后代,这是这两种理解的一致处,其文本根据在《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之句和《桃花源诗》中“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之句。两种理解的分歧点,则在是否认为渔人所见桃花源中人为仙。很明显,苏轼的申论就是直接针对神仙说提出的,析而言之,要点有三:其一,渔人所见桃花源中人乃避秦之人的子孙,并非避秦之人或其子孙成仙者;其二,《桃花源记》中“杀鸡作食”之语,可以佐证渔人所见桃花源中人并非神仙;其三,陶渊明所记桃花源实有其地,且这样的地方在世间有很多。其中前两点比较清楚,第三点则仍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理解第三点的关键在于,既然苏轼认为“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那么,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只要说明桃花源实有其地,就意味着成功地反驳了神仙说。需要注意的是,不唯隐居说与神仙说本身不一定矛盾,实有说与神仙说本身也不一定矛盾。倘若一个道教信徒,认为成仙并非子虚乌有之事,而是一条走向理想生活的真实道路,那么,以凡人成仙为实有之事,以仙人所居为实有之地,就是很合适的。从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苏轼的申论更像是被韩愈直接激发出来的。韩愈在上引诗中对于神仙之有无提出了质疑,进而断言桃源之说为荒唐,在诗末再次质疑说“世俗宁知伪与真”。苏轼显然在基本立场上与韩愈一致,即以神仙为子虚乌有之事。苏轼想要进一步明确辨正的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并非神仙所居之地,于是,苏轼就以桃花源实有其地立论,来反驳流行的神仙说。苏轼的申论其实可以概括为:神仙是子虚乌有之事,但桃花源却是实有其地的,而且类似的地方世间有很多。
王安石、苏轼反对神仙说而提出的隐居说,得到后来多数论者的认可。如宋人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云:“渊明《桃花源记》,初无仙语,盖缘《诗》中有‘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后人不审,遂多以为仙。……皆求之过也。惟王荆公诗与东坡《和桃源诗》所言最为得实,可以破千载之后如惑矣。”明人蒋冕辑《琼台诗话》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皆惑于神仙之说,唯王介甫指为避秦之人,为得渊明《桃源记》意。先生尝作《桃源行》,则又以为楚人避秦来居于此,意尤新奇,盖桃源本楚地也。”清人李光地《榕村诗选》卷二云:“公意谓古之隐者,于此避地,遂长子孙,至于历年代而与世不相闻耳,不以为神仙异境也。”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云:“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固不必言矣。然此题咏者,唐、宋诸贤略有不同。右丞及韩文公、刘宾客之作则直谓成仙,而苏文忠之论则以为是其子孙,非即避秦之人至晋尚在也。此说似近理。……王荆公诗亦如苏说。”清人王先谦《读吴愙斋尚书桃源记书后》云:“《桃花源》章,自陶靖节之记,至唐,乃仙之。……余谓靖节作记,但言往来种作,男女衣着如外人,设酒杀鸡,作食饷客,无殊异世俗事,不当以为鬼物。东坡言渔人所见,乃避秦人之子孙。”
一些论者还提到了神仙说产生的原因,析而言之有三。其一,神仙说的产生与唐代道风之盛行不无关系。清人郑文焯批《陶集郑批录》云:“陶公是记,得之武陵渔者所说,亦未尝一字着神仙家言。特唐人慕道,故附会其事,亦仁者见仁之义,奚以辩为?”其二,神仙说与武陵桃花观(被认为是陶渊明所记桃花源所在之地)的一些传说有关。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六引唐人康骈曰:“渊明所记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观即是其处。自晋、宋来,由此上升者六人,山十里皆无杂禽,惟二鸟往来观中,未尝有增损。每有贵客来,鸟辄先鸣庭间,人率以为占。”清人方堃《桃源避秦辨》云:“渊明花源一《记》,宋苏子瞻、王十朋、胡明仲,明粤东叶氏诸公论之详矣,而世犹疑仙疑幻,何哉?盖因唐瞿童有秦人棋子之说,后之人一唱百和,遂成荒唐之论,而皆借口于渊明之《记》,此不可不辩也。渊明《记》中无仙字,诗称贤者避其世’,明纪贤而非纪仙。”其三,神仙说在文本根据上更多地关联于《桃花源诗》而非《桃花源记》。如上引吴子良之语,就是认为对《桃花源诗》中“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一句的误解是导致以桃花源为神仙所居之地的看法的关键因素。
不过,王安石、苏轼提出的隐居说虽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在后来的议论中,苏轼在韩愈的激发下所提出的实有说则不乏批评者。这些批评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往往并不直接反对苏轼以桃花源为实有其地的看法,而是认为苏轼对《桃花源记并诗》中某些文字过分拘泥的理解导致他提出了实有说,而桃花源是否实有其地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理由是,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并诗》,其主旨在于有所寓意,是否纪实则是次要的。于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批评者在批评的同时往往着意指出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并诗》的寓意所在。
寓意说既然留意于作为作者的陶渊明在写作《桃花源记并诗》这一作品时的意图,那么,其自然的思路就是从作为作者的陶渊明在其实际生活和全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品出发来理解《桃花源记并诗》。由这种批评实有说的角度而提出的寓意说主要有两个版本,代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个是耻事二姓说,其思路是从陶渊明的生活遭际去探寻《桃花源记并诗》的寓意所在。明确首发此论的是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云: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诋,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
其后附论者亦多,如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云:“此愤宋之说也。事在太元中,计太元时晋尚盛,元亮此作,当属晋衰裕横之日,借往事以抒新恨耳。观其记曰‘后遂无问津者’,足知为追述之作。观其诗曰‘高举寻吾契’,盖以避宋之怀匹避秦也。避秦有地,避宋无地,奈之何哉?篇内曰‘无论魏晋’,而况宋乎?曰‘皆叹惋’,悲革运之易也。曰‘不足为外人道’,叹知避之难也。渔人事或以为神仙,东坡以为隐者子孙,此俱不必辨,元亮之意总在寄托,不属炫异。”清人孙人龙云:“此乃寓意于刘裕,故托之秦以为喻。”清《题桃花源诗碑并序》云:“渊明《桃花源记》,解者纷纷,率多附会。惟不仕伪宋一说,深得靖节本怀。按陶诗全集,但书甲子,而此记首书晋年号;其诗又云‘虽无纪历志’,则不屑臣宋之意显然。况篇末引刘子骥自况,而以‘高尚’称之,其志愈见矣。
以“耻事二姓”为陶渊明的整体思想定位,其来有自。洪迈所引沈约之言即其滥觞。洪迈所引胡宏《桃源行》诗句中,“先生高步窘末代”之“末代”当指晋之末代,若“雅志不肯为秦民”是指陶渊明不肯为刘宋之民,则胡宏此诗即为“耻事二姓说”张本。由此亦可看到,认定陶渊明以“避秦”寓意“避宋”,是此说诠释上的关键所在。又葛立方特别聚焦于《读史述》之《夷齐》、《箕子》与《鲁二儒》等篇以阐发耻事二姓说。《韵语阳秋》卷五云:“世人论渊明自永初以后,不称年号,只称甲子,与思悦所论不同。观渊明《读史九章》,其间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齐》、《箕子》、《鲁二儒》三篇。《夷齐》曰:‘天人革命,绝景穷居,正风美俗,爰感懦夫。’《箕子》曰:‘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鲁二儒》曰:‘易代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贞夫。’由是观之,则渊明委身穷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邪?”而朱子以“逸民”论定陶渊明,表明其亦可能赞同耻事二姓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