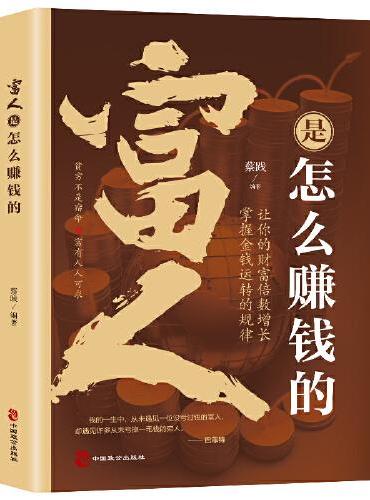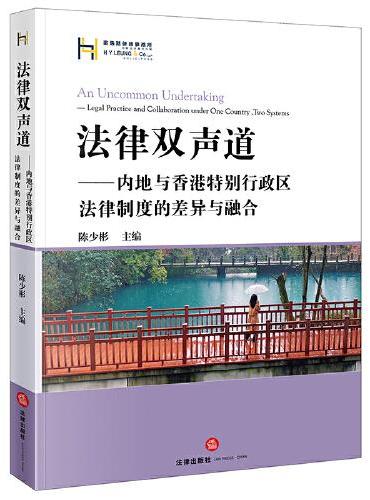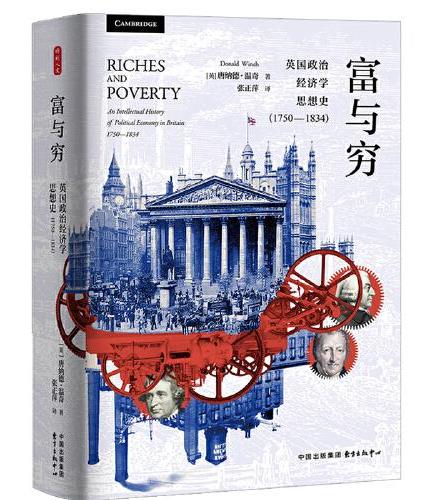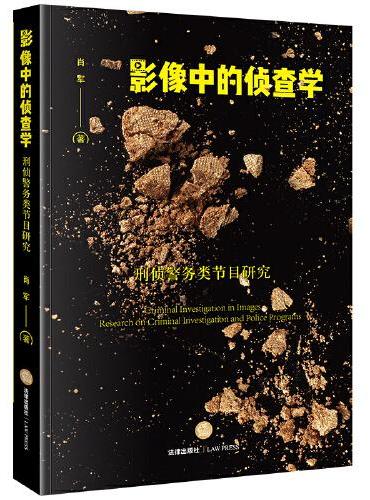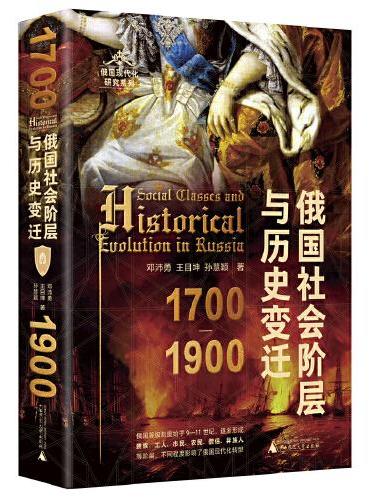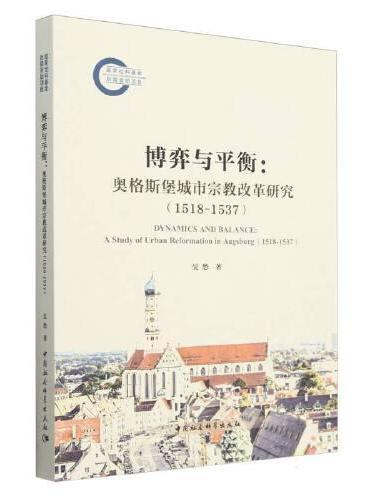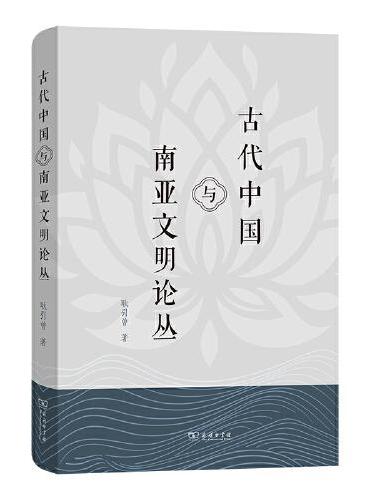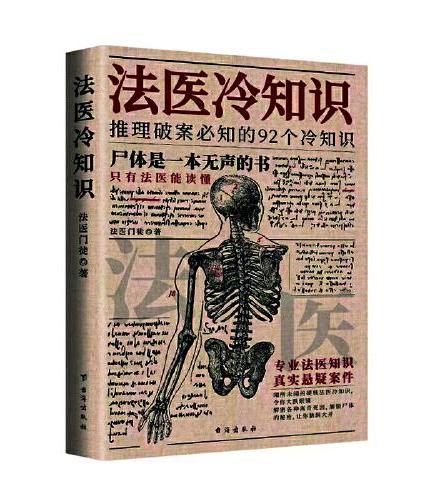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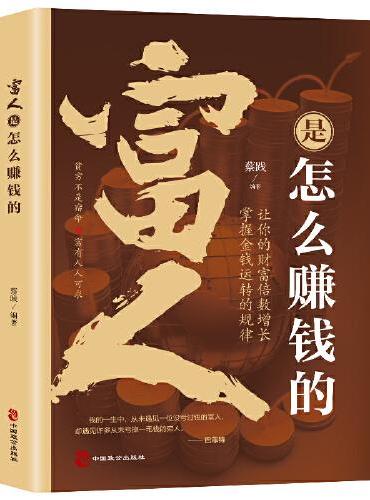
《
富人是怎么赚钱的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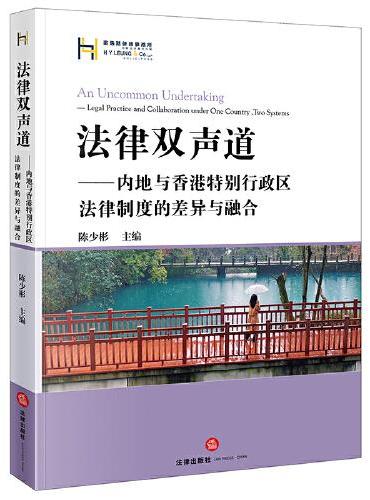
《
法律双声道: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的差异与融合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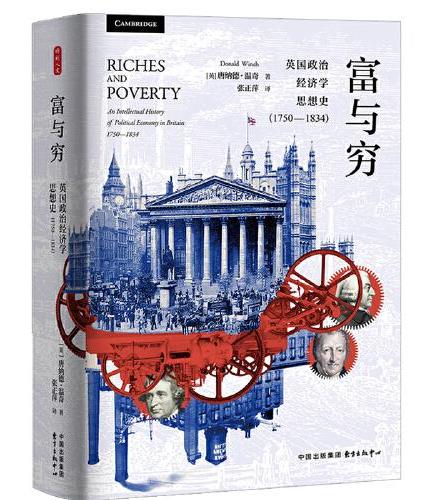
《
时刻人文·富与穷: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750—1834)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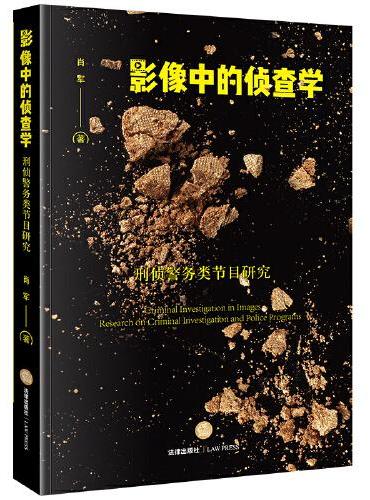
《
影像中的侦查学:刑侦警务类节目研究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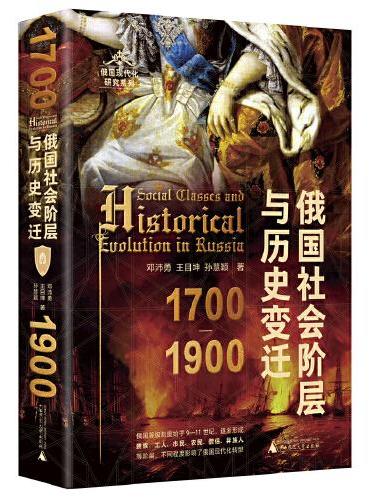
《
俄国社会阶层与历史变迁(1700—1900)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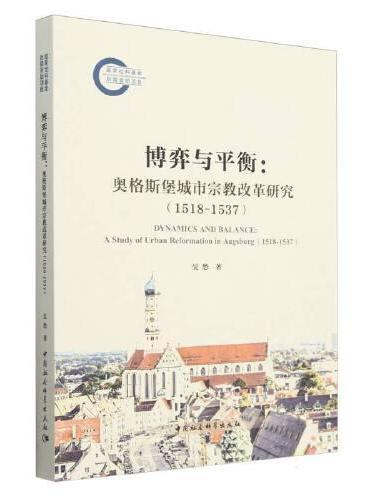
《
博弈与平衡:奥格斯堡城市宗教改革研究(1518-1537)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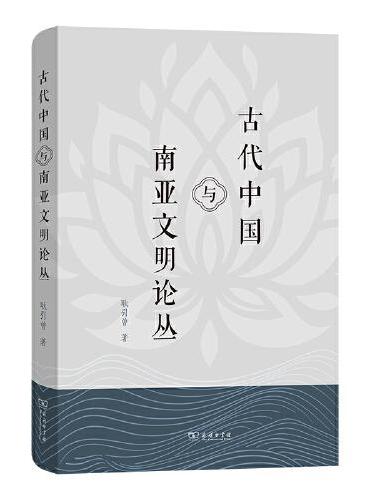
《
古代中国与南亚文明论丛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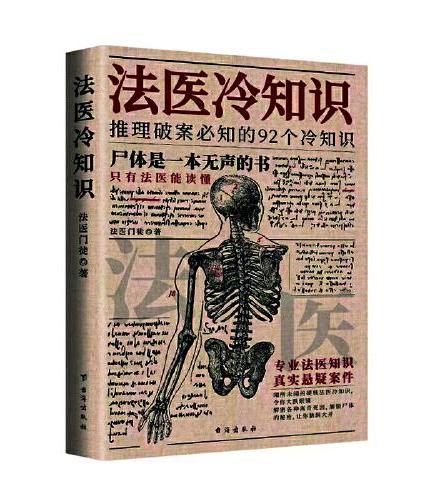
《
法医冷知识——尸体是一本无声的书,推理破案必知的92个冷知识 法医门徒 著
》
售價:NT$
305.0
|
| 編輯推薦: |
? 在短期主义盛行的当下,洞悉历史学发展的向长时段叙事回归的大趋势,呼吁回归大历史和深度史。
? 引发关于数字化时代史学及人文科学的作用的辩论,鼓励史学家打破一个世纪以来的种种心灵枷锁,重新关注长时段的大问题。
? 思想深刻、论证缜密、研究深入,对当代历史编纂学发起振奋人心的挑战!
|
| 內容簡介: |
|
史学家该如何向当权者讲述真理?这一点为何至关重要?就规划未来而言,为什么500年的视野要优于5个月或者5年?为何历史——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对理解造成当今社会种种矛盾的多重过去如此不可或缺?撰写《历史学宣言》一书的目的就是向史学家及任何有感历史在当今社会该如何发挥作用的读者吹响战斗的号角。著名史学家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经历了数十载术有专攻的专业发展之后,深刻洞悉了史学近年来出现的向长时段叙事回归的大趋势。在著者看来,这种大趋势对未来的史学学术及史学向公众的传播而言至关重要。本书观点鲜明、论证缜密,对人们论辩和思考数字化时代史学及众多人文学科所能发挥的作用颇有裨益,其受益者包括决策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以及普通听众、观众、读者、学生和教师等。
|
| 關於作者: |
乔?古尔迪
美国历史学家,埃默里大学定量方法教授。著有《通往权力之路:英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史》(2012)。
大卫?阿米蒂奇
英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英帝国的意识形态根源》(2000)、《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2013)、《弥尔顿与共和主义》(合编,1995)、《博林布鲁克政论集》(编辑,1997)、《史学、文学和理论著作中的英国政治思想,1500—1800》(合编,2006)、《莎士比亚与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合编,2009 )等。
|
| 目錄:
|
总序
推荐语
中文版序
前言
导论 人文学科的篝火
第一章 后顾前瞻:长时段的兴起
第二章 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
第三章 长短论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气候变迁、公共治理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第四章 大问题、大数据
结论 史学的大众前景
索引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中文版推荐序
“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宣言》的开篇好像是模仿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但是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目的不是政治宣传与革命鼓动,他们的作品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诉求之表达,而是一本充满激情和挑战性的历史编纂学专著。两位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近年来通过不同的讲堂、讨论班以及与众多同行的讨论,最终写成了这本精炼而深刻的小书。书稿完成之后,他们决定仿效一些数学家的做法,把全文连同目录和索引一道完整地发布到互联网上,以期引起更多学界人士对历史学的未来以及历史学家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等议题的关注。2014年10月3日,《历史学宣言》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上网,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部先发布电子版再付梓的学术专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推介广告中写道:
史学家该如何向当权者讲述真理?这一点为何至关重要?就规划未来而言,为什么500年的视野要优于5个月或者5年?为何历史——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对理解造成当今社会种种矛盾的多重过去如此不可或缺?撰写《历史学宣言》一书的目的就是向史学家及任何有感历史在当今社会该如何发挥作用的读者吹响战斗的号角。著名史学家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经历了数十载术有专攻的专业发展之后,深刻洞悉了史学近年来出现的向长时段叙事回归的大趋势。在著者看来,这种大趋势对未来的史学学术及史学向公众的传播而言至关重要。本书观点鲜明、论证缜密,对人们论辩和思考数字化时代史学及众多人文学科所能发挥的作用颇有裨益,其受益者包括决策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以及普通听众、观众、读者、学生和教师等。
应该说,出版社与作者的宣传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历史学宣言》自出版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该书网上发布还不到三个星期,2014年10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就组织了一场广播辩论会,三位到场的嘉宾包括作者之一的阿米蒂奇,以及一位身为保守党下院议员的历史学家和一位“历史与政策”组织的负责人。后两人并不完全赞同《历史学宣言》中的观点,特别是书中对经济学家过多影响政府而导致当今政策短视的指控,以及对有关“长时段”和“短时代”优劣的评价等。
不过学界的多数回应是积极与肯定的。巴黎政治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令人耳目一新的书”,“呼吁以更全球化的、长时段的和跨学科的方法探索包括气候变迁、不平等根源和资本主义的未来等大问题”。纽约大学的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说:“这本精心撰写、思想深刻、研究深入的书,是对当代历史编纂学令人振奋的挑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评论道:“阿米蒂奇和古尔迪通过《历史学宣言》发出了响亮的呼声,不仅要求对过去有更多的认识,而且集中于对公共知识自身历史的深刻而广泛的理解。”弗吉尼亚大学的贝瑟尼?诺维斯基(Bethany Nowviskie)赞道:“大问题遇到大数据,这是一个在公共领域作长时段思考的令人叹服的案例。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不仅为历史学科开辟了一条新航路,而且向公众说明了跨学科历史的用途。我深信,大历史的回归在理论上是充分的,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政治上更是势在必行。”
通观全书,其核心思想是批评当前史学界的短视与碎片化倾向,呼唤长时段历史(long-term history)的回归,号召史学家在政治决策与公共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作者在书中警告道,历史学科正在逐渐失去对普通公众的吸引力,它往昔在政治决策者那里的优越位置正被其他学科所代替,但后者的立场往往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满足当权者任期需要为重要参照。他们特别指出,以美国为例,至少在气候、世界政府和不平等这三个公众议题上,有关未来发展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那些将人的本质看作静态的经济学家手里。
两位作者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学是人类文明创造出的最富韧性、最为持久的组织之一;而20 世纪问世的大公司、大企业,平均半衰期只不过75年。长期以来,大学中的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是向后代灌输“人之为人”这一教育信条的最基本的工具。作者说,至少在过去的500 年里,历史学家始终是人群中最敢于向当权者讲述真理的,他们善于观察长时段的社会变迁,勇于向公众揭露腐败行为,因此有能力把历史过程置于更大的背景下加以拷问。
根据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分析,长时段历史的消退产生了两个互相关联的后果:其一是无论在公共机构还是在私人企业那里,都缺乏从整体上对国家与社会未来负责的可持续计划;其二是对眼下正在削弱的大学,特别是其中人文学科的生存带来更多的伤害。关于前一点,只要看看美国的金融政策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就一目了然了。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指出,在这个争斗片刻不停和迅速获得回报的压力无时不在的时代,政治决策和市场战略乐于听命于短视的建言。对于后一点,他们补充道,随着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兴起,诸如物理学、经济学和神经科学等显学(star disciplines)将会逐渐统治整个知识王国,而这一过程也会随着近期出现在许多国家科研教育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而加速。最终,那种通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经验的整理与追索,去发现人类“存在之由”(raison d’être)的伟大批判传统正在迅速灭绝。
除了分析与警告,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也提出了一些正面的建议。他们号召历史学家利用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契机,拥抱计量史学(cliometrics)的复兴。书中介绍了一些历史学家创造的研究工具,包括作者之一发明的“纸机”(Paper Machines)、多种功能强大的词频统计器、图示软件、解密引擎以及超大型的资料库。这些新型的工具大大提升了大数据的精准解析,其功效是以往的历史学家不可想象的。作者认为,这种新的可用于思考历史与未来的数据分析正迅速取代老式的经济学分析,未来的信息科学家、环保学家,甚至金融分析师,一旦试图放眼未来,他们必将首先考察其应用的数据来自何方,那时的历史学家必将肩负愈来愈重要的社会使命,历史学也将被当作一种借以反思当前和前瞻未来的有力工具。
概言之,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呼吁当代人珍视历史学的人文价值,强调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风骨。《历史学宣言》的最终目标是重新唤回公众对历史的兴趣,鼓励历史学家积极介入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以期迎来一个光明的“历史的公共未来”(the public future of the past)。在全书最后,作者再次仿效《共产党宣言》,煽情地发出“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Historians of the world,unite)的呼吁。
《历史学宣言》的问世与西方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大历史”(big history)思潮不无关系。推动这一思潮贡献最大的人,是现在供职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其代表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2004)将人类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视为同一时间维度下的整体,其开端是大约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2010年,国际大历史学会宣告成立,受到比尔?盖茨支持的全球大历史研究所和旨在向中小学生传授“大历史”知识的网络教育计划相继出台。延续克里斯蒂安思路的著作也纷纷问世,如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的《进化的史诗:宇宙的七个阶段》(2006)、辛西娅?布朗(Cynthia Brown)的《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2007)、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2010),以及克里斯蒂安本人的《极简人类史》(2007)等。
《历史学宣言》在叙述“长时段回归”的时候,也提到了这种被作者称为“深度历史”(deep history)和“大历史”的研究,但是他们的“长时段”主要限于人类活动的历史,特别是文明诞生以来的历史。两位作者特别推崇年鉴学派提倡的“长时段甚至超长时段的历史”(lhistoire de longue,meme de très longue durée),也就是以数世纪或数千年为尺度的历史叙事。这一点与晚近兴起的“大历史”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国外对《历史学宣言》的一些批评集中在作者对“长时段”的强调上,不过在我看来,阿米蒂奇与古尔迪争辩的要点不是“长与短”的优劣,而是呼吁当代历史学家要有宽阔的视野和考察大问题的雄心。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宽阔视野和追索大问题之雄心的学者,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超出了“中国”和“科学技术”的范畴。作为国际跨文化研究的先驱,李约瑟的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理解,而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与技术成就正是抵达这一目标的理想引桥。
由此想到《历史学宣言》谈到的“反事实思维”。作者声言,这是历史学家熟悉并经常应用的一种拷问方法。书中写道:“假如我们抛弃了蒸汽机,我们是否就能够沿着气候变迁之路向回转呢?仅靠风力舰船和高效铁路运输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能支撑这个世界吗?我们还要思考一下:再回到牛耕时代是否就可以发展成可持续的农业生态呢?假如回到过去便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那我们究竟要往回走多远呢?”读罢这段话,不禁想起那些以“未曾发生的事对历史学无意义”来质疑“李约瑟问题”的做法,然而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并不认为李约瑟的“why not”式提问是一个类似“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的无聊设问,他们声称:“历史思维中的因果关系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历史责任问题都是反事实思维的结果。在可持续发展时代,每一个人都须从事反事实思维,因为这种形式的历史思维对试图建造一种不会带来气候变化的拖拉机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对试图设计可持续发展世界农耕技术的遗传学家,均可谓不可或缺。”
其实有关这一问题可能遭致的误解,李约瑟本人早有意识。他在1969年出版的《大滴定》的导言中写道:“我将这些文章集合成书,希望能对比较知识社会学中这个伟大而悖谬的主题做出阶段性说明。”它的“伟大”出自宽阔与长时段的视野;它的“悖谬”在于丰富而深邃的内涵--近代社会的起源、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以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普适性之间的张力,这些都是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中富有挑战性的大问题。“李约瑟问题”也是一个高度凝炼的启发式论纲,可以借此展开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宏大叙事。
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在《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中写道:“我们承担不起背弃历史教训的骂名。两个伟大的古代文明,中国和希腊,各自进行了意义深远、发人深省的研究。今天无论是在我们自身的智力操练当中,还是在政治、道德和教育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中,我们仍能从两个伟大文明的古代研究中深受教益。”李约瑟正是站在长时段大历史的制高点上,以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为智力操练的对象,提出了意义深远而发人深省的大问题。
《历史学宣言》对于当代中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在经济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生态与文化建设的滞后、政治口号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贪腐官员与百姓利益的冲突、行业及地区差距的拉大,种种潜伏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并葬送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矛盾,不应该仅仅听从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长时段大历史的经验需要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
近代科学、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相关的历史变故都没有发生在中国本土,到了晚清“西学东渐”大潮高涨的时代,西方已经走过了300多年的路程,而对理性与价值关系的追索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如果对这些历史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了解,弘扬科学精神与提倡科学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与科学精神截然对立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思潮不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一个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千年痼疾。对权威的怀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相对缺位的,它与反智论的肆虐相得益彰,由此提供了群氓和奴才生长的土壤,对国民精神造成难以治愈的创伤。借助长时段大历史,我们不仅能够通过弘扬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而且可以发现自己精神方面的缺失以利于治愈和康复。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编纂学传统,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史家的最高境界。《史记》还开创了将天文、历法、地理、音律、计量学、水利工程和经济史料包括在官修正史中的传统,这与当代“大历史”的提倡者们将历史学的对象从单纯研究人际关系扩充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谓异曲同工。大气磅礴的《太史公自序》可以说是公元前2世纪的一篇《历史学宣言》,该文首先追溯史家源流,从“昔在颛顼”开始直到“谈为太史公”;又述及出身、家学与游学经历,“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气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复记先父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旨,最为传神的是司马谈临危执子之手而泣,连呼“是命也夫,命也夫”,及至最后作者发出宏愿:“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历史学家的使命感表达得如此淋漓酣畅,放眼世界,在司马迁之前或之后相当长的年代里,还找不到第二个史家能写出如此高贵与庄严的文字。可以说,司马迁为中国历史编纂学建立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与读书人的精神生活中,历史学这门知识构成最坚实的内核。“六经皆史”,此之谓也。
近来在新式媒体上看到,有人断言历史学将成为中国当代的显学。这不是因为各种古装片、宫廷戏的大行其道,也不是“大国崛起”之类的正片引起人们对全球史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公众强烈渴望了解历史的真相,特别是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与曲折之后,一个正在追求伟大复兴的民族面临重大道路选择的时刻。我真心希望这一断言成真,《历史学宣言》的呼唤在中国得到更热烈的回应,司马迁的雄心与李约瑟的视野能得到国人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本书的译者孙岳硕士阶段主修英美文学,博士期间攻读历史,现在供职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历史学院全球史中心,多年来一直关注融合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大历史”。他还是上面提到的国际大历史学会理事,同时是刘新成教授领导下的全球史中心的骨干成员,该中心编辑出版的《全球史评论》系列是国内从事长时段大历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孙岳亦曾翻译过本书作者之一阿米蒂奇的另一本书《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颇得作者赞许。由他来翻译《历史学宣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祝愿《历史学宣言》在中国获得更多的读者与关注。
刘钝
|
|